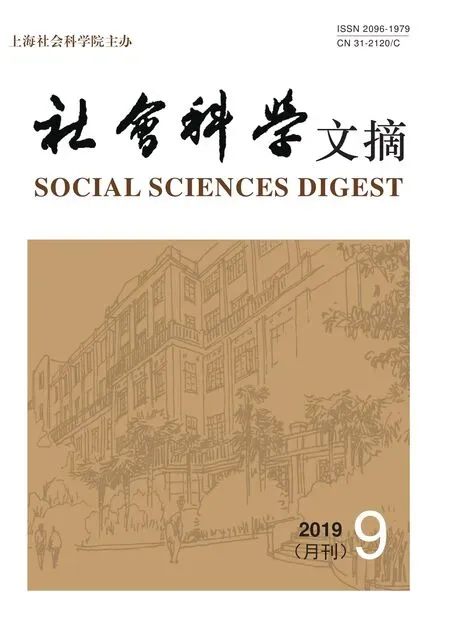西方文論關鍵詞:后人文主義
文/陳世丹
后人文主義的提出
后人文主義思想是在對傳統人文主義思想的反思和批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后人類”的字面意義是指存在于超越人類狀態的個人或實體(entity)。這一概念提出了倫理學與正義、語言與跨物種交流、社會制度和跨學科知識等問題。在批評理論中,后人類是一個思索性的存在,它代表或追求對人類的重新設想。在現代高新技術盛行的背景之下,后人文主義首先意味著一種試圖克服人類身體有限性的超人形象,這也是后人類給予人最直觀的印象。后人文主義以人類作為自己批評的對象,它批判地質疑人文主義。
后人類可以被定義為人類和智能技術越來越互相纏繞的狀況。更具體地說,后人類是一種人類設計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那些信仰后人類的人所說的信息模式使我們成為所是之物,這種模式的開放將把對人性關注的焦點從我們的外觀轉移到那些信息模式。這樣,關注的焦點將會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形式上:人性將被根據一個物種如何起作用來定義,換句話說,根據它是否像人那樣加工信息——即它是否是有感情的、感情移入的、智慧的,等等——而不是根據它的長相來定義。
后人文主義派生于后人類,因為后者代表人文主義主體的死亡。構成主體的品質取決于作為一種特殊的獨立實體的特權地位,這種特殊的獨立存在擁有使它在宇宙中例外的獨特性,例如對于所有其他生物而言它具有獨特的優秀的智力,或擁有一種獲得自由的自然權利,而這種自由是其他動物所不能同樣獲得的。如果焦點是在所有智能系統本質的信息上面,物質和身體本質僅僅是攜帶生命的全部重要信息的基板,那么在人類與智能機器或任何其他種類的智能系統,例如動物、外星人或一些構成智能存在的物質,例如一群蜜蜂、某一行星的生態層、一組演算法、一組細胞自動機或一群細胞(畢竟它們就是人類的身體)之間,不存在有意義的差異。換句話說,人類例外主義死了。我們面對一個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自己僅僅是與其他系統結合的系統。這就是人文主義的主體之死,它導致了如何考慮后人文主義主體地位困境的問題,這也是“后人文主義”所應對的學術上的當務之急。
后人文主義的發展
后人文主義的根源可追溯到后現代主義的第一次浪潮,但是“后人類轉向”完全是由20世紀90年代女權主義理論家所創造的。它發生在文學批評領域,所以后來被界定為“批判性后人文主義”。同時,文化研究也接受了它,提出了一個被稱為“文化后人文主義”的看法。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批判性后人文主義和文化后人文主義發展成為一種更聚焦在哲學上的探究,如今被稱為哲學后人文主義(philosophical post-humanism),它是一種綜合的嘗試,通過一種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文主義假設的新認識,重新進入哲學研究的每一個領域。后人文主義經常被解釋為后人類主義和后人類中心主義(postanthropocentrism),因為它出現在人類概念之后和人文主義歷史之后,而這兩者都是建立在分等級的社會建構和以人為中心的假設基礎之上的。物種歧視(speciesism)變成后人類批評方法整體構成所必需的一個方面。不過,后人類對人類首位的克服不應該被其他種類的首位(例如機器的首位)所替代。后人文主義可被視為一種后排他主義(post-exclusionism),即反對人的任性和自以為是的狀態:一種調解的經驗哲學,它以其最寬廣的意義提供了一種存在的和諧。后人文主義并不使用任何正面的二元論或對立面,通過解構的后現代實踐使任何本體論的對立非神秘化。
后人文主義是一個后現代的明確特征。被后人文主義置于危險中的不僅是傳統西方話語的中心,這一中心已經被其外圍(例如女權主義理論、批判性種族理論、酷兒理論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等)從根本上解構了。后人文主義是一種后中心化,在某種意義上它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心,而是認為有許多特殊的興趣中心;它既以其霸權的模式又以其抵抗的模式解散單數形式中心的中心性。后人文主義承認多種興趣中心;但這些興趣中心是不確定的、游動的、短暫的,其視角必須是多元的、多層的,盡可能是綜合的和包容的。
哲學后人文主義的出現
到20世紀90年代末,批判性后人文主義和文化后人文主義的發展成為更多聚焦在哲學上的探究,如今被稱為哲學后人文主義,它試圖通過一種新獲得的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文主義假定(assumption)的認識,重新進入哲學研究的每一個領域。美國著名的后現代主義文論家伊哈布·哈桑曾闡明,當人文主義把自己變成人們無助地稱為后人文主義的某事物時,人文主義可能就行將結束了。這種觀點在時間上早于后人文主義潮流的大多數觀點,后人文主義潮流是在20世紀晚期以多樣化的但互補的思想和實踐領域內形成的。例如,哈桑的理論著作清楚地提出了后工業社會中的后現代性。后人文主義超越后現代主義研究,被各種各樣的文化理論家展開和利用,經常作為對人文主義和啟蒙思想中成問題的形而上學的內在假定的反應。
后人文主義通過把人類降回到許多自然物種之一而與經典人文主義不同,從而拒絕了基于以人類為中心統治的任何要求。根據后人文主義,人類沒有破壞自然或以先天道德理由使自己高于自然的固有權利。先前被視為世界的規定性方面的人類知識也被降至很少控制性的地位。人類權利、動物權利與后人類權利都存在于一個范圍。人類智能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是眾所公認的,但它并不意味著拋棄人文主義的理性傳統。
后人類話語的支持者們認為,創新進步和新興技術勝過了笛卡爾等與啟蒙運動時期哲學有關系的思想家們提出的人類傳統模式。后人文主義話語追求重新界定現代哲學對人類認識的邊界。后人文主義代表一種超越當代社會邊界演化的思想演化,被放在后現代語境中追求真理的基礎之上。這樣一來,它就拋棄了其早先要建立人類學共性的嘗試,那種人類學共性被灌輸了以人類為中心的假定。
哲學后人文主義的核心觀念
后人文主義對人文主義挑戰的第一個關鍵點是作為人文主義理論基石的“人”的概念。因為事實上,至少自17世紀以來,所謂的人文主義不得不依靠某種從宗教、科學和政治借來的“人”的概念。后人文主義在解構了傳統人文主義賦予人的一系列特權,例如優先權、中心性、絕對性、超越性、自主權等之后,宣告被傳統人文主義奉為神圣的“人”死了。依據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的話,上帝已死的時代已被人已死的時代所取代;法國人類學家和哲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公開宣布,我們必須拋棄主體(人)這個令人討厭的寵兒,因為它占領哲學舞臺太久了。列維-斯特勞斯指出薩特發展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主觀性哲學。實際上,自笛卡爾以來,法國哲學一直是被主體的概念所控制。如果我們想要獲得其他真理,我們必須選擇另一種觀點,一種不同的觀點。于是,后人文主義就用下列方法圍剿作為中心而存在的“人”。
首先,后人文主義向人的中心性和優越性發難。我們知道,各式各樣的哲學人文主義都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它們假定的理論前提,都抬高人類,認為人類至高無上,而且將主體置于現實和歷史的中心。根據后人文主義的觀點,這是一種自大狂(megalomania),一種渴望將人類自己變成上帝的征兆。理查德·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在其《人文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Humanism,1981)一書中認為,所謂人文主義的終結就是自大狂傳統的終結。人類的這一特權被認為是唯心主義的特權。在后人文主義者看來,人文主義所尊敬的主體性并非根深蒂固地隱藏在表面作用下被心理學、社會學等科學所研究的哲學現實。它是一種不需要解釋的深層結構或深刻理性的表面現象。后人文主義將“去中心”作為武器,使自我非中心化。作為中心的傳統自我被當作幻覺、信仰的產物而被拋棄。后人文主義的結論就是“我們是非統一的、多元的存在”。
關于對人的中心性的抨擊,后人文主義進一步破壞了人的優先權和自主權。后結構主義思想家福柯用考古學方法對“人”進行了考古學研究,其研究成果震驚世界。根據他的分析,值得尊敬的“人”本身的西方概念不是永恒的、無限的存在,而是一種特殊時代和特殊知識的有條件的產物。薩特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而且它肯定人的存在性,所以存在主義就是我們時代的真正哲學。對此,福柯的反應是所謂的人的概念僅僅是特定歷史時期的一種認識論的建構。不僅人是有限的,而且所謂人的自主權和創造性也只是一種“神話”,人并非人文主義者以為的能動的創造者,而是被想象出來的,其存在是“現代思想所構成的”。我們總是習慣性地以為在某種意義上個人或人類主體是首位的,其實個人或人類主體只不過是無個性特征的語言或思想體系的表面結果。因此,對后人文主義者而言,主體就被放逐了、被邊緣化了。最初在傳統人文主義中被認為是終極根源和構成主義的人被變成了后期生成的、派生的和建構的事物。
后人文主義另一重要的理論內容是對人性論、不變的人性和人本質的討伐。后人文主義者認為,不存在普遍的、一般的和不變的人類本性和人類本質,傳統人文主義的“人類本性”和“人類本質”的概念應當拋棄,因為人并非人文主義以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理性和一種獨立存在的事物,而是歷史的產物,是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產物。根據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激進的實證主義觀點,人們不再對解釋的動機感興趣,而只重視行動。人們不再設法查明不同的人實際上是否是不同形式的相同的個人,而只認角色為唯一可以被認識的關于個體的真理。
人文主義認定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和無限的認知能力,人的思想能夠絕對地認識關于一切的真理。后人文主義用懷疑論顛覆了人文主義在思維和存在關系上的自信。在此基礎上,后人文主義進一步推翻了人文主義的人類進步的概念。這種人類自信主要表現在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古老的格言上面。后人文主義挑戰這一信仰,其挑戰首先從尺度開始。根據伊哈布·哈桑的分析,“尺度的理想模式是封閉在真空里的計算器,但這一用來計算長度的儀表也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一直是通過早期的白金(platinum)到銥(iridium)到光譜(spectrum)、光的波長(light wavelength),再到86氪(krypton)桔紅線(the orange line)”而反映的。其特征是越來越非實體化、非物質化。然后,哈桑以馬歇爾·杜尚(Marcel Duchamp)的畫《罐裝機遇》(Canned Chance)為例,又解釋說關于同一理想長度我們可以有三種觀點。既然所謂的客觀的準確的尺度總是變化的、各種各樣的,那么作為“尺度”的人必定不可能是絕對的。他的結論是我們生活在作為尺度的人開始變化的門檻上。那種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從絕對向相對轉變。
在后人文主義者看來,人類只能相對地認識事物,不可能絕對地掌握事物。確實存在我們不能講述的事物,它們自己顯示自身,可稱為神秘的事物。人并非是傳統人文主義以為的那樣無所不能,因為一切都不是特定的,一切都不是已知的。作為后人文主義的理論先驅,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曾談到存在一種不可避免的未加思考的(unthought)事物。傳統的人文主義錯誤地理解了未加思考的事物,或視其為客體的抽象形式或視其為主體的抽象形式。換言之,所有的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家們通過人為地把復雜的、多重的事物還原為簡單的、單一的性質而犯了一個過分簡單化的錯誤。海德格爾的“精神”(spirit)、尼采(Freidrich Nietzsche)的“權力意志”(power will)、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力比多(libido性沖動)”、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都與此類似——把復雜的、多重的事物還原為簡單的、單一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人文主義是一種唯心主義。后人文主義把思想看作一種進一步產生復雜性的事物,并且認為不存在任何不證自明的思想。知識不再是笛卡爾式的個人考查思想內容的確定性結果,而是社會地產生的。笛卡爾的“我思”不是認識的前提,而是認識的結果,而且是唯心主義的簡單化認識的結果。此外,笛卡爾式的內省、自省、自我研究方法將不再起作用,因為對我們自己而言,我們“不再是自我透明的”。相反,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知道我們將如何認識和我們將認識什么。
在后人文主義者看來,人文主義還有一個盲目樂觀主義的謬誤,其理論基礎是把人置于上帝的位置,并把人類自由的進步等同于人類理性的進步。這種盲目樂觀主義無法回答后人文主義提出的下列問題:人類有文明,可是為什么他們日益焦慮和孤獨?人類有科學,可是為什么他們不斷地感到困惑?人類不斷獲得豐富的知識,可是為什么他們覺得自由離他們更加遙遠?與傳統人文主義相比,后人文主義表現出一種悲觀主義,這顯然是對人文主義的廉價樂觀主義的否定。這種否定是有深刻的歷史內容的。與此否定相聯系的是對進步概念的幻滅。人文主義思想家們所曾經講述的各種各樣關于“人類不斷進步的故事”現在僅僅被后人文主義視為一種“虛構”,“一種人為的虛構”。
總之,后人文主義是一種時代的哲學、一種當代西方正在進行的具有廣闊影響的哲學文化思想。它既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反思,也是對后工業社會的回應。它既是一種對現實的哲學反思,也是對哲學本身的自我反省。從哲學的視角看,后人文主義的主要貢獻是使我們重新認識人在世界和現實中的地位,重新認識曾自以為是“萬物的尺度”和“中心”的人,重新認識曾經以為是清楚已知的世界。具體地說,后人文主義使曾經被認為是絕對的人的存在相對化、多元化、復雜化了,因為世界本身是相對的、多元的、復雜的。可見,后人文主義完全拋棄了唯心主義的“主體觀念”。在批判唯心主義和抽象的人類本質這一點上,后人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殊途同歸——他們都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后人文主義者所說的“人之死”是指“被主觀主義地理解了的人的死亡”。一旦人身上的各種各樣的“本質”和“特權”被剝奪,人就會被還其本來的、相對的、多元的、復雜的真實面目。與經典人文主義不同,后人文主義通過把人類降回到許多自然物種之一,從而拒絕了基于以人類為中心統治的任何要求。在明確人類權利、動物權利和后人類權利都存在于一個范圍內的認識基礎上,后人文主義形成了建構和諧社會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一)建構尊重自然、不同物種相互依存的生態社會;(二)人類必須用后現代倫理道德與政策法規指導、規范科技實踐,合理利用高科技;(三)人類要尊重和關愛非人類,平等對待智能機器人賽博格(Cyborg),建構多元物種和諧共生的后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