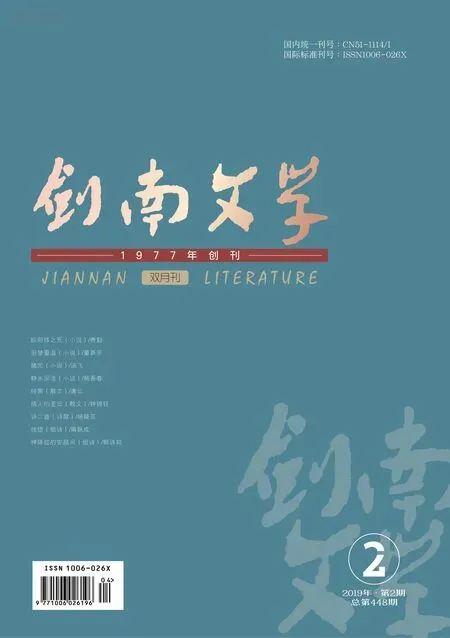經(jīng)常
□謝 云
“經(jīng)常”這個詞,很有意思。
它既可作形容詞,表“平常”“日常”,也可作副詞,表“時常”“常常”。兩者當(dāng)然有關(guān)聯(lián):“平常”“日常”都有、都在、都做的,當(dāng)然也就會“時常有”“時常在”“常常做”。漢語里,同一詞語處于不同位置,便有不同的詞性和詞義,這很正常——“正常”即是符合一般情況、規(guī)律或習(xí)慣:既是“一般”,也往往普遍;既是“規(guī)律”或“習(xí)慣”,也便可能常常出現(xiàn),或?qū)掖伟l(fā)生,或反復(fù)進(jìn)行。
從六書角度說,“常”是形聲字,從巾,尚聲。本義為“旗”。《尚書》有“紀(jì)于太常”,孔安國傳注說:“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即是說,旗上畫日繪月之類,是為“王旗”。許慎《說文解字》則云:“常,下裙也。 ”按清人段玉裁的注解,古人所穿,“上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蔽也。”衣、裳之類,最初的功用就是遮蔽,遮美或遮丑,后來才有了裝飾、美化的意味。
許、段以為“常”通“裳”,清人朱駿聲卻持反對意見。在《說文通訓(xùn)定聲》里,他說:“常裳二字,經(jīng)傳截然分開,并不通借。”但我依然傾向于許、段的說法。原因在于,“王旗”之類,并非“常用”“常見”之物,下裙卻是“常服”,需要“常穿”——因其“常”,才有引申為“規(guī)律、準(zhǔn)則”的可能。
從詞義演變來說,“常”首先是指“一般的,普通的,平常的”,其次是指“長期的,永久的,固定不變的”,然后才有“規(guī)律、準(zhǔn)則”之義,“時常、常常”之義——規(guī)律或準(zhǔn)則,總是“長期性、經(jīng)常性、永久性”的。這其實是常識,只是如我所感嘆的,很多時候,我們對“常識”是“常常不識”。
包括,對“經(jīng)常”這個詞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里的這句話,太常見,因而“常熟”得不必解釋。就像舊時把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定位于“倫常”“綱常”“五常”一樣。但是,把“常”引申為“規(guī)律、準(zhǔn)則”,或許正是自荀卿始。
“常”字的虛化,即表示“時常、經(jīng)常、常常”,古籍里似乎常見。《列子》所謂“常生常化者”,即是此義。《史記》“良因異之,常習(xí)誦之”,韓愈《馬說》里的“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都用此義。
再來說“經(jīng)”——“經(jīng)”源自古老的紡織業(yè)。這肯定是受“你耕田來我織布”的農(nóng)業(yè)文明影響。《說文解字》云:“經(jīng),織也。從糸巠聲。”顯然也是形聲字。表形的糸(mì),指織布時用梭穿織的豎紗,也指編織物的縱線。縱線也好,豎紗也罷,織布時,我們知道,經(jīng)線是不動的,只有緯線,會隨著梭子的翻飛而走動。
所以,就織布而言,“經(jīng)”是固定的標(biāo)準(zhǔn),或者說,有標(biāo)志性的意義。
織布也好,紡紗也罷,都要不斷地整理線頭。所以,整理也叫“治”。成語“治絲益棼”,即是指“理絲不找頭緒,結(jié)果越理越亂”。比喻解決問題不得其法,而使問題更加復(fù)雜。今之所謂經(jīng)商、經(jīng)營、經(jīng)天緯地,都是治理、管理之義。
“經(jīng)”與“緯”相對。唐人賈公彥《周禮·疏》說:“南北之道謂之經(jīng),東西之道謂之緯。”以經(jīng)緯定道路、斷四方,也是陳例。南北為經(jīng),東西為緯,這甚至影響到地理學(xué)上的東經(jīng)西經(jīng)、南緯北緯——顯然,這是就空間維度而言。其實,“經(jīng)”也還有時間意義上的指向,所謂的“經(jīng)由”“經(jīng)過”“經(jīng)驗”即源自于此。因此,“經(jīng)”又引申為雖時間推移而歷久不變的。
歷久不變,或者說“總是如此”,自然就成了“經(jīng)常”“恒常”“通常”,用劉勰的話說,叫“恒久之至道”,或“不刊之鴻教”(刊:改動。一個字都不能改動的偉大教導(dǎo),成語“不刊之論”,或源自于此)。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顛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永恒真理、絕對真理,而記錄這些真理的,就是我們熟悉的“經(jīng)”。
柳宗元曾謂:“經(jīng)也者,常也。”就是說,“經(jīng)”即為“常”,“常”亦為“經(jīng)”。“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既可成為標(biāo)志、標(biāo)準(zhǔn),也可視為規(guī)律、規(guī)范。而古人所謂的“經(jīng)”,道也好,儒也罷,以至五經(jīng)、六經(jīng)、十三經(jīng),都是可為思想、行為、道理規(guī)范的“經(jīng)籍”。雖然春秋有變換,世代有更迭,但這些“經(jīng)籍”,和其中承載的道理,卻歷久彌新,如日月恒在,自然也就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經(jīng)典”。
這樣的“經(jīng)典”,顯然是重要的。無論古今,無論中外——包括三藏十二部的“佛經(jīng)”,也包括基督教的《圣經(jīng)》,伊斯蘭教的《古蘭經(jīng)》。盡管它們只作用和約束于各自的信徒,但無疑是相對而絕對的“經(jīng)典”。
說到“經(jīng)典”,不由得想到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
軸心,即旋轉(zhuǎn)的中心,意指樞紐或關(guān)鍵。所謂的“軸心時代”,就是人類文明的樞紐和關(guān)鍵時期。按雅斯貝爾斯所說,是指公元前6世紀(jì)前后,在遙相隔絕的東西方主要文明區(qū)塊內(nèi),都相繼出現(xiàn)了文化和文明上的“突破”。而這所謂的突破,既指精神的覺醒,也指思想的飛躍,而且是空前絕后的——孔子、老子,優(yōu)波尼沙、佛陀,耶穌,蘇格拉底、柏拉圖……
雅斯貝爾斯說:“一個民族的中心價值大體是在這一階段定型的,而這些價值對該民族此后的發(fā)展則起著范疇的作用。”“范疇”之說,既是指那個時期人們的認(rèn)知和理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典籍,代表著人類文明和智慧的高度,同時又有著超越時空的永恒魅力,至今仍有著不可忽視的深刻影響。用學(xué)者馮天瑜的說法,那是一個創(chuàng)造了“元典”的時代——“元”,開頭的,起始的,最初的;元典,即最初的經(jīng)典,顯然,這比后來的經(jīng)典更經(jīng)典。
這樣的“元典”,既是權(quán)威的,又是典范的,既無可替代,又常讀常新。
現(xiàn)代漢語里,和“經(jīng)”字聯(lián)系最多、最緊密的,其實就是“經(jīng)常”。按柳宗元的說法,經(jīng)者,常也,經(jīng)就是常,是常言,也是常理,更是常道,是重要的,也是緊要的,更是必要的,是日常生活和行為中,必須遵守、依循和踐行的。
有意思的是,佛教本土化后,也有“常”字,取“恒久”之意,以命名“無生無滅無變易”之類的東西。而且,學(xué)者們在“解經(jīng)”時,有了更獨特的創(chuàng)見:所謂的經(jīng),就是“徑”,也就是“路”;即是說,“經(jīng)”,就是指明方向和道路的。
就此而言,“軸心時代”的那些“經(jīng)典”,不但有意無意地指引著各民族的發(fā)展方向(范疇),也指導(dǎo)著由此而降各色人等的生命道路(范本)。
我愿意相信,所謂的“經(jīng)常”,就是說,經(jīng)典總是常在的。雖然時代在不斷變遷,人世在不斷代謝,但是人性是相對恒定的,標(biāo)準(zhǔn)和規(guī)律也相對恒常。就像一條河流,河水有豐盈枯竭,河道有曲折更易,但河流,始終還是那條河流。
又仿佛,今人與古人,雖然體形、容貌有所區(qū)分,但人體內(nèi)血氣通行的道路,尤其是那些較大的“經(jīng)”(即經(jīng)脈、經(jīng)絡(luò)),卻始終未變,而且如《黃帝內(nèi)經(jīng)》所說,它們依然是“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的地方,所以需要不斷地舒筋(經(jīng)?)通絡(luò),方能始終保持人體的正常運行和流通——按古人的說法,通則不痛,痛則不通。
基于此,我愿意說,所謂 “經(jīng)常”,就是要“常常”重溫的古老“經(jīng)典”,或者說,真正的“經(jīng)”,就是要常念常讀、常記常誦的——惟其如此,才能繼往開來,溫故知新,惟其如此,才能舒筋通絡(luò),明目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