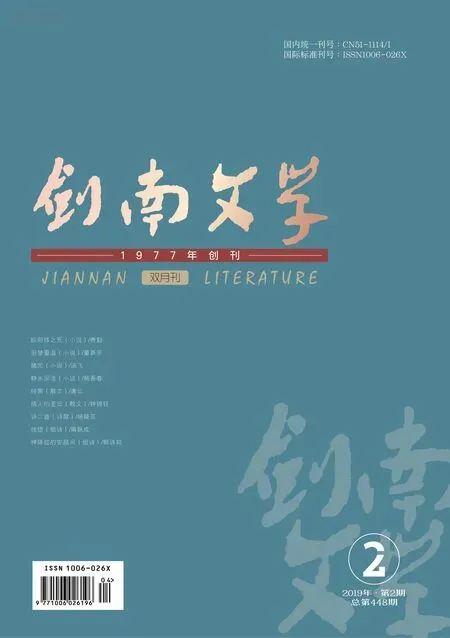靜水深流
□ 楊吾春
晚上十點半,苗東平在周大信、謝孝溫和花蕊的陪同下,走出了東街楊家祠堂里的“水煮三江沙龍”茶館,結束了周大信他們為他安排的一天的活動。
忙碌了一天的周大信和謝孝溫還要準備明天的安排,兩人告辭先走了。
花蕊也告辭要走,苗東平叫住了她。
“想不想吃夜宵?”苗東平說,“我請客。”
“你感冒還沒有完全好,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花蕊說道。
“已經基本上好了。”苗東平說。“怎么?不想給我這個面子?”他笑道。
“你這么一說,我還真有點餓了。”花蕊笑道。“難得老大有這份雅興,那小女子只好恭敬不如從命啰。”
“我就喜歡你的性格,從不虛情假意。”苗東平笑著說。“好,上我的車,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花蕊坐進了車里。苗東平發動野馬車,把自動離合推到了D檔。他松了剎車,踩下油門,向城南休閑廣場開去。
“想知道我和大信部長、孝溫秘書長下午看到你從柳淑芳家回來時的心情嗎?”花蕊按下了玻窗,讓晚風吹進了車里。
“是不是覺得特狼狽?”
“豈止是狼狽!”
“那是……?”
“心酸。”
“為什么?”
“我們在想,讓你留在三江是不是太難為你了。”
“對我沒有信心?”
“那倒不是。”花蕊說,“只是覺得你不應該受那樣的苦。”
“這么多年,我在你媽媽的愛護下養尊處優,現在也輪到我出來擔當受苦了。”
“讓我們沒想到的是,你下午一句抱怨都沒有。”
“你們都那么拼,我有什么理由抱怨。”
“現在我才知道,情懷才是戰勝一切的動力。”
“我同意。”
“今天下午,我和大信部長、孝溫秘書長突然有一種感悟。”
“什么感悟?”
“或許因為你的留下,三江會抒寫一段新的歷史。”
“別這么高估我,我的能力我知道,沒有你們三個人,我在三江可能一事無成。”
“你的堅韌已經感動了我們,我們沒有理由不為三江的未來竭盡全力。”
“謝謝你們!”
“我們要謝謝你,為我們已經快要降到冰點的心,點燃了希望。”說完,花蕊眼眶濕潤了。
“好了好了,”苗東平看著淚盈滿眶的花蕊說道,“別這么多愁善感了,還有好多事情需要我們去做。”
花蕊輕聲笑了。“是的是的。”她輕輕擦去眼眶里的淚水。“你看,我這是怎么啦!”
“這就對了,你可別學我。”苗東平看著花蕊笑道:“我的脆弱是天生的,開始跟你媽媽的時候,經常被你媽媽教訓得偷偷哭鼻子。”
“我聽媽媽說起過。”
“對了,記住下午我給你們說的兩件事了嗎?”苗東平問。
“記住了,一是通知交通局把到柳淑芳家那個鄉的那一段山路列入今年的鄉村道路改造計劃;二是安排公安檢察院馬上查一查幫你推車那個村的財務。兩件事情孝溫秘書長已經全部落實了。”
“那就好。”苗東平說,“下一步要安排市委政研室作一次村社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專題調研,請他們拿出一個適合三江實際情況的方案。蟹島村民上訪,幫我推車的村民抱怨,問題都出在村社干部身上。村社基層干部隊伍建設不能忽視,這關系到民心所向。如果民怨載道,無論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都無顏再見我們的父老鄉親。”
“好的。大信部長在分管這一塊,我把你的意思告訴他,他會去安排。”
“好的。”
“怎么?忙了一天,你沒有一點疲憊?”花蕊看著苗東平問道。
“現在我興奮著呢!”苗東平說。
“沒想到吧,”花蕊說,“在你的眼皮底下,還有這么一批有激情的三江人?”花蕊說的是他們剛剛參加的“水煮三江沙龍”夜談。
“是的,他們不僅有激情,而且很有思想。他們是真愛三江,他們那些對三江發展的建議很多值得采納。”苗東平說:“說實話,完全出乎我的預料。”
“有臥虎藏龍之感吧?”
“他們把我感染了。”
“不要忘記毛主席教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說得有道理。和他們在一起,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什么意思?”
“我為我當了四年碌碌無為的三江市長感到羞愧。”
“實事求是地講,沒有和強勢的尚官杰爭權奪利,以你的軟弱,維護了三江班子的團結,你對三江還是有貢獻的。”
“其實,我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以懦弱選擇了逃避。”
“你能意識到這一點,我和大信、孝溫為你高興。”
“我需要你們的鼓勵,讓信心不從我身上溜掉。”
“我們對你信心十足。”
“今天晚上我突然明白了,現在,不是我一個人在為三江的明天奮斗。”
“老大,沒看出來,你的進步突飛猛進啊!”
“我說真的,包括上午見到的付美江,雖然心情沉重,但是,他在那樣的環境下,還在為蟹島PX項目做貢獻,對我觸動很大。比如今天晚上參加‘水煮三江沙龍’的這些人,我看得出來,有的人生活得并不如意,甚至可能很艱辛,但是,他們沒有抱怨,沒有放棄,對三江的未來仍然那么充滿信心,真讓我感動。面對他們,我沒有理由再逃避。”
“尚官杰也常常被他們的激情所感動。”
“現在我知道,人活著是需要有情懷的。”
“一個有了情懷的人,就不會感到孤單。即使寂寞,也會寂寞得像一座花園。”
“我已經感覺到了。”
“五一之后,你的感覺會更深刻、更強烈,到那個時候,與你一同向前的,將是三江五百五十萬純樸善良的市民。”
“我開始喜歡我選擇的生活了。”
“這就是情懷帶給你的動力。”
“是不是還有即將到來的絕對權力?”
“是的,就像何新堯所說,權力會增加你的荷爾蒙。”
“現在我的氣質怎么樣?”
“與前幾天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改變那么大?”
“當然。”
“我不會變得狂妄自大,忘乎所以吧?”
“難說,絕對權力會改變一切。”
“要是我真變成那樣了,會是一個什么樣子?是不是很可怕?”
“沒有情懷,沒有朋友,沒有親情,只有孤獨和寂寞。”
“我可不愿意自己把自己打入冷宮。”
“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要是我真的變成那樣了,你得提醒我。”
“我會的,希望那時候的你,還能聽得進忠言。”
“我會讓忠言永遠不逆耳。”
“但愿如此。”
苗東平看了看車外,然后問:“剛才那個腿有點殘疾、個子小小的、留著大胡子、建議搞三江愛心詩歌節提升三江文化品位的年輕人叫什么名字?”
“文三江,他是三江小有名氣的詩人,綽號‘小號魯智深’。這人很了不起的,他自己殘疾,不靠政府,自食其力,還拿出寫詩的稿費,辦了一個雕塑小作坊,安排了十幾個殘疾人就業。他還多次發起全市愛心大行動,幫助弱勢群體。他是三江愛心志愿者協會的發起人。”
“過幾天你把他請到我辦公室來,我想和他聊聊。”
“好的,五一之后吧,我去接他。”
“我要和他交朋友。”
“你應該多交一些這樣的朋友。”
“我會的,只有他們才是最真誠的,他們能激發我的斗志。”
“他們絕不會像那些虛偽的房地產老板,想方設法和你交朋友,目的只有一個,盯著你手中的權力,貪婪地向你要地,然后虛高房價,把老百姓的錢財毫無愧色地收刮進自己的腰包。那些人,只能讓你精神頹廢、意志消沉。”
“我已經把房地產老板打入另冊了,五一之后我也會要求三江其他領導干部這樣做。”
“你做得很對。”
“我要干干凈凈做人,絕不與物欲為伍。”
“結交沒有物欲的朋友,會讓你的靈魂干凈。”
“我相信,剛才從茶館出來,我的心很空靈。”
花蕊點了點頭。
車又向前開了一段路,拐上了城南大道。
“聽說上午你在城管執法大隊發了火?”花蕊問。
“我很生氣,沒有控制住情緒。不過,我沒敢當眾發火,只是把城管局長叫到一邊批評了幾句。”
“我能理解,釣魚執法的確不可思議。”
“怎么能那樣干呢?這完全是腦殘式執法!那些開黑車的也不容易,哪有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去開黑車的?都是生活所迫。”
“包括交警罰款、城市停車費,可是政府一筆不小的收入呢。”
“在老百姓身上拔毛,被罵娘收來的錢,我看這樣的收入一分沒有更好。政府生財,也應該取之有道,絕不能把眼睛盯在老百姓身上,尤其是搞歪門邪道。”
“聽說這種方法是公安局在誘捕毒犯時發明的。”
“是嗎?這倒是第一次聽說。”
“一珍嫂子沒有給你講過?”
“沒有。她從來沒有教過我破案。再說,我對她的工作沒有興趣。”
“建議你從現在開始多向她請教。”
“對我代理市委書記有用?”
“過去州官的工作主要是審案。”
“現在已經沒有這項功能了。”
“但是,你的很多工作都涉及到執法。如果你主政的三江,處處違法執法,在執法過程中不透明,和老百姓玩躲貓貓,你將喪失民心。一個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法制、缺乏道德的地方,發展只能紙上談兵。”
“我是不是應該清除釣魚執法這個毒瘤,對當事人進行嚴肅處理?”
“還是要謹慎一點,這里面涉及到不少人的利益。你一旦動了這個利益鏈,肯定就會有人找你的麻煩。尚官杰就是路見不平,必將除之而后快,結果呢?我們面對的人際關系千絲萬縷,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你現在的位置不允許你感情用事,更不能沖動。”
“我該怎么做?”
“問你一個問題,你女兒做錯事,你會打她嗎?”
“我從來沒有打過我女兒。”
“你很愛你的女兒?”
“是的。”
“要是你氣得不得了,非打她不可怎么辦?”
“那就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嚇嚇她,出出氣算了。”
“就用這一招。”
“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是的。為了避免上海爆出釣魚執法后、政府官員不誠實表態帶來的被動局面,你要馬上叫城管局長向媒體公開承認,他們在打擊非法營運過程中確實使用了釣魚執法。而你呢,要在另外的場合高調宣布,為了維護政府誠實形象,一定要對參與釣魚執法的人進行嚴肅處理。”
“這叫‘高高舉起’。那怎么‘輕輕落下’呢?”
“把城管局長降職,調他到公安局任副局長,把參與釣魚執法的人分流到巡警大隊做民警。當然,所有人的級別和待遇不變。”
“這樣好嗎?”
“怎么不好?這叫三全其美啊。”
“我明白了,就按你的意思辦。”
野馬車繼續向前開去。過了一個紅綠燈,苗東平問花蕊:“你和大信、孝溫三個人能不能搞一個城市管理條例之類的東西,拿給人大去討論?”
“尚官杰不是已經搞了一個《三江城市管理條例》嗎?”
“我想針對釣魚執法,尤其是針對城管執法大隊的地位、作用和權限搞一個修訂方案。”
“要保留城管執法大隊嗎?”
“你們認為沒有必要保留,就建議撤銷,把城市管理的職能交給公安局,我看公安局的巡警支隊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
“怎么有點英雄所見略同的感覺?”
“不然怎么兌現你的人事安排?”
“好的,我和大信、孝溫找幾個相關部門務務虛,先討論討論。”
苗東平意識到自己有點急,接著說道:“當然,這事也不用太急,先放一放,等我們把工作全面開展起來以后再說吧。”
“好的,我按你的意思辦。”
野馬車繼續向城南方向開去。
“尚官杰的事情,你告訴你姐姐花蕾了嗎?”苗東平轉移話題問道。
“我和她通了電話,她說我媽媽已經告訴她了。”花蕊說。
“她有什么反應?”
“沒有任何反應。她只是說,這下好了,為她和尚官杰盡快辦理離婚找到了理由。”
“這個時候辦理離婚手續,是不是對尚官杰打擊太大了?”
“在這之前尚官杰堅持不離。”
“既然已經這樣了,尚官杰為什么還要堅持?”
“尚官杰相信我姐是愛他的。”
“你姐真的還愛他?”
“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我姐是那種不太愿意與人交流的人。”
“和你也不交流?”
“不。 ”
“和你媽媽呢?”
“偶爾說說話,但她很聽我媽媽的話。”
“你媽媽好像一直對尚官杰有看法?”
“我姐和尚官杰談戀愛的時候,我媽媽就堅決反對。”
“為什么呢?”
“我媽媽覺得尚官杰太張揚,鋒芒畢露,出事是遲早的事情,他不適合我姐姐。”
“那倒是,兩人的性格差異很大。”
“我姐姐是那種只對自己的醫學專業感興趣,堅決奉行不貪權,免得自己給自己找麻煩的人。她希望過一種平平安安的寧靜生活。而尚官杰呢,是一個有政治抱負,對仕途和權力有極強欲望的人,他的個性決定了他不可能過安穩的日子,他們根本是南轅北轍。”
“我同意你的分析。”
“聽說你姐姐堅決要和尚官杰離婚,主要是因為蟹島PX項目?”
“不完全是。我姐在結婚的第二天就向尚官杰提出了離婚。”
“那為什么要結婚呢?”
“可能與我有關。”
“與你有關?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姐姐只給我媽媽說過。”
“尚官杰好像一直不太聽你媽媽的?”
“可能觀念上有些分歧。”
“我經常聽到你媽媽在公開場合點名批評尚官杰,連外人都認為她這個省長丈母娘對女婿要求太嚴了。”
“其實,在上蟹島PX項目之初,我媽媽找尚官杰談過幾次話,希望尚官杰不要把那么大的項目攬到三江去,三江的民意、環境、經濟實力、人才、管理等諸多方面,都不具備承接PX項目的條件。說白了,我媽媽擔心尚官杰的政治野心,會把PX這個燙手山芋弄成三江乃至西都省隨時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時炸彈。”
“這些情況我知道,你媽媽找尚官杰談話,我也見過一兩次,當時我覺得你媽媽說得有道理。”
“尚官杰沒有把我媽媽的話放在心上,可能他也想通過上PX項目,把自己的能力體現給我媽媽看。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久之后,尚官杰在北京做通了馬學東的工作,背著我媽媽爭取到了PX項目。”
“馬學東是向著尚官杰的。”
“畢竟尚官杰曾經是省委書記馬學東的秘書。”
“其實,你媽媽沒有必要……再怎么說,尚官杰畢竟是她的女婿,況且……”
“我媽媽這個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她認定的事情,誰要是反對了,她一定不會善罷甘休的。所以,在蟹島PX項目這件事上,我媽媽首先認為尚官杰不聽話,還有就是,她認為尚官杰堅持要上PX項目,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大概就是老百姓所說的,官當得越大,心胸就越狹隘的緣故吧。”
“其實,在外人眼里,都認為你姐姐和尚官杰是很般配的一對。一個有成就的醫學專家,一個有抱負的政治精英,加上你們家的政治背景,他們應該很幸福。”
“婚姻的悲劇,在于彼此看到對方的一切并非真實。”
“有道理。”
看著車燈照射的前方,苗東平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節選自長篇小說《靜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