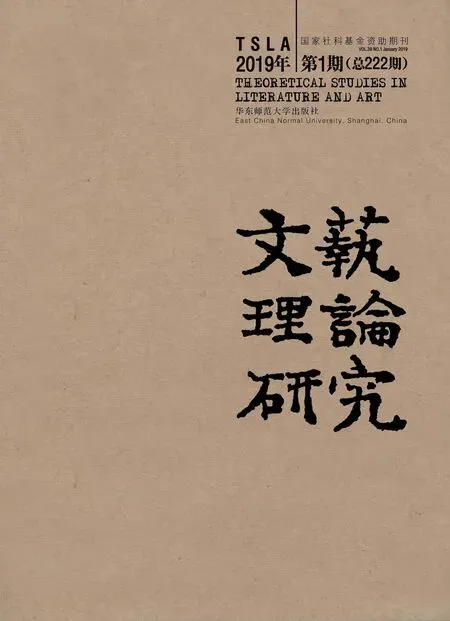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評(píng)述
——?dú)v史、現(xiàn)狀與反思
趙雪梅
引言:創(chuàng)傷理論——一個(gè)跨學(xué)科的人文研究領(lǐng)域
作為人文學(xué)科研究中的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創(chuàng)傷研究的興起與充滿了創(chuàng)傷事件的人類二十世紀(jì)歷史密不可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猶太人大屠殺等人為暴行構(gòu)成了二十世紀(jì)殘暴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創(chuàng)傷研究的興起與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土壤與文化契機(jī)。正如著名的創(chuàng)傷研究學(xué)者肖莎娜·費(fèi)爾曼(Shoshana Felman)所言,二十世紀(jì)是“一個(gè)創(chuàng)傷的世紀(jì)并且(同時(shí))是一個(gè)創(chuàng)傷理論的世紀(jì)”(Felman,Juridical
1)。當(dāng)代創(chuàng)傷研究以美國(guó)為重鎮(zhèn),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紀(jì)80年代的兩大重要啟發(fā)性事件:一是越戰(zhàn)老兵呈現(xiàn)出的一系列戰(zhàn)爭(zhēng)后遺癥,促使美國(guó)精神病學(xué)會(huì)將“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PTSD)宣布為一種疾病,進(jìn)而引發(fā)了包括醫(yī)療界在內(nèi)的研究者對(duì)創(chuàng)傷的日益關(guān)注;一是對(duì)猶太人大屠殺的關(guān)注,尤其是由杰弗里·哈特曼主持的耶魯大學(xué)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檔案庫(kù)的建立對(duì)創(chuàng)傷研究的興起有著重要的推動(dòng)作用。多利·勞布(Dori Laub)、肖莎娜·費(fèi)爾曼以及凱茜·卡魯思(Cathy Caruth)建構(gòu)創(chuàng)傷理論的幾部重要專著正是隨著檔案庫(kù)的建立而完成的。就涉及的學(xué)科領(lǐng)域而言,創(chuàng)傷研究涵蓋了精神心理學(xué)、神經(jīng)醫(yī)學(xué)、歷史學(xué)、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以及文學(xué)等多種學(xué)科。如較早從事大屠殺文學(xué)研究的詹姆斯·揚(yáng)(James E Young)將自己的研究稱為“文學(xué)歷史編纂學(xué)”以凸顯其跨學(xué)科特點(diǎn)。在創(chuàng)傷研究的跨學(xué)科特點(diǎn)的形成中,費(fèi)爾曼和多利·勞布的《證言:文學(xué)、精神分析和歷史中的見(jiàn)證危機(jī)》(Testimony
:Crisi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 1992)以及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記憶中的探索》(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 1995)兩書(sh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們被認(rèn)為是“試圖將創(chuàng)傷研究發(fā)展為一種聯(lián)合文學(xué)批評(píng)家、社會(huì)學(xué)家、檔案保管員、電影人以及精神病醫(yī)生的跨學(xué)科對(duì)話的兩個(g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編輯出版物”(Hinrichsen 606)。凱茜·卡魯思、肖莎娜·費(fèi)爾曼以及杰弗里·哈特曼等人的早期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Literary Trauma Theory)研究,則被認(rèn)為是“審查精神分析理論與文學(xué)間進(jìn)行復(fù)雜對(duì)話的方法”(606)。隨著創(chuàng)傷研究的推進(jìn),一方面,創(chuàng)傷研究的經(jīng)典研究領(lǐng)域——大屠殺研究進(jìn)一步得到發(fā)展。心理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和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們不斷從新的視角來(lái)擴(kuò)展大屠殺研究,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詹姆斯·揚(yáng)、埃里克·桑特納(Eric Santner)、羅伯特·杰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以及邁克爾·羅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的作品,大多“試圖去理解作為一件創(chuàng)傷事件的大屠殺是如何對(duì)再現(xiàn)做出基本要求的”(Hinrichsen607)。此外,后結(jié)構(gòu)主義等哲學(xué)家對(duì)大屠殺的關(guān)注也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創(chuàng)傷研究的發(fā)展。“大屠殺和創(chuàng)傷研究”這兩個(gè)領(lǐng)域之所以被認(rèn)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見(jiàn)解”(Koopman236),與德里達(dá)和利奧塔等思想家對(duì)大屠殺話題的思考不無(wú)關(guān)系。
另一方面,創(chuàng)傷研究不再專注于大屠殺與戰(zhàn)爭(zhēng)等激烈的人為暴行,而日益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軌。對(duì)此,哈特曼在上世紀(jì)90年代早期已有所認(rèn)識(shí),他指出:“創(chuàng)傷研究的激進(jìn)涌現(xiàn)與其說(shuō)是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和大屠殺這種暴力行為的強(qiáng)調(diào),不如說(shuō)是對(duì)一些諸如強(qiáng)奸,以及婦女與兒童的虐待等‘常見(jiàn)的’暴力的關(guān)注。尤其是,它并沒(méi)有忽視情感與日常傷害的爆炸性性質(zhì)。顯而易見(jiàn)事故——即那些明顯簡(jiǎn)單的日常事件也揭示,或被卷入到一種創(chuàng)傷的氛圍中去。”(Hartman, “On Traumatic”546)隨著臨床心理學(xué)醫(yī)生對(duì)創(chuàng)傷研究的介入,哈特曼的這一觀點(diǎn)不僅在朱迪斯·赫爾曼(Judith Herman)的《創(chuàng)傷與復(fù)原》(Trauma
and
Recovery
, 1992年)這一創(chuàng)傷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中得到印證,也在眾多的社會(huì)文化現(xiàn)象中得以體現(xiàn)。《創(chuàng)傷問(wèn)題》(The
Trauma
Question
, 2008年)一書(shū)的作者盧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由此認(rèn)為,當(dāng)今的文化已“被創(chuàng)傷滲透,”具體表現(xiàn)為,“在政治上,它包含了政府的調(diào)查,醫(yī)療工作者和草根壓力群體。它侵入了今天的暢銷書(shū)單,學(xué)術(shù)專著與名人傳媒。”(Luckhurst 2)近年來(lái),創(chuàng)傷研究作為人文學(xué)科界的一個(gè)重要領(lǐng)域與研究熱點(diǎn)日益引起國(guó)內(nèi)學(xué)界的關(guān)注。就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創(chuàng)傷研究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問(wèn)題。其一,創(chuàng)傷研究在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與理論探討兩大領(lǐng)域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不平衡的態(tài)勢(shì)。創(chuàng)傷研究者更傾注于創(chuàng)傷文學(xué)的文本批評(píng),并獲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對(duì)理論的探索則較為滯后。這種滯后一方面表現(xiàn)為研究成果的稀少,另一方面則體現(xiàn)為已有的研究多立足于創(chuàng)傷理論的心理學(xué)與精神病學(xué)的學(xué)科基點(diǎn),將其作為一項(xiàng)跨學(xué)科的人文理論來(lái)進(jìn)行寬泛的解讀,缺乏必要的文學(xué)視角與立足點(diǎn),這也意味著創(chuàng)傷理論的文學(xué)建構(gòu)還是一個(gè)亟待挖掘與開(kāi)拓的研究領(lǐng)域。其二,作為一個(gè)“發(fā)明”于西方19世紀(jì)晚期的人工制品,創(chuàng)傷概念的起源可以“定位于各種涉及歐洲與美國(guó)的工業(yè)化經(jīng)歷、性別關(guān)系以及現(xiàn)代戰(zhàn)爭(zhēng)的醫(yī)學(xué)與心理學(xué)的話語(yǔ)。”(Young 5)正如埃德金斯(Jenny Edkins)所言,“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不僅僅在歷史上,而且在地理上是特殊的[……]它吸收了聚焦于個(gè)體的個(gè)性概念,并于一個(gè)特定的歷史時(shí)刻在西方出現(xiàn)。”(Edkins 43)創(chuàng)傷概念產(chǎn)生的歷史與文化情境表征了其與生俱來(lái)的西方特性,同時(shí)也揭橥了這一概念特定的歷史文化語(yǔ)境與研究對(duì)象。然而,這一事實(shí)長(zhǎng)期以來(lái)并未引起創(chuàng)傷研究者的重視。鑒于此,本文從文學(xué)與文化的視角出發(fā),擬對(duì)文學(xué)中的創(chuàng)傷研究,尤其是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進(jìn)行探討,希冀在梳理其歷史與現(xiàn)狀的基礎(chǔ)上,反思其存在的問(wèn)題與不足,進(jìn)而推動(dòng)國(guó)內(nèi)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相關(guān)研究。
一、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起源
文學(xué)與相關(guān)學(xué)科領(lǐng)域的創(chuàng)傷理論的來(lái)源主要受以下四股思潮的影響。首先是歷史學(xué)科中的“記憶”轉(zhuǎn)向。相關(guān)研究主要涉及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在20世紀(jì)80年代的著作,優(yōu)素福·耶魯沙爾米(Yosef Yerushalmi)的專著《扎赫爾:猶太歷史與猶太記憶》(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 1982年),米歇爾·福柯的記憶的政治學(xué),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記憶-政治學(xué)”研究以及對(duì)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20世紀(jì)20年代開(kāi)始從事的集體記憶的研究成果的再發(fā)現(xiàn)與翻譯;其次,一些臨床心理學(xué)醫(yī)生如朱迪斯·赫爾曼的《創(chuàng)傷與復(fù)原》與亞瑟·弗蘭克(Arthur Frank)的《受傷的講故事者》(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1995年)等著作也給創(chuàng)傷理論研究者帶來(lái)了一定的啟發(fā),使他們聚焦于創(chuàng)傷事件以及個(gè)體性創(chuàng)傷;再次,拉康及齊澤克的黑格爾-拉康式的政治化的精神分析(或曰精神分析的政治學(xué))也對(duì)創(chuàng)傷理論的研究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一些受此啟發(fā)的理論家的著作通常將創(chuàng)傷作為一個(gè)核心概念來(lái)使用。如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和《戰(zhàn)爭(zhēng)的結(jié)構(gòu)》等書(shū)涉及了對(duì)創(chuàng)傷、悲痛與哀悼等問(wèn)題的研究。最后,德里達(dá)與德曼等人的解構(gòu)主義思想及其影響下的凱茜·卡魯思和肖莎娜·費(fèi)爾曼等人的創(chuàng)傷研究成為創(chuàng)傷理論的重要來(lái)源與組成部分。(Buelens, Sam, and Robert 2)除了當(dāng)代心理學(xué)與精神病學(xué)的相關(guān)研究外,文學(xué)領(lǐng)域中的創(chuàng)傷理論還和耶魯學(xué)派、文學(xué)理論的倫理轉(zhuǎn)向以及歐洲哲學(xué)等思想主張或理論體系緊密相關(guān)。其中,耶魯學(xué)派與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關(guān)聯(lián)首先體現(xiàn)為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檔案庫(kù)的建立。其次,這種關(guān)聯(lián)還體現(xiàn)為以德曼和哈特曼為代表的耶魯學(xué)派成員對(duì)以卡魯思為代表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家的影響。據(jù)比利時(shí)布魯塞爾天主教大學(xué)的湯姆·托里曼斯(Tom Toremans)考證,肖莎娜·費(fèi)爾曼的《教育與危機(jī),或教育的興衰》(Education and Crisi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Teaching, 1991年)一文的標(biāo)題就借鑒了德曼的《批評(píng)與危機(jī)》(Criticism and Crisis, 1983)一文的寫法。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肖莎娜的這篇文章“將當(dāng)前處于批評(píng)構(gòu)造之中的創(chuàng)傷術(shù)語(yǔ),引導(dǎo)至美國(guó)的理論場(chǎng)景中”(Ramadanovic 2)。德曼的《對(duì)理論的抵抗》(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1982年)一文則是卡魯思的《落體和引用的影響》(The Falling Body and the Impact of Reference, 1996年)一文的起點(diǎn),該文成為她的《不被宣稱的經(jīng)歷》(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1996年)一書(shū)中探討創(chuàng)傷的理論話語(yǔ)的可能性條件的重要文本之一。此外,卡魯思對(duì)創(chuàng)傷的界定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哈特曼的影響。1994年秋,哈特曼在接受卡魯思的訪談時(shí)說(shuō)過(guò):“創(chuàng)傷大體上被界定為一種不被體驗(yàn)到的經(jīng)歷,它抗拒或逃避意識(shí)”(Caruth, “An Interview” 631)。這一表述在卡魯思1996年的《不被宣稱的經(jīng)歷》一書(shū)中得到了重現(xiàn):“創(chuàng)傷無(wú)法定位于某人過(guò)去發(fā)生的某個(gè)單純暴力的或最初的事件,而是定位于它的那種獨(dú)特的本質(zhì)——它的那種在最初無(wú)法被確切感知——過(guò)后返回來(lái)纏繞幸存者的方式。”(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
4)卡魯思的這一界定被研究者視為創(chuàng)傷的權(quán)威定義而一再引用,創(chuàng)傷的不可言說(shuō)論的主導(dǎo)性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確立。鑒于凱茜·卡魯思和肖莎娜·費(fèi)爾曼等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研究的骨干成員與耶魯學(xué)派的學(xué)術(shù)淵源,她們也被認(rèn)為是耶魯學(xué)派的成員,和杰弗里·哈特曼一起,代表著耶魯學(xué)派“揭示了文學(xué)批評(píng)和創(chuàng)傷理論之間那種獨(dú)特的密切關(guān)系,而且暗示出創(chuàng)傷理論以不為人知的方式內(nèi)在地與文學(xué)相連。”(Whitehead 4)耶魯學(xué)派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影響還體現(xiàn)為杰弗里·哈特曼對(duì)早期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建構(gòu)。哈特曼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傷的關(guān)注始自20世紀(jì)60年代早期,在關(guān)于華茲華斯的研究中已涉及詩(shī)人身份的形成或變形與創(chuàng)傷之間的關(guān)系。他1995年的那篇有名的題為“論創(chuàng)傷知識(shí)與文學(xué)研究”(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綱領(lǐng)。文中,哈特曼將創(chuàng)傷理論稱為“一種關(guān)注詞語(yǔ)與創(chuàng)傷的關(guān)系,借助文學(xué)幫助我們?nèi)ァ喿x創(chuàng)傷’的理論,”一種“強(qiáng)烈受到文學(xué)實(shí)踐影響”(537)的理論;將創(chuàng)傷理論研究者們比作“一個(gè)虛擬社區(qū)的探險(xiǎn)家”(537);將創(chuàng)傷知識(shí)分為兩種沖突的元素:創(chuàng)傷事件與事件的一種記憶。并指出,“就詩(shī)學(xué)層面而言,文字與形象應(yīng)該與這兩種類型的知識(shí)相對(duì)應(yīng)。”(537)緊接著,哈特曼以具體的文學(xué)實(shí)例論述了創(chuàng)傷與文學(xué)間的緊密聯(lián)系。他指出:“我懷疑沒(méi)有普通事物的這種‘襲擊’現(xiàn)代小說(shuō)是否有可能(出現(xiàn)):從哥特故事中祖先畫(huà)像的奇怪面容到托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中的驚世駭俗的遭遇,品欽的《叫賣第49組》(The
Crying
of
Lot
49)的百納被褥,里爾克的《馬爾特·勞瑞茲·布里格的筆記本》(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
)中感覺(jué)-認(rèn)知的瓦解或反抗,或神秘小說(shuō)中的一些無(wú)罪的(對(duì)偵探而言)但富有啟迪性的事故,或小說(shuō)中的任何‘現(xiàn)實(shí)的’的片斷”(546)。顯然,在哈特曼看來(lái),日常性普通創(chuàng)傷既是現(xiàn)代小說(shuō)產(chǎn)生的重要契機(jī),也是它的重要表現(xiàn)主題。而作為一種閱讀創(chuàng)傷的文學(xué)理論,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盡管“在文學(xué)研究的范圍之內(nèi)運(yùn)作時(shí),并沒(méi)有最后的答案”(547),但它“使我們獲得一個(gè)更為清晰的有關(guān)文學(xué)與精神功能在引用,主體性和敘述幾個(gè)關(guān)鍵領(lǐng)域的關(guān)系的觀點(diǎn)”(547),從而使“文學(xué)研究可能變得更富有想象力”(551)。其次,作為文學(xué)理論倫理轉(zhuǎn)向的產(chǎn)物,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誕生與文學(xué)理論的危機(jī)緊密相關(guān)。在文學(xué)學(xué)者被指控為“在解構(gòu)主義的,后結(jié)構(gòu)主義,或文本主義的偽裝下,對(duì)‘發(fā)生在真實(shí)世界中的事物’(文本之外的世界:歷史,政治,倫理)變得冷漠或不關(guān)注”的情況下,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自信地宣稱它自己是理解‘真實(shí)世界’的一項(xiàng)必要的裝備,甚至也是使它變得更好的一項(xiàng)潛在手段。”(Buelens, Sam, and Robert 45)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這種倫理維度在本領(lǐng)域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均有體現(xiàn)。如在《不被宣稱的經(jīng)歷》一書(shū)中,卡魯思指出,較之后結(jié)構(gòu)主義批評(píng)引發(fā)的認(rèn)識(shí)論問(wèn)題導(dǎo)致的“政治與倫理的麻痹”(10),創(chuàng)傷批評(píng)為我們接近歷史提供了獨(dú)特途徑,“通過(guò)創(chuàng)傷概念[……]我們可以知道對(duì)引文的再思考并不是旨在消滅歷史,而是將其重置于我們的理解中,確切來(lái)說(shuō),旨在允許歷史在無(wú)法即刻理解的地方出現(xiàn)。”(11)文學(xué)創(chuàng)傷通過(guò)對(duì)創(chuàng)傷(歷史)的再現(xiàn)賦予了文學(xué)研究倫理意義。這是因?yàn)椋鳛橐环N新的閱讀和聆聽(tīng)模式,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有助于破除由創(chuàng)傷經(jīng)歷施加在個(gè)體與文化上的隔離。畢竟,“歷史,和創(chuàng)傷一樣,從未僅是某個(gè)人自己的,[……]歷史恰是我們被牽連進(jìn)彼此的創(chuàng)傷中的方式。”(24)和卡魯思一樣,費(fèi)爾曼也強(qiáng)調(diào)一種倫理的批評(píng)實(shí)踐的必要。她指出,證言需要一種見(jiàn)證行為,它包含了“鎮(zhèn)壓的政治維度與反抗的倫理維度。”(Felman,Testimony
12)此外,就研究領(lǐng)域來(lái)看,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的一些重要領(lǐng)域如有關(guān)猶太大屠殺幸存者文學(xué)文本誘發(fā)幸存者有關(guān)大屠殺記憶的原因、方式及其影響的研究,由越戰(zhàn)引發(fā)的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對(duì)于越戰(zhàn)老兵的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及性侵與虐待等日常創(chuàng)傷的受創(chuàng)者個(gè)體再現(xiàn)創(chuàng)傷的方式等研究均涉及了倫理的考究。簡(jiǎn)言之,“在最近的幾十年里,在大屠殺和創(chuàng)傷研究中,圍繞再現(xiàn)暴力與苦難的倫理討論已經(jīng)更加切題。”(Koopman 236)需要指出的是,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倫理轉(zhuǎn)向說(shuō),哈特曼持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文學(xué)的創(chuàng)傷研究固然有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關(guān)懷,但其“結(jié)果未必就是倫理批評(píng),因?yàn)檫@一最新的(文學(xué)研究)視角并不試圖提供個(gè)體作品的一種固定判斷或評(píng)估。[……]它關(guān)注的是潛在地以一種文學(xué)的認(rèn)知方式來(lái)揭示一種無(wú)意識(shí)或不為人知的知識(shí)。[……]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語(yǔ)言的想象性使用,而不是一種完美的清晰意義。”(“On Traumatic Knowledge” 544)最后,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還受到了德里達(dá)、福柯和阿多諾等歐洲哲學(xué)思想的影響。德里達(dá)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影響無(wú)需贅述,福柯對(duì)創(chuàng)傷研究的影響在露絲·萊斯(Ruth Leys)的《創(chuàng)傷:一個(gè)譜系》(Trauma
:A
Genealogy
, 2000)一書(shū)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xiàn)。她坦承由于深受福柯的系譜學(xué)的影響,她在著作中“努力回應(yīng)了福柯的勸告。”(657—58)詹姆斯·揚(yáng)則毫不諱言自己《書(shū)寫與重寫大屠殺:敘述與闡釋的影響》(Writing
and
Rewriting
the
Holocaust
:Narrativ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pretation
, 1988)一書(shū)的寫作受到了羅蘭·巴特、福柯、德里達(dá)和海登·懷特等學(xué)者的影響。在《否定的辯證法》一書(shū)中,阿多諾對(duì)奧斯維辛集中營(yíng)猶太人大屠殺事件的分析完美地展現(xiàn)了他的否定辯證法,成為以卡魯思為代表的早期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家建構(gòu)理論主張的重要哲學(xué)基礎(chǔ)。在阿多諾看來(lái),奧斯維辛集中營(yíng)之后,首先意味著肯定性與意義的消亡,這是因?yàn)椋颓楦卸裕覀兎磳?duì)奧斯維辛集中營(yíng)事件確實(shí)存在的這種肯定性說(shuō)法,并拒絕以談?wù)撃切┦芎φ叩脑庥鰜?lái)獲得意義。取而代之的是絕對(duì)的否定性以及死亡的異化。當(dāng)數(shù)百萬(wàn)人被以管理的手段進(jìn)行謀殺后,死亡成了一件司空見(jiàn)慣,并不可怕的事,那些死去的人不再是一個(gè)個(gè)正常體驗(yàn)生命死亡的個(gè)體生命,而被異化為一種抽象的“樣品。”(362)種族滅絕和死亡也成了“絕對(duì)的一體化”與“純粹同一性”的代名詞,并“在意識(shí)形態(tài)上潛伏著對(duì)非同一性的破壞。”(363)然而死亡也并非絕對(duì),因?yàn)椤耙磺卸际翘摕o(wú)”,“任何帶有真理性的東西都是不可思議的。”(372)盡管如此,死亡畢竟導(dǎo)致了批判反思性思維的消滅殆盡以及意義的空乏。意義的空乏也意味著語(yǔ)言的徒勞以及創(chuàng)傷的不可言說(shuō)。這是因?yàn)椋捌髨D用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死亡歸根到底在邏輯上是無(wú)用的。”(372)悖論在于,當(dāng)肯定性消亡后,語(yǔ)言對(duì)死亡的徒勞這一論斷本身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質(zhì)疑。對(duì)此,盧克赫斯特的總結(jié)可謂一語(yǔ)中的:“整個(gè)西方文化轉(zhuǎn)瞬間被奧斯維辛污染,成了它的同謀。然而對(duì)文化的拒絕同樣是野蠻的。如果沉默無(wú)濟(jì)于事,那么阿多諾賦予藝術(shù)和文化批評(píng)的嚴(yán)肅卻又自相矛盾的使命就是,竭力再現(xiàn)不可再現(xiàn)的事件。”(5)二、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發(fā)展與現(xiàn)狀
1. 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第一波——?jiǎng)?chuàng)傷的無(wú)法言說(shuō)論
阿多諾的上述言論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創(chuàng)傷的無(wú)法言說(shuō)論在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中的理論基調(diào)。與此同時(shí),心理學(xué)上創(chuàng)傷健忘癥概念的提出(心理學(xué)家將那種無(wú)法記住一次異常痛苦的經(jīng)歷的現(xiàn)象稱為創(chuàng)傷健忘癥)為創(chuàng)傷的不可言說(shuō)論提供了心理學(xué)依據(jù)。這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杰弗里·哈特曼、肖莎娜·費(fèi)爾曼以及凱茜·卡魯思等第一波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家達(dá)成的一項(xiàng)共識(shí):受創(chuàng)者可能遺忘,或無(wú)法確切地描述創(chuàng)傷。因此,盡管由多米尼克·拉卡普拉(2001)和邁克爾·羅斯伯格(2000)提出的創(chuàng)傷聲音說(shuō)也在創(chuàng)傷研究界占有一定市場(chǎng),但無(wú)法言說(shuō)論依然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的起點(diǎn)而被廣泛接受。
在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出現(xiàn)之前的上世紀(jì)80年代中期,伊萊娜·斯卡里(Elaine Scarry)就語(yǔ)言與痛苦之間關(guān)系的探討可視為無(wú)法言說(shuō)論的先聲。在《處于痛苦中的身體》(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 1987)一書(shū)中,斯卡里探討了用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痛苦(身體的或精神的)的困難。斯卡里認(rèn)為,痛苦的特征在于它的“不可分享性(unsharability),以及它通過(guò)對(duì)語(yǔ)言的抗拒來(lái)確保這種不可分享性。”(4)由于痛苦對(duì)語(yǔ)言的抵抗是“構(gòu)成痛苦的關(guān)鍵”,因此“痛苦不只是簡(jiǎn)單地抗拒語(yǔ)言,而是積極地去破壞它,導(dǎo)致一種對(duì)前語(yǔ)言狀態(tài)的即刻回歸。”(5)盡管痛苦抗拒語(yǔ)言,但我們依然“處于并經(jīng)歷試圖發(fā)明語(yǔ)言結(jié)構(gòu)來(lái)容納這一語(yǔ)言通常無(wú)法接近的區(qū)域的險(xiǎn)境之中。”(6)就詩(shī)人而言,使一種能夠表達(dá)別人的痛苦與悲痛的語(yǔ)言產(chǎn)生的工作甚至更加困難。因?yàn)椤爸挥挟?dāng)人的聲音變得可見(jiàn),”(8)發(fā)明一種能有效描述痛苦的語(yǔ)言的努力才會(huì)實(shí)現(xiàn)。哈特曼對(duì)創(chuàng)傷的不可言說(shuō)論的理論貢獻(xiàn)在于他對(duì)“梭子之聲”這一經(jīng)典隱喻的提出。他是這樣闡述這一隱喻的:
我斗膽把述說(shuō)創(chuàng)傷定義為一種妥協(xié)形態(tài),就是在無(wú)法言說(shuō)條件下的言說(shuō)。這是指你力圖有創(chuàng)造性地表達(dá)自己,但基本的前提是因?yàn)橥纯噙^(guò)多而無(wú)法言說(shuō)。不過(guò)你仍然能找到你的聲音,這一過(guò)程可以用一個(gè)精辟的隱喻來(lái)概括:“梭子之聲”。[……]“梭子之聲”聽(tīng)上去高深莫測(cè),實(shí)際上它濃縮了菲羅美拉被強(qiáng)奸后又被割掉舌頭的故事。她遭受了雙重創(chuàng)傷。她回應(yīng)的方法就是織一條毯子來(lái)描寫她的強(qiáng)奸;這樣,“梭子之聲”成了她的聲音。這個(gè)形象指向一種補(bǔ)救性的變形,每次我思考創(chuàng)傷,思考藝術(shù)尋找“無(wú)法言說(shuō)”的言說(shuō)來(lái)表達(dá)創(chuàng)傷的可能性時(shí),它都會(huì)出現(xiàn)在我腦海里。(謝瓊74)
可見(jiàn),“梭子之聲”所指涉的正是文學(xué)藝術(shù)對(duì)于創(chuàng)傷的意義——使無(wú)法言說(shuō)的創(chuàng)傷得以言說(shuō)。這一隱喻本身所蘊(yùn)含的悖論一定程度上質(zhì)疑了它的合理性,但其終極意義在于賦予了文學(xué)藝術(shù)言說(shuō)創(chuàng)傷的可能性,將絕望轉(zhuǎn)化為希望。顯然,“梭子之聲”無(wú)處不在,存在于文學(xué)藝術(shù)中,也存在于各種形式的記錄中。如大屠殺幸存者證言視頻是幸存者們見(jiàn)證與交流大屠殺創(chuàng)傷的一種獨(dú)特方式。在哈特曼看來(lái),除了幸存者證言視頻,大屠殺這一事件通常難以通過(guò)其它方式得以充分地再現(xiàn)。視頻證言的優(yōu)勢(shì)在于它們雖然是視聽(tīng)的,但并不予視覺(jué)優(yōu)先或刺激我們的眼睛,即它們避免了“二次創(chuàng)傷”(Caruth, “An Interview” 643)的蔓延——即便依然震驚,但它們給予了敏感的心靈以反思的空間。
就卡魯思而言,《創(chuàng)傷:記憶中的探索》和《不被宣稱的經(jīng)歷》的出版奠定了她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之母的地位。卡魯思在《不被宣稱的經(jīng)歷》一書(shū)中對(duì)創(chuàng)傷的界定直指創(chuàng)傷的再現(xiàn)危機(jī)——?jiǎng)?chuàng)傷的無(wú)法言說(shuō),旨在表明創(chuàng)傷事件作為一種壓倒性突發(fā)事件,迫使人們當(dāng)時(shí)心理無(wú)法正常處理它。創(chuàng)傷過(guò)后,受害者旋即可能徹底忘記了這一事件。即便是創(chuàng)傷記憶又返回到人們腦海當(dāng)中,它們通常也是非語(yǔ)言的,即受害者可能無(wú)法用言語(yǔ)來(lái)描述它們。這種脫胎于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定義的不可言說(shuō)的創(chuàng)傷觀被巴拉耶夫(Michelle Balaev)稱為創(chuàng)傷的經(jīng)典模式(Balaev 1)。這是因?yàn)椋瑒P茜·卡魯思及其創(chuàng)傷的無(wú)法言說(shuō)論在較長(zhǎng)時(shí)間內(nèi)始終是創(chuàng)傷研究界的權(quán)威存在。在露絲·萊斯的《創(chuàng)傷:一個(gè)譜系》一書(shū)中,萊斯用了足以與弗洛伊德匹敵的一整章的篇幅來(lái)介紹卡魯思的著作。2011年,劍橋大學(xué)舉辦了一次針對(duì)卡魯思著作的研討會(huì),在同年出版的一篇文章里,珍·懷亞特(Jean Wyatt)寫道,創(chuàng)傷理論依然處于由卡魯思介紹的“理論框架的支配。”(31)
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的經(jīng)典模式之所以能在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中維持霸主地位,首先在于這一模式能激發(fā)起一系列相關(guān)問(wèn)題的研究,如有關(guān)個(gè)體與文化群體所經(jīng)歷的創(chuàng)傷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受害者、行兇者與證人之間的關(guān)系等問(wèn)題的探索;其次,這一經(jīng)典模式的魅力還在于有關(guān)精神與記憶過(guò)程的神經(jīng)心理學(xué)理論與有關(guān)語(yǔ)言、關(guān)聯(lián)和象征化過(guò)程的符號(hào)學(xué)理論的結(jié)盟。正如巴拉耶夫所言,“創(chuàng)傷研究的經(jīng)典模式的動(dòng)人之處是支配創(chuàng)傷功能的心理學(xué)規(guī)則與支配語(yǔ)言意義的符號(hào)學(xué)規(guī)則的明顯聯(lián)姻。”(Balaev 2)再次,創(chuàng)傷研究經(jīng)典模式持續(xù)的吸引力或許還在于“她們的那種闡述方式修正了弗洛伊德的概念使之符合解構(gòu)主義與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閱讀模式”(Hinrichsen 607)。最后,創(chuàng)傷的經(jīng)典模式之所以能長(zhǎng)期抵制批評(píng)并維持持久的使用價(jià)值,是因?yàn)椤翱斔紝⑺睦碚摯髲B建立在一個(gè)科學(xué)基礎(chǔ)之上。”(Pederson 334)這里的科學(xué)基礎(chǔ)是指以朱迪斯·赫爾曼和貝塞爾·范·德·科爾克(Bessel van der Kolk)為代表的一些當(dāng)代杰出的心理學(xué)家和精神病學(xué)家的臨床經(jīng)驗(yàn)或研究著作。正是這些在上世紀(jì)90年代中期的創(chuàng)傷研究領(lǐng)域中極具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在科學(xué)的層面上撐起了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的不可言說(shuō)的斷言。
創(chuàng)傷的經(jīng)典模式之所以在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研究界意義重大,根本原因在于它賦予了文學(xué)交流創(chuàng)傷的獨(dú)特力量與權(quán)力。1994年,哈特曼對(duì)采訪他的卡魯思說(shuō)到,“在事件的非病理學(xué)過(guò)程之中,你稱之為‘不被宣稱的經(jīng)歷’的創(chuàng)傷只能通過(guò)文學(xué)知識(shí)被再次宣稱。”(Caruth, “An Interview” 641)1995年,在《創(chuàng)傷知識(shí)與文學(xué)研究》一文中,哈特曼指出,文學(xué)允許我們“閱讀創(chuàng)傷”,處理“那個(gè)遭受損失的變形世界的現(xiàn)實(shí)。”(537)2003年的一篇文章里,哈特曼再次指出,“創(chuàng)傷研究作為一項(xiàng)特別致力于文學(xué)的工作,探索言語(yǔ)與創(chuàng)傷之間的關(guān)系。[……]然而,文學(xué)的語(yǔ)言表現(xiàn)依然是使創(chuàng)傷被感知,沉默被聽(tīng)見(jiàn)的基礎(chǔ)。”(“Trauma Within” 259)哈特曼的這些論斷被認(rèn)為是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傷的強(qiáng)有力辯護(hù):“如果只有文學(xué)能夠接近創(chuàng)傷,那么或許只有文學(xué)能以它最真實(shí)的形式來(lái)傳遞現(xiàn)實(shí)。”(Pederson 349)同樣,盡管卡魯思認(rèn)為創(chuàng)傷無(wú)法用語(yǔ)言來(lái)再現(xiàn),但和阿多諾一樣,卡魯思依然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應(yīng)該處理創(chuàng)傷。盡管正常的,散漫的語(yǔ)言不能言說(shuō)創(chuàng)傷,但想象性的文學(xué),或形象,而非字面語(yǔ)言,卻可以“言說(shuō)”創(chuàng)傷。文學(xué)作為虛構(gòu)作品有助于那些遭受創(chuàng)傷的個(gè)體或群體發(fā)出聲音。卡魯思甚至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將是解釋創(chuàng)傷這種無(wú)法解釋之物的最適當(dāng)?shù)拿浇椋驗(yàn)樗赡苓\(yùn)用了那種“正如它宣稱的那樣,挑戰(zhàn)我們的理解力”(Unclaimed
Experience
, 5)的語(yǔ)言。卡魯思指出,“假如弗洛伊德借助于文學(xué)來(lái)描述創(chuàng)傷經(jīng)歷,那是因?yàn)槲膶W(xué)和精神分析學(xué)一樣,對(duì)已知與未知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興趣盎然。的確,創(chuàng)傷經(jīng)歷的精神分析理論與文學(xué)語(yǔ)言正是在已知與未知特定的交叉點(diǎn)上相遇的。”(3)基于上述言論,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理論由此被視為“是對(duì)文學(xué)的見(jiàn)證功能的一種斷然的認(rèn)可”(Pederson 334)。在《證言》中,費(fèi)爾曼與勞布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diǎn)。她們指出,為了處理“至今仍未被解讀的歷史危機(jī)的后果與進(jìn)展,”人們必須求助于文學(xué),因?yàn)椤拔膶W(xué)成了一個(gè)目擊者,而且也許是歷史中的恰好不能被明確表達(dá)的,無(wú)法在歷史本身的既定范疇內(nèi)被證明的危機(jī)的唯一的目擊者。”(Felman,Testimony
, Xviii)巧合的是,這一觀點(diǎn)也獲得了林賽·斯通布里奇(Lyndsey Stonebridge)的呼應(yīng),在她看來(lái),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通過(guò)“從精神分析與文學(xué)的角度來(lái)解讀創(chuàng)傷,使人文學(xué)科得以與歷史創(chuàng)傷重新連接,而不(可能)會(huì)陷入一種天真的歷史主義的陷阱中。”(Stonebridge 26)2. 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現(xiàn)狀
上世紀(jì)90年代初,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隨著凱茜·卡魯思、肖莎娜·費(fèi)爾曼、卡莉·塔爾(kali Tal)以及杰弗里·哈特曼等美國(guó)創(chuàng)傷研究者的相關(guān)研究專著的出版而產(chǎn)生,迄今已二十余年。在這二十余年里,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首先是學(xué)科重心的轉(zhuǎn)移,正如哈特曼在2003年指出的那樣,“無(wú)論如何,文學(xué)研究中的創(chuàng)傷理論已經(jīng)將注意力從病因?qū)W轉(zhuǎn)移到文學(xué)情感的效果。這一轉(zhuǎn)移,使我們有關(guān)言語(yǔ)的力量與徒勞的意識(shí)得以增強(qiáng)。”(“Trauma Within” 260)
其次是研究主題的變化:聚焦點(diǎn)由早期的猶太人大屠殺文學(xué)向包括種族與性別等在內(nèi)的日常生活暴力創(chuàng)傷文學(xué)擴(kuò)展。如2003年9月16—18日,美國(guó)布蘭迪斯大學(xué)(Brandeis University)專門舉辦了一場(chǎng)題為“大型暴力的文學(xué)回應(yīng)”(Literary Responses to Mass Violence)的研討會(huì)。會(huì)議吸引了來(lái)自非洲,中東和美國(guó)的十余名作家與學(xué)者參加。與會(huì)作家與學(xué)者圍繞三大主題展開(kāi)了討論:“文學(xué)與證言”;“國(guó)家,人口,語(yǔ)言”;以及“尋找暴力時(shí)代的話語(yǔ)。”(Hassenfeld Conference 7)
再次是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地域的擴(kuò)展。盡管90年代初部分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專著已出版,但“直到凱茜·卡魯思的《不被宣稱的經(jīng)歷》與卡莉·塔爾的《傷害的世界:閱讀創(chuàng)傷的文學(xué)》(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在1996年出版后,文學(xué)批評(píng)中的創(chuàng)傷研究領(lǐng)域才獲得了重大的關(guān)注。”(Balaev 1)因此,我們可以將上世紀(jì)90年代初至1996年視為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興起時(shí)期。上世紀(jì)90年代初到20世紀(jì)末,美國(guó)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研究重鎮(zhèn),可謂一枝獨(dú)秀。2000年,英國(guó)倫敦大學(xué)皇家霍洛威學(xué)院歷史系的大屠殺研究中心(The Holocaust Research Centre)的成立標(biāo)志著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在英國(guó)的興起,推進(jìn)了創(chuàng)傷與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的學(xué)科化發(fā)展。作為歐洲大屠殺研究的學(xué)術(shù)中心,皇家霍洛威學(xué)院也是英國(guó)唯一開(kāi)設(shè)有大屠殺研究文學(xué)碩士課程的國(guó)際型大學(xué),常年招收來(lái)自全球包括歷史、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哲學(xué)、電影與媒體研究,文化研究與社會(huì)學(xué),大屠殺與種族滅絕研究等不同領(lǐng)域的研究生。2004年,安妮·懷特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專著《創(chuàng)傷小說(shuō)》的出版將英國(guó)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與批評(píng)推向了高潮。隨后,2007年比利時(shí)根特大學(xué)成立的文學(xué)與創(chuàng)傷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uma,簡(jiǎn)稱LITRA)在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與批評(píng)史上意義重大。一方面,它是國(guó)際上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專門研究機(jī)構(gòu);另一方面,它的成立標(biāo)志著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向英美之外的歐洲國(guó)家的拓展。2010年,根特大學(xué)文學(xué)研究系的英語(yǔ)文學(xué)副教授斯德弗·克拉普斯(Stef Craps)博士成為該中心的主任。2014年,該研究中心正式更名為文化記憶研究組織(The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Initiative,簡(jiǎn)稱CMSI),以跨文化與跨學(xué)科為導(dǎo)向,以文化為中介,致力于從記憶的角度來(lái)展開(kāi)創(chuàng)傷文化與文學(xué)的研究。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領(lǐng)域的另一件大事是專業(yè)雜志《文學(xué)與創(chuàng)傷研究雜志》(The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rauma
Studies
,簡(jiǎn)稱JLTS)的創(chuàng)辦。該雜志由來(lái)自曼徹斯特城市大學(xué)的大衛(wèi)·米勒(David Miller)擔(dān)任主編,由美國(guó)的內(nèi)布拉斯加大學(xué)出版社(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負(fù)責(zé)出版發(fā)行。這一雜志的誕生標(biāo)志著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向國(guó)際型大融合的邁進(jìn)。這一點(diǎn),我們從它的編委會(huì)名單可管窺一二。不僅凱茜·卡魯思、肖莎娜·費(fèi)爾曼,安妮·懷特海德和斯德弗·克拉普斯等當(dāng)今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界的一些重量級(jí)人物都是其編委會(huì)成員,甚至特里·伊格爾頓也名列其中。作為同行評(píng)議的,一年兩期的雜志,《文學(xué)與創(chuàng)傷研究雜志》致力于從批評(píng)的、理論的和方法論的角度出發(fā)來(lái)探討文學(xué)與創(chuàng)傷的關(guān)系。其目的在于培養(yǎng)哲學(xué)、精神分析與文學(xué)批評(píng)間的一種廣闊的質(zhì)疑性對(duì)話,并為文學(xué)中的創(chuàng)傷與文學(xué)的創(chuàng)傷研究開(kāi)發(fā)新的研究方法。雜志的使命是鼓勵(lì)那些以文學(xué)為基點(diǎn),以哲學(xué)、政治與歷史為導(dǎo)向來(lái)探索創(chuàng)傷的一切形式與表現(xiàn)的研究。此外,隨著新的研究方法出現(xiàn),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發(fā)展日益多元化。大致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其一,新的創(chuàng)傷研究模式挑戰(zhàn)了經(jīng)典模式以普遍性特征與效果來(lái)定義創(chuàng)傷的統(tǒng)治原則。一些諸如萊斯(Ruth Leys)和茨維特科維奇(Cvetkovich)這樣的批評(píng)家建立了一種有別于經(jīng)典模式的心理學(xué)框架,從而得出了創(chuàng)傷對(duì)語(yǔ)言、感知與社會(huì)的影響的不同結(jié)論。這種新的創(chuàng)傷研究不扎根于傳統(tǒng)方法,而是“從一個(gè)定義創(chuàng)傷的不同的心理學(xué)起點(diǎn)出發(fā),這將允許批評(píng)家對(duì)創(chuàng)傷的特殊性與記憶的過(guò)程進(jìn)行一種重新的聚焦”(Balaev 2)。其二,許多運(yùn)用精神分析與符號(hào)學(xué)理論的最新創(chuàng)傷批評(píng)重構(gòu)了我們對(duì)文學(xué)中的創(chuàng)傷功能的理解。通過(guò)聚焦于修辭學(xué)的、符號(hào)學(xué)的以及創(chuàng)傷的社會(huì)含義,當(dāng)代批評(píng)家開(kāi)發(fā)出了新拉康式、新弗洛伊德式以及新符號(hào)學(xué)的創(chuàng)傷研究方法。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中的這一變化已經(jīng)衍生出了一系列聚焦于創(chuàng)傷體驗(yàn)特定的社會(huì)成分與文化語(yǔ)境的批評(píng)實(shí)踐。許多從事創(chuàng)傷的修辭性成分研究的批評(píng)家通過(guò)將精神分析理論與后殖民理論或文化研究相結(jié)合,來(lái)探索文學(xué)是如何以及為何反映創(chuàng)傷體驗(yàn)的。例如,批評(píng)家羅斯伯格和富德(Forter)是從新弗洛伊德以及后殖民主義的理論框架來(lái)展開(kāi)研究的。批評(píng)家盧克赫斯特、曼德?tīng)?Mandel)、耶格爾(Yaeger)和維瑟(Irene Visser)則是在“不同的理論框架之內(nèi)從事創(chuàng)傷的社會(huì)與政治含意的研究”(Balaev 2-3)。總之,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已經(jīng)由早期的精神分析的方法轉(zhuǎn)向一個(gè)理論性的方位。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某種程度上由那些人們所熟知的精神分析,文化研究與后殖民理論的跨學(xué)科方法而引起的議題、問(wèn)題以及結(jié)果”(Balaev 5)。
三、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反思與展望
隨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由將創(chuàng)傷想象為不可言說(shuō)的初期階段轉(zhuǎn)向了一種吸納了文學(xué)的多樣化描述與文化的深遠(yuǎn)影響的多元化創(chuàng)傷觀。與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多樣化理論模式與批評(píng)實(shí)踐相對(duì)應(yīng)的是,對(duì)創(chuàng)傷的不可言說(shuō)這一單片式概念的質(zhì)疑與檢測(cè)成為當(dāng)前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研究的一項(xiàng)重要工作,它展示了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領(lǐng)域不斷拓展的邊界,釋放了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無(wú)限的闡釋潛能。
對(duì)創(chuàng)傷不可言說(shuō)論的經(jīng)典模式的質(zhì)疑主要集中于對(duì)其主要倡導(dǎo)者卡魯思的質(zhì)疑與批判。2000年,露絲·萊斯在《創(chuàng)傷:一種系譜學(xué)》一書(shū)中指出,由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概念主導(dǎo)的創(chuàng)傷研究模式,其主要危害在于“抹殺了受害者與作惡者之間的區(qū)別”(Hinrichsen 607)。總體而言,對(duì)卡魯思的經(jīng)典創(chuàng)傷模式的批判與反思主要有三類。一是通過(guò)摧毀卡魯思的理論得以建構(gòu)的臨床心理學(xué)研究基礎(chǔ)來(lái)質(zhì)疑經(jīng)典創(chuàng)傷模式的合理性,進(jìn)而推出可能的替代模式;一是直接批駁卡魯思的觀點(diǎn)進(jìn)而指出其理論的不足之處;一是以卡魯思為中心,立足整個(gè)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研究界,分析當(dāng)前的困境,探索可能性出路。這三類研究中,對(duì)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經(jīng)典模式最具殺傷力的是第一類,即源自臨床心理學(xué)的創(chuàng)傷研究。
2003年,哈佛大學(xué)心理學(xué)系的理查德·麥克納利(Richard McNally)出版了《記住創(chuàng)傷》(Remembering
Trauma
)一書(shū)。這一新的研究成果被廣泛認(rèn)為是射向創(chuàng)傷研究這艘巨輪之上的一記炮彈,被那些有志于質(zhì)疑創(chuàng)傷研究的經(jīng)典模式的人稱為一部“懷疑主義者的圣經(jīng)”(Brewin 148),成為創(chuàng)傷研究者的必讀書(shū)籍。在該書(shū)中,麥克納利的中心論點(diǎn)可總結(jié)為:創(chuàng)傷遺忘是一個(gè)神話,當(dāng)受害者可能選擇
(choose)不訴說(shuō)他們的創(chuàng)傷時(shí),幾乎沒(méi)有證據(jù)表明他們不能
(cannot)訴說(shuō)。由于麥克納利在書(shū)中對(duì)卡魯思建構(gòu)其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臨床心理學(xué)基礎(chǔ)——范·德·科爾克與赫爾曼的觀點(diǎn)提出了質(zhì)疑,所以該書(shū)也被認(rèn)為“為針對(duì)卡魯思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批評(píng)奠定了基礎(chǔ)。”(Pederson 334)除了提供了一些“針對(duì)創(chuàng)傷記憶理論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片斷的簡(jiǎn)潔的、令人信服的反撥”(336)外,麥克納利的著作還“摧毀了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的文學(xué)理論的兩個(gè)十分重要的原則:創(chuàng)傷記憶‘不被記錄’或‘不被宣稱’的觀念,以及創(chuàng)傷記憶逃避徑直的口頭再現(xiàn)的想法。”(336)具體而言,麥克納利一方面摧毀了范·德·科爾克的創(chuàng)傷健忘癥的概念——他的創(chuàng)傷記憶不被記錄的看法。麥克納利認(rèn)為,這種斷言沒(méi)有被實(shí)證研究所證實(shí)——甚至不被范·德·科爾克自己的研究證實(shí)。創(chuàng)傷健忘癥的支持者們將一種不愿意思考創(chuàng)傷的行為與一種無(wú)法思考創(chuàng)傷的行為等同。另一方面,麥克納利也對(duì)創(chuàng)傷記憶不能用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的觀點(diǎn)提出了質(zhì)疑,他用研究表明,“創(chuàng)傷受害者不僅能記住,也能詳細(xì)描述他們的創(chuàng)傷的過(guò)去。”(338)范·德·科爾克和赫爾曼的臨床研究結(jié)論的顛覆,意味著以此為基礎(chǔ)的卡魯思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合理性受到了質(zhì)疑。正如佩德森所言:“假如麥克納利的著作挑戰(zhàn)了對(duì)第一波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科學(xué)數(shù)據(jù),那么這一領(lǐng)域的批評(píng)家應(yīng)該要適當(dāng)看待他的理論。”(Pederson 334)以麥克納利的研究為契機(jī),佩德森提出了所謂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新模式。他將這一模式概括為三條原則。
第一,“從事文學(xué)中的創(chuàng)傷研究的批評(píng)家應(yīng)該將他們的關(guān)注點(diǎn)由文本的空缺轉(zhuǎn)向文本本身。”(Pederson 338)由于第一代創(chuàng)傷理論家們認(rèn)同創(chuàng)傷無(wú)法言說(shuō)的觀點(diǎn),他們?cè)陂喿x中被文本的空隙所吸引。他們以空想家的姿態(tài)來(lái)搜索事物無(wú)法被言說(shuō)的文本證據(jù)。約書(shū)亞·佩德森(Joshua Pederson)認(rèn)為,由于“麥克納利的研究認(rèn)為創(chuàng)傷記憶既是可以記憶的也是可以言說(shuō)的,因此,新一代的創(chuàng)傷理論家應(yīng)該既強(qiáng)調(diào)創(chuàng)傷記憶的可及性,也強(qiáng)調(diào)受害者建構(gòu)創(chuàng)傷記憶的可靠描述的可能性,應(yīng)該將他們的注意力遠(yuǎn)離文本缺口而朝向?qū)嶋H文本。這種新的方法將為闡釋開(kāi)發(fā)新的廣闊的材料區(qū)域。”(338)此外,這一方法還能帶來(lái)兩大額外益處。其一,它使我們遠(yuǎn)離了具有潛在危害的創(chuàng)傷健忘癥理論。其二,受害者的創(chuàng)傷的文本敘述具有治愈的力量。
第二,“創(chuàng)傷理論家應(yīng)該找出文本中那些增強(qiáng)的敘述細(xì)節(jié)的證據(jù)。”(Pederson 339)新的研究表明創(chuàng)傷事實(shí)上可能會(huì)加強(qiáng)記憶,而非妨礙或消除它。“情感壓力強(qiáng)化記憶是壓力化經(jīng)歷的中心特征。壓力不會(huì)損害記憶,而是加強(qiáng)它。”(McNally 62)創(chuàng)傷記憶并不是易忘的或缺席的,它們有可能比正常記憶更詳細(xì)且更強(qiáng)大。而且,創(chuàng)傷記憶通常是多維感知的,受害者可能不僅通過(guò)視覺(jué),也通過(guò)聽(tīng)覺(jué)、嗅覺(jué)、觸覺(jué)和味覺(jué)提示來(lái)記錄它。麥克納利的這一發(fā)現(xiàn)為創(chuàng)傷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從文本本身去探尋創(chuàng)傷再現(xiàn)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科學(xué)依據(jù)。
第三,“創(chuàng)傷理論家應(yīng)該關(guān)注那些在時(shí)間上,物理上或存在論上被扭曲的經(jīng)歷的描述。”(Pederson 339)這是因?yàn)椋芎φ叩膭?chuàng)傷記憶得以加強(qiáng)的同時(shí),這些記憶可能被改變,即所謂的“意識(shí)中的游離變化(時(shí)間放慢,一切看起來(lái)不真實(shí))。”(McNally 182)簡(jiǎn)言之,一個(gè)人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會(huì)以種種方式被扭曲地感覺(jué)到。這種情況下,“文學(xué),也許最有說(shuō)服力的是現(xiàn)代文學(xué),——能捕捉到這一情況下的效果。因此,那些在文學(xué)中尋找創(chuàng)傷的批評(píng)家應(yīng)該使自己與文本中喚起的困惑,空間與時(shí)間的變化,親身的經(jīng)歷,以及一種總體上的不真實(shí)感合拍。創(chuàng)傷不能抹去記憶,但它可能歪曲它,這種扭曲的文本描述可能為我們?cè)谖膶W(xué)中辨認(rèn)創(chuàng)傷的效果提供線索。”(Pederson 340)總的來(lái)看,佩德森在麥克納利的臨床創(chuàng)傷心理學(xué)基礎(chǔ)上提出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的新模式更多的是一種文學(xué)創(chuàng)傷的批評(píng)策略與方法,而非一種文學(xué)創(chuàng)傷的理論性闡釋與建構(gòu)。
隨著多元化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方法的實(shí)施,卡魯思的經(jīng)典創(chuàng)傷模式遭到了更直接的質(zhì)疑。研究者指出,首先,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起初不被人知曉”以及創(chuàng)傷“過(guò)后返回去纏擾幸存者”這一論斷將創(chuàng)傷的心理維度與創(chuàng)傷經(jīng)歷與反應(yīng)的范圍狹隘地概念化了。它將創(chuàng)傷與離解之間的關(guān)系視為固有的因果聯(lián)系,即一次極端的經(jīng)歷直接導(dǎo)致一種過(guò)去的真相隱藏其中的離解意識(shí)的產(chǎn)生,這種觀點(diǎn)成為卡魯思的這一論斷的重要支撐。事實(shí)上,“心理學(xué)研究表明,失憶、離解,或壓抑可能是創(chuàng)傷的反應(yīng),但它們并非創(chuàng)傷所專有的反應(yīng)。”(Balaev 6)
其次,伴隨著對(duì)將創(chuàng)傷界定為一種延期的,復(fù)發(fā)的傷害這一定義的依賴,經(jīng)典創(chuàng)傷模式的另一問(wèn)題在于,創(chuàng)傷的這種公式化表述去除了創(chuàng)傷經(jīng)歷中的確定價(jià)值。創(chuàng)傷經(jīng)典模式的理論二元制圍繞著一個(gè)假定矛盾旋轉(zhuǎn):“我們?cè)诮^無(wú)可能認(rèn)知某件暴力事件時(shí),對(duì)它的最直接的親歷才可能發(fā)生。”(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
92)這一觀點(diǎn)在修辭學(xué)、心理學(xué)及社會(huì)層面否認(rèn)了創(chuàng)傷的具體確定性,與此同時(shí),欣然接受了病理學(xué)對(duì)意識(shí)的永恒影響這一觀點(diǎn)。通過(guò)忽視幸存者的經(jīng)歷與自我的認(rèn)知,創(chuàng)傷的經(jīng)典模式的結(jié)果之一是剝奪了幸存者對(duì)創(chuàng)傷的能動(dòng)作用,這就限制了創(chuàng)傷的可變性并忽視了隨著時(shí)間而變化的不同的價(jià)值。事實(shí)上,“由于對(duì)創(chuàng)傷的特征的關(guān)注并未排斥創(chuàng)傷的體驗(yàn)與回憶中呈現(xiàn)了社會(huì)、語(yǔ)義、政治以及經(jīng)濟(jì)因素這一事實(shí),如果影響暴力的更大型的社會(huì)、政治以及經(jīng)濟(jì)實(shí)踐起初是創(chuàng)傷經(jīng)歷的背景語(yǔ)境或穿插在它的構(gòu)造中,那么創(chuàng)傷的意義就是可定位的,而非永久性喪失。”(Balaev 6-8)最后,創(chuàng)傷理論經(jīng)典模式的另一局限在于它遠(yuǎn)離了創(chuàng)傷的鮮活體驗(yàn)這一事實(shí)。卡魯思的創(chuàng)傷無(wú)法言說(shuō)論是以遺忘這一事實(shí)——?jiǎng)?chuàng)傷是在特定的時(shí)間與地點(diǎn),發(fā)生在特定團(tuán)體中的真實(shí)的人們身上為代價(jià)的。她的“創(chuàng)傷從未僅是某人自己的”以及“我們被牽連到彼此的創(chuàng)傷中”(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
, 24)的斷言導(dǎo)致了涉及暴力的責(zé)任的分配以及了解直接行為與間接行為間的關(guān)系等問(wèn)題的出現(xiàn)。將每個(gè)人都包括在創(chuàng)傷的受害者之內(nèi)的企圖也承擔(dān)著將每個(gè)人都包括在行兇者之內(nèi)的風(fēng)險(xiǎn)。這種斷言客觀上將創(chuàng)傷的經(jīng)歷普遍化以及將暴力的教唆者集體化,這兩種結(jié)果都有助于使暴力的施行者與接受者變得匿名。這就“合并了事物的因果,由此也隱藏了責(zé)任與權(quán)力的問(wèn)題。”(Balaev 7)以斯德弗·克拉普斯為代表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研究者立足整體,對(duì)卡魯思的經(jīng)典創(chuàng)傷模式及當(dāng)前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與批評(píng)提出了質(zhì)疑與反思。這些反思主要聚焦于以下幾方面。
首先,包括卡魯思的作品在內(nèi),已有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奠定性文本大多忽視了創(chuàng)傷的差異性特點(diǎn),沒(méi)有結(jié)合創(chuàng)傷產(chǎn)生的具體情況來(lái)區(qū)分我們對(duì)創(chuàng)傷的不同理解,反而將在西方的現(xiàn)代歷史中形成的創(chuàng)傷定義的普遍有效性視為理所當(dāng)然。如今,創(chuàng)傷的概念被廣泛用來(lái)描述人們對(duì)那些跨越了時(shí)間與空間的極端事件的反應(yīng),并引導(dǎo)它們的處理。然而,正如艾倫·揚(yáng)(Allan Young)在其《幻想的和諧:發(fā)明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Inventing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1995)一書(shū)中提醒我們的那樣,創(chuàng)傷事實(shí)上是一個(gè)西方的人工制品,“發(fā)明”于19世紀(jì)晚期。它的起源可以“定位于各種涉及歐洲與美國(guó)的工業(yè)化經(jīng)歷,性別關(guān)系以及現(xiàn)代戰(zhàn)爭(zhēng)的醫(yī)學(xué)與心理學(xué)的話語(yǔ)。”(Young 5)這一事實(shí)表明創(chuàng)傷的西方定義并非可以不成問(wèn)題地被出口到別的環(huán)境中。盡管如此,“創(chuàng)傷根植于一個(gè)特別的歷史與地理語(yǔ)境的這一事實(shí)的深遠(yuǎn)內(nèi)涵被學(xué)術(shù)研究者,包括那些為社會(huì)弱勢(shì)群體承受的精神痛苦的公共認(rèn)可而戰(zhàn)的積極分子學(xué)者長(zhǎng)期忽視。”(Craps 53)除了形成于特定歷史背景外,創(chuàng)傷的這種異質(zhì)性特點(diǎn)表明它并非鐵板一塊,那種將創(chuàng)傷作為一種單一的、統(tǒng)一的、永恒的以及普遍現(xiàn)象的觀點(diǎn)顯然是錯(cuò)謬的。因此,在具體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中,我們應(yīng)該“考慮到創(chuàng)傷敘述產(chǎn)生與接受的特殊的社會(huì)與歷史環(huán)境,樂(lè)于接受并留意這些環(huán)境所招致或需要的再現(xiàn)的不同阻力與策略。”(Buelens, Sam, and Robert 51)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對(duì)創(chuàng)傷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忽視一定程度與主導(dǎo)的創(chuàng)傷概念將創(chuàng)傷視為一種個(gè)體現(xiàn)象,缺少對(duì)更廣闊的社會(huì)背景的關(guān)注有關(guān)。由于較狹窄地關(guān)注于個(gè)體精神層面,研究者通常對(duì)導(dǎo)致創(chuàng)傷產(chǎn)生的社會(huì)條件不予質(zhì)疑,如種族主義,經(jīng)濟(jì)控制或政治壓迫,那些本來(lái)是政治或經(jīng)濟(jì)的問(wèn)題被醫(yī)學(xué)化了。此外,由于創(chuàng)傷理論繼續(xù)堅(jiān)持傳統(tǒng)的基于事件之上(創(chuàng)傷是一件單一的,反常的災(zāi)難性事件的結(jié)果)的創(chuàng)傷模式,隨之而來(lái)的是創(chuàng)傷理論提供的概念框架無(wú)法對(duì)現(xiàn)有的種族主義與其他形式的壓迫所造成的創(chuàng)傷影響進(jìn)行充分地描述。這就涉及當(dāng)前的創(chuàng)傷研究存在的另一問(wèn)題。
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對(duì)創(chuàng)傷的異質(zhì)性的忽視還與它的西/非西方這種本質(zhì)上屬于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創(chuàng)傷的二分法有關(guān),這也是當(dāng)前的創(chuàng)傷研究中存在的第二大問(wèn)題。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創(chuàng)傷研究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是將出現(xiàn)于西方文化語(yǔ)境下的創(chuàng)傷概念及其外延作為創(chuàng)傷的唯一模式進(jìn)行全球化推廣,與之相應(yīng)地忽視非西方或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如當(dāng)今的創(chuàng)傷研究界對(duì)猶太人大屠殺的聚焦,以及對(duì)包括中國(guó)的南京大屠殺在內(nèi)的亞非拉美地區(qū)的創(chuàng)傷問(wèn)題的冷漠乃至忽視就很能說(shuō)明這一點(diǎn)。這種唯西方創(chuàng)傷是從,以猶太大屠殺為中心的創(chuàng)傷研究形式的后果在于“往往會(huì)掩蓋全球創(chuàng)傷的異質(zhì)性特點(diǎn)。”(Buelens, Sam, and Robert 64)因此,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創(chuàng)傷研究者不僅“需要擴(kuò)寬創(chuàng)傷理論的通常的聚焦點(diǎn),也應(yīng)該承認(rèn)那些非西方或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創(chuàng)傷。”(48)這就將非西方語(yǔ)境下創(chuàng)傷概念及其相關(guān)理論的建構(gòu)提上了日程。
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chǎng)也衍生出對(duì)于處于男/女,白人/非白人以及下層/上層等二元對(duì)立中的弱勢(shì)群體創(chuàng)傷及其話語(yǔ)的忽視。據(jù)塔爾考證,“有關(guān)創(chuàng)傷的文學(xué)批評(píng)著作主要由那些特權(quán)階層的成員為他們自己創(chuàng)作的——它們基于那個(gè)階層的假設(shè)并復(fù)制階層成員們的缺陷。[……]沒(méi)有哪本有關(guān)創(chuàng)傷與記憶的書(shū)吸收了一位非裔美國(guó)批評(píng)思想家的著作或理論。它們很少提及那些處于直接的創(chuàng)傷與記憶的批評(píng)書(shū)寫圈之外的女性主義理論家的著作。近20年來(lái)產(chǎn)生的后殖民理論的主體被創(chuàng)傷學(xué)者們徹底忽視。考慮到少數(shù)族裔作家和婦女對(duì)創(chuàng)傷、記憶、沉默和離解問(wèn)題的關(guān)注,這種忽視,盡管可能不是故意的,也是令人迷惑的。”(Tal 86)為此,塔爾呼吁,有必要“通過(guò)介紹非裔美國(guó)作家和女性主義批評(píng)理論的一些元素,對(duì)由白人批評(píng)家得出的關(guān)于記憶與創(chuàng)傷的結(jié)論提出質(zhì)疑。”(86)塔爾的提醒可謂切中肯綮,這也正是當(dāng)前的創(chuàng)傷研究界亟需解決的問(wèn)題。
對(duì)創(chuàng)傷認(rèn)定的簡(jiǎn)單化,以及對(duì)創(chuàng)傷的再現(xiàn)與敘述的單一化與片面化是當(dāng)前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存在的另一重大問(wèn)題。首先,隨著創(chuàng)傷研究的推進(jìn),創(chuàng)傷的認(rèn)定會(huì)更加復(fù)雜。畢竟,創(chuàng)傷并非是對(duì)所有的暴力與苦難的最佳描述,即便那些我們確認(rèn)為創(chuàng)傷的事物通常也伴隨著許多其他形式的暴力與苦難。同時(shí),創(chuàng)傷的認(rèn)定會(huì)更加多元化。一些原本不在創(chuàng)傷的范疇之內(nèi)的事物也可能被認(rèn)定為創(chuàng)傷。如過(guò)度開(kāi)發(fā)和生態(tài)毀壞也可以是創(chuàng)傷的,必定能間接導(dǎo)致各種創(chuàng)傷,但它們的實(shí)質(zhì)也同樣復(fù)雜(Buelens, Sam, and Robert xvii)。其次,一些有關(guān)文學(xué)見(jiàn)證創(chuàng)傷的觀點(diǎn)與假設(shè)也應(yīng)該得到修正。現(xiàn)有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者通常“偏愛(ài)或甚至規(guī)定唯一勝任見(jiàn)證創(chuàng)傷工作的是一種現(xiàn)代主義的碎片與困惑美學(xué)。”(46)他們持有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只能通過(guò)實(shí)驗(yàn)性的、現(xiàn)代主義的文本策略才能被充分表現(xiàn)的觀念。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當(dāng)一次經(jīng)歷超越了已有敘述知識(shí)的可能性,它最好能以一種失敗的敘述表現(xiàn)出來(lái)。因此,這里呼喚的是對(duì)傳統(tǒng)再現(xiàn)模式的打破,比如那些在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中找到的表現(xiàn)形式。這一假設(shè)的結(jié)果是可能會(huì)導(dǎo)致一種狹隘的創(chuàng)傷經(jīng)典的建立,現(xiàn)代主義畢竟是“一種歐洲的文化傳統(tǒng),它們是主要由西方作家創(chuàng)作的,非線性的現(xiàn)代主義文本。”(50)顯然,這種現(xiàn)代主義審美規(guī)約下的創(chuàng)傷經(jīng)典,注定難逃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的宿命。
在實(shí)現(xiàn)對(duì)創(chuàng)傷的歐洲-美國(guó)研究中心的超越后,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終將走向何方?有學(xué)者指出:“文學(xué)批評(píng)中創(chuàng)傷理論的演變最好從變化著的創(chuàng)傷心理學(xué)的定義和符號(hào)學(xué)、修辭學(xué)以及文學(xué)與社會(huì)中作為創(chuàng)傷研究的組成部分的社會(huì)問(wèn)題的角度來(lái)理解。”(Balaev 2)這一論斷某種程度上準(zhǔn)確地描繪了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的發(fā)展脈絡(luò)。隨著創(chuàng)傷研究對(duì)后殖民文學(xué)的介入,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的未來(lái)走向也日益明朗化。有關(guān)創(chuàng)傷理論與后殖民文學(xué)研究關(guān)系的討論始自《小說(shuō)研究》(Studies
in
the
Novel
)雜志于2008年發(fā)行的春/夏特輯。該期初步完成了創(chuàng)傷理論與后殖民文學(xué)理論間的“友好建交”。2010年4月,奧地利維也納大學(xué)舉辦了一場(chǎng)有關(guān)當(dāng)代南非小說(shuō)創(chuàng)傷,記憶與敘述的研討會(huì)。與會(huì)批評(píng)家與學(xué)者們就創(chuàng)傷理論能否與后殖民文學(xué)研究實(shí)現(xiàn)有效的結(jié)合進(jìn)行了激烈的討論。這場(chǎng)討論預(yù)見(jiàn)了創(chuàng)傷理論的復(fù)雜性與爭(zhēng)議性的前景,同時(shí)也認(rèn)真地論證了它對(duì)后殖民文學(xué)研究的闡釋價(jià)值。此外,以杰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和羅恩·艾爾曼(Ron Eyerman)為代表的美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的研究成果為“處于主導(dǎo)地位的后結(jié)構(gòu)主義-精神分析的創(chuàng)傷理論提供了另一選擇。”(Khadem 146)亞歷山大等人所倡導(dǎo)的文化創(chuàng)傷理論因“創(chuàng)傷的社會(huì)文化建構(gòu)”以及“集體創(chuàng)傷”等理念而備受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者,尤其是后殖民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者的推崇。文化創(chuàng)傷的核心思想是:“創(chuàng)傷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一種被社會(huì)建構(gòu)起的事物。”(Alexander 7)作為文化創(chuàng)傷的研究對(duì)象,集體創(chuàng)傷在文化創(chuàng)傷研究中處于絕對(duì)的核心。文化創(chuàng)傷的這一核心特征成為它與后殖民創(chuàng)傷文學(xué)研究結(jié)緣的重要促成因素。在2010年的一篇有關(guān)后殖民創(chuàng)傷的論文中,斯德弗·克拉普斯指出,后殖民創(chuàng)傷“往往是集體的經(jīng)歷,而在傳統(tǒng)上,創(chuàng)傷研究聚焦于個(gè)體的不幸。[……]創(chuàng)傷研究的對(duì)象必須從個(gè)體轉(zhuǎn)移到更廣大的社會(huì)實(shí)體,比如社區(qū)和國(guó)家。拒絕由個(gè)體精神轉(zhuǎn)向社會(huì)情境只會(huì)產(chǎn)生有害的后果。”(Craps 55)2012年,在其《后殖民見(jiàn)證:越界的創(chuàng)傷》一書(shū)中,克拉普斯再次指出,目前的后殖民文學(xué)研究呼喚一種閱讀、理解以及闡釋創(chuàng)傷的新模式,它將提供閱讀集體創(chuàng)傷的方法。這種新模式的學(xué)科歸屬主要是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學(xué),這是因?yàn)椋坝捎谒鼈冊(cè)趯⒋蟊姷纳鐣?huì)反應(yīng)理論化方面的強(qiáng)大傳統(tǒng),它們那面對(duì)集體創(chuàng)傷的理論也更杰出。”(Balaev 108)凱瑟琳·巴克斯特(Katherine Baxter)也指出,創(chuàng)傷理論的一種社會(huì)學(xué)框架可以“回應(yīng)當(dāng)前后殖民文學(xué)研究中反思并解決專一性與綜合化要求之間的持續(xù)性張力這一需要。”(Balaev 108)荷蘭格羅寧根(Groningen)大學(xué)英語(yǔ)語(yǔ)言與文化系從事現(xiàn)代英語(yǔ)文學(xué)研究的艾琳·維瑟認(rèn)為,創(chuàng)傷研究被認(rèn)為是“當(dāng)今最顯著的文化范式之一。在20世紀(jì)90年代早期,文化與文學(xué)批評(píng)接受了由杰弗里·哈特曼等創(chuàng)傷理論家提出的(創(chuàng)傷理論對(duì)文學(xué)的)新的闡釋潛力的希望,[……]自那以后,文化創(chuàng)傷理論日益被當(dāng)作一種文學(xué)實(shí)踐的理論性框架來(lái)運(yùn)用。”(Visser 270)同時(shí),由于“文學(xué)在社會(huì)學(xué)家杰弗里·亞歷山大所說(shuō)的‘創(chuàng)傷過(gu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Balaev 110),因此,“在后殖民創(chuàng)傷的社會(huì)文化建構(gòu)中,后殖民文學(xué)是創(chuàng)傷過(guò)程的一個(gè)貢獻(xiàn)主力。然后,在后殖民文學(xué)批評(píng)中,一個(gè)重要的進(jìn)展是在社會(huì)群體中標(biāo)畫(huà)出創(chuàng)傷、權(quán)力與意識(shí)形態(tài)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正如一些批評(píng)家指出的那樣,為了能充分地與文學(xué)銜接,作為一個(gè)必要且新的視角,創(chuàng)傷理論必須向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開(kāi)放。”(Balaev 111)
誠(chéng)然,文化創(chuàng)傷對(duì)“集體創(chuàng)傷”與創(chuàng)傷的“社會(huì)建構(gòu)性”的關(guān)注因契合了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中的后殖民文學(xué)批評(píng)而備受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者的青睞。接下來(lái)我們要思考并解決的問(wèn)題是,作為一種新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研究模式,文化創(chuàng)傷這一社會(huì)學(xué)理論是否對(duì)后殖民文學(xué)之外的創(chuàng)傷文學(xué)研究適用?文化創(chuàng)傷又是經(jīng)過(guò)哪些途徑,采取哪些方式,運(yùn)用哪些機(jī)制來(lái)實(shí)現(xiàn)其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傷的有效性闡釋的?或許,對(duì)文化創(chuàng)傷理論自身的詩(shī)學(xué)特質(zhì)的挖掘正是我們實(shí)現(xiàn)其對(duì)于文學(xué)創(chuàng)傷闡釋的有效性的理論前提與必要準(zhǔn)備。
注釋[Notes]
① 如創(chuàng)傷研究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哈特曼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所謂的‘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PTSD)以及它跟越戰(zhàn)老兵的經(jīng)驗(yàn)的關(guān)系終于被承認(rèn)了,這在1980年前夕引起了重視。如果我們一定要找出美國(guó)的創(chuàng)傷研究的根源,那我們必須提到這一點(diǎn)。”(謝瓊69)
② 在提及大屠殺幸存者證言檔案庫(kù)時(shí),哈特曼坦承:“這個(gè)檔案確實(shí)能實(shí)現(xiàn)它的那些目的,也理所當(dāng)然地幫助了創(chuàng)傷研究,盡管它背后并沒(méi)有某種創(chuàng)傷理論的支持。此后,當(dāng)然杜里·勞伯和蘇珊娜·費(fèi)爾曼寫出了他們關(guān)于證言和創(chuàng)傷之間復(fù)雜關(guān)系的著作,卡西·卡魯思也寫了自己的書(shū),等等。事情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發(fā)展下去了。”(謝瓊69)
③ 哈特曼等人并未采用“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提法,這一提法的出現(xiàn)是近幾年的事,如2014年,Michelle Balaev主編的《文學(xué)創(chuàng)傷理論的當(dāng)代方法》(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uma
Theory
)一書(shū)即采用了這一提法。④ 創(chuàng)傷研究對(duì)大屠殺與戰(zhàn)爭(zhēng)等激烈人為暴行的側(cè)重與美國(guó)精神病協(xié)會(huì)對(duì)“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PTSD)的界定有一定關(guān)系。這一點(diǎn)也為卡魯思所詬病,這是因?yàn)椋坝擅绹?guó)精神病協(xié)會(huì)所界定的“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PTSD)中所謂的創(chuàng)傷事件必須是‘人類(日常)經(jīng)歷之外’的例外事件的說(shuō)法使得創(chuàng)傷將女性受創(chuàng)群體排除在外。這是因?yàn)椋捎趮D女的性虐在北美日常生活中比較常見(jiàn),沒(méi)有超越‘人類經(jīng)歷之外’。”參見(jiàn)Cathy Caruth, ed.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01.⑤ 這并非意味著創(chuàng)傷概念不能用于闡釋非西方的創(chuàng)傷性事件,由于現(xiàn)有的創(chuàng)傷概念主要是西方文化歷史語(yǔ)境之下的產(chǎn)物,因此它對(duì)于非西方文化語(yǔ)境下的創(chuàng)傷事件并不具有闡釋的普遍適用性。而且,就當(dāng)前的創(chuàng)傷研究而言,盡管廣島和長(zhǎng)崎的原子彈事件等東方創(chuàng)傷事件已進(jìn)入部分研究者的視野,但創(chuàng)傷研究的主體對(duì)象始終聚焦于以猶太大屠殺和美國(guó)越戰(zhàn)等為代表的西方歷史文化語(yǔ)境與事件。
⑥ 如杰弗里·亞歷山大認(rèn)為,“如果創(chuàng)傷理論局限于對(duì)西方社會(huì)生活的提及,這將是一個(gè)很嚴(yán)重的誤解。的確,正是西方社會(huì)最近提供了針對(duì)他們的國(guó)族史上的創(chuàng)傷事件的最戲劇性的辯解。但正是世界的非西方地區(qū),連同他們中的那些最無(wú)防御性的人們?cè)馐芰艘恍┳羁植赖膭?chuàng)傷傷害。”(Alexande 28)基于這種理念,亞歷山大試圖將文化創(chuàng)傷發(fā)展為一種對(duì)東西方創(chuàng)傷事件具有同樣的闡釋效果的通用型理論,從而遭致了創(chuàng)傷研究界同行的詬病,“不幸的是,亞歷山大、艾爾曼及其同事的睿智的介入(聲稱他們的研究是認(rèn)識(shí)論的一次嚴(yán)格的訓(xùn)練),使得創(chuàng)傷研究放棄了對(duì)道德或社會(huì)責(zé)任的考量。同時(shí),他們所憑借的理論假設(shè)也是牽強(qiáng)的(且不足掛齒)。這一假設(shè)認(rèn)為,一種完全基于來(lái)自歐洲與美國(guó)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的理論之所以能夠‘被流暢自如地?cái)U(kuò)展到西方社會(huì)之外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是因?yàn)椤鞣絼?chuàng)傷的受害者不成比例的是下層階級(jí)和邊緣化群體’。”詳見(jiàn)Rebecca Saunders and Kamran Aghaie. “Introduction: Mourning and Memory.”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25.1(2005):16-29,18.⑦ 具體論述見(jiàn)Toremans, Tom. “Trauma: Theory-Reading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ake of Trauma.”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7.3(2003):333-51.⑧ 〈https://pure.royalholloway.ac.uk/portal/en/organisations/holocaust-research-centre(1fbd5b1b-effc-43e3-aa41-afab77a3408a).html〉.
⑨ 〈http://www.cmsi.ugent.be/about/〉.
⑩ 〈http://www.jlts.stir.ac.uk/?page_id=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lexander, Jeffrey C.Trauma
:A
Social
Theor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特奧多·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張峰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
[Adorno, Theodor.Negative
Dialectics
. Trans. Zhang Feng.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1993.]Balaev, Michelle, ed.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uma
Theory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Brewin, Chris R. “Impossible Histories: Review ofRemembering
Traum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8. 1 (2005): 148-52.Buelens, Gert, Sam Durrant, and Robert Eaglestone, eds.The
Future
of
Trauma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Caruth, 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Caruth, Cathy, and Geoffrey Hartman. “An Interview with Geoffrey Hartman.”Studies
in
Romanticism
35.4 (1996): 630-52.Craps, Stef. “Wor(l)ds of Grief: Traumatic Memory and Literary Witnessing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Textual
Practice
24. 1 (2010): 51-68.Edkins, Jenny.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Felman, Shoshana.The
Juridical
Unconscious
:Trials
and
Traum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M. D.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Hartman, Geoffrey.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New
Literary
History
26.3 (1995): 537-63.- - -. “Trauma Within the Limits of Literature.”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7.3 (2003): 257-74.Hinrichsen, Lisa. “Trauma Studies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U.S. South.”Literature
Compass
10.8 (2013): 605-17.Hassenfeld Conference Center Brandeis University.Literary
Responses
to
Mass
Violence
.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2003.Khadem, Amir. “Book Reviews.”College
Literature
41.4 (2014): 144-46.Koopman, Emy. “Reading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The Ethical Possibilities of ‘Empathic Unsettlement’”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4.2 (2010): 235-52.Luckhurst, Roger.The
Trauma
Question
. London: Routledge, 2008.Leys, Ruth, and Marlene Goldman. “Navigating the Genealogies of Trauma, Guilt, and Affect: An Interview with Ruth Leys.”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79.2 (2010): 656-79.McNally, Richard J.Remembering
Trauma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ederson, Joshua. “Speak, Trauma: Toward a Revis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rauma Theory.”Narrative
22.3 (2014): 333-53.Ramadanovic, Petar. “Introduction: Trauma and Crisis.”Postmodern
Culture
11.2 (2001): 1-11.Scarry, Elaine.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Stonebridge, Lyndsey. “Bombs and Roses: The Writing of Anxiety in Henry Green’sCaught
.”Diacritics
28.4 (1998): 25-43.Tal, Kali.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 〈http://kalital.com/Texts/Worlds/index.html〉.Visser, Irene. “Trauma Theory and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47.3 (2011): 270-82.Whitehead, Anne.Trauma
Fiction
.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Wyatt, Jean. “Storytelling, Melancholia,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Louise Erdrich’sThe
Painted
Drum
.”MELUS
:Multi
-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
.S
. 36.1 (2011): 13-36.謝瓊:“從解構(gòu)主義到創(chuàng)傷研究——杰弗里·哈特曼教授訪談”,《文藝爭(zhēng)鳴》1(2011):67—76。
[Xie, Qiong. “From Deconstruction to Trauma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Geoffrey Hartman.”Debates
of
Literary
and
Art
1 (2011): 67-76.]Young, Allan.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Inventing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