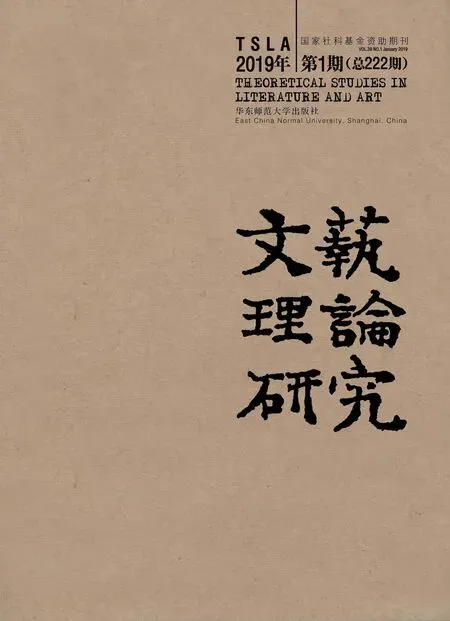蘇軾的游寺詩及其禪悟的進階
——兼論北宋文人游寺詩創作的三種類型
李舜臣 高 暢
Gao
Chang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n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of China (14BZW085), 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lassics Compilation Committee ([2014]097), and the Jiangxi Province Key Project of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佛寺,又稱伽藍、精舍、蘭若,既是彰顯宗教文化的重要場所,亦是迥異于俗世的“另類空間”。東晉以還,文人酷愛悠游佛寺,親近禪侶,抒寫禪悅風致,名篇秀句,郁起迭出,詩苑遂有“游寺詩”一門。爰至北宋,佛寺林立,文人公假尤多,自放閑適,游寺之風更顯熾盛,游寺詩數量亦度越前朝。
趙德坤、周裕鍇先生曾考察過北宋文人的游寺之風,探析了他們寺院書寫的模式及其意義,不過他們研討的對象是“散體之文”,未涉詩歌。事實上,文人佛寺文多因“僧人請托”而作,寫作行為未免帶有“他性”,而游寺詩則是詩人的主動書寫,最直觀地呈現出他們接受佛禪的心理和程度。北宋游寺詩的作者、數量相當繁復,稍具聲名者幾乎皆涉之。這其中尤以蘇軾最為典型,據現存資料統計,他至少游歷了140所寺院,游寺詩達266首,近其詩總數的十分之一。若仔細分析,蘇軾游寺詩的創作明顯存在階段性: 他居汴京前后雖達八年之久,卻只有20首;而外任鳳翔、杭州,貶謫黃州、嶺南之時,游寺最為頻繁,游寺詩數量亦最為突出。更為重要的是,這四個時期的游寺詩不僅頗為鮮明地反映了蘇軾習佛的進階,而且基本涵括了北宋文人游寺詩創作的幾種類型。
一、外任鳳翔、杭州時期:從“不知禪味深”到“久參白足知禪味”
蘇軾很早就與佛寺結有不解之緣,傳說他少時即讀書于連鰲山的棲云寺及實相寺、華藏寺。嘉祐初,蘇洵攜蘇氏兄弟進京趕考,抵澠池,“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閑之壁。”(蘇轍12)此或為蘇軾的第一首游寺詩,可惜后來“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97)嘉祐五年二月,蘇氏兄弟隨父至京應制科考,于西岡賃一宅,常游臨近精舍。蘇轍《和子瞻宿臨安凈土寺》憶及此事曰:“昔年旅東都,局促吁已厭。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覘。每來獲所求,食飽山茶釅。塵埃就湯沐,垢膩脫巾韂。不知禪味深,但取饑腸饜。”(蘇轍70—71)末兩句表明他們只是寄食佛寺,尚不知玄遠之禪味。
蘇軾現存最早的游寺詩是他陪侍蘇洵自蜀至荊州,途經峽州時所作《寄題清溪寺》和《留題峽州甘泉寺》。王十朋將二詩歸為“寺觀類”,然前詩評鬼谷子、蘇秦、張儀的命運,后詩則憑吊姜詩之純孝,紀昀還批評說“糾纏姜詩,牽強無味。”(紀昀1857)因此,與其說它們是“游寺詩”,毋寧說是“詠史詩”。
嘉祐六年十二月,蘇軾簽判鳳翔,至治平二年二月還朝。四年間,蘇軾游歷了11所寺院,作游寺詩18首。著名的《鳳翔八觀》,乃記鳳翔“可觀者八”,其中的“三觀”即天柱寺維摩像、開元寺王維吳道子畫、真興寺閣。嘉祐七年二月,蘇軾分往屬縣減決囚禁,數日間,游寶雞龍宮寺,題詩于中興寺、郿縣橫渠鎮崇壽院;次年七月,禱雨磻溪,先宿僧舍僧閣,又宿青峰寺下院翠麓亭,再宿南山蟠龍寺。鳳翔期間,蘇軾對佛寺產生了一定的興趣,嘉祐七年重陽節,他甚至不預府會而獨自出游普門寺。因此,梁銀林先生說:“敘寫佛寺之作,成為他鳳翔期間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這些詩歌實際與佛教關系并不密切,像《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題畫文殊、普賢》,著重描寫寺中的壁畫、雕塑,要旨則評賞二公之技藝,雖用了“雙林”“祇園”等佛語,但皆是敘寫佛像故事,別無深意。《是日自磻溪,將往陽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一詩,恰如查慎行所評“俱是禱雨之作”(《蘇軾資料匯編》1771),其余游宿寺院之作,則皆只記游蹤,甚至連寺院的景觀都很少著墨,基本與佛教無關。因此,蘇軾自稱嘉祐末“予始未知佛法”(《文集》1965),應是如實之語。
熙寧四年六月,因政見不合,蘇軾通判杭州。杭州佛寺林立,甲于天下,章衡撰于元祐三年的《敕賜杭州慧因教院記》中記杭州寺院多達532所。公務之余,蘇軾常探幽攬勝,訪僧尋寺,曾自言:“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詩集》644)倅杭三年,他共游歷寺院41所,游寺詩凡79首,占此期詩歌總量的22.32%,并呈逐年遞增之勢: 熙寧四年十一、十二月5首,熙寧五年20首,熙寧六年33首,熙寧七年正月至八月18首。更為重要的是,他與佛禪的關系也隨著時日增加而愈加密切。
初至杭州,蘇軾游寺的初衷是“名尋道人實自娛”(《詩集》318),因此詩中皆描繪寺院清音、僧侶風致和內心體驗。例如,寫雙竹湛師房:“羨師此室才方丈,一炷清香盡日留。”(《詩集》524)寫與海月辯公“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文集》638)聽僧昭素彈琴后,自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詩集》576)等,似乎暫忘了塵煩熱惱,覓得了自適平和的心境。蘇軾甚至還體認到俗世與佛寺之間的巨大反差,并重新審視自我。“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閑”(474)、“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548)等詩句,皆意在凸顯方內、方外之別,表達了他對此岸與彼岸意義的重新考量。
隨著時日的增加,蘇軾對佛禪的理解漸次深入,自言“久參白足知禪味。”(548)于山水清音,亦始“別具只眼”,故詩中每含禪味、禪境。例如,熙寧五年八月作《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380—81)首句即進入非有非無之境,復自稱“幽人”,更添清幽之味;末句拈出“當空之月”,又具有空寂之感,故周紫芝《竹坡詩話》以“清絕過人”(周紫芝350)評之。作于熙寧七年的《游鶴林、招隱二首(其一)》,亦清腴拔俗,“古寺滿修竹,深林聞杜鵑”二句,紀昀贊曰“不減‘曲徑通幽’之句。”(紀昀1887)
自嘉祐末“喜佛書”至熙寧四年末,歷時八年,佛禪文化潛移默化于蘇軾的精神世界,他的游寺詩還常流露出“空觀”“無常”之思。例如《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原是追懷建寺者錢镠,但并沒有循著一般懷古詩的思路,而是用“佛家法眼”抒寫了“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郁紆”(323)的曠達,用“是身如浮云,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維摩詰經》36)的理論消解內心的執念。另如“廢興何足吊,萬古一仰俯”(345)、“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347)等詩句,皆是言說無常世事;而“入門空有無,云海浩茫茫”(577)、“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331)等詩句,則直接陳說“諸色皆空”的思想。需指出的是,蘇軾在演繹這些佛教思想時,多出之以概念、術語,明顯未臻至圓融無跡之境。
蘇軾此期的游寺詩還略具禪偈之風。例如《游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推倒垣墻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巧歷如今也被謾。”(2525)該詩仿偈頌體,出以粗淺、直白之語,故紀昀評有“禪偈氣”(紀昀1883)。又如著名的《書焦山綸長老壁》,以長鬣人為喻,言心無所住之理,紀昀評曰:“直作禪偈”(紀昀1887),趙翼《甌北詩話》亦曰:“絕似《法華經》、《楞嚴經》偈語。”(趙翼1147)不過,這類仿偈頌體的詩歌仍顯得比較生硬,模仿之跡明顯,因此趙翼批評道:“摹仿佛經,掉弄禪語,以之入詩,殊覺可厭[……]此等本非詩體,而以之說禪理,亦如撮空,不過仿禪家語錄機鋒,以見其旁涉耳。”(趙翼1146—47)
綜上可見,蘇軾倅杭時期的游寺詩漸有禪味,屢用佛典,兼及佛理,甚至略具“禪偈味”,但總體未臻圓融之境,更像是應特定場域而作。這反映出他與佛禪的關系仍處于認知的階段。熙寧六年,蘇軾循行富陽,作《自普照游二庵》中云:“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后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434)表明了他仍眷戀紅塵,難耐孤寂。這是以典型的文人“用舍行藏”的處世方式對待佛教,佛寺于其意義只是暫時的遁世之所。
熙寧七年九月,蘇軾去杭,歷任密州、徐州、湖州。五年中,因客觀環境、個人境遇之變,游寺詩的數量急劇減少,僅有29首,所占比例約為6.97%,游歷寺院11所。他在密州、徐州創作的詩歌總量與倅杭大致相當,但游寺詩卻從79首下降至14首。此中原因,乃在于密州等地佛教不昌、寺院稀疏之故,而且茲地臨近鄒魯,詩禮簪纓,儒家的濟世思想占據其心。這些游寺詩總體更接近鳳翔期間,無太多佛禪色彩。元豐二年,蘇軾致信久上人說:“北游五年,塵垢所蒙,已化為俗吏矣”(《文集》2530),體現出他在密州、徐州期間與佛禪的疏離。后赴湖州,相伴者乃舊友、高僧,蘇軾游寺詩創作熱情高漲,占此時期詩歌總量為20.27%,內容上也出現某種程度的回歸。例如“虛明中有色,清凈自生香”(944)言說佛教色空理論;一些詩作亦富有禪機,如“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943)、“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985—86)等等,暗含著佛家隨緣任運的思想。無論從內容還是格調看,與倅杭時期頗為接近。
二、黃州時期: 洗心歸佛,以求安心
元豐二年八月,蘇軾身陷“烏臺詩案”,貶謫黃州。數月“魂驚湯火命如雞”的牢獄生涯,不僅使其備受摧殘,更增添了內心的“無常”、“幻滅”之感,從而促發了他重新省思原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抵黃州后,他常杜門卻掃,反躬自省,“間一二日輒往(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文集》392)從此覓得鋤其本、耘其末的自新之方——歸誠佛教,并自號“東坡居士”,且“常著衲衣”(惠洪2204),開始了“如實修行”的習禪生涯。
蘇軾因文字而坐獄,至黃州后仍如驚弓之鳥,憂讒懼禍,“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文集》1752)又為待罪之人,不便隨意行游,“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文集》1567)因此,黃州四年詩歌數量僅184首,游寺詩17首,分別為元豐三年13首,四年3首,七年1首。
元豐三年的13首游寺詩,有8首為初至黃州所作,呈現出蒼涼、悲寂的格調。這些詩歌寫景的筆墨明顯減少,寄懷抒慨的成分增加,即便是寺中賞花,寄寓的也是身世感慨:“看花嘆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1035)、“忽逢絕艷照衰朽,嘆息無言揩病目”(1037)。但蘇軾絕非自我沉淪者,為擺脫內心的困頓,他歸誠佛教,滌除是非,安頓身心。作于赴黃州途中的《游凈居寺》,他反復陳說歸佛之愿:“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1025)、“愿從二圣往,一洗千劫非”(1026)。他甚至嘆聞道之晚:“嗟我晚聞道,款啟如孫休”(1018),“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早”(1170)。值得注意的是,蘇軾歸誠佛教的初衷并非為解脫生死,而是期獲靜達之心,他在《答畢仲舉二首》中言:“不知君所得于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仆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文集》1672)因此,他“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為問道庵”(1108),著眼于佛教“安心”之用。
如果說倅杭時期,蘇軾游寺詩中表達的“空觀”“無常”思想多指向他者或外物,那么黃州時期則是慰藉心靈,指向自我。例如,《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薩泉見餉,二首(其二)》曰:“寒泉比吉士,清濁在其源。不食我心惻,于泉非所患。嗟我本何有,虛名空自纏。”(1045)以“寒泉”自比,用《易經》“井渫不食,為我心惻”謂寒泉本自清凈,而我本空無,何以自縛于虛名?用“諸色皆空”之理,勸誡自我。又如《游武昌寒溪西山寺》一詩,先寫孫郎石、陶公柳皆如飄渺云水,消散于歷史時空之中,彌漫著濃厚的空幻意識;繼而轉向自我:“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1050)相比于倅杭時期,他的歸隱之志也更為堅決,所言佛理也更注重于自我心靈境界的構建。
黃州時期的蘇軾對佛禪義理的參悟,較以往也更進一層。例如,他的游寺詩多次寫到寺院澡浴,呈現出的卻是不同的意趣。熙寧五年七月的《宿臨安凈土寺》云:“晚涼沐浴罷,衰發稀可數。”(345)只寫沐浴的行為,無關佛理。熙寧六年八月的《宿海會寺》曰:“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497)用《維摩詰經》“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凈華,浴此無垢人”(《維摩詰經》155)之意,言澡浴兼具洗身、洗心之功用。而元豐三年所作《安國寺浴》云:
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發不到耳,尚煩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煙霧蒙湯谷。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發臨修竹。心困萬緣空,身安一床足。豈惟忘凈穢,兼以洗榮辱。默歸毋多談,此理觀要熟。(1034)
蘇軾由“洗身”而悟出的“洗心”之法,實際就是洗去“凈穢”、“榮辱”之念。然身垢易洗,心垢難除。“心困”兩句用《維摩詰經》“唯置一床,以疾而臥”(97)典故,闡明“洗心”之法應心無所住,徹悟色空不二、無待至樂之理。此詩之意,恰如同年所作《勝相院經藏記》云:“愿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文集》389)這三首游寺澡浴詩,隨著時間、境遇的變化,闡發的意趣明顯不同,從洗身之垢到洗心之垢,再到洗凈垢、榮辱之執,這種變化體現了蘇軾對于佛教義理漸次深入的事實。
黃州游寺詩雖僅有3首詩援引佛典,但側重于佛教義理的闡說,且較多用事典,更顯精確、圓融。例如,《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云:“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四方同此水中天。”(1085)紀昀評曰“竟是偈頌。”(紀昀1917)“何處”句實脫化于《楞嚴經》卷五:“月光童子[……]我有弟子窺窗觀室,唯見清水,遍在室中,了無所見。”(236)是借月光童子修習水觀之事,言己謫黃而得清凈之心。“四方”句則契合《楞嚴經》“有佛出世,名為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觀,入三摩地”(236)之“水天”,不著痕跡。
黃州時期,蘇軾運用佛禪文化來反觀自省,用是身如幻、一切皆空的理論來洗心,以求心不染物,斷除妄念。安國寺五年的暮旦往還,似乎使他終獲“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里翛然,無所附麗”(《文集》392)的心境。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言:“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于不去也。”(《文集》1671),他的游寺詩也反映了內心“雜草”旋去旋生的事實。例如,作于元豐七年的《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一詩,先寫“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1190),繼而發出“平生所向無一遂,茲游何事天不阻”(1190)的哀嘆。蘇軾雖努力忘凈穢、洗榮辱,欲臻至無心之境,但這個過程并非一蹴而就。
黃州之后,元祐之前,一年之多,蘇軾輾轉多地,詩作共計204首,游寺詩26首,游覽寺院16所。游寺詩關涉佛禪雖不多,但明顯更顯圓融、成熟。例如《贈東林總長老》,“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凈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1218—19)首二句,用《法華經》:“世尊[……]現大神力,出廣長舌”(《法華經》442)中的意象,闡述佛教義理無所不在,暗合“郁郁黃花,無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之意。“八萬四千偈”出自《楞嚴經》:“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凈寶目。”(260)言佛家法輪日月運轉,浩蕩無垠。再如《題西林壁》,亦是書寫游寺之悟,紀昀評:“亦是禪偈,而不甚露禪偈氣,尚不取厭。”(紀昀1924)相對于此前的禪偈詩而言,這兩首詩從借佛語說理,轉化成以禪悟達理,更富理趣。
元祐時期的八年內,蘇軾作詩570首,游寺詩30首,所占比例為5.26%,游歷寺院15所。游寺詩數量急劇下降,而實際當時汴京的寺院并不少。究其原因,蘇軾此期“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文集》699),王事鞅掌,無心游寺,自言“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于外。”(《文集》1870)因而所作之詩主要以應酬、唱和、贈答為主,“交際性的詩歌占其此時期作品總數的80%以上”。(“詩可以群”131)此期的游寺詩亦多唱和之作,較少涉及佛禪,甚至在杭州一年余,所作僅10首,也基本屬于游玩賞物之作,其中最具佛禪色彩的《觀臺》一詩,則被紀昀譏為“五六九僧一派。”(紀昀1945)無論是數量還是與佛禪的融攝程度,都遠不及倅杭時期。正如蘇軾自云:“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澀,無與鋤治。”(《文集》1870)蘇軾與佛禪的關系似乎又回到了鳳翔時期,但實質上更表明了他的禪悟進階充滿著法緣與俗緣的反復糾葛,順、逆之境深刻地影響著他與佛禪的距離。
三、嶺海時期: 即心即佛,無思之思
紹圣元年,蘇軾謫知英州軍州事,后累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已近耳順之年的蘇軾,再貶至“九死南荒”之地,對佛禪又有了新的領悟,游寺詩的創作亦呈現出新的特征。
紹圣元年八九月間,蘇軾過大庾嶺龍泉寺,題詩于寺鐘曰:“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凈。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發受長生。”(2057)一念頓悟,本性清凈,浩然天地間,惟我獨正,這是南宗禪倡導的“佛性即自性”的詩意呈現。黃州時期,蘇軾執著于覓求“安心法”,實則為“逃世之機”,而此時他“身世永相忘”,已無是非之想。不久,蘇軾再入曹溪,禮六祖惠能真身,作《南華寺》詩云: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2061)
首二句點明禮佛之意在于“識本來面”;次用《壇經》“惠明求法”(27—30)《楞嚴經》“指月眩目”(63)典,言己了知萬法,不為外物所迷;“我本”以下諸句,觸境寄感,既抒寫了篤實修行的宏大誓愿,又表達“今是昨非”之恨。全詩情真意切,表明他的習佛進階已逐漸從洗凈穢、去榮辱,上升到對“本來面目”的覓求。紹圣元年十月在惠州嘉祐寺,蘇軾立有“思無邪齋”,且作《思無邪齋銘》,其并敘曰:
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于是得道。(《文集》575)
所謂“有思而無所思”,即“無思之思”,心無外物,是一種拋去功利、擬議、作用、語言之思。這與溈山靈祐開示門人之語:“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普濟527)之意,頗相契合。溈山靈祐認為,“思無思”可返觀自我之“靈焰”,識得本心,從而達到理事不二的真如境界。次年,蘇軾又作《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云:“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于無所得故而得者。”(《文集》390)究其實,“無思”乃佛家“無念”之意,即去除妄念,擺脫相念之執,性相一體,圓融無礙。
蘇軾覓得以“無思之思”之法來探尋“本來面目”,游寺的心態發生了明顯變化。嶺南蠻荒,九死一生,但他的游寺詩卻極少悲愁、孤寂之象,反而呈現出怡然自得、隨緣任運的情調:“二年流落蛙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2112)、“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云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2063—64)他俯仰人生、天地、宇宙,無不以一種“無思”“無待”的態度視之:“嬉游趁時節,俯仰了此世”(2099),“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2195—96)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蘇軾的寺院書寫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即29首中有近20首純寫游賞之樂。他不再刻意使用佛經語匯和經教義理,而是將佛教的思想經義內化為一種生活情調、價值取向,將佛理融攝于詩中,書寫“無思之思”的精神狀態,表達主體的精神自足。表面上看,這與鳳翔時期寫景記游的游寺詩很相近,但實有本質之別,是他“即心即佛”后的大徹大悟,寺院純為客體景觀,不著半點主觀色彩,這頗類于青原惟信“見山是山”的第三重境界。
紹圣四年蘇軾再謫儋州,三年中詩作共133首,但游寺詩僅《入寺》1首。揆其原因,蓋儋州地區寺院較少之故。據劉正剛先生考察,宋代海南佛寺凡26所,而儋州僅開元寺、光孝寺、凌霄庵3所。不過,這首《入寺》亦值得注意:
曳杖入寺門,輯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旦隨老鴉起,饑食扶桑暾。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璃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忙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2283)
首四句,先述入寺禮佛,轉言自己為“玉堂仙”,流露出道家思想。次四句,返觀自照,從佛教角度言己宿業已盡,習以道家養生之法。“光圓”以下四句,王文誥案“謂光明透徹,無所不了也”,言己參透佛禪,心魔消散。末四句,寫自我心境,無欲無求。此詩融攝佛道,以道家養生之法而達無思無欲的佛禪境界,可謂“仙山佛國本同歸”(2267)。
紹圣四年七八月間,蘇軾至儋州,“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名曰“桄榔庵”,并摘葉書作《桄榔庵銘并敘》。在這篇銘文中,蘇軾澄懷觀道,“神尻以游”,跳脫“百柱屃屭,萬瓦披敷”草庵之縛累,無顧于“海氛瘴霧”“蝮蛇魑魅”之侵凌,俯仰宇宙,“以動寓止,以實托虛”,不僅抒寫了豁然曠達的情懷,更表達了識得“本來面目”的體驗:“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發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余。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都乎?”(《文集》570)蘇軾用了禪家常用的“非非”句式,破除了對名實、動止、虛實、欠余的知解執著,認識到萬事萬物皆平等如一,從而達到心不住相,永息諸念,回歸到最初真如佛性之狀態,由“即心即佛”而達到“非心非佛”的境地。
元符三年五月,蘇軾再移廉州安置,后北歸,作詩94首,游寺詩16首。此期的游寺詩很明顯的表征是頻用佛典,占此期游寺詩比例的75%。所用佛典多出僧傳、燈史,其中《景德傳燈錄》8次,《五燈會元》3次,涉及禪宗公案多達13處。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蘇軾對燈錄、佛經了熟于心,信手拈來;另一方面這些詩歌多為與僧人、習佛之士的贈答、戲和之作,故常用佛典以切合贈答對象。例如《戲贈虔州慈云寺鑒老》,除“道人有句借宣揚”外,其余7句皆引佛典,廣涉《景德傳燈錄》中諸多禪宗公案,如鷲嶺善本禪師“水浴無垢”(道原1286),古靈神贊“蠅子投窗”、“佛放光”(道原591),石霜慶諸“遍界不曾藏”(道原1085),南泉禪師“寸絲不掛”等公案(道原494),以及《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子說圓通偈一事(《楞嚴經》264—69),跋陀婆羅并同伴十六開士于浴堂忽悟水因,于熏籠焙浴具,得大安樂之典。(《詩集》2448—49)皆信手拈來,足見其對僧傳、語錄的諳熟程度。蘇軾前期的游寺詩援引佛典多為言說佛法,而此期或為戲贈他人,或抒寫自我心境,或延及萬事萬物,這可謂游戲圓通,左右逢源,故查慎行評曰:“盡用禪家語形容,可謂善于游戲者也。”(《蘇詩補注》1360)
嶺海時期,實質也是蘇軾人生歷程的最后階段。數十年的游寺、參禪、悟道,不僅使他獲得了精神慰藉,煉明心志,更使他能以一種“無思之思”如實修行,徹見“本來面目”,對佛教達到了一種高度的認同。這種認同首先體現在身份上的認同。蘇軾“前世為僧”之說,始于元豐七年。是年,他赴筠州省弟,與云庵禪師、聰禪師說夢,“自是常衣衲衣。”(惠洪2204—2205)紹圣元年謫英州,蘇軾遣書佛印,中云“戒和尚又錯脫也”(惠洪2202),視己為戒和尚。紹圣二年,于惠州作《答周循州》曰:“蔬飯藜床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詩。前生自是盧行者,后學過呼韓退之。”(2151)紹圣三年,《次韻子由所居六詠(其四)》中言己:“蕭然行腳僧,一身寄天涯。”(2208)后再貶瓊州,又稱自我是“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苦行僧”(《文集》1841)。北歸游靈峰寺,“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2401),以得道高僧德云自比。后復官,監玉局觀,作偈曰:“卻著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惠洪2202)盡管都是述說自我是僧,但皆隨蘇軾對佛禪的體悟程度而變化,從最初的自疑為僧,著衲衣,進而認定為“盧行者”“行腳僧”“苦行僧”,最后自比為得道高僧“德云”,“自疑身是五通仙”,可見蘇軾佛禪境界的漸次上升。
四、北宋文人游寺詩創作的類型
綜上所述,蘇軾對佛禪的接受、領悟的進階,非常清晰地呈現在他的游寺詩之中: 鳳翔時期,因“不知禪味深”,游寺詩基本未涉佛禪;倅杭期間,因彼地濃郁的佛禪氛圍以及文人禪悅之風的興盛,蘇軾積極地訪僧尋寺,所作之詩開始營構禪境,演繹佛理,甚至帶有“禪偈氣”;貶謫黃州,因身心俱創,終日宴坐佛寺,歸誠佛教,游寺詩處處言禪;嶺海時期,蘇軾已逾耳順之年,轉而內求本來面目,游寺詩常以“無思之思”書寫自我對佛禪的感悟,最終完成了對生命終極意義的探尋。
蘇軾思想融攝儒、道、釋三家,歷來被視為北宋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作詩文最能凸顯彼時的文化風尚。他的游寺詩不僅直接反映了熙寧、元祐間文人極盛的禪悅之風,更饒有興味的是,其不同階段的游寺詩亦基本代表了北宋文人游寺詩創作的風貌。根據詩人的創作心態及詩歌自身的特質,綜括言之,北宋游寺詩大體可概括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 紀實繪景型
此種類型與蘇軾鳳翔時期的游寺詩頗為相類,寺院往往純為文人游賞的客觀場域,宗教意涵非常薄弱。這是游寺詩最基本的創作類型,貫穿于北宋各個時期,尤以北宋初期最為突出。
宋初文人盡管身份殊異、思想有別,但他們的游寺詩除了極少數書寫羈旅之情、寺院歷史、集會宴飲外,絕大多數以摹繪景物為主,率皆等同于通常的山水游覽詩,并且呈現出明顯的程式化特征: 首聯一般敘寫行程,中二聯著力繪景,末聯言歸隱、戀景之意。例如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云:“底處憑闌思眇然,孤山塔后閣西偏。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煙。遲留更愛吾廬近,只待重來看雪天。”(《全宋詩》1213)所寫茂林、良田、孤鳥、夕陽、寒煙諸景,皆寓目所見,真實可感,但與佛禪并無直接關聯,詩題中的“孤山寺”,完全可以置換為某個亭臺、樓觀,而詩意、詩境不會有太大變化。再如,田錫《題天竺寺》、潘閬《秋日題瑯琊山寺》、趙湘《題國清寺》、寇準《游花巖寺》諸作,亦皆如此。盡管有的文人如潘閬、趙湘等,詩中之景頗含空寂、幽靜之味,但究其實,這并非因之于佛教精神的影響,而是山水清音洗郁的結果。
宋初文人游寺詩的這種風貌,直接反映了他們與佛禪的關系。“會昌法難”,像教陵夷,唐末五代雖逐漸走上復蘇,但宋初奉佛文人并不普遍。清人彭紹昇《居士傳》僅輯有楊億、李遵勖晁迥、王隨四位宋初居士,而且他們亦未認真思考詩與禪的相通機制,詩與禪實際仍處于一種疏離狀態。楊億堪稱宋初最著名的佛教居士,曾刊定了《景德傳燈錄》等禪門文獻,深悟禪觀,《五燈會元》甚至將他列于廣慧元璉禪師法嗣。但讀他僅有的4首游寺詩,像《留題南源院》《留題黃山院》《題顯道人壁》皆無關佛理,而《大中塔》則純為繪景,舂容典贍,猶未脫臺閣之氣。其余像徐鉉、錢惟演、張詠等詩人的游寺詩,更與佛禪精神相距甚遠。此正如周裕鍇先生所言:“直到北宋文化發展到鼎盛,出現文化整合思潮時,詩歌和禪宗相融的潛在可能性才變為現實性,詩人才真正從參禪活動中受益。”(《文字禪》48)
這種“以寺院作為客觀場域”的創作類型,主要是出自受佛禪浸染不深的詩人之手,在北宋中、后期仍比較普遍,例如曾鞏、歐陽修、范純仁、畢仲游等人的游寺詩。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寺院除供奉三寶、安禪弘法等宗教功能之外,因其遍布于通都大邑、山林爽塏,還兼具避難、讀書、客宿、雅集等功能,這些功能大大地拉近了它與世俗之間的距離。文人游寺或為消除勞頓,或因讀書修業,或是奔赴雅集,寺院的宗教功能反而被遮蔽,他們的游寺詩關注的焦點自然不會是宗教本身。
(二) 闡理寫心型
慶歷年間,儒學復古思潮興起,文人皆倡道統,辟佛老。契嵩作《原教》、《輔教編》等文,明儒釋之道一貫,護法輔教,厥功至偉。嘗詆佛教為“夷教”的歐陽修亦尊禮之,并在居訥中敏的循誘下,最終潛心向佛,自號“六一居士”。歐陽修前后態度的變化,意味著宋代居士佛教發展的重要轉向。自此之后,儒釋互滲互融的局面漸開,文人耽于釋典,禪悅之風大盛。寺院的宗教意義逐漸突顯,游寺詩的書寫亦呈現出新的特征: 一方面是以禪入詩,闡發佛理;另一方面是書寫游寺參禪的內心體悟,有兩種表現途徑,一是通過營構禪境,表現禪悅之思;二是書寫參禪后的心境及以佛安心的愿望。這種特征,與蘇軾在杭州、黃州時期的游寺詩創作比較接近。
宋初的游寺詩基本不涉佛典。但至北宋中后期,禪門語錄、僧傳、燈史頻出,“文字禪”漸盛,文人們諳熟于各種佛教典籍,在游寺詩中援引佛典、公案的現象就顯得比較普遍,甚至一詩中用多個佛典,像秦觀《圓通院白衣閣(其一)》、李廌《少林寺詩》、黃庭堅《題吉州承天院清涼軒》、蘇軾《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等詩。這些文人對于佛典的運用,還不止停留泛化的層面,而逐趨深層次地詩禪一體,形式上也非常接近禪偈。像黃庭堅《戲題葆真閣》:“真常自在如來性,肯綮修持祗益勞。十二因緣無妙果,三千世界起秋毫。有心便醉聲聞酒,空手須磨般若刀。截斷眾流尋一句,不離兔角與龜毛。”(黃庭堅1636)此詩句句用佛語、佛典,涉及《傳燈錄》《楞嚴經》《法華經》《長阿含經》《維摩詰經》諸經,于語言文字中,游戲三昧,橫說豎說,不可純以詩格繩之。此外,王安石《題半山寺壁二首》、李復《題大圓庵二首》、彭汝礪《云蓋寺談空亭》《法輪院》等,亦皆通篇用佛典明理,彌漫禪偈之氣,充滿禪機禪趣。
除了表達禪學見解外,文人們還經常書寫游寺時的感悟。一種表現即在詩中營構禪境,表達法喜禪悅。這類詩歌表面上看與“紀實繪景型”相類似,旨趣卻不盡然。“紀實繪景型”的游寺詩歌重點是表現“自然”,樂景閑適;而此類詩歌雖通篇繪景,但實為“寫心”。這些詩歌多出于那些虔誠向佛的文人之手,最為典型的莫過于王安石。王安石早年為官時,即頻游寺廟,廣交禪僧;晚則退居金陵,遍游鐘山諸寺,且舍宅為寺,注《楞嚴經》、《華嚴經》等經,深通禪理。其晚年所作游寺詩常藉景抒懷,營構清幽、空寂之境,書寫禪悅的風致。例如《定林院》:“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留云對宿,仍值月相尋。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王安石517)詩中既描寫了寺中清景,“枕石漱流”之中,更表現出詩人物我兩忘游憩之樂和曠達的胸襟。再如《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其二)》云:“獨尋飛鳥外,時度亂流間。坐石偶成歇,看云相與還。”(王安石579)似有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之禪境。另如王安石《游草堂寺》《臺城寺側獨行》、文同《吉祥院》、張耒《寺西閑步》等詩,皆寓禪味于自然景物之中。另一種表現則是抒發游寺參禪后內心的超脫及以佛法安頓身心的愿望。例如,郭祥正《游鹿苑寺》“煩心沃醍醐,頓悟超十地”(《全宋詩》8847),李復《周巨寺》“金篦刮病膜,清冰沃煩腸”(《全宋詩》12413)等,都肯定了游寺參禪滌除心垢的功用。正如張方平《游瑯邪山寺》所云“俗游殊不意,僧話粗寬心”(《全宋詩》3856),文人們游寺不再是“俗游”,而是一種“精神之游”,期望通過參禪問道來澡雪精神,清凈內心。然而,這種希冀從高僧言語中開悟的安心之法,仍是以佛為用,向外覓求,此正如《五燈會元》卷十二守芝禪師所言:“向言中取則,句里明機,也似迷頭認影”(普濟708),終非第一義諦。
(三) 明心見性型
這種類型主要是通過游寺詩書寫識得本來面目后的自適及對生命終極意義的領悟,類似于蘇軾嶺海時期的游寺詩。表面上看,寺院在詩中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詩人游寺的目的既非禮佛賞景,亦非借佛洗心,而是返諸自我,省察內心。例如,“鹿門居士”米芾的《登米老庵呈天啟學士》云:“我居為江山,亦不為像法。劫火色相空,未覺眼界乏。屹然留西庵,使我老境愜”(《全宋詩》12261),米芾參悟了“萬法皆空”“像法”亦空,故所求惟自性之愜意,而非佛法。其游潤州甘露寺,作《凈名二首(其一)》云:“依靜家如寺,游頻寺是家。何須傅大士,芰制著袈裟。”(《全宋詩》12251)禪家常以“家”比喻“自性”,此處“家”亦象征“自性”,“寺”則指代佛法,米芾以為只要“自性清凈”,家即是寺,寺即是家,非家非寺,這與蘇軾在《桄榔銘》所說的“無作無止,無欠無余”是同一層意思。
北宋中后期的居士文人參悟佛法日益精深,一些游寺詩開始書寫徹見真如本心的體悟,非常接近禪家的悟道偈。例如李之儀《浴南寺園頭求詩》曰:“一重洗盡一重生,塵垢昏人不自醒。會得栽茄種瓜意,始知松竹本來青。”(《全宋詩》11198)前兩句是針對神秀禪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試,勿使惹塵埃”而言(《壇經》10),否定向外求法,漸悟成佛的可能;后兩句中的“栽茄種瓜”則隱含“觸類是道而任心”之意,“松竹本青”則暗喻人自性清凈。此詩之意即向外求佛實是逐物迷己,應向內明心見性。

游寺詩書寫明心見性的感悟多集中于北宋后期,這一方面是他們涉佛之深的體現;另一方面,此一時段黨爭愈發激烈,促使文人轉向對自我命運和生命價值的思考。同時,理學蓬勃發展,與佛禪互滲互融,與傳統儒學相比更注重道德、心性的內省來澄明生命的意義,這也深刻地影響著文人對自我心性的省察,這種種機緣,促進了文人對真如本性的體認,也從整體上提升了北宋游寺詩的品格。
總之,從時段上看,北宋文人游寺詩大體經歷了這三種類型的發展過程: 即宋初以“紀實繪景型”見多,中后期則以“闡理寫心型”為主,同時也出現了“明心見型”。需要指出的是,這幾種類型發展僅是一個粗略的輪廓,并非嚴格的線性發展。就具體的詩人而言,情況更為復雜,就像蘇軾一樣,隨著其習佛進階的提升,這幾種類型可能皆涵括在他的創作之中。
余 論
寺院在中國文化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大抵相當于西方社會中的“教堂”,都是導人信仰、傳播教義的“宗教場域”。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寺院還兼具讀書、客宿、雅集、游賞、救濟等功能,實為連結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公共場域”。處身于這種“場域”之中,不管是宗教徒,還是非宗教徒,因受宗教力量的感召,都會或多或少獲得一種不同于世俗生活的情調和境界。他們常將這種情調、境界訴之于詩歌,表達自我對宗教精神的認知和體悟。本文通過梳理蘇軾不同時期創作的游寺詩,不僅可以窺見其禪悟的進階,而且表明游寺詩的創作風貌實質取決于詩人對佛禪體悟的程度。可以說,游寺詩是探討個體文人甚至某個時段的文人奉佛的絕佳視角,其意義值得我們進一步重視。
注釋[Notes]
① “游寺詩”一詞,最早見于釋皎然《詩議》:“如游寺詩,鷲嶺雞岑,東林彼岸。”《文鏡秘府論》南卷引釋皎然《詩議》(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144—45。目前學界尚無對“游寺詩”的統一界定。我們認為,詩題中凡出現“止宿”“游覽”“過”寺院、僧舍、招提、精舍者;詩題中有“訪僧”“題寺壁”等字眼者;詩題雖未出現以上字眼,但明顯寫寺院風物者,皆可視為游寺詩。
② 趙德坤、周裕鍇“濟世與修心: 北宋文人的寺院書寫”,《文藝研究》8(2010): 63—69。目前關于蘇軾游寺詩的論文有: 施淑婷“蘇軾參訪寺院之因緣”,《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學報》1(2009): 31—66,主要探討蘇軾游寺之因緣;賈曉峰“蘇軾黃州寺院詩的新變”,《內蒙古大學學報》5(2016): 100—105,將黃州寺院詩與前期寺院詩對比,探究蘇軾黃州寺院詩在內容上、情感強度上及意象營構上的變化。
③ 本文數據統計以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為藍本,除去卷四十六帖子詞口號65首。
④ 孔凡禮《蘇軾年譜》卷二,“傳嘗讀書連鰲山棲云寺及三峰山、實相寺、華藏寺”(北京: 中華書局,1998年)40。
⑤ 梁銀林《蘇軾與佛學》,2005年四川大學博士論文: 20。
⑥ 李翥纂輯《慧因寺志》卷六,白化文、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6冊(揚州: 廣陵書社,2011年)69。
⑦ 此詩在外集編卷四倅杭詩中,查慎行注、馮應榴注皆從之。王文誥注本刪去不收,底本補編于卷四十七。王文誥刪此詩并無根據,本文據外集、查注、馮注移至倅杭時期。
⑧ 黃啟江《北宋汴京之寺院與佛教》一文考察后認為:“宋室南渡之前,汴京寺院約有九十所”,載《北宋佛教史論稿》(臺灣: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100。
⑨ 劉正剛“宋明海南佛寺與佛教世俗化研究”,《古代文明》3(2017): 97—108。
⑩ 袁衷等錄,錢曉汀: 《庭幃雜錄》卷下。(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1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道原: 《景德傳燈錄譯注》,顧宏義譯注。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
[Daoyuan.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Tran. Gu Hongy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0.]傅璇琮等編: 《全宋詩》。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Fu, Xuancong, et al., eds. Complete Poetry from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黃庭堅: 《黃庭堅詩集注》,任淵等注,劉尚榮校點。北京: 中華書局,2003年。
[Huang, Tingjian.An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Huang
Tingjian
’s
Poetry
. Eds. Ren Yuan, Liu Shangrong,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惠洪: 《冷齋夜話》,《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Huihong.Night
Talks
of
the
Cold
Studio
.General
Views
o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Literary
Sketches
. Ed.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紀昀: 《蘇文忠公詩集》,《蘇軾資料匯編》,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4年。
[Ji, Yun.Collected
Poetry
of
Su
Shi
.A
Sourcebook
of
Su
Shi
. Ed. Sichuan University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Research Depart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孔凡禮: 《蘇軾年譜》,北京: 中華書局,1998年。
[Kong, Fanli.A
Biographical
Chronicle
of
Su
Shi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普濟: 《五燈會元》,蘇淵雷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
[Puji.A
Compendium
of
the
Five
Lamps
. Ed. Su Yuanle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蘇軾: 《蘇軾詩集》,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
[Su, Shi.Collected
Poetry
of
Su
Shi
. Eds. Wang Wengao and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蘇軾: 《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北京: 中華書局,1986年。
[Su, Shi.Collected
Essays
of
Su
Shi
. Ed.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蘇轍: 《蘇轍集》,陳宏天,高秀芳校點。北京: 中華書局,1990年。
[Su, Zhe.Collected
Works
of
Su
Zhe
. Eds. Chen Hongtian and Gao Xiuf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壇經》,賴永海主編,尚榮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
[The
Platform
Sutra
. Eds. Lai Yonghai and Shang R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法華經》,賴永海主編,王彬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
[The
Sutra
of
Saddharmapundarika
. Eds. Lai Yonghai and Wang B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楞嚴經》,賴永海主編,劉鹿鳴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
[The
Sutra
of
Surangama
. Eds. Lai Yonghai and Liu Lum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維摩詰經》,賴永海主編,高永旺、張仲娟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
[The
Sutra
of
Vimalakirti
. Eds. Lai Yonghai, Gao Yongwang,and Zhang Zhongj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王安石: 《王荊文公詩箋注》,李壁箋注,高克勤點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Wang, Anshi.An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Wang
Anshi
’s
Poetry
. Eds. Li Bi and Gao Keqi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趙翼: 《甌北詩話》,《清詩話續編》,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Zhao, Yi.Poetry
Commentaries
of
Oubei
.A
Sequel
to
Qing
Dynasty
Commentaries
on
Poetry
. Eds. Guo Shaoyu and Fu Shous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查慎行: 《初白庵詩評》,《蘇軾資料匯編》,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4年。
[Zha, Shenxing.Poetry
Commentaries
in
Chubai
’s
Hut
.A
Sourcebook
of
Su
Shi
. Ed.Sichuan University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Research Depart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4.]——: 《蘇詩補注》,王友勝校點。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3年。
[- -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to
Su
Shi
’s
Poetry
. Ed. Wang Yousheng.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3.]周裕鍇:“詩可以群: 略談元祐體詩歌的交際性”,《社會科學研究》5(2001): 129—34。
[Zhou, Yukai. “Poems Teach the Art of Sociability: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Yuanyou-style Poem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 (2001): 129—34.]——: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
[- - -.Literary
Zen
and
the
Poe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7.]周紫芝: 《竹坡詩話》,《歷代詩話》,何文煥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1年。
[Zhou, Zizhi.Poetry
Commentaries
of
Zhupo
.The
Poetry
Commentaries
Through
Ages
.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附表一: 蘇軾游寺詩數據統計

時間詩歌總量游寺詩數量寺院數量游寺詩所占比例援引佛典詩歌數量援引佛典詩作數量占游寺詩比例鳳翔前期78222.56%00鳳翔時期138181113.04%316.67%鳳翔后杭州前1900000杭州時期354794122.32%1417.72%密州時期142553.52%00徐州時期205914.39%111.11%湖州時期7415520.27%640%黃州時期1841769.24%317.65%黃州后元祐前204261612.75%415.38%元祐時期57030155.26%516.67%惠州時期199291314.57%517.24%儋州時期133110.75%00北歸至金陵94161217.02%1275%補編、輯佚、他集互見36419125.22%15.26%詩歌總量27582661409.64%5420.3%
(注: 本文以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為藍本。詩歌總量除去卷四十六帖子詞口號65首。據《蘇軾年譜》,《蘇軾詩集》補編、輯佚、他集互見部分移動情況: 《題李景元畫》、《游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題雙竹堂壁》、《會雙竹席上,奉答開祖長官》均移至倅杭時期;《宿資福院》移至黃州后元祐前;《惠州靈隱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于其下》移至惠州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