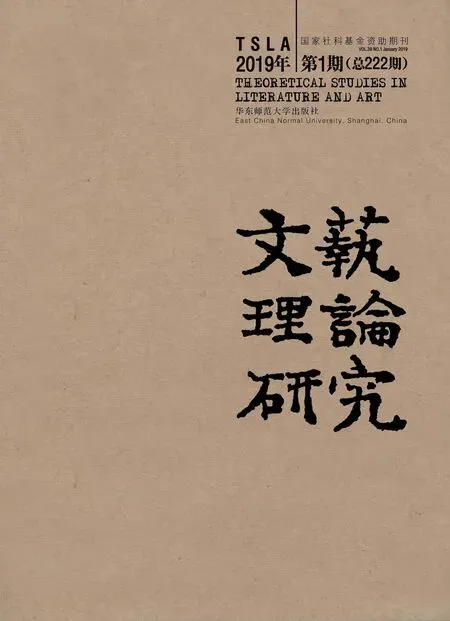從詩史名實說到敘事傳統
董乃斌
一、辨“詩史”名實
筆者近年研究中國詩歌敘事傳統,擬以“抒敘兩大傳統貫穿文學史”之觀點破解“抒情傳統唯一”的說法,補正其偏頗,因而自然關注到詩史問題的討論——歸根到底,“詩史”的核心乃是與抒情“對壘”的敘事,詩史傳統實即與抒情傳統共生并存的敘事傳統。既如此,論說敘事傳統又怎能離得了“詩史”?
關于“詩史”的言說,在中國詩歌史和詩學史上,可謂觸目皆是。直至今日,相關言說和歧議仍然非常之多。在眾多歧說中,劈面遇到的便是“詩史”的名實問題,故不能不先來稍加辨析。
詩史二字組聯成詞,習慣的說法是起于晚唐孟棨的《本事詩》,或更早一點沈約《宋書·謝靈運傳》。事實是否如此?我以為不妨打個問號。
按常識,任何事物總是先有其實,后有其名。“詩史”一名亦當在詩史的事實存在且逐漸被人認識之后才會產生。今知“詩史”常用之義有二,一是詩歌史的簡稱,一是對具有史性特征之詩歌作品(或詩人)的指稱。前者事實清楚,名實相符,沒有爭議,故得通用。后者則須先有了頗具史性而堪稱“詩史”的詩篇,從而顯示出詩歌與歷史的密切關系,才會使人的意識逐漸產生“詩史”的觀念,并逐漸凝聚為“詩史”概念和名詞,再后來這觀念和名詞才會進入文學批評領域。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的認識和實際應用常處變動之中,情況復雜,導致“詩史”之實與名的契合難以穩定,更無從統一,而表現為對“詩史”解釋之見仁見智、歧見紛紜,甚至于或擁護或否定乃至批判的狀態。
沈約書中的“詩史”是詩與史的并列,可以勿論;孟棨其實也不是“詩史”概念的真正創造者。作為某些學人奉為“詩史”出處的《本事詩·高逸第三》之首條,大段講述的是李白的高逸行為,多次引錄的是李白的詩篇,在鋪敘了七百多字之后,才終于提及杜甫的“贈李白二十韻”,但仍未引其文,僅云“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孟棨14)。這之后,才是我們在前面注文中所引那句含有“詩史”二字的話,總共不到三十個字。這個表述清晰顯示了孟棨整個敘述的主次,顯示他幾乎只是順便地提及、轉述了“當時”對杜甫詩歌的議論。當然,雖是簡單一筆,卻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此種無心栽柳柳成蔭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在學術史上,并不罕見。但由此可知詩史的事實早已存在,詩與史的密切關系早為人們所關注,“詩史”概念早在潛滋暗長,“詩史”之名早晚要出現。這是一種必然性,至于它究竟見于今日留存的哪個文獻,卻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這偶然性在杜甫身上得以落實,卻又有深刻的必然之理。
《本事詩》對杜甫詩史的闡說反映了孟棨對當時已存在的“詩史”概念之理解,正如我們今日談論“詩史”,所談的也只是我們的理解而已。誰的理解也不能成為“詩史”的標準定義,更不存在一個經典的不可違拗的所謂“本義”。事實上,“詩史”之名雖然產生,但在文學批評的運用中,“詩史”的含義又是在人們的理解中繼續生成并演變著的。“詩史”概念具有某種開放性,“詩史”的實際運用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因而又有相當的隨機性。同時,“詩史”既可以是對詩歌事實的指稱,也能夠成為詩人自覺期許的目標,因此既可以是他稱,也可以是自稱。杜甫的許多詩篇無疑夠格稱為“詩史”,但也不是說他的每一首詩都是“詩史”,當然“詩史”亦非杜甫一人的專利。文學史和批評史實際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正因為如此,竊以為既不能把“詩史”名稱的發明權歸諸孟棨,也不必奉孟棨《本事詩》為經典,而應實事求是地將《高逸第三》之首條看作一位唐人對“詩史”的理解,亦即“詩史理解史”上的一個環節。然后立足文學史實,斟酌古今,因應時變,參與到對“詩史理解史”的延續運動中去,探索今日能為更多人理解接受和運用的詩史概念,努力把研究推向深入。
說到“詩史”之名產生的必然性,當然首先應該注意到中國詩歌的歷史事實,這才是問題的根本,也是研究的正路。我們只要認真閱讀留存至今的古代詩歌原典,比如《詩經》,便不難發現許多詩篇的敘事性,發現它們的敘述詠嘆與歷史(歷史事件和某些歷史人物)的關系。《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篇,《小雅》中的《六月》《采芑》《出車》《節南山》《十月之交》等篇,國風中《新臺》《載馳》《碩人》《清人》《南山》《黃鳥》《株林》等篇,古人早已反復證實其敘事內容的實在性、歷史性,今人也認為它們與某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有關。說這些作品具有某種“史性”,堪稱“詩史”,似乎沒有什么不合適。如其不然,試問又該如何切合其內容的性質給它一個簡潔準確的名稱呢?倘若我們能夠不因曾將西方的epic譯為“史詩”,就非得以西方的epic奉為史詩的唯一標準,那么甚至不妨稱它們為“史詩”也無不可。這些作品的存在就是“詩史”概念和名稱產生的真正根源和依據。后人,特別是漢人對《詩經》作品的研究理路,如《毛詩》小序大序和許多漢唐人的注疏直至今人的注釋所顯示的,也充分表明他們確信詩歌與歷史有著直接的關系。
再進一步說,原來,在中國,從我們的人文初始時期,詩與史還曾有過一個渾融一體的階段。那時文字尚未成熟,應用很費勁而不普遍,人的認識水平低下,史識猶淺,有詩心而缺史德,以致詩、史皆已萌生滋長而卻彼此不分,可以互代。詩(文)和史由渾沌不分到明確分開,是人類史發展到一定階段才發生的事。而且,即使到有人認識到文史應該分家,并從各方面努力使它們得以分開之時,卻仍很難徹底割斷二者的關系。甚至直到今天,文史早已儼然為分庭抗禮的兩大學科,然文(也包括詩)史在某些方面依舊渾然難分,從而被認為是學術上的一個大問題。文與史似乎總有一部分是兼體的。不僅在中國是如此,在外國,也是如此。所謂文和史,都是人類智力創造物,又都離不開文字的表述傳達,二者本有許多內在的同一性。所以文史難分很可能是一個將要伴隨人類存在之始終、人類自身所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問題。
既然詩與史有過一段渾然不分的經歷,“詩史”或“史詩”便是人類實踐的一種產物,也就是一種歷史事實,一種客觀存在,一種無法漠視的現象,那就早晚會在人的思維、語言和文字中反映和表現出來。“詩史”這個詞遲早是一定會在中國出現的,只不過在現存哪個朝代的文獻中發現這個詞,卻有些偶然性而已。
中國人確實很早就發現并論說了詩史關系的密切——因為,在上古,文字產生并成熟之前,它們一度曾是二位一體的混沌存在。產生于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戰國后期)的《孟子》,其《離婁下》有云:
孟子曰: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之矣。”(孟軻 192)
這是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對這句話,歷來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王者之跡”指什么?何謂“王者之跡熄”?“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應怎樣理解?句中的“詩”字,是泛指的詩,還是作為專名的《詩》?“詩亡”又該如何解釋?等等,都有不同說法。但無論怎樣理解,這句話涉及古人對于詩與史存在密切關系的看法,應該是清楚的。
由此我們也許可以做些思考,引出幾點認識:
第一,孟子所言涉及了我們所關注的詩史關系。他的意思似乎是“詩亡”之后,“史”才全面、正式地出現(沒說此前是否有“史”,但事實上是有的)。這里的“詩”指《詩三百》的可能性較大,此前的詩歌肯定還有,但缺少可靠的文本依據。所以,我們今天要談“詩史”,談詩與史的關系,談詩歌敘事傳統,為此提出實證,如果鑒于種種困難暫不再向前追溯,那么,起碼也應從《詩經》開始。
第二,孟子雖沒有明說“詩亡”之前的詩是“詩史”或詩中有史,但從這話的語氣來看,實乃隱含這層意思。即以為《詩三百》(應該還包括《詩》成書時被刪落以至后來逐步被遺忘的那些詩)都曾經是一種史述或至少含有史述的意味。在那時,雖然列國已有自己的史官、史記,但這些詩也是被當作“史”的一部分。其時,詩與史的區別主要不在其內容,而在其形式與表達。詩記政治大事,也記生活瑣事,詩的語言(文字)允許夸張隱喻,還可有比興手法,史文則更強調直筆和樸實(雖實難避免形容和虛飾),“其文則史”,這個“文”是和詩同時而相對地存在著的。詩與史,無論作為文體還是學科,在后世是被分開了,但“詩史”一詞卻仍把二者聯為一體。這時“詩史”則是指文學性的詩歌與歷史性的史述兩種不同性質的文體存在著密切關系,“詩史”也好,“史詩”也好,其詞的重心都是在于“詩”,主要是指那種具有濃厚史性質地的詩歌(或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詩史或史詩都是指文學作品(而非歷史著作);而所謂“史性”,其內涵與實質,無非是以接近實錄的態度和直筆的手法表現和記敘現實、時事、新聞——從社會的一般日常生活、各行各業、人際瑣事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直至改朝換代、政權更替那樣的重大事件等——經時間的淘洗而堪與史述相印證、媲美者。
第三,當《詩經》尚未成書之前,各國就已經存在“史”,晉有《乘》,楚有《梼杌》,魯有《春秋》。那時詩、史一家,二者并無嚴格區分。那時的詩也便是史,是史記、史料的一種,所以那時不需要“詩史”這個名稱,而已存在“詩史”的現象或曰事實。既有其實,則“詩史”之名,便隨時可以出現,至于究竟何時出現,何時被記錄于文字,記錄下來會丟失還是會流傳等等,則有偶然性。今日我們在《本事詩》中初見“詩史”,焉知將來不會有新的發現?
第四,《詩三百》有比興隱喻、美刺諷諫,與之同時存在的各國春秋“其文則史”,似乎在表述上還沒有“詩”那么多花樣而比較質樸簡陋。孔子的貢獻是把詩的表現手法借用到史的寫作中,使一字褒貶這種“春秋筆法”成了著作史書的“大義”,對后代產生了巨大影響。而詩與史分家的種子,也在一開始就埋下了;詩與史從最初的混沌不分到漸漸各顯特色,有所區分,到基本分開了卻又藕斷絲連,保持難分難解的狀態,在新的背景和不同層次上出現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景,這個漫長而幾乎無止境的過程,也就啟動了。而所謂“詩史”,其含義也就不僅是記錄史事,還包括了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價(贊美或批判乃至鞭撻),包括了對歷史經驗教訓和規律的總結,對歷史學的探索研討等等。“詩史”在發展中至少涉及了史述、史論、史學三個層次,故對“詩史”實亦不可一概而論。
要說明當孔孟之時,詩史不分實為一家,不須遠求,就在《孟子》書中,便可以看到他把《詩》之原文當作史料運用的例證。
《梁惠王上》記載孟子和梁惠王關于“賢者之樂”的對話。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問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軻 5)。孟子巧妙地將話題引到賢不賢不在于是否因擁有池沼鴻雁而樂或不樂,關鍵是能否與民同樂。他指出,能夠與民同樂,那么即使役使百姓修建池沼,百姓也會樂意,君王也才快樂;如果相反,百姓就會詛咒反對,君王擁有池沼鴻雁也不可能得到快樂。為了證明自己的論斷,孟子引用了正反兩條史料。正面的是《詩經·大雅·靈臺》的“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牣魚躍”(孟軻5)。用周文王修靈囿百姓踴躍從事的例子來闡說“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軻5)的道理。反面例子則是夏桀,引用《尚書·湯誓》“時日害(曷)喪,予與女偕亡!”發出“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軻5)的警告。孟子在這里,完全是把《靈臺》詩的描述當作史實看待的。在他看來,《靈臺》就是《詩》亡而《春秋》作之前的歷史記述。所以此節引用的文字較多,是十二句,四十八字,而不像在其他地方引《詩》往往僅是兩句八個字而已。
這樣的例子,《孟子》書中還有多處。如與梁惠王談到“文王之勇”,引用《詩經·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孟軻31),這是《皇矣》篇描寫“密人不恭,敢距大邦”(31),周文王興師問罪的一節。又如在回答齊宣王自稱“好貨”“好色”時,引用《大雅·公劉》和《綿》,說明只要是“與百姓同之”,好貨好色都不成問題:
昔者公劉好貨,《(公劉)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橐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36)
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綿)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美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37)
這顯然是把《公劉》和《綿》的詩文當作了敘述先王事跡的歷史記載來使用的。
再如《滕文公上》記述滕文公向孟子問“為國”,孟子引《邠風·七月》“晝爾于茅,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榖”(117)教以“民事不可緩”(117)之理,接著引《小雅·大田》論歷代田稅制度的不同與優劣,最后引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118)(《大雅·文王》)的話,鼓勵滕文公以周文王為榜樣既繼承傳統不違舊制,又努力創造新氣象。
《孟子》又一處用《詩經》史料為借鑒論述現實政治的例子,是引用《大雅·文王》篇“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168)來闡釋服從天命與實施仁政的關系。《文王》的詩意是時運一過,殷商后代即使優秀也只能臣服于周。無論大國小國,只有實施仁政才能獲得天佑,而不實施仁政,就猶如《大雅·桑柔》所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熱天卻偏不肯沖涼”(168),完全是悖時而行,必然事與愿違。

二、“詩史”的現代義涵
詩史一詞流傳下來,歷代學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今天也同樣。對追溯梳理其演變過程,做學術史研究自有其必要與意義。但也不妨提出今人的看法,參與到學術的增進與變革中去。
在這里,我覺得聞一多先生《歌與詩》一文中對“詩史”的理解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他對上古時代“《詩》即是史”的闡釋,特別是他對詩歌史系統梳理中提出的幾個主要觀點,值得重視,不宜被輕易否定。






其次,從字詞之源入手探討,難道就那么要不得嗎?王國維不是也用此法、善用此法嗎?比如他的《釋史》一文,開篇即引《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王國維27)以下一路從甲骨文說到金石之文,從《尚書》《周禮》追溯到殷和殷前之“史”,將古文字與古文獻聯系、對照著分析解說“史”之古義。似尚未見有人說他是“字源謬見”。當然,考察字源只是論證之一途,遠非全部。聞先生認為“志”字原含記憶、記錄、懷抱三義,舉例甚夥,推論亦不失嚴謹。但他在文末還是說:“在上文我們大體上是憑著一兩字的訓詁,試測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詩歌發展的大勢,我們知道《三百篇》有兩個源頭,一是歌,一是詩,而當時所謂詩在本質上乃是史”(191),對字源考證的有效性持清醒的態度,沒有宣布唯我獨對,而是特意說明其文是在試測、試述上古詩歌史。今天我們即使完全不用這種方法,仍然能夠充分論證“上古詩史曾經混而不分”的觀點。我們欽佩聞先生,卻沒有聞先生的學力,只好不用字源考證之法,卻并不認為此法一無是處,甚至一涉此法便墮“謬見”。
說過感想,仍回正題。
聞先生講得很清楚,他所說的“詩即史、史即詩”,那是遙遠的古代之事,而且在那時二者也只是性質相通并非完全同一,否則哪還需要二名?人類發展到今天,情況已經變化。今日大家還在言說的“詩史”,早已不是“詩即史、史即詩”之意,也不是“詩即以史為本質”之意,而是在詩、史二分之后,有些詩歌作品中所敘述描寫的生活之“事”、現實之“事”,在人們看來具備了一定的“史性”,可以印證、比照乃至豐富歷史記載的某些方面,甚至觸及某些歷史的經驗教訓或某種歷史規律,從而使這作品具有了史述(或史論、史學)的某些意味。“詩史”是詩歌(文學)創作中的一種現象,也可以說是詩歌(文學)的一個品種或類別,而在文學批評中,則不過是一種評語或概念而已。
聞先生的論證,在我們看來,還可以導出如下的觀點: 當歌、詩尚在二分的時候,歌主抒情,詩主敘事,但抒情敘事是表現手法的不同,并不決然對立,甚且相互滲透,因而詩歌早晚是要合流的,抒情與敘事的對壘性也就早晚要化合為詩歌特質的統一性。而且進一步從根本上講,詩歌中不會有毫無感情色彩的敘事,也不會有絕對無事、無來由的抒情,抒情敘事雖可分剖解析,有不同的側重,卻實難截然割裂。既然如此,一部詩歌史當然只能從頭就由抒情和敘事來貫穿,從而形成并發展出抒敘對壘互動、融滲互競的傳統,而不可能是任何單一傳統的貫穿史。
果然,聞先生在第三節中作出了更精彩的論述:
詩與歌的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結果乃是《三百篇》的誕生。一部最膾炙人口的《國風》與《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詩歌合作中最美滿的成績。一種如《氓》《谷風》等,以一個故事為藍本,敘述方法也多少保持著故事的時間連續性,可說是史傳的手法,一種如《斯干》《小戎》《大田》《無羊》等,平面式的紀物,與《顧命》《考工記》《內則》等性質相近,這些都是“詩”從它老家(史)帶來的貢獻。然而很明顯的,上述各詩并非史傳或史志,因為其中的“事”是經過“情”的泡制然后再寫下來的。這情的部分便是“歌”的貢獻。由《擊鼓》《綠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顯而隱,“情”的韻味由短而長。那正象征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遞增。再進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脹,而“事”則暗淡到不合再稱為“事”,只可稱為“境”,那便到達《十九首》以后的階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樣,在相反的方向,《孔雀東南飛》也與《三百篇》不同,因為這里只忙著講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詩的第二階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處。總之,歌詩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發展是詩第三階段的進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質。(190)

聞先生重視詩的史性,但也沒有忘記詩歌的抒情性審美性。他認為,“詩言志”“詩傳意”“詩緣情”,志、意、情實是一回事,而“‘詩言志’的定義,無論以志為意或為情,這觀念只有歌與詩合流才能產生”(191)。“《三百篇》時代的詩,[……]是志情事并重的”(191),后來人的觀念中卻“把事完全排出詩外”以至“詩后來專在《十九首》式的‘羌無故實’空空洞洞的抒情詩道上發展,而敘事詩幾乎完全絕跡了,這定義(指‘詩言志’)恐怕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191)。聞先生把《詩三百》視為抒敘良好結合的典范,又認為出現《十九首》式的抒情詩,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在詩中排除“事”而過偏地強調情志意(“詩言志”理解的狹隘化)的緣故。這個說法非常符合中國詩歌史的實際,而又極具啟發性,對我們研究詩歌敘事傳統,用抒敘兩大傳統貫穿全部詩歌史文學史,極具指導意義。


三、“詩史”的核心是敘事,詩史傳統在敘事傳統中

的確,詩史言說雖然紛繁,但在眾多說法中,最有價值、能對諸說起到提綱挈領作用的,正是敘事說。
史的本質和核心要義是事與記錄事實,簡言之即敘事。“史”從誕生伊始,無論是指人還是指此人之行為、活動或其產物,皆與書策記敘之事相關。王國維《釋史》引《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引《書·顧命》“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引《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女史掌內令”等,謂“周六官之屬,掌文書者亦皆謂之史,則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為事”(王國維28—32)。而史官所作、所讀、所藏之書,則皆與記敘史事、史言有關。史與事的關系不僅可從字源追尋,尤其應以事實證明,亦可從道理闡明。《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敘》:“茍無事跡,雖圣人不能作《春秋》,茍不知其事跡,雖以圣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397)圣人如此,何況我輩?史既如此,詩又何嘗不如此?“詩史”當然更不能不如此。敘事遂成為“詩史”與“史”發生關聯的根本基礎。
不過,“詩史”畢竟是詩而不是史,即使是具有史性的詩歌,也不能丟失抒情、言志和表意的功能。于是兩相融和,則凡具“史性”之詩,即“詩史”,其本質特征便該是富于感情色彩地敘述評說歷史之人與事,此類詩之敘事成分必然較重,且所敘之事又當多與國族命運遭際相關,否則不夠稱“史”,但也須不乏感情(包括議論)色彩和感人力量,如若質木無文味同嚼蠟,也就不足稱“詩”。所謂“詩史”其義大抵如此,并無其他特異神秘之處。
再看得通達些,所謂歷史乃是往日之現實,而今日之生活,過后也就成為歷史。“詩史”也者,就內容言,號稱反映或表現歷史,換言之則是記述昔日現實生活點滴而已。而就藝術手法言之,“詩史”的寫作是在抒情、敘事二法中,偏于敘事,而不廢抒情,但多用客觀素材,多關注與觀察體會他人事跡境遇和心態情緒,甚至干脆化身為角色,代他人(尤其是向來極少話語權的人)發聲,而不是僅僅以詩人自我為中心抒發一己感情。因而一般說來,“詩史”中攝入的具體生活事實乃至故事、畫面、人物動態等比一般抒情詩皆較多較富,作者感情往往寓于敘事之中,較少直白呼喊,故藝術風格也往往較為沉實而不空泛虛浮。前人總結創作經驗,有云:“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馀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魏泰322)大概“詩史”就有這種好處。被稱為“詩史”的作品,至少不會如聞一多先生批評的那樣“羌無故實,空空洞洞”。
詩史須具“史性”,也應具有詩性,已如上述。也許后者還須再作強調。“詩史”是詩,畢竟與規范的史書不同,它帶有更強烈的感情色彩,不但記什么不記什么、何事用濃墨何事用淡筆甚至略去,都是帶著感情有意選擇的,而且其表述(選詞擇字造句修辭等)必有傾向,往往在一字半句之微中透露愛憎,寓含褒貶,顯示美刺,表達方式往往含蓄用晦,變化莫測,時而直賦,時而比興,隱喻有之,影射有之,皮里陽秋有之,嬉笑怒罵有之。這就是史詩或詩史作者從主觀出發的敘事干預,是其文學性之妙用和所在,也是其審美意味之所由來。“詩史”是史性、文學性和審美趣味的精巧結合或深度融合。后世人們重視“詩史”,就是因為“詩史”猶如合金鋼,兼有二者的優長,形成了更高的思想強度和美學價值。通過詩史的文學性去探索其隱含的史性,可以在盡享審美樂趣的同時收獲認識價值,啟發更深廣的思考。

鑒于題旨,這里我們著重圍繞詩歌敘事傳統來談。自《詩經》之后,歷代堪稱詩史的作品,乃是由《詩經》史詩孳乳而生。楚辭,漢詩,漢樂府,魏晉文人詩,南北朝樂府詩與文人詩,乃至唐宋元明清和近現代的文人詩和民間詩歌中,都有堪稱史詩和詩史的好作品。直至今日,“詩史精神”仍是許多詩人作家自覺秉承和追求的良好傳統。杜甫則是在漫長的中國詩歌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尤其是在“詩史”之發展演變史上,杜甫因其創作特色與成就,因其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而居于獨特的高峰地位。“詩史”雖非由杜甫開創,非其獨家專利,也不能說杜甫的任何一首詩都是“詩史”,但杜甫作品中堪稱“詩史”者確多,且創作成就特高,“詩圣”之譽與“詩史”之名相得益彰,相互增價,杜甫成為中國“詩史”的首席代表。若就這一點而言,孟棨《本事詩》倒是功不可沒。

杜甫的功績正在于以優異的創作實績抗衡了這個語境,扭轉了積習甚深的詩壇風氣,從而使詩歌重新回到抒情與敘事雙線交融并進的健康道路上去。具體來說,是在安史之亂造成的國破家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以其一系列史性和文學性都很強的作品,使詩歌的敘事功能,詩歌的史性內涵,得到全面的發揚和提升,顯示出巨大的思想力和美學能量,使詩歌關懷現實、記錄歷史的職能重新獲得人們的注意和重視,使數百年來幾乎漸被遺忘的《詩經》史詩敘事傳統,重新成為人們關注和熱愛的對象,不但使這一傳統得以延續,而且在當時就產生很大的影響。以元稹白居易李紳諸人為代表的新樂府創作在中唐興起絕非偶然,而杜甫的正面影響則更貫穿一千多年,至今未衰。杜甫所接續和弘揚的《詩經》史詩和樂府民歌的精神,也就是中國詩歌抒情和敘事并存互動的優秀傳統。
以杜甫為典范和代表的敘事傳統,其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多方面研究闡述。許多研究杜甫的論著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于此,可謂成果累累。在此基礎上,我們對中國詩歌敘事傳統的內涵要義,試作概說如下:
一、中國詩歌敘事傳統往往更為關注歷史,也更關注現實生活,把創作的視線和筆觸更多地超越個人而投向客觀世界: 他人、社會(甚至底層)和國族之事,表現出對時事、政局、新聞、街談巷議、民情風俗等的興趣,且善于將其攝入筆下,作出多樣的載錄。而在種種復雜的社會矛盾面前,往往能以國族的安危利害作為關切的首要問題和判斷是非、采取寫作策略的根本依據。


傳統的這個內涵也限制了“詩史”之稱的運用范圍。前文論到“詩史”之本質實即詩與生活的關系,故“詩史”既有其崇高性,又并非神秘稀奇得高不可攀。那時留下一個漏洞: 那么是不是任何反映一點兒生活內容的詩都能稱為“詩史”?“詩史”概念豈不過于寬泛?闡明了敘事傳統的這一內涵,當可避免這個誤解,等于打了一個補丁。
二、敘事傳統不廢以個人為中心的抒情詠懷,但強調將家庭的悲歡離合、個人的喜怒哀樂與國族安危大事緊密結合,把小家的聚散苦樂放在大家乃至國家安危存亡的背景之下,形成崇高而感人的家國情懷。
杜甫在這方面表現最為突出,膾炙人口的作品亦多,如五古《北征》《羌村三首》,五律《春望》,又如被譽為“生平第一首快詩”的七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均是史性很強的敘事與寫懷言志的抒情和諧融合,標志著被稱為“詩史”的杜甫作品在思想和藝術上能夠登臨怎樣的高峰,也標志著詩歌敘事傳統具有怎樣的親和力和情感容量,更標志著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雖有各自的側重和專長,卻具有天然的親緣關系。
三、敘事傳統強調明確的彰善癉惡意識,愛憎鮮明,褒貶有力,贊美英雄仁人,諷刺丑惡宵小。或以為這是受到“史”的影響所致,其實正好相反,孟子那句名言引孔子說:“其義則丘竊之矣”(孟軻192)。這個“義”即指《詩三百》所寓含的褒善貶惡之義。詩具美刺,曾對史述產生過重要影響。孔子《春秋》能使亂臣賊子懼怕的“一字褒貶”法,就是從《詩經》的比興美刺學過去的。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的史學宗旨和撰寫原則又長期反哺詩人,使中國詩歌,特別是那些貫徹了詩史意識和詩教精神的敘事性詩歌,大多是有為而作,有的放矢,對培育民族正氣和儒家倫理精神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四、表述樸實簡潔,但不廢反復詠唱,也不廢議論抒情。史述對文字的要求是簡潔,劉知幾《史通》從史家立場出發,對史述的敘事提出了明確要求,那就是信實簡要,文約事豐。“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如何才能簡要?他提出了省句、省字、點煩、用晦等法(152—71),并親自做了“點煩”趨簡的示范。一方面是這種理論的影響,一方面也是詩歌文體自身的要求,詩歌自然不能像文章那樣細致狀寫、任意揮灑,而必須用有限的語詞(律詩還須合律)來描述歷史事件或概括歷史現象,而這種簡約的敘述還必須蘊含作者想訴說或想宣泄的深意。應該說,中國詩歌敘事傳統的這一要求相當高而苛刻,也正是這種要求造就了中國詩歌內涵的深刻和藝術的優美,但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詩歌敘事、描寫的舒展縱放。
五、風格溫柔敦厚,符合“詩教”的原則,具體而言,是美刺褒貶均須合度有節,而不過分。這不但是中國詩歌的傳統,也是儒家社會倫理的重要內容之一,實際上全面滲透貫徹在古今中國人的生活和理念、品格之中。這里不僅有掌握“度”的難題,實際上還存在著深刻的自相矛盾。劉知幾主張史必實錄、痛惡曲筆,同時卻又認可“避諱”:“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183)顯然,當求真與避諱沖突時,讓步的便只能是求真,否則便違背了詩教。上面提到劉知幾提倡史述含蓄用晦,也與此有關。
除上述外,中國詩歌敘事傳統,即詩史傳統、詩史精神,當然還有其他種種內容,只是這五點似乎比較明顯而重要。
僅就此五點而言,這個傳統自有許多值得肯定和繼承的正面精神,如熱愛國族而勇于奉獻、甚至勇于舍棄個人的精神,其基本面無疑值得發揚光大,而且只要中華民族存在,這種精神就不能也不會泯滅。然而,即使正面之中亦不是不含負面,如因顧全大局而不得不對官府吏員的兇殘暴行有所容忍,便是正面中所含的負面因素,而且明知其為負面因素,要在正面行為中剔除和避免之卻還相當困難。至于詩風的溫柔敦厚,固是中國詩歌的美學特征之一,也是中國人素質和品格的一種優美之點,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應結合歷史和時代背景對之做具體分析,充分看到其負面作用和影響。這種矛盾現象既規定了中國詩歌的特點,也造成了它的弱點和缺陷。如果說掌握分寸、褒貶合度是必要的應該的,那么為尊者和親者諱卻必然使詩歌的史性和思想銳利深刻的程度大打折扣。而當其在國勢孱弱的情景下,就更易于虛偽軟弱、自欺欺人甚至與對強敵的奴顏媚骨相混,成為戕害和背叛國族的毒藥。
中國詩歌敘事傳統就是這樣有其優秀卓越的一面,也有其不良落后的一面。我們實事求是地揭示它,為的是繼承發揚前者而努力克服后者。尤其需要說明的是,中國詩歌傳統可以而且應該從多角度多方面進行探討總結。從藝術表現方法的不同入手,將其概括為抒情敘事兩大傳統,不過是許多角度中的一個而已。“詩史”固然可以是評價好詩的一個標準,但好詩并不一定非得“詩史”不可。文學是萬紫千紅百花爭艷的世界,任何“唯一”“獨尊”的念頭都是要不得也行不通的。
注釋[Notes]
① 歷代與當代言及“詩史”或討論“詩史”問題的論著,包括博碩士論文數量繁多。英年早逝的學者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 三聯書店,2012年)對此作了系統梳理。此書之后,有關論文仍多。本文涉及某些論文,將在后面相應處注出,這里就不羅列了。
② 據陳尚君考證,《本事詩》作者孟棨,應作孟啟。我相信陳先生的考證,這里只為讀者習慣,暫用舊名。
③ 請參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引言及第一章。孟棨《本事詩》:“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又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史臣曰:“至于先士茂制[……]并直舉胸臆,非傍詩史。”或謂“詩史”指《詩》《史》二事,然王世貞則據此曰“然則少陵以前,人固有‘詩史’之稱矣。”參王世貞: 《藝苑卮言》卷三,《歷代詩話續編》(中),丁福保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第991頁。
④ 杜集作《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浦起龍云:“前十韻敘其才名寵渥,以及去官之后,文酒相從。后十韻,傷其蒙污被放。為之力雪其誣,訴天稱枉。”見《讀杜心解》卷五之二(北京: 中華書局,2015年)第718頁。
⑤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北京: 三聯書店,1986年)認為孟棨《本事詩》所記“詩史”“這種話本是當時流俗隨便稱贊的話,不足為典要。”(188)既是流俗之語,早就存在的可能是存在的。
⑥ 參看彭敏:“詩史: 源起與流變”,《求索》1(2016): 152—56。此文認為“詩史”觀念的實踐從先秦至明清一脈相承,詩史之實遠早于其名,并概略而系統地論述了宋前“詩史”傳統的流變。筆者贊賞其觀點。
⑦ 請參[波蘭]埃娃·多曼斯卡編著《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⑨ 討論孟子這段話含意的論文,至今不斷,見解各有側重,均有參考價值,這里不能一一引用。其中如劉懷榮:“孟子‘跡熄《詩》亡’說學術價值重詁”,《齊魯學刊》1(1996): 63—65;馬銀琴:“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重詁”,《上海師范大學學報》3(2002): 74—79;魏衍華:“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發微”,《理論學刊》4(2010): 105—108;蔡英俊:“‘詩史’概念再界定——兼論中國古典詩中‘敘事’的問題”,《語言與意義》(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3—83頁,等,對此皆有專論,觀點基本與楊伯峻《孟子譯注》一致。楊氏此節譯文:“孟子說: 圣王采詩的事情廢止了,《詩》也就沒有了;《詩》沒有了,孔子便創作了《春秋》。(各國都有叫做〈春秋〉的史書)晉國的又叫做《乘》,楚國的又叫做《梼杌》,魯國的仍叫做《春秋》,都是一樣的。所記載的事情不過如齊桓公、晉文公之類,所用的筆法不過一般史書的筆法(至于孔子的《春秋》就不然)。他說:‘《詩》三百篇上寓褒善貶惡的大義,我在《春秋》上便借用了。’”(卷八193)錄以備考。
⑩ 即使僅引用二句八字,也是在運用史料,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但引得多,史料意義更明顯。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杜甫: 《讀杜心解》,浦起龍撰。北京: 中華書局,2015年。
[Du, Fu.A
Kernel
Interpretation
of
Du
Fu
’s
Poems
. Ed. Pu, Qil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孟軻: 《孟子譯注》,楊伯峻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
[Meng, Ke.Note
on
Mengzi
. Ed.Yang Bo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孟棨: 《本事詩》,《歷代詩話續編》(上),丁福保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
[Meng, Qi.Benshishi
.A
Sequel
to
Poetry
Notes
across
Dynasties
. Ed. Ding Fub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劉知幾: 《史通通釋》,浦起龍通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Liu, Zhiji.Note
on
Shi
Tong
. Ed.Pu Qilo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王國維: 《王國維集》第四冊,周錫山編校。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Wang, Guowei.Col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 Vol.4. Ed. Zhou Xish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魏泰: 《臨漢隱居詩話》,《歷代詩話》(上),何文煥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1年。
[Wei, Tai.Poem
Theory
of
Lin
Han
Yin
Ju
.Poetic
Remarks
in
Past
Dynasties
.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聞一多: 《聞一多全集》第1冊。北京: 三聯書店,1982年。
[Wen, Yiduo.Collected
Works
of
Wen
Yiduo
. Vol.1.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蕭統編選: 《文選》,《四部叢刊》影宋六臣注《文選》本。
[Xiao, Tong, ed.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The
Four
Categories
of
Books
.]永瑢等: 《四庫全書總目》(上)。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
[Yong, Rong, et al..Complete
List
of
Si
Ku
Quan
Shu
Collection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張暉: 《中國“詩史”傳統》。北京: 三聯書店,2012年。
[Zhang, Hui.Poetry
as
History
:A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