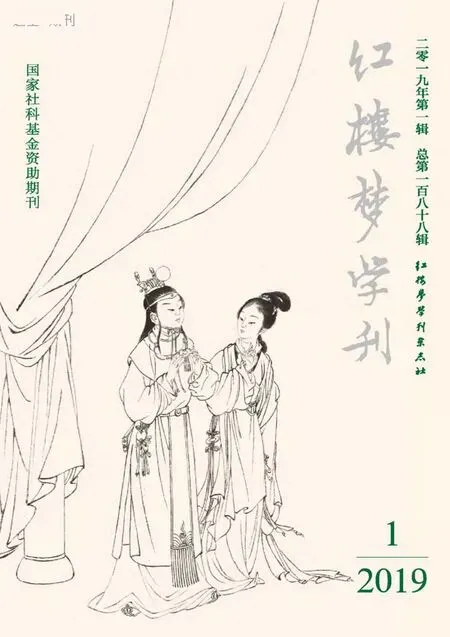仁厚長者李希凡
希凡先生是在我們沒有任何精神準備的情況下,遽然離去的。前天還在電話里聽到他的聲音,今忽杳然。一種巨大的空白和失落襲來,生前種種,宛在眼前。這里只能就我的直感,追憶片斷,難窺全豹。
希凡從《人民日報》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在1986年,那時已五十九歲,進入人生的中老年。也就是說,他的后半生是在研究院度過、在這里離退的。我認識他雖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但較為熟悉還是在他來院之后,真正接觸較多是近十幾年的事,在這期間,每年有少則三兩次多則十來次的見面,電話則不曾間斷。在他晚年相對寂寞的歲月中,我是一個能夠傾聽、易于溝通的晚輩友人,在我心目中,希凡的形象也較前更為親和真切,他是一位仁厚長者。
他的仁厚,以我觀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藝術研究的眷眷之情,是一種懷念,包含著欣慰和感激。
一是對紅學事業的拳拳之心,是一種摯愛,包含著關切和期望。
先說第一方面。他曾多次說過,“不后悔來藝術研究院”,雖則調令逋出,告狀不少,阻力不小,但他決心已下,且得到時任文化部長王蒙的支持。來院后,他在任內做了實事,并未虛度。
說實在的,李希凡從《人民日報》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很大程度上是角色的轉換。從一線新聞單位到研究單位,性質不同;從直面現實發言寫文章到沉淀積累靜心搞研究,特別是從自己上陣到領導眾人,位置不同。希凡從來未做亦不擅行政工作,尤其不擅理財開發,曾因當法人代表而被債主包圍,十分狼狽。但他懂得研究院的主業是搞研究出成果。他尊重前輩,愛惜人材,在政治風波中竭力保護了一批人,使研究院不傷元氣,我曾在過往為文中提及。這里只想說,希凡在回首這一段經歷時有兩個關鍵詞“前海學派”“藝術通史”,令我印象深刻。
所謂“前海學派”并非實體,我理解是對基礎研究、對各學科奠基工程的重視,是對群策群力樸實學風的肯定。近年他還充分評價我所參與的紅學基礎工作為“前海紅學”。希凡在職期間,規劃和支持了此類項目,自身雖無暇寫作,而研究院早期各種成果的背后有他的辛勞,為此付出他是心甘情愿的。
另一個不斷提到的關鍵詞是“藝術通史”,即《中華藝術通史》,這是他退休之際所領的一個項目。在國家藝術科學規劃會上,他提出了兩個項目,藝術概論和藝術通史,前者被北大領走,后者無人問津。他掂量再三,終于鼓足勇氣認領了下來。
此舉還真有點“犯傻”。退休了,本可放松下來,寫自己的東西,駕輕就熟,照樣著書立說;而他卻選擇了吃苦受累,去挑擔子,進入那并不熟悉充滿挑戰和風險的領域。當年院內外不乏質疑甚至輕蔑之聲,他要承受多方面的壓力。外部的經濟壓力,沒有錢,錢不夠;更吃重的是人才壓力、知識積累和理論提升的壓力。對他個人而言,須重新學習、拓荒開疆。他給我的電話很多是有關通史的,比方說坦陳自身知識結構的局限而“惡補”,比方說感念北師大出版社的投入,比方說如何請專家講課,比方說經歷十三次編委會每次講話都自己寫稿,更多的是提到編寫人員特別是分卷主編,欽佩他們的學識、感謝他們的堅守。他懷念已故的、牽記健在的,總說稿酬很少,并無名利。每有通史消息,如評論、獲獎、譯成外文版等,他都會很快告知,欣慰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十分可貴的是他的凝聚力。希凡不僅是學者,更是學術帶頭人。長時段集結一批優秀學者共同完成一項學術工程,談何容易,沒有堅韌意志和學術民主是做不到的。幾年前,《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談會上有一位藝術通史骨干也是我北師大校友說,原先以為李希凡鋒芒尖銳,存有戒心,多年相處,“他真是一位忠厚長者!”誠哉斯言。
我曾說,希凡為官一任,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留下了一張學術名片。當然,他很清醒,不足未善多有,但無論如何,填補空白的首倡之功不可沒。他有理由欣慰。不討巧,不避難,唯醇正仁厚者方能為之。
以下再說他對紅學事業的拳拳之心。
人們看到,來院之后的幾十年間,李希凡大大淡化了他“紅學家”的角色。客觀上職責所在任務壓身,他沒有時間專事紅學寫作和活動,主觀上他從不以紅學家自詡,更不以“小人物”光環炫人。但他熱愛《紅樓夢》,心系紅學,竭盡全力支持和推動以馮其庸為代表的紅學同道,開辟了紅學新時期。
順便說一下,李希凡和馮其庸二位,個性不同、學養不同,馮較多藝術氣質,李更具理性風范;堅強的事業心和報國的大情懷使他們友誼深固,互相支撐、互為補充。新時期的紅學活動,馮其庸在前臺,李希凡似只在幕后。
然而李希凡是不可或缺的。當歷史進入2016年,也就是希凡九十歲的時候,才有了“李希凡與當代紅學”的學術座談會,這是第一次,如今也是最后一次了。在這個會上,我鄭重提出:歷史選擇了李希凡,歷史檢驗了李希凡,他是新時期紅學航船的“壓艙石”。
紅學是顯學,體量巨大,影響廣泛,眾聲嘈雜,牽動多方。這艘航船唯有行穩,才能致遠。“壓艙石”對穩定船體、把握航向,關系至大。茲舉大端:
首先,促成了紅學界的大團結。1980年開了首屆全國紅學研討會,成立了中國紅樓夢學會,之前創辦了《紅樓夢學刊》和紅樓夢研究所,在紅學歷史上都屬于首次。須知紅學界的大團結來之不易,紅學淵源深長、路徑繁復,老中青、東西南北、高等學校和研究單位、資深和新銳、考據和評論……各路神仙、各有訴求。其間李希凡和藍翎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他們順應潮流、不負時代、協調各方、瞻顧大局,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實現了紅學空前的大團結。中國紅樓夢學會的第一任會長是吳組緗,第二任是馮其庸,李希凡始終是副會長。
與此同時,他協助和支持馮其庸為新時期紅學搭建了一個起點很高的平臺。時當改革開放之初,學術開始復蘇,紅學猶如一枝報春花,她的綻放得到了格外的關注和多方的澆灌,只要列舉當年參加紅學會議和活動的人物就可見盛況。不必說原本就是治紅學和文史的俞平伯、顧頡剛、吳世昌、吳恩裕、周汝昌和本院的王朝聞、郭漢城等,更有文化教育界的重量級人物沈雁冰、王昆侖、葉圣陶(沈老為題刊名,葉老為看校本,王昆老寧可人大常委會請假也要來開紅學的會)。特別是文藝界的資深領導人周揚、林默涵、賀敬之和本院的蘇一平都給予熱情支持以至親自與會。至于為刊物題詞、賦詩、賜稿的就更多了,有吳組緗、啟功、夏承燾、端木蕻良、霍松林,豐子愷、聶紺弩、陳從周、姚雪垠、舒蕪等,從大學教授到著名作家,濟濟萃萃。當然,還有一大批與李希凡馮其庸年輩相仿的學人:藍翎、蔣和森、陳毓羆、魏紹昌、魏同賢、蔡義江、吳新雷……名家之多、層級之高,均屬空前。應當說,此乃拜時代所賜、改革開放的風氣所賜,今天想來不禁神往。李希凡促成和親歷了這一盛況,深刻地意識到紅學的興旺和延續乃是一種歷史的責任。
其次,作為“小人物”,希凡自己不提起、不矜持(他的七卷本《文集》連1954年的文章也沒有收)。然而社會上多議論、多質疑,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對此,李希凡的基本態度是“堅守史實,任由評說”,顯示出“壓艙石”的定力。
在紅學界以至學術界,可以說很少有人像李希凡那樣,受到如此之多的誤解、曲解、猜測、質疑以至污蔑謾罵,甚至海外的謠言,十分離奇,居然也有人為之傳播。筆者閉塞所知甚少,只是聽他說起,那些海外奇談,匪夷所思,不勝其煩,只能不予理睬。然而,面對國內許多對此抱有興趣的學人和傳媒,不論是想重新評價或探索研究,都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就有了幾十年來不斷的訪談。希凡出于歷史當事人的責任,以極大的耐心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采訪,向采訪者提供史實,回答各種問題。希凡本人只寫過有限的回憶文章,而對外界以至身邊的各種看法和著述,從不干預。
對于一個歷史事件,評說可以見仁見智,然而歷史事實只有一個。在維護歷史真實這一基本點上,希凡從不含糊、旗幟鮮明,顯示政治的定力和學術上的獨立精神,從不隨風搖擺,隨人俯仰。
遠的不說,只說兩件近事。一是2011年我在海外探親,偶爾從網絡上看到一篇“揭秘”1954年的長文,回來后詢及希凡,其時他老伴病危、心力交瘁,然因事關重大,必須澄清,他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自己口述由大女兒李萌筆錄,予以全面回應。事實俱在,本無秘可揭,他以當事人的責任,維護歷史現場,斬釘截鐵地說:“誰都休想讓我把‘有’說成‘無’!”
另一件時間更近,已到2016年,外地的一位紅學研究者張勝利正撰寫一本關于王佩璋女士(俞平伯先生助手)的專著,有一個重要史實要向李希凡先生求證,即所謂1954年由王佩璋之文引發了李希凡藍翎與俞平伯先生的商榷(即“第一槍”) 是否屬實,此說的來源是《紅學:1954》,流傳甚廣。李希凡雖早有此著,但與其文藝觀、世界觀歧異,不想與相差四五十歲的青年爭論,亦料想不到此說影響之廣。如今有研究者來認真求證,希凡先生以十分鮮明的態度鄭重地做了書面答復。老實說,希凡要求書面作答大出我的意料,我自愧缺乏他那永不褪色的革命激情和堅韌意志。他在答復中嚴正陳明:以事實論,當年他根本不認識王佩璋,從未謀面,亦未讀過她的文章。以邏輯論,一場觸發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大討論竟由俞先生門下的一篇版本文章引起?無此可能。以情論理,說李、藍本無學術勇氣,是從王文那里借了膽,這未免太看輕了當年“小人物”的氣概了。在這一字一句答復的最后,不禁感概萬端地說:“我雖已幾近九旬,卻還是為六十多年前的戰斗豪情(一生只有這一次)被漫畫化,感到屈辱,不得不出面一辯。”這是李希凡生前的最后一文,十分沉痛。
由此,可以感受到李希凡的剛正之氣和坦蕩之心,見出其經歷風雨摧折而始終屹立的堅韌品性。
復次,“壓艙石”的作用,還在于維護正常的紅學生態、抵制各種歪風邪氣。
作為一個經歷風雨的長者,李希凡有足夠的度量容納不同的學術意見,愛護青年,平等待人;但他決非無原則的好好先生,不是庸俗的和事佬。
比如,他對一切戲說、揭秘、解構及新老索隱說“不”,那火爆一時的“秦學”他是不贊成的。他認為《紅樓夢》不需揭秘,并非皇權爭奪和宮廷內幕的演繹。無論是接受采訪或發言為文,他都重申《紅樓夢》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的審美品性和不朽價值。
又比如,他對小說作者的種種新說也不以為然,始終維護曹雪芹的著作權。在曹雪芹逝世250 周年之際,還發文見于報端(《中國文化報》2013年6月26日),并參加各種紀念活動。他在文中列舉了大量內證、外證后指出曹雪芹是《紅樓夢》、即八十回《石頭記》的真正的作者“無可置疑”。“至于非給《紅樓夢》另外找出一個作者,不管那些遐想出來的論證說得多么天花亂墜,都不如曹雪芹親友們的這些文字確證更有力,更有信任度。”
再比如,也是更為切近之例,當2015年初,邪風起于蕭墻,是他以高度的敏感識破了所謂致主編信(兼致我)的用心,第一時間電話告知了我,“你對辭典質量的善意被誣為‘破壞’,信里充斥著攻擊,你要通過組織、據理申訴,維護學者的尊嚴。”他建議申訴并與其庸共同為我作證。在此后的幾年間,尤其在另一主編馮其庸病危和逝世后。李希凡縈繞于心念念不忘的是《紅樓夢大辭典》的重新修訂,不遺余力地推動、促進。他曾提出自己出資幾萬元作為啟動之用,不斷提出要請客慰勞大家編寫工作的辛勞。其庸逝后重發他的《相知五十年》,他特別提出,倡揚馮氏的研紅之路,“不只是寄托自己的哀思,而且有益于糾正當前紅學的亂象。”最近幾個月他一再說要寫一封信遞上去,為辭典、為刊物、為紅學,孰料信未成而人已去……對紅學事業可謂鞠躬盡瘁,至死不忘。
希凡仁厚,不是無底線的忍讓,而是有剛正之氣為依憑的大仁。他喜論辯,是為真理而辯,光明磊落,可以說,他一生沒有什么私敵,“仁者無敵”。我從這位仁厚長者那里感受到的是正氣和溫暖。
希凡仁厚,不是無是非的茍且,而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定力。他不像某些知識分子那樣怨天尤人,滿腹牢騷。當我時常因社會的負面現象而喪氣時,電話那頭會傳來他的聲音:“你放心,這個世道自有擔當的人。”每有令人振奮的國內外大事發生,他會立即打個電話過來,直抒觀感。
希凡仁厚,愛才舉才,更能洞見人的深層品性,察知正邪、真假、偏私。他幫助和提攜過許多人,得失長短,心明如鏡。他從不強加于人、強人所難,比如他受老賀(敬之)所托為其友寫序欲委我,我不應終于作罷。他看似大大咧咧,其實善解人意,舉最近之例,他給大辭典修訂負責人專致一信,陳明修訂目的在學術,特別提出“啟祥同志就不要擔任什么名義了,她還是編委”。這真是說到我心里去了。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辭所長至今,并未汲汲名利,希凡知我心跡。
回顧這段時期,他雖離退居家,卻關心世界大勢、國家前途尤其是文藝現狀。我常驚嘆八九十歲視力有限的老人還能看幾十集的電視連續劇,從《北平無戰事》到《傳奇大掌柜》都是他推薦給我的。他能記住許多劇情的橋段,叫出許多演員的名字。有一次(2017年10月21日)電話打了個把鐘頭,詳細復述故事情節,點評表演得失,竟然是地方臺節目。他常說,還是有肯吃苦的導演,會表演的新人,有生活氣息的作品。然而當文化部文聯偶爾請他開會或征詢時,他會對當下文藝界的歪風亂象痛加指斥、直言不諱。我感嘆老李是個天生的文藝批評家,他對文藝事業如同對紅學事業一樣,關切牽記,期盼風清氣正,達到真正的創作和批評的繁榮。
最后我想說,作為曾經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掌門人的李希凡、作為《中華藝術通史》學術帶頭人的李希凡、作為新時期紅學“壓艙石”的李希凡,當然,還有文藝批評家的李希凡,單是那多卷文集顯性著作是不足以概括其貢獻的,他在背后的默默付出和傾力支持、他的仁厚風范和磊落胸懷,是留給我們的可貴精神遺產。
生活就是這樣,當你失去了什么就會加倍地珍惜。希凡先生離去帶來的失落在此,今天追思的意義也在于此。
本文收束之際將發之前距希凡離世已近一月,回想10月29日晨接她女兒李芹電話如驚雷震心,茫無所措、思緒紛然,曾草一聯今稍修葺,以寄哀思:
大音希聲 不同凡響 文壇驚艷小人物
風雨歷煉 初心不改 紅學痛失壓艙石
(注:首句為九十壽辰祝詞,末句為多篇悼文題目)
2018年11月1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