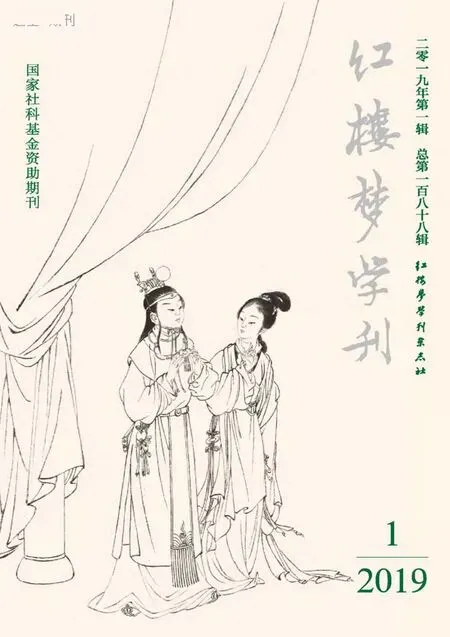熱毒·冷藥·雪中高士
——釋、道哲學光照下的“冷香丸”及其文化寓義
內容提要:“熱毒”是釋、道哲學中極為重要的“精神喻象”,由“熱”(躁、火、焚)到“冷”(靜、清、寧)往往象征著個體生命由耽溺癡迷走向清凈解脫的過程。《莊子》的“飲冰祛熱”之旨與佛禪的“清涼”境界經過不斷的文化承續與演變,形成了“吞梅餐英”“嚼雪飲露”“飲冰食蘗”等一系列與之精神貫通的“同質性”的意象群,“冷香丸”就是對此意象群的高度融煉與創造性升華,其中凝融著“高士人格”的文化基因。曹雪芹通過“冷香丸”在進行一種價值的調和與扭轉,借茲滌蕩已被世俗化、鄉愿化、功利化的儒家價值觀的積垢暗塵,去消解紅塵癡迷的熱瘴煩惱。
寶釵第一次出場為第七回,曹雪芹對其形貌風神略作點染后卻濃墨重彩地鋪陳了與她相關的“無名之癥”與“海上秘方”。原來寶釵因從娘胎里帶來的一股“熱毒”,犯病時出現喘嗽等癥狀,世間凡藥皆不中用,后有癩頭和尚授以“冷香丸”之“海上仙方兒”,得以療治。然而這煞有介事的“熱毒之癥”卻如空谷來風一般,在一場炫目新奇的“首秀”之后,便戛然而止,再無照應與渲染,寶釵這樣的“登臺亮相”極為耐人尋味。就前八十回來看,寶釵身體素來清安,其病若何?是身病,是心病?抑或此段描寫只是作者的文字游戲,以悅諸看官眼目?歷來《紅樓夢》的讀者無不為“冷香丸”的新奇雅逸所傾倒,同時對其解讀也眾說紛紜。或缺乏文獻依據,鑿空立論,弛騁臆說;或拘于文本表層敘事而浮略闡釋,未悟深旨;更有甚者以科學實證之法,結合中西醫學,欲考此藥之實際效用,諸家雖各顯神通,實則并未探得驪珠,識芹真義。在筆者看來,此病、此藥并非“寫實”性描寫,而是具有人格標識與哲理玄思的象征符號、隱喻意象,其中蘊藏著濃縮了的文化信息,常秉具輻射全篇或點醒本旨的作用。只有通過“文化尋根”與“同質聚焦”的方式,將諸多內涵相通的意象放置在“紅樓文本”與“文化傳統”的對話結構中,沿波討源,探賾索隱,方可尋獲驪珠,避免無根游談與穿鑿附會之弊。故筆者意欲在堅實的文獻考據基礎上,擬通過文本解讀和文化闡釋的融合,以期對“冷香丸”之文化淵源、象征意旨及同人物塑造間的呼應關系做出探析,借茲進一步呈現作者措辭立象的幽意深旨。
一、“熱毒”(內熱)之癥的釋、道哲學底蘊
“冷香丸”之效用原為醫治“熱毒”之癥,此病在傳統醫學中甚為常見,《中醫大辭典》即將其所涉之病類分為三種。然從更深層次的文化角度考查,“熱毒”乃是釋、道哲學極為重要的“精神喻象”,由“熱”(躁、火、焚)到“冷”(靜、清、寧)往往象征著個體生命由耽溺癡迷走向清凈解脫的過程。“熱”字在道家思想中極富哲理意味,《莊子·外物》云:“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于是乎有僓然而道盡。”人常因榮辱得失、利害窮達而心火熾烈,不得清寧。“內熱”是與“焚和”相聯類互文的另一個喻象。《則陽》指出人如果背離天性真情,就會患有“內熱溲膏”之類的惡疾。《達生》描寫了一位練達世情的“鄉愿”式人物——張毅,他為了獲得各色人等的“贊譽歡心”,刻意營構,既使對卑微低賤者亦謙恭好禮,然而最終勞精悴神,“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莊子》此篇以“達生”標名,即是要人通達生命的真正價值,從而摒除各種外欲之引誘,心神寧寂,事事釋然,回歸到得之于天,純然本真、自由超脫的本性之中。總之,“內熱”患者在熾盛激蕩的欲求心、偏執心的驅使下,沉迷于塵俗物欲,以致迷失自我的真性本源,他們“思慮紛擾,不能內省,一意外慕,不求諸已,以致心火上炎,血脈錯亂而生此疾”,可謂身心相依且相害也。因此,在這種“熱昏”狀態下,道家哲學所提倡的清寧虛靜、淡泊內守,實乃切重人心疾弊的一味“冷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莊子·人世間》中創造出了“飲冰祛內熱”的經典文本,“冰”成為帶有文化寓意可供“清熱解毒”的“藥食”意象。楚大夫葉公子高接受國君任命而出使齊國,由于害怕有辱使命,故焦燥煩懣、患得患失,“朝受命而夕飲冰”,意欲借此消解“內熱”。成玄英云:“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愁,內心熏灼。”至此,“飲冰”與“冷香丸”雖形質不同,然就“祛內熱”的效用而言,已有了某種潛通暗應之處。
“冷香丸”的配方原本即為和尚所贈,故此藥的佛禪“因緣”,頗堪尋味。釋典中常將佛喻為“大醫王”,《雜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佛、菩薩如同醫生一般善于分別病相,曉了藥性,治療眾病。《紅樓夢》中和尚贈藥的描寫即根源于釋典關于“醫王救世”的敘述。此外,佛教常將人內心的煩惱塵垢、貪嗔癡欲等與“熾熱燃燒”的“烈火”聯系起來,形象地稱之為“熱惱”“內熱”“熱毒”“煩熱”,諸如此類皆是眾生在塵世所患的“疾病”,故佛教將超脫塵俗達至彼岸的解脫境界稱為“清涼境”。如《本起經》:“凡人為惡,不能自覺。愚癡快意,后受熱毒。”《十地經論》云:“是諸眾生因隨逐貪欲嗔恚愚癡,常為種種煩惱熾火之所燒然,不能志求出要方便,我應令彼眾生滅除一切煩惱大火,安置清涼無畏之處。”解除“熱毒”的藥物除了象征“佛法”“智慧”的清涼“法水”外,還有大藥王(樹)意象,“譬如雪山有大藥王,名曰善現。若有見者眼得清凈,若有聞者耳得清凈,若聞香者鼻得清凈,若嘗味者舌得清凈,若有觸者身得清凈。若取彼地土,悉能除滅無量眾病,安隱快樂。”總之,在佛教語境中“醫”與“患”、“藥”與“病”、“冷”與“熱”乃具有形而上的宗教象征意義,佛陀這位醫王所治療的即是眾生的“熱毒之癥”。《紅樓夢》從某種角度而言,是一部帶有濃重宗教情懷的“度脫”小說,所有“夢中之人”皆要在人間經歷悲歡苦樂,于是也難免“熱毒纏身”,當一僧一道出現之時,正是“療病度脫”意旨的集中呈現,故而“熱病”—“冷藥”—“三寶”(佛法僧)之間本身構成了一個深層次的“象征結構”。在以上關于大藥王(樹)的典故中,“雪山”“植物”“清凈”“療疾”等諸多因子與“冷香丸”之間已然存在著某種精神呼應。佛教的“清涼境界”包涵著“歡喜”“解脫”“智慧”等精神,這種境界無憂亦無喜,身心安和而自在。藥方的“冷香幽韻”與佛教的“清涼境界”之間的潛通默應,確實可以觸發起我們對小說文本內蘊的多重聯想。故而,如果我們忽視了那個縹緲恍惚置身五云之端的“贈藥和尚”,便極易遮蔽作者通過“冷香丸”而營構出的“形而上”空間及超驗的宗教性關懷。
在筆者看來,《紅樓夢》的敘事深受佛教“表法”觀念的影響,佛陀在說法過程中常常通過具體的幻境、物象、人事等引導眾生從其中體證覺悟出至深微妙的義理,故佛經中呈現出的諸多境象、事跡等并非為了新奇有趣、眩人心目,它們大都是某方面佛理意旨的象征、符示與隱喻,是達意悟道的載體,因此學道者須“觀象而見理”,透過敘事表層(物、事、人)而達到對自身本質及宇宙實相之理的洞徹。脂硯齋對曹雪芹的這種苦心悲愿深有體會,“作者發無量愿,欲演出真情種,性地圓光,遍示三千,遂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畫一幅大慈大悲圖。(略)情里生情。借幻說法。”(戚序本第五十七回回前批)在這種“借幻說法”“造境表法”的總體意構下,人物與故事本身已超脫出泛常的平面寫實性,而具有更閎闊、更高遠的普遍“象喻”意味。因此曹雪芹拈舉出“熱毒癥”這一名目,并非完全將其意蘊封閉于某個具體人物之中,而是輻射整部小說的敘事空間,具有更為普泛的現實批判維度。就小說而言,賈雨村“趨熱”,依傍賈家貴勢而弄權營私,草菅人命;孌童“趨熱”,凡財勢貴盛者,無不曲意奉承,獻媚陪笑;其他如“中山狼”孫紹祖等忘恩負義之徒,更在趨炎附勢之中,隨時易主求榮;即使如僧尼道流等方外之人,亦饞羨賈家貴勢而奔走匆忙,鐵檻寺之凈虛、清虛觀之張道士等,無不是一幫利火焚心的“熱客”……天下熙熙攘攘,營構籌謀,大抵皆在利欲之途與熊熊火宅之中競逐奔波、顛沛浮沉。青埂峰下的“補天棄石”,因聽到一僧一道講說“紅塵中的榮華富貴”不覺間“凡心偶熾”,意欲造劫歷世。曹雪芹特別拈出“熾”字形容此石被“紅塵聲色”所引動的心境,即是與“內熱生火”同一理趣。
總之,《紅樓夢》呈現了一個“脂正濃,粉正香”“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繁華世界,功名富貴、酒色財氣、愛欲嗔恨的熱焰充斥于小說之中,因此“熱毒癥—冷香丸”的設置即具有深沉的“警世”意味。“利欲熱毒”對人心的扭曲與煎迫,并非某一歷史階段與階層所特有,乃是人類普遍之生存境況與心理狀態,因此“清熱解毒”與“尋求解脫”的精神追索,會獲得愈加持久深廣的共鳴。從這個意義上看,《紅樓夢》正是為陷溺“火宅”、身患“熱毒”的眾生所創制的一卷“清涼經”、一味“冷香丸”,作者自述衷懷云:
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愿他們當那醉淫飽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腳奔忙之苦。(第一回)
曹雪芹勾勒了俗世中身患“熱毒”的眾生相,作者要借著“紅樓夢境”透視功名、家室、財權、欲色的虛妄本質,引導眾生跳出“迷人圈子”,洞徹人生之實相,而獲得內在精神的清明與解脫。就寶釵而言,她深懷家勢衰敗下的受命不堪之“熱”,“窮年憂家運,嘆息腸內熱”,頗有諸梁那般“朝受命而夕飲冰”的精神意態,飽嘗清醒者的苦痛。寶釵對人情世故亦有刻意經營的“熱”切,她除了對元妃所代表的皇權貴勢由衷地歆羨頌揚外,亦對儒家的經濟功名甚為戀慕“熱心”。然而大批所謂“讀書上進”之人常常“茍于進取以速利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為”,已然泯滅了圣賢經傳的真精神和士人獨立崇高的人格,讀書應舉異化為其獲取功名利祿、滿足貪欲營求的工具,曹雪芹憤慨由衷,對此痛下針砭。
二、“冷香丸”的前文本及其與“高士人格”的文化關聯
朱麗婭《符號學》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轉化。”“冷香丸”雖是“細故微物”,然細探隱頤、追根溯源,其背后鉤聯的正是一部文化史! 從現實的藥理層面而言,“冷香丸”的配料皆為“清熱解毒”之物,然而《紅樓夢》對它的描寫實界于“寫實”與“隱喻”之間,亦虛亦實,亦真亦幻,“托物言志”“借物寓理”方是作者修辭立象的總意度、真精神。從審美文化的角度詳察細考,則“深有意味”,文曰:
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曬干,和在藥末子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壇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第七回)
《紅樓夢》對冷香丸的工筆細描反復渲染“時令”“時節”“時機”,此藥能否配置成功,無關乎藥料的貴重稀有而關鍵在于“得乎其時”“機緣湊泊”。寶釵的精神人格中處處潛藏著“時”的文化基因,其“行為豁達,隨分從時”“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第五十六回的回目云:“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其實,“冷香丸”之“時令”書寫最終指向儒家文化。《周易·系辭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又《艮卦·彖傳》:“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尊重實際和審時度勢是儒家決擇出處進退的重要依據,“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一切唯“時”是依。故《孟子》云:“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仁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能夠順時而動,不偏執一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在不同的時機處境之下皆能圓成自我,完善德性,達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境界。因此如果未能夠“審時”而妄動,則是背道而行,于事功德業諸方面皆不能成就,即就“冷香丸”而言,假若原料擇取“失時”,則其效用亦將徹底渙散。曹雪芹對寶釵的塑造即是在著意模擬儒家這種“時行時止”的文化理念,寶釵能根據現實處境與時機選擇合宜的生存策略與價值理想,她的顯山露水與藏鋒隱芒皆能“依時而動”,故“行為豁達”的背后是對“時”之精義的深度把握,“從時”“隨時”的人生姿態正呈現出能屈能伸,知進知退,處事泰然的氣度。另一方面,“時”在文化傳統中深切關乎興替窮亨,謀身達命與否,士人的升沉榮辱、悲歡哀樂皆受其牽系,所謂“時可以謀身,時可以達命,季子變說,宣尼歷聘。平津列侯,長卿國命,時廢時通,知之則慶。”(唐·趙自厲《時賦》)寶釵在賈府就甚為“得時”“走運”,她既蒙元妃的特別嘉許而獨得“紅麝串”,又受到賈母、王夫人等人寵愛而廣邀稱譽。可見,冷香丸反復渲染“時令”確實有一份深永的寄托。
此藥方之花卉分別為: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白”在文化傳統中積淀了獨特的意蘊,儒家有“繪事后素”與“白賁”之象,道家申言“五色目盲”之戒與“虛室生白”的內在境界,佛禪義理中亦常見“銀碗盛雪”“雪月藏鷺”之喻與靈虛清明的心性證悟。“白”色素潔幽冷,淡泊清靜,具有晶瑩朗澈、純粹無瑕的光感,相比于五色炫目、秾華繁彩的“外向型”感官刺激與張揚爭逐而言,“白”更具備避世斂抑,“內在自足”,超越物欲與外境的精神特質。即如“牡丹”而言,其本為富貴之花,秾姿華艷,然而“白牡丹”在歷代詩人的書寫中卻別具精神意態。白居易《白牡丹(和錢學士作)》云:“城中看花客,旦暮走營營。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略)憐此皓然質,無人自芳馨。(略)對之心亦靜,虛白相向生。”色彩妖艷的花卉往往與營營競逐,趨時附勢的“熱客”相呼應,然而白牡丹卻幽獨清超,皓然純質,正是象征著恬靜淡泊、虛室生白的高士人格。可見,正是由于顏色的變異,牡丹的文化內涵與精神指向便從“富貴熱鬧”轉向了“清凈超逸”。“白荷花”亦因與東晉慧遠“白蓮社”的文化關聯,而具“出世之資”,顯與世俗之爭名逐熱不同,如白居易《贈別宣上人》云:“上人處世界,清凈何所似。似彼白蓮花,在水不著水。”《寒山詩》云:“免有染世事,心靜如白蓮。”藥方中白芙蓉與白梅花等,實與以上花卉同一標格,此類例證甚多,不遑多舉。可見,在傳統思想文化的積淀下,“白色”花卉的書寫已不限于物理、生理、美感直覺的層面,而具有了人格象征與文化精神的喻示作用。
需要補充的是,“冷香”二字本身在中華抒情傳統與花卉審美之中積淀著既定的豐厚內涵,其意項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冷”除了如上文所述強調花卉素白的“冷”色調外,還關涉到開放季節的“寒冷”。就“花時”而言,梅、菊等開放于早春、寒秋、嚴冬的花卉常被稱為“冷香”,如王建《野菊》:“晚艷出荒籬,冷香著秋水。”陳景沂《全芳備祖》引司馬光、王圭詠白梅之句云:“色如虛室白,香似主人清;冷香疑到骨,瓊艷幾堪餐”此類花卉不在熱鬧暄暖之時“爭艷”于桃李,而“疏時遠世”,甘守清寒冷淡,這種姿態極易得到高逸寒士的精神認同,并成為其人格象征。前文已提到,“時”在文人世界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時世”“時命”“時運”“時勢”“時數”“天時”等皆關乎出處進退的抉擇與自我價值的認定,“冷”而“香”即意味著不趨“時”赴“熱”,主動疏離于世道之外,幽獨自處,葆持精神世界的香魂一縷,這是清潔孤高的自賞自珍。總之,“冷香”審美之中滲透著“尚清雅”“尚野逸”“尚脫俗”的文化精神,和尚藥方中的花卉皆屬遠離繁華名利場與富貴窟的“冷香”系列,其文化底蘊多與釋道隱逸傳統、高人寒士的清超之節聯類互映。
“冷香丸”以“花卉”為君料,“雨露霜雪”為輔料,這種奇異的構思,并非無源之水。實際上,在古典詩詞中早已形成一種借餐食“清英芳華”與啜飲“雨露霜雪”,而象征精神人格的書寫傳統。《離騷》首唱“夕餐秋菊之落英”以寄高標芳潔的襟懷,在后世詩文中,“餐英”意象往往浸透著濃郁的浪漫詩性與逸隱絕塵的雅趣。就“嚼梅”而言,真山民《王廉使》云:“公余詩興清于雪,細嚼梅花入肺肝。”羅椅《酬楊休文》:“臥看山月涼生夢,饑嚼梅花香透脾。”文士對其他清雅花卉的餐食,其精神意旨亦不出乎以上所述,曹雪芹取譬聯類,融花香為藥香,盡顯清風雅懷。此外,服用“冷香丸”要“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黃柏別名檗木、檗皮,性味“苦寒”,具有清熱燥濕,瀉火解毒之功效。藥方中徑直地道出“食蘗”,乃是暗中貼合著“飲冰食蘗”的典型意象。如李商隱《為滎陽公上仆射崔相公狀》云:“飲冰食蘗之規,實惟素誠,敢有貳事?”又《林君霈》:“有飲冰食蘗之貞。”文士常借此典喻示擺脫物欲名利而清潔自勵、淡泊自守的情操。“白雪”亦有“解熱”之功效,“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郁,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那些競奔于利害憂患之域的“熱毒患者”正需要以雪療治。故詩文中出現了與“飲冰”同質的“嚼雪”意象,程公許《題詩卷》云:“嚼雪哦詩格外清,誰令失腳入紅塵。”李流謙《訪楊少虞得小詩并呈才夫》:“抱冰嚼雪豈能清,火里芙蕖初出浴。”可見,“嚼雪”乃在于呈現人格精神的清逸超俗,是對紅塵擾攘的疏離。“冷香丸”的配料中尚有“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飲雨”之意蘊與“嚼雪”相類,“積雨烹茶”多顯清雅絕俗之致。櫳翠庵品茶一節中,妙玉即用舊年蠲的“雨水”與梅花上的“積雪”烹茶待客,曹雪芹即借此細節渲染其人“高人逸士”一般的品性,誠非虛設炫奇之浮文矣! 莊騷抒情傳統對“飲露”意象的創發,厥功甚偉。《逍遙游》中藐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風飲露”。“飲露”意象在后世詩文中不絕如縷,王灼《讀王尼傳》:“誰能百無營,飲露如寒蟬。”趙必曄《和榴皮題壁韻》:“四仙吸露餐霞者,卻勝人間煙火馀。”可見,“飲露”意象中已積淀了“百無營”“除煙火”等精神意旨,它象征著內心的澄明清凈,遠離塵氛與利欲煩熱,蟬蛻于濁穢,皎然不滓。
由以上引征的文獻可以看出,《莊子》的“飲冰祛熱”之旨與佛禪的“清涼”境界經過不斷的文化承續與演變,形成了“吞梅餐英”“嚼雪飲露”“飲冰食蘗”等一系列與之精神貫通的“同質性”的意象群,這類意象雖在形態上有所差別,但內在本質、價值蘊涵卻相近類似,像不同的音響、樂器共同強化同一“主旋律”,它們來自于古典抒情傳統。“冷香丸”特別標舉牡丹、荷花、芙蓉、梅花之“白蕊”與雨、露、霜、雪、苦柏為原料,“服食以祛熱”,正是對此意象譜系中分散的文化因子進行集中聚焦、高度融煉與創造性升華,作者“一篇之中三致焉”的苦心孤詣及潛伏在表層敘事下的“微言大義”,就以這樣的匠心呈現于“納須彌于芥子”式的意象創造之中。“熱毒”與“清涼”,以及“冷香丸”的各種原料,一方面是現實的醫學術語和藥材,關乎身體的“病癥”與“療救”,另一方面它們又是古典宗教、哲學及詩學中的“原型意象”與“象征性符號”,其中積淀著豐富的文化信息、情感內蘊,代表“精神層面”的“煎迫之苦”“利欲之火”與“解脫之道”。這一系列“色白質冷”的意象皆深深浸透著釋、道哲學的色彩,于是世俗之中那些極為張揚的聲色鋪陳與充滿欲望挑逗、功利炫惑的觀照對象都被剔除消解了,而表現出對“清冷”“清涼”“清逸”之境的追求,共同喻示著對塵俗物欲的升華和對現實功利的隔絕,同時主體因內心擺脫了滯累、焦慮、妄執和外在世界的干擾,而呈現出淡泊超脫,自足于內的情懷,以及清幽淡雅的審美追求,別具“雅人深致”,所謂“吞梅嚼雪,吸風飲露,不食人間煙火”。這一切正是“高士精神”的核心特質。
“冷香丸”正寄寓著曹雪芹自身的“人格向往”。《紅樓夢》開篇“正邪二氣所賦論”中,即標舉“生于詩書清貧之族”的“逸士高人”,并列出從許由、陶潛到黃大癡、倪云林、祝枝山等的精神流承譜系。“高士”是文化傳統中極被尊崇的群體,其志趣高尚,超脫世俗,多受釋道精神的影響。故此類人“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厲濁激貪”,是文化中的一道清流,極純粹而高貴。“正邪二氣所賦論”不僅是整部《紅樓夢》的精神主脈與人物塑造的綱領指南,亦是作者自已安身立命的哲學依據。曹雪芹對補天濟世之志、峨冠博帶之人甚為不屑,朋輩的贈詩亦頻頻呈現其瀟灑自適、憤世嫉俗、傲世獨立的精神風骨,誠可謂此類“逸士高人”精神骨血的異代流傳。就《紅樓夢》對“冷香丸”的細節性描述來看,此藥并非可以對病癥起到一次性“根治”的效果,若“發病時,即取一丸服用,也便好些了”,且藥物配料的所有劑量皆為“十二錢”,象征十二月與十二時,以此包舉年年歲歲、朝朝暮暮所有的時間節點。作者的言外之意乃謂:人的中和清安之性往往外誘于利欲功名、內困于七情紛擾,故對凡夫俗子而言,“熱毒之癥”隨時“發作”,故需要“勤勤拂拭”“時時提澌”“多作警醒”。
三、以玄旨寫俗情:雪中高士的“冷香”人格
清人許葉芬言:《紅樓夢》一書,“錯綜離合,大半托諸寓言。惟其以玄旨寫俗情,密縷細針,自是小說中另有一副空前絕后筆墨。”“以玄旨寫俗情”“托諸寓言”是極為精深獨到之論。就本文所述之旨而言,曹雪芹讓寶釵時常服用“冷香丸”以祛除“熱毒”,實際上是將某種蘊含著釋道精神的文化基因注入人物塑造中,使本來偏向于儒家事功與道德名教的人物,不致于走向異化之途而泯滅真性靈。曹雪芹用“冷香丸”祛除寶釵體內的“熱毒”,進而升華凈化、提澌喚醒著其“靈性”生命的根芽。故“冷香丸”之于寶釵,就像“通靈玉”之于寶玉一般,都是“命根子”,都是葆養生命真境界與詩性華彩的“光源”與“靈物”。
正是在這種“疾患—療救”的隱喻模式下,我們明顯在人物身上體察出“功利經世”與“淡泊自處”兩種精神人格間的張力,這里既有曹雪芹閱世窮理的冷峻眼光,也有超越塵俗的人格蘄向。寶釵雖精于商道、通達事故,然而始終葆有不累于富貴的清雅淡泊之趣。對于“富貴”,諸多紅樓秀彥很少能表現出閎闊不滯的氣局,如:孤高自許,名士氣十足的妙玉在賈母等人面前以珍奇茶具自傲,依然富貴塵心未泯;同為皇商的夏金桂粗俗狂奢,由于長于富貴窟中而養成“盜跖”之性;探春因為出身的緣故,對于富貴財利、名份等級更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敏感執著;既使超然物外的林黛玉也以“富貴之眼”打量貧苦的劉姥姥,而以“母蝗蟲”譏之;鳳姐雖有“閨中宰相”的濟世宏才,然而卻在富貴場中造業無數……至于其他俗下之人更是“一片體面心,兩只富貴眼”。相比而言,寶釵的“喜素尚潔”顯得極為突出,她“自小從不愛花兒朵兒”與俗艷之物,在“春裝兒女競奢華”之際,她卻“疏是枝條淡是花”,一片素雅風韻。在其身上并沒有富家千金的嬌矜跋扈、奢華勢利、刻薄寡恩,富貴非但沒有荼毒她的心性,反而養成了其慷慨大度、施恩仁愛的悲懷。當其他女兒還沉浸封閉在自我的世界天地中時,寶釵卻心量開闊,包容外物,處處能體量他人之苦樂悲辛,予以熱切關照。刑岫煙的“冬衣”、史湘云的“螃蟹筵”中皆熠耀著寶釵為人的豁達開朗。第三十回中大觀園“興利除弊”而引發了一場“利義之辯”,寶釵普遍施恩,顧及大體,未陷入純粹的功利營求,即在積極有為之中頗顯出一份闊達與溫厚。故富察明義贊之云:“威儀棣棣若山河,還把風流奪綺羅。”戚蓼生云:“薛家女子何貞俠,總因富貴不須夸。發言行事何其嘉,居心用意不狂奢。”“貞俠”二字即為點睛之筆。故寶釵終究未被“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變其素質清操。其作詩亦以清冷意象自勵,如“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欲償白帝憑清潔”,這里除了象征女性的幽貞之美外,更有一種高士精神的流溢。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唐宋以后的文化語境中,“高士”并非僅指隱居于山林巖谷之中的避俗之人,而是重在呈現一種灑脫淡泊、不同流俗的雅趣高致。士人多于出處進退之間尋求一種調和,“居廊廟之崇而志在山林,處宮室之奧而情寄物表”,“雖跡顯勢崇,而蟬蛻污濁之心,未嘗不與造物者游”。于是在儒家積極進取、濟世有為的現實功業之外,能超拔于名利富貴的羈陷,不為物役,不受俗遷,而保持淡泊灑脫的人格風度,此即為“高尚之士”,他們“嘯然一室,左琴右書”,“周旋乎世故,酬酢乎萬變,蓋不離于物,而亦不撓于物。”韓元吉的《淡齋賦》頗為切合寶釵“喜淡”性情中的深層文化旨趣,“君子之于道也,內以存其心,外以應于事,雖酢酬萬變而無留焉者,是亦將泊然混然而后己也。夫惟泊然混然,故隨所用而無不可,世之為是說也。茍以為無嬰于名利而不湛于嗜欲,泛然與世不相町畦,則亦不足以獨立于萬物之表。”寶釵正是這樣的人格典型,她的“淡泊”并非離塵去世式的“超然獨往”“了無掛懷”,而是在“酢酬萬變”“接應外事”之中呈現出不被富貴欲利所纏陷的清雅之懷,時常保持冰雪之潔與梨花之淡(寶釵居“梨香院”即有此寄義)。
此外,“高士人格”的重要面向還表現為對苦難困境的“超越”,文化史上的“高人逸士”大多身經喪亂浮沉或物質窘迫,然而仍能超脫外境、齊一榮辱,葆持著心性人格的自由澄明與詩性浪漫,如此境界方是“高逸”二字的真詮。曹雪芹把象征“高士精神”的“冷香丸”融入寶釵生命,亦將相關的文化基因注入其人格與命運中。脂硯齋在論及“冷香丸”需“黃柏煎湯送下”時,有一段頗富深義的評語:“歷著炎涼,知著甘苦,雖離別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謂香可冷得,天下一切,無不可冷者。”(見于戚序本第七回雙行夾批)此評并非著眼于某一情節,而是批者通覽曹雪芹的“真本全文”后,對寶釵整個人格操守與立身行事,所下的“蓋棺”式“定論”,且包涵著對八十回后情節的暗示。意謂寶釵雖置身華侈之場而游心淡泊之境,未被富貴荼毒心性;后來嫁于寶玉,成為寒士之婦,面對外緣際遇之跌宕突變,內心既不掛懷流連,隨其悲喜,也不改變志節操守,仍能“豁達安分”,“坦然自若”,所謂“風雨陰晴任變遷”“任他隨聚隨分”“濃淡由他冰雪中”(以上皆為寶釵自道襟懷之句)。寶釵判詞有句“可嘆停機德”,曹雪芹將其比作樂羊子妻,此女在貧窘的環境中依然對財利與生命,非義而不取,非理而不求,嘗言:“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
總之,曹雪芹對寶釵的塑造乃是融“美姝”與“士人”為一體。如果我們忽略寶釵所秉具的“文化人格”,便極易造成對“紅樓人物”與“敘述意旨”詮解的表層化、庸俗化、泛常化。寶釵身上既有儒家積極有為的入世精神,又有超塵脫俗的高潔人品、隨緣順遇的自適情懷,這正是曹雪芹要著意珍惜引申、表彰頌揚的。《紅樓夢》精魂所聚雖在女兒世界,然而并非專書閨情艷情的“香奩”之作,亦非單純才子佳人式的情愛書寫,其中的諸多“瓊閨英秀”乃是融“女兒心性”與“士人精神”為一體,這類形象多具“文化人格”“文化寓托”與“文化原型”。馬一浮云:“大抵境則為史,智必詣玄;史以陳風俗,玄以極情性。”“史”是“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的“寫實傳真”,以見興衰治亂,人情物態;“玄”是在對現象界、人間世的觀照體察中覺悟“道真”,以見宇宙人生之本源大端與真實相,并寄寓價值理想。曹雪芹作為詩人哲學家,其筆下的某類人物正具有“史玄交融”,亦“寫實”亦“象征”的特質,他們凝聚著深厚的文化哲學之意蘊,乃是某種“價值理念”的“肉身化”存在,故《紅樓》諸多人物非可按一般小說的人物性格而論之,讀者須具有一種“文化的眼光”與“互文性視野”,方能“超以象外”,得其真精神、真意旨、真寄托。
注釋
① 對“冷香丸”作純醫學考據的觀點,可參見以下著作:薛慧、趙紅瑾《薛寶釵的冷香丸神在何處》(《探秘〈紅樓夢〉養生智慧》,汕頭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第50頁。)宋淇《薛寶釵的冷香丸》(《〈紅樓夢〉識要》,中國書店出版 2000年版,第206—211頁。)其他關于“冷香丸”之醫學考察多未能超出此二文之主要視域。
② 于智敏主編《中醫藥之“毒”》,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頁。
③ 呂本中《紫微雜說》,清十萬卷樓叢書本。
④ 《雜阿含經》,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頁。
⑤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卷·本緣部下,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第161頁。
⑥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五卷·諸宗部,第390頁。
⑦ 佛經中“法水”是“佛法佛力”與“正覺智慧”的象征,常被用于作為解除“熱毒”的“藥物”。《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云:“譬如夏月地極炎熾人亦煩熱,水能除解悉得清涼,菩薩亦復如是。以其法水息除一切有情界中煩惱炎熾逼迫之苦。”“冷香丸”中“雨雪霜露”等清涼液體之作用,或可與“法水”之寓義相互參證。
⑧ 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918頁。
⑨ “表法”分為三類:(一)人物表法,如觀音象征“慈悲智慧”,普賢象征“理德行德”,文殊象征“智德正德”等,人物本身即攜帶著文化符號,并成為某種教義佛理的載體;(二)事件表法,佛教中很多看似生動真實的故事乃具有“寓言”“象喻”的用意,如佛陀割肉飼虎乃為了呈現無量慈悲與“無我之境”,《法華經》“火宅”故事即象征眾生被五濁八苦之所煎逼而不得安隱;(三)物體表法,如荷花、摩尼寶珠、衣珠等,皆是深蘊哲理的“象征意象”與“原型符號”,并非無關宏旨的泛常之物。《紅樓夢》的整體敘事即具有鮮明的“寓言”意味,佛教的三種“表法”方式皆被運用于小說的情節安排、人物塑造、意象融煉、結構設置之中,故呈現出一個多維交織、層層深入的意蘊空間,浸透著深沉的形而上色彩。此處略加提點,有待他文詳述。
⑩ 李之亮《蘇軾文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 2011年版,第110頁。
? 轉引自朱立元《現代西方美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947頁。
? 《神農本草經》云:“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熱”型病人宜吃寒性或涼性的藥物與食物,以便起到清熱瀉火、解毒利水等功效。“冰”,《醫林纂要》:“凡天行熱毒,傷寒陽毒,陽明壯熱,以至神氣昏迷者,置冰塊心胸間,即可清醒”;“牡丹”,《本草綱目》謂其“和血、生血、涼血、治血中伏火,除煩熱”;“荷”之花與梗能清心涼血、解熱解毒,《羅氏會約醫鏡》云:“荷花清心益腎,黑頭發,治吐衄諸血”;芙蓉花味微辛、性平,《本草綱目》說它“清肺涼血,散熱解毒”;“梅”,《神農本草經》云:“梅實味酸平,主治下氣,除熱煩滿”,“能治頭目赤痛,利肺氣去壅止熱。”(《致富全書》);“蘗木”即黃柏,性“苦寒”,有清熱燥濕,瀉火除蒸,解毒療瘡的功效。
?? 朱熹《周易本義》鳳凰出版社 2011年版,第59、298頁。
? 馬積高、萬光治等編《歷代詞賦總匯》唐代卷,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4年版,第2663頁。
?? 白居易《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9、96頁。
? 王啟興主編《校編全唐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頁。
? 王建《王建詩集校注》,巴蜀書社 2006年版,第167頁。
? 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卷一“花部”,明毛氏汲古閣鈔本。
? 轉引自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62頁。
? 在諸家關于“冷香丸”的論述之中,林方直師探本窮源,靈犀獨覺,對“用黃柏湯服藥”細節之出典作出堅實考論,啟我良深。(參林方直《“冷香丸”是“飲冰食蘗”的“假語村言”》,《陰山學刊》2016年第3期。)
? 李之亮箋注《蘇軾文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2011年版,第252頁。
?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卷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李流謙《澹齋集》卷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李孝中、候柯芳輯注《王灼集》,巴蜀書社 2005年版,第45頁。
? 范曄《后漢書·逸民列傳》,中華書局 1965年版,第2755頁。
? 皇甫謐《高士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 如“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誠《贈曹雪芹》)“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一醉酕醄白眼斜”(敦敏《贈芹圃》)“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借問古來誰得似?野心應被白云留。”(張宜泉《題芹溪居士》)(以上諸詩見于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4頁。)
? 一粟《〈紅樓夢〉書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頁。
??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50頁。
?? 陳基《松雪巢記》,《夷白齋稿》卷三十,四部叢刊三編景明鈔本。
? 陳基《六柳莊記》,《夷白齋稿》卷三十,四部叢刊三編景明鈔本。
?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十五,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 范曄《后漢書·列女傳》,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953頁。
? 丁敬涵編注《馬一浮詩話》,學林出版社 1999年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