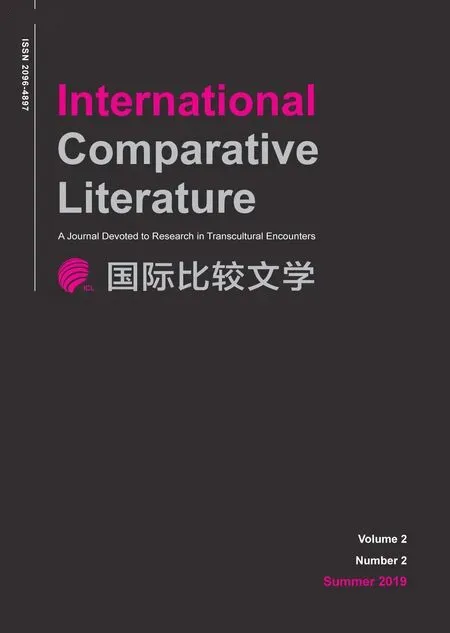“興”的構造:道德之現象學意向性的直接性*
2019-11-12 05:19:40李志春同濟大學浙江學院
國際比較文學(中英文)
2019年2期
李志春 同濟大學浙江學院
文章的任務在于揭示“興”之構造有哪幾方面構成,并不進一步以此“構造”對“興發”的經驗現象做過程性描述。不描述不等于不重要,在詩歌、繪畫等領域,“寄興”的狀態與上乘創作直接相關,但這躍出了文章的任務,亦非寥寥數語能闡明,待他日成文。
對“興”之構造的揭示在現今“興”概念的研究中有重要意義。以往對“興”的理解,無論是修辭學(表現手法)、經學(解經方式)亦或文化人類學,都未能直面“興”本身,即便彭鋒教授在《詩可以興》中提及了“興”是一種存在方式,也未能說明此種方式何以可能——怎樣構成?怎樣發生(機制)?
對“興”之構造的揭示,涉及西方概念,這與現今國際學術共同體之交流有關(否則彼此無法理解),因此對西方概念的梳理、界定與中西概念間的“差異說明”有其必要。
思維、語言與生存方式之間具有同構性,從語言敘述的獨特性入手可以見出一個民族的精神旨趣,葉嘉瑩從文論中的“形象”(image)入手,在中西比較中發現西方文論中的“形象”在中國詩歌中都出現過,但是“所有這八種情意與形象的關系,只類似中國詩歌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中的‘比'……而中國所說的‘興'的這種關系,在西方沒有相當的一個字來表達……說明‘興'的作用在西方的詩歌創作中,不是重要的一環。他們(西方)內心的情意與形象的關系,主要是用理性的客體跟主體的安排和思索說出來的……可是,有時候‘興'卻講不出什么道理來……”
“興”之內涵在西方找不到相當的詞進行表達,反應出不同民族間不同的世界圖式。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