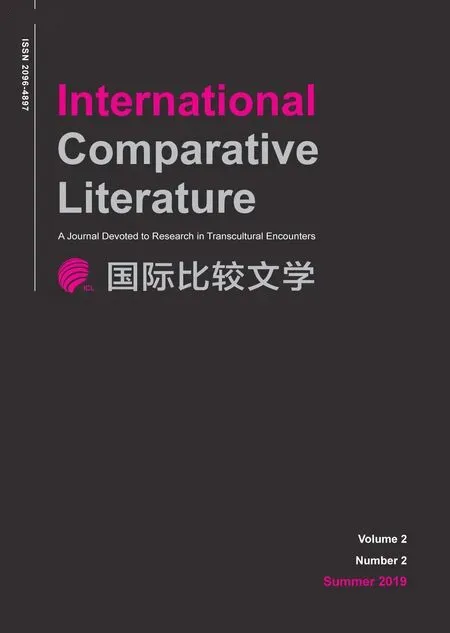謝 志超:《 自由主義傳統的書寫者:杰克·克魯亞克》
2019-11-12 05:19:40董伯韜
國際比較文學(中英文)
2019年2期
董伯韜
自碩士論文《〈去吧,摩西〉的藝術性》算起,春華秋實,風雨星霜,從岳麓山到鏡月湖,從人生的初春到仲夏,謝志超教授的問學之途由約克納帕塔法縣一路伸延至康科德、洛厄爾鎮、紐約長島……,于是,福克納、愛默生、梭羅、惠特曼,這些璀璨的名字輝映在她的筆端。而更讓人感佩的是,面對這些神魔之人,她始終保有身為研究者的矜持與適度的疏離。愛固然可以是學術思考的起點,但多一份自尊與獨立的愛當然更成熟。研究中,她既不率意褒貶,更不趨奉某家之說,而是盡量多地收集、利用最原始、直接的文獻,以期進入當日的歷史-文化-心理語境。
新著《自由主義傳統的書寫者——克魯亞克》凸顯了她的這一治學風格。在書的開篇,她即以細密的史料揭示了克魯亞克形如悖論的人生:外表樂觀、開朗,內心卻盈滿脆弱、感傷;行事獨立卻慣于依賴;從小厭倦漂泊,漂泊終成宿命;一面一再否定、拒絕外在的秩序,一面不懈追尋、構筑內心的和諧。顯然,這已不完全是人們先前熟知的那個出現在文學史或現代名人“點鬼簿”里的克魯亞克:那個與金斯伯格、巴勒斯齊名身為“垮掉派”代表人物的克魯亞克;小說家克魯亞克;禪修者克魯亞克;因崇敬陶淵明而改名為“陶·杰克·克魯亞克·明”的克魯亞克,眼里蘊著叛逆、蓄著依戀、藏著天涯的高傲、俊朗、不馴的克魯亞克;由作者、研究者、譯者、讀者共同營造的存在于自己的不存在之中的神話的克魯亞克。相反,在全書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