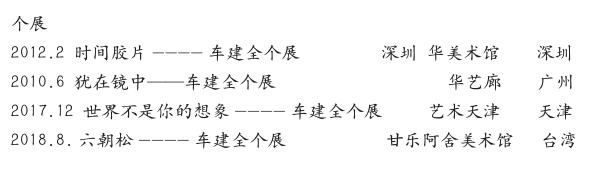重述的時間
在一個國家經歷社會結構轉型和向現代文明轉型的劇烈變化中,每一個伴隨巨變的個體心靈都同樣遭受著無法想象的陣痛和精神磨難。在這種歷史的激變中,我們享受諸多驚喜刺激的同時也面臨著更多的選擇不安和焦慮。我們的記憶被不斷快速的涂抹,修改,重新塑造和顛覆,我們通過不斷失憶來確保自身心理的安定與常態,這種集體無意識的不安正在成為時代轉變的典型心理癥候。一方面,我們需要面對不知所措的變遷護持自己僅有的記憶來理清生命的線索,另一方面,伴隨太多的顛覆,我們不斷學習失憶,學習刪除,才有勇氣和力量面對處在變化之中的社會環境。那些暫時與片刻的感受不時把人們從瞬間安慰拋向長久不安,我們經歷著不停在前進或退后的此岸,并在飄搖中不斷偏守著某個不確定的彼岸。當代藝術準確地呈現了這種歷史性的心照,它既是暫時的,支離破碎的有關記憶與抹煞記憶的真實心理再現,也是被壓抑的集體無意識的感官釋放,是對歷史變革中的天路歷程的心靈書寫,也是對此時此刻的時間意義上的視覺回應。
這種在后殖民文化沖擊之下沖刷出來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潮流中,中國傳統藝術和審美思維也在必然經歷一個重新發現的過程。無論是對傳統圖像的挪用,還是對傳統智慧的重新闡釋,都成為當代藝術中去殖民化的一種努力,或是一種策略,從某種意義來看,它更像一種對傳統文化的視覺重建。但是這里所指并非膚淺的取悅西方的中國元素。
相對當代藝術中的夸張的戲劇性和唯我性,我更希望能夠越過當下,和它保持一定的距離,去重述越過此刻這個時間之外的東西。這種東西所具有的穩定性會給我自己帶來心理的安慰。
選擇中國古代山水作品作為我的表現主題,事實上是在尋找一種避開當下性的方式,或者說是擺脫時代性不安的方式,一種用穩定的記憶面對不確定失憶的方式,一種對失憶的反抗。我選擇了我最喜歡的古代畫家的作品,通過重述把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另一幅畫。決定這種取向和工作方式的根本原因源自對個人視覺記憶的信念。它是我在此時對彼刻的心照。
這個信念就是重述一個時間的概念,通過對記憶中的傳統繪畫圖像和被經驗改變的那部分進行重述,抵抗支離破碎的記憶與失憶。童年時代我就開始接觸古代山水畫,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臨摹,很多時候是在博物館對著原畫臨摹。那個時代除了物質匱乏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回憶,這跟我的家庭式教育有關。那是一種幾乎完全封閉的看起來與周圍環境沒有多大關系的成長經歷。大學的時候才開始對封閉生活的反叛,關注現代藝術,西方哲學,去嘗試很多新鮮好奇的東西,幾乎每天都在面對兇猛涌入的新事物,但是80年代就像披頭士的時代一閃而過,所有人的理想都在瞬間變成對消費時代的匆忙適應。我自己的學習和創作也在那個時刻經歷了很多挫折,甚至絕望到放棄。周遭的環境和不斷改變的文化氛圍既讓我質疑又不知所措,特別是對繪畫意義本身的質疑。很多年以后,當我有能力把與自身無關的很多東西剔除和否定之后,或者真正認清自己的局限之后,才開始重新建立了對繪畫的信心。用格哈德?里希特的話說:“一切都是虛空,但是繪畫還存在,我們仍然愛它,借助于它,需要它”。每個人的疆界都很有限,即使你能縱橫世界五大洲,真正的疆界就那么一點。只是每個人擁有的記憶和經驗不同,開放的狀態和思考的角度不同。我能做的工作就是那么一點,呈現僅僅屬于我的個人的記憶,創造一個疏離于當下的時間。并通過這種工作方式讓我游離在具體的時間之外,不斷堅定一個相對穩固的記憶來反抗不斷被顛覆的記憶,它能夠撫慰所有內心的不安和焦慮。
我一直懷疑某種文化理想,也懷疑關于文化理想的種種爭論。因為任何一種信念都是要靠堅持不懈的努力來實現的,只有作品是代替所有語言的東西。我的工作是關于我自身的,同時,也是關于時間的。這個時間的概念不是變化不定的此刻,也不是想象中的彼刻,而是流動中的此刻對彼刻的眺望,是眺望過程中彼刻對此刻的保護和安慰。我希望創造一個時間,一個能夠超離當下的時間,超離不斷用失憶來減輕內心苦痛的時間,同時這個時間也能夠給他人人帶來精神的撫慰。
認真閱讀中國傳統繪畫,特別是山水畫的漫長演變,我找到了這個時間。這個時間是恒定的,我們幾乎很難察覺具體的時間對一個恒定時間的干擾,或者說歷史的轉變對時間的明顯干預,我們能夠看到的更多是審美方向和語言方式的轉變。那些時代的藝術家對當下的所有反應都通過人格化的語言方式在共同塑造一個能夠超離具體時間的更為穩定的時間概念,這個集體塑造的時間概念形成了一種可以帶來精神慰籍的連續的圖像記憶,能夠讓人脫離當下的所有不安和傷痛。無論我在郭熙或者王冼的作品面前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我會脫離了所在的具體時間。
如何重述這個記憶和時間一直是我工作的中心。在我的理解中,當代藝術家對古典陣營和傳統政體的反叛已經結束了,作為西方解讀中國當代精神符號的中國面孔也在成為過去,時間在清理這些過去時的時候仍然留戀地把它認為是當下,事實上那是過去二十年的藝術家集體創造的一個神話。這個神話在成為過去。我們對當代藝術的固有理解正在成為過去。在當代藝術通過反抗和破壞競相走向極端的過程中,倒退也是一種當下的姿態。它有助于我們從所有短期的巨變當中疏離出來,從坐過山車的心跳和幻滅感中疏離出來,不只關注眼前,或者剛剛過去的二,三十年,而是去感受一個更寬泛的時間概念,個體生命的感受就會更符合常態。
這里的倒退是對傳統的重新認識,尊重與責任,是轉變任何習慣意義上對傳統的理解方式,是站在當下對傳統的重新解讀。它有助于我們脫離失憶的無奈和痛苦,更常態地面對泡沫和幻滅,因為有一個和當下保持疏離的時間能夠有力量來平衡這些的不安和焦慮,就是傳統藝術創造的那個穩定的時間。
事實上,在人人堅持自我,不斷快速更新的當下,自我往往是最貧乏的。這種貧乏不同于政體時代的貧乏,而是獨立精神的貧乏。即人格的獨立性,獨立人格是真正的自由精神,也是藝術信念的真正來源。獨立的意義在于能夠讓我們超離當下作出最自由清醒的藝術判斷。因為在物質解放我們的感官的同時,并沒有建立起相應的信念,這是當下所有不安和焦慮,記憶和和失憶的心理根源,倒退是一種平衡,更是一種獨立的態度。
藝術家 車建全
1967年生于天津,1990年畢業于天津美術學院油畫系,1992年至1996年任教于天津美術學院油畫系,2001年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獲碩士學位。現為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天津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院長(特聘), 廣東美術家協會實驗藝術委員會委員,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項目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