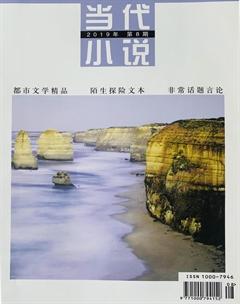方生未死
羽瞳
我從小就想當堯小智的媽,他比我小兩歲,長得像個洋娃娃。出生時臍帶纏脖,早產,差點兒給憋死在娘胎里,打出生起堯小智就像個一掐脖兒就能斷氣的小雞崽兒,比人家矮,比人家瘦,比人家多災多病,也比人家的腦殼來得憨。
比如那個爛大街的問題,“樹上有十只鳥,一槍崩死一只,還剩幾只呀?”
堯小智會瞪著他那雙大葡萄似的眼睛,盯著我家院兒里的臭椿樹,認認真真地回答,“烏鴉。”
真是個好孩子。
堯小智他媽在他三歲大時跟一個磨剪子戧菜刀的跑了,這事兒在他媽跑之前就已經是胡同里心照不宣的秘密,男人扛著扁擔來,一聲吆喝八條胡同外都聽得見,那吆喝總得在堯小智家門前銷聲匿跡一陣兒。堯小智在門口蹲著,跟三四窩螞蟻玩兒,那時候我剛從幼兒園光榮畢業,因為歲數不夠被小學拒之門外,一整年賦閑在家,我們兩家門對門,我提溜著褲子從公共廁所出來,問他,“你家到底有多少菜刀要磨?”
堯小智抬起白白凈凈的臉,一手的螞蟻,“我媽說,我家的刀,沒人家的好使。”
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明白這句話的,那時候我和堯小智都還沒屁大,他因為腦子有問題三歲了還穿著開襠褲,晃蕩著他家院兒里唯一一只鳥兒。我們都處在一個性別模糊的年紀和年代,分不清男和女究竟有什么區別,后來,在我意識到這一生都有可能擇不清的時候,我莫名地想起并明白了堯小智他媽說的話。
他媽跑的那天,堯小智也在門口和即將鉆入地底過冬的螞蟻玩兒,他被咬了一手的紅點兒,我從我媽的醫藥箱里偷藥膏給他抹上,模仿我媽的手法把他的手纏成了個粽子,看著像電視里的僵尸,他用這只全是藥膏味兒的爪子蹭了蹭我的臉,對我說,“謝謝,小北哥。”
那些螞蟻密密麻麻地往我心尖里鉆,我覺著有什么東西從血管里活過來,很熱,滿足感沖昏了一個五歲孩子的頭腦,我拉住他的手放在嘴邊親了一下,“以后我給你當媽吧。”
他手舞足蹈咯咯直笑,我以為他同意了,他揮舞著胳膊沖我后頭脆生生地喊,“天使!”
我嚇得一哆嗦,猛回頭瞧見我媽正站在我身后,她又把堯小智的奶奶領回來了,佝僂成一只螞蟻的老太太對我媽大聲喊,“小智他媽走了。”老太太好幾年前就聾了,在堯小智他爸去包頭找建筑工地之前,她就聾了,她成天起得比雞都早,拎著把折疊板凳去胡同口曬太陽,一曬一天,看見一個人出去就在腳邊放一枚石子,回來一個人便拿走一個,石子每天每天只多不少。
我媽沖老太太笑笑,伸手摸了摸堯小智的臉,我媽原本是個婦產科護士,堯小智就是我媽接生的。醫院倒閉之后,我媽騎著婆家唯一的彩禮、一輛乳白色永久自行車,把藥箱放在車筐里上門打針。這片日本人遺留下來的棚戶區里基本沒有人沒挨過我媽的針。棚戶區像一塊破竹席,我和堯小智住的胡同像一根爛藤條穿插其中。老人傳說這條胡同叫“卡蠟思”,不明白什么意思,日本人跑了幾十年,鳥羽一樣排列的房子中間塞滿了虱子似的違章建筑。
我媽瞄了一眼堯小智的手,推了一把我的腦袋,“你干的?”
我怕她聽見了我剛才對堯小智說的話,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怕,我在褲子上擦了擦手汗,“啊。”
“還行,有天賦,”我媽說,“回去我教教你。”
我松了口氣,堯小智還在叫我媽天使,他腦子有問題,兩歲多才會說話,那天他在我家看電視,電視上在播醫療題材的電視劇,我媽在廚房做飯,堯小智突然跑出去,沖我媽喊,“天使!”
我媽把堯小智抱起來,堯小智的口水蹭在我媽的白棉服上,我媽總是一身白,自行車也是白的,在以臟亂差為主要特征的胡同里分外扎眼。她親了一下堯小智的大腦門兒,堯小智晃蕩著他的小細脖兒上的大腦袋,細胳膊細腿地在我媽懷里撲騰,我媽側腰也被他踹臟了一塊。
我媽說,“你跟你小北哥玩兒一會兒,等姨把飯做好了給你們端一份。”
我媽把他放下來,他沒站穩,往前撲了一下,先天不足加上后天缺陷令他的大腦袋和小身子極不成比例,像掛在小賣部墻上的洋娃娃,我扶了他一把,他抬起臉看著我笑,堯小智長得好看,比洋娃娃好看,像他剛剛離家出走的媽,我看著我媽推著自行車進院門的背影,突然意識到,在街坊四鄰眼里,堯小智早就是個沒娘的孩子了。
我說,“拿上你的槍,我要上廁所。”
堯小智歡呼一聲跑進院兒里拿槍,一把黑色的玩具槍,比他還高,槍口拖在地上早就磨起了毛茬,這把槍是我媽給他買的,能打塑料子彈,我媽經常要用鑷子把這花花綠綠的小塑料球從小孩兒鼻孔里取出來,所以她只給堯小智買了槍,沒有買子彈,并且再三叮囑我也不許買。
我還是給他買了,一整包都倒進槍里,并且命令他在我去公共廁所的時候站在外面站崗放哨,如果有人要進來就開槍,反正他是個傻子,不會有人和他一般見識。堯小智很喜歡這個游戲,除了為我站崗,他平時從不碰這把槍,整片日本房只有兩個男孩不喜歡玩兒槍,一個是我,一個是堯小智,我不好意思說我更喜歡喝洋娃娃玩兒喂奶打針的游戲,堯小智只對螞蟻、麻雀、烏鴉一類活著的東西感興趣。
胡同的公共廁所在我家旁邊,旱廁,兩個簾子兩扇水泥門簡易地區分了男女,在我五歲那年春天,不知是誰在女廁里生了個孩子,生在茅坑里,孩子直接淹死了。
我媽念叨了一晚上造孽,她趴在床上,邊往廢舊的演算本背面記賬,邊講起她護士長的女兒,她說那女孩十七八歲和男人有了孩子,找赤腳醫生打胎,結果人死了,男人和醫生把她和死胎裝進冰柜扔進了大凌河。
我媽說,“你長大了可不能當玩弄女孩的畜生。”我心不在焉,把臉埋進她的腰窩,嘴貼上去,吹出一連串“噗噗”的響聲,她身上酒精和藥水混合的氣味鉆進了我的鼻孔。
我是在這種氣味里長大的,母親的氣味。關于父親,我沒有任何概念,我媽不說,街坊不提,我也不問,至少在我五歲之前,我不覺得我的生命里需要這樣一個角色。我媽能給我所有我需要的,我很崇拜她,有時候我跟她去別人家打針,羨慕無論男女老幼都乖乖聽她的話,也羨慕所有人都很信任她,我看到過高燒不退不停抽泣的小女孩在她懷里破涕為笑,也看到過她握著七八十歲老人的手低聲細語,老人臉上對她的依賴甚至比我對她更加厚重,這時我心里便會涌起崇拜和驕傲。
幼兒園總會組織小孩玩一種游戲,女孩發洋娃娃、小廚具、醫護玩具,男孩子發沒有水的水槍、類似于大檐帽的兒童帽,全班一起過家家,我在第一次做游戲時就發現了自己的異樣,我對水槍毫無興趣,我盯著女孩懷里的洋娃娃,想起我媽,想起堯小智他媽敞開衣襟給堯小智喂奶的樣子,在那個幼兒園里其樂融融的下午,我被突如其來的恐懼擊潰,毫無理由地哭了起來。
從那天起,我便不能站著撒尿了。
這件事只有堯小智知道,只有他知道就等于沒人知道。他把遵守約定當成比吃喝拉撒更重要的事,我曾經聽到過他和烏鴉約定明年再來,生我養我的小城每年冬天都會迎接成千上萬的烏鴉,在日本房這一帶,烏鴉只會停歇在“卡蠟思”胡同,每家每戶的樹梢電線上全都黑壓壓地墜滿烏鴉,是樁怪事,見怪不怪。
我的衛兵提著槍站在門口,“小北哥,我媽也是蹲著撒尿的。”
“你見過啊,”我一邊綁褲繩一邊罵他,“小流氓。”
堯小智沒回答我,他開槍了,連發掃射踏著正步高喊順口溜的毛豆和二餅,這倆小癟三是隔壁胡同的,比我大一歲,已經上一年級了,昂首挺胸聲音嘹亮,生出了我和堯小智這種無業游民難以理解的光榮和驕傲。
“一九九一年,我學會開車,上坡下坡,壓死二百多。警察來抓我,我跑進女廁所。女廁所沒開燈,我掉進粑粑坑。我和粑粑作斗爭,差點沒犧牲!”
好死不死,當年在街頭巷尾操場教室流傳的順口溜里我最膈應這首,每次聽都有種被現場抓包的驚心動魄,這種頭皮發麻的感覺時至今日也不得消散,只要想起就能回憶起童年棚戶區旱廁的惡臭和堯小智開槍的聲音,塑料子彈迸濺在石子地面,彈起來崩到了毛豆的臉,毛豆和二餅尖叫著“小瘋子”撲過來把堯小智按在身下,我從廁所沖出來,抄起我媽忘在門口的爐鉤子,瞄準二餅背著書包的后背掄了下去。
我們迅速扭打成一團,也迅速被我媽分開,二餅和毛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媽打針,我媽一瞪眼他倆立刻噤若寒蟬,他倆惡人先告狀,控訴小瘋子無緣無故用槍打他們,我媽把堯小智一直死死抱在懷里的槍接過來,晃了晃聽了聽子彈碰撞的嘩啦聲,她狠狠剜了我一眼,對他們說,“小智是弟弟,還不懂事,你們倆過幾天就戴紅領巾了,是大孩子了,讓讓他,好不好?”
二餅抽了抽鼻子,不等他說話,我媽按住我的后腦一使勁兒,“道歉!晚上不許吃飯!”
我乖乖道了歉,抬頭看見他倆偷偷沖我做鬼臉,一股火“騰”地燒起來,我媽又說,“還有,以后誰再叫小智瘋子,阿姨就給誰多扎幾針。”
二餅臉色一白,毛豆捂住了屁股,連跑帶顛地穿小道回家去了,我心里的火立刻又降了下來,沖他們跑遠的方向呸了一口,我媽給了我一腳,我怕她追問我堯小智開槍的原因,連忙說,“媽你看,小智的臉劃破了。”
我媽蹲下身,把又開始玩兒螞蟻的堯小智抱起來,看了看他臉上的擦傷,又看了看他手上蹭掉的紗布,堯小智的奶奶在院兒里大聲放收音機,她聽不見,卻每天晚上都要聽收音機,我媽沖堯小智家望了一眼,嘆了口氣,抱著他進院兒去了。
進了十月,晚上冷了,棚戶區沒有暖氣,我媽怕我凍著,早早生了爐子,屋里一股煤灰和苞米糊子混合的煙味兒,棚戶區的天黑得也早,沒有路燈,月亮的光暈被遠處的火車站和大馬路吞噬,只有些許的余溫落在沙土路、瀝青屋頂和紅磚墻頭,薄薄的一層,像爐蓋上的灰。
我鉆進被窩,緊挨著我媽看電視。晚上我還是吃到飯了,堯小智吃剩下的雞蛋糕,他吃了我家的雞蛋糕,還拿走了我媽前些天收拾東西翻出來的牡丹相機,我和我媽都不喜歡照相,傳說兩三歲時我只要被鏡頭對著就會嚎啕大哭,堯小智看見柜子上的相機,抓起來就不撒手,我媽從抽屜里找出一卷膠卷裝進去,教他給正蹲著捅爐子的我拍了兩張。
堯小智歡呼,死死抱著對他而言又重又大的黑盒子,我媽說,“喜歡就送給你。”我嚇了一跳,“啊?你不是說這相機是我姥爺送你的嗎?”我媽說,“我也用不上了,再說了,這東西給小智比給你保險。”
那天的堯小智失去了令他生的人,得到了令他死的寶貝。我媽在很多年后仍因這件事追悔莫及,可那時的我們誰也不會預測未來,我媽沉浸在對堯小智的憐愛和同情里,而我從那時起就在被困擾我一生的問題糾纏,根本無暇顧及其他。
電視開始播廣告,我把下巴擱在枕頭上,聽我媽嘆了口氣,“小智他奶有一天沒一天的,他爸也不回來看看。”
我說,“小智他奶要是沒了,小智怎么辦?”
“跟他爸走吧,他爸在外邊兒打工肯定有……”我媽頓了一下,“落腳的地方。”
我媽時常接觸生死,她無處可講,就講給我聽,我也就比其他孩子更早地對生與死有了認知。我媽八成是怕我問下去,話頭一轉說,“我今天上午給老李頭兒打針,下午人就沒了,歲數大了真沒辦法,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我問她,“媽你怕死嗎?”
她側臥過來,摸了摸我的臉,“怕,沒你的時候我不怕。”
我愣住了,我覺得我不怕死,這使我很羨慕母親,有這么幾分鐘的時間,我甚至想把隱瞞的一切都和我媽坦白,我又想起了堯小智,想起他比洋娃娃還好看的臉,想起他在我媽懷里的樣子。我說,“媽,我也想怕死,我想當媽媽。”
我媽沒有回應,她太累,已經睡著了。我像被兜頭澆了一盆涼水,冷汗從頭出到了腳,我躺在床上暗自慶幸她沒聽到我的話,屋外傳來幾聲烏鴉叫,又到了鬧烏鴉災的季節,我這么想著,第一次徹夜未眠。
從那天起,堯小智不管去哪兒都抱著我媽的牡丹相機,吃飯抱著睡覺抱著。我媽找了根繩兒把照相機掛在他脖子上,像在他的小細脖兒上墜了個枷,隨時都能把腦袋下來。一卷膠卷十塊錢,三十六張,他不和那些活物玩兒了,改成了拍,讓它們都活在他的小盒子里。入了冬,除了人以外能找見的活物越來越少,于是他開始每天坐在門口等烏鴉過路。
我比他閑,見天揣著張乘法口訣,往磚頭上一坐死盯著堯小智,他等烏鴉,我守著他和相機。那時候,治安也遠不及現在穩定。我家離火車站近,遍地小偷兒,小偷兒在公交車上用鑷子掏包,被抓包了敢拎著水果刀跟到家里報復。我家被偷過一次,賊是從木條窗框爬進去的,我媽回來冷靜地檢查了一遍,發現家里丟了半桶豆油,一袋沒拆封的鋼絲球,還有她剛收的沒來得及存的藥費。她檢查了一下堆在臥室的紙殼箱,藥一瓶沒丟,我媽開火做飯,跟我說,“這賊真不識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