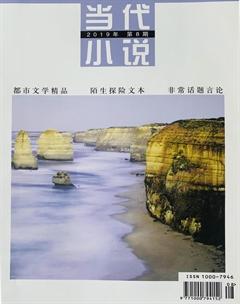梯云溪猜想
孫葆元
芙蓉街以變身活在歷史的歲月里,說它是一條古街,是它遺落在典志里不同時期的記載,變幻著不同的身姿,與風云打個照面就轉身離去。1934年的《濟南便覽》是一面鏡子,從這里看,它是一條百貨街,珠寶琳瑯,間雜幾家出版社和報館。如果往前推至晚清,它是應試舉子的必經之道,更應該是一條文化朝圣的街,應該有客舍牙店,書樓茶肆。如果往后推,在1934至1948的14年間,它是一條騷動的街,街面上談論著家國淪喪,奴役與解放,是民不聊生的市井。濟南解放以后,經過幾年短暫恢復,工商經濟進入社會主義改造,這條街沉寂下來,成為一條民居街。改革開放以來,沿街門戶洞開,店標競彩,酒樓比鄰,飯攤相接,就把它打造成一條“吃”街。
在無數次的變身中芙蓉街經歷著衰朽與新生,2018年迎來最近的一次整體大修,把路面鋪成古樸的石板路,在整修中讓一度撲朔迷離的梯云溪重見天日。梯云溪與芙蓉街北端的貢院和文廟息息相關,那條流水是舉子們的吉祥,攀梯而上。溪上有橋,便叫步云橋。平步青云是當時士子們的所求。一系列建筑構成一組開科取士的文化圖。有學以來這是選拔人才的肇始,綿延千年,形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動脈。從這個意義上說,芙蓉街應該是一條梯云街。
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梯云溪,那是典志上記載的一條屬于士子的河。在擁擠的人流中移步芙蓉泉畔,一道臨時圍欄圍起一道小溝,有水少許,外延不足跬步。這哪是溪?充其量是條溝!抬腿便可跨越,更別說在“溝”上建橋了。現實與歷史竟這樣大相徑庭?正是這樣的差距讓我重新審視文廟。
這座文廟除了基址如舊,一切都是拔地新建。從職能上說文廟是祭祀先師孔子的地方,舉子應試應該在文廟左鄰的貢院。右上左下,符合禮制。舉子試前先行拜師禮,然后進入考場,按這個程序,文廟與貢院是一組不可分割的建筑。梯云溪和溪上的步云橋很可能是文廟與貢院的連接通道。如此多的試子云集在應試之日,文廟的影壁外應該是一個寬闊的廣場。這個廣場足以容納一條河流通過或繞過,而且河上架著一座通往理想的橋。廣場周邊有數條巷口通向四方,芙蓉街是其中的一條。如此的街、場、院、廟構成一組州府文化建筑群。1901年是光緒二十七年,光緒帝下詔,停止武科考試,文科考試也漸漸式微,貢院終結了它的歷史使命。此后便是學校教育興起,科舉制度淡出人們的視野。這一片古老的科考試場就成為遺跡。在梯云溪的挖掘中我們挖掘出另外一番啟示,任何文化都不是虛無的,都有與它相對應的物質存留,當一種制度消失,它的存留便失去根基,在歷史中荒蕪就是必然的。
芙蓉街荒蕪著它的取仕之路,貢院無存,文廟雖然得以修復,但是它的外環境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現今影壁前那幾條狹窄的巷道絕容不下當年士子的人流,更別說恢復梯云溪,步云橋了。于是我們不得不對那個失去的廣場進行大致的推測:坐北朝南的圣廟,它的外廣場往南應該延伸至芙蓉泉一側,往西應該包容貢院門首,才符合士子們前程廣闊的仕途胸襟,梯云溪才能穿過這個廣闊流進它的遙遠。如今的狹窄是文圣去后,生民居住和營生對它的蠶食。在逐年蠶食中,廣場萎縮,民宅進逼,形成它柴米油鹽的繁華。
被壓縮的還有梯云溪。這條河絕不止芙蓉泉一個源頭,它應該是珍珠泉水系多個泉的合流。《水經注》記載,此地源泉眾多,“枝津合水”,亂流如注,自古是游人經停、野炊宴飲之地。地面建筑的變遷改變不了地質的變遷。房屋街衢可以百變,占地奪泉,筑舍掩渠,不僅街巷的格局改變了,連泉流走向也改變了。我認識一位張姓醫生,他主持的醫院就曾設在芙蓉街口,有一年,他的同事病了,他去探望。同事居住在芙蓉街某處院子里,他告訴張醫生,我的床底下還有一眼泉,打開床下的木蓋就能舀水喝。
我記下了這個故事,曾經探訪那處秘密的泉眼。怎奈巷如棋盤,院如迷宮,民宅尊嚴,上哪里去找這眼泉?在那個地帶徘徊久了,我堅信,每一塊青石板下都有一口泉眼,即使你用青石板蓋住它,它也會成“枝“流瀉,在地下奔騰。現今的芙蓉街充其量就是一條河的寬度,有河無街,從芙蓉泉往北應該是那片廣場。
桂林保留著一座王城,王城里有一所貢院,門衛森嚴,進得門去,就見一間間隔房并排而列,那房,三面圍墻,一面敞開,對著甬道,士子的桌面赫然可見,一切作弊都在監考可視之內,足見取士的嚴格。濟南的貢院已經湮沒在歷史的風塵中,只留下一道墻根供歲月懷想。文廟的大成之魂似乎在回歸,一群不愿意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重新裝扮好在這里舉行開筆禮,用古老的儀式開啟現代教育的大門。還有無數的紅絲帶系在先師足下的圍欄上,帶上寫著,先師護佑,考取某某學校之類。人生每臨大的競爭都有一場這樣的心理活動。在我看只是一場游戲。
特約編輯:陳?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