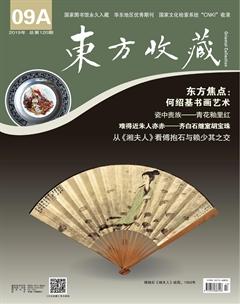“清代書法第一人”何紹基書法藝術
張明堂



在中國書法史上,清代是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在經歷了魏晉、唐、宋明帖學的昌盛和輝煌后,從清中期開始碑學興起,于是書風為之一變,名家輩出,流派紛呈,史稱書道中興。在清代眾多名家中,成就最大的是何紹基,他被譽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清代書法第一人”。
何紹基,道光十六年進士,官至國史館提調、總纂,四川學政,主持過幾省鄉試。晚年主山東濼源、長沙城南、蘇州揚州諸書院。何紹基博涉群書,精心學問,于六經子史,皆有論述,造詣甚深。然而影響大的是他的書法,五體皆擅,而成就最高的是他集眾家所長,創造性地將顏體楷書筆法應用到行草書,形成了獨特的“何體”書法。
清代有帖學和碑學之分。碑學始于宋代,清嘉慶、道光之前,書法崇尚法帖,嘉慶、道光以后,金石大盛而碑派書法興起,阮元倡為南北書派論,包世臣繼起提倡北碑,崇碑之風一時大盛。碑派書法以金石碑刻改造傳統書法,確實給書法注入活力,特別是借古開今的精神和表現個性的書法創作,開一代局面,功不可沒。然而,后來碑派卻走上極端,崇碑抑帖,以致發展到以談碑學碑為榮,以談帖學帖為不屑,與帖學對立、水火不相容。固執一端,未免失之偏頗。書法的精髓在通變,清代碑派書法最突出成績是用金石碑刻筆法改造隸書,當時感覺耳目一新,實際上不過是外形的新奇嫁接而已,并無實質意義。不從根本上博通隸變,寫出來的只是不倫不類的八分書,而不是真正的隸書。
碑學與帖學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各有特點,碑學雄壯,帖學秀美,可以互相補充、融會貫通,有機統一。
何紹基出身于書香門第,其父何凌漢曾任戶部尚書,是知名的書法家、教育家、學者、藏書家,其書法出入歐、顏,名重一時。何氏一門四代無不擅書。何紹基精于帖學,自稱“少壯時,喜臨《爭座位帖》,廷對策亦以顏法書之。”之后傾心“二王”書法,這從《漢書補注稿》《贈汪菊士詩冊》可見一斑。中年后,又醉心于歐陽通的《道因法師碑》。另外,受碑學思想的啟蒙,何紹基早年即論書崇尚北碑,提出化分入楷、推崇北魏《張黑女》,何紹基晚年更是大量臨習漢碑,從咸豐八年至同治元年間,所臨漢碑有《禮器碑》《張遷碑》《石門頌》等十余種,其中尤以《張遷碑》及《禮器碑》用功最勤,動輒百通以上。專攻隸書之余,間亦臨習篆書,并且創造性地將金文與小篆結合。
何紹基高明之處在于博通帖學和碑學,南北兼收,碑帖并重,把碑和帖有機地融合起來,取碑帖眾家之長,將篆隸楷行草筆法融為一體。他說:余學書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草、篆、分、行熔為一爐,神龍變化,不可測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書法風格。何紹基于楷書、行書、隸書、草書、篆書無所不精,而獨具神韻。其楷書取顏字結體的寬博而無疏闊之氣,又摻入碑刻以及歐陽詢、歐陽通書法險峻茂密的特點,以及《張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氣,小楷兼取晉代書法傳統,筆意含蘊,其篆書,中鋒用筆,并能摻入隸筆,瀟灑自然,其行書厚重,用筆十分開張大氣,線條方圓兼施,一任自然。大字常將篆隸筆意融入,極富金石氣,而小字則常將顏蘇以及篆籀書風隨手拈來,融會貫通,自然天成。其書法既保留了帖的風神,又有碑的氣息,從而成為有清以來能成功融會碑和帖而顯示獨特書法面貌的開創性書家。
何紹基書法筑基于顏真卿。受其父何凌漢晚年師顏的影響,何氏一門四代均能顏書。何紹基中年顏體書法,更是臻于極致。他說:“余平生于顏書手鉤《忠義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文》、大字《麻姑壇記》《李元靖碑》。”而于《爭座位帖》用功尤深,其早年臨《爭座位帖》,目前已知者僅三件,一為上海博物館藏道光十四年三十六歲所臨,一為道光二十一年左右約四十三歲為霽南所臨,另一件即為三十九歲為陳慶鏞所臨。由于何紹基對顏書用功至深,后人公認其為有清顏書四大家之一。這是“何體”產生的基礎。
何紹基書法成功于對顏體的通變。在書法諸體中,草書與楷書風貌距離最遠,最具實踐難度,其價值也最高。顏真卿以降千余年來,學顏者多囿于顏楷,不能越雷池半步,何紹基取法顏真卿,主張“學書重骨不重姿”與“書家須自立門戶”,成功地將顏楷雄壯廟堂之氣內化入行草書中,引楷入草,形成了獨特的“何體”書法藝術,這既是對顏體書法的發展,又是草書書法的新境界,也使中國行草書法藝術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在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曾國藩特別推崇“何體”書法,他說:“子貞書法,必傳千古。”馬宗霍先生稱譽何紹基“把中國書法藝術推向第三個高峰。”確實如此,“何體”對近現代書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百多年后,何體書法風靡九州,已成為當代書法熱潮中的重要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