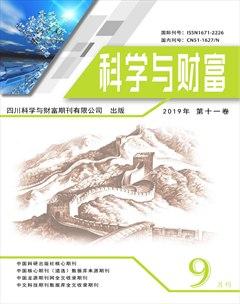背(續(xù)一)
鄒開權(quán)
又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jié),每到此時(shí),都特想我高齡的母親。前兩年的母親節(jié),我都回老家看了母親,并以《背》為題,寫了一些文字。祝母親健康長(zhǎng)壽,希望我一年一篇的《背》能延續(xù)到《背-續(xù)十》,菩薩保佑!今天一早驅(qū)車回老家看母親,推開門看到母親的背影,還是坐在客廳老位置的椅子上(母親自去年冬天以后就不能站立了)。她聽力很好,我喊她,她馬上就答應(yīng)。而且,這次她居然未經(jīng)提示,直接叫出了我的小名:七婆。原來(lái)看過龍應(yīng)臺(tái)寫的《目送》,抒寫父母與子女之情的,很受感動(dòng)。但我也覺得,自母腹中誕生以后,人生可能會(huì)與父母漸行漸遠(yuǎn),但終究身體和心靈會(huì)回歸母體。這兩年隨著母親的年齡增高、癡呆癥加劇、身體更加虛弱,我身在外地,卻越發(fā)地想念母親,想到很早以前母親的一些事。
聽我母親說(shuō)過,我在很小的時(shí)候差一點(diǎn)讓人抱養(yǎng) ,因家里姊妹太多擔(dān)心不能養(yǎng)活。事實(shí)上我頂上的一個(gè)姐姐生下不久就餓死了,當(dāng)然那正是60年過糧食關(guān)時(shí)期。兩年后我出生了,情況稍好一點(diǎn)點(diǎn),但我父親卻得了重病。估計(jì)是父親自知無(wú)法盡撫養(yǎng)之責(zé),擔(dān)心日后母親難把孩子養(yǎng)大,私下答應(yīng)將我抱給本街的一對(duì)張姓夫婦,但我母親堅(jiān)決不干。那家夫婦早上來(lái)領(lǐng)人時(shí),母親拿一條長(zhǎng)凳橫放在門口,她坐在當(dāng)中,硬是沒讓那家人把我抱走。那家人住在老家小鎮(zhèn)的上街子,童年時(shí)每天讀書都要從他家門前經(jīng)過。街上人稱那女的叫“尸孃”,就是“仙婆”一類的吧,小時(shí)候想到這名字,心里多少有點(diǎn)毛乎乎地。她的顴骨有些突起,跟魯迅筆下的楊二嫂一樣,樣子難看。總之,就覺得她“惡叫叫”的,不像個(gè)好人。門前街陽(yáng)上擺一個(gè)小灘,賣些水煙等等亂七八糟的東西。那男的長(zhǎng)得很是高大,五官還算周正,臉上堆了些許橫肉,雖算不上怒目圓睜,但總感到有一絲寒意。不過大多數(shù)時(shí)候是:小灘邊放有一張長(zhǎng)馬駕椅,他手里握一支很長(zhǎng)很長(zhǎng)的煙桿(估計(jì)解放前是抽大煙的),翹著二郎腿躺著。長(zhǎng)大些后,我常常慶幸:幸虧自己沒被抱養(yǎng)給他們,那對(duì)夫婦可真不是個(gè)善主。不然我的人生不知好陰暗、有多悲催……聽母親說(shuō),父親得的是“鼓脹病”,臨死前肚子里裝滿了水,肚子很大。小時(shí)候街上有些小伙伴老是叫我“大肚皮”,這顯然是一個(gè)貶義的,含辱罵語(yǔ)氣的外號(hào)。這不是在別人傷口上撒鹽嗎!心中很是不快。那個(gè)年代的人,大大小小的,素質(zhì)都極低。其實(shí)父親得的就是肝病,沒法治,兩年之后便去世了,那時(shí)我三歲,弟弟才一歲。
母親原是老家鎮(zhèn)上的一家飯店的職工,屬于集體所有制的那種社會(huì)商業(yè),與我家僅一墻之隔。還記得店名叫“青春食堂”,可能是因?yàn)榈昀锬贻p人(主要是年輕女子)多些的緣故罷。文革開始后,啥都要革命,要有革命色彩,一片紅,于是改名為“工農(nóng)兵飯店”。我家所住的“友愛街”,也沒能逃脫厄運(yùn),名字也被“革命”了。搞笑的是,把“友愛街”從街中間剖開,我家住北面的半邊街改為“反修街”,對(duì)面的半邊街改成為“反帝街”。這樣一來(lái),改個(gè)街名,順便就把美帝蘇修一并給收拾了。那個(gè)時(shí)候母親是不會(huì),也不可能跟著那些年輕女子去享受青春的浪漫的,也更不去摻和那些是是非非的“政治”。母親是文盲,又一個(gè)人拖兒帶女。她只知道上班干活,只知道怎樣讓家中的孩子不餓著、不凍著。印象中母親總是忙忙碌碌的。那時(shí)候,家里生活確實(shí)很困難,感覺好像經(jīng)常是饑腸轆轆的,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tài)。因我家在飯店隔壁,母親常常能撿回些飯店食客吃剩的“油湯湯”,以補(bǔ)充我們的食物。“油湯湯”香噴噴的,比家里的煮紅苕、面疙瘩好吃多了,我們兄妹幾個(gè)都爭(zhēng)著吃。那時(shí)才不講究什么衛(wèi)不衛(wèi)生喲。這樣看來(lái),我們兄妹幾個(gè)在那個(gè)年代都能活下來(lái),到現(xiàn)在個(gè)個(gè)身體都健康,必須得歸功于我們從小練就的一身“抗病毒”的神功。不過那時(shí)大家都難,到飯店的食客大多都吃不上大餐,充其量點(diǎn)一道葷菜享用,就算豪華了,所以我們能吃到的真的就是殘湯剩水了。
從小我就有這樣一種感覺,母親特別喜歡幫助別人,按我們俗語(yǔ)說(shuō)的就是很愛幫忙。街坊鄰居、親戚朋友,大事小事,只要是她能做到的,她都盡其所能地給予幫助。物質(zhì)上幫不了的,她就會(huì)給你出主意、想辦法,總之是一個(gè)典型的“熱心腸”人。老家地處內(nèi)樂公路的中間,過往的車輛較多,且多在老家小鎮(zhèn)吃飯,甚或住宿。那些常年跑車的師傅,特別是鹽業(yè)地質(zhì)鉆井大隊(duì)的師傅,經(jīng)常得到我母親的幫助。有的師傅出車時(shí)都不多帶衣服,反正如遇天氣降溫時(shí),在長(zhǎng)山黃大姐那里加衣服就是了。以至于我父親去逝多年,母親照樣把他的衣服經(jīng)常都洗得干干凈凈的,為了讓那些外出的年輕師傅們加衣御寒。當(dāng)時(shí)家里生活困難,但一年四季泡菜卻多,因?yàn)橛械膸煾党燥垥r(shí)喜歡泡菜,母親便回家取過來(lái)(那時(shí)飯店是不提供泡菜的)。如此種種,母親就是這樣地與人友善,關(guān)愛他人。同樣地,我想那些得到過母親幫助的人,也一定很感激和敬重我母親的。我不能確定有沒有個(gè)別的師傅,有時(shí)甚至?xí)c(diǎn)一個(gè)葷菜,然后故意吃不完,好讓我母親帶回家,讓我們解解饞呢?!也許有吧。多年以后的一次經(jīng)歷可以對(duì)此佐證。98年,我考入鉆井大隊(duì)駐地的那座城市的師范學(xué)校,那年我16歲。國(guó)慶節(jié)放假幾天,沒錢,卻想回家,于是我決定走到鉆井大隊(duì)去碰碰運(yùn)氣。那單位較大,人多,車也不少,可轉(zhuǎn)悠了好一陣子,也沒碰到一個(gè)熟面孔。我沒灰心,干脆直接走進(jìn)他們的辦公室。那么大一個(gè)單位,我本來(lái)就認(rèn)識(shí)不了幾個(gè)人,更不知道名字。忘了當(dāng)時(shí)怎樣問的,總之,有個(gè)人立馬站起來(lái),吃驚地說(shuō):你就是黃大姐的娃娃?然后,他便帶我去車隊(duì),只聽他大聲嚷嚷:今天有車發(fā)長(zhǎng)山嗎?這是長(zhǎng)山黃大姐的娃娃……好幾個(gè)人都過來(lái)看我,但他們的車都不發(fā)長(zhǎng)山方向。后來(lái)他又帶我去大隊(duì)調(diào)度室,查到第二天有發(fā)長(zhǎng)山方向的車。當(dāng)天中午在他們單位食堂吃飯時(shí),他照樣跟眾人介紹:這是長(zhǎng)山黃大姐的娃娃。同樣地很多的人都過來(lái)看我,詢問搭車的事落實(shí)了沒。下班后,他帶我回他家,直到第二天把我送上車。
我家的房子比較寬,長(zhǎng)條形的,外面當(dāng)街,后門臨河。臨街的那間正屋特別大,后面左邊隔出一間臥室。印象中,這正屋不是我家人能享用的,一到趕場(chǎng)天,全被鄉(xiāng)壩頭的人“霸占”。對(duì)此,看不出我母親有丁點(diǎn)抱怨,也許母親是專門為他們提供方便的。我的父親是入贅的,老家離鎮(zhèn)上幾里路。光輝大隊(duì)、人民大隊(duì)的本家、熟人特多,自然我家就成了他們的會(huì)館。那些人有事無(wú)事,只要上街,都到我家落腳。也是,老家小鎮(zhèn)確實(shí)小,抽半支香煙就能走過通街,那些人轉(zhuǎn)夠了,不到我家來(lái),又到哪里去!那個(gè)年代,總覺得閑人特別多。身無(wú)分文,也不辦任何事,就要竄到街上轉(zhuǎn)悠。印象很深的是:中午放學(xué)回家,夏日炎炎,街上好像沒倆人,家里卻是黑壓壓的一大片。門檻上坐了人,我得擠著跨過門檻,再擠著走到里屋。人困馬乏,想躺上床睡個(gè)大覺,卻只見床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人,“陣地”被鄉(xiāng)壩頭的人占領(lǐng)了……
善良和仁慈總是孿生兄弟,我的母親,心腸既是火熱的又是柔軟的,她天生有一顆憐憫之心。她同情弱者。文革時(shí)期有一次,街上造反派揪斗毆打一個(gè)鄰居走資派,她挺身而出,仗義執(zhí)言,不許他們打人。母親出身貧農(nóng),又沒文化,她才不管那么多呢!有時(shí)趕場(chǎng)天“四管會(huì)”外面橋頭上,會(huì)有個(gè)把人被捆起雙手示眾。主要是小偷之類的,也有重慶知青,因?yàn)橥缔r(nóng)民的雞被逮住。那些重慶知青,小小年紀(jì),背井離鄉(xiāng),遠(yuǎn)離父母,也許確實(shí)也太餓了。示眾就算了,但有的人偏要?jiǎng)邮执颍€不輕。每每遇到這種情形,母親都會(huì)極力勸說(shuō)制止,說(shuō)這些娃娃也很“遭孽”(可憐)。
成年后,我當(dāng)了一名中學(xué)老師,在母親的眼里是個(gè)文弱書生。工作十五年后,沒想到竟然“投筆從戎”,改行當(dāng)了一名警察。記得改行后不久,母親知道點(diǎn)我工作的特殊性質(zhì),告誡我:七婆(我小名),你別打他們哦,那些人也很“遭孽”的。我這人,天生自負(fù),一般人的人的話我是不會(huì)聽的。但母親的話,在我心中就是圣旨,我是決計(jì)要遵從的。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有“碰”過一次我的工作對(duì)象。
小時(shí)候, 母親從沒有打罵過我們兄妹幾個(gè),特別是對(duì)最小的我和弟弟兩個(gè),她都寵愛有加。不管我們有多頑皮,甚至搞些惡作劇,她都不會(huì)打我們的。記得有一次,傍晚,和兒時(shí)鄰居玩友,看到母親上班的飯店外停有一輛架架車(板車),那是幾十百里外三江、馬踏來(lái)我老家煤廠拖煤的,我老家產(chǎn)煤。我們輪換著去練板車駕駛技術(shù),因操作不當(dāng),架架車在急駛中觸地,導(dǎo)致把手折斷,惹下一場(chǎng)大禍,心想,遭了,要賠“耍黨”(因玩耍時(shí)損壞東西而賠償),嚇得不得了。要知道那些外地人,真的很可憐。他們帶著干糧,揣著一年工分換來(lái)的錢,趕百多里路來(lái)買一年用的燒煤。后來(lái),還是一小伙伴的父親,拆一根自家的鋤把換上,免強(qiáng)代替駕駕車把手。那些外地人也真本份老好,一點(diǎn)都沒要挾我們各家的大人。不知那些人終究把煤拖回家沒有?應(yīng)該夠他們一路折騰地。總之,沒見他們趕回程時(shí)來(lái)找麻煩。照例,這次我仍然沒挨打。不過,出了鋤把的那家娃兒,被打慘了,估計(jì)是他父親出了鋤把,還得出氣……
母親退休以后,開始信佛。她經(jīng)常去朝真武山醒悟寺(就在老家),一直到得了老年癡呆癥以后才停止。母親很慷慨,成了那兒的一個(gè)大施主。我佛慈悲,佛恩浩蕩,佛的善良慈悲,不就是我母親一生的寫照嗎!在母親節(jié)來(lái)臨之際,我祝愿母親健康長(zhǎng)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