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碩作品集》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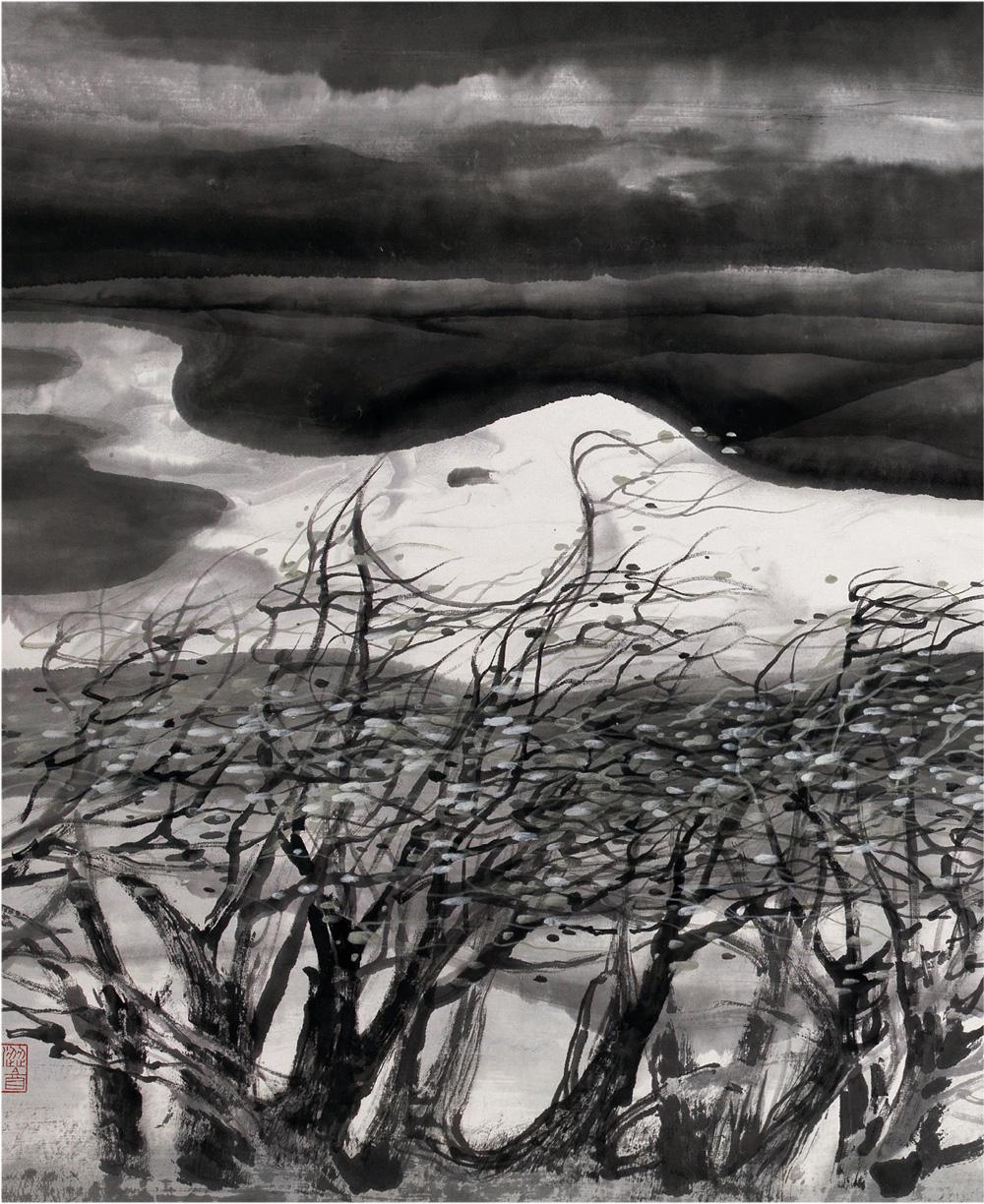


何懷碩,1941年生于廣東。畢業(yè)于臺(tái)灣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系。美國(guó)紐約圣若望大學(xué)藝術(shù)碩士。曾任教于中國(guó)文化大學(xué)、臺(tái)灣“清華大學(xué)”、臺(tái)北藝術(shù)學(xué)院、臺(tái)灣師范大學(xué)美研所。出版有《懷碩三論》《煮石集》《繪畫獨(dú)白》《何懷碩文集》等。
這本畫集距離20世紀(jì)最末一年我那本名為《心象風(fēng)景》的畫集剛好二十年。現(xiàn)在我已到俗稱“喜壽”的年紀(jì)(因?yàn)椴輹跋病弊趾芟衿呤撸2恢挥X(jué)間,也配稱老畫家了。但二十年不開(kāi)畫展、不印畫冊(cè),按現(xiàn)代的標(biāo)準(zhǔn),還能算畫家嗎?我的畫冊(cè)很少,連這一本,只有六本,包括極薄的兩本小冊(cè);另一方面,除了專門抄襲古人的畫家之外,同代畫家沒(méi)有不竭力求新求變、花樣百出、以新奇怪誕為創(chuàng)新者,而我卻幾乎一生都在追求表現(xiàn)自我藝術(shù)主張的個(gè)人風(fēng)格,絕不與時(shí)潮浮沉。
畫冊(cè)不多,是因?yàn)樽髌窙](méi)有大量生產(chǎn),所以畫展也不多。畫家的才情與創(chuàng)作力、作品的多寡應(yīng)無(wú)直接因果關(guān)系,如果有的話,多半呈反比。一心求好,無(wú)心以藝術(shù)去換取虛名實(shí)利;要求質(zhì)高,自然量少。所以,我想做畫家,但不想做“職業(yè)畫家”。
許多朋友說(shuō):你畫那么好,不畫太可惜了;有的說(shuō):你的畫拍賣價(jià)不俗,你怎么不畫呢?的確,我問(wèn)自己,也沒(méi)答案;一句話,我不愿改變初衷。我對(duì)大陸同道說(shuō),真希望有一條政策:活著的畫家作品不準(zhǔn)上拍賣市場(chǎng)。我很痛心,商業(yè)化使藝術(shù)庸俗、淺薄,甚至死了。30多年前趙無(wú)極來(lái)臺(tái)北,閑談間,他告訴大家他很用功,去畫室工作有定時(shí),好像上班,我會(huì)心一笑。不久前看到日本小說(shuō)家村上春樹(shù)自稱“職業(yè)小說(shuō)家”,我也覺(jué)得可笑。商業(yè)化把藝術(shù)創(chuàng)作當(dāng)產(chǎn)業(yè)了。現(xiàn)在雖然還有詩(shī)人也者,但能有“職業(yè)詩(shī)人”嗎?
西方現(xiàn)代至后現(xiàn)代主義以反傳統(tǒng)、新奇怪誕為“創(chuàng)造”,我的創(chuàng)作與理念都反對(duì)、抗逆這個(gè)時(shí)潮,甘愿踽踽獨(dú)行。
20世紀(jì)之初,西方現(xiàn)代主義從出現(xiàn)、開(kāi)花、異化到變質(zhì),成為歐美西方中心主義殖民、貶抑、毀滅非西方文化,宰制全球的利器。我從欣賞、懷疑到批判,如果我不讀書、不到歐美認(rèn)真考察,長(zhǎng)年思考、研究、寫作,建立自己的理念,探尋自己應(yīng)走的方向,試問(wèn)我提起筆來(lái),怎么畫?許多人忘記我最初是一個(gè)年輕的畫家,我一邊畫,一邊讀、思、寫,是為我自己的困惑求解不得不然的尋索。有人以為我喜歡不務(wù)正業(yè),貪求“左手文、右手畫”的美名,其實(shí)誤解。
20世紀(jì)中期,臺(tái)灣藝壇出現(xiàn)復(fù)古與西化強(qiáng)烈反差的現(xiàn)象,畫家們面臨歧路,若只學(xué)藝而無(wú)自己獨(dú)立的思想,必然陷于迷途。當(dāng)時(shí)歐美“前衛(wèi)藝術(shù)”各派洶涌而人,復(fù)古派卻依樣畫葫蘆。中國(guó)藝壇,南轅北轍,各行其是,是我青年時(shí)代最大的困惑,我渴望找到答案。我反對(duì)藝術(shù)家做變色龍,也反對(duì)藝術(shù)的全球化。我認(rèn)為民族特色與個(gè)人風(fēng)格是藝術(shù)不可欠缺的要素。獨(dú)特風(fēng)格要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的努力,才有希望登上高峰。不斷求新、求變是商業(yè)化的伎倆,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以降反傳統(tǒng)的流毒所引發(fā)的集體熱病。我認(rèn)為藝術(shù)家建立自己的高峰,為人類貢獻(xiàn)真正的藝術(shù)成就,正如同思想家、科學(xué)家、文學(xué)家與一切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的學(xué)者,都應(yīng)秉持同樣的態(tài)度:專一,不見(jiàn)異思遷、堅(jiān)持到底,才有希望取得重大成就。這樣平實(shí)而遠(yuǎn)大的道路,不只是藝術(shù)應(yīng)走的方向,何嘗不是人生應(yīng)走的方向。
不肯依附時(shí)潮的藝術(shù)家,便自覺(jué)幾乎自動(dòng)被開(kāi)除出局。我選擇我自己服膺的道路,只能自我邊緣化。20年不曾辦個(gè)展,躲在一隅,獨(dú)立自守,不如此,我還能如何?這是我“掉隊(duì)”的原因。
我創(chuàng)作至今約半個(gè)世紀(jì),重讀過(guò)去五本畫冊(cè)自序,可以回顧初心。
1973年《何懷碩畫集》是第一本,有梁實(shí)秋、葉公超兩位前輩的序,太難得了。自序中我說(shu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二個(gè)課題的整合,是對(duì)現(xiàn)代中國(guó)畫家最嚴(yán)重的考驗(yàn)。頑固的復(fù)古與盲目的西化,都不是有志建設(shè)現(xiàn)代中國(guó)畫者所應(yīng)有的態(tài)度。”這個(gè)基本觀念,我五十年未變。當(dāng)時(shí)西方流行現(xiàn)代繪畫,臺(tái)北一班西潮追隨者便提倡“中國(guó)現(xiàn)代畫”,我要建設(shè)的是“現(xiàn)代中國(guó)畫”。因?yàn)槲也徽J(rèn)為“現(xiàn)代畫”是世界性的,也不認(rèn)為我們應(yīng)加入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
第二本畫冊(cè)已到了1981年。《懷碩造境》的自序中,我說(shuō):“當(dāng)復(fù)古與西化大行其道的時(shí)候,我卻一直獨(dú)立于主流之外。”“藝術(shù)不僅是美的追求,而且表現(xiàn)了藝術(shù)家對(duì)世界與人生的觀照,表現(xiàn)了一個(gè)時(shí)代中最具深度、最超越的識(shí)見(jiàn)與理念,最崇高的心靈所堅(jiān)持與憧憬的價(jià)值。”好的藝術(shù)會(huì)為這些超越的心靈代言,壞藝術(shù)只能媚俗。
梁實(shí)秋老師為我1984年在“歷史博物館”個(gè)展作品的畫題英譯,是第三本畫冊(cè)《何懷碩畫》。我說(shuō)到,我們有限的生命,透過(guò)藝術(shù)展現(xiàn)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與萬(wàn)種風(fēng)情,進(jìn)入藝術(shù)家獨(dú)特感應(yīng)與發(fā)現(xiàn)的意象世界,也提出我特別標(biāo)示的“苦澀的美感”,使藝術(shù)的美超越感官而直人哲思之境。
《庚午畫集》是第四本,我最大的一本畫冊(cè),也不過(guò)170多頁(yè)。1990年我在臺(tái)北美術(shù)館舉辦個(gè)展,那是性一的一次。在自序中我揭示了中國(guó)繪畫另一個(gè)老毛病:“中國(guó)繪畫傳統(tǒng)的桎梏,最難擺脫的,不只是筆墨技法的制式化,更嚴(yán)重的是千篇一律都是群體的感情。題材與感情意念的陳詞濫調(diào),中國(guó)繪畫因而在中古徘徊,難以進(jìn)入現(xiàn)代。”溥心畬與張大干是最典型的復(fù)古畫家,這也是“八股”的一種。不論中西,那些古人所創(chuàng)造、成為程式的拿手題材不斷復(fù)制,都是同一病癥。藝術(shù)創(chuàng)作如果缺少獨(dú)特的取材與獨(dú)立的發(fā)現(xiàn),便難有自己的風(fēng)格。崇奉西方的“主義”或中國(guó)的“門派”,都是自我局限。畫家要掙脫束縛,最重要的是表現(xiàn)自己。
20世紀(jì)最后一年,臺(tái)灣“歷史博物館”又一次邀請(qǐng)我舉辦個(gè)展。我的自序用了“真實(shí)的幻景”為題,因此第五本畫冊(cè)名為《心象風(fēng)景》,我用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文學(xué)家)最先得吾心的“夢(mèng)幻比實(shí)在為更高的真”這句話。最好的藝術(shù)差不多都是主觀夢(mèng)幻的寫實(shí)主義。畫與文學(xué),大致如此。我在自序中說(shuō):“我認(rèn)為有自覺(jué)的藝術(shù)家都必以他的生命去創(chuàng)造他個(gè)人獨(dú)特的藝術(shù)史,亦可說(shuō)是以藝術(shù)去表現(xiàn)他個(gè)人的生命史。”繪畫只有具象與抽象,未免太簡(jiǎn)陋。在那本畫冊(cè)中,我以一幅畫來(lái)表現(xiàn)我對(duì)20世紀(jì)的總體印象(感受、懷念與批判所構(gòu)成的視覺(jué)意象),畫題為《世紀(jì)末之月》,作于1995年。這幅畫的構(gòu)想與表現(xiàn),是我少數(shù)的佳作之一。后來(lái)北京故宮博物院八十周年征藏當(dāng)代代表作,我將此畫捐獻(xiàn)給北京故宮博物院。
我前半生屬于20世紀(jì),新世紀(jì)也已快過(guò)了五分之一。這本畫冊(cè),是回顧所來(lái)徑,也借以自省、自勉。我—生堅(jiān)持走自己的道路,逃過(guò)許多誘惑,不肯折節(jié),成為今日的我,良有以也。
這一本不叫畫集,而稱作品集。因?yàn)槌水嫞€有書法。關(guān)于書法,我曾寫過(guò)文章,這里只談一點(diǎn)感想。
歷來(lái)中國(guó)文人,包括散文家、小說(shuō)家、詩(shī)人、理論家、哲學(xué)家、學(xué)者等等文筆佳妙的一大群,大都有書法修養(yǎng),甚至極擅書法;有的干脆同時(shí)是書法史上的大家。王羲之、顏真卿等不消說(shuō),李白、杜甫、蘇軾、陸游、黃道周、倪元璐、文徵明、康有為、梁?jiǎn)⒊际恰Wx書多的武^、官員、名人寫一手好字的也大有人在。書法當(dāng)然是中國(guó)藝術(shù)的一種,而且是中國(guó)文化所獨(dú)有。熊秉明以“書法是中國(guó)文化楊心的核心”來(lái)為書法精神定位,非常高明。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老年常以書法為心靈之寄托。我近20年書法上較多用功,深知書畫同源而又不同流。畫比較顯而露,書則蘊(yùn)而斂。用書法來(lái)傾泄情感、抒發(fā)懷抱、玩味美感,書法的魅力,不止在欣賞者,更在書寫者的感受中。
世界大變遷,人類生存的物質(zhì)環(huán)境進(jìn)入危機(jī);精神價(jià)值、傳統(tǒng)文化也不斷如冰山消融。藝術(shù)面目全非,瀕臨絕境。回想我在舊世紀(jì)結(jié)束前后對(duì)繪畫創(chuàng)作意興闌珊,實(shí)在原因是我對(duì)人類世界大沉淪的失望,因之詩(shī)意的想象枯竭,靈感頓失,只好以思考、寫文、著書,來(lái)表達(dá)我的憂思與所見(jiàn)、所知、所思。許多好友鼓勵(lì)、督促我不應(yīng)放下畫筆,我又感激又慚愧。承蒙許多人的錯(cuò)愛(ài),我不應(yīng)辜負(fù)知己。其實(shí),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之中,心靈的愉悅,實(shí)為抗拒“黑暗年代”、重放人文光輝,找到自我釋放的最佳憑借。老驥伏櫪,還得努力向前。
責(zé)任編輯:陳春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