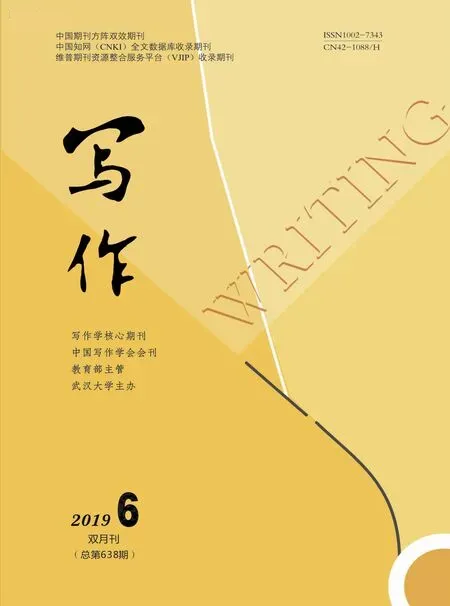1930年代中日現代詩歌寫作比較
陳 璇
20世紀30年代是中日兩國現代詩歌從交互式影響關系到尖銳對立的重要轉折時期。雖然兩國的現代詩均是在西方詩歌的刺激和啟發(fā)下產生發(fā)展而來,并且日本曾一度扮演著中國知識分子了解西方的“文化橋梁”,但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接受逐漸擺脫了日本的路徑依賴,特別是對20世紀20年代盛行于歐洲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接受,中日兩國幾乎同步。然而,中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導致兩國現代詩歌的發(fā)展產生創(chuàng)作意識上的激烈對抗以及發(fā)展路徑上的大相徑庭。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下,大部分日本詩人投入到“侵華詩”的創(chuàng)作,日本詩壇涌現出大量鼓吹戰(zhàn)爭、美化侵略的“現代詩”,使詩歌淪為軍國主義國家意志的宣傳工具,從而使現代詩藝的探索遭到凍結,導致藝術退行。而我國的現代主義詩人在民族危難中將現代主義詩歌藝術與民族的苦難現實相結合,通過詩的創(chuàng)造實現了中國人現代性的精神探索,將現代漢語詩歌藝術的發(fā)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侵略”與“反抗”并非這一時期兩國詩歌關系的唯一底色,日本反戰(zhàn)詩人與中國詩人的交流為中日詩歌在和平與發(fā)展時期的平等對話埋下了火種。本文將聚焦1930年代,特別是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日兩國的現代詩歌寫作狀況,通過詩歌作品的文本分析,深入探索這一歷史時期中日現代詩的互動關系,并在論述方式上側重于對我國現代詩壇而言仍缺乏了解的日本現代詩歌的闡述。
一、1930年代上半葉中日現代詩歌發(fā)展概況
1930年代上半葉的中日現代詩歌發(fā)展狀況具有以下兩點共性:第一,現代詩壇流派林立,現代主義詩歌蓬勃發(fā)展;第二,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接受已從共時性接受向歷時性接收轉變,并與世界文學潮流發(fā)展同步。
我國新詩從誕生到發(fā)展初期受到了日本文壇的顯著影響。以梁啟超、黃遵憲、魯迅以及郭沫若、郁達夫、田漢、馮乃超、穆木天等創(chuàng)造社成員為代表的留日文人群體對我國新詩的誕生與發(fā)展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貢獻。倪正芳以拜倫在中國的傳播為例,將日本對中國詩人的影響方式概括為“日本橋梁之四維”,指出日本不僅為我國知識分子提供了開展文學活動的平臺,也為我國文人接觸西方文學資源以及直接利用日本已有的文學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①倪正芳:《拜倫與中國》,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第27-32頁。。與此同時,日本文學思潮的流變同樣影響了我國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接受,兩者具有顯著的同調性,對此王向遠在《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1998年)已有詳細論述,本文不再贅言。然而,20世紀20年代末期以降,留日詩人群體的主要詩歌活動已經較少看到來自日本的直接影響。例如“創(chuàng)造社”成員穆木天與蒲風、楊騷等人于1932年創(chuàng)辦中國詩歌會,而穆木天本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已摒棄了在日本受到熏染的象征主義詩風,轉向現實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與此同時,我國現代派詩歌于1930年代興起。以戴望舒的《我的記憶》《望舒草》《望舒詩草》為代表的現代派詩集相繼刊行,《無軌列車》《新文藝》《現代》等戴望舒參與主編的詩刊,與創(chuàng)刊于全國各地的現代詩刊,構成了我國蔚為大觀的現代主義詩歌運動圖譜。“在20年代末至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以戴望舒為領袖的現代派詩潮,蔚為氣候,風靡一時,‘新詩人多屬此派,而為一時之風尚’,成為30年代詩壇上與提倡寫實主義與大眾化的中國詩歌會代表的‘新詩歌派’,提倡新格律詩的后期新月派鼎足相峙的三大詩派之一,與它們一起,構成了新詩短暫‘中落’后的‘復興期’”②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頁。。
20世紀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日本現代詩壇呈現出現代主義詩派與普羅詩派分庭抗禮的局面。從根岸正吉、伊藤公敬合著的“勞動詩集”《歌于最底層》(1920年)、詩刊《播種人》(1921年創(chuàng)刊)、《文藝戰(zhàn)線》(1924年創(chuàng)刊)到該刊同人于1925年結成日本普羅文藝聯盟,普羅詩派逐漸發(fā)展為日本現代詩壇的重要一極。另一方面,1920年代后期《詩與詩論》《MAVO》《薔薇·魔術·學說》等現代派詩刊相繼創(chuàng)辦,呼應了西歐超現實主義、新達達、主知主義等藝術潮流。1928年,春山行夫創(chuàng)刊的《詩與詩論》匯聚了安西冬衛(wèi)、飯島正、上田敏雄、北川冬彥、近藤東、竹中郁、外山卯三郎、三好達治、瀧口修造、西肋順三郎、堀辰雄等詩人,成為日本現代主義詩歌的主陣地。春山行夫提出要確立以歐美開展的新詩運動、新詩精神為現代詩歌導向,打破既往日本詩壇“無詩學”的狀況,明確區(qū)分“近代”與“現代”。
中日兩國現代派詩刊的大量涌現以及詩派林立的狀況說明,截至20世紀30年代兩國的現代詩歌發(fā)展均已步入與世界詩潮同步的階段。日本學者坪井秀人指出日本“1920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刷新了此前后發(fā)于西歐,并從模仿它而發(fā)軔的日本近代詩的歷史,以與世界(這里的‘世界’限定指‘西歐’)之詩并駕齊驅(synchronize)而傲然于世”①坪井秀人「日中戦爭と詩」、『現代詩大事典』三省堂2008頁、516頁。。吳曉東指出“在現代中國文學幾十年的歷史進程中,象征主義的傳播構成了一條持續(xù)而貫穿的線索……在傳播方式上,對象征主義的介紹是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結合。在第一階段(1919-1927)以共時性傾向為主,各種象征主義傾向和象征派作家?guī)缀跬瑫r涌入中國文壇,在第二(1928-1937)和第三階段(1938-1949),則在共時基礎上又體現為歷時性特征,表現為與西方后期象征主義進行中的歷史過程的一種同步關系”②吳曉東:《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頁。。由此可見,從1920年代末期開始,中日兩國詩歌均已展現出從對西方文學的共時性接受向與世界文學同期發(fā)展的歷時性共振轉變的趨勢。特別是對興起于西方的現代主義詩潮,兩國詩壇均對此進行了自覺吸收。以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在中日兩國的傳播為例,第一位將艾略特介紹到中國的是于1924年至1926年間留學劍橋大學的葉公超;而首先將艾略特譯介至日本的是于1922年至1925年間留學于牛津大學的西肋順三郎。兩者均在英國留學期間閱讀《荒原》而深受觸動進而將其介紹至各自文壇。
由于兩國現代主義詩歌發(fā)展的世界同步性,我國在外國文學接受上已不再依賴于“日本橋梁”。“創(chuàng)造社”成員等留日群體的文學活動重心于1930年代也從日本轉移至國內,中國文人通過日本接受西方文學思潮的現象已不再顯見。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在中國,現代派、“新詩歌派”、后期新月派三足鼎立;在日本,普羅詩派與現代主義詩派分庭抗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日現代詩的發(fā)展均發(fā)生了重要轉折并體現出截然相反的命運軌跡。
二、現代主義詩藝在中國的拓展與在日本的停滯
1937年以降,隨著中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日本“侵華文學”與中國“抗戰(zhàn)文學”尖銳對立。與日本“國家主義文學同盟”(1932年)、“文藝懇話會”(1934年)、“日本文學報國會”(1942年)等日本國粹主義文學團體相抗衡的是我國“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1931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等抗日文藝組織。1937年,日本國內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成立所謂“筆部隊”,眾多日本作家、詩人被派遣至中國考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fā)起旨趣》明確表述:“我們應該把分散的各個戰(zhàn)友的力量,團結起來,象前線將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fā)動民眾,捍衛(wèi)祖國,粉碎寇敵,爭取勝利。”文學刊物方面,與日本《我思》③《我思》刊名的日文表記為“コギト”(Kogito),來自于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四季》《日本浪曼派》④《日本浪曼派》創(chuàng)刊于1935年3月,終刊于1938年3月,以保田與重郎為首,以近代批判和古代贊歌為主要內容,提倡“向日本傳統(tǒng)回歸”。須要注意的是,該刊刊名中的“浪曼”一詞不同于一般漢字表記的“浪漫”。等國粹主義刊物相對立的是《抗戰(zhàn)文藝》《詩創(chuàng)造》《中國新詩》等以抗日和民族救亡為宗旨的文學刊物。在創(chuàng)作意識上,兩國詩人也呈現鮮明對立之勢。以穆木天(1900-1971年)與日本詩人三好達治(1900-1964年)為例,二者曾先后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前者于1926年,后者于1928年),并于同一學校同一專業(yè)同一時期接受了西方象征主義文學的熏陶。自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穆木天的創(chuàng)作扎根于中國被壓迫的社會現實,強調“現時代的詩歌,是民族解放斗爭的呼聲,并不是幾個少數的人待在斗室中的吞云吐霧的玄學的悲哀的抒情詩”⑤穆木天:《關于抗戰(zhàn)詩歌運動》,《文藝陣地》1939年第3期;轉引自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年1999版,第238頁。,并通過詩歌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進行了批判。而三好達治則于戰(zhàn)爭時期拋棄了習得的西方文學精神,轉向國粹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對日軍的侵略行徑進行了美化和宣傳,在1942至1945年間刊行所謂“戰(zhàn)爭翼贊三部曲”。
此外,與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在抗戰(zhàn)時期迎來了藝術拓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現代主義詩歌藝術遭遇停滯乃至退行。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詩人們開始積極探索現代詩藝與抗日救亡的社會現實相結合的詩歌創(chuàng)作道路,他們“一面撇開了藝術至上的觀念,撇開了人生的哲學的說教,撇開了日常苦惱的傾訴,撇開了對于靜止的自然的幸福的凝視;一面就非常迅速地……把自己投進了新的生活的洪流里去,以人群的悲苦為悲苦,以人群歡樂為歡樂。是自己的詩的藝術,為受難的不屈的人民而服役,使自己堅決地朝向為這時代所期望的,所愛戴的,所稱譽的目標而努力著,創(chuàng)造著。卞之琳、何其芳、曹葆華,都寫了好多詩,這三位詩人,最顯著地受到抗戰(zhàn)的影響,他們都同樣地為自己找到了他們新的棲息的枝椏”①艾青:《抗戰(zhàn)以來的的中國新詩——〈樸素的歌〉序》,《文藝陣地》1946年第6期;轉引自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頁。。然而,戰(zhàn)爭時期的日本現代詩壇,現代主義詩刊卻紛紛凋敝,詩人們或放棄詩歌創(chuàng)作,保持沉默,或龜縮到藝術至上主義的園囿,或轉向國粹主義。坪井秀人指出“基于個人主義進行高度知性表象的日本現代主義詩歌方法論在戰(zhàn)爭詩的時代經歷了不可修復的斷絕”②坪井秀人「日中戦爭と詩」、『現代詩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516頁。,“太平洋戰(zhàn)爭對詩的決定性意義在于,它凍結了盛行于20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主知主義的詩歌意識與視覺主義的語言實驗,取而代之的是向國體共同性的同化……”③坪井秀人「大東亜戦爭と詩」、『現代詩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394頁。軍國主義日本對外不斷侵略擴張,對內施行嚴苛的言論管制,以及現代詩人們集體失語,放棄反抗乃至轉向,導致日本現代詩淪為國家意志的宣傳工具,現代詩藝的探索喪失了必要的社會條件和文化環(huán)境。
三、以“侵華”為主題的日本現代詩
侵華戰(zhàn)爭時期日本現代詩的主要特點有三:第一,在國家政策導引下,大量時局詩、戰(zhàn)爭詩進入量產階段,成為該時期日本現代詩歌淪為政治工具的表征;第二,《我思》《四季》等國粹主義詩刊取代現代主義、普羅詩派的地位,成為詩壇主流;第三,詩人的創(chuàng)作意識從現代主義轉向國粹主義。
(一)侵華詩的量產
日本文學史中并不存在“侵華詩”這一說法,而是將侵華戰(zhàn)爭時期以侵略中國為題材,對日軍侵略行徑進行鼓吹和美化的詩歌作品統(tǒng)稱為“戰(zhàn)爭詩”,在指稱上淡化了這類作品的本質屬性。在國策的引導和鼓勵下,侵華詩無論從創(chuàng)作群體,還是從創(chuàng)作數量上,都達到了較大規(guī)模。
明治一代的老詩人首先為響應時局而發(fā)聲。1932年1月,日軍策動“上海事變”,3月明治詩壇的“明星”詩人與謝野鐵干(1873-1935年)當即發(fā)表《爆彈三勇士之歌》。同年8月,土井晚翠(1871-1952年)刊行詩集《向亞細亞叫喊》,收錄大量戰(zhàn)爭應援詩。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近衛(wèi)內閣于同年10月發(fā)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并于翌年制定“國民總動員法”,祭出“八纮一宇”“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等欺瞞式口號試圖將侵略戰(zhàn)爭合理化。“七七事變”之后半年內,日軍的戰(zhàn)火從華北五省蔓延至上海,并于1937年12月發(fā)動了慘絕人寰、震驚國際社會的南京大屠殺。這一時期,高村光太郎(1883-1956年)、中勘助(1885-1963年)、佐藤春夫(1892-1964年)等為代表的詩人群體有力地應援了日軍的侵略擴張。
高村光太郎于“七七事變”后的第二個月即發(fā)表詩作《秋風辭》④收錄于詩集《偉大之日》(『大いなる日』1942年)。。高村首先引用了漢武帝所作《秋風辭》起首兩句“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作為副標題,接下來寫道:“秋風起兮白云飛/今年向南急行的是吾同胞之隊伍/等待在南方的是炮火/街上百般之生活皆搓捻成一/毋寧以淚洗胸/哀嘆昨日思索之亡羊者/苦于日日食不果腹之面色青白者/街巷中只能做著浮浪之夢者/如今只化作澎湃著熱氣之死。/草木黃落時/吹遍世間每個角落的夜風雖未變/但造訪今年這個國度的秋天/是祖先們也不曾見過的龐大之秋/遙遠他方的雁門關,古生代地層迸裂紛飛/過去雁門關向西而閉/今天雁門關面東而碎/越過太原,涉過汾河,望向黃河/秋風一連吹過了胡沙、海洋和座座島嶼。”詩人將日軍1937年的侵略行徑比作無堅不摧、無往不至的“秋風”,借用了中國古典詩詞的意象美化了日軍侵華的不義之舉。由“秋風”一句引領的八行詩便以一個文化上位者的姿態(tài)歌頌了一路收割著中國百姓生命的日軍暴行;由“草木”引領的后八句詩結合時局,預言了日軍定能突破雁門關,拿下山西,侵吞華北,無往而不利的強勁走勢。然而事實卻是在該詩發(fā)表后不到一個月內,由賀龍指揮的八路軍切斷了日軍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補給線,取得了“雁門關大捷”,這無疑是對高村等日本“愛國詩人”莫大的諷刺和有力的回擊。
繼高村之后,中勘助刊行的詩集《大戰(zhàn)之詩》(1938年)、《攻陷百城》(1939年)中不僅收錄了歌頌日軍“戰(zhàn)果”迅速擴大的《山西》,而且收錄了將南京大屠殺的慘絕人寰置若罔聞的《南京》。佐藤春夫曾以“中國通”自居,并參與過魯迅作品的翻譯推介,曾與田漢、郁達夫①郁達夫于1938年5月14日的《抗戰(zhàn)文藝》上發(fā)表《日本的娼婦與文士》一文,對佐藤春夫在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際的轉向表達了諷刺和憤慨。等有過密切交往,然而在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其當即發(fā)表《立于盧溝橋畔而歌》對“暴支應援”“圣戰(zhàn)”美化頌揚。高村光太郎、中勘助、佐藤春夫等詩人代表了日本詩壇中堅力量對日軍侵華的應援,以上詩作均是日本“現代詩中實質性的戰(zhàn)爭詩的最初代表”②鈴木亨「第八講 第二次大戦下の詩と精神」、『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275頁。。此后,高村光太郎于1940年至1942年歷任日本大政翼贊會文化部中央協力會議議員、日本文學者會設立委員以及日本文學報國會創(chuàng)立總會的詩部會長,成為中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國民詩人”的領軍人物。
由山本和夫編輯、山雅房出版的《野戰(zhàn)詩集》(1941年)系詩壇邊緣的日本年輕詩人創(chuàng)作的代表。詩集收錄了加藤愛夫、西村皎三、長島三芳、佐川英三、風木云太郎、山本和夫6位“支那事變從軍詩人”的作品。詩集的目錄“再現”了他們跟隨部隊深入中國腹地的侵略步伐,如加藤愛夫的《大場鎮(zhèn)》《在嘉定》《蘇州》《渡揚子江》《南京入城》《黃河》《渡大運河》《在即將攻陷的徐州附近》《徐州入城》《徐州》《在安慶》《瀘州》《赴漢口之路》《漢口初夜》《黃鶴樓》,長島三芳的《廬山》《鄱陽湖》,佐川英三的《北京之眼》,風木云太郎《廣東入城之日》等。這使該詩集已然成為日軍侵華的歷史注腳。
從明治老詩人們的先聲附和,到大正詩人們的有力聲援,再到青年詩人們的高聲吶喊,從詩壇巨擘到邊緣詩人皆執(zhí)詩筆參與到“愛國詩”的大合唱。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青年詩人聯盟(2月)、大日本詩人協會(6月)、全日本女流詩人協會(7月)、詩人協議委員會(8月)紛紛成立。侵華詩的量產成為日本現代詩歌軍國主義工具化的表征。
(二)以《我思》《四季》為主流的日本詩壇
1930年代以來,在日本當局打壓下,日本普羅詩派的發(fā)展日益衰落。1933年2月,普羅文學旗手小林多喜二被日本特高警察虐殺,給普羅文學敲響了喪鐘。在詩壇白色恐怖日益深重的大趨勢面前,一向游離于社會現實之外的現代主義詩人體現出缺乏抗爭意識的軟弱性。村野四郎指出“國家權力與弱小的現代主義者的意圖相比,是無與倫比的強大的。現代主義詩人們……的悲觀主義甚至連游擊隊一般的抵抗威力都沒有”③村野四郎「第一講 昭和という時代」、『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13頁。。與現代派詩人的軟弱形成鮮明對照的四季派詩人強有力的發(fā)聲,吉本隆明指出“昭和十年以降,提起詩就立即意味著‘四季’派的抒情詩。這一派的詩已經超越了單純一個現代詩流派的問題,它甚至對整個詩概念的整合都產生了巨大的規(guī)約力”①吉本隆明「『四季』派の本質——三好達治を中心に」『詩學敘説』、思潮社2006年、221頁。。《四季》的創(chuàng)刊分兩期,第一期(1933.5-1934.10)為堀辰雄主編的季刊,共出2冊;第二期改為月刊,由三好達治、丸山薰等共同編輯,從1934年10月至1944年6月,共出81冊。《我思》創(chuàng)刊1932年3月,停刊于1944年9月,通卷146號。兩刊取代了現代派、普羅詩派地位,持續(xù)時間幾乎貫穿了日本“十五年戰(zhàn)爭”始末,成為詩壇主流。
《四季》集結了日本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主要的現代詩人,包括三好達治、萩原朔太郎、田中克己、中原中也、伊東靜雄、保田與重郎等。其中,堀辰雄、三好達治、丸山薰從《詩與詩論》群派分化出來,意圖糾正現代主義詩歌運動,主張將日本的傳統(tǒng)抒情方式與現代詩相結合,創(chuàng)出主知的典雅的抒情詩。《我思》同人包括保田與重郎、田中克己、中原中也、草野心平、萩原朔太郎、高村光太郎、立原道造等。該刊深受德國浪漫派詩人施萊格爾、荷爾德林的影響,主張高揚浪漫主義旗幟并彰顯日本古典美學精神。1938年11月第78號刊的《我思》裱紙內頁赫然印刷著大字“漢口占領,皇軍大勝”。在《我思》基礎上,以保田與重郎為中心,神保光太郎、龜井勝一郎、中島榮次郎等聯名創(chuàng)刊國粹主義文學雜志《日本浪曼派》(1935年3月至1938年8月,共出29冊)。從主要的編輯者、撰稿者可見,“四季”派同人三好達治、堀辰雄等一方面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接軌,一方面以神保光太郎、保田與重郎、田中克己等為中介,與《我思》和《日本浪曼派》等國粹主義文學一脈相通。
(三)從現代主義到國粹主義的創(chuàng)作轉向
日本現代主義詩藝探索的停滯與乃至退行,一方面與日本國內言論統(tǒng)制下現代主義詩刊紛紛廢刊,詩人失去詩歌活動陣地有關,一方面與詩人創(chuàng)作意識的國粹主義轉向密切關聯。以下以高村光太郎、三好達治和田中克己的創(chuàng)作為例,論述侵華戰(zhàn)爭時期日本現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特點。
1.高村光太郎:向日本漢詩傳統(tǒng)復歸
高村光太郎曾留學歐美,傾心羅丹,譯過惠特曼和維爾哈倫,在戰(zhàn)爭時期卻放棄了從歐美文學中汲取的謳歌生命與自由的精神,轉而投向國粹主義的懷抱。高村曾于1906年至1908年間留學美、英、法等國期間,由于人種差異而倍受歧視,這種屈辱感在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以一種“反西方”的泛亞主義的方式表現于詩歌當中,體現出與軍國主義的強烈共鳴。大岡信在《現代詩鑒賞講座》(角川書店1969年)中指出“曾于《在雨中歌唱的巴黎圣母院》這樣的詩篇中熱烈稱頌過歐洲精神的高村,刺痛其內心深處的‘黃色人種’的劣等感,現在以一種強烈的道義的自我主張形式被補償,在成為其精神內部之‘叫喊’的詩歌中結晶”。以《秋風辭》為代表,高村光太郎摒棄了現代性的創(chuàng)作意識,轉而向明治文明開化以前日本漢詩文傳統(tǒng)復歸。
“詩”這一文類概念在日本經歷了從漢詩系向西詩系轉移的過程。在西方詩歌傳來之前,“詩”在日本即指漢詩,是對中國古典詩歌“仿制鏡”“國姓爺”②関良一「第一講 伝統(tǒng)詩歌と近代詩」、『講座日本現代詩史1』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3-4頁。式地移植。1882年,在被視為日本現代詩嚆矢的《新體詩抄》中,編撰者井上哲次郎首次提出“夫明治之歌應為明治之歌,而非古歌,日本之詩應為日本之詩,而非漢詩,此乃作新體之詩之所以然也”③井上哲次郎:《玉之緒之歌·小引》;轉引自陳璇《中日現代詩歌寫作比較研究——19世紀末現代詩始發(fā)點對“新體”的想象》,《寫作》2018年第5期。。日本漢詩在西方文明大量襲來之時不可抵擋地衰退,至20世紀初,“詩”最終成為指稱起源于西方poetry的“新體詩”的專有名詞。而1914年高村光太郎的詩集《道程》的問世,恰恰標志著日本現代詩在形式上擺脫了七五定形律的束縛,確立了口語自由詩的發(fā)展道路,并實現了明治、大正以來,具有現代意識的日本詩人通過積極地接受和轉化西方文學來擺脫漢詩傳統(tǒng)的影響,樹立“現代日本詩歌典范”的努力成果。然而,在《秋風辭》中,高村通過對漢詩漢典的攝取與模仿獲得詩意生成機制,從日本現代詩的發(fā)展角度來看,這無異于創(chuàng)作意識的倒退,體現出高村向日本文化傳統(tǒng)中對漢文化“宿命式”的復歸,于是此處形成一種吊詭現象——用來補償其“黃色人種”劣等感的“道義的自我主張”的恰恰是其蔑視和侵略國度的古典詩歌,這到底是一種文化的自信還是不自信?而借漢詩美化侵華日軍“圣戰(zhàn)”的行徑本身也說明了日本戰(zhàn)爭詩的自我欺瞞性。
2.三好達治:向日本傳統(tǒng)感性復歸
三好達治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之后,相繼翻譯了波德萊爾、梅里美、弗朗西斯·雅姆等大量法國詩人詩作。其作品亦深受這些法國詩人的影響。其第一本詩集《測量船》(1930年)將日本傳統(tǒng)的抒情性與西歐象征詩的批判性融合一體,開拓了新的抒情趣味,三好借此確立了詩壇地位。然而自《故山迎英靈》(1938年9月)一詩發(fā)表以來,三好的創(chuàng)作逐漸向戰(zhàn)爭詩轉移。此后《草千里》(1939 年)、“戰(zhàn)爭翼贊詩集三部曲”即《捷報至》(1942 年)、《寒柝》(1943 年)、《干戈永言》(1945 年)的相繼刊行,標志著三好成為侵華戰(zhàn)爭時期日本文壇“最有力的國民詩人”。從初期的《測量船》到后期的“翼贊詩集三部曲”,詩人的創(chuàng)作意識發(fā)生了重大轉變——西方現代文學影響日益淡薄,傳統(tǒng)詩歌形式與語言的運用大幅增加,抒情方式上也從個性化的情感表達轉向忠實于大眾宣傳的“萬能”的意象表現。《昨夜落于香港》即為三好此類詩歌的代表作。“昨夜落于香港/主基督降誕祭日黃昏/那維多利亞峰的山寨上/翩翩然他們的白旗招展!/百年來,他們是東亞海域/倒買倒賣的海賊/是魔藥鴉片的押賣行商/巧取豪奪了香港——//那香港島上/東海猛鷲紛飛交織/巨彈雨下/重炮炸裂/凈化萬物的兇猛火焰焚盡了連日來的病灶/此刻在那奸惡與詭詐與驕慢的一個世紀的荒蠻無理之后/……啊終于將那曾經東亞之天地最大的悖德與最大的屈辱/拂拭而去了”。該詩收錄于1942年刊行的《捷報至》,創(chuàng)作背景為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軍侵占。詩人將日軍的戰(zhàn)機轟炸形容為“東海猛鷲的紛飛交織”,“凈化萬物”的烈火焚燒,而香港則是其筆下的“最大的悖德與最大的屈辱”。
吉本隆明指出三好詩中 “這種情緒的殘忍感覺是三好將原始神道進行論理的開掘所帶來的傳統(tǒng)感性的一個頂點”,而這種“傳統(tǒng)感性”的本質與原始人的自然觀無異,即“從日常生活的需求出發(fā),將漁獵或屠殺其他部族天然地作為一種手段,殺戮、巨大鐵量的沖突、思想的對立,這一切不過是進入他們自然認識范疇的某個部分”“他們無法區(qū)分對社會的認識和對自然的認識。權力社會也被納入他們的自然觀范疇,于是權力社會與權力社會的國際性抗爭,撼動的也僅僅是他們的傳統(tǒng)感性”①吉本隆明「『四季』派の本質——三好達治を中心に」『詩學敘説』、思潮社2006年、234-237頁。。吉本認為三好等四季派詩人所體現出的殘忍感性與原始人的野蠻無異,因此將此類戰(zhàn)爭詩的創(chuàng)作稱之為“返祖”退行。而三好、高村等詩人之所以會拋棄曾經習得的西歐文學精神,向國粹主義轉變,源于在他們的觀念意識里,“西歐的現代意識與日本的傳統(tǒng)意識基本無矛盾、無對立、無瓜葛地以原始形態(tài)并存”。當戰(zhàn)爭爆發(fā),必須做出取舍時,他們的“西歐教養(yǎng)便如塵芥般消弭得無影無蹤,之后如同庶民的大多數所遵循地那樣,完美地返祖退化而去了”②吉本隆明「『四季』派の本質——三好達治を中心に」『詩學敘説』、思潮社2006年、231頁。。而這正是現代性與封建性(反現代性)并存的日本社會體制導致的必然結果。詩人創(chuàng)作意識的集體退行導致了現代性藝術探索的停滯,因此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對其本身的現代詩歌藝術而言亦是沉重的打擊。
3.田中克己:浪漫主義與國粹主義相抱合的詭異秘境
《我思》同人田中克己畢業(yè)于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詩集西康省》(1938年)和《大陸遠望》(1940年)中收錄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文獻與傳聞。在《大陸遠望》序言中,田中言及“大陸”(中國)之于其創(chuàng)作的意義:“這數年間,帶給我作詩刺激的是大陸。作詩時,我總遠望著它,并始終將它置于我的意識里,因此這數年應該是我人生中詩寫得最多的浪漫時代。”然而,田中所謂的“大陸意識”依然是將“中國”置于軍國主義的侵略意識下,將日本恒常民眾的殘忍感覺與優(yōu)美典雅的審美意識相并置,創(chuàng)造了一種“藝術至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抱合的詭異秘境”①鈴木亨「第八講 第二次大戦下の詩と精神」、『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278頁。。
田中在《皇紀二千六百年》(收錄于《大陸遠望》)中這樣寫道:“當第一縷陽光/……/將富士山頂染成了鮮紅之時/近衛(wèi)步兵第一連隊吹響了起床號/我家兒子睜開了眼睛/西方尚在沉睡 在睡夢中/每個人都做著深深期待之夢/于是在北京、濟南、太原、開封、安慶、南京、杭州、南昌、武昌、廣東、南京這十一座省城當中/不眠的哨兵等候著清晨……”在后記中,詩人講到這首詩初發(fā)表時將皇軍占領的城池只寫了九個,“不好意思非常抱歉弄錯了,但也因此為皇軍占領的無以計數的中國城市再一次感到歡欣。”在《大陸遠望》一詩中詩人以問答的形式寫道:“‘你為何一直望著那個方向/那片海的彼岸有著粗蠢的容貌/有著五千年的詭詐與流血的歷史/黃色之民組建村落建設都市/在那里日日是爭吵的喧囂與愚蠢的奔忙/除此之外,你還眺望著什么’/……”。這里田中克己展現了與德國納粹分子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如出一轍的人種優(yōu)越論。
通過上述考察,我們看到侵華戰(zhàn)爭時期的日本現代詩在軍國主義統(tǒng)治時期,普羅詩派遭遇毀滅性打擊,現代主義詩歌的藝術方法遭遇“凍結”,以侵略為主題的詩歌創(chuàng)作成為主流。造成這一狀況的因素,除了社會時局的影響外,離不開詩人主觀上的藝術選擇。高村光太郎、三好達治、田中克己等詩人主動放棄了現代性的詩藝探索,轉而向日本舊詩文傳統(tǒng)復歸,以傳統(tǒng)感性迎合時局號召,使詩歌淪為軍國主義國家意志的宣傳工具。
四、1930年代的中日詩歌交流
對抗并非戰(zhàn)爭時期中日現代詩關系史的唯一底色。中國詩人與日本反戰(zhàn)詩人小熊秀雄、金子光晴在戰(zhàn)時的文學交流意義深遠;另一方面,從世界性的現代主義詩潮傳播角度看,燕卜蓀、奧登等西方詩人在中日兩國展開的文學活動又將中日現代詩歌發(fā)展納入到了世界現代主義文學運動范疇。
(一)反戰(zhàn)詩人小熊秀雄、金子光晴與中國詩人的交流
小熊秀雄(1901-1940年)出身于日本北海道,其詩歌創(chuàng)作從前衛(wèi)詩運動出發(fā),后積極投身普羅詩運動。1935年刊行詩集《小熊秀雄詩集》《飛橇》。其第三部詩集《流民詩集》(1947)本應于1939年出版,但受時局影響卻未能如期刊行。1940年因長年貧病交加,小熊死于肺結核,享年39歲。在《飛橇》《長長秋夜》等長篇敘事詩中,詩人借饒舌與幽默的表現手法進行了尖銳的社會諷刺和深刻的人間洞察,其視野不僅僅局限在日本,還擴展至中國、俄羅斯、朝鮮乃至北海道原住民阿依努族人等,不失抵抗精神的同時無損詩歌語言的清新。小熊作品所展現的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同樣感染了中國詩人雷石榆和蒲風。雷石榆在留日期間曾于詩刊《詩精神》發(fā)表詩文,并于1934年11月該詩刊同人的《一九三四年詩集》出版紀念會上與小熊有過直接會面,現存有二者的詩文往來稿件30余通。蒲風曾于1934年冬赴日留學。1936年4月,蒲風訪問了當時正在流亡中的郭沫若,并詢問其是否讀過小熊的《飛橇》②蒲風:《郭沫若詩作談》,《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4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第237頁。。秋吉久紀夫認為蒲風的詩集《黑陋的角落里》(廣州詩歌出版社1938年)幽默諷刺的創(chuàng)作風格鮮明地受到了小熊的影響①秋吉久紀夫「小熊秀雄と二人の中國人留學生」、『中國現代詩人論』、土曜美術社、2013年、142-163頁。。
“正好這個時候,郁達夫帶著郭沫若秘密地來到了我家,于是就請他為書的封面題寫了鮫這個大字。送去印刷的時候,發(fā)生了盧溝橋事件,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詩人》)詩人金子光晴(1895-1975年)回憶詩集《鮫》(人民社1937年)出版前夕郁達夫為其題寫封面,反映出在中日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之際,懷有正義感的日本詩人與中國詩人們的精神契合與密切聯系。詩集《鮫》收錄了金子游歷歐洲、東南亞,包括中國的上海和香港等地之后創(chuàng)作的詩篇。其中大量作品諷刺了昭和初期日本政府彈壓的社會現實,凸顯了金子的“反骨”。日本戰(zhàn)后詩人田村隆一曾感言“太平洋戰(zhàn)爭之下,僅有金子光晴一人續(xù)寫著真正配得上‘戰(zhàn)爭詩’之名的詩”②田村隆一「地獄の発見」『田村隆一全集6』、河出書房新社2011年、463頁。。對于中國而言,金子光晴不僅與中國詩人郁達夫、郭沫若有過極具象征意義的交際,并且是在中日戰(zhàn)爭期間,走過中國的戰(zhàn)場之后直言不諱地說出“日本是侵略者,是強盜,是人類文明的倒行逆施者的唯一的日本詩人”③鈴木亨「第八講 第二次大戦下の詩と精神」『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283頁。。

(二)威廉·燕卜蓀與W.H.奧登在日本和中國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后期象征主義詩潮興起,作為國際性的文學運動,其影響范圍涉及中國和日本。20世紀30年代,在社會危機與戰(zhàn)爭恐怖的時局下,威廉·燕卜蓀與奧登等歐洲詩人在日本和中國展開的詩歌教學與文學交流活動,更加深了中日兩國在世界性后期象征主義詩潮傳播下的內在關聯。
燕卜蓀于1931至1934年間曾先后任教于東京文理科大學、東京大學。在日本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氛圍中,燕卜蓀工作了三年。1937年至1939年與1946年至1951年,燕卜蓀曾兩度來華工作,以第一次影響最為深刻。在王佐良《一個中國新詩人》《穆旦:由來與歸宿》、趙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袁可嘉《詩人穆旦的位置》、周玨良《穆旦的詩與譯詩》等文章均對燕卜蓀任教西南聯大的情景進行了追憶。可以說,燕卜蓀在日本和中國的教學活動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在日本和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
奧登與依修伍德于1938年1月19日至6月12日期間訪華,此后奧登創(chuàng)作了1930年代 “最偉大的英語詩篇”④Edward Mendelson,Early Auden,London:Faber &Faber,1981,p.384.十四行組詩《在戰(zhàn)時》。隨著奧登的親身來訪以及燕卜蓀的介紹,中國掀起了“奧登熱”。穆旦、杜運燮、袁可嘉等中國新詩詩人群體深受奧登詩歌的影響,最終推動了中國現代詩向前發(fā)展。日本左翼詩刊《新領土》(1937年5月創(chuàng)刊,1941年5月終刊,共出48冊),刊名便來自于奧登的文學陣地New Country。日本學者中井晨指出《新領土》正是通過廣泛譯介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與當時占據文壇主流的國粹主義傾向的刊物相對抗,“為了克服‘國家主義’,通曉‘國際主義的文學、文化基準以及動向’才成為必要”⑤中井晨『荒野へ―鮎川信夫と『新領土』(1)』、春風社2007年、10-11頁。。在戰(zhàn)時言論統(tǒng)制日益嚴苛的情勢下,《新領土》仍然譯介了奧登的《西班牙》(1939年7月號)、《1939年9月1日》(1940年1月號)等名篇,并刊載了多篇斯彭特的奧登論。因此,在抗戰(zhàn)時期被中日詩壇譯介的奧登,將具有反侵略和國際主義意識的中日現代主義詩人聯結在了一起。
五、結語
20世紀30年代是中日現代詩歌關系發(fā)生轉折的重要時期。以此為節(jié)點,中日很多現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意識和審美觀念都發(fā)生了巨大轉變。截然不同的是,中國現代詩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收獲了大量優(yōu)秀的藝術成果,孫玉石將這一時期稱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拓展期(1937-1949)”①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頁。;而日本則經歷了現代詩歌藝術探索史上的“暗黑時代”②村野四郎「第一講 昭和という時代」『講座日本現代詩史3昭和前期』村野四郎、関良一、長谷川泉、原子朗編、右文書院1973年、12頁。。然而,小熊秀雄、金子光晴等詩人在戰(zhàn)爭時期的反抗為和平時期中日現代詩歌的交流留下了火種;世界性現代主義詩潮的歷時性接收又使中日現代詩共同加入到“世界文學的精神循環(huán)”。這一歷史時期的詩歌狀況決定了兩國詩歌未來的發(fā)展走向。因此,戰(zhàn)爭時期的中日現代詩歌比較研究是和平時期兩國現代詩展開對話與交流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