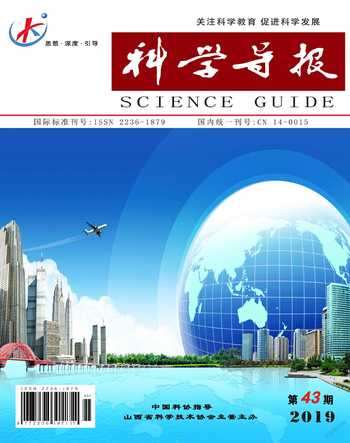傳統文化有助于國際文化交流
摘??要:人們往往是憑借已知來認識未知事物的,將未知的新事物與已知的事物加以比較,往往就能很快地把握新事物的特點。傳統文化與所引進外來文化,并非是對立的關系,兩者是可以并存的,而原有的文化,恰恰又有助于認識外來文化的性質特點。
關鍵詞:傳統文化;現代化;文化交流
多年來,一直有這樣的看法,即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性質不同,兩種文化是有差異乃至是有矛盾的,因此,傳統文化被看做是了解和引進西方文化的障礙。這種看法其實是似是而非的。文化有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三個層面,唯有制度文化特別是根本性的制度,常常相互排斥的,即是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采取某一種根本制度即不能同時采取另一種根本制度,而物質文化的引進多是對原有文化的補充與豐富。精神文化則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補充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論。也就是說,傳統文化與所引進外來文化,并非是對立的關系,兩者是可以并存的,而原有的文化,恰恰又有助于認識外來文化的性質特點,人們往往是憑借已知來認識未知事物的,將未知的新事物與已知的事物加以比較,往往就能很快地把握新事物的特點。這是引進事物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例如,中國本土原沒有西紅柿和馬鈴薯,引進之后,把西紅柿叫“番茄”,叫“西紅柿”,這是把這種新的蔬菜或水果與已有的“茄子”或“柿子”加以比較,而把握了這種新蔬菜或水果的特點。把馬鈴薯叫“洋芋”,“山藥蛋”,也是分別將之與已有的“芋頭”或“山藥”相比較,而把握了這一新事物的特點。物質文化的引進是這樣,精神文化的引進也是這樣。一個中事先有中國哲學方面的知識,他們在接觸西方哲學之時,就會有意無意第將西方哲學與自己已經了解的中國哲學相比較,因而能夠很快地認識西方哲學,把握西方哲學的特點。曾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就這樣講:“對于歐美的東西,我總喜歡用中國的尺度來衡量。這就是從已知到未知的辦法。根據過去的經驗,利用過去的經驗獲得新經驗也就是獲得新知識的正途。譬如說,如果一個小孩從來沒有見過飛機,我們可以解釋給他聽,飛機像一只飛鳥,也像一只長著翅膀的船,他就會了解飛機是怎么回事。如果一個小孩根本沒有見過鳥或船,使他了解飛機可就不容易了。一個中國學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據他對本國文化的了解。他對本國文化的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據這種推理,我覺得自己在國內求學時,常常為讀經史子集而深夜不眠,這種苦功總算沒有白費,我現在之所以能夠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這些苦功的結果。”1蔣夢麟說得很清楚:閱讀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是了解掌握和真正西方文化典籍的一個前提條件。蔣夢麟這里所說的是自己的經歷,也可以看做是對許多學人學習經驗的概括。上個世紀前期,學界出現了不少學貫中西的大師。陳寅恪、趙元任、錢鐘書、朱光潛、季羨林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些學者的成長道路,幾乎都是幼年即接受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有著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陳寅恪兒時啟蒙于家塾,學習四書五經,后家中開辦思益學堂,先后延聘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等國學名師執教。錢鍾書和陳寅恪一樣出身學問世家,其父親錢基博是著名學者,錢鐘書是從讀《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十八家詩鈔》?等開始系統學習。趙元任兒時即跟小姐姐們讀古詩,他回憶說:“我頂記得他們念的吳偉業的《圓圓曲》,我連字都沒有看見已經背下來了。還有白居易的《長恨歌》,他們比我們先念,趕到我起頭兒念到《長恨歌》的時候都已經聽得半熟了。”朱光潛6歲開始在家讀《書經》、《左傳》。《詩經》沒正式地讀,但“家塾里有人常在讀,我聽了多遍,就能成誦大半。”他們都是因為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接觸西方文化時能夠有條件將中西文化加以比較,在比較中迅速掌握了兩種文化各自的特點,由此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師。對于這些大師來說學,所謂“學貫中西”,并非只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簡單的相加,而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而對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了解西方文化的過程反過來又有助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也就是說,經過兩種文化的相互比較,對兩種文化各自的特點都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梁宗岱就講孔子的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與古希臘赫拉克里特的名言加以比較,說道:“大家都知道,那相信宇宙流動的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多士關于河流也有一句差不多同樣的警辟的話:‘我們不能在同一的河入浴兩次’。不過,他這話是要用河流底榜樣來說明他底宇宙觀的,是辯證的,間接的,所以無論怎樣警辟,終歸是散文;孔子底話卻同時直接抓住了特殊現象和普遍原理底本體。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動,所以便覺得詩意蔥蘢了。‘川流’原是一個具體的現象,用它來形容它底特性的‘逝者’二字表出來,于是一切流逝的、動的事物都被包括在內,它底涵義便擴大了,普遍化了;‘永久’原是一個抽象的觀念,用‘不舍’一個富有表現力的動詞和‘晝’、‘夜’兩個意象鮮明的名詞襯托出來,那滔滔不息的景象便很親切地活現在眼前了。”2這樣一比較,雙方的特點就都凸顯出來了。
還應補充說,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也是這樣。也就是說,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的民族,更容易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華。如東歐洲亞的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在吸收歐洲現代文化方面就很迅速很有成就。他們對自己傳統文化的保護并沒有阻礙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與此相反,非洲的一些國家,自己民族文化根底不夠深厚,同樣是面對西方文化,所能吸收的卻很有限,自身的發展也比較緩慢。與美國著名文化學者亨廷頓曾將韓國與非洲的加納加以比較,說道:“20世紀90年代初,我碰巧瀏覽了加納和韓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經濟統計數據,驚訝地發現兩國當時的經濟水平何其相似:它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致相等。在經濟構成方面,初級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所占比例彼此相近;絕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級產品,韓國當時僅生產為數不多的若干工業制成品。它們接受的經濟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韓國成了一個工業巨人,經濟名列世界第14位……加納卻沒有發生這樣的變化,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近相當于韓國的1/14。發展快慢相差如此懸殊,能作和解釋呢?無疑,這當中有多重因素,然而在我看來,文化應是一重要原因。”3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參考文獻
[1]??蔣夢麟:《西潮與新潮——蔣夢麟回憶錄》,第94頁,東方出版社,2006年
[2]??梁宗岱:“說‘逝者如斯夫’”,見《梁宗岱批評文集》,第117、118頁,李振聲編,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3]??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第7頁,新華出版社,2010年
作者簡介:唐曉敏,1952年5月,黑龍江省綏化市,漢族,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文化、語文教育、古代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