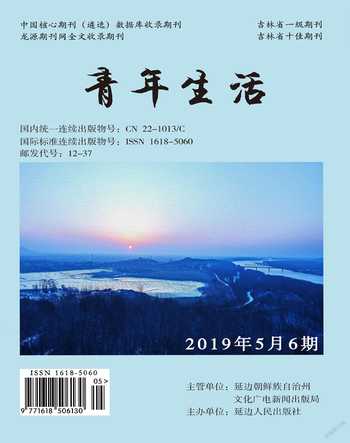試論“表演理論”民間敘事文化場域的存在
胡建雄
動的口頭性建立了套以表演為中心的民間故事研究視角。顯然,從表演理論出發將民間敘事視為藝術性的言語活動,則必然有著言語活動的“場域”。本文認為,表演理論下民間敘事實際存在潛在的文化場域向度。而文化場域則在交流層面上構成了敘事存在的傳承權威,敘事與理解的有效性等潛在成因
關鍵詞:民間敘事;表演;場域;歷史文化
理查德·鮑曼及“表演理論”學派視民間文學的本質形態是口頭藝術,并借此反對普拉普故事原型以文本中心的研究方法,反對民間敘事及其文類是“文化遺留物”。“被我們習慣性地視為口頭傳統素材的文本,僅僅只是對深度情境的(deeply?situated)人類行為單薄的、部分的記錄而已。”表演理論把民間敘事納入到具有特定情境的交流性活動表演中,將口頭藝術這一具有社會交流性質的活動取代文本,成為民間敘事的豐富而完整的記錄體。
在表演理論中,民間敘事的表演和文本的地位置換,民間敘事的文本依附于表演言說方式的總體框架,其素材生成、故事闡釋及其審美意義的實現在表演的過程中進行并且文本本身也是表演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地位的置換,文本的集體記憶和個體言說的創作性權重同樣易位。在此,民間敘事的記錄體“口頭藝術”仍然離不開內在的文化性問題。
一、場域中的民間敘事
表演理論將民間敘事視作基于口頭敘事之上的言說交流活動——表演,言說交流顯然將受到演繹場合,特殊情境,社區慣例等限定,這些限定影響著民間敘事能否在言說中被闡釋和被理解。根據表演理論,民間敘事只有在諸如故事敘述,戲劇,評書,宗教吟誦乃至具有藝術性的言說式活動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實現,而既存文本作為民間敘事的部分記錄僅為言說提供抽象化,晉遍化和輪廓化的摹本。言說活動的實施成為民聞敘事存在和敘事有效性的中心,這個是語境和文本相互依賴的過程,并與飽含了場所、社區種群和文化慣例的特殊情境息息相關。因此基于同一民間敘事文本的表演由于情境化的語境參與使得言說受到社會慣例的限制,并使敘事內容在實際具體的,具有特定情景的表演中發生新生和更替。
筆者認為,從表演本身來看,其演繹空間,社區,及表演時的特定情境,隱含著實現民間敘事演繹和傳播的有形場域范疇;而從表演的內容來看,表演者講述的事件(經表演者演繹的文本)和被講述的事件(能夠被文本記錄的事件)之間的差異性和互文性,又涉及到民間敘事實現過程中即時表演和歷史文本,新生內容和文化質料之間的關系,即是否能交流歷史文化場域范疇。
二、語境——文化場域的存在
表演理論重視民間敘事在不同文化場域的語境展演。用理査德·鮑曼的話說:在一個社區的交流性的傳統語料庫當中,表演往往存在于那些被最為有意識地傳統化的形式當中,也就是說它們被理解和建構為一個通過互文關系連接起來的更大的重復序列的一部分。盡管表演理論重視表演民間敘事具體、特殊情形處理的新生性,但仍有隱性的社區語料庫和傳統化的形式。
從文本層面上,表演在文化集群中劃分出的空間中進行。文化場域對表演的物理場域形成包裹,并通過象征物的觀念集群在不同文化場域的差異將表演進行社區化的切分。因此,文本在多樣化的文化場域中存在異文現象。文化場域引起的異文不同于表演者與觀眾在交流過程中的新生性異文,它包括口頭言語活動,還包括被文本記錄的核心母題。《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一書中記錄了文本在跨社區的轉寫和更改現象:
啊母親現在已在移動
啊母親現在已在移動
如今黎明誕生
啊母親現在已在移動。
該經跨區域轉回改為
母親從沉睡中醒來
她醒來了,因為夜晚早已過去
黎明的跡象早已呈現
東方誕生了新的生命
由兩則文本可見,原始文化場域中文本原有的換氣、停頓和句法結構在跨社區轉寫的過程中改寫為新文本的結構,而從敘事意義上,其內在的文化意象和觀念派生出“夜晚”、“東方”和“生命”等新生的隱喻概念,敘事已經脫離了原始意義。
三、有效——在文化共通中理解
表演被標定為藝術性的言說活動,用之與其他言說活動相區別,這種標定借助模式化的手段而具體可行,但實際上,表演理論所使用的標定手段牽涉若個文化場域內的語言范式和觀念集群。理查德·鮑曼將標定手段歸類為:特殊的符碼、比喻性的語言、平行關系、特殊的輔助語言特征、特殊的套語、對表演的否定六種手段,這六種手段存在于言語共同體中,并受其限制。文化建構了表演中慣用的模式和語義概念,理查德·鮑曼論述的特殊的符碼、套語及輔助語言特征也與社區慣用的語言形式并行捆綁,不同社區的語言慣例使得同一套語言形式并不具備超文化場域的普適性。而比喻性的語言和句法的平行關系更是社區內集體象征物的符引七,比喻性語言和平行關系具有的觀念集群使得民間敘事無法直接超地域進行傳播和正確解讀。
標定手段確定了表演形式的通則,但其并無法擺脫其內在的文化模塊,標定手段中由下無形的文化場域存在,使得表演的標定定框架同樣具有社區文化的隔膜。也就是說,文化場域阻拒并限定著一次藝術性的言說活動多大范圍內能夠被認定為是表演。這便要求民間敘事脫離抽象故事原型的研究藩籬,回到民間敘事實踐的文化場域中,對其特定的語言形式和符號化的象征物給予同等的重視。
與文化標定相對應的是表演是否“在此框架內發生的交流能夠在該社區中被理解”民間敘事的實現是在有效性的判定基礎之上,即表演者和觀眾的交流能夠在社區內能夠形成相互理解。理查德·鮑曼認為理解的前提是表演者和觀眾之間存在著“傳統語料庫”和“傳統化的形式”,使得雙方能夠進行交流。文化作為一種與可見實物相對的概念化場域,通過社區語義系統、句法和修飾習慣、節日和儀式、故事素材等文化觀念集群滲透到表演者的表達中,構成了表演者在表演時相對固定使用的口頭表達傳統。而觀眾則在文化觀念的沉積中具有相應的理解能力,能夠在表演者使用的諸如特殊的隱喻中找到社區通用意象的對應物。總結而言,在表演理論看來,當表演者和觀眾居于同一或者通用相似的文化場域,才能夠實現交流的有效。
四、權威——與史協商的傳統
回到表演者敘事自身,文化場域以歷史的權威姿態存在于口頭表演中。盡管自表演理論誕生以來,有學者對表演理論過分重視個體敘事與當下語境而提出批評,但實質上忽視了表演理論內部對傳統的妥協。以表演為中心的民間敘事承認傳統的存在。在表演看來,新生性內容與文化場域的內在傳統并非對立的兩端,而是顯與隱的關系。不論是口述詩人還是故事的講述者,其敘事內容有著文化場域內既有傳統提供的藍本。文化場域作為歷史的沉積物,構成了諸如詩歌固定使用的意象般的凝練語義群,闡釋框架及基本故事素材(如原始傳說和逸聞軼事),并在表演者的口頭敘事中得到反復使用。
與此同時,歷史形成民間敘事真與偽的鑒定尺度。敘事能否在交流中令觀眾覺得真實可信,可以借助求諸傳統使敘事內容向歷史趨攏得到實現。如故事講述者在表演開始時使用結構性的話語:“這個故事是從我父親那里聽來的”、“下面要講的這些是曾經真實發生過的事。”在這里,社區內過去發生的事被史料化而獲得客觀性印證,表演者的敘事內容借助求諸傳統而轉變為歷史的再現。盡管這種歷史化顯然是表演者的展演手段,但歷史作為表演對象的沉積已久的文化觀念具有不可懷疑的權威,歷史化的話語對敘事內容進行粉飾,其本身的虛構成分已經悄然隱退,獲得真實性地位。在眾多表演的案例中,觀眾往往根據過去的表演對現下表演進行衡量,可以說表演者趨近傳統也使得自己的表演內容取得經典地位,上升為一個文化場域內新的歷史性范本。
傳統存在于表演的范疇中,并與表演者的個人創造達成協商。社會慣例、即成事實作為文化和歷史的代表名詞,與表演者的個人創造是協商的兩種聲音。協商形成民間敘事的兩個層面:一方面是傳承的敘事,現下表演是對過去表演的模仿,在內容上與后者形成互文,并試圖在歷史話語和文化集群的運用中對其進行追溯。另一方面則是獨特的敘事,正如前文所言,表演者和觀眾的交流是即時的、隨意的,這個編織內容的過程無法進行復制,并且表演者本身負有的藝術性責任也驅使看表演者于利用文化沉積質料之外,生成其自身敘事的標志性內容。
五、結語
將“場域”概念引入到研究民間敘事的表演理論中,可以發現表演本身具有限定“場域”適用性,即物理場域和歷史文化場域形成具體表演的時空限定;再者,表演作為一種場域內的行動,其物理場域及言說行動元限定和編織民間敘事內容,由此能夠探討民間敘事在交流中復雜多變的傳播狀況,而表演與不同場域之間存在著場景與文類的對應關系。此外,在本文看來,將歷史文化場域作為民間敘事的潛在因素,語言系統影響著社區內民間敘事的交流的有效性,構成了民間敘事中慣常使用的表達方式,而觀念集群和社會慣例在民間敘事中的反復使用是民間敘事的口頭傳承形態,新生表演與傳統表演之間的互文現象由傳統與新生的協商產生。
參考文獻:
理查德·鮑曼.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M].楊利慧,安德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103
[1]周福巖.民間故事研究的方法論[J].社會科學輯刊,2001(3)
[2]理查德·鮑曼.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M].楊利慧,安德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79
[3]楊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鮑曼及其表演理論——美國民俗學者系列訪談之一[J].民俗研究,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