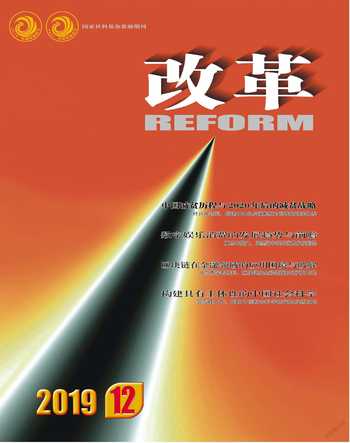新中國 70 年扶貧開發基本歷程、經驗啟示與取向選擇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扶貧開發從“救濟式扶貧”“體制改革推動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從“區域性扶貧”到瞄準貧困縣、“整村推進”,再到“精準扶貧”,實現了從溫飽到小康的跨越。我國逐步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不僅為我國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而且為其他國家扶貧開發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借鑒。2020年后我國扶貧重點應該從解決貧困群體的“兩不愁三保障”等基本問題轉向滿足他們更高層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從主要關注農村貧困轉移到統籌城鄉減貧一體化上來,由“扶貧”向“防貧”轉變,不斷加強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效銜接,對貧困群體實施分類精準救助,解決好部分群眾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
關鍵詞:扶貧開發;精準扶貧;脫貧攻堅
中圖分類號:F323.8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7543(2019)12-0076-11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堅韌不拔、團結奮斗,用70年的時間,成功地打了一場消除絕對貧困的攻堅戰,為全球扶貧開發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作為重大民生工程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我國扎實有力有序有效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譜寫了人類扶貧開發史上的壯麗篇章。這里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扶貧開發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剖析我國扶貧開發的時代特征、發展階段,總結扶貧開發的經驗成就,并結合目前脫貧攻堅中存在的問題和挑戰,對2020年后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難點進行研判。
一、新中國70年扶貧開發歷程回顧
新中國成立后,充分發揮制度優勢,以大規模的專項扶貧為抓手,減少農村貧困人口,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路徑[1]。總體來看,我國扶貧開發歷程可分為六個階段。
(一)保障生存救濟式階段:遍地開花,以“救急”為主(1949—1978年)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人均國民收入僅為27美元,是亞洲人均國民收入的2/3[2],農民生活普遍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為改變這一狀況,我國積極恢復國民經濟,通過土地改革和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加快農民脫貧;通過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和普及了高級合作社,徹底切斷了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產生的經濟根源,避免了更多的農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貧困。這一階段采取的具體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灌溉設施和交通條件。二是建立全國性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體系,截至1978年,我國建立了由近6萬個鄉鎮、縣級以上營業機構和35萬個生產隊信用站組成的農村金融服務網。1952—1978年,農村信用社累計為農民提供農業貸款1373.5億元[3]。三是建立從中央到鄉鎮的農業技術推廣網絡。四是改善農村基礎教育,形成了生產大隊辦小學、公社辦中學、“區委會”辦高中的農村教育格局,通過政府和集體共同分擔,農村基礎教育快速發展。1949—1978年,學齡兒童平均入學率由20%上升到95.5%[4]。五是農村基礎醫療衛生事業快速發展,形成了以集體經濟為基礎、個人相結合的農村醫療合作體制。1976年,公社有衛生院的占90%以上,辦合作醫療的生產大隊占93%,大批的“赤腳醫生”有效防控了農村的瘧疾和寄生蟲病等疾病的傳播,農民體質大大增強[5]。六是對孤寡老人、殘疾人和孤兒,由集體實行“五保供養制度”,即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老人)或保教(孤兒),有效地抑制了輕度災害和一定范圍的貧困程度的加深。但是,在工作中也出現了急于求成、忽視客觀規律的問題,加之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科學認識,我國農村反貧困事業總體進展較為緩慢。
受客觀條件、主觀認識等方面的制約,這一階段我國沒有開展大規模有指向性的更高層次的扶貧,主要是保障貧困人口生存需求的小規模救濟式扶貧。相關措施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時期的貧困狀況,但使我國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和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為后來的農村改革發展和扶貧工作開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6]。1978年我國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國家貧困線設為100元,估計的貧困人口規模為2.5億人,貧困發生率為30.7%[7]。
(二)農村體制改革推動扶貧階段:間接瞄準,局部扶持(1978—1985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當時黨和國家的頭等大事。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扶貧事業進入了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驅動扶貧的嶄新歷史階段。
針對農村生存性貧困,國家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替代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以及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實行統分結合,農民獲得了對農業剩余的索取權,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奠定了我國農村扶貧的制度基礎。針對農村收入性貧困,國家大幅度提高糧棉等主要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允許除國家控制的糧棉油之外的農副產品在城鄉之間進行貿易往來,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性收入。針對農村發展性貧困,國家不斷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管理制度,準許農村居民以自籌資金、自理口糧方式向城鎮和非農就業轉移,支持社隊(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農民非農收入不斷增加,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設立“支援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資金”、“三西”①農業建設專項補助資金,1984年國家投入專項資金實施“以工代賑”扶貧計劃。與此同時,國家在全國“老、少、邊、窮”地區劃定了18個貧困地帶進行區域重點扶貧。
1978年以來,農村經濟體制的結構性變革所帶來的巨大體制改革紅利,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加上專項扶貧資金的設立,使得農村貧困狀況大大緩解,由1978年的2.5億人下降到1985年的1.25億人,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1985年的14.8%[8]。這一時期,確定貧困戶的主要依據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和房不避風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適應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扶貧更多地靠外力驅動,缺乏內生動力且未建立直接的目標瞄準機制,兼具局部性、間接性和救濟式特征。隨著國家扶貧開發進程的不斷深入,政府扶貧開發重點逐漸轉向激發貧困地區的經濟內生動力,以彌補救濟式扶貧存在的缺陷。
(三)有組織的開發式扶貧階段:區域瞄準,明確到縣(1986—1993年)
隨著改革不斷深入,我國的扶貧理念也發生了變化,逐步由救濟式扶貧轉向開發式扶貧,確立了區域扶貧和開發式扶貧的基本方針。1986年5月16日,國家成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1993年12月28日改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1988年7月國務院決定將其與“三西”地區農業建設領導小組合并。
這一時期,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18個貧困地區,主要為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以及特困地區,即所謂的“老、少、邊、窮”地區。為提高扶貧工作成效,讓貧困人口更有效地獲得扶貧資源,我國將貧困人口占比較高的縣作為專項扶貧計劃的基本瞄準單位(又稱國定貧困縣)。1986—1993年,共有331個縣被確定為國定貧困縣。同時,各省份根據中央政府要求按照一定的收入標準來確定各省份的重點貧困縣,到1988年,全國共有370個縣被確定為省級貧困縣。中央政府安排專項扶貧資金(主要包括專項扶貧貸款、以工代賑和財政發展資金)對確立的331個國定貧困縣進行扶持。1986—1993年,中央政府累計提供扶貧資金467.2億元,其中專項貸款249億元,以工代賑資金89億元,財政發展資金129.2億元①。
這一時期,我國扶貧開發成效明顯,但因城市改革對農村整體經濟帶來了沖擊,農村經濟增速減緩,扶貧開發難度增大,減貧速度有所減緩[9]。到1993年底,農村貧困人口下降到800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4.8%下降到8.7%。
(四)集中解決溫飽的“八七”扶貧攻堅階段:縣域瞄準,多元共治(1994—2000年)
1994年,國家開始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明確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七年左右的時間,到2000年底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按照“四進七出”②的調整原則,對過去確定的331個國定貧困縣進行了首次調整,經過調整,國定貧困縣數量變為592個,涵蓋了全國72.6%的農村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荒漠、高寒山區等地。這一時期中央把省一級作為考核單位,明確權利、責任、資金、任務“四個到省”原則,中央專項扶貧資金、“東西協作”扶貧資金、“以工代賑”資金、“三西”專項建設資金、國際發展援助資金以及各種捐款等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中央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1242億元,平均每年投入177.4億元[7]。將加強對口扶貧與部門扶貧相結合,穩步推進社會扶貧,推動東西協作扶貧機制,定點幫扶主體范圍不斷擴大。中國政府重視少數民族、殘疾人以及婦女等特殊人群的貧困問題,對少數民族給予特殊優惠照顧政策,安排專項資金開展殘疾人扶貧,鼓勵婦女參加學文化、學技能,比成績、比貢獻的“雙學雙比”活動,實施“幸福工程”“母親水窖工程”等活動。1995年,政府又投入中央專項資金在568個國定貧困縣、284個省定貧困縣實施“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
這一階段,“雙基”③目標基本實現,鄉鎮醫院、農機推廣等在貧困地區大量出現,這使得貧困地區科教文衛事業有了極大發展。到2000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從1993年的8000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3209萬人,貧困發生率也由1993年的8.8%下降到2000年的3.5%④。這一階段開展了以貧困縣為重點的開發式扶貧治理[10]。總體來看,政府仍是扶貧工作的主角,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參與度不高,政府沒有擺脫輸血救濟式的扶貧理念,貧困人口參與度不高,貧困人口自身造血能力缺乏。
(五)鞏固溫飽成果的綜合扶貧開發階段:村域瞄準,整村推進(2001—2012年)
為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鞏固脫貧成果,2001年6月我國發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為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2011年12月我國發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明確了“兩不愁三保障”的扶貧新任務。
我國在21個省份確定了592個縣(旗、市)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覆蓋全國61.9%的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為瞄準貧困人口,將扶貧開發的具體措施落實到貧困鄉村,國務院扶貧辦指導地方各級政府在全國共確定了14.8萬個重點村,覆蓋了全國總貧困人口的近80%①。2011年,我國全面推進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確定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作為扶貧攻堅的主戰場(包括680個縣),動態調整38個貧困縣,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名單總數仍為592個,這與14個連片特困地區重合440個縣,扣除重合部分后,共計832個貧困縣。2004—2012年,每年中央“一號文件”均聚焦“三農”問題,通過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相關政策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實行整村推進、連片開發,完善雨露計劃,通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貧困農戶基本的生存權利,進一步動員社會各界參與扶貧開發,繼續加強東西扶貧協作,堅持并不斷完善定點扶貧,探索國有企業、部隊、重點高校、科研院所參與扶貧開發的多種有效方式,有效減緩了貧困現象。
我國貧困線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進行調整,貧困人口也隨之發生變化。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絕大多數農村人口處于絕對貧困狀態。1977年前,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熱量攝取量大都小于2100大卡,1978年的貧困線為100元,貧困人口為2.5億人。2008年以前國家設定了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1985年以206元作為絕對貧困標準,隨著物價消費等因素進行動態調整;2000年國家制定了865元的低收入標準,2007年底這一標準又調整為1067元。2008年,國家把絕對貧困標準和低收入標準合二為一。受價格和消費變動影響,2009年國家扶貧標準調整為1196元,2010年又調整為1274元。2011年,中央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按照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進行計算,2010—2012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6 567萬人減少至9899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7.2%下降到10.2%。
(六)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階段:精準到戶,不落一人(2013年至今)
隨著扶貧開發事業的推進,傳統粗放型的區域開發扶貧方式導致貧困人口底數不清、情況不明,項目安排“大水漫灌”,資金使用“撒胡椒面”,幫扶工作“走馬觀花”,貧困縣不愿“摘帽”等問題逐漸凸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放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提升到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高度,審時度勢地提出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吹響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進軍號。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省湘西十八洞村調研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思想,他強調:“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在此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就精準扶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觀點,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任務,全面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明確指出精準扶貧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是“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即“六個精準”;提出“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的“五個一批”實現路徑;解決“四個問題”: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我國建立起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扶貧工作機制,實行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共抓扶貧,層層壓緊壓實主體責任,做到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扶貧工作取得決定性進展。按照現行農村貧困標準,2013—2018年我國農村減貧人數分別為1650萬人、1232萬人、1442萬人、1240萬人、1289萬人、1386萬人,每年減貧人數均保持在1000萬人以上。6年來,農村已累計減貧8239萬人,年均減貧1373萬人,6年累計減貧幅度達到83.2%。截至2018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至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2020年,我國的絕對貧困問題有望得到歷史性解決①。
二、新中國70年扶貧開發的主要成就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扶貧開發事業取得重大成就,主要表現在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對全球減貧的貢獻和貧困地區居民經濟生活改善等方面。
(一)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
我國扶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新中國成立初的全國普遍性貧困,到1978年的全國農民30%絕對貧困,再到2018年的以2010年貧困基準線,累計減貧7.5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了95.8個百分點。由于缺乏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數據,因而全面說明1949—1977年的貧困人口狀況是很困難的,這里從每日營養攝入量角度來反映當時的貧困狀況。表1反映了1954—1978年農民每日營養素攝入量。1957—1977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熱量攝取量都小于2100大卡[5],說明這段時間農民平均營養水平未達到維持人體最低營養需要的標準;農民的食物消費水平在20年中提高幅度較小,以營養標準來衡量,改革開放以前至少有40%~50%的人群處于生存貧困狀態[11]。改革開放以來,在針對性扶貧開發政策的支持下,我國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實施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使每年減貧人數均保持在1000萬以上。
(二)中國減貧加速了世界減貧進程,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全國范圍內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專項扶貧開發,貧困人口大幅減少,為全球減貧貢獻了中國力量。具體表現在:一是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1981年全球貧困人口由19.97億人減少到2013年的7.67億人,累計減少12.3億人,貧困發生率從1981年的42.39%下降到2013年的10.9%;同期中國貧困人口從8.78億人減少到2511萬人,累計減少8.53億人,貧困發生率從88.3%下降至1.9%。我國減貧人口占全球減貧總規模的69.35%,減貧速度明顯快于全球,貧困發生率顯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見表2,下頁)。二是中國實施的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參與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開發式扶貧,特別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的實施,從內容、措施、理念等方面為全球減貧提供了中國范本,貢獻了中國智慧。三是中國在自身減貧的同時還積極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減貧。
(三)貧困地區貧困居民經濟生活改善明顯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貧困地區居民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支出快速增長,與全國農村平均水平差距不斷縮小。1952年農村家庭居民人均收入為49.35元,2018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0 371元。201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4 617元,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全國農村平均收入水平的71.0%,差距不斷縮小②。1952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水平為54元,2018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8956元,名義水平是1952年的165.85倍,年均名義增長8.05%。201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2 124元,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相當于全國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的73.9%①。二是貧困地區居民家庭耐用消費品從無到有,進行了升級換代。2018年貧困地區農村每百戶擁有電冰箱、洗衣機、彩色電視機等傳統耐用消費品分別為87.1臺、86.9臺和106.6臺,每百戶擁有汽車、計算機等現代耐用消費品分別為19.9輛、17.1臺②。三是貧困地區農村住房條件、飲水安全情況不斷改善。從住房條件看,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土坯房較為普遍;1978年,我國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僅為8.1平方米;1979—1987年,全國共新建房屋62.57億平方米,比1957年農村擁有的房屋總數多出1.3億平方米;1990年平均每人年末住房面積17.83平方米[12];2017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戶均住房面積139.5平方米,居住房屋的材質有58.1%為鋼筋混凝土或磚混結構。從飲水安全看,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農村飲水主要以人拉肩挑為主;后來國家大力實施農村安全飲水工程,2017年貧困地區89.2%的貧困農戶飲用水沒有困難,通管道農戶為70.1%③。
三、新中國70年扶貧開發的經驗啟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不僅為我國農村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而且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扶貧開發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1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保障了扶貧開發規劃和政策的實施,而扶貧開發的實施則體現了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新中國成立70年來,扶貧開發取得的偉大成就根本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一直致力于領導全國人民擺脫貧困的面貌,實現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執政為民,急貧困群眾之所急,想貧困群眾之所想,在扶貧事業中總攬全局、協調四方,調動各方資源合力推動扶貧工作,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投入扶貧開發事業[14],這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政治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運行的高效率使得國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我國堅持黨對扶貧開發事業的全面領導,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成立了跨部門的扶貧開發領導機構,建立起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扶貧工作機制,實行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共抓扶貧,層層壓緊壓實主體責任,做到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牢記初心與使命,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不斷出臺有利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發展的政策,針對不同人群組織實施扶貧規劃,堅持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相結合,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
(二)不斷完善市場機制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
市場是最有活力的,運用好市場機制,不僅能夠拓寬扶貧開發資源,破解片面依靠行政手段的弊端,而且可以有效提高扶貧的效率和精準度。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不斷完善國民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從“基礎性”轉變為“決定性”。貧困地區多數為市場發育程度低、資源利用效率低、開放水平低的地區,我國在扶貧開發中引入市場機制,利用內外兩種資源,推動貧困地區市場經濟發展,由市場決定貧困地區適合發展什么、怎么發展,做到因時因地制宜,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集中扶貧資源到最需要的貧困地區,形成扶貧資源優勢、力量優勢,從而快速實現預期脫貧目標。
(三)經濟發展的“涓滴效應”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我國扶貧成就的取得主要依靠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通過綜合發展實現減貧[15]。70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為679億元,2018年達到900 309億元。按不變價計算,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1952年增長175倍,年均增長8.1%;1952年,我國人均GDP僅有119元①,而2018年人均GDP達到64 644元,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0 371元②,絕大多數群眾脫離了貧困,生活水平總體上達到小康。我國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大力實施“兩減免、三補貼”等政策,保障了農民權益,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增加了農民收入,大幅度減少了貧困人口。
(四)堅持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參與的大扶貧開發格局
扶貧開發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新中國成立70年來,扶貧開發事業堅持政府主導,并逐步引導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多元主體參與扶貧開發事業的積極性不斷高漲,構建了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全國范圍內整合配置扶貧資源,形成扶貧開發合力。設置了跨政府部門的政府減貧機構,廣泛宣傳,鼓勵并高效引導市場、社會資源向貧困地區匯集;廣泛動員,制定優惠政策措施,改變“政府熱、社會弱、市場冷”的狀況,形成“人人皆愿為,人人皆可為,人人皆能為”的扶貧理念,構建了全社會共同關注、支持、參與扶貧工作的良好格局。
(五)堅持救濟式扶貧與開發式扶貧相結合,扶貧開發和社會保障有機銜接
在70年的扶貧開發實踐中,我國逐漸形成了救濟式扶貧與開發式扶貧相結合的扶貧模式,將扶貧開發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有機銜接起來。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是以解決貧困人口吃飯穿衣為基本要求的救濟式扶貧,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通過給予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支持,開發利用貧困地區的資源,幫助貧困人口提高自我發展能力,扶貧方式向開發式扶貧轉變。從1956年“五保供養”制度到2007年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我國農村扶貧工作堅持低保救助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兩輪驅動”。實施開發式扶貧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銜接,既能夠實現貧困地區經濟的良性循環,又有利于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16]。
四、2020年后我國扶貧工作的未來取向
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按照現行的農村貧困標準,農村貧困將在統計意義上消失,但相對貧困問題將長期存在。2020年后我國減貧事業將進入新時代,扶貧重點應該從解決貧困群體的“兩不愁三保障”等基本問題轉向滿足貧困群體更高層次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從主要關注農村貧困轉移到統籌城鄉減貧一體化上來,從政府主導幫扶向提高貧困人口可持續生計能力轉變,由“扶貧”向“防貧”轉變。未來反貧困的重點將從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的絕對貧困問題轉向表現在收入、公共服務的不平等,以及教育、醫療服務、養老等社會保障的低水平方面的相對貧困問題和多維貧困問題[17-20],這些新的變化迫切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和探討。
(一)構建相對多維貧困線,統籌城鄉減貧一體化
2020年后,我國致貧和返貧的原因會更加多元化。2020年后新貧困標準的制定是估算貧困人口規模、特征和分布的前提[21]。相對貧困階段,宜按照農村居民收入0.4~0.5的均值系數增設相對貧困線,作為衡量貧困的一把尺子[22]。中央政府可以根據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水平,建立貧困線制度,制定相對貧困標準,即一個包含收入、教育、醫療、住房、食物以及個人護理等多指標在內的多維貧困量度標準,地方政府可以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作適當調整。在相對貧困階段,要對不同程度的貧困進行嚴格的數量化定義,區分開“非貧”“近貧”“貧困”“赤貧”[23]。中央統籌貧困線與低保線有效銜接,細化申請評定內容,變兩套標準為一套標準;構建以市場化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的農村減貧和農民增收長效機制;集中救助職能,整合扶貧辦、民政部、衛計委、教育部等多個部門貧困救助內容,搭建統一的救助平臺,設置專門的扶貧開發綜合管理部門,探索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減貧和城市減貧并重、全面統籌的城鄉貧困治理體系。
(二)實施貧困群體分類精準救助
“留守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是扶貧工作的難點,健康和教育所體現的人力資本是影響收入水平的關鍵因素,對農戶脫貧具有顯著作用[24]。2017年,我國17歲及以下青少年兒童貧困發生率為3.93%,60歲以上老人貧困發生率為4.3%[25]。應構建減貧的綜合保障體系,滿足貧困人口包括物質、服務、護理、精神慰藉以及融入市場、社會參與的多方面、多層次的需要[26]。2020年后,貧困群體的致貧原因、貧困類型都會發生變化,要根據這些變化實施分類精準救助。對于兒童貧困問題,要關注義務教育,輟學保控,普及普通話,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要注重兒童早期的發展教育、兒童學前教育潛能開發,兒童早期(0~3歲、3~6歲)的營養干預[27];等等。對于老年人貧困,要探索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創新“互聯網+護理服務”模式,通過自治、法治、德治多措并舉,解決脫貧和養老問題。殘疾人和重癥病人則可以通過制度化的社會保障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大病保險等)來兜底,構建以家庭為本的殘疾人和重癥病人社會福利制度[28],依托和整合現有公共服務設施開展集中照護服務,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貧困重度殘疾人照護服務,積極創新健康扶貧模式。現今我國更多的是現金救助形式,以后對于特殊人群可以設計代金券的形式進行救助,如兒童的食物券,兒童、老年人與殘疾人的營養補助券等。
要關注新出現的農民工貧困問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運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估算出2004年中國農民工收入貧困發生率為5.2%,消費貧困發生率為52.3%[29]。蔣南平等根據CFPS數據測算出2014年中國農民工整體貧困發生率為6.8%,農民工貧困狀態處于波動之中,返貧是主要原因[30]。如果依據世界銀行每天消費3.1美元進行測算,中國農民工收入貧困發生率為2.07%,消費貧困發生率為12.3%[31]。農民工多維貧困主要受其教育維度的影響,為此,應加大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完善農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32],積極調整完善社會政策, 切實消除人文貧困[33]。
(三)加強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戰略的有效銜接
精準扶貧是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基礎,是首要任務;鄉村振興為精準扶貧提供長效內生動力,是深化和保障。從鄉村振興五大目標任務來看,應著力體制機制統籌落實、鼓勵產業多元發展、積極培育鄉村振興主體意識[34],做好政策銜接,定方案,重落實。產業興旺與產業扶貧高度契合,應積極探索小農產業發展,創新土地流轉方式,盤活貧困戶資產,增加其資產性收益;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便捷度,深入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實現生態宜居,提高貧困戶脫貧滿意度;培育貧困戶主體意識,通過鄉規民約培育貧困戶內生動力,緩解精神貧困,倡導文明鄉風,改變不文明的婚嫁陋習,抵制大操大辦和天價彩禮,警惕因婚致貧和因婚返貧現象;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規范貧困戶動態調整機制;加強農村“三產融合”,延長產業鏈,拓寬貧困戶增收渠道,努力實現貧困戶生活富裕與精神富足。對于貧困地區來說,脫貧攻堅為鄉村振興打牢基礎,屬微觀施策;鄉村振興是鞏固脫貧攻堅的良方,全方位考慮和解決貧困人口在脫貧后的各種需求,屬整體規劃。兩者相輔相成,能更好地促進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長效脫貧。
(四)關注非貧低收入戶和返貧戶,設立防貧返貧基金
對于生態脆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基層組織功能弱化、自然災害多發的貧困地區,貧困瞄準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關注貧困邊緣低收入戶與返貧戶,脫貧摘帽重在非貧困戶不致貧、脫貧戶不返貧。要積極發揮保險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創新保險品種,開發適合非貧低收入戶和返貧戶的防貧返貧保險;對脫貧戶設立返貧防貧保險基金,以國家現行農村扶貧標準為基礎,設置防貧監測線和防貧保障線,以保險形式來保證其生活和生產。例如邯鄲市把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國家現行農村扶貧標準的1.5倍為限,低于1.5倍的人納入防貧范圍,針對因病、因殘、因學、因災等致貧返貧設置防貧監測線和防貧保障線,以“大數據”為基礎,當納入檢測范圍的對象可能發生致貧返貧時,政府購買“第三方”服務,借助保險公司專業化手段,對可能的致貧返貧人群入戶勘察核算,對于超出救助標準的自付費用給予分段按比例實施救助,防貧效果顯著。除此之外,還要繼續完善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參與的大扶貧開發格局,引導市場、社會積極參與防貧返貧活動。
(五)解決好部分貧困群眾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
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是發揮個體的主體性和主動性[35],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是實現減貧可持續的重點。應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注重扶貧同扶德、扶志、扶智相結合[36],除此之外,還要“扶技”。通過“扶德”,開展感恩、自強、誠信主題教育,樹立典型示范,講好脫貧故事,教育引導貧困戶摒棄安貧守貧觀念,樹立自強不息、誠實守信、自強脫貧的思想觀念和感恩意識,把心思和行動用在產業發展、家庭增收致富上,積極依靠雙手和勤勞實現致富奔小康,使其“想脫貧”。通過“扶志”,增強貧困戶脫貧的信心和決心,引導貧困人口樹立“我要脫貧”的主體意識,建立貧困戶貧困等級標準,完善扶貧資源分配,使貧困戶貧困程度與資源分配成正比,破解貧困戶“不愿脫貧”“等靠要”的思維,使貧困戶自我認識到位,使其“要脫貧”。通過“扶智”,幫助和指導貧困群眾提升脫貧致富的綜合素質,提高貧困戶自我組織、自我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增強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使其“能脫貧”。通過“扶技”,積極開發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鼓勵其就業;將貧困戶技能培訓等情況與物質幫扶掛鉤,激勵貧困戶自主參加培訓,通過“合作社(企業)+”等產業幫扶模式,將貧困戶、市場、企業聯結成穩定的產銷關系,改變貧困戶心中不敢脫貧的包袱,使其“會脫貧”。
參考文獻
[1]汪三貴,殷浩棟,王瑜.中國扶貧開發的實踐、挑戰與政策展望[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18-25.
[2]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312.
[3]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00)[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49.
[4]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76.
[5]周彬彬.人民公社時期的貧困問題[J].經濟研究參考,1992(Z1):821-837.
[6]朱小玲,陳俊.建國以來我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歷史回顧與現實啟示[J].生產力研究,2012(5):30-32.
[7]張磊.中國扶貧開發歷程(1949—2005年)[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24.
[8]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農村扶貧概要[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2.
[9]張琦,馮丹萌.我國減貧實踐探索及其理論創新:1978—2016年[J].改革,2016(4):27-42.
[10]邢成舉,李小云.超越結構與行動: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經驗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32-47.
[11]汪三貴.在發展中戰勝貧困:對中國30年大規模減貧經驗的總結與評價[J].管理世界,2008(11):78-88.
[12]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中國農村50年[M].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1999:304.
[13]張琦,孔梅.“十四五”時期我國的減貧目標及戰略重點[J].改革,2019(11):117-125.
[14]汪三貴.中國40年大規模減貧:推動力量與制度基礎[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6):1-11.
[15]吳國寶.改革開放4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成就及經驗[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17-30.
[16]向德平,華汛子.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貧困治理的歷程、經驗與前瞻[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59-69.
[17]李小云,許漢澤.2020年后扶貧工作的若干思考[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1):62-66.
[18]何秀榮.改革40年的農村反貧困認識與后脫貧戰略前瞻[J].農村經濟,2018(11):1-8.
[19]汪三貴,曾小溪.后2020貧困問題初探[J].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7-13.
[20]CHEN K G, WU G B,HE X J, et al. From rural to rural urban integration in China: identifying new vision and key areas for post-2020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21]陳夢根.貧困購買力平價和地區貧困線:理論與測算[J].改革,2019(4):88-102.
[22]陳宗勝,沈揚揚,周云波.中國農村貧困狀況的絕對與相對變動——兼論相對貧困線的設定[J].管理世界,2013(1):67-75.
[23]白增博,孫慶剛,王芳.美國貧困救助政策對中國反貧困的啟示——兼論2020年后中國扶貧工作[J].世界農業,2017(12):105-111.
[24]程名望,JIN Y H,蓋慶恩,等.農村減貧:應該更關注教育還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長和差距縮小雙重視角的實證[J].經濟研究,2014(11):130-144.
[25]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8)[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11.
[26]左停,徐衛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反貧困的經驗與啟示[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92-99.
[27]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弗洛.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修訂版[M].景芳,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47-48.
[28]汪三貴,曾小溪.從區域扶貧開發到精準扶貧——改革開放40年中國扶貧政策的演進及脫貧攻堅的難點和對策[J].農業經濟問題,2018(8):40-50.
[29]Asian Development Bank. Urban povertyin Asia[R/OL].(2014-09-01)[2019-09-30].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59778/urban-poverty-asia.
[30]蔣南平,鄭萬軍.中國農民工多維返貧測度問題[J].中國農村經濟,2017(6):58-69.
[31]郭君平,譚清香,曲頌.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的測量與分析——基于“收入—消費—多維”視角[J].中國農村經濟,2018(9):94-109.
[32]白永秀,劉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我國城鄉反貧困的特點、難點與重點[J].改革,2019(5):29-37.
[33]葉普萬.農民工貧困的演變路徑與減貧戰略研究[J].學習與探索,2013(12):111-116.
[34]豆書龍,葉敬忠.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有機銜接及其機制構建[J].改革,2019(1):19-29.
[35]林閩鋼.激活貧困者內生動力:理論視角和政策選擇[J].社會保障評論,2019(1): 119-130.
[36]劉合光.精準扶貧與扶志、扶智的關聯[J].改革,2017(12):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