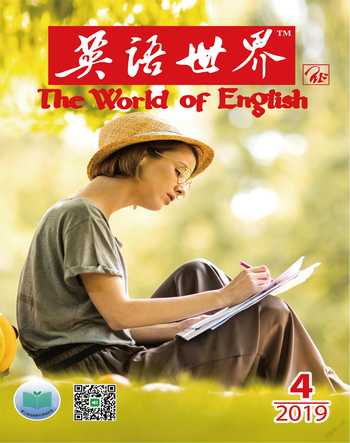從余光中的譯論譯品談文學翻譯的創作空間(三)
金圣華
余光中出身英文系,畢生以母語創作,歷經數十載而詩心如初,筆耕不輟,因此對中英雙語文化的差異、語法的不同,領悟最深,體會最切。他在幾篇重要的論文,如《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1979)、《中文的常態與變態》(1987)、《論的的不休》(1996)等文之中,對于拙劣的譯文體大肆筆伐,并對這種非驢非馬的譯文體荼毒現代中文的現象迎頭痛擊。余光中與另一位翻譯名家蔡思果惺惺相惜,兩人對于翻譯的認知亦相契相合。他們為彼此的翻譯論著寫序及寫讀后感。蔡思果為余光中的《翻譯乃大道》作序時提到:“余兄說的話無不中肯……他本人中西學都扎實,不是空頭文學家……他的英文修養很深,中文不用說,這種人才能翻譯。外文理解有問題,中文表達情意不高明,就不必翻譯了。”1余光中在為蔡思果的《翻譯研究》撰寫讀后感時,更強調說:“譯者追求‘精確’, 原意是要譯文更接近原文,可是不通順的譯文令人根本讀不下去,怎能接近原文呢?不‘通順’的‘精確’在文法和修辭上已經是一種病態。要用病態的譯文來表達常態的原文,是不可能的。理論上說來,好的譯文給譯文讀者的感覺,應該像原文給原文讀者的感覺。”2這段話言簡意賅,對某些詬病翻譯名家(如傅雷)的譯品過于流暢通順的論述,恰好予以當頭棒喝!
余光中與蔡思果,正如本文筆者一般,多年來對翻譯中常見的譯病不斷口誅筆伐,大聲疾呼,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譯文體對現代漢語荼毒的情況越演越烈,已經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此處茲將余翁有關英譯中的重要提示綜述如下,以作為檢驗余譯與他譯之間風格異同以及創作空間寬窄的依歸。
首先,且勿論文化底蘊和文字結構的差異,中文和英文在文法修辭和習慣用語方面是截然不同的。英譯中時,譯者為求信實,往往會跟隨原文的語法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半步,殊不知這種做法時常“欲簡得繁”,立意在精確,結果得累贅。最常見的例子,就是譯文中“代名詞”泛濫成災,“連接詞”連綿不絕,“形容詞”的的不休,“介系詞”累贅不堪,“復數”“們”不勝悶,“被動式”“被”無可避,“抽象名詞”比比皆是的現象。
先說“代名詞”。英文使用代名詞的機會很多,中文除非必要,不太多用代名詞。余光中在《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中,從流行西化用語和句法中舉出一些典型例子,以探其病根。作者謙稱自己只能“約略”探討,“因為目前惡性西化的現象交莖牽藤,錯節盤根,早已就成了一團,而索其來源,或為外文,或為劣譯,或為譯文體的中文,或則三者結為一體,渾沌沌而難分了” 3。一般來說,中文里的代名詞往往可以省略,例如寫信時自述可以不用第一人稱代名詞;文章里第三人稱代名詞用作受詞時,一般略而不提;代名詞所有格在英文里連串出現時,譯文里可免則免等。這些原為中文行文的慣例,譬如我們說“今日早起,一如往常,洗臉刷牙,穿衣看報”,絕不會說成“我洗我的臉,我刷我的牙,我穿我的衣服……”,可惜在拙劣譯文的影響之余、惡性西化的催動之下,一般讀者對這種譯文體中文已習以為常,好壞不分了。
中文里使用“連接詞”的習慣和英文并不相同,英文里如果并列連串詞匯,不論是名詞、形容詞、動詞、副詞或介系詞,必然在最后一個詞之前加以and一字,以示連貫。中文里說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紅黃藍白黑”五色時,絕不會在最后一個字前加個“和”字。此外,縱然使用“連接詞”時,也不應由一個“和”字去統籌解決。“目前的中文里,并列、對立的關系,漸有給‘和’字去包辦的危機,而表示更婉轉更曲折的連接詞如‘而’‘又’‘且’等,反有良幣見逐之虞。這當然是英文的and在作怪。”4詩翁這段話說得一針見血。
余光中有篇談論翻譯的名篇《論的的不休》,那是1996年應筆者邀請,來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主辦的“外文中譯研究與探討”學術會議上的主題發言。在這篇文章里,他把白話文中濫用“的”字的現象剖析得淋漓盡致。“白話文的作文里,這小小‘的’字誠不可缺,但要如何掌控,不任濫用成災,卻值得注意。”5他接著表明“的”字如果“驅遣得當,它可以調劑文氣,厘清文意,‘小兵立大功’。若是不加節制,出現太頻,則不但聽來瑣碎,看來紛繁,而且可能擾亂了文意。”6因此,詩人翻譯時,頗為自制,“我早年的文章里,虛字用得較多,譯文亦然,后來無論是寫是譯,都少用了。這也許是一種文化鄉愁,有意在簡潔老練上步武古典大師”。7
介系詞的用法,翻譯時也頗有講究。“介系詞用得太多,文句的關節就不靈活。‘關于’ ‘有關’之類的介系詞在中文里越來越活躍,都是about、concerning、with regard to 等的陰影在搞鬼。”8此外,余光中對于翻譯中濫用“作為”一詞,頗不以為然。的確,“作為一個老師”這樣的說法,為什么不可以用“身為老師”來表達呢?
詩人在多篇文章里提及翻譯時亂用西化復數“們”的弊端。其實,中文里的復數,是不必一概以名詞之后加個“們”字來表達的。當然,指稱人物時,可以用“們”,但也不能濫用,例如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中有一段:“尹雪艷總也不老。十幾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樂門舞廳替她捧場的武陵少年,有些頭上開了頂,有些兩鬢添了霜;有些來臺灣降成了鐵廠、水泥廠、人造纖維廠的閑顧問,但也有少數卻升成了銀行的董事長,及機關里的大主管。”9這段文字里,說到“武陵少年、閑顧問、董事長、大主管”等人物,其實都是復數,但作家既一個“們”字也沒用,讀者念來也不會混淆不清。然而這些字眼,一旦翻譯成英文,卻必須立即補上復數s,連“鐵廠、水泥廠、人造纖維廠、銀行、機關”等也得加上s,可見中英文的生態是完全不同的。邇來常見在坊間的譯文中,每逢復數必加“們”字,不但在人物后如此,在其他在事物后亦如此,譬如“石頭們、汽車們”,現代漢語西而不化至此,實在令人不忍卒讀。余光中和林語堂意見相同,對“人們”一詞也十分厭惡。林語堂曾說一輩子不用“人們”;余光中則謂:“其實我們有的是‘大家’‘眾人’‘世人’‘人人’‘人群’,不必用這舶來的‘人們’”。10
翻譯時,一見英語被動式,就在中文里毫不猶豫手起“被”落,實在是十分懶惰的做法,毫不足取。其實,英文多被動語氣,中文卻不然。譬如說:“門前有株棗樹,結了四顆棗子,兩顆掉了,兩顆采了”,這句簡單的話里,“兩顆掉了”是主動式,“兩顆采了”是被動式,這后面一半是不必強加“被”字來表達的。中文里萬一真要表示被動語氣時,除了“被”,也有多姿多彩的說法,例如“為” “經”“受”“遭”“挨”“給”“教”“讓”“任”“由”等字。“目前中文的被動語氣有兩個毛病。一個是用生硬的被動語氣來取代自然的主動語氣。另一個是千篇一律只會用‘被’字……卻不解從‘受難’到‘遇害’,從‘挨打’到‘遭殃’,從‘經人指點’到‘為世所重’,可用的字還有很多,不必套一個公式”。11然而目前流行的中文,無論名家或初手筆下,“被”字已經無所不在、避無可避了。此處再引用一段白先勇的小說:“左半邊置著一堂軟墊沙發,右半邊置著一堂紫檀硬木桌椅,中間地板上卻隔著一張兩寸厚刷著二龍搶珠的大地毯”(《游園驚夢》)12,這段文字里一個“被”字不用,翻譯成英文,“置著、隔著”卻都變成了were grouped、was covered這樣的被動式。
英文里的抽象名詞,就如原野中隨地蔓生的雜草,一叢叢,一堆堆,翻譯時必須小心摸索,繞道而行,以免絆倒。余光中認為“抽象名詞的‘漢化’應有幾個條件:一是好懂,二是簡潔,三是必須;如果中文有現成說法,就不必弄得那么‘學術化’,因為不少字眼的‘學術性’只是幻覺。”13他提出本來可說“很有名”時,不必造出一個“知名度”;說書本“很好看”“很動人”或“引人入勝”都可以,不必說“可讀性很高”;“更具前瞻性”也不見得比“更有遠見”高雅。這種所謂的“學術化”抽象名詞泛濫的結果,中文里出現了很多“性”“元”“度”“值”“化”那樣的字眼,久而久之,“英文沒有學好,中文卻學壞了,或者可以說,帶壞了”14。
余光中對于美麗的母語,念茲在茲,畢生守護,他是中華文化這座巍巍巨廈勤勉不休的“守夜人”15。詩人不斷為純凈優雅的中文受到惡劣譯文體的影響而大聲疾呼:“對于這種化簡為繁,以拙代巧的趨勢,有心人如果不及時提出警告,我們的中文勢必越變越差,而地道中文原有的那種美德,那種簡潔而又靈活的語文生態,也必將面目全非。”16他更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美麗的中文,我們這民族最悠久也是最珍貴的一筆遺產,正遭受日漸嚴重的扭曲與污染……翻譯教師正如國文教師,也正如一切作家與人文科學的教授,對于維護美麗的中文都負有重大的責任,對于強勢外語不良影響的入侵,這該是另一種國防。”17
以上所述,不過是中文受到惡性西化的典型例子,其他惡劣的影響不勝枚舉, 難以盡述。這種西而不化的譯文體,在余光中眾多譯品中,卻絕對難以得見。這也是余譯之所以膾炙人口、勝人一籌的重要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