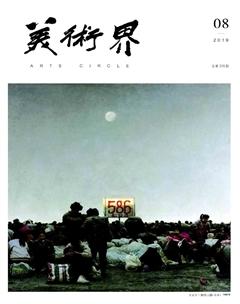抽象與有機的融合
歐陽波


【摘要】亨利·摩爾是英國現代著名雕塑家,其作品《國王與王后》為其創作旺盛時期的命題之作,雖然追隨現代藝術創作方式,但又蘊藏著對歷史文脈及人性的延傳與探索,將現代藝術表現與人文歷史精神關懷融為一體,打破傳統古典藝術的固化表現形式,推行模糊化、陌生化處理,力圖引導人們回歸對藝術造物本身的思考。雕塑作品本身不單單是概念性的無規則抽象,更是一種自然形態的富有有機生命的抽象,將雕塑材質自然的質地、肌理和內蘊生命力、歷史生成力相結合,表達著更深遠的意味。
【關鍵詞】抽象形式;自然肌理;人文情懷;生命有機體
亨利·摩爾(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年)是20世紀享譽世界的英國現代著名雕塑家,他出生于英格蘭約克郡產煤小鎮卡素福特(Castleford),曾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一生創作無數,主要題材涉及母與子、人體組合、王與后等,以大理石、青銅材質見長。他曾成立基金會資助青年雕塑家舉辦展覽,將自己的莊園改作雕刻公園奉獻世人,獲得過牛津、哈佛、劍橋等大學的名譽學位以及英國的功勛獎章,蜚聲海內外。①作品《國王與王后》是雕塑家亨利·摩爾1952—1953年間創作的青銅雕塑,此時正處于他的創作旺盛期,當時的藝術批評家及大眾已普遍認可了他的雕塑藝術成就及地位。該作品實際上是藝術家受英國人委托而進行的創作,帶有一定的命題性質。這件作品最后定稿高度為161.3厘米,青銅材質,被放置在蘇格蘭丘陵地帶。與西方古典學派的雕塑藝術相比,亨利·摩爾的這件作品更趨于抽象化表達,國王和王后的身體呈扁平狀,毫無帝王帝后華貴的繁瑣裝飾。倘若置身在藝術走下神壇,走向大眾化、平民化的現代文化語境中,其坐姿似乎是雕塑家在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有意將國王與王后的坐姿形態抽象化,意在將“權貴”降為“平民”,使作品對象帶有“人”的普遍平等性和模糊價值性的探視,以作品題目引發人們對作品的無限遐想。
從亨利·摩爾的藝術創作軌跡來看,《國王與王后》的誕生離不開藝術家本人獨特的人生藝術歷練、對社會的感悟以及對現代主義思潮的反思及個人重構。亨利·摩爾曾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過兵,后因獲得退伍軍人獎金和獎學金而得以進入藝術院校深造,接受藝術創作實踐教育;二戰期間亨利·摩爾曾在英國防空洞中授命作為戰地藝術家記錄戰時情景。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讓他關注人,更熱愛生命,展現人與歷史的關系,思想更深邃,關注現代藝術進程中人探知未知的勇氣。②亨利·摩爾在英國利茲美術學校和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求學期間,一方面接受了學院派古典雕刻技法的訓練,奠定了自身扎實的雕塑功底,同時通過讀書不斷提高自己,打開藝術認知的眼界,例如羅吉爾·弗賴的《意象與設計》(1920年出版)、愛斯拉·龐德的《Gaudier Brzeska》(1916年出版)等書中關于“黑人雕塑”“古代美術藝術”的文章當時就曾深深影響了摩爾對藝術的感覺③;另一方面他經常參觀博物館,進一步加深了自己對古埃及、墨西哥及中世紀宗教雕塑、原始美術的理解,并對原始藝術產生了著迷和向往之情,亨利·摩爾認為“一切原始藝術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那生氣勃勃的活力。這是人民對生活的直接感受的再現”④。同時亨利·摩爾也先后到過意大利和巴黎,接觸到現代派藝術——立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作品。
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兩次世界戰爭擊碎了資本主義帶來的太平盛世、物欲橫流,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觀追求受到了否定,人對傳統社會標榜的古典傳統亦產生了巨大的質疑,以藝術表達自我滿足與自我表現成了現代藝術家展現自我存在的突破口。藝術語言、藝術媒材的多樣化選擇與抽象表達成為現代藝術顯露個性的戰場。亨利·摩爾在迷戀抽象的超現實主義等藝術風格的同時,也漸漸形成了自己對藝術抽象、藝術材料、藝術表現的獨特理解。他認為“所有好的藝術作品中都有‘超現實性和‘抽象性。這是感情或想象力的非邏輯靈感的混合物,……是與藝術家的經驗和他的藝術實踐的理想的結合”⑤。從亨利·摩爾的諸多作品分析來看,他對雕塑的理解似乎不單單是概念的抽象組合,更是一種自然形態的富有有機生命的抽象,將雕塑材質自然的質地、肌理和內蘊生命力、歷史生成力相結合,表達更深遠的意味。
如果說,遭遇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使亨利·摩爾更關注人作為自然生命體的存在,那么學院派的古典雕塑技法則是奠定了藝術家本人的造“人”塑型功底(指以人為主題的雕塑類型),而獨特的閱讀經歷和博物館參觀愛好讓他看到了藝術服務于人民、表現人民、自古至今最本質的精神傳承,正如藝術評論家赫伯特·里德所言,從原始藝術尋找原型題材(如埃及藝術、蘇美爾藝術等)進行有關“人”題材創作的角度來看,似乎亨利·摩爾比一般的學院派藝術家“更為因循傳統”⑥;而接觸現代藝術流派可以說是整合、提升亨利·摩爾綜合性藝術素養,凝練其藝術思想,觸發其藝術創造動機的關鍵。
《國王與王后》這件作品在藝術形象的選擇上,如果不借助藝術史家或藝術家本人的闡釋似乎很難尋出線索。亨利·摩爾在自傳中講過,“《王與后》是一個大題材。在我做的過程中,在大英博物館中的那件我多次觀察過的埃及的雕塑《坐著的官吏和他的妻子像》給了我啟示。然而雕塑家卻使他們超越了自己的身份,而使得他們具備一種巨大的高貴氣派和自信心,幾乎是一種極高貴的目的使得他們呈現出高于普通生活的狀態。我一直試圖把這種感情匯入我的雕塑中去”⑦。摩爾還講過,“《王與后》很奇特,……我無法確切地解釋它是怎樣變成這樣的。任何東西都能夠啟發出一件雕塑作品的聯想,這件作品是在玩弄一小塊鑄模蠟時產生的。那時我正在考慮動手開始弄我自己的鑄銅工作室,我決定刪掉第一個步驟,(也就是制作石膏模型的步驟)然后直接用蠟造型。同時一邊擺弄著這一小塊蠟,它開始有點像一只角,像潘神蓄著胡須的頭。接著變成了一只皇冠,這時我馬上意識到它像是一個皇帝的頭。我繼續做下去,安上了軀體,當蠟變硬之后,它幾乎像金屬一樣硬。我把這種極為強烈地在頭部發現的貴族式的精致典雅在軀體上又再度體現出來。當我加上另外一個人像之后,它就變成了《王與后》。我意識到這是由于我每天晚上給我六歲的女兒瑪麗讀的故事大部分都與王、王后和王子有關”⑧。亨利·摩爾認為理解《國王與王后》的線索“正在這個‘王的頭部,那是冠、胡須和顏面的綜合體,象征著原始王權和一種動物性的‘潘神似的氣質的混合。‘王的姿態比起‘后來顯得較為從容和自信,而‘后則更為端莊,且帶點帝后的自覺。在我開始做雕像的手和腳的時候,有機會使它們做得更為現實,以進一步表達我的想法,我想以此說明人類的溫良和原始王權觀念之間的對比關系”⑨。對《國王與王后》形象的理解,在藝術家摩爾看來,《國王與王后》形象的考量綜合了多種因素。潘神,是希臘傳說中的農牧神,為人羊混合的形象,負責關照放牧人、獵人、農民等住在鄉野之人,是鄉野田園管理之神。王冠,是人間至上王權的象征。另外,藝術家因考慮蘇格蘭的屬地的歷史象征意義,以傳說中推行平等機制的圓桌會議的亞瑟王和王后作為《國王與王后》的雛形出發點。在這里,藝術家看似無意、實則有意地創作拼湊而將潘神、獸像、人(戴王冠者)抽象化變形處理雕塑頭部,以此傳達人性、神性中王權亙古承傳的歷史性與人文性特質。作品似乎在有意契合作品的屬地性質——在串聯神話與歷史、古代與現代的同時,也連接起了英格蘭的古老文化和民族平等精神。


在藝術材料選擇方面,《國王與王后》沒有使用慣常的大理石,而是采用青銅材質,似乎是看中了青銅獨有的延展性特質,將人物形象有意拉長,以材質的無限延展表達所塑造形象的無限延展可能。這與摩爾所主張的“雕塑的尺寸應大于實物”,以減少開闊空間對物體尺度的影響相一致。⑩在造型手法上,亨利·摩爾打破以往古典雕塑家突出人體美感的做法,采用怪誕的形式——人體呈現被捏造的抽象的扁平狀態,與其說是突出形式,不如說是有意扭曲簡化形式,以簡約之形塑精神之形。這里的“國王”與“王后”呈現的坐姿,與埃及法老與王后的坐像雖然存在極度地相似,但卻沒有傳統國王的威嚴與端莊,沒有華麗的服飾和傲慢的神態,有的只剩下怪誕的形式探索——簡單的平面身軀,扭曲的臉部面具式表現,仿佛是抽象的、類似從遠古走來的人坐在那里,倘若沒有作品名稱《國王與王后》的提示,似乎也可以被認定為普通人的現代藝術方式下的怪誕抽象表現。在這里,有意抽象化、陌生化的表現與其說是藝術家個體的創作,不如說是社會現代性的共同追求,以反叛古典藝術傳統,有意追求形式的“陌生化”。正如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什克洛夫斯基所闡述的“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就是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頭顯出石頭的質感。藝術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覺到事物,而不是僅僅知道事物。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長度,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設法延長”??。由此形成“燦爛至極歸于平淡”“豪華落盡見真淳”的藝術表現效果,表達藝術作品本真的存在感。亨利·摩爾的《國王與王后》坐姿,在某種意義上說,屬于“傳統風格”的現代重構。
雖然藝術家亨利·摩爾自己也承認許多作品的闡釋都是事后產生的,但是藝術家本人對雕塑作品的理解和藝術知識的串聯、藝術精神的昭示已經不自覺地融合進作品的創作當中,作品的多元隱喻性因此誕生。倘若“國王”與“王后”塑造得十分逼真,那么欣賞者一眼便能知曉它的“國度”“歷史”“性格”“脾氣”等。這件作品隨之變成了某個國王與王后生活的真實寫照與古典歷史留念。而眼前的《國王與王后》這個作品卻是現代社會背景和現代藝術欣賞習慣中而產生,可由觀者駐足欣賞而容易產生無限遐想,更甚者,他可以隨意放置在其他公共環境中,形成休憩的游人的景觀雕塑,而不會產生不和諧感。倘若不是文獻提示,我們似乎更覺得是地理環境決定著作品的身份——作品反映的不是國王與王后,而是一對平民夫婦,或者說成英倫的王與后,而非其他地方的王與后,等等。這一類的想象已經擺脫了藝術史家、雕塑家對藝術作品的固化傳唱,促成了大眾對現代藝術的主觀性介入、互動和參與。藝術作品與現實的距離感在多元的想象與聯想中消失。可以說,正是這種隱喻性成就了作品的多元適應性和現代欣賞性。
《國王與王后》被置于蘇格蘭曠野丘陵的布局,作品與環境正好融為一體,形成一道靚麗的人文景觀,恰似歷史上亞瑟王審視統治的國土,又似神話傳說中的牧羊人管理勞作的田地,也似現代社會休閑的夫婦平靜地欣賞丘陵上的風景……可以說抽象的《國王與王后》雕塑作品有意形成了抽象而模糊的印象,既融入天然的自然環境中,也融入了歷史神話傳說的人文環境中,形成無盡的意味,讓藝術真實、藝術幻象與情感想象共存,讓人產生在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維度共同看待國王與王后古今滄海之變的錯覺,在歷史的共鳴中,回味現代人自我營造的無名無識、無自我存在感的蒼涼與迷惘,或許這正是現代藝術共性存在的不確定性表現。
注釋:
①海藍等:《圖說西方雕塑藝術》,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180頁。
②陸軍:《摩爾論藝》,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1年,第109頁。
③[英]赫伯特·里德:《亨利·摩爾》,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9年,第16—19頁。
④轉引自洪復旦、馬新宇、韓顯中《美術鑒賞》,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9頁。
⑤亨利·摩爾:《觀念·靈感·生活》,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第29頁。
⑥[英]赫伯特·里德:《亨利·摩爾》,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9年,第80頁。
⑦同上,第53頁。
⑧同上,第54—55頁。
⑨轉引自陳衛和《西方雕塑·二次大戰前后的范例》,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3年,第160頁。
⑩轉引自周衛星《20世紀的雕塑巨匠亨利·摩爾》,《名作欣賞》2001年第3期,第127頁。
轉引自陳旭光《藝術問題》,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12年,第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