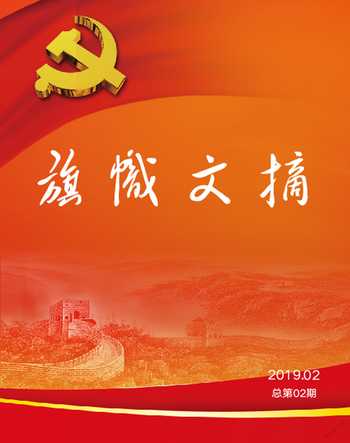他的紀錄片,不按套路出牌
李璇
“你為什么會長這么高?”
“我是在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還有老師的幫助下長這么高的。”
這段對話,來自張以慶的紀錄片《幼兒園》。這部展示武漢一座寄宿制幼兒園孩子日常生活的紀錄片,一經推出,便引來熱議。
“拍攝幼兒園紀錄片,一百個導演會選擇拍講故事、唱歌、畫畫,一萬個導演會拍慶祝六一兒童節,這都是我堅決不拍的。春游、小河邊、手拉手、做游戲這些是概念,只要是概念,我就不拍。”張以慶這樣說。
于是,觀眾驚異地發現,幼兒園里的孩子竟也懂得仿佛只有在成人社會才存在的種種“潛規則”。
這部《幼兒園》,連同此前那部“捧紅”了舟舟的《舟舟的世界》,讓張以慶在紀錄片界名聲大噪,并獲得范長江新聞獎、中國電視金鷹獎等多項國內外大獎的肯定。多年以來,他的作品,一直被列入大學影視專業的必看片單。
“張以慶當年出現時是有些突兀的,他完全是紀錄片潮流之外的人,但是他的作品,又給我們帶來了非常豐富的啟發。”在近日舉辦的張以慶導演學術研討會現場,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同道這樣評價。
張以慶與舟舟的相遇純屬偶然。
1995年,在拍攝一部表現大學生就業的紀錄片《起程,將遠行》時,張以慶去武漢樂團拍一個學生,遇到了常年在樂團旁聽的舟舟,后來便有了《舟舟的世界》這部紀錄片。
《舟舟的世界》播出后,反響熱烈,舟舟從此成為婦孺皆知的人物,有了真正上臺指揮的機會。而張以慶獨特的拍攝理念,也漸漸被外界知曉。
“這個題材,如果只拍成一個患有唐氏綜合癥的孩子和音樂的故事,那就永遠是獵奇,而直到今天也沒有人說這是獵奇。為什么?因為我是在表現一個人和他的生存環境的關系,這是關系到每個人的世界命題。看到舟舟,每個人都會看到自己。”張以慶說。
在《英和白》里,張以慶則將視角轉向世界上唯一一只被馴化的熊貓“英英”與馴養師“白”的關系上。在整部片中,英和白都保持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只有一臺電視機,將外部訊息帶入他們共同生活的那個七八十平方米的房間。
與強調現場感、同期聲、長鏡頭的主流紀實觀念相比,“不走尋常路”,是大多數人對張以慶作品最直觀的印象。
張以慶的新作《君紫檀》,講述的是紫檀匠人顧永琦的故事。不少人擔心,張以慶這次會拍出“高級的廣告片,或者是好人好事表揚稿、一位民營企業家的傳奇”,砸了自己的牌子。
結果,這一次張以慶又沒按照眾人的設想行事。拍攝初期,他沒有將鏡頭對準顧永琦,而是先找來關棟天、陳丹青等文化名人,又引入了昆曲、京劇等門類的藝術表演。
即便是拍攝顧永琦本人,張以慶也選擇“偷拍”的形式。據顧永琦透露,“我平時愛打太極拳,結果我二弟(張以慶)就在寒風里躲著偷拍我,凍得不行了也不說一句。”
直至看完成片,顧永琦才知道,張以慶都請來了哪些客人,而與他有關的畫面,也記錄了不少連他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片段。
事實證明,這次張以慶還是沒有拍“甲方片”。
張以慶最怕的,就是在創作上重復自己。
“我覺得每一次表達都要有一個全新的東西。我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一個導演應該做到,作品在五年之后還能拿得出手,十年之后還能不臉紅。”張以慶說。
從《舟舟的世界》《幼兒園》到《英和白》,張以慶的作品越來越弱化敘事,而增添了哲學思考和藝術化探索。
“張以慶的作品有一個大的趨勢:從具象到抽象、從文學到哲學。《舟舟的世界》還覺得像小說,有人物、故事;《英和白》就像寓言了,主角可以沒名字,也沒故事;《幼兒園》更是一堆碎片,那些孩子叫什么一點都不重要。這部《君紫檀》準確地講,完全沒有故事,連一件家具從開始到完成的過程都沒有。”張同道說。
在《君紫檀》里,由于紫檀家具與人的感知息息相關,張以慶便嘗試拍出紫檀材質的“觸感”。通過引入綢緞、水滴、嬰兒、纖手等意象,紫檀的光滑觸感在觀眾的通感中得到了體現,而京劇念白的解說詞、流動的邏輯線,也為整部影片營造出了強烈的詩意。
張以慶的作品曾被許多人質疑是否屬于紀錄片這個范疇,他的碎片化的剪輯方式也常被人們評價為“看不懂”。
對此,張以慶有一個著名的“紅線”比喻:“現在(講故事)經常出現一條紅線,我煩透了一條紅線穿珠子,我不穿珠子行不行?大珠小珠落玉盤行不行?我不要那個紅線行不行?我紅線是隱性的行不行?我是綠色的線行不行?”
“很多人只重視紀錄片的社會性、新聞性、歷史性,但是不把紀錄片當作藝術來看待,張以慶的創作則更多關注那些超越表層行為的精神層面的東西,體現出了藝術性,這點很難得。”中央電視臺軍事節目副總編輯徐海鷹說。
“平生三十年,我沒做過一個領導交辦的片子,這在電視行當里是很少見的。”張以慶說。
究竟是什么樣的創作生態,讓張以慶得以成為“張以慶”?
1987年,張以慶從武漢市手表廠調入湖北電視臺。他的前任上司、湖北衛視原總監景高地如今還清楚地記得,張以慶借調到電視臺期間,曾拍攝過一部名為《童年,七彩的歌》的紀錄片。
張以慶很重視這部片子,而當時電視臺的制片主任審完片后,一句話都沒說就走了。
張以慶以為“片子完蛋了”,與攝影師來到景高地的宿舍里,“倒在床上起不來”。
景高地對他們說:“主任走了并沒有說這個片子不能播,我告訴你這個片子能播。”
正式轉入電視臺后,湖北電視臺的多位領導,也都對張以慶采取寬松甚至是“放任”的態度。
“我說張以慶需要報什么選題呢?張以慶既然是個奇葩,就讓他自由生長吧。他找到了好選題就會告訴你,你只要告訴他行還是不行就完了。拍幾年那是他的事,什么時候出來那是他的事,他怎么痛苦去拍那是他的事。”景高地回憶。
對此,電視臺的同事也并非沒有過非議,景高地則統一回應:“只要你能拍出《舟舟的世界》,我就給你這個待遇。”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電視臺的知人善任,成就了張以慶。
(瞭望東方周刊 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