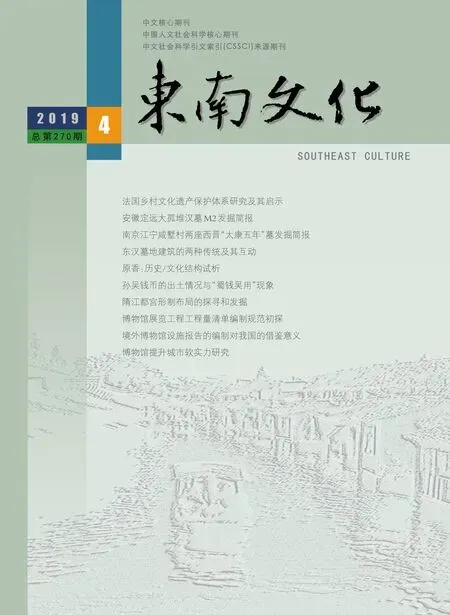傷痛記憶博物館功能的再思考
許 捷
(浙江大學考古與文博系 浙江杭州 310028)
內容提要:有別于大部分猶如人類文明豐碑一般存在的博物館,傷痛記憶博物館保存與展示的是人類文明的創傷事件及由此形成的社會記憶。在文化記憶理論的視角下,傷痛記憶博物館超越了單純的記憶保存角色,通過對傷痛記憶的博物館化,成為群體記憶的中心。當歷史站在集體記憶即將失效的臨界點上,傷痛記憶博物館從引導群體內部認同和外部普遍情感建立兩方面,可以發揮彌合社會裂痕的作用,讓人類文明的“負資產”發揮出積極的作用。
隨著作為見證人的幸存者逐漸離世,時間正在將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社會創傷的事件“歷史化”。在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將2017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定為“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博物館講述難以言說的歷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后,更多的人意識到人類文明的進程并非都光鮮亮麗,博物館對于歷史記憶的展示也不應只有其正向的一面,但以展現人類文明豐碑為主要特征的圣地模式仍然是博物館的主流。如何保存因公共罪行造成的傷痛記憶?如何理解人類文明的“負資產”?為什么說傷痛記憶的“博物館化”是比“歷史化”更為有效的記憶保存方式?面對難以言說的歷史,博物館可以說的其實有很多。
一、博物館不僅僅是文明的豐碑
自繆斯神殿以來的博物館傳統一直都帶有人類文明豐碑的色彩。在今天的博物館,大部分觀眾和博物館都沒有擺脫這種模式。在博物館以物為中心(object-centered)的年代,文明豐碑的取向表現在對于藏品的選擇上,博物館選擇那些精美珍貴的、帶有明顯精英生活屬性的展品作為鎮館之寶進行廣泛宣傳,觀眾則帶著尋寶獵奇的心態前往博物館參觀。當博物館展覽從以展出“物”為中心轉為向觀眾傳播信息為中心,其本質是博物館收藏邊界的擴展[1]。博物館對社會記憶的保存超越了實物展品的范疇,現象與記憶也進入到收藏的視野中。
(一)傷痛記憶博物館定義
在長期的文明豐碑模式中,觀眾已經習慣了在博物館中尋找人類文明的成就一面,對文化遺產的理解也更偏向正面的解讀。然而歷史并不總是光鮮亮麗或令人愉悅的,事實上,存在著一類保存展示人類文明“負資產”的博物館。在國際博物館協會的31個專業委員會中,有一個名為“國際公共犯罪受害者紀念博物館委員會”(IC MEMO,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這一委員會認為有一類紀念博物館(memorial museums)的目的是紀念由于國家、社會或意識形態導致罪行的受害者[2]。
傷痛記憶由自然災害和國家、社會以及意識形態公共罪行兩類造成。在公共犯罪受害者紀念博物館中,有一些主題對塑造一個地區或民族的共同認知形成了極大影響,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猶太人大屠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和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這類博物館的工作對象是那些造成了傷痛記憶的公共罪行,但促成其建館的核心動因其實是社會共有的傷痛記憶,因此這類博物館可以稱為傷痛記憶博物館。
由國家、社會以及意識形態公共罪行造成的傷痛記憶是一種社會記憶,相對于個人記憶,社會記憶由某一地區的人群共同擁有。戰爭、大屠殺、恐怖襲擊這些創傷事件就像是人類文明的瘡疤,傷痛記憶博物館則成為保存與展示這些瘡疤的平臺。一方面傷痛記憶是一種文明的“負資產”,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個地區或民族的共同身份認同和當代面貌。以下所討論的傷痛記憶博物館特指其工作對象是公共罪行這一類。保存記憶、不忘歷史、反思過去是我們賦予這一類傷痛記憶博物館的使命。在這些博物館里,觀眾們看到令人不悅的回憶和證據。在和平時代,我們為什么要保存這樣的記憶;當創傷事件的受害者們都已經過世,繼續保存這些記憶的意義又是什么?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
(二)“負資產”的正面作用
傷痛記憶作為一種文明“負資產”被保存下來,其對社會發展是否有正面的作用?
首先,傷痛記憶有助于群體身份認同的形成。猶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銘記歷史的儀式性活動,他們所紀念的歷史并不是猶太民族的輝煌或對世界的貢獻,而是歷史上他們流離失所的經歷,猶太人群體的認同與他們的苦難經歷密不可分。保存集體記憶本質是在尋找服務于當下的意義,當一個群體面臨危機,需要團結一致和適應新環境時,他們通過敘述自己的過去,建構起共同的過去視域,從而與被回憶的人群組成一個共同體。在殖民統治結束以后,許多新建立的國家都把自身的歷史建構在受難和遭受痛苦的敘事上[3]。在傷痛記憶的紀念儀式中,人們由于共同的遭遇所滋生的認同感,更容易形成“我們”和“他者”的概念,凝聚力油然而生。
其次,對傷痛記憶的強調往往是一個群體對于可能發生危機的預防性反應,表達對創傷再次形成的憂慮。以猶太人大屠殺為主題的博物館并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就迅速建立的。20世紀中期開始的幾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聯合攻打以色列使得猶太族群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猶太人深恐民族悲劇再一次上演。1978年,總部位于美國芝加哥的美國納粹組織在伊利諾伊州的斯科基(Skokie)舉行威脅性的游行,引起了大屠殺幸存者的抗議。1978年4月16—19日,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播出了一部長達9個半小時的迷你劇集《大屠殺》(The Holocaust),觀眾人數約為1.2億,引發了大眾關于大屠殺記憶在流行文化中庸俗化的激烈爭論。為了安撫猶太社區以及其他的政治目的,1978年5月1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宣布成立專門委員會慶祝以色列建國30周年,并動議建立大屠殺紀念館[4]。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修建肇始于一場外交風波。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審定通過了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書中刻意淡化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戰爭性質,對于南京大屠殺的陳述則刪除諸多關鍵史實。此舉激起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及其遺屬們的無比憤怒,他們紛紛要求把南京大屠殺血寫的歷史銘刻在南京的土地上。南京市人民政府順應了人民的呼聲,于1983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殺江東門集體屠殺和萬余名死難者叢葬地遺址上立下奠基碑,并著手籌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5]。今天,以南京大屠殺事件為代表的日軍侵華傷痛記憶已是中國人的共同記憶。如果需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語境中尋求普遍的認同感,那么對于南京大屠殺這一傷痛記憶的紀念就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最后,紀念傷痛記憶對社會具有療愈作用。創傷事件發生后,人們容易陷入茫然無措的悲情狀態,渴望被安慰,需要有人為他們指明繼續前進的方向。人們常常會選擇在創傷事件的發生地舉行紀念儀式,講述經歷,分享感受,祈福未來。“9·11”恐怖襲擊發生后,人們在世界貿易中心遺址上舉行了多次紀念活動,幸存者們在這樣的紀念活動中確認自己沒有被遺忘。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Obóz Koncentracyjny Auschwitz-Birkenau)其被改造成紀念博物館之后,也為戰后的猶太人提供追溯過往、了解本民族、認識自我的機會。1970年12月7日,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后,自發下跪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這一舉動后來被稱為“華沙之跪”(Kniefall von Warschau),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聯邦德國與東歐諸國改善關系的重要里程碑。承認創傷事件,紀念傷痛記憶,對事件的受害者來說具有被肯定的重要意義,這也是其療愈力量的來源。
二、傷痛記憶與博物館
既然傷痛記憶有其正面的意義,今天的博物館在拓展了收藏邊界之后,具有保存展示物質文明和記憶的雙重身份,是不是可以認為用博物館來保存傷痛記憶就可以抵擋時間的侵蝕?博物館對傷痛記憶的保存與展示相較于其他記憶又有什么區別?
(一)從集體記憶轉向文化記憶
當創傷事件的幸存者和見證者都離世后,我們該如何保存這些記憶?針對這個問題,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認為,如果不想讓時代證人的記憶在未來消失,就必須把它轉化為后世的文化記憶。這樣,鮮活的記憶將會讓位于一種由媒介支撐的記憶,這種記憶有賴于像紀念碑、紀念場所、博物館和檔案館等物質的載體[6]。
記憶一直與大腦聯系在一起,被認為是一種人類個體生理的機能,而社會并沒有生理意義上的大腦,人類社會并不像個體那樣保存記憶[7]。揚·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記憶理論將記憶分成三種形式: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和文化記憶。個體記憶是我們平時理解的一種生理機能。集體記憶在群體個體間的交流中是隨著具體環境變化的記憶。這些記憶以個體記憶的形式存儲在頭腦里,個體之間不需要過多的解釋便能夠對這些記憶進行交流。這類記憶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變化,離開活生生的個體便無法生存,并隨著世代交替而變化,一旦人與人的交流終止,集體記憶便宣告消亡。借助肉身完成的集體記憶一般只涉及三代人,即80~100年的時間。文化記憶既不是“知識”也不是“傳統”,而是深植到群體的文化習俗中,成為群體身份認同建構的一部分。文化記憶需要特定的社會機構借助文字、圖畫、紀念碑、博物館、節日、儀式等形式創建,會對相關機構或群體的延續起到定型和規范作用。那些歷史悠久的文化記憶通過書寫、節慶等文化規則擺脫了時間的侵蝕。相比集體記憶,文化記憶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時間視域,它可以長達兩三千年。但文化記憶也需在以不斷重復為基礎的儀式化的公共紀念中得到鞏固,這需要專人維護,并需要相應的時間和日期作為支撐[8]。
我們也許會問,當記憶成為歷史文獻難道不是已經不朽了嗎?為什么還要尋求諸如成為文化記憶的其他路徑?記憶的歷史化存在兩方面問題。首先,今天的世界依然存在歷史被銷毀的風險。2015年,伊拉克摩蘇爾(Mosul)當地的圖書館在戰爭中被摧毀,大量珍貴的古跡和手稿被毀,依托于物質載體的書面歷史事實上極其脆弱。其次,書面歷史并不是一個會進行主動傳播的媒介,可以認為今天主要的書面歷史都是面對專業人員的,普通人很少會主動在書頁中尋找歷史。成為書面歷史的記憶事實上成為了一種“死記憶”。隨著時間的推移,事件和情緒的濃度都在減淡。對今天大部分在和平年代出生的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能還是日常會觸及的話題,而更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則已遠離日常,僅存在于歷史中了。隨著創傷事件的幸存者和見證者離世,“歷史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要讓記憶保持鮮活,就要讓“記憶”成為“文化記憶”。
文化記憶理論把博物館、檔案館、紀念碑都作為記憶存儲的容器,是維持文化記憶長期延續的重要構成部分。但如果僅僅把博物館作為一種保存媒介,也許太過低估了博物館作為一種文化象征的力量。傷痛記憶的博物館化是成為文化記憶的重要過程。
(二)傷痛記憶的博物館化
不論是集體記憶階段還是文化記憶階段,社會記憶都需要紀念儀式進行維護。普遍意義的紀念儀式具有兩種形態,一種是行為模式,另一種則是建筑模式。行為模式是指悼念、回憶、祭奠、公共討論等活動,這一模式在世界范圍內都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在一個趨于穩定的傷痛記憶中,行為模式的紀念儀式往往具有周期性,例如周年性的常規紀念以及逢五周年或十周年倍數的大型紀念。建筑模式則是指紀念碑、公共雕塑、紀念公園、受保護遺址等具有象征意義、能夠激發回憶的物理實體。行為模式的發生往往在地理位置上與建筑模式產生聯系,人們通常會選擇在紀念碑紀念廣場上舉行紀念活動。

表一// 紀念儀式與傷痛記憶博物館功能構成對比
傷痛記憶博物館將紀念儀式中行為模式和建筑模式有機統一,從意識和形式上將紀念儀式以博物館陳列展覽的方式長期保存與展示,可以認為是一種固化的紀念儀式。如果比較紀念儀式和博物館,我們可以發現紀念儀式的行為模式和建筑模式都可以在傷痛記憶博物館中找到對應的展覽要素(表一)。
1.創傷事件敘述
創傷事件的敘事通常是構成傷痛記憶博物館常設陳列的主體部分,通過各種證據再現創傷事件的發生過程來保存與展示傷痛記憶。與之相對應的是紀念儀式上常見的主題演講,一般都會包含對創傷事件的回顧。創傷事件的敘述是傷痛記憶作為集體記憶得以長期保持鮮活的基礎,對于創傷事件的敘述讓傷痛記憶博物館的展覽帶有強烈的敘事性。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開幕策展人約舒華·溫伯格(Jesajahu Weinberg)將紀念館稱為一座三幕劇形式的敘事博物館,從宏觀視角講述了納粹進行大屠殺的時代[9]。傷痛記憶博物館的展覽相對于創傷事件的敘事而言,并不像一般歷史博物館中歷史事件單純的呈現,敘述的過程事實上是對創傷事件發生的舉證和控訴。
2.靜思空間(Meditation space)
紀念儀式參與者通常在儀式主持人的引導下,在一定的時間內默哀表達對死者的敬意。觀眾參觀傷痛記憶博物館的過程通常是不受強制約束的,然而靜思空間卻以空間營造的方式,讓觀眾進入到靜默或靜思的狀態,達成與紀念儀式中默哀一樣的效果。靜思空間是傷痛記憶博物館區別于其他類型博物館的獨有空間,這個空間通常不做創傷事件的具體敘述,卻能讓博物館通過身體習慣控制加強傷痛記憶的保存。華盛頓的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和柏林的猶太人博物館(Jewish Museum Berlin)都設立了專門的靜思空間。
3.遇難者姓名的展示
遇難者姓名的展示是紀念儀式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可以說遇難者名字的呈現是紀念儀式合法性的基礎;同時,遇難者的姓名也是相關社群與記憶關系最為緊密的部分。姓名陳列的完整與列入標準是社區能否對傷痛記憶達成基本共識的標志。2011年9月11日,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十周年的紀念儀式上,遇難者家屬兩人一組逐一念出2977名遇難者姓名,在一邊的水池型紀念碑上,遇難者的名字被刻在76塊青銅板上。2017年改陳后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也保留了名字檔案盒的設計。
4.象征性展項
傷痛記憶博物館內的象征性展項與紀念儀式中的建筑模式有著相同的功能屬性。傷痛記憶博物館的建筑本身通常也被賦予象征意味,柏林猶太人博物館破碎、異形、沖突的建筑設計語言是這類博物館中最廣為人知的案例。另有不少關于傷痛記憶的紀念碑是直接與博物館共生出現的。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遺址上,巨大的兩座水池型紀念碑,以瀑布般的水流沖向深淵形成的負空間來象征消失的雙子塔。而在“9·11”紀念館內矗立的兩個巨型“三叉戟”,它們曾經是原世貿中心北塔外觀結構支撐的一部分,這已經不僅僅是一件單純的展品,而成為整個創傷事件的象征,是博物館內記憶觸發的中心,展項通過造型凝聚了傷痛記憶的情緒。
在文化記憶理論中,文化規則讓歷史發揮對回憶的鎮靜或刺激作用。傷痛記憶博物館展覽讓原本只在紀念日舉行的紀念儀式,通過建筑與展覽固化為全年不間斷的紀念。創傷事件敘事、建筑紀念形式、定期的紀念儀式,讓傷痛記憶博物館成為構成文化規則的重要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范圍內建立的猶太人紀念館就是對納粹大規模屠殺猶太人這一傷痛記憶固化的紀念儀式。紀念館相較于紀念碑有更強大的敘事能力,猶太群體回憶的中心轉移到了博物館上。從某種程度而言,傷痛記憶被博物館化的這一刻,就開始從集體記憶轉向文化記憶了。
三、傷痛記憶博物館促進裂痕彌合
如果說創傷事件的發生是社會裂痕的產生,那么傷痛記憶博物館的建立是對裂痕的承認和保存,也是防止裂痕擴大的重要措施。這里的裂痕發生在兩個層面上,一是“施暴者”群體和“受害者”群體之間的裂痕,二是受害者群體內部的裂痕。前者易于理解,造成傷痛記憶的創傷事件本身就是兩個群體間沖突的結果,這種裂痕在事件發生時就已經存在,在不加干預的情況下并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自動彌合。柏林猶太人博物館的建立,就可以看做是曾經的“施暴者”群體通過理性的認識和反思試圖彌補裂痕的一種嘗試。第二種裂痕的產生是由于創傷事件中不同的故事都想在歷史中爭得一席之地,人們為捍衛他們的故事而斗爭,這種裂痕在傷痛記憶博物館建立的過程中也可能出現。最初提議建立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是因為卡特政府希望通過建立一個紀念場以緩解當時比較緊張的美國政府與猶太社區的關系,但事與愿違,博物館的設計過程在最初選擇委員會代表時便陷入各方爭執的漩渦。猶太社區強調“大屠殺”(the holocaust)一詞只能用于二戰時期德國人針對600萬猶太人的屠殺行為,在他們的敘事中,猶太人是大屠殺的第一受害者(the first victim)。但是波蘭人、烏克蘭人為主的東歐社區則聲稱,那些死于大屠殺的500萬非猶太人同樣應該納入到紀念的范圍內。兩個群體針對“大屠殺”究竟應如何定義、博物館應如何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進行回憶等問題產生了長時間的激烈爭論。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建設也引發了亞美尼亞和吉普賽后裔的激烈反應。這些族群的領袖認為,如果發生在二戰的大屠殺應該被廣為紀念,那么之前的針對亞美尼亞人和吉普賽人的屠殺事件同樣應被紀念。而猶太群體不認為世界歷史中有其他任何一場的大屠殺能夠與猶太大屠殺相提并論。在經歷了長達15年的爭論后,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最終被確定為一個為所有美國人保存大屠殺記憶的場所[10]。前文提到在“9·11”紀念地設立的遇難者名牌,家屬曾就這些遇難者名字的排列方式提出各種苛刻的要求,名字排列的順序幾乎無法達成一致,最后設計師用計算機設計了一個極為復雜的算法才解決了排列的問題。可以看到即便是同為“受害者”,不同群體間也存在著裂痕。
遺忘當然也是一種彌合裂痕的方式,但這種方式是消極的,且在未來某個不確定的時間點,在某一個外力的作用下,這種被刻意遺忘的記憶仍然可能被再度喚醒,傷疤可能會被重新撕開。從南京大屠殺幾乎被遺忘的那30年可以看出,作為一種交流記憶的集體記憶并不穩定。這份記憶是否需要最終沉淀到整個社會的基石中,在當時是沒有那么確定的。文化記憶需要有專人來維護,傷痛記憶博物館正是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促進裂痕的彌合,是傷痛記憶博物館在記憶由集體記憶轉向文化記憶時期的新使命,符合為記憶尋找服務于當下意義的要求,保持了記憶的鮮活。當集體記憶轉向文化記憶,傷痛記憶博物館需要從兩方面來促進裂痕的彌合。
(一)引導群體認同的建立
對單一傷痛記憶的強調往往容易淹沒同一事件中其他受害者群體的聲音,從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建館過程中的爭論就可窺見一斑。在認可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中華民族建立集體身份認同的重要作用時,我們也要看到,2014年我國的國家公祭日設立后,雖然公祭對象包括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化學武器死難者、細菌戰死難者、勞工死難者、慰安婦死難者、三光作戰死難者、無差別轟炸死難者等七大類,但由于公祭活動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南京大屠殺巨大的影響力似乎淹沒了其他的公祭對象。官方和民間對記憶的認知存在偏差,典型例子是公眾對于慰安婦問題的認識。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曾報道了上海“海乃家”慰安所舊址的拆遷爭議,一些受訪者將慰安所等同于妓院,將慰安婦等同于妓女,視之為國家的恥辱。在這種撕裂的社會輿論中,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的開放有著重要的意義。
雖然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分館,但與主館洶涌的參觀人潮相比,前往該館參觀的人并不多。但這也說明建立慰安婦紀念館的必要性,它有可能糾正一部分人因傳統道德判斷導致的對傷痛記憶的認識偏差,同時也對今天的女性權利、性暴力問題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更重要的是紀念館以一種國家認同的方式積極引導群體認同的建立,促進對群體內裂痕的彌合。
(二)建立人類社會普遍的情感
在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網站上,人們可以查閱到多種語言的研究資料和宣傳資料,其內容不僅僅是猶太大屠殺或同一時期傷痛記憶的研究,也有對其他族群的關懷。可以看到,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不僅僅是在試圖愈合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裂痕,也關注到了其他的傷痛記憶,并將其列入到博物館的工作對象。
柏林猶太人博物館有一個由以色列藝術家瑪納什·卡迪詩曼(Menashe Kadishman)創作的名為“秋之落葉”(Fallen Leaves)的裝置。這個藝術裝置由兩萬多枚“金屬臉”組成,走在這條鋪滿貼片“金屬臉”的路上,腳下會發出吶喊一樣的回響,讓人感知那些如秋日落葉般隕落的生命。2018年,瑪納什·卡迪詩曼的兒子將“秋之落葉”藝術裝置中的四枚“金屬臉”雕塑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些“金屬臉”雕塑與其他當代藝術家的創作,共同表達著對創傷事件傷痛的關注和關懷。
“金屬臉”雕塑的捐贈和展出,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和猶太人大屠殺聯系了起來。雖然是兩個不同的事件,但人類共同的情感和基本的價值認同,讓觀眾能夠感受到共同的傷痛情感。這擴大了傷痛記憶的認同范圍,通過事件的鏈接,在彌合社區之間裂痕的同時,擴大了事件的影響力。這說明對和平的企望,避免類似慘劇的發生,是跨越國家、民族的共同期盼。從這些嘗試和努力中可以看到,建立一種人類社會普遍的情感,可以拉近不同群體間的距離,建立共情。在“秋之落葉”的捐贈案例中,南京大屠殺和猶太人大屠殺被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共同背景中,讓不同的群體成為記憶的共同體,期盼世界和平成為一種普遍共通的情感。
四、結語
我們仍然身處在一個傷痛記憶不斷產生的世界,對那些曾經造成社會嚴重裂痕的創傷事件進行紀念,對于不同的國家或者民族依舊有著現實意義。通過傷痛記憶的博物館化,集體記憶逐漸轉向文化記憶,傷痛記憶博物館成為建構文化記憶過程的重要一環。隨著裂痕的彌合,更大范圍的記憶共同體正在形成,而只有當更多的人成為文化記憶的一部分,認識到它的價值,這種記憶才能抵抗時間的洪流,長久續存。
面對難以言說的歷史,也許大部分的博物館扮演的依舊是人類文明豐碑的角色。但為了讓這些豐碑能夠名副其實地繼續矗立下去,傷痛記憶博物館所保存與展示的人類文明“負資產”,可以作出更為積極的貢獻。
[1]嚴建強、邵晨卉:《論收藏視域拓展對博物館文化及展覽的影響》,《博物院》2017年第1期。
[2]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EB/OL][2018-05-12]http://network.icom.museum/icmemo/about/aims-of-ic-memo/.
[3]孫歌:《實話如何實說》,《讀書》2000年第3期。
[4]Edward Linenthal.Preserving Memory: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s Holocaust Museu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11-12,19.
[5]朱成山:《國家公祭與南京大屠殺史第三次固化》,《日本侵華史研究》2015年第1期。
[6]〔德〕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頁。
[7]〔德〕揚·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0頁。
[8]同[6],第475頁。
[9]Jesajahu Weinberg.A Narrative History Museum.Curator:The Museum Journal,1994,34(4):231-239.
[10]同[4],第38—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