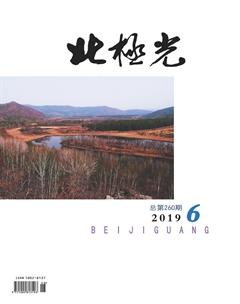歲月,母親之河(外二篇)
許瑤林
歲月,那是時間在人世間經歷了種種,而拼湊起來的一段段過往。
歲月,那是一只只從流光中飛出的螢火蟲,閃耀著,寂滅了,終歸于一方凈土。
歲月,那是一個個的生命流淌過的母親之河,而我,是這條長河上的一個孩子。是來承載時光和生命,被歲月照拂和送別的一個孩子。
而她呢?歲月,就似一架循環不息的水車輪,忘了盡頭,轉動不止。當無數個我經過這條臍帶,被送往現實的路途中,沒有誰能擺脫,從此與人世間結下一段段的緣。
歲月,又似一朵開在幽冥河邊的彼岸花,她送走了無數個我歸去后,又站在另一頭接引下一個我。如此,渡過去一個,又迎來了一個。
只是我,依稀模糊了那些關于我的一切。
歲月,恰似一聲來自產房的嘹亮啼哭聲,她點亮了一束生命之光,之后用長長的時間相伴,一個個生命的成長。
而我呢?只有當她送別的時候,才記起,原來我不僅僅是歲月的一個孩子!
夢歸故鄉
冷月如鉤,四野闃然。
在燈火闌珊的海灣一隅,濕地園林上寒煙籠翠,翠中流出一席青波,蕩漾起無邊的秋夜。
一如往日,兒子逛了整個屋子,搜刮完三床被子,又讓我搭把手往他的小床上放。見他堆疊得不欲樂乎,我便耐心地等他空閑。
又到了該講故事的時候,只不過這一次,我有點心不在焉。
“媽媽,講個故事唄!”忽然,嫩聲嫩氣的聲音從背后傳來,我嗯了一聲,情緒仍在意識外,只是慢慢地轉身。
屋里的光線如同黃昏時一般,是兒子用遙控器調節了燈光。我倦懶地問道:“今晚,想聽什么故事?”
“我要聽詩歌,詩歌里的故事。”
“好吧!”我別過頭,嘴里念了一首《鄉愁》。
待到我的話音一落,兒子不樂意地搖頭晃腦,撅起嘴,說道:“媽媽,把《鄉愁》改成鄭愁予的《錯誤》吧!要和昨晚上一樣,快樂版的。然后你再編一個江南故事。我特別喜歡那達達的馬蹄聲,很有節奏。”說完,他雙臂往床上一趴,翹起屁股昂首學馬叫。
這副可愛的小模樣倒是逗得我一笑,只是笑過后,心里酸酥酥,突覺得別扭。于是我說:“我給你講一個關于民國時期、戰亂離別的故事,但是,你要先跟我背《鄉愁》。”
我也不管他答不答應,就自己念了起來:“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郵票是什么?媽媽。”
“是你想我的時候,我又不在你身邊,你就用一張精美的小圖片貼在信上,代表你很想我。”
“那你想我呢?”
“我給你貼兩張郵票,不,更多。”
然后,兒子粉嫩的臉上禁不住流露出盈盈的笑臉。我接著往下念:“長大后,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
“新娘!那是愛情啊!”
“你長大了,也會有新娘。”
“我不要!”兒子說完,雙手捂著臉往被窩里一埋,又很快地側出半邊的臉說:“為什么新娘要在那頭?”
“戰亂年代的愛情,新郎是蒲公英,而新娘就是勿忘我,一個要飛向遠方,一個要守候等待。不過,你們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孩子,都是向日葵,應該熱情大方。”
“我不要愛情!太害羞了!”這一次,他將整張被子蒙住自己的頭和半副小身體,屁股依然撅得高高的。
“后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里頭。”隨之情緒一落,千頭萬緒又如流水倒灌回我的心窩。
“媽媽,墳墓里的人能跟外面的人對話嗎?”其實,當我念到這一句時,嗓子眼帶著一絲哽咽。經兒子打了岔,正好化掉我的尷尬。
“不行。”
“用郵票寫信呢?”
“不行。”
“那,用靈魂對話呢?身體里不是還有靈魂。”
“也不行。”
“總有辦法的,讓神仙幫忙捎個話。”
我硬氣地說:“神仙不管這事兒。”
“你不是神仙,你不能代表他們回答。”才六歲的孩子,競如此堅決地反駁我。
我頗有些動容,卻繼續說:“離世的人必須往生,沒有誰能停留不走。”
“離世是什么意思?往生又是什么意思?”
“離世就是離開這個世界,往生就是離開后再回來。”
兒子靜靜地低眉,片刻,他再抬起頭,一雙烏黑明亮的大眼睛沖我舒顏一笑。知子莫若母,見他一副了然的神情,我明白他肯定以為生命的一來一往,世事不遷,從未有任何改變。
夜漸深了,兒子把被子蹬開,眼睛卻盯著天花板,不見任何轉動,如此過了一會兒,他就合眼進入了夢鄉。我走過去拉過一張兒童被子,蓋在他身上。
走回窗前,未斷的思緒又將我再度拉至那一道淺淺的海灣,遠岸是香港。
童年的時候,我最盼望每年的大年初一。在爆竹聲中,兩扇叮鈴鐺啷的大門,一開一合,屋內簾子掀角時,便是滿堂大人小孩的歡聲笑語。最美的時光屬中午時刻,委實難得一見,定居在香港的親人回鄉了。一年就見一次面,見一次面不過半日光陰,雖然吃頓團圓飯便又道別,但是席坐間,觥籌交錯的相聚中,盡是一年美好的愿景。
如今我也遠在故鄉的千里之外。每當懷念起臨江的古街上一座座莊嚴林立的牌坊,古色古香的百年老店里賣出了潮州最具特色的小吃、古玩、手工藝品。一條開滿火紅木棉花的江邊長廊上,一側是勾欄重檐頂的城樓一字排開,一側是白浪滾滾的韓江水,而對岸山色秀麗,古樸端肅的韓文公祠坐落于此。江上一座“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廣濟橋,牽動起海內外無數潮州兒女的綿綿情懷,仿佛是一條割不斷的臍帶,系著這片山水鄉情。
罷了,罷了!不如就在今夜,讓秋來之風將我送走,飛回那日思夜想的古城,與無數的思鄉兒女一樣,陶醉在故鄉的夢里。
窗外,起風了!
糧食站
隨著氣溫驟降,透進的光是一片森冷灰白,氣氛越感壓抑,雖然沒到點燈的時候,卻不得不點起了一盞臺燈。
這時燈亮了,仿佛屋里的光也被吸走了,吸入到一塊暈黃色中,照在客廳的角落里,一張小小的書桌上。讓我聯想剄年代久遠的老照片,那花白的底沾了斑斕的黃,是嚼得出味道的記憶。
小時候家里窮,其實那個年代誰家不窮,也因彼此皆是一樣,人心倒是敞亮。街坊鄰里,有事也會相幫。
那些年每個家庭還派發糧票,這是在特定經濟時期發放的一種購糧憑證,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停止使用。當時我父母在離家十幾公里外上班,做飯的任務自然就落在我身上,每次發現米缸沒米,我便從一個鐵盒子里掏出幾張米票,攜上一個麻布袋,走過四條巷子,到一個小小的糧食站打米。
那是一間敞開四扇青漆木門的大街面,里面一排的人面壁而立,雙腳岔開,雙手拎緊一個袋口,抵在墻上嵌有的一個四方漏斗之下,白花花的米就從漏斗里滾滾落下。不一會兒,再重新換上另一排的人,仍舊以這樣的姿勢背對著大門。印象中在大門口,橫著一張兩抽屜的長桌子,桌子后面坐著一個盤頭的中年婦女,滿臉橫肉,目光敏銳。對遞過來的每一張糧票,她的動作是手一撈,放在眼底看個仔細,從不跟人多說話。
當輪到我的時候,這位婦女臉頰上的肉抖了抖,讓我莫名心慌,猜不懂大人的心思,我低下頭,趕緊往墻邊站。
由于我的個子小,米袋又沉,幾乎總是逃不過手忙腳亂的情形,甚至有一次把整袋米滑落地上。頃刻間袋里的米,漏斗滾落的米,全撒滿了地板。胖婦女見狀一聲大吼,只要在場空著手的大人全跑進來幫忙。大家用手捧,一邊捧一邊數落我父母:這么小的孩子,也沒一個大人來,米掉光了可怎么辦。 其實,米非但沒有掉光,還多了幾顆磕牙的沙石。往后我淘米就多了一個習慣,總要細細翻看一遍再放水去淘。至于那袋沉甸甸的米,畢竟我的力氣小,扛不回去,只好先挪到墻邊角落。胖婦女當作沒看見,繼續收她的票。
街坊鄰居認出了我家的米袋,順道也扛了回來。偶爾下早班的父母發現掛在窗戶前的米袋不見了,便尋到糧食站,在眾人的目光下,默默地扛了回家。
前幾日快遞員通知我,他把兩袋米擱在樓下保安室,讓我去取。我拎著兩袋米,可真重啊!
我掂了掂手中的米,半開玩笑地對兒子說:“你拎一袋,媽媽手疼。”
兒子瞪圓了眼睛,反笑道:“我這么小,這袋米都快跟我一樣高了。”
“你太夸張了。不幫就不幫,媽媽小時候總要幫家里打米的。”
“怎么打,拿棍子還是拿戒尺?”
“你那是打人。”我笑起來。笑過后,我瞥過一個眼神,用心道:“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事,物資極度匱乏,糧食實行統一收購、統一供應的政策。糧票是一種購買憑證,發到每家每戶,大家憑著手中的糧票到糧站購買。日子有計劃地過著,因為大家都窮,必須節省度日。”
“后來呢?”
“后來,改革開放了,市場經濟推動了整個社會進步,糧食局并入其他部門,我們現在買賣都是用錢,不再用票了。”
“那是什么票,長什么樣子?”兒子像聽故事一樣,充滿好奇。
我略思考,覺得無法用三兩句話描繪清楚,于是說:“等以后有機會,我找一找照片給你看。”
“媽媽,憑票就可以取米,當時國家得多有錢啊!那為什么不直接給錢?給錢,大家就不窮了。”
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問題。錢,從何而來;沒有經營,沒有創收,沒有儲蓄,溫飽尚且勉強,又何來富余。
常聽老一輩人說:這一代趕上了好時光,下一代的孩子們將更幸福。事實上這些孩子如同園子里培育的美麗花朵,陽光、雨水、土壤經過科學調配,多一分即減,少一分即加,優良的培育,唯獨少了一份磨礪。
我想到這里,沒有再說什么。恰好學校放寒假,我提筆在寒假守則里加一條:煮飯。
起初,在淘米的時候,兒子掉了一水槽的米。他不肯撿,認為米臟了,要丟掉。我不言語,卻一顆不落地全撿了起來,當著他的面又淘了一遍,放進鍋里一起煮。幾次之后,兒子已經掌握了怎樣不讓米順水流出來的方法,即使偶爾掉落,也會撿起來。當有一次,他吃著自己煮的米飯,忽然富有詩意地感慨:當硬邦邦的一顆小米粒,經過水的浸泡和電飯煲的加熱后,競散發出香味,軟糯香甜。
如今糧食站是特殊歷史的印記,早已淹沒在時代中。糧票作為歷史的產物,也成為一種票證文物,日漸被收藏者喜愛。而我無數次憶起那段童年,只是想從昏昏逐逐中,擺脫趨名逐利,獲得一份真實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