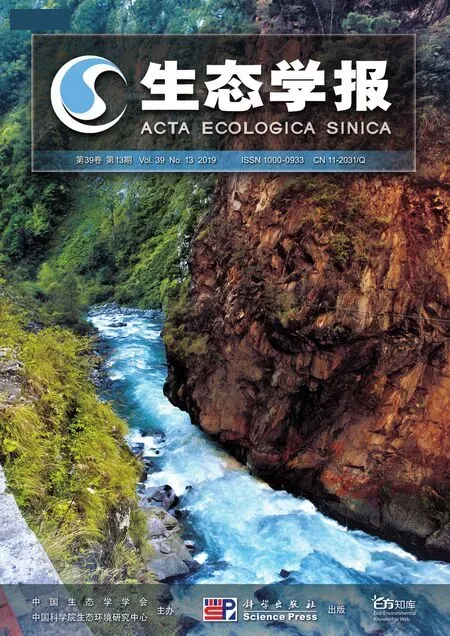贛江上游流域景觀生態風險的時空分異
——從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視角
趙 越,羅志軍,*,李雅婷,郭佳瀅,賴夏華,宋 聚
1 江西農業大學國土資源與環境學院,南昌 330045 2 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西安 710127 3 北京師范大學環境學院,北京 100875
生態風險評價是基于一種或者多種外界因素導致的可能會發生的或者正在發生的對生態環境產生不良影響的評價方法,其重點為評價人類活動在生態環境中產生的不良影響[1]。景觀格局表示景觀組分的空間分布特點與組合規律,體現著景觀的異質性與各類生態過程在不同尺度上的作用結果[2],通過研究景觀格局的變化及演替規律可獲知地區生態空間結構的變化特點,可用于對地區潛在的生態風險的綜合評估[3- 4]。土地利用/覆被變化是全球環境變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活動占優的景觀內,土地利用的方式和強度的變化對生態產生區域性和累積性影響,并且較為直觀的反應在生態系統的組織和結構上,可以根據土地類型結構進行區域生態風險評價,以綜合評估各生態影響的類型和程度[5- 6]。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國土生態-生產-生活空間的發展目標:“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這一空間劃分方法與國內外認可的生態-生產-生活“三支柱”理念不謀而合[7]。但當前對于三生空間的研究探討還處于初步階段,基于“三生”與土地利用主導功能的視角將三生空間理念與區域生態風險進行結合的研究較為缺乏。
流域生態風險評價與其他區域生態風險相比具有獨特的流域特征[8],在現有研究中主要采用景觀分析法對流域生態風險進行分析[9]。如許妍等[10]根據危險度、脆弱度、損失度3個層次構建流域生態風險評價模型對太湖流域生態風險進行評價;Paukert等[11]將土地利用與景觀結構進行結合,利用生態威脅指數對科羅拉多河流域的生態風險狀況進行評估;謝小平等[12]根據景觀脆弱度、景觀結構指數與景觀組分面積構建生態風險評價體系對太湖流域生態風險進行評價。以上研究成果對國內外流域生態規劃、景觀結構調整與優化、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提供了理論依據。本文采用由景觀干擾度及景觀類型脆弱度指數共同構建的景觀生態風險指數,并將“三生空間”的理念納入生態風險評價過程對流域生態風險的時空分布特征及空間關聯特征進行評估,通過空間自相關和半方差方法的研究生態風險的時空分布。以期為贛江上游流域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高效利用提供理論依據和參考。
1 研究區域概況
贛江上游流域位于江西省南部(113°54′—116°38′E, 24°29′—27°09′N),處于中國東南沿海向中部內陸延伸的過渡地帶,也是內地通向東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之一(圖1)。流域均位于贛州市境內,總面積約為35699 km2,占贛州市全域面積的90.65%,由章貢區、安遠縣等16個區縣構成。贛江上游地形復雜多樣,山地、丘陵廣布,地勢起伏較大。屬亞熱帶氣候區,降水充沛,熱量豐富,年平均降水為1573 mm,年平均氣溫為18.9 ℃,成土母巖主要為第四季紅色黏土、花崗巖等。土壤以紅壤為主、還有黃壤和紫色土等土類分布。由于近年來人地矛盾突出,各類開發建設項目增多,人類活動范圍擴大,導致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

圖1 研究區范圍Fig.1 Study area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及處理
1995年、2005年和2015年數據均采用監督分類與人工目視解譯相結合的方法對不同時期遙感影像數據進行解譯,采用隨機采樣的方式,將采樣隨機點分別與其實際類型進行比對,得出解譯精度結果,各期影像總體精度均大于83%,滿足本研究需要[13]。地形等相關因子由分辨率為30 m×30 m的規則格網數字高程模型(DEM)提取。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標準(GB/T21010—2007),并結合研究區土地利用的特點,將土地利用分類系統分為6個一級土地利用類型,分別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及未利用地等,和25個二級土地利用類型。土地利用功能可根據各自特點,結合土地利用類型劃分為農業生產空間、城鄉生活空間、林地生態空間、牧草生態空間、水域生態空間、其他生態空間六大類[14],如表1所示。

表1 土地利用主導功能分類
2.2 生態風險評價模型構建
景觀生態風險指數構建取決于區域生態系統受到外部干擾的強弱和內部抵抗力的大小。不同的景觀類型在維持區域生態穩定、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景觀格局自然演化方面的作用往往有所差異[15]。景觀格局指數將景觀格局信息進行了高度的濃縮,用于表現其結構組成和空間配置某些方面特征的簡單定量指標。結合前人研究成果[16],根據生態系統的景觀格局與生態風險之間的聯系,利用景觀結構指數、景觀脆弱指數建立生態風險指數的計算模型(表2)。基于網格采樣法,將研究區土地利用景觀格局進行5 km×5 km的網格劃分,得到采樣區1542個,并在此基礎上通過計算每個樣區的生態風險,以此作為每個樣區中心點的土地利用生態風險值。

表2 景觀格局指數構建方法
2.3 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GeoDa 5.1i軟件進行生態風險指數空間自相關分析,通過空間權重計算與Moran′s I指數計算,以得出研究區生態風險的空間自相關性。空間自相關分析用來檢驗某些空間變量在特定位置的屬性值是否與鄰近位置的屬性值顯著相關的算法,可以分為全局空間自相關與局部空間自相關[23],全局空間自相關用來研究變量屬性的空間相關性與規律性,而局部空間自相關更能展示生態風險的空間聚集,可以通過圖形的形式展現生態風險的空間聚集情況,通過空間關聯局域指標(LISA)分析生態風險空間格局,可分為高-高聚集、高-低聚集、低-低聚集、低-高聚集[24],全局自相關(式1)與局部自相關(式2)分別表示為:
(1)

(2)
式中,xi代表樣本i標準化后的單元標準值;xj代表樣本j標準化后的單元標準值。通過Geoda軟件進行Moran′s值的計算,并采用ArcGIS 10.2軟件進行LISA圖的制作。
2.4 半變異函數分析方法
地統計學與GIS相關技術的結合在空間分析的領域內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本文采用GS+7.0軟件進行半變異函數擬合,并建立擬合模型,反映不同距離觀測值的變化[25],假設采樣點數據變量符合二階平穩和本征假設,則半變異函數可以表示為:
(3)

2.5 主成分分析方法
生態風險演變的機理與其生態過程較為復雜,土地景觀格局的變化對生態風險的演變具有重要影響[27]。演變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生活、經濟等,常見的土地利用在人文方面的驅動因素有:人口、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結構等[28]。結合相關研究成果[29- 30]與本研究實際需要,從人口、經濟、城市方面選取了與生態風險演變可能存在聯系的總人口(X1)、糧食總產量(X2)、第三產業比重(X3)、第二產業比重(X4)、人均GDP(X5)、社會固定資產投資(X6)、公路里程(X7)、城鎮化率(X8)8個因子對其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獲知對研究區帶來較大影響的驅動因素。
3 結果與分析
3.1 土地利用類型演變
從各地類增減變化來看(表3),城鄉生活空間面積擴張迅速,其面積由1995年354.89 km2增加至2015年的546.26 km2,面積增加191.37 km2,增幅達到53.92%。農業生產空間面積減少,凈減少面積為121.76 km2,減少1.89%。牧草生態空間、林地生態空間面積逐漸較少,分別減少42.92、49.22 km2,占比分別為2.00%與0.19%,水域生態空間面積有小幅度的增加,由1995年的352.62 km2增加至2015年的375.42 km2,增加6.47%。其他生態空間面積較小,僅于1995年至2005年期間減少0.27 km2,減少10.93%,于2005年至2015年期間無變化。從轉移類型來看(表4),城鄉生活空間主要由農業生產空間、林地生態空間轉入;水域生態空間主要由農業生產空間轉入;林地生態空間中減少面積主要轉為農業生產空間、城鄉生活空間。
3.2 生態風險空間分析
空間自相關分析常常用來檢驗某些空間變量在特定位置的屬性值是否與鄰近位置的屬性值顯著相關,而在此基礎上的局部自相關研究更能體現生態風險的聚集特征,本研究以前文所得歷年生態風險指數為基礎,運用GeoDa 5.1軟件進行空間局部自相關分析。莫蘭指數常能用來研究區域的整體分布和空間聚集情況,但并不能展現空間上的相互聯系,故采用局部自相關LISA分析來探討研究區生態風險的相關程度和研究其是否具有空間聚集性。根據自相關分析,得到研究區1542個樣區1995年、2005年和2015年的生態風險局部自相關LISA結果(圖2)。
由圖2可知,贛江上游流域生態風險高的地區明顯集中于章貢區、南康區、信豐縣、興國縣、于都縣等地區的中心城區附近,形成高-高聚集,這主要是因為此區域海拔較低,城鎮化建設速度較快,工業化水平較高,交通較為便捷,景觀破碎化程度高。生態風險的低值區主要聚集于崇義縣、安遠縣、龍南縣等地區,形成低-低聚集,此區域海拔普遍較高,土地利用類型多為林地生態空間和牧草生態空間且分布集中,景觀破碎程度較低。1995—2015年,章貢區、南康區、信豐縣、寧都縣等地區高風險區分布范圍逐漸擴大,主要是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生活空間面積的擴大,景觀分離程度、景觀優勢度增大導致的。低風險區的范圍逐漸縮小,崇義縣、安遠縣、會昌縣等縣市的低風險區范圍變化最為明顯。主要由于人類活動范圍擴大,對林地生態空間、農業生產空間等分布區開發活動增多,景觀破碎程度提高,造成了低生態風險區面積的減少。

表3 1995—2015年贛江上游流域土地利用變化/km2

表4 1995—2015年土地利用轉移矩陣/km2

圖2 研究區生態風險局部自相關圖Fig.2 Local autocorrelation map of ecological risk in the research area
通過半變異函數的擬合來探討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空間變異特征,以更好地研究贛江上游流域的生態風險的空間屬性。通過對贛江上游流域生態評價指數進行半變異函數模型擬合(表5),結果表明1995年、2015年生態風險指數最適宜模型為高斯模型,其決定系數(R2)分別為0.982和0.963,2010年生態風險指數最適宜模型為指數模型,其決定系數(R2)為0.997,擬合效果均較好。塊金值(C0)用來表示隨機部分的空間異質性,而3期半變異擬合模型中塊金值均較小,分別為0.0020、0.0016與0.0023,表明在較小的尺度上,某種過程可以忽略。3期模型的基臺值(C+C0)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1995年、2005年、2015年基臺值分別為0.011、0.012、0.013,表明研究區生態風險最大變異程度穩中有升。1995年、2005年、2015年C0/(C+C0)分別為18.38%、13.59%、17.74%,表明說明在所選擇的5 km采樣間距以內,還存在一些小尺度的非結構性因素(如人類活動等)影響著該區生態環境的質量,但結構性因素(如地形、土壤等)仍然是該區生態風險指數空間分異的主導因素。

表5 土地利用生態風險指數半變異擬合參數
根據生態風險指數計算結果,通過密度分割法對其進行標準化處理和生態風險等級劃分,可將研究區劃分為5個等級[21,25- 26],分別為:低風險區(<0.3)、較低風險區(0.3—0.5)、中風險區(0.5—0.6)、較高風險區(0.6—0.7)和高風險區(>0.7)。以每個采樣范圍的中心點屬性值為基礎,借助ArcGIS 10.2中的地統計功能,進行普通克里格插值,形成4期贛江上游流域的生態風險空間插值圖。
由圖3、表6可知,高風險區的分布范圍與前文中高—高聚集區空間分布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主要集中分布于南康區、信豐縣、于都縣等區域;低風險區集中分布于崇義縣、安遠縣等低風險區。而1995—2015年間贛江上游流域高風險區、較高風險區與中風險區面積逐漸擴大,低風險區與較低風險區面積逐漸縮小,表明研究區生態風險逐漸提高。
3.3 “三生空間”用地轉型對生態風險的影響
區域的生態風險程度往往同時發生著改善和加劇兩種相反的趨勢,而“三生空間”的發展變化,影響著區域的生態安全格局。由表7可知,研究區“生態-生活-生產”空間呈現出顯著的生態、生活空間向生產空間轉移、生態空間向生產空間轉移的趨勢,而其轉移過程中必然發生景觀生態格局的轉變,從而影響引起區域的生態風險變化。根據研究區實際特點,并在借鑒相關研究的基礎上[14],采用土地利用轉型生態貢獻率獲知某一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所引起的區域生態風險等級的改變,從各類用地功能轉型的類別中選取轉型面積較大,轉

圖3 贛江上游流域生態風險等級空間分布圖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ecological risk grad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Ganjiang River Basin

生態風險等級Ecological risk grade199520052015面積 Area/km2比例 Percent/%面積 Area/km2比例 Percent/%面積 Area/km2比例 Percent/%高風險區High risk area1806.375.061902.765.332299.026.44較高風險區Higher risk area3462.809.703398.549.523798.3710.64中風險區Middle risk area6793.5219.036932.7519.426936.3219.43較低風險區Lower risk area11605.7432.5111273.7431.5811313.0131.69低風險區Low risk area12030.5633.7012191.2134.1511353.8531.81

表7 影響生態風險程度的主要用地轉型及貢獻率
型特征明顯的八類,用于研究其指數變化與貢獻比率。結果顯示:用地功能的轉型普遍造成區域生態風險的提高,其中城鄉生活空間轉為林地生態空間導致的生態風險等級提升的效果最為明顯,林地生態空間轉為城鄉生活空間,導致生態風險等級降低。林地生態空間轉為農業生產空間、農業生產空間轉為林地生態空間的貢獻比率較高,分別為17.90%與17.59%,土地利用類型的轉變導致景觀結構指數、景觀脆弱指數發生變化,使得原有較完整的景觀變得破碎,景觀生態風險增加,尤其是不規則的景觀結構變化最容易引起生態風險等級的提高。結合前文中半變異分析結果,結構性因素是引起區域生態風險的主導因素,非結構性因素則影響較弱,用地功能的轉型均為結構性因素與非結構性因素作用的體現。
3.4 流域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分析
為了增強數據的準確性和科學性,更好的反映生態風險與各類驅動因素之間的協調性,將指標數據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用以主成分分析研究,旋轉前后各因子的特征值、貢獻率和累積貢獻率如表8所示:當驅動因素特征值大于1時表明該因素主成分影響力足夠大,反之則表明其主成分影響力較弱。存在三類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對應的累計貢獻率為84.598,由此可知,這三類因子應為研究區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驅動力。提取的3個因子代表著8類因子的綜合信息,需要對其進行旋轉分析確定其代表因子,使因子載荷值向兩極端趨近,以明確各因子代表的含義。由表9可知,旋轉使因子載荷值向兩極端趨近更為明顯,可以用以綜合因子的命名。第一主成分代表總人口、公路里程、城鎮化率、糧食總產量與第一主成分呈最大正相關,表明以上因素是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人均GDP、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第二主成分具有較大正相關關系;第三產業比重與第三主成分正相關作用較強,第二產業比重負相關作用較強。上述分析表明,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變化受總人口、公路里程、城鎮化率影響較大,人類活動對土地利用格局的影響力度范圍不斷增強。

表8 驅動因子主成分特征值與貢獻率

表9 旋轉因子載荷矩陣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1995、2005、2015年3期景觀類型數據,構建基于景觀格局與生態學過程的景觀生態風險指數,借助半變異分析與自相關分析方法對流域生態風險空間變化特征及驅動因素進行研究,以揭示研究區生態風險時空演變特征與規律,結果表明:
1995—2015年間通過對贛江上游土地利用類型的統計分析,可知贛江上游地區土地利用類型中農業生產空間面積逐漸縮小,城鄉生活用地面積逐年增加,農業生產空間分離程度變大,城鄉生活用地分離程度與破碎度減小。表明贛江上游土地利用類型主要由生產空間和生態空間向城鄉生活空間轉化,土地利用程度提高。根據貢獻率分析結果顯示用地功能的轉型會引起區域生態風險的變化,不同的轉移類型貢獻率大小不一。通過空間自相關分析與半變異分析可知,高值-高值(H-H)聚集類型主要分布于章貢區、南康區、信豐縣等附近,低值-低值(L-L)型聚類多分布于安遠縣、崇義縣等附近,其高—高聚集區和低—低聚集區與高風險區和低風險區的分布范圍有較高的一致性。根據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分析結果顯示,人口的增長與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是驅動著土地利用類型變化的根本因子,總人口、公路里程、城鎮化率因素對土地利用格局的影響力度范圍不斷增強,而土地利用類格局的變化影響著區域的景觀格局變化,進而影響區域的生態風險。需要在未來的發展中注重對“三生空間”的協調和優化,科學規劃,避免土地利用類型和景觀格局的無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