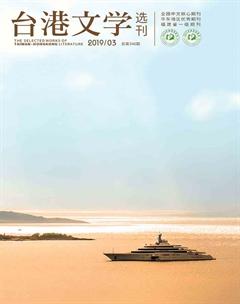最后的晚餐
林黛嫚

不知道為什么,當旁人向我道喜時,我一點喜悅的感覺也沒有,這是不正常也是不應當的。和男友交往多年,每一個階段都備受祝福,可說是在原該荊棘滿布的愛情路上穩健地走過來的。
真的,日子近了,我的一顆心卻仿佛進了死胡同,高墻遮斷陽光,陰森而微帶尿臊,著禮服、足登高跟鞋的我不知所措,是在那兒獨自啃嚙凄楚無助的孤單,等人來救,或是掀高裙擺自己闖回頭路?
今天像往常一般時間回到家(從前我喜歡“偷”個五、十分鐘回去,享受那種竊竊自喜及一點點慌憂的情緒)。父親得晚一點。冬還沒去遠,這個時間天色猶黑,我捻亮每一間屋子的燈,把黑暗的恐懼整個趕到外頭,讓它們結群去嚇唬晚歸人。屋子一亮,心底的那洼沉郁更顯明了。
持起鍋鏟,油在撲撲響著,父親在桌上理好一色色菜肴,等我把它們變成一頓晚餐。數一數,有六道。過年才用的細瓷碗和同花色的瓷杯擱在桌沿,我小心地挪近桌央,因為我曾經摔過三個碗、兩個杯子、一個大碗及咖啡器的上座。父親常在我下廚時聽見哐啷的鍋盤掉落或是“鏘”的清脆的破裂聲,他不會出來探看,穩穩地坐在躺椅上,兀自看他的報紙。只有那次,我摔破心愛的咖啡器,攤在眼前那碎得幾乎消失的玻璃,以及泡了湯的一餐咖啡,令我不禁哇哇大哭。他慌忙跑出來,甚至忘了擋住紗門,任它碰起一大響,然后迭聲安慰我:“沒關系,再買嘛,人沒傷到就好了。”我仍抽噎不止,他只好哄著:“別哭,別哭,我去買。”我收住淚:“百貨公司才有賣,南投這小地方,你到哪買?”一派他無知的語氣。滿地碎屑還是他掃干凈的。
我這樣的粗枝大葉,怎么為人媳婦呢?空心菜在熱油蓬起的一大叢白煙中翻兩下便盛起,無法與父親炒的那嫩嫩的翠綠相比,但它在我們上桌時早涼了,我總是忘了青菜最后才炒。

接著我要煎魚。
小時候父親是很有威嚴的,除了大姐,或是躲不掉的話,誰也不敢向他多說。記得最清楚,有一個月,我只對他說過一句話:“書法簿四元。”他抓起褲袋中幾個零角塞到我手里便算完事。他以為有多,其實只有三元五角,我不敢再要,跑去向大姐哭著討五角。升初中后輪我煮飯,但我只會炒簡單的青菜,碰到要煎魚,總磨蹭到父親不注意,去央二姐幫忙。一次被撞見了,他吼我一句:“長這么大,魚都不會煎!”惹得我眼睛紅了,水光泛上,滴溜溜的淚就要滑下來,然而那淚畢竟不敢落。
現在魚都是他煎的,他怕我燙到。我會在幾天豬肉、牛肉替換之后,說一句:“想吃魚?去買啊!”不僅煎魚,像剁雞肉、削結子菜、切長年菜、腌菜心等都是他的工作。
魚在油鍋中淋淋撈起,為了煎熟它,我放多了油,倒像在炸魚。父親為何會在這個節骨眼擺上一條魚讓我煎呢?是要我練習,要我體會主事的難,或是不讓我這最后一餐輕松打發呢?也許他在提醒我他的煎魚歲月,也許他要讓魚挪走我一些悲戚的情緒。他再不能為我煎魚了。
在我發愣的當頭,剛起鍋的魚停止皮下滲油的冒動,漸漸冷卻硬掉,原本金亮的魚皮,也變成滲冷起皺的土黃,看起來一點胃口也吸引不了。我嘆了一口氣,繼續做菜。
我把筍片放在一鍋水中沉浮,再把魷魚芥菜一塊兒在大火中炒幾下,直到平扁的魷魚片卷成一團便罷手,不再理會余下的菜,往日那種整治好珍肴后的倦怠感又盤據心頭,我根本不想張嘴來迎接食物,這些盡夠父親吃了,又何必制造剩菜的麻煩?
母親還在的時候,家中的剩菜剩飯都倒在一個餿水桶中,有養豬戶來收取,后來那個養豬戶不來了,她說我家的餿水不油,豬不吃。是啊,那時能倒在里頭的不過是稀飯、洗米水或是配菜的佐料,罕少的魚、肉每餐皆刮得干凈,剩下湯汁拌飯喂貓狗,盤子給狗舔得似洗過,哪有食余可入餿水桶?只好把殘羹往垃圾桶、水溝倒,在母親享福不到的歲月里,殘肴隨著經濟好轉變豐盛,有時剩得太多,倒得人心驚肉跳,怕遭雷劈更怕挨父親罵——父親時常要在我們面前數算苦難歲月的艱辛掙扎,他怎容得如此暴殄天物!
電鍋的一聲響,提醒我飯煮好了。我看著這個用了好多年的十人份大電鍋,跟父親提過換了吧,他總是搖頭,“還用得著哪。”姐妹們嫁的嫁,外出求學或是謀職,接著也是要嫁人啊,他知道的,這個電鍋不過是維系住他渴盼兒孫承歡膝下的心愿。我既然了解便不再勸他,但這個電鍋制造了不少剩飯。他會在我洗罷碗后,把殘肴拿去喂狗或倒掉,他現在的觀念是,失了味的食物吃到肚里沒什么好處,尤其我有副挑剔的胃,不新鮮的食物一概抵制。他也許以為自己年紀大了,便是遭雷劈也不算枉死。只是雷公看到他那發白、背駝和手腳上靜脈嚴重浮凸的模樣,可還忍苛責?
飯菜都上桌后,父親回來了,接續起我不打算完成的工作,尤其是一盤雞肉,一會兒工夫已在室內漫起濃重的香味。我心底喃喃念著,我過去后難道會缺肉吃嗎?我再好吃肉,這個時候還吃得下嗎?我……汩汩的淚悄悄潺潺地流。
溫好的紹興酒在瓷杯中靜靜等著,叫人看了喉頭便起一陣滑膩的酒香,它可以使我心底的沉郁醉去,不再來影響我,因此我把杯子握得好緊,緩慢地把酒往肚子內澆,然后眼中看出去的世界就變得迷離,一切仿佛都套上白紗,而且輕微搖晃著,很美,很不真實的美。
父親應該皺眉的,我弄了多么糟的一餐飯;他應該只動那盤雞肉的,但它擺在我前面,也慢慢冷了,和其他菜一樣不好吃了,我才突然迅速夾一塊,父親以為要給他,把碗閃開,我卻放進嘴里,好苦,一股冷腥味,嚼得急了嗆到,猛烈咳嗽起來,眼淚、鼻涕都下來了。他盛一碗湯放在旁邊,繼續慢條斯理地扒飯。他總是這么細心,知道我怕窘,便輕描淡寫讓事情過去,這么一想,禁不住的辛酸也乘機伴著淚涕流泄出來。
他有心臟病,要是哪天發作了沒人照料;他的朋友愛灌他酒,他去年才因而住院的腎禁不起過量,沒人替他擋酒了。誰幫他洗衣服?誰陪他看新聞?誰幫他挑錄影帶?誰……這些問題一個比一個可怕,我想得驚起一身冷汗,連日來蘊積的不耐、煩躁、擔憂、哀傷的情緒便爆發了。
“我不要嫁了!”真的,我是那樣堅定地、孤注一擲地、很大聲地吼出來。
然后我和他一起笑了。剛喝的酒在這一陣翻攪之后化成汗,紅潤逐漸漫散,我有點餓了,開始吃剩下的菜,邊吃邊叨念:“天,這么難吃。”“太咸了。”“肉這么硬!”唯一幸免的是使我嗆到的那盤雞肉。如是,我竟然把菜全部都吃光。父親夸張地把眼睜得、嘴張得都像個O形,說:“你這么會吃,還好嫁掉了,要不然老爸被你吃垮!”我們又笑了。笑得很開心。
飯畢,先前的問題、愁結又回到心上,但那是躲不掉且終會解決的,我相信父親也為這些問題困擾著,只是他知道,單是想并沒有用,我們能做的,便是愉快地吃這最后一餐。我終于做到了。
(選自臺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我的父親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