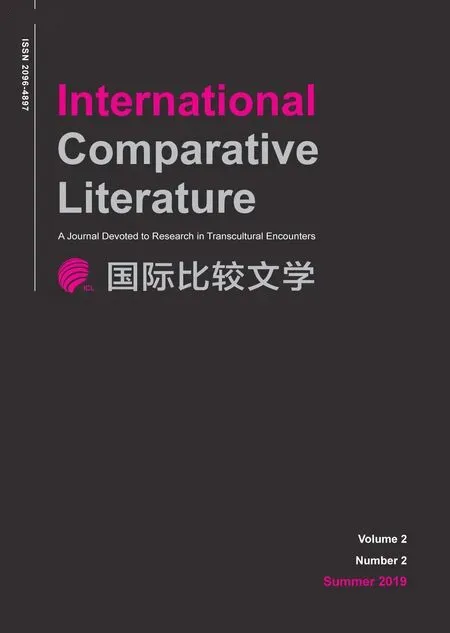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域和方法論
——楊慧林教授訪談錄* #
楊慧林 中國人民大學
吳劍 上海師范大學
時間:2018年5月19日上午10點至12點
地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楊慧林教授辦公室
錄音整理:吳劍(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生)
吳劍(以下簡稱“吳”):楊老師,您好!這次劉耘華老師帶我們來北京,跟您做個訪談,主要是想請您結合自己的研究工作,談談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理論和方法方面的問題,大概有七到八個問題。
楊慧林(以下簡稱“楊”):好。
吳:我們知道,您現在主要做比較文學和神學方面的研究,但您以前給人的印象是做外國文學研究的。請問您是怎么從外國文學研究轉到比較文學研究的?
楊:我讀書的時候,都是在中文系和哲學系,沒讀過外文系。碩士研究生讀的是西方文論,做過一點有關莎士比亞的研究。當時年輕氣盛,曾經跟我的老師趙澧先生說:中國的莎士比亞研究有很多東西其實都不需要做,因為西方已經做得很細了,我們討論的那些問題都有大量的西方文獻,我們想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入門級的,有必要再說一遍嗎?如果真做的話,我自己覺得必須有兩個跨度,一個是400年的時間跨度,另一個就是中國和西方的文化跨度。趙先生說,你這想法雖然有點狂妄,但是這么想是不錯的。
如果做莎士比亞的研究,中國人未必不能在有些方面比西方人更敏感。比如,莎士比亞作品中有關宗教的問題,在西方人看來可能自然而然,但對中國人來說就更值得追究。耶魯大學的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基本興趣就在于莎士比亞和圣經研究,最近有位博士生專門研究布魯姆的理論來源靈知派,由此進入文學研究與基督教神學,可能會比較有趣。這就是最初的想法。

劉耘華(以下簡稱“劉”):可以說它們本來就是一個東西,或者說一個東西的不同側面。
楊:是的。
劉:只是我們以前關注的焦點有點差別而已。
楊:所以后來我讀博士的時候,就直接選擇了宗教學。當時方立天先生是我的導師,方老師做了一輩子的佛學研究,我總覺得自己的選題也應該與佛教有點關系,何況我這名字“慧林”本來就是和尚的名字。而方老師卻說:你要是還想做基督教神學,就繼續做,沒有問題。這些老先生們的寬容,不光體現在為人處事上,在學術上同樣如此。他們并不需要學生跟老師做同一個東西,也不在乎什么所謂的師門傳統。而是希望幫你找到一個更有發展前途的學術空間,然后支持你去做相關研究。這一點讓我印象至深,而且特別受益。
吳:您以前接受梁燕城采訪的時候曾經說過,相比于基督教的神學解讀,您更喜歡文學家的解讀,還說總想把基督教神學的話題還原為人文學的話題。您覺得神學和人文學究竟是什么關系?請您談一談。
楊:這是一個好問題。我一直希望人文學者能與神學家更多地對話,這在西方其實是很普遍的。對后世影響最大的神學,幾乎無一例外地超越了教會神學的框限,與人文學的問題領域、人文學的學術話語息息相通、相互交集。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如果抽離信仰的背景,或可說系統神學就是人文學。對一些宣教式的神學,人文學者可能沒什么興趣。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就連禮儀神學其實也不僅僅關注教會內的禮儀傳統,而是必然涉及其中的符號意義和文化衍生。比如liturgy(圣餐儀式)本身,既可以說是dramatical liturgy(戲劇性的儀式),也可以說是liturgical drama(儀式性的戲劇)。關于禮儀神學的人文學討論,可能會給傳統神學帶來沖擊,但同時也是很大的啟發。
有人提出過一個問題,說西方的古典學在荷馬研究方面基本上都是做辯護,在《圣經》研究方面卻基本上都是做批判。比如根據研究者的考證,《約翰福音》的作者根本就不是約翰,摩西五經的作者當然也不是摩西。但是從根本上說,無論古典學還是“釋經學”,并不是要顛覆古代文本,而是從不同側面揭示文學研究中的Canonization(經典化)問題。《圣經》同樣是通過“經典化”的過程才成為一個Sacred Scripture(神圣的文本)。所以人文學研究的批判性常常是建設性、而不是顛覆性的。這就是為什么神學家特別需要人文學的資源,也需要人文學的視角和方法。
反過來,人文學也需要神學。我曾經跟耘華老師說過,神學對人文學最重要的貢獻,可能就在于它獨特的方法和邏輯。這在詮釋學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它把詮釋學的問題逼到窮盡的時候,恰恰又提出一種詮釋學的解決。比如談文本的豐富性,你怎么看我怎么看都沒關系,一千個人可以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在信仰的問題上這可能是不行的,神學的詮釋學沒有退路;而沒有退路如何還能談這個問題,這就有趣了。所以,不同領域的相互激發是絕對必要的。西方有一本《法律與文學》,早就翻譯過來了,有很多法學領域里的人在閱讀。我們以為法學研究者不怎么看人文學的書,以為他們主要看案例什么的,其實不然。這本書真的是被法學家們視為名著,我手邊有這本書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是人大法學院的學者送給我的。
劉:今年我們學科引進了一個千人計劃專家湯晨曦,是中國人,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德語文學系主任,很年輕,專門做法律與文學的研究。他上次來上海師大作的一個演講很有意思。法律與文學的話題在西方很熱門。
楊:確實是這樣。又如我們的外國文學史會講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西方文論史可能涉及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而《論法的精神》則是法學領域的經典。
吳:在比較研究的方法論方面,您覺得有哪些值得我們進一步拓展的地方?
楊:我認為比較研究是一個特別有前途的學術空間。無論在學科意義上怎么看它,這個學術空間一定會影響整個人文學的學術品格。但是與之相關的一些方法論的問題,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思考。我覺得中國學者需要做的,可能是通過比較研究找到一種工具性的概念,而不只是停留于描述性的概念。真正具有解釋力的思想工具到底是什么?我覺得,許多當代思想家的路徑可能不同,落點卻可能正在于此。比如海德格爾所討論的Ereignis,被分別翻譯為“本有”“成己”“事件”“自在發生”等等,但是很難幫助中文讀者理解海德格爾的意思,另有“緣構”的譯法倒可能比較切合人與存在的“原初共屬”;海德格爾所謂的“人思索存在時,存在也就進入了語言”,亦可作如是解。“緣構”當然也需要解釋,比如什么是“緣起”之緣,什么是“構建”之構。但是無論如何,這樣的解釋有可能在中西之間激發出一系列“緣構性概念”的思考,比如相互性(Mutuality),關聯性(Correlation),對極性(Polarity)等等。這都是Comparation(比較)的題中應有之意,目前的討論還遠遠不夠。在西方,最為典型的例子除去海德格爾還有法國哲學家巴丟(Alain Badiou)……
吳:您的文章中還提到過齊澤克(Slavoj ?i?ek)。
楊:齊澤克來過人民大學,跟他聊天挺有趣的。很多人不喜歡他,覺得他寫東西可能太快了,但是我覺得這個人絕頂聰明,他能敏銳地把握住當代西方哲學里面最重要的東西,然后把它變成自己的討論。
吳:您剛才提到的“事件”或者“緣構”,都是他們在討論的。
楊:是。這些東西翻譯成中文以后,有時候光從字面上沒有辦法去了解它的意思。其實最簡單的說,它是動詞性的緣構,而不是名詞性的描述。它和中國的很多思想資源,是可能有所碰撞和激發,并且得到重新解釋的。我甚至認為,這種productive(生成性的)而不是descriptive(描述性的)的解釋工具,在中國古代思想里可能更豐富。
吳:是的,劉耘華老師做的關于關聯思維的研究,和您說的可能有一點類似。2017年您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那篇文章,側重于談“發生”的問題,文章引用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骰子一擲絕不會破壞偶然》,提到了巴丟對“發生”的看法: “除了發生,什么也沒有發生,也許只有,一種關聯”。巴丟的這句話大概就是他對Ereignis的一種理解。
楊:那篇文章比較短,關于“發生”的問題,還有很多內容沒有寫在文章里面。巴丟對“發生”還有很多解釋。他有一個想法我覺得特別有趣,就是predicative descriptions are sufficient(謂詞性描述是自足的)。什么是“謂詞性描述”?其實就是那些緣構性的動詞。由此才可以理解為什么“存在”就存在于“是動詞”(the verb ‘to be')的表達之中,“事件”的根本為什么就在于“發生”。這些東西又跟神學有關。因為海德格爾的“存在”直接出自《出埃及記》的“我是我之所是”(I am what I am),海德格爾的“事件”又可以通過奧古斯丁追溯到《啟示錄》的“今在、昔在、永在”(The grace is from him who is,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who is,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就是奧古斯丁說的現在、過去和未來三個時間,表達這一時間的卻并非時間,而是“謂詞性描述”的三種時態。其中的關鍵在于:我們無法表達什么是“時間”“存在”“事件”或者“上帝”,“是”或者“發生”式的“謂詞性描述”卻恰恰給出一種“緣構”,是為“自足”。
劉:所以叫做Ereignis,他用的是名詞,其實他表達的是動詞。
楊:跟“事件”是一樣的。事件(Event)本來是個名詞,卻有西方學者認為其根本在于動詞的性質,所以用作eventing,甚至把God(上帝)也這樣用,成為Godding。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就叫《名詞的動詞性與動詞的交互性》。
劉:關于Ereignis這個詞,還有人翻譯成自生自成、大道、本有、本是、緣構等等。
楊:有很多翻譯。如果不加解釋,它的意思可能會被淹沒掉。比如“大道”在漢語里的原本意思很難對應于海德格爾的討論。
劉:您的意思是,這樣一個工作性的詞匯,其實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楊:是的。
劉:把所有東西都聚攏。
楊:有時候需要這些工具性的概念,作為一個入口。
劉:這樣就把我們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并置于哲學或者神學的思考,并置于同樣的思想平臺。
楊:我確實有這樣的想法。其他的研究方法當然也很好,但僅僅如此恐怕是不行的。
吳:您的文章中的有些詞匯,Correlation,相互關應,還有Constellation,您把它翻譯成關聯,它們不是實體性的概念,也許從其中可能會生發出新的工具性的概念吧。
楊:如果進一步追究,也許可以看看巴丟自己對“事件”的解釋,從而就可以理解他是怎么讀馬拉美的詩。我覺得一個哲學家讀詩跟一般的文學欣賞真是不一樣。馬拉美那首詩,幾乎從來沒有被人讀明白過。我給北大學報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想核對一下原文,于是孟華老師從巴黎大學圖書館把法文版、英文版的pdf文檔都發給我了。她說又順便看了一下,覺得這詩真不是寫給人看的。確實沒法看。好在法文版、英文版都有很多注釋。巴丟可能看過那些注釋,但是他的引申跟那些注釋沒什么關系。我覺得巴丟在引用馬拉美的詩句時真是一語中的,把最有哲學味道的東西一下子抓出來了。他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句話,他引用了很多次:除了發生,什么也沒有發生。這里的“發生”與一般的文學讀解大有不同,而是融入了巴丟的哲學,也跟海德格爾等人的上述思考有關,簡單說就是predicative(謂詞性)。
吳:這和語言學里面的performativity,有人譯成“述行性”,是不是有一點關系?
楊:有關系。很多人翻譯成“述行”,我有時候還是把它翻成“行為性”。因為德里達討論宗教的時候,經常用這個概念,performativity,或performative event什么的。翻成“述行”,我覺得譯者也是盡量想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但如果聯系到上述的一系列討論,說到底就是predicative,謂詞性,動詞性,行為性。
再說一句,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其實我們所能把握的也許只是工具性的概念,而不是工具性概念推導出來的任何結果。工具性可能推導出結果,在《圣經》里面就是上帝,在海德格爾哪里就是存在。但是什么才是上帝,什么才是存在?按照《圣經》的說法:不可妄稱上帝之名;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是存在。我們所討論的其實是上帝和存在是如何生成的。這就是圣經里面的那個“我之所是”的表達。為什么不能妄稱上帝之名?希伯來文的雅赫威(YHWH)里面沒有元音,是讀不出來的。這個YHWH到底什么意思,說實話沒有人真正知道。但是人們認為它在古希伯來語里面就是“是”。上帝從來不說“我是上帝”,而說我是“我之所是”(what I am),YHWH那四個字母,就是“我之所是”。借助這一類思想工具,應該可以在比較文學領域激活很多資源。
劉:您講的海德格爾理論中的“predicative”,我覺得他特別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認為一個東西(thing/being)要出來,要呈現,讓自己是其所是,要同時通過肯定和否定、遮和顯的相互作用,一個東西要把自己亮出來,同時把沒有亮出來、被遮蔽了的東西也帶出來了,換言之,“顯”就是“去-蔽”。它把否定和肯定的那種動態的關系揭示得比較好。他認為只有通過詩歌或繪畫,才能做到這樣。
楊:對,無法顯現的東西,往往是通過藝術得到一種顯現的形式。自古以來,哲學家和文學家最后的交匯點可能都是這樣。另外,海德格爾這些東西如果讓耘華老師來解釋,你就會發現中國古代資源太豐富了。佛教的相關討論也極為深刻。比如《心經》有言:“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后來吉藏用“八不”講解“中道”,即: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去、不來。總之,西方哲學中“在”或“不在”的問題被轉換為“緣起”與“性空”的問題,轉換為生與滅、斷與常、一與異、去與來之間的關系。如果能用現代的哲學方式和邏輯工具重新解讀,可能才更有意思。
吳:楊老師,您的著作《文學與神學的邊界》里面談到過邊界的問題。我們知道,現在每個學科都有核心或者軸心,都有自己的個性。那么我們做跨學科的研究,就面臨一個怎么處理學科邊界的問題。請您就這個方面談談看法。
楊:我們現在談的是“邊界”和“跨”這兩個概念的關聯。那么這個邊界是到底是什么?有的時候,也許就是為了“跨越”,才有了“邊界”。大概跟剛才說的不一、不異、不去、不來有點像。其實文史哲的相互交融,無論在中在西,自古而然,沒有問題,后來突然都變得有問題了。談到跨越的時候,讓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在英國訪問,發現他們很多大學的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根本不是文史哲之間的跨越邊界,更不是跨越文學里面的八個二級學科的邊界。它是跨越文學和自然科學、哲學和自然科學,這才算跨。這當然未必就是對的,但是其中包含著一種有趣的暗示:就人文學而言,某些人為的界限本來并不需要刻意持守,更不必執著于自己跑馬圈地的學科領域。
在中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被劃入中國語言文學以后,可能也對中國語言文學傳統的學科邊界構成了某種挑戰。相對而言,我更覺得比較文學是一個問題領域,也引入了獨特的研究方法。而這種問題領域和研究方法的意識,對于文史哲相關學科的研究都構成了別具意味的啟發。邊界的存在可能就是為了讓你在邊界處游走,在邊界處體會和吸納不同于自己的東西。這可能是另一層意義上的相互性、關聯性問題,也是比較研究中最有意思的東西。
吳:楊老師,您曾經主編過一套人文學科關鍵詞的叢書。以往的關鍵詞研究,有一種做法是把它看成觀念史的一部分,研究在某個觀念或術語的生成、建構、擴張和變異等歷時性的演變。您這套叢書的做法似乎和它不一樣,您顯然有自己專門的考慮。請就此談談您的看法。
楊:人們通常會把關鍵詞放在一個比較具體的概念層面來界說。比如反諷啊,象征啊,或者其他什么。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反諷不只是一個具體的反諷概念,而是從古希臘以來的、通過反諷得以顯示的一系列思想模型。象征也是一樣。如果作一個更寬泛的理解,那么象征可以說就是一套符號的結構,一套符號的邏輯。如果這樣去討論問題的話,我覺得這樣的關鍵詞也是一個問題領域,可以在其中串聯思想史的相關內容。這可能是當時的主要想法。這些關鍵詞都可以做細致、具體的解釋,也可以引出發散性的討論。發散性討論更多關注的是一個問題領域,而不只是某一個概念。這也是我覺得可以用productive和descriptive區分兩種概念的原因。descriptive是具體的、描述性的界說,但是productive則是開放的、生發性的。關鍵詞研究之所以能把相關的思想資源串聯起來,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學科領域里討論問題,我覺得可能都跟這種productive的性質有關。
吳:關于經文辯讀,按照西班牙的宗教學者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的觀點,在當今時代,我們需要從歷時性的解釋學轉向跨文化的、共時性的解釋學,也就是從一個文明傳統當中的、從古到今的、歷時性的解釋學(diachronical hermeneutics),轉向跨文化的、跨區域的、歷地性的解釋學(diatopical hermeneutics)。您做的經文辯讀工作,和這種跨文化的解釋學在旨趣上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請問您是怎么進入經文辯讀活動的?
楊;經文辯讀的緣起是比較偶然的。英國當時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他現在已經退位,回到劍橋大學當教授去了。威廉姆斯曾經來華訪問,他回國后開始組織中英對話的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會議的地點就在坎特伯雷主教的駐地蘭貝絲宮(Lambeth Palace),安排我回應劍橋大學的大衛·福特教授(David Ford)的發言。當時福特正在做Scriptural Reasoning(經文辯讀),他把那本書里面的第八章發過來給我看,我看完了以后覺得特別有意思。后來我就從他那第八章里提煉出來了十個主要命題。有些神學家覺得這有點太激進了,提煉出來以后福特教授自己都有點吃驚,但是我覺得非常了不起,甚至可以說是革命性的。
福特教授等西方學者推動的經文辨讀,是基于同屬“亞伯拉罕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獻。而中國可能與之相關的最大資源,就是傳教士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翻譯和詮釋。這方面的文獻如果放到這個大傳統里面就更有意思,因為所有的翻譯其實都是詮釋,傳教士的翻譯和詮釋則是立足于基督教的理解系統。這些工作從來都面臨兩方面的批評。一方面的批評是可能來自一些中國學者,說你們根本就是用基督教的詮釋學來糟改我們;另一方面來自他們自己,說你好好地干你的傳教工作就得了,結果你們最后都是給中國人當傳教士,把中國的經典介紹到西方。這兩方面的批評交織在一起,正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理論場域和研究空間,而且資料極其豐富。福特教授他們聽到后特別興奮,后來就專門來了兩次,到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央民族大學。接下來英國國王學院在倫敦組織了一次會議,讓福特教授回應我的發言。我們又在Scriptural Reasoning的基礎上組織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比較文學與經文辯讀”專門委員會;后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在巴黎召開年會,我們組織了一個專題圓桌會議。包括吉萊斯皮(Gerald Gillespie)在內的幾個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前幾任主席,都對這個事很感興趣。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請過宗教學界的人參加比較文學的會議,就是西方的宗教學者也沒有請過。參加這次會議的彼得·奧克斯(Peter Ochs)來自弗吉尼亞大學,奧利弗·戴維斯(Oliver Davis)來自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大衛·賈斯珀(David Jasper)來自格拉斯哥大學,司馬懿(Chlo? Starr)來自耶魯大學,他們在宗教學領域都很有影響,但是從來不參加文學的會議。這次會議以后他們都覺得比較文學還是挺有意思的,跟純粹的宗教學討論很不一樣,雙方都能有所收獲。
吳:請問經文辯讀工作現在推進到什么程度了?還在繼續嗎?
楊:還在做。前年我曾去耶魯大學開會,除去美國學者之外,參加會議的中國還有張隆溪、游斌、來自臺灣的曾慶豹等。會上的許多發言都與這個話題相關,會議組織者之一就是耶魯大學的司馬懿教授。她與中國學界的交往很多,對經文辯讀也有相當深入地了解。去年耶魯大學出版社為她出版了一本新書(Chinese Theology: Text and Context),起初我并不知道,后來看到這本書大吃一驚,因為里面有一章是寫我,并且特別提到在中國研究神學的人,有一種Card-carrying CCP member(或可直譯為“有黨證的共產黨員”)。后來我跟她開玩笑說:中國共產黨好像從1949年以后就不用黨證了,我還真不是Card-carrying。好在那一章的副標題是an academic search for meaning(對意義的學術追尋)。我想這就是她對經文辯讀以及中國學者相關研究的理解。
吳:我讀過您發在《中國社會科學》上關于《經文辯讀》的論文,這篇文章將老子的“虛靜”“虛心”與《圣經》里面的“虛己”“自我清空”等相互參照,讓中國思想跟西方思想產生連接。您能不能結合您的經文辯讀的實踐,談談我們該選擇什么樣的路徑,采用什么方法來進行經文辯讀?比如從傳教士的翻譯文本來進入。
楊:我先說明一下,為什么我覺得理雅各的《中國經典》譯本是一個最有意思的文本,因為它的注釋太豐富了。有很多譯本,翻譯就只是翻譯,注釋并不多。但是理雅各的翻譯完全不同,在他的書里,我甚至覺得最大的價值不是翻譯,而是那些注釋。他的注釋有兩個基本的參照,一個就是他自己的西方神學背景,還有一個就是他所能看到的中國注疏,比如朱熹等等。畢竟他身邊有王韜這類人給他提點,所以有很多中國古代文獻他都看過,我感到挺吃驚的,現在的人都未必能看那些材料。
吳:理雅各能夠體會到一些細微的差別。如果他覺得某個地方跟西方的或基督教的理解不一樣,跟他的價值觀念不一樣,那他在作注或者翻譯的時候,就會直接指出來,或者給以反駁。
楊:他在翻譯《四書》的時候,提出的質疑和批評相對較多。翻譯《道德經》的時候,他做的關聯性的讀解可能更多。當然,他翻譯《道德經》是比較晚的時候,譯法包括格式都不一樣。他翻譯的《道德經》是很有味道的,里面確實太多的可能性,能把中國古代思想和基督教神學建立某種關聯。虛己(kenosis)的那個說法,肯定會有人不同意,說這個基督教的虛己神學怎么跟虛空啊、虛靜啊放在一起。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沒辦法說原文是不是跟這個有關,而是事實上它已經被建立了關聯。我們能看到的,就是在這種事實關聯的基礎之上,考察它是如何被關聯起來的,是不是還有可能進一步闡發。我覺得理雅各這種闡發特別重要,其中也包含著某些工具性的概念,具有剛才說到的productive的意義。比如現代人將“韜光養晦”理解為“隱藏實力、等待時機”,反而是理雅各提出過更積極的解釋。理雅各為什么能從“韜光”看到“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的深層含義?簡單說,就是因為他沒有把“韜光養晦”放在后世越來越“權謀化”的背景,而是將它回溯到中國的古代智慧。
吳:這對我們加深對中國古典的理解也有幫助。
楊:當然有幫助。我忘了在我的文章里有沒有寫“韜光養晦”后來的翻譯。開始的那個翻譯太咄咄逼人了,后來外交部的正式翻譯改用keep a low profile,保持低調。但是平心而論,我們的韜光養晦是保持低調的意思嗎?實事求是地說,韜光養晦在漢代以后確實是有權謀化的趨向,但是理雅各顯然認為這與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有所不同,所以他才試圖追索《道德經》等古代文獻中的可能意義。你看比較研究多么有趣,我們不只是通過比較去了解西方,也是讓我們由此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們自己未必真的那么了解我們自己。
吳:再接著問一個關于經文辯讀的問題。您覺得經文辯讀未來對我們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和觀念可能會起到什么樣的推動作用?
楊:我覺得經文辯讀可能有兩個比較重要的方面。一個是有足夠的材料,這個材料是中國學界可以與西方互補的;還有一個就是方法。因為經文辯讀的方法在西方有點像religious practice,跟中國的純粹學術性研究不太一樣。他們是幾個人坐在一塊,你是猶太教,你是伊斯蘭教的,我是儒家的,咱們一塊兒把經典放在這兒讀,變成一個儀式性的實踐。他們甚至把經文辯讀帶到醫院里面,嘗試某種治療的作用。這與中國學者的主要興趣確實不同。前面提過的猶太教哲學家Peter Ochs參加了幾次與中國學者的對話之后,為《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寫了篇文章,題目是“從實踐到理論”(From practice to theory)。我相信中國人的想法對他是一個重大的提示。經文辯讀有一個很大的理論空間,我覺得這個理論空間是顛覆性的、革命性的。為什么呢?他們的文本細讀、比較閱讀,其實是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這種方法導致的結果讓他們很吃驚。因為,現在宗教分歧那么大,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伊斯蘭教里面的什葉派和遜尼派,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和新教,到處都是分歧。但是所有的東西追到源頭,你會發現原來的經文沒有那么大的差別,有的甚至完全一樣。西方學者后來做了詳細整理,把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經典里面的類似表達都并列在一起。從而可以發現:人們想表達的神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顯現形式,而這些顯現形式最并沒有那么大的差別。后來差別越來越大,這個變成上帝,那個變成真主,乃至人們以為自己所把握的神圣才是惟一的。我覺得比較的方法對于文化理解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應該會有更大的作為。
吳:換一個話題。您在文章中經常談到,現代世界面臨價值和意義的消解,確定性和客觀性的喪失等情況,但是人類始終還是要尋找意義,尋找終極的價值和歸宿。您也提到了一些后現代神學或者哲學家,比如德里達、巴丟等人,其實他們并不是在說這個世界毫無價值。我覺得這種對于價值和意義的追尋,是不是跟比較文學也有共通的東西?兩者應該也有關聯。比較文學其實也在尋找意義。像您做的經文辯讀,要找共通的東西,也是對價值和意義的追尋。
劉:對,樂黛云老師也說比較文學是人文主義,新人文主義。
楊:是的。這就是為什么“作為方法的比較文學”那么重要。比如剛才說的,海德格爾他們為什么找那種緣構性的概念,其實也是因為如果沒有緣構性的概念,我們好像只是用充滿歧義的名詞去指代某一種意義,比如存在、上帝、絕對、善或者正義等等,但所有的這些概念都是非常可疑的。為什么可疑?就因為我們抓到的只是有待解釋的名詞性稱謂,而被我們忽略的卻是它何以衍生的意義結構。剛才提到的大哲學家,他們最后要找的、要說的,都不是最后說出來的那個東西,不是那個名詞、那個理念、那個注定經不起質疑的解釋,而是生成了這一切的那個緣構。
至于意義被消解,從神學的邏輯上講,意義本來就是“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ility)。承認絕對意義上的“不可能”,才能討論什么是可能的。“不可能”就是我的“限度”,但是如何在否定的基礎上談論終極的價值,那就是可能。如果從神學的角度回到人文學,“不可能的可能性”就是我們與意義之間的結構性關系。換句話說,我們不可能充分地把握意義,也無法為意義提供終極的表達,但是恰恰如此,這一結構性關系才使意義的“確定性”得以維系。這可能是神學對人文學的基本啟發。
所謂緣構性的的概念工具正是如此。思想的工具并非從中推出的任何結論。這是基本的人文學態度,也是人文學的方法。如果沒有這樣的態度和方法,如果只能用新的價值理解取代原來被動搖的價值,在邏輯上的結果應該是一樣的,注定會陷入同樣的圈套。如果我們不斷拋棄過往的意義理解,卻無從擺脫理解的慣性,可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比如我們常常認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那么又當如何?如果現在的說法不行,返回古代就可以嗎?如果中國的說法不行,找到西方就可以嗎?執著于這樣的邏輯,是建構不出穩定的意義空間的。意義空間的穩定性,不在于“世人皆醉我獨醒”,更不在于我的理解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許只有在“我不能”的前提之下,才能就“意義”給出有意義的討論。這也是“緣構性概念”的價值所在。
吳:比如說不同文化相互碰撞,意義總是處在生成當中。
楊:正如“世界文學”并不“存在”,但是它“正在發生”。
劉:首先是,我們每一個出場的人,要保持虛己,自我清空;同時大家來坐在一塊一起討論,各自拿出各自的剛才您說的工作性質的概念……
楊:很多中國概念之中的工具性,有時候常常被我們自己忽略了。比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那個“恕”字我多次拿來當例子。在中文里,我們未必覺得“恕”字有什么工具性,但是理雅各把它翻譯成西方的時候,所用的概念是reciprocity。把reciprocity再翻譯回中文的時候,我們多用“互惠互利”,但是reciprocity本來的基本含義應該無所謂“互惠互利”,而是推己及人的“交互性”。“交互”與名詞化的“恕”完全不同。而理雅各將其翻譯為reciprocity,本來是與朱熹的解說暗合,只是后來被我們的日用倫常所淹沒了。
吳:還有一個問題,關于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您曾經擔任過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非常了解。中國比較文學自八十年代以來,長期搬用西方比較文學的研究體系,如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等等,但是一直也有建立中國學派的提法。那么,就現階段而言,跟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相比,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有沒有大的突破,或者說怎樣給它一個定位,它將來的理論發展該往哪個方向走?
劉:這里還有學科定位的問題。比較文學,是從最初的法國人的民族文學史的輔助學科,到建立比較文學系。在中國,經過摸索,把它放在中國語言文學下面,作為二級學科。從邏輯上看,比較文學是高于國別文學和民族文學的。雷馬克(Henry Remak)曾經打比方,說國別文學是墻,比較文學就是跨在墻上。現在我們的比較文學不僅不是在“墻上”,實際上還是在“墻下”,它只是中國文學這種國別文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它需不需要從二級學科里面獨立出來,成為單獨的一級學科?
楊:老實說,我并不覺得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感到也沒有需要去特別倡導中國學派,學科的意識可能也不必太過急切。我們不斷建立的“學”已經夠多了,有幾個“學”能真正留下?從以往的經驗看,藝術學從一個一級學科變成門類,歷史從一個一級學科變成三個一級學科,對學術本身真有促進作用嗎?要發展中國的比較文學,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中國的問題和比較的方法。借助中國的人文學傳統,應該能在比較研究中激發出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意識,也應該會逐漸凸顯出獨特的研究方法。這或許更值得我們關注,并且有所期待。
吳:好的,楊老師。謝謝您接受訪談,并提出了讓我們很受教益的觀點。今天的訪談先就這樣了,后面的整理工作還期盼您給予進一步的指導。
楊:好,應該的。也謝謝你們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