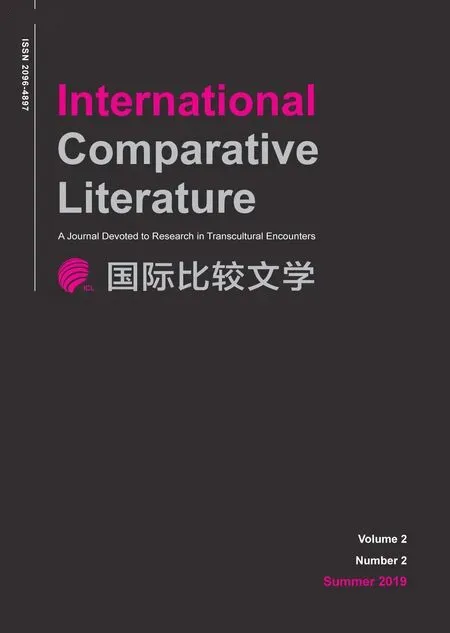《 誤讀》與“不存在”的戲仿*
——論埃科的批判性詮釋觀念及創作踐行
盧嫕 輔仁大學
一、引言: 《誤讀》“序言”中的表述空白
小品文集《誤讀》(Misreadings)的原名為《小記事》(Diario Minimo),是翁貝托·埃科(Umberto Eco)在1963年結集出版的實驗性創作讀本。1993年,此書被譯為英文,埃科在此英文版的 “序言”中將其重新命名:
于是,Il Verri 上就出版了《小記事》。后來,在1963年,當那些發表在雜志上篇目被收集成冊時,它被取了同樣的名字,盡管其中的內容并非是一般意義上的“記事”。那冊書出版了好幾個版本,并成為現今這個英語版本的基礎。因為書名《小記事》(Diario Minimo,1963),從字面上直譯毫無意義,所以我更喜歡稱它為《誤讀》(Misreadings,1993)。
有趣的是,自此之后,在當代的文藝批評話語場域中,該命名似乎已經成為了隨處可見的革命性標語,但大多數批評者的援用也僅僅是只聞其名,不解其意。甚至,隨著埃科的聲名遠播,此作的原本意圖與訴求反倒顯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就另一個角度而言,《誤讀》亦非是埃科的一次成熟的文本實踐。事實上,該書所輯錄的數篇 “小文”,說到底也不過是些許零散地刊載于文藝批評雜志上的實驗性嘗試,恰似他在 “序言”中所言:
在這樣的一份出版物(Il Verri)里,遍布著新先鋒派的語言實驗和數篇討論埃茲拉·龐德(Erza Pound)以及中文表意符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而我卻引入了幾頁對一些小話題的無拘無束的反思(free-wheeling reflections)。這些話題常常旨在戲仿該雜志的其他撰稿人的作品,他們的寫作狂熱更甚于我。所以,在一開始,我想要為我寫下這一頁頁的蓄意地滑稽( deliberately comic )、怪誕(grotesque)的文字向讀者們道歉,所以跟雜志的其他內容相比,顯得不那么斯文體面。
“無拘無束的反思”(free-wheeling reflection)、“蓄意地滑稽”( deliberately comic )、“怪誕” (grotesque),在這些看似謙虛戲謔的話語中,暗含著埃科對當代先鋒創作實踐的思慮。為此,他在隨后也進而說明了此種書寫游戲的濫觴:
最初的文本無論是我寫的還是朋友寫的,在文學類型上都類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話學》(Mythologies)。……我相信是在閱讀了巴特以后,出于謙卑,我放棄了《神話學》的風格,逐漸向混成模仿體(pastiche)發展。……我采納混成模仿體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如果新先鋒派的作品在于把日常生活和文學語言顛覆得面目全非,那么,蓄意地滑稽、怪誕也應該屬于那個項目的一部分。在法國,混成模仿體的傳統擁有如此著名的實踐者如普魯斯特、格諾(Queneau)和烏力波(Oulipo)工作坊,但意大利文學界可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由此可見,在一方面,埃科不但把《誤讀》所呈現出的諸多美學性文本表征概括為“混成模仿體”(pastiche),還希望借該項書寫傳統回應時代對在地創作者的需求;而在另一方面,他卻又在此“序言”中提到了另一個術語“戲仿”(parody),且賦予了此命名下的文本實踐更加普遍的意涵:
戲仿(parody),如同其他所有的詼諧書寫(comic writing)的作品一樣,與時空相關。俄狄浦斯(Oedipus)和安提戈涅(Antigone)的悲劇故事依然令我們感動,但是,如果我們缺乏對古雅典的了解,那么就會被阿里斯托芬的許多暗指難住。……今天,我意識到最近的許多有關“解構閱讀”(deconstructive reading )的習作,仿佛是受到了我的戲仿(parody)的啟發。這恰恰是戲仿的使命:絕不要害怕走得太遠。如果目標正確,它只不過是毫無愧色地、不動聲色地與莊嚴自信地向人們宣告今后可能產生的寫作。
綜合以上的表述,我們可以在此簡略地概括埃科所謂的“ 混成模仿體”與“戲仿”。在他看來,“混成模仿體”(pastiche)是一種繼承了文學傳統的文體風格,而“戲仿”(parody)則是建立在“解構閱讀”之上的跨時空創作。那么,“戲仿”,作為一種與書寫時空密切相關的 文本現象又該如何與 “混成模仿體”有所區隔呢?而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又該如何定義“戲仿”呢?以上的兩項質詢,是埃科的“序言”留給我們的問題。
二、什么是“戲仿”: “戲仿”問題的邊界與可能

詞源學的探索或許暗示了,“混成模范體”和“戲仿”會因上述緣由而存在著某種本質性的差異, 但是,無論是就歷史上的諸種文藝現象、還是就當下或未來的創作實踐而言,此研究視域必然是有限的。 另外,不管從歷時性的角度還是從共時性的角度來看,我們就“混成模范體”概念與“戲仿”概念展開的討論,最終亦會在“后現代”敘事研究的領域中,演變成為一個更為復雜而廣泛的議題,也就是隨后我們將會談到的,即“戲仿”概念的界定與描述問題。所以,針對該議題,本研究需要為接下來的探索劃定疆界,以便更好地把討論的范圍限定在合適的領域內。
首先,以下的兩個問題需要被區分,即“什么是戲仿?”(What is parody?)與“戲仿會是什么?”(What would the parody be ?)。就前一個問題展開的討論往往會把一系列相似的文本現象、形式風格、文學技法與美學策略明確地指認為“戲仿”,并嘗試憑借各自的理論視域(形式類型分析、詮釋學、歷史研究等等)對此種文藝現象進行論述與分析。可以說,這類就“戲仿”問題展開的系統性研究自始至終都圍繞著這一概念本身展開。可就后一個議題而言, “戲仿”概念的界定、描述與相應的文藝實踐并不在這類研究的關注范圍之內,甚至可以說,對于這類研究者而言,與“戲仿”相關的議題已經超越了此概念所能承受的閾限,從而能夠被更加龐大的系統性理論所包含。正因如此,該類探討亦常常呈現出一種過程性,“戲仿”問題亦持續地和一些不斷涌現的龐雜概念、議題相呼應,且這些概念與議題幾乎涵蓋了當代文藝理論的方方面面,并始終圍繞著作者、文本/作品與讀者之間的三元關系(作者與作品/文本之間,作品/文本之間,作品/文本與讀者之間以及作者與讀者之間)展開。以形式主義文論為例, 一種具備“現代性”精神(即“進步”與“破壞”)的文學形式進化論是他們在談論“戲仿”概念時的基本前提。在《情節編構手法與一般手法的聯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ices of Plot Construction and General Devices of Style,1991)中,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Borisovic Sklovskij)在探討“母題”(motifs)問題時,把“戲仿”視為一種新舊文學技巧更迭的表征,且認為該種表征總是產生于新興創作與既存樣式的類比與對立過程中。隨后,在《作為戲仿的小說:斯特恩的〈商第傳〉》(The Novel as Parody: Sterne's Tristram Shandy,1991)中,他又把“戲仿”與后來被稱為“后設小說”(metafiction)的敘事形式關聯起來。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即該種敘事所呈現出的“自我意識”(self-reflection)特征也使“戲仿”概念成為了形式主義者所一貫主張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技巧的一種轉義。換言之,“后設小說”通過“戲仿”技法,將能有意識地曝露了前文本的書寫機制,從而使已經成為表述慣例的藝術技法得以“陌生化”。然而,對于巴赫金(M.M.Bakhtin)而言,“戲仿”并不僅僅與某種藝術作品的風格與形式相關聯 ,而是植根于雙重指向的話語(double-directed discourse)實踐之中,且是暗含于其中的語義、意圖加入“對話”的一種體現。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Пpoблeмы пoэтики Дocтoeвcкoгo/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1963)中談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語類型”(types of prose discourse)時,就提出了“戲仿”話語(parodistic skaz/parodistic discourse)的“雙聲性”(double voiced),并指出這種“雙聲性”往往反映在對“他人語匯的使用”(use of some else's words)之上:
可類比于戲仿話語(parodistic discourse )的是反諷,或是任何的其他使用他人語匯(use of some else's words)的雙聲性(話語)(double-voiced);亦在這些例子中,另一種話語被用以傳達與之敵對的渴望。在我們的日常的一般發言中,這種使用他人語匯的現象是極其普遍的,特別是在對話(dialogue)中,一位說話者時常單純地重復(literally repeat)其他說話者的表述,并為這種表述注入新的價值,且藉由懷疑、憤怒、反諷、嘲弄、調笑等這類表達以其自身的方式強調它。
盡管巴赫金的后續論述仍舊沒有完全擺脫上述悖論性的發展觀,但他卻賦予了新舊文藝一種辯論性而非迭代性的表述位置,并在建構“眾生喧嘩”(heteroglossia)、“狂歡化”(carnivalesque)等概念的過程中,把“戲仿”的那種必須借助雜糅式戲謔的手段來實現的“嚴肅性”,視為文藝作品的內在價值的一種體現。(如,中世紀狂歡節中的“神圣戲仿”Parodia Sacra)。
在巴赫金之后,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發展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成為了“戲仿”概念的又一代名詞。但在她的“互文性”理念中,“戲仿”于風格上所表現出的喜劇效果(如滑稽、嘲弄與詼諧等)被策略性地否認了(“笑客是沉默的”),而“戲仿”概念的中性價值卻因符號進程(semiotic process)的非定向性,獲得了格外的強調。例如,克里斯蒂娃在建構巴赫金的“對話主義”(dialogism)理論時,把“戲仿”視為具備“雙重性”(double)的“悖存語匯”(ambivalent words)的一種:
然而,在第三種例子中,書寫者能運用他者的詞語,并賦予它全新的意義的同時又能保持它已有的含義。這樣的結果是,一個詞語具備了雙重意涵(two significations):它成為了悖存性的(ambivalent)。這種悖存詞(ambivalent word)因此成為了加入兩種記號系統的結果。……第二種悖存語匯的分類以“戲仿”(parody)為例,與前幾種相比十分不同。在這里,作家引入了一種與他者詞語相對的表意。……狂歡節的笑客(The laughter of the carnival )不單純是戲仿性的(parodic),它的喜劇性不會多于悲劇性;它是同時是二者,或者我們可以說它是嚴肅(serious)。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克里斯蒂娃在此文中主張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替代“主體互涉”(intersubjectivity)概念時,以下的一種趨勢似乎不可避免了,即以 “文本主義”(textualism)為代表的某些的極端化的結構主義或后結構主義思潮使“文本”“詞語”的內涵義無限膨脹,以至于吞沒了獨立于實踐境遇中的主體價值。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把該議題進而置于哲學與思想領域,那么“戲仿”現象的產生是否也就意味著書寫、敘事和言說行動與其表述對象或發言者之間的主客關系正面臨著絕對的消解?
除此之外,在探討讀者與文本的關系時,讀者接受理論的學者們則堅持認為,“戲仿”技法是文本喚詢讀者的期待視域并加以摧毀的一種方式。因為在他們看來,“戲仿”概念的革命性恰恰在于:它破除了審美史上長存的迷思,即作者權威、甚至是文本權威,且把一種過程性的比較視域引入到“戲仿”概念之內。正如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認識到的那樣,在讀者比較與接受的過程中,標的文本與一種“藝術性模仿”(artistic heightening of the imitation)或“批判性模仿”(critical imitation)之間的落差被突顯出來。而且,姚斯亦會認同以下的觀點,即如果不存在著該種文本預設與讀者預期之間的落差,那么 “戲仿”概念因“破懷性”而具備的創造潛力也就無法顯現。雖然,讀者接受理論強調了“戲仿”概念的“創造性”,但該理論并未視文本的詮釋者為“創作者”,更不用說把“作者”與“讀者”同等地視為兩種能動的主體,并相信它們能在流動的文本中相互轉化。
不可否認,以上的梳理無法盡述與“戲仿”概念相關的探討,但是在此時,我卻必須要為該文中將會涉及到的討論設限,以便更好地聚焦在《誤讀》的論述及相應的文本實踐上。根據上述歸納,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即在“戲仿是什么?”的問題上,“戲仿”概念不過是縱橫交錯的拓撲式理論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但以此為“原點”,卻能牽動從“現代”蔓延至“后現代”的眾多復雜且龐大的議題脈絡,如“后設小說”“陌生化”“互文性”“對話主義”以及“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等等。因此,本文的論述將會以“什么是戲仿?”的問題為始,終于“戲仿是什么?”這一問題的開端,從而僅僅選取那些借助不同的方法論、理論視域把“戲仿”概念的界定與相應的文本實踐視為主要對象的研究。不得不承認,該種策略性的選擇是對此項充滿著可能性的“后現代”概念所進行的一次人為閹割,但如果沒有該種限制,討論便無從談起,而到頭來我們的一切論述不過是一些飄忽不定的能指與 “不存在”的意義。有趣的是,在《戲仿》(Parody,2000)一書中,作者西蒙·丹提斯(Simon Dentith)對“戲仿”及近義概念之間關系的“再描述”,將有助于我進一步的闡明“戲仿”問題的邊界及其可能。在此書中,丹提斯接受了巴赫金的“對話”理念,把“戲仿”詮釋為一種“處于過程中的普通語言互動進程”(the normal processes of linguistic interaction proceed)。因此在該意義上,“戲仿”及相關的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 被其形容為一段“光譜”(spectrum):
(就戲仿展開的)一系列文化實踐能被便利地組織為一條光譜(spectrum),在這條光譜之上,根據一定的評價標準,不同的形式構成了它們所引用的文本 ,攜帶敬意的引用(citation)作為這條光譜的一端(如,“我今天的文本來自……”),而帶有敵意的戲仿(hostile parody)作為這條光譜的另一端,而在這兩端之間有著眾多正在形成的文化形式。這樣一來,這條光譜將包含模仿(imitation)、混成模仿體(pastiche)、模仿英雄體(mock-heroic)、滑稽諷刺的作品(burlesque),拙劣的嘲弄(travesty),滑稽的模仿(spoof),以及戲仿自身。
由是,“光譜”的譬喻并未先驗性地賦予“戲仿”特殊的定義,而是把它描述為在兩個端點間、由無數的中介地帶構成的現象領域。在此,我希望部分援用此譬喻,把問題“什么是戲仿?”與問題“戲仿是什么?”視為這條光帶的兩端,而在這兩端之間不斷地涌現著眾多意圖參與進來的討論,且這些從不同的理論視域出發的探索不但豐裕了既存的“戲仿”概念,還拓展著這兩個端點所劃定的邊界。綜上,以下的論述將會涉及到這條“光譜”上的一些具備代表性的理論與觀點,其中既有以形式分析為主要方法論的文藝類型學、聚焦文本現象與主體互涉觀念的詮釋學,又有對“戲仿”概念脈絡所作的系譜考。最終,此文的探索將會回歸到《誤讀》所收入的一系列文本實踐及埃科的相關論述中去,而這次探索無疑又會透過符號接受者視角,在符號衍義系統中,一窺“戲仿”概念的成因,以及該現象所暗喻的“后現代”處境。
三、“戲仿”概念的界定: 哈琴的文藝類型學與瓦爾德斯的詮釋學視域
事實上,琳達·哈琴(Linda Hutcheon)的研究恰巧為埃科尚未展開的討論帶來了不小的啟發。在《一種戲仿的理論:二十世紀藝術的諸種形式導引》(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1985)中,哈琴對“戲仿”概念的界定,是建立在該術語及其相似概念間的共時性拓撲關系之上的。由是,她的討論涉及到了在語義上與“戲仿”相近的一些歷史性術語(例如,“satrice”“irony”“ridicule”“imitation”“plagiarism”與“pastiche”),且借此揭示出了“戲仿”概念在當代文藝實踐語境中的復雜性:
那么,“戲仿”,在其反諷式的“跨語境”與顛覆中,成為了一種具備差異性的 “重復”。(亦即)一種暗含于被戲仿的背景文本與新的、正在加入的作品之間的 “批評的間距”。而在新的合成作品中,存在著一種常常被反諷標識的 “間距”。但該種 “反諷”既能被游戲亦能被輕視;該種 “反諷”既能是批判性的建構又能是一種(批判式的)解構。
在哈琴看來,“戲仿”概念的界定問題往往取決于文本本身能否同時滿足以下的兩項基本條件,即“跨語境”重復(“transcontextualized”repetition)與批評間距(critical distance)。在文本結構上,所謂的 “跨語境重復”意味著 異質性雙重文本的同時在場,并且在發揮語境功能的 “背景 文本”與表層的陳述性與補充性“前景 文本”間總是構成了某種緊張的 “模仿”(imitation)關系,并且該種關系常常需要某位來自異域文化的“解碼者”(decoder)從“前景文本”中識別,并進而據此推論、建構出第二重意義(the second meaning)。因此,“‘戲仿'則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近似于 ‘隱喻'(metaphor)”。但是, “反諷”(irony)策略的加入卻又使“戲仿”有別于“隱喻”。換言之,“反諷”營造出了一種有效的 “批評的間距”,該種間距不僅使“雙重文本”得以 “結構性共存”(structurally coexist),還暴露出了“文本”之間的摩擦與沖突。由是,“戲仿”才得以有別于 其他幾種亦具備“跨語境重復”性質的概念,例如, “模仿”(imitation)、“引述”(quotation)與 “影射”(allusion)等等。此外, “反諷”還是一種實踐策略,在“戲仿”現象中,它不但能使以上 代表“跨語境重復”的非忠實性“摹仿”不再局限于多重文本關系網絡的內部,而且還使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效應不僅作用于文本,且能對倫理實踐的領域產生影響。
不得不承認,上文對“反諷”特征的強調似乎要讓它成為把“戲仿”從其他近義概念中區隔出來的關鍵標識。但是如此一來,我們又該如何解釋作為傳統文藝修辭的“混成模仿體”,亦暗含了一種對固定修辭模式的“反諷性”戲謔意向呢?顯然在哈琴觀念中,“戲仿”并不能夠與“混成模仿體” 成為同一概念下的替換義項:
戲仿是一種雙重文本性的綜合體,有別于諸多如混成模仿體一般的、僅僅強調相似性的諸多單一文本形式,戲仿更注重差異性。……在我看來,戲仿追求和其模式(model)間的異質性關系;混成模仿體則往往更多地通過相似性與一致性來運作。……戲仿之于混成模仿體,或許,如同修辭性轉喻之于陳腔濫調。
根據以上的描述,哈琴認為, “戲仿”與 “混成模仿體”之間的根本差異反倒體現在“跨語境性”(transcontextualized)上。也就是說,因為 概念“混成模仿體”往往傾向于強調數種文體、文本的相互融合,且意在主張它們之間的兼容性與一致性,所以該概念更適合在同一類型的文本內部使用。例如在小說《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1980)中,那些對經典偵探敘事片段與場景的“模仿”(如:威廉修士識馬的情節,是埃科對狄爾泰的小說《查第格》中查第格辨馬情節的模仿)盡管亦帶有“反諷”的意向,卻更有助于一致性、整體性敘事的形成,是敘事中的功能性成分。所以,在哈琴看來,概念“混成模仿體”或多或少地缺乏了概念 “戲仿”所強調的革命性,即一種“跨類型游戲”(cross-genre play)。她引用了丹尼爾(Daniel Bilous)的論述, 把“戲仿”視為一種“跨文本”(intertext)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ed)的轉義、變形(transformational)實踐,而“混成模仿體”不過是在文學技法上,完成了對不同文體風格的 “跨文體”(interstyle)模仿(imitation)。
由此可見,憑借著“跨語境性”,哈琴的 “戲仿”概念不但暗示了傳統文學修辭在用以描述當代文藝實踐時,所可能遭遇到的局限性,還為該命名能夠作為一種開放性的文本現象,在“后現代”語境下具備某種合理性奠定了基礎。最終, “批評間距”與 “跨語境重復”實則成為了 “戲仿”概念中相互闡釋的兩端:“批評間距”幫助“跨語境重復”有效地排除了那些僅僅在形式上表現出“單純”的 “模仿”關系的文本現象,而“跨語境性重復”又反之保證此種“模仿”關系并非源自話語系統的排他性自我增殖(即同一邏輯框架下的自我重復)。不可否認,在一方面,哈琴的上述設想為“戲仿”概念的演繹鋪設了自洽的理論背景,但在另一方面,這套清晰簡明的分類判準只有在文藝類型學(literary typology)的一種預設性框架下才能成立。除卻她所一貫主張的方法論,即“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作為一種文本實踐的“戲仿”,則時常在符號的衍義與詮釋場域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形態。換言之,當我們談到“文本的不確定性可能”(indefinite possibilities of texts)時,便不得不去面對種種這樣或那樣的質詢,即試問在 “后現代”語境中,哪一個 “解碼者”對前文本的理解不會是一次“跨語境性”的 “戲仿”實踐的起點呢?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又能否把某些“混成模仿體”視為“戲仿”實踐呢?但是,倘若我們把這一概念的外延義無限地拓展,那么又是否該約束因此產生的 “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呢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者之間的本質性差異也并非反映在對“類型”還是 “文體”、“跨文本”還是 “跨體裁” 等一系列二項式的選擇上。實際上,該種類型學框架本身亦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哈琴的另一重意圖,即她既要肯定作為一種歷史性境遇的“后現代”之于“戲仿”的獨特性,卻又需成功地把“戲仿”與它歷史遺產隔離開來。換言之,作為一種過時、保守的文藝范式,“混成模仿體”必須被更加靈活、復雜且符合時代語境的的 “戲仿”命名所取代。毫無疑問,該意圖甚至悖論式地反映在她對羅斯(Margaret A.Rose)那部影響甚廣的著作的批評之上。在她看來,羅斯的界定與描述并不準確,只因福柯式的文學系譜史解讀法(foucauldian reading),使她把當代的“戲仿”實踐視為一種迭代認知范式下的非連貫性(思維)模式(mode of discontinuity)的再現:
羅斯對不相應性,不一致性以及非連貫性的強調并不能解釋曾被我們檢驗過的、二十世紀的諸種的“戲仿”形式。她對 “戲仿”喜劇效果呈現(沒有它,她感覺任何的定義皆不能作為批判的術語,服務于一種有用的、獨特的目的)的堅持也是局限的。一種與批評性差異重復有關的、更為中立的定義將允許意圖性范疇與可能性效果呈現在當代的戲仿作品中。
耐人尋味的是,另一位加拿大學者馬里奧·J·瓦爾德斯( Mario J.Valdés)在他的著述《詩意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Poetic sense,1998)中同樣強調了“后現代”語境與“戲仿”實踐之間的關系。但是,因為在邏輯上,瓦爾德斯的詮釋學視域與哈琴的文藝類型學方法論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所以他并不像哈琴那樣在乎“戲仿”概念在表現形式上所可能呈現出的多樣性,而反過來強調“戲仿”實踐在“后現代”語境下所能分享的一種普遍性的精神。因此,在界定“戲仿”實踐時,他把那種強調相似性、一致性的 “模仿”(imitation)概念視為 “戲仿”實踐的基礎:
假如我們接受這一基本思想,戲仿是一種對另一件文本或作品意識召喚,那么我們也必須接受所有模仿都是戲仿之作。然而我們還要注意到,至少有兩種不同類別的戲仿作品:反諷的戲仿與作為敬意的戲仿,在諷刺文學中還有一種戲仿方式的使用。
正因如此, 瓦爾德斯不但在批評方法上,用文本細讀取代了分類界定,還在賦予了 “后現代”語境某種 “準先驗性”(quasi-transcendental)后,把 “主體互涉”(intersubjectivity)現象視為 “戲仿”實踐的核心精神。換言之,在 “戲仿”或 “混成模仿體”的問題上,他對哈琴的回應可能會是: “客體”的 “精準特性”(precise properties)已不足以成為判斷一項文本實踐“戲仿”與否的基準,在當下,區分二者的關鍵取決于文本實踐,即作為繁復、具體的 “此在”能否及時地給予 一種超越性的“存在” 歷史性的回應 。就該角度而言,哈琴所枚舉的種種文本現象、修辭類型(如:“satire”、“ridicule”、“imitation”等等 )若能在 “后現代”語境中,成功地轉化為一種把歷史性主體及相應文化經驗裹挾在內的 “互涉”實踐,那么它們皆可被 “戲仿”命名。可見相較于哈琴的類型學判準,瓦爾德斯的詮釋學式的描述仿佛更好地兼顧了多樣而復雜的文本現象。但亦不可否認的是,他的觀點也間接地導致了一種“任意性”。事實上,作為一種更強調一般性原則而非特殊呈現的方法論,詮釋學勢必使瓦爾德斯難以調和兩種相向發展的論述傾向之間的矛盾,即 “戲仿”概念的普遍意義與因偶然性境遇所顯現的特殊“戲仿”現象之間的矛盾。例如,他就曾不由分說地把封閉性的簡單 “引用”(citation)現象驅逐出 “戲仿”的概念之外:
戲仿對別的文本開放的、公然的借用,不僅大張旗鼓地將別的文本置于次要的位置,更為嚴重的結果是喚起了對戲仿寫作根本性質的注意。一個把復雜問題過分簡單化的想法是,戲仿文本關系是一種封閉的借用,即簡單的直接引證(citation)。反諷性戲仿的明確優勢在于兩種文本都處于一個更大的語境之中,即我所謂的共享性的敘事世界。
不得不承認,這段論述將導致的后果可能會是:當瓦爾德斯在強調“更大背景之中的敘事性共有(敘事性的共享世界)”并試圖深化 “戲仿”的內涵義時,他卻又必須策略性地忽視那種他所謂的粗暴的“引用”,在 “后現代”語境中所可能產生的 “或然性”。該種 “或然性”也許源于敘事主體的一次非意指性的文本實驗,但它卻在與“他者”的意外邂逅中,把一種不在 預設之內的意義從“封閉”帶向了“開放”。
綜上所述,由埃科的表述所進而引伸的議題,既難以被哈琴的分類與界定所解答,又無法被瓦爾德斯的解釋所完美地兼容。在埃科那里, “戲仿”似乎一種是可與傳統 修辭概念“混成模仿體”并存的詼諧書寫;在哈琴哪里, “戲仿”又成為一種有別于諸種傳統文學技法的 “后現代”理念;而在瓦爾德斯那里, “戲仿”甚至可以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后現代”詮釋現象。至此, 不但“戲仿”概念的界定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戲仿”命名本身,仿佛也在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四 、《 乃莉塔》:一次探索“戲仿”概念的文本實踐
無論如何,我們也許可以暫時停止發掘這兩位學者論述中的矛盾,而借具體的文本實踐來檢視他們的思考。首先,哈琴與瓦爾德斯的論述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地聚焦兩個暗含于“戲仿”概念之中的關鍵術語,即 “模仿”(imitation)與“反諷”(irony)。從此角度來看,哈琴選擇視二者為同一概念所暗含的兩種相異的屬性,并希望把它們發展成為被特殊的時代語境所詢喚的客觀標準(即“重復”與“間距”);而瓦爾德斯卻選擇將 “戲仿”概念抽象化,并視 “模仿”與 “反諷”為某種超越性意義所指派的具體現象(即“反諷的戲仿”與“作為敬意的戲仿”)。 盡管兩位學者理解有所差異,但如果我們在語言表意實踐的話語范疇內探討它們,那么“模仿”與“反諷”試圖再現的,也許是兩種使意義增衍的邏輯模式。
埃科的文本實踐《誤讀》中的首篇,是名為 《乃莉塔》(Nolita)敘事性的小品文,此作是埃科對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著名小說《洛麗塔》(“Lolita”)所進行的一次詮釋性改寫。在基本人物的設置上,《乃莉塔》就有別于原作。在原作《洛麗塔》的故事中,名為“亨伯特·亨伯特”的中年男子愛上了其喚為“洛麗塔”的幼女,而在《乃莉塔》中,該設置卻被改寫成了名為 “安伯托·安伯托”的青年男子愛上了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婦人的故事。鑒于《洛麗塔》在出版時所遭遇到的道德批判,這項改編倒不啻是一次饒有興味的實驗性宣言。
然而,在繼續分析《乃莉塔》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把這篇美學性文本(aesthetic text)視為一個完備的、可供考察的中性衍義系統(system of semiosis),從而姑且能夠把它的結構劃分為兩個層面,即形式修辭層面( the level of rhetoric)與意向性層面(the level of intention)。在這個擁有雙重結構的衍義系統中,埃科的模仿行動更明顯地體現在前一個層面上,例如以下敘事開篇處的“手稿轉述體”:
本手稿是皮埃蒙特大區的一個小鎮的典獄長交給我的。典獄長向我們提供了關于在牢房里留下這些紙片的神秘囚犯的情況,以及籠罩作者命運的撲朔迷離,這些消息都不甚可靠,而且凡是跟下面這幾頁文字的作者生命之旅相交的人,都表現出三緘其口,讓人不可思議,這些都迫使我們不得不對現有的了解感到心滿意足:由于我們必須對手稿上所殘留的內容感到滿足……由于我們感到,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讀者還是能對這個安伯托·安伯托(Umberto Umberto)的不同尋常的故事(除非這個神秘的犯人或許就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本人……)形成一個概念,并且最終他(讀者)能從這些書頁中提取那種隱藏的教訓——(正如)那些放蕩外表之下(總是暗含著)的一個崇高道德教訓(e possa infine trarre da queste pagine quella che ne è la lezione nascosta——sotto le spoglie del libertinaggio una lezione di superiore moralità)。在原作《洛麗塔》中,因惡疾突發而去世的罪犯 “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 Humbert)曾留下了一部記錄其罪行緣由的手稿。最終該手稿經由其律師,輾轉至一位精神病學博士的手中,并由其在“序言”(“Foreword”)中道明此書的來由及出版意義。有趣的是,相較于原作中的這位轉述者所聲明的“完整無缺”(intact),《乃莉塔》的創作者既對原作 的“序言”進行了一次簡化版的 “模仿”(盡管在該次簡化版的模仿中,書寫手稿的那位 “l'autore empirico”,即“經驗作者”的形象變得更加地模糊與殘缺),又借助該種“模仿”,回應了原作的 “模范作者”(l'autore modello),即“精神病學博士”所聲明的那種書寫意圖。在《洛麗塔》中,這位帶著轉述者 “面具”的 “作者”原本希望此手稿的出版,能為大多數懷有與 “亨伯特”相似欲望的美國成年男性提供道德教化的參考,但《乃莉塔》中的這位一度占據了前讀者認知位置的手稿轉述者,卻暗示了《洛麗塔》的“序言”所提到的 “崇高道德教訓”,也許并非是文本作者所言明的意圖,而是在讀者詮釋行動介入后所產生的一種反饋效果。
事實上,我們或可將《乃莉塔》中的這段借助手稿轉述者 的“面具”來表述的 “序言”,視為埃科從詮釋理論的角度,以一位符號接受者的身份,對這部影響甚廣的著作進行評價。在他看來,小說的 “經驗作者”納博科夫所秉持的美學主張,也許并不能成為他的創作免受指摘的合法前提。換言之,作品一旦完成 便進入到開放的詮釋場域, 那種因情色的藝術性所帶來的無關道德的、純粹的與封閉的美學體驗也必須要面臨新的審視。不可否認,一部作品的美學價值不該由其倫理的取向所決定,卻也不應缺少該種介入視域。由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私人性的表述一旦在脫離了自洽的文本空間后,被置于公共的會話場域,它們也就必須學會開始面對那些來自各方的批評、反思與會話(而其中亦包含著對其道德性的反思,但這也正是敘事思辨性的價值所在)。
除此之外,《洛莉塔》亦通過第一人稱視角,對少女美麗、誘人的軀體施以濃墨重彩,而在《乃莉塔》中,這些刻畫亦被呈現為一種美學風格上的 “模仿”:
穿過飯廳的時候我仍然跟在黑茲太太后面,在飯廳之外,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蒼翠……接著事先沒有一點預警,一片藍色的海浪在我的心底涌起,……那是同一個孩子——同樣嬌弱的、蜜黃色的肩膀,同樣絲綢般柔軟、裸露的脊背,同樣的一頭栗色頭發。她的胸前扎著一條帶波點的黑色圍巾,是在躲避我年老而粗野的(老猿般的)目光,卻不是在躲避我少年記憶的凝視,我在一個不朽的日子里撫摸過的那對年輕的乳房。
于是在《乃莉塔》中,少女稚嫩軀體所呈現出的自然美感,被作者變本加厲地扭曲為于老婦人面容之上顯現的一種過分雕琢的丑態:
……只為了在附近竊視那些如同被火山的褶皺開鑿出的老臉(quei volti scavati da vulcaniche rughe),那些如同大瀑布般多水的眼睛(quelle occhiaie acquose di cataratta),以及那個干枯嘴唇的顫動(il vibratile moto delle labbra riarse),壓迫著一張無牙嘴優雅地下陷(depresse nell'avvallamento squisito di una bocca sdentata),狂喜的唾液留下的柔滑亮澤的小溪在她的臉上犁出了痕跡(solcate talvolta da un rivolo lucente d'estasi salivare),以及那些布滿老繭的喜悅之手(quelle mani trionfanti di noduli),緊張地帶著淫穢又挑逗的顫抖慢慢地撥動著念珠(nervose nel tremolio lubrico e provocante dello sgranare una lentissima corona)!
如果按照納博科夫的理解,原始的 “色情”描述意味著 “行動局限在陳腔濫調的連接中”、“性場面的描寫之間的段落就必須簡化為意義的縫合、最簡單設計間的邏輯橋接,以及扼要的解說與說明”,那么聚焦于少女軀體之上的過剩書寫,無疑已是一次對二流色情文學風格的顛覆。但是,該種意圖在《乃莉塔》中又遭遇到了第二次顛覆,老婦人面容所呈現出“極致之丑”,不但無法招致因個人體驗式的美學書寫所產生的 “同情”,甚至消解了作者為純粹審美經驗的合法性所作的辯護。
如此一來,上述暗含于形式修辭之下的 “雙重倒置”(double inversion),無疑是“經驗作者”埃科在“批評”之上進行的批評、針對“反諷”所進行的反諷。然而,《乃莉塔》卻因為模仿“反諷”本身,暴露了文本系統所生產的意義與作者意向之間的矛盾(即被文本系統所規范的“模范作者”與處于言說活動中的“經驗作者”之間的話語矛盾)。換言之,如果說在《洛麗塔》中,轉述者所聲稱的那種益于道德教化的功用被 “經驗作者”,即納博科夫以再現其美學主張的細膩刻畫悖論式地消解了;同樣,《乃莉塔》的手稿轉述者所期待的道德寓言,也遭遇了 摧毀它的 另一種極致美學。
綜合以上的分析,埃科的“反諷”意向,是借助形式修辭層面上的“模仿”來實現的,可是,我們又能否把這次自反性詮釋事件視為“戲仿”實踐的一種呢? 根據哈琴的文藝類型學判準,《乃莉塔》因其對前文本的直指性,無疑在形式修辭的層面上滿足了 “跨語境重復”的要求,但它在需要被 “反諷”所標識的 “批評間距”方面卻顯得有些隱晦了。事實上,“模仿”與“反諷”之間的關系并非不言自明,況且上述關系得以被揭示,則更有可能是因為作為“經驗讀者”的“我”,曾懷抱著對深層意圖的期待,“過度地”詮釋了埃科的創作。就該角度而言,此文本不但在形式修辭層面與原作保持著某種相似性,還在意向性層面上,未能明顯地傳達出一種異質性訴求。因此,《乃莉塔》并不嚴格地符合哈琴為“戲仿”概念所設立的兩項判準。但是,當我們透過瓦爾德斯的詮釋學視域來看待此文本現象時,該問題的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按照他的觀點,意向性的詮釋行動理應較之文本結構享有更多的特權。因此,當作為讀者的“我”,積極地去詮釋對象時,兩個原本各自擁有完整、自洽系統的文本就開始脫離互不相干的獨立語境,在瓦爾德斯所謂的 “敘事性的共享世界”(the shared world of narrativity)中顯現出一種普遍性的意義(例如,美學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所以,從詮釋學的視角來看,《乃莉塔》又無疑是一次 “戲仿性”(parodistic)的文本實踐。
五 、“ 摹仿”與“反諷”: 歷史中的“戲仿”概念

摹仿者所摹仿的對象既然是在行動中的人,而這種人又必然是好人或壞人……因此他們所模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壞(或是跟一般人一樣)……首創戲擬(仿)詩的塔索斯人赫革蒙(Hegemon)和《得利阿斯》的作者尼科卡瑞斯寫的人物卻比一般人壞。……悲劇和喜劇也有同樣的差別:喜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壞的人,悲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好的人。

它(戲仿)是一種更為強烈的辭格,命名取自模仿他者之歌,卻成為一種語言的誤用(...an abuse of language),即在詩句與散文詩中被指派為模仿性修辭。
在一定程度上,昆體良對該技巧的提倡,無疑揭示出了主體可以利用 “辭”與 “物”間的錯位關系,能動地營造修辭效果的能力,而這對 “戲仿”概念而言,又確是一個頗具意義的觀點。相較于亞里士多德的 “摹仿論”以及古希臘戲劇的附屬性設置,該表述或多或少地已涉及到了當代“戲仿”概念所強調的那種主體意向性層面的問題。根據羅斯的研究,在《七本書的詩學》(Poetics libri Septem)一書中,J.C.斯卡利杰爾(J.C Scaliger)雖然從 “戲仿”概念中指認出了“顛倒”“荒謬”(ridiculus)等特征,但卻也致使“戲仿”僅僅被視為一種滑稽性美學技巧,并在18世紀后被歸類于戲謔性修辭次范疇下。此外,一些與 “戲仿”相近的早期文藝實踐也令“戲謔”“插科打諢”等元素成為了該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在文藝復興時期,“反諷性”(ironia)的即興口語敘事就明顯地體現出了這些特征。在當時,行吟詩人(icanterini)的敘事往往取材自一個從古典時代或中世紀開始就被反復講述的故事。然而隨著時代精神的轉變,敘事者亦必須根據道德標準與聽眾需求作出即時的演繹,而該種演繹時常是以戲謔、反諷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說,假如我們是那個時代的聽眾,便會對以下的一種文本現象習以為常,即“經驗作者”(即行吟詩人)常假托權威之口(即故事中的 “模范作者”)講述一出與在場的敘事者雖無經驗性關聯,但卻能因“模范作者”的權威性而聲稱 “真實”的傳奇故事。在敘述的過程中, “經驗作者”常置身于故事中的人物及其“模范作者”之外,并作為第三方敘事者,以一種 “無傷大雅”的姿態,調笑與反諷 其敘述的對象。該種傳統的口語敘事模式不但能表達敘事者的個人立場,而且有效地緩解了因時代錯誤而造成的 疏離感,還能夠使一個老生常談的故事在新的語境中煥發生機。另外,在羅斯所提及的文藝現象中,古希臘人已經能夠自覺地在創作中添加一些戲謔性的模仿和改寫,并能夠自發地混合那些能使“上下文不協調”的角色與元素, 以創造喜劇。
在羅斯的表述中, “戲謔性”(burlesque)似乎是 “戲仿”概念不可或缺的關鍵,即便這些戲謔、滑稽、插科打諢與反諷元素所導致的結果,極有可能是致使“戲仿”實踐走向意義的消解(如同 “解構主義”曾經招致的那些指責那樣),但是,此概念所暗含的“雙重性”亦如中譯文 “戲”字的多義現象所影射的那樣, 即“戲仿”既能是一種看似漫不經心文本美學 “游戲”,又能是一種彰顯智力較量的 “展演”。至此,該觀點似乎也在回應哈琴對羅斯的批判,及其就此提出的“中立”主張 (在策略上,哈琴使用了更具批判意向的 “irony”一詞取代了僅僅強調了形式美學的 “ridiculus” “burlesque” 等傳統修辭,并賦予了其 “批評間距”這樣一種更為中立的內涵)。然而,羅斯的探討亦未止于“戲謔”,更何況,一些繼承了昆體良觀點的論述,也傾向于把 “戲仿”,視為一種包含了“復雜的信息”而非僅僅強調“戲謔”功能的“嚴肅”概念:
當其他一些現代批評家將戲仿當作更現代的戲謔概念,并由于他們認為它具有的‘滑稽的嘲笑'特征而指責它微不足道時,另一些 ‘晚期現代'的戲仿作家則一并否認它的滑稽效果或結構的重要性,將戲仿從這樣的毀譽中挽救出來,……其(戲仿)中目標文本也許不但被諷刺,而且被 ‘重新賦予功能'……戲仿的用法既是針對滑稽效果,又旨在傳達復雜而嚴肅的信息,而且當描述其他這樣的特征時,我們對戲仿定義中的滑稽不能抹去。
上述羅斯的系譜考揭示出了當代的文藝概念“戲仿”與一些經久不衰的修辭現象和詩學問題之間的密切關聯。 可見,早在那些探討“摹仿 ”“戲謔”與“反諷”等概念的傳統修辭學、詩學理論中,“戲仿性”的創作已經成為了它們的主要考察對象。此外,該歷史性研究也使我們意識到,當代就“戲仿”議題展開的一些研究往往會因此概念的表征,選擇性地遮蔽了另一項關鍵的議題,即“戲仿”實踐,到底是一種從符號系統中派生出的美學性技巧,還是對該動態衍義機制的一種自反性的揭示?也許,此議題才是使“混成模仿體”概念與 “戲仿”概念的界定得以問題化的真正緣由,亦是那個暗藏在哈琴與瓦爾德斯的“戲仿”理論背后的根本邏輯。換言之,如果我們先從瓦爾德斯的詮釋學視域出發,暫把其中先于具體實踐而存在的普遍性預設懸置,再而根據意義生產機制或符號的衍義邏輯對哈琴的類型學分類進行歸納,那么我們便會得到關于“戲仿”的第三種意涵,即此概念,描述了兩種使意義增衍的基礎模式。從以上對文藝現象“模仿”與“反諷”的梳理中,我們可知,其中一種模式通過重復、轉錄外部現實或前文本,不斷地挖掘未被揭示的終極意義;另一種則通過持續的自我批判,探索一種不以任何旁支、派生形式存在的潛在價值。可以說,在這一意義上,似乎不存在著一種擁有獨特的美學價值,且以派生性技巧形式存在的“戲仿”。
六、《碎片》及《乃莉塔》: “批判性詮釋”視域下的兩種“戲仿”實踐
按照以上的討論,我們仿佛要再一次地否認純粹的形式游戲與美學實驗在歷史的語境中所能開拓出的可能性,亦無法保證以“戲仿”去命名始終處于動態運動中的文本現象不會是一種過時的思維模式所導致的偏見。也許,“戲仿”概念留給我們的真正的難題是如何使上述兩種看似矛盾的指涉共存。
根據《讀者的意圖:有關接受符號學的簡記》(“Intentio Lectoris:appunti sulla semiotica della ricezione”)一文中的回顧,我們可以推斷,《誤讀》中收入的數篇創作,是埃科在其所謂的“前符號學視域”時期(un orizzonte pre-semiotico,1957—1962)的產物,而在同一時期內出版的,還有他的代表作《開放的作品》(Opera Aperta, 1962)。但是,他于此作中提出的理念,也曾為其招致了不少的批評與爭議。例如,在 “結構主義”思潮興盛的1960年代初期,埃科就大膽提倡讀者之于信息的必要性,并認為只有被特定語境中的讀者詮釋,信息才會有意義(...message signifies only insofar as it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given situation):
現在,我們必須將我們的關注從作為唯一參考來源的信息轉向信息與接收者間的溝通關系,在那里,接受者詮釋決定有助于使可能的參考變得有價值……如果有人想要分析一種可能的 “溝通結構”(a communicative structure)那么他必須將接受者一方計算進去。
不過,他在此文中亦承認,這種論點無疑會遭到 “文本主義”(textualism)的簇擁者的指摘。例如,在語言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èvi-Strauss)看來,每一個成型的作品都是帶有一系列 “精準特征”(precise properties)的客體,作為詮釋者只能將自身限制在尋找論證這些特質的證據上,而不是把所有可能的詮釋填充進去。針對這樣的批評,埃科反駁道,他所謂的 “開放的作品”并非提倡讀者對文本無限、過度的詮釋,相反,他認為“藝術性文本”(il testo artistico/artistic text)本來便擁有這樣的“開放性”結構,且該種結構鼓勵和支持多種詮釋的可能。
由此可見,“藝術性文本”,作為 “開放的作品”,不但強調了讀者詮釋的在場,還預設了自身對未來接受者的期待,且未把自身局限為一種奢求鑒賞者目光的排他性藝術客體。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所謂的 “詮釋者”難道不是那些在無數的敘事中被改寫和形塑的另一類客體么?如果我們承認上述事實,那么除了他們,又還有誰能使作品的豐富性與無限可能性得以顯現呢?因此,與其說在《開放的文本》中,埃科的目的是通過主張對作品的無限詮釋來彰顯讀者的主體性價值,還不如說較之對作品的本質屬性的探討和論證,他更傾向于關注信息與接受者、作品與詮釋者之間的動態關系,且旨在考察兩種看似處于穩定狀態中的客體,是如何因此關系而持續、不斷地改變的。
綜上所述, 既然我們承認讀者的詮釋對作品而言至關重要,那么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即作品也應為邂逅“未來的”讀者而不斷地生成新的交流形式與美學策略呢? 也許,《誤讀》中的另一類文本實驗能為我們解答此困惑。相較于《乃莉塔》,《碎片》(“Frammenti”)所運用的美學策略更趨向于 “混雜”而非“模仿”,且主要表現在糅合不同的文體風格與敘事類型于一體,以至于在形式修辭層面上,它更接近哈琴所描述的那種“混成模仿體”。所以,就文本類型而言,《碎片》盡管是一篇以未來想像為主題的懸測性虛構敘事(speculative fiction),但它卻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呈現。
在此作中,未來的人類考古發掘出了一些文藝、娛樂產品的殘片,而當時的學者透過這些來自1980年毀滅性災難,即“大爆炸”前的只言片語,便建構出了一個只有當代讀者(甚至是只有當代的意大利讀者)才會貽笑大方的故事:
大爆炸之前的意大利文化始終為深深的謎團所籠罩,盡管對于最初幾個世紀,其他國家的秘密圖書館提供可足夠的文獻證明。的確,在認真仔細挖掘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也同樣令人困惑的、非常容易受損的文件。在此,我用科桑巴(Kosamba)挖掘出來的一個小紙片作為印證。上面的文字,他很正確地認為,恰好說明了意大利人喜歡精辟的短詩。我全文引用如下: “在吾生命旅途之中點。”科桑巴還發現了一卷書的封套,顯然是有關園藝的論文,叫做《玫瑰的名字》,是某個叫阿科(Arche)或伊科(Eke)(斯特格表示,殘片的上半部不幸已被撕掉,因此名字不詳)的人寫的。
如果讀者們熟知埃科在1980年代出版的小說《玫瑰的名字》,那么他們在閱讀這段文字時無疑能會心一笑,因為這位來自未來的考古學家大概是徹底 “誤讀”了這部既非“短詩”亦非“園藝論文”的敘事性作品。但僅就此現象而言,學者的“誤讀”也不過是源自就現存檔案展開的實證分析,而《碎片》的接受者對作者幽默的領會亦基于一種相似的理解境遇,即他們曾經作為天真的讀者首先準確地把此書理解為一部以歷史題材為主的“偵探小說”,而非對某些非在場性 “神秘文本”的隱喻。有趣的是,從 “誤讀”(misreading)到“領會”(understanding),這兩種暗含著 理解風險的認知事件中 ,埃科借助 “元敘事”(metanarration)使一種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首要關系得以顯現,即我們曾經是也應永遠是一個在場文本字面意義的“天真”讀者,而文本總是率先透過字面意義的在場,邀請讀者進入詮釋活動。可是,這一點卻時常被一些 “世故老練”的詮釋者忘卻,他們恐怕早已習慣去使用一套成型、穩固的認知框架,并將一種過度的意圖(過分僵化的前理解或是生活經驗附會)施加于文本之上。也許,這正是埃科為何試圖將兩種風格截然不同的類型在創作中混合的重要緣由。毫無疑問,該種實驗性的探索往往旨在營造一種“陌異感”(uncanny),從而迫使詮釋者不得不放棄使用任何一種僵化、固態的理解模式去對文本施加暴力。
至此,我們便可重返啟發本文思考的那個最初的問題,即 “混成模仿體”與“戲仿” 之間的聯系與差異。然而,無論是在哈琴的兩項判準下還是在瓦爾德斯的預設中,如同“混成模仿體”這樣的一種統稱不過是對文本現象的單純描述,在某種程度上,該術語似乎缺乏那種使“戲仿”命名得以合理化的普適標準。但是,如果我們根據以上的論述,把“混成模仿體”與 “戲仿”視為作者因預設讀者的差異而采取的相應符號策略,那么這兩個術語之間的潛在沖突,仿佛也能因以上的視域得到有效的調和。
因此在兩位學者的探索之后,“戲仿”概念需要在埃科的詮釋理念與讀者接受觀中被再描述與重新命名。在此我把以《乃莉塔》為代表的一類 “戲仿”創作視為 “意向性戲仿”(intentional parody),而以《碎片》為代表的一類 “混成模仿體”實踐視為 “修辭性戲仿”(rhetorical parody)。盡管,二者皆是某種借由實驗性的探索表達各自反思性訴求的文本,但在形式修辭的層面上,前者往往呈現出令人熟悉的 “模仿”,因此它的 “反諷性”意向也只有在讀者閱讀活動的后期,才能被進一步揭示;而后者的符號策略則顯得略微激進,該類“戲仿”往往以混雜、怪異的面貌示人(它給讀者造成的“印象”就如同我們在閱讀神話時所想象的那種混合型生物),并且它的目的是促使讀者拒絕刻板化的想象與僵化的認知范式,從而這類讀者能以詮釋者的身份,重新加入到就某種特定文本類型與文體風格展開的敘事活動中去。
事實上,“意向性戲仿”與“修辭性戲仿”源自創作者對兩種尚待啟示的“讀者”的預設。埃科曾認為,“創作”(creative writing)之深意本應體現在對讀者的詮釋行動的啟示上,而非致力于發明一種前所未有的文本。因此,根據他在《讀者的意圖》中曾提出的論點,這兩類“戲仿“實踐的標的讀者皆處于其所謂的 “語義學詮釋”(l'interpretazione semantica/semantic interpretation)層次,即是一種“語義的模范讀者”(il lettore modello semantico)。相較于在 “元語言”活動中,始終追尋“批判性詮釋”(l'interpretazione critic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的“批判的模范讀者”(il lettore modello critico),處于該階段的讀者更擅長利用曾經獲取的經驗,將既予的意義賦予 “線性呈現的文本”。然而,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它們分處同一詮釋層次中的不同詮釋階段。因此,我把 “意向性戲仿”所預設的讀者描述為 “寓意的渴求者” (interpreters who desire for the allegoric senses),而 “修辭性戲仿”所預設的讀者描述為 “精神的領悟者” (interpreters who comprehended the anagogic senses)。這兩種描述來自但丁曾在《書信十三·致斯卡拉親王坎格蘭德書》(Epistola XIII a Cangrande della Scala)中所提出的作品的多義性(polisemos)觀點及四種意涵,即字面意義(litteralis),寓意(allegoricus),道德意義(moralis)與神秘的啟示意義(anagogicus):
正如我以下的表達所呈現的那樣,你必須知道作品的含義并不是單一的,更確切地說,它應該被稱作多義性的(polisemos),也就是多重含義的;第一重含義來自字面(per litteram),第二重含義來自字母所意味的(per significata per litteram)。第一種意涵被稱為字面義(litteralis),第二種意涵被稱為寓意(allegoricus)或者道德意義(moralis)或者神秘的啟示意義(anagogicus)。
隨后,但丁以《圣經·舊約》中的“出埃及記”為例,分析了這一特殊事件在不同意義層面上的意指。在他看來,無論是“寓意”、“道德意義”還是“神秘的啟示意義”皆可被視為對文本的第二重 “寓意性”(allegorici)含義的不同詮釋,但在我看來,在理解與詮釋的進程中,上述的三種意涵仍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因此,所謂的“寓意渴求者”無疑處于第二重詮釋階段的初期,即“寓意詮釋階段”,該類詮釋者不但能憑借經驗性的回顧,持續地將字面意義或一種對歷史事實的描述置于相似性、關聯性的邏輯框架中,而且總是能從這些描述中歸納出某種不在場的寓意,并在隨后的詮釋實踐中把此種寓意賦予相似的符號現象; 而“精神的領會者”則處于該詮釋階段的末期,該類詮釋者不只是通過總結經驗,揭示寓意,還擅長從中發現對未來的再現形式具有啟示意義的 “神秘”規律。
正因“寓意的渴求者”處于詮釋初期,所以作為一種詮釋活動學習者,他們總是在不斷地尋求與應用寓意。也就是說,正是《乃莉塔》與它的戲仿對象《洛麗塔》在形式修辭層面上的高度相似,致使了這類讀者的詮釋欲望總是無法得到及時的滿足。于是透過對細微差異的發掘,他們被引向文本背后的深層意圖。相反, 從現象的相似性與關聯性中,“精神的領會者”不但提煉出了“寓意”,還通過對這些寓意的歸納與分析,逐漸領會到文本的發展趨勢。是以,對該類讀者而言,熟悉的再現反而會過早地終結他們的詮釋欲望。所以,當《碎片》在形式修辭上帶給詮釋者一種 “陌異感”時,這種“陌異感”將可能喚起這些精神領會者的閱讀焦慮與探索興趣。
雖然如此,埃科真正的意圖并不是單純地給上述兩類 “天真”的讀者設置文本陷阱,他還向他們提出問題,以喚醒一種反思行動,正如他在《讀者的意圖》中所宣稱的那樣:
也見我對阿萊士(Allais) 的 《巴黎好人》(Un drame bien parisien)分析,那里展示了無論文本在多大的程度上一步一步地欺騙天真的讀者,但也在同時給予他們許多本應防止他們掉入文本陷阱的線索。顯然,這些線索只有在第二次閱讀的過程中才能被偵察到。
在他看來,為了防止讀者成為被文本結構所固定的 “唯一正確”(only right)的詮釋者,創作的啟示意義將意味著透過 “線索”(埃科在談論“偵探小說”時經常會使用到的一種隱喻)給讀者以警惕,并迫使其在 “第二次閱讀”(a second reading)中成為一種反思者。如此一來,詮釋者也就進入其所謂的 “批判性詮釋”(critical interpretation)層次。在該層次中, “詮釋者”將不只是意義的被動接受者、文本模式的遵循者,還是一位能夠借助反問、質詢,使文本的意義在不確定性中不斷增衍的敘事主體。當然,在此意義上,作為一種以詮釋為前提的二次創作,“戲仿”作品的客體性身份也發生了轉變,“戲仿”既能因此被視作一種繼承一定文藝傳統的美學策略、文學技法,又能在普遍意義上成為一種符號的自反性生產裝置。換言之,透過暴露衍義系統、文本結構與話語體系中的矛盾, “戲仿”不但不會讓自身解構為一次次無意義的書寫,還將 “意義”本身銘刻在 “實踐”的基石之上。
也許,上述就文本與讀者關系展開的思考,可以透過 “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一說來理解。如果說 “詮釋循環”在詮釋實踐的場域意味著以下的幾個周期性階段,即部分零散文本現象的積累、整體知識的獲得以及對其中抽象規律的把握,那么對于上述兩類讀者而言,決定他們成為敘事主體的關鍵并非是被動地追尋不在場的整全意義、終極規律,而是主動地去選擇從上述永無止境的“追尋”中返回到 “字面意義”(literal sense)上。該種選擇意味著,詮釋者必須重新面對零散且復雜的文本現象,并利用從探尋中獲得的 “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重塑一種“再現”。換言之,任何以“美學文本”(aesthetic text)形式再現的主體詮釋行動亦應需伴隨著對“平常語句”(ordinary sentence)的首次認知與重述。而以此角度觀之,“字面意義”既是對 “事實”再現,又可成為一種意義生產的藝術裝置(artistic devices)。而在周而復始的循環詮釋中,“字面意義”既因語境變遷具備道德意義(moral sense)、歷史價值(historical sense),還成為了一種具備 “隱喻”功能的 “寓言”。
根據上述闡釋,讀者的閱讀實踐與理解活動再次質詢了“戲仿”這一看似不言自明的概念下的復雜性。最后,我們可以《誤讀》為創作素材,從符號性衍義的角度,對該類文本的未來形態進行一番想像。讓我們試想一下,如果《乃莉塔》的讀者意欲在當代的歐洲語境中創作一篇主題為 “少女迷戀成年男性”的故事,那么《乃莉塔》或《洛莉塔》所暗含的那個永恒的敘事命題(即美學價值與道德倫理之間的沖突),又該以怎樣的形式呈現呢?如果《碎片》是一篇失憶癥患者所撰寫的日記體報告,那么怎樣的書寫才能使讀者不但能欣賞其破碎和混雜的美學形式,還能意識到這樣一種形式下所暗藏的表述意圖呢?
七、結論: “后現代” 語境下的回聲書寫
事實上,無論學者們如何界定 “戲仿”, 那些縈繞在“戲仿”概念四周的經典的議題,都將與每一個希望成為敘事主體的詮釋者密切關聯。更何況,在我們的思索中,一個亙古永存的恐懼總是揮之不去,即每一個個體都害怕成為不在場 “他者”的復制品。此種恐懼亦讓我們想起那位名為“回聲”(Echo)的希臘女神的故事。在奧維德的版本中,女神因用言語協助宙斯的私會而被赫拉懲罰,從此她無法再擁有自己的話語,只能不斷地重復戀慕對象的聲音。如果在這個故事里,我們把女神視為“讀者”,而把女神的戀慕對象及其言說視為“作者”與“作品”,那么當代的敘事似乎也在應驗這則來自遙遠時空的“寓言/預言”。但是,誠如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所言,在某種程度上,作為 “敘事體”的我們亦是“經驗、信息、我們所讀的書、想象的事物的一種綜合,”(un combinatoria d'esperienze, d'informazioni, di letture,d'immaginazioni)所以就該角度而言, “戲仿”創作無疑是以此為前提而進行的一種積極嘗試,即憑借詮釋行動,個體得以主動地擁抱自身的客體地位,以便在一種依存/博弈關系之中,把自身轉化為敘事的主導。事實上,一旦我們承認 “戲仿”是主體在其無法主宰的敘事中把握命運的方式,那么反之另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卻是,主體也必定是該種“宏觀敘事”的接受者。埃科曾用 “故事中的讀者”(lector in fabula)來強調讀者之于故事的必要性。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任何一位在其敘事中扮演造物主角色的敘事者也應該謙虛地認識到,他們不但受其敘事本身制約,還必須加入到一種協作性、公共性的敘事活動中。正因如此, 埃科認為 “戲仿”問題與時空密切關聯;哈琴、瓦爾德斯則堅持 “后現代”語境中的文本實踐對“戲仿”概念的界定至關重要;而羅斯的系譜考亦無法把敘事傳統與當代文藝現象相割離。
在《一位年輕小說家的自白》中,埃科曾把一種古典時代的修辭形式重新描述為 “過度鋪排”(excess prodigality)。在他看來,古典時代的創作者之所以常常使用此種修辭,是因為在 “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的語境中,他們對表達一種形而上的存在感到悵惘。但在當代語境中,伴隨著認識論的改變,該種悵惘逐漸轉化為了 “成熟文化”(mature culture)敘事中的一種革命性策略:
清單成了重新組構世界的一種方式,幾乎就是將泰紹羅(Tesauro)的方法付諸實踐——不斷積累事物的屬性,以便在相互分離的事物間找到新的聯系,并且也能對被常識所接受的那些關系提出質疑。未來主義、立體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各以不同方式啟動了既有形式的崩潰,而混亂的清單則成為這一崩潰的模式之一。
顯然埃科認為,處于 “成熟文化”階段的 “后現代”意味著一個不再 “單純”的時代。先驅們留下的歷史遺產既是財富亦是桎梏,它使當下的每一句言語都仿佛是來自歷史深淵的回聲。由是,曾經的 “先鋒派”(avant-garde)創作者們不得不憑借激進的行動,即所謂的 “為藝術而藝術”、“破壞過去”以及 “把過去毀容”,把文藝作品的再現形式純粹化、極簡化,以對抗普遍存在影響焦慮。當然,面對難以負荷的歷史遺產,出現了另一種看似更為 “保守”的聲音,即敘事者開始透過模仿 “他者”,回避其自身作為衍生物、復制品的 “真實 ”,也就是說,讓敘事者 “帶上面具”,也許我可以如此援用埃科在探討其創作策略時所使用的表達。在他看來, “面具”是 “一位年輕小說家”掩飾 “單純”,筑造一種可供其驅馳語詞的世界的方式:
事實上,我不僅僅決定講中世紀,我還決定身處中世紀講述,且借助一個當時的編年史作者的口來講。我在敘事方面從來是個新手,直至那時,我都是從另一個有所阻礙的方向看待敘事者們的。我從來羞于講故事。……一個面具,這就是我所需要的(una maschera, ecco cosa mi occorreva.)。我反復地閱讀中世紀編年史作家的書寫,為了獲取一種節奏,一種純粹。如果編年史家為我說話,我就擺脫了任何嫌疑。擺脫了任何嫌疑,卻擺脫不了互文性的回聲,我就是這樣重新發現了所有作家總是了然于胸(并且告訴過我們不知多少遍)的事情:一本書總是講著其他的書,每一個故事都在講一個已經講過的故事,……我發現,最終,在第一個例子里,一部小說與言語毫無關系(ho scoperto dunque che un romanzo non ha nulla a che fare,in prima istanza, con le parole.)。寫一部小說,是一件關系到宇宙學的事物,就像《創世紀》里的那些敘事一樣。
以上的敘事將會遭遇到的悖論是:“面具”的隱喻既是回避,卻又是始于主體內部的結構性裂隙的一種反擊。是以,它在遮蔽的同時也曝露了一種 矛盾的“真實”,即敘事主體往往借由遮蔽被誤認為真實的 “假面”,曝露了將被眾人誤認為虛假的 “真實”。最終, “戲仿”復雜性反倒使其作為一種 “互文性的回音”,一種 “講述其他故事的故事”成為了這個世故時代表達純粹、單純的特殊方式:
我考慮到后現代態度的時候就想到了下面的一種情況:一個男人愛上了一個很有教養的女人,并且他知道他不能對她說 “我絕望地愛著你”(“ti amo disperatamente”),因為他知道她已經知道(并且她知道他也知道)這些句子已經被作家莉爾拉(Liala)寫過了。但是有一個解決辦法。他可以說: “就像莉爾拉所說的那樣,我絕望地愛著你。”他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既避免了偽造的單純又清楚地表明他不能以這種單純的方式表述,這個男人還是向這女人說出了他想說的話:他愛她,但是是在一個單純墮落的時代愛著她。
這樣,作為一種針對“后現代”敘事困境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戲仿”不僅僅借由 “他者”的假面表達了主體的 “純粹”,還折射了這個時代、以及在這個 “世故”時代表達純粹的艱難。
Bibliography參考文獻
Aristotle.“Poetics.” In Poetics, On the Sublime and On Styl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alliwel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ighieri, Dante.Tutte Le Opere.Roma: Newton Compton, 1993.
Bakhtin, M.M.“From the Prehistory of Novelistic Discourse.”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Translated by Michael Holquist and Caryl Emers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No.1.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41-83.——.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Translated by Caryl Emerson.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Vol.8.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Calvino, Italo.Lezioni americane: sei proposte per il prossimo millennio.Opere di Italo Calvino.Milano: Mondadori, 2005.
Dentith, Simon.Parody.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Eco, Umberto.Confessions of a Young Novelist.Richard Ellmann Lectures in Modern Literature.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Diario Minimo.Milano: Mondadori, 1963.
——.Misreadings.1st ed.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 1993.
——.“Postille a ‘Il nome della rosa'.” In Il Nome della Rosa.Milano: Bompiani, 1983.
——.Sei passeggiate nei boschi narrativi: Harvard University, Norton lectures 1992-1993.Saggi tascabili 59.Milano: Bompiani, 2003.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Advances in Semiotic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Hutcheon, Linda.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1.
Kristeva, Juli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Edited by Leon S.Roudiez.Translated by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Roudiez.European Perspectives.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80.
Nabokov, Vladimir.“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 In Lolita.New York: Vintage, 1956, 207-11.
——.Lolita.New York: Vintage, 1989.
“pastìccio in Vocabolario-Treccani.” Accessed June 16, 2018.http://www.treccani.it//vocabolario/pasticcio.
Quintillian.Institutio Oratoria of Four.Translated by H.E.Butler.Vol.III.Books VII-IX.Harvard / Heineman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59.
Rorty, Richard.“Idealism and Textualism.” In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Essays, 1972-1980.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Rose, Margaret A.Parod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Cambridge;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Reception Theorists.” In Parod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Cambridge;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0-77.
Sklovskij, Viktor Borisovic.“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ices of Plot Construction and General Devices of Style.” In Theory of Prose.Translated by Benjamin Sher.Elmwood Park, Ill: Dalkey Archive Press, 1991.——.Theory of Prose.Translated by Benjamin Sher.Elmwood Park, Ill: Dalkey Archive Press, 1991.
Valdés, Mario J.Hermeneutics of Poetic Sense: Critical Studies of Literature, Cinema, and Cultural History.Theory/Culture.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