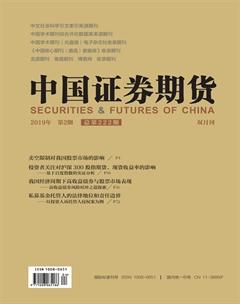英國公司治理中的股東會中心主義
張弛
摘要:英國作為現代公司制度的發源地對于普通法世界的公司治理理論與實踐持續發揮著重要的樣板作用。包括英國在內的英美法系國家的公司治理以股權分散(dispersed ownership)的所有權結構為基礎,進而形成了與大陸法系以及轉型國家風格迥異的公司治理發展道路。然而,股權分散模式其高昂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s)使小股東利益的保護成為英國現代公司治理中的難題與法制改革的核心議題。自2006年英國國會頒布新公司法以來,英國公司法逐步形成了以股東積極主義為基礎,以小股東保護為核心價值,以股東會中心主義為特征的公司治理模式。本文試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國股權市場的變革入手,以英國公司立法與司法判例為素材,詳細剖析英國現代公司治理的基本原理和價值取向并思考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治理模式的生存土壤與制度條件,從而為轉型中國的公司治理研究拋磚引玉。
關鍵詞:公司治理 英國公司法 小股東保護
一、分散股權結構與股東積極主義在英國的興起
自“二戰”結束至20世紀80年代,英國公司的所有權結構經歷了從集中到分散的發展過程,解讀其背后的政策與經濟背景對于理解現今英國公司法變革及其公司治理實踐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英國經濟在經歷了“二戰”的炮火摧殘后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能夠依靠自由市場恢復戰前的活力,同時千瘡百孔的英國社會也需要強大的公權力進行重建。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英國政府在戰后至20世紀50年代末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政策,同時,小型企業的發展也由于資金不足和市場疲軟等因素,發展較為緩慢,家族控制仍然在英國公司治理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換言之,英國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在20世紀60年代前仍然以股權集中為主要特征。實際上,股權分散模式最早出現于美國而非英國,其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早在19世紀后期,美國的股票交易所就建立了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以嚴格規制上市公司行為,保護投資者利益。相反,遲至20世紀60~70年代,英國才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規則,并且直到英國國會于1986年頒布《金融服務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倫敦股票交易所(LondonStock Exchange,LSE)才正式享有撤銷和中止上市公司非合規交易(non-compliance transac.tions)的權力。與此同時,英國本土的銀行、投資服務公司、大型律師事務所以及會計師事務所在這一時期也隨著英國股市的復蘇而迅速發展,進而使英國在歐洲金融服務領域拔得頭籌。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倫敦股市監管的規范化和金融服務市場的專業化直接吸引了大批海內外投資者向英國公司拋出橄欖枝——英國公司的所有權結構也因此從集中走向分散。
早在1932年,美國學者A.Bedes和G_Means在《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一書中指出:公眾公司股東所有權與控制權實際上已經因為股權的高度分散而產生了分離,進而產生了高昂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s)。在稍晚出現股權分散化的英國,公司股東——特別是小股東對于公司治理的管控以及自身經濟利益的維護越發無力。同時,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股權分散意味著股東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動力主動行使股東權,且由于每個股東持股比例的微小導致發起股東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左右公司治理的成本過于高昂。進而,手持大量資金準備投資英國公司的歐美投資人開始尋求專業的投資機構代為集中管理資本,從而增強股東在公司治理中的話語權。此外,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領導下的私有化浪潮為英國海內外機構投資者提供了豐富的投資機會,從而加速了以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在英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正是以上市場環境的變化與經濟改革措施使英國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在保持股權分散特征的同時出現了股權相對集中的回歸并直接催生了以股東積極主義(shareholder activism)為核心的英國公司治理變革。
按照歐洲公司治理協會(European CorporateGovernance Institute,ECGI)的定義,所謂股東積極主義是指‘股東得以通過主張其作為公司所有者的權力從而影響公司行為的一種方式。具體而言,西方現代公司治理理論中的股東積極主義具有以下三個核心特征,首先,股東通過行使公司法賦予的法定權利能夠有效影響公司決策;其次,股東積極主義可以降低董事會中心主義下產生的高昂代理成本;最后,股東大會通過行使法定權利可以對于公司管理層做出的不當決策予以及時修正從而減少公司治理失敗的風險。在英國現代公司治理實踐中,股東積極主義主要通過“公司法的契約化(contractualization of compa-ny law)”和降低司法干預的方式建構以股東會中心主義為核心的股東保護機制,從而提高英國公司治理的效率,維護公開資本市場的穩定。
二、英國《2006年公司法》與股東會中心主義
相較于以往公司立法,英國現行公司法(Companies Act 2006)在加強股東話語權以及保護小股東利益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構建的股東會中心主義治理策略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剖析,即公司契約(包括公司章程和股東協議)修改權中的小股東保護、公司決策中的小股東權利、股東對董事會的監督權以及類別股對于異質化股東權利的平衡。下文將從上述四個維度對英國《2006年公司法》中的股東會中心主義展開論述。
(一)公司契約與小股東保護
盡管英國現行公司法長達一千多個條文的篇幅使其成為現代立法中巨典式的龐然大物,然而,其中竟沒有關于股東具體權利的任何規定。盡管這一令人費解的立法現象與英國的判例法傳統息息相關,然而實際上其對于公司股東權力行使范圍之界定已經通過契約自由的方式授予了股東自身,從而允許不同公司根據自身特點在公司章程與股東協議中詳細規定股東會與董事會的權力分配。依據《2006年公司法》,任何企圖變更公司章程的提議僅需要由股東大會以持有不少于75%的股東表決權以特殊決議(special resolu-tion)的形式表決通過方具有法律效力。上述規定必然對于持股比例較小的股東構成了實質性威脅。對此,英國《2006年公司法》獨具匠心地引入了“剛性條款(entrenched provision)”制度加強對大股東修改公司章程權力的限制。根據該法第22條之規定,所謂剛性條款是指在公司章程中針對某些特殊事項如公司董事任命、股份轉讓等設定高于法定投票比例的股東會表決制度,從而有效制約大股東在公司治理的關鍵事項中對小股東的壓迫。在實踐中,剛性條款不僅被用于抬高股東表決票數,同時也常被用來針對特定事項附加特定股東許可,否則該項提案的股東會表決結果不具有法律效力。由此不難看出,剛性條款的應用將有效限制大股東在股東表決中的權力,增加小股東在公司治理中的話語權。
盡管剛性條款在維護小股東利益方面發揮了實質性作用,其對于某些持股比例微乎其微的小股東的利益保障仍然是存有疑問的,然而作為一部具有強烈法治精神的公司法典,平等地給予所有股東以平等和充分的保護是其應有之義。正是基于這一立法精神,《2006年公司法》第29條同時允許了在公司章程之外另行訂立股東契約(shareholdersagreement)的做法。在英國公司法實踐中,股東契約一般由全體股東一致達成并用以規定如公司顧問酬勞等公司管理事務之外的事項。由于股東契約屬于合同法的范疇,因此依據合同法基本原理,合同條款的修改非經全體合同當事人同意不得更改,進而股東協議的存在為持股比例難以達到公司章程以及剛性條款投票門檻的小股東提供了有力的保護。
(二)公司治理與小股東決策權
早在英國國會制定《2006年公司法》之前,英國學界和實務界就已經強烈意識到:強化股東在公司治理中的參與權將成為英國現代公司法發展的方向。在現行公司法中,小股東被賦予了更為便捷的治理權:首先,對于非公開公司,股東決議可以僅通過書面形式即可生效而不必召開股東大會表決;出于對小股東的保護,公司法允許持有公司不少于5%的投票權(或在公司章程中明確規定的比5%更少的投票權)的股東提出書面申請以干預公司決策。其次,對于公眾公司,公司法僅要求持有5%的投票權的股東同意即可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大會。此外,對于在倫敦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監管層要求凡是超過公司市值25%的交易須經股東大會批準才可執行。
此外,盡管英國公司法出于對契約自由的極大尊重從而放棄了股東公司治理權力分配規則的法定主義,然而對于股東締約能力的盲目信任也未必是降低公司治理風險的上策。對此,英國《公司示范章程》在賦予了董事會管理權的同時明確了公司股東就某一待定事項以股東會特殊決議的形式要求董事會從事或限制特定行為的權力,只要這一事項尚未被董事會決策。盡管在英國“遵守或解釋(comply 0r explain)”的金融監管體制下,《公司示范章程》僅具有參考性質,但在實踐中英國公司出于節約交易成本、降低合規風險的考慮,紛紛向《公司示范章程》中的治理規則靠攏。因此,英國公司股東的治理參與權也已經得到了市場和監管層的認可甚至是鼓勵。
(三)股東對董事會的監督權
依據《2006年公司法》第160條之規定,對于公眾公司(public company)兩名或以上董事任命,須由股東大會以單一決議(single resolu-tion)的方式逐一通過。除此之外,我們很難從法律條文中找到關于董事任命方面關于股東權力的界定。同時,出于公司決策效率的考量,英國《公司示范章程》規定,無論私人公司抑或公眾公司,董事任命僅由股東大會普通決議(ordinaryresolution)即可通過。換言之,如果僅從上述法律規定看,小股東仍然面臨著對于董事任命束手無策的窘境。事實上,英國現行公司法已經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賦予了股東會強有力的監督權,以約束董事會的行為。具言之,《2006年公司法》第168條第1款規定:“公司可以通過普通決議在某董事任期結束前免除其職務,無論該董事是否與公司簽訂任何契約。”該規定文字雖短,卻實乃賦予了公司股東對董事會持續性的監督權并排除了董事利用職務或控股股東身份之便阻撓小股東行使監督權的可能。因此,這一規定可謂是懸在英國公司董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時刻約束著公司管理者的行為。實際上,這一規定不僅要求公司董事時刻盡職管理公司事務,切實履行受信義務(fiduciary duty),同時,由于該規定沒有設定任何先決條件,故在實際運作中將迫使董事會在決策中不得不時刻考慮股東會的感受——一旦股東會對于董事會的管理不滿,即便董事會的行為沒有觸及法律底線,股東會亦有可能依據該條規定讓董事丟了飯碗。由此,我們不難再次感受到英國公司立法對于股東會中心主義的高度認可以及對于股東積極主義的制度性保障。
(四)類別股與異質化股東權利的平衡
盡管學術界在論述公司治理結構的時候普遍將注意力集中在董事會與股東大會之間的權力分配上,然而,股權設計與股權結構的微妙差異亦將對公司治理產生重要作用。英國作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發源地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母國,對于多元化以及契約自由的尊重不可謂不深厚。英國公司股權結構的分散化必然要求多元化的股權制度以滿足不同股東在公司治理中差異化的經濟訴求。進而,基于契約自由精神的類別股(class shares)制度在英國公司治理中扮演著越發重要的作用。根據英國現行公司法之規定,股份(shares)的本質乃是公司成員(members)的私有財產(personal property),公司股東享有決定公司股份面值以及股份轉讓等事項的權利。此外,《2006年公司法》明確了公司針對不同股東發行不同種類股份的權利。據此,英國公司的股東得以在同一股份中匹配不同的決策權和經濟權。在公司法實務中,應用最為廣泛的類別股莫過于普通股(ordinary share)和優先股(pre-ferred share)。前者擁有完整的表決權,但在公司分紅和破產清算時處于劣后的地位;相反,優先股則在放棄完整表決權的同時享有優先分紅、優先受償的權利。基于上述權利分配的靈活性,普通股和優先股混合使用的股權設計方案在英國公司,特別是私人股權(private equity)和風險投資基金持股的公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從而巧妙地平衡了側重公司控制權的公司創始股東和注重短期經濟回報的財務投資人的利益,將二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訴求通過股權設計方案予以合理表達。
三、司法保守主義:判例法中的股東權利救濟
縱覽英國公司法乃至整個商法制度的發展史,卷帙浩繁的普通法與衡平法判例構建了英國公司治理特別是股東權利保護制度的基本框架。然而,考慮到訴訟活動對于商業效率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早在英國國會制定《2006年公司法》前,英國法律委員會(The Law Commission)的專家們便就普通法中的董事義務規則在英國公司法中是否應當予以成文化展開了激烈辯論。同時,普通法派生訴訟程序冗長、裁定標準不清的問題也被認為有礙于英國公司適應瞬息萬變的現代商業社會。盡管如此,當代英國公司法實踐中的諸多基礎性規范仍然不能脫離于判例法規則的基本框架。特別是在崇尚司法保守主義的英國,法官通過推翻先例從而創制新的判例規范并非易事,經典判例中的股東權利救濟規則仍然時刻左右著英國公司治理的發展。下文將從公司契約變更中的小股東保護,派生訴訟的嚴格化以及不公平損害救濟制度三個方面闡釋英國公司法判例中的股東會中心主義以及《2006年公司法》對于上述判例規則的發展。
(一)公司契約變更中的小股東保護
如上所述,公司股東修改公司章程的權利受成文法保護,直至20世紀初,任何含有限制股東修改公司章程的合同條款通常被英國法院認定為無效。在一案中,公司章程中規定其創始人兼執行董事sy.mons及其遺囑執行人有權任命和罷免董事,且公司隨后在一份獨立合同中約定,公司章程不得修改。在Symons過世后,遺囑執行人與董事產生爭執,董事會以特殊決議的方式廢除了上述限制性條款并等到了法院支持。法院認為,公司章程的修改權屬于強制性規范,因而排除合同約定的空間。然而,如果完全放棄對于股東限制公司章程修改的異議權,也可能導致小股東在創制公司內部治理規范的話語權遭到大股東的踐踏,因此,英國司法實踐逐步承認通過股東協議的方式在公司章程之外對于公司事務予以限制,從而以股東自治的方式維護小股東利益。一案中,原告與另外四名公司創始人在公司成立后以股東協議的方式約定,未經合約各方一致同意,公司不得再發行新股。然而,公司董事會隨后提議要求股東大會表決通過發行新股的決議。Russel作為該股東協議的締約方遂發起訴訟,要求法院判定董事會的做法違反合同并發布禁止令(injunction)阻止股東大會投票。此案在一審、二審中,法官均以該股東協議限制了公司發行新股的法定權利為由認定合同無效。最終,原告不服上訴至英國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并獲得上議院法官的支持。上議院認為,盡管公司法賦予公司自身的權能(如發行股份)不可剝奪,但公司作為獨立法人,其自身行為與公司股東的行為應當予以區分,即股東個人之間關于限制公司章程修改的額外契約合法有效。換言之,如果在股東創設公司章程時設置了類似條款,那么,這一條款將因為違反公司法而歸于無效,然而,股東協議畢竟屬于合同法的范疇,因此,契約自由和股東自治原則是應當予以優先保護的——否則作為對抗大股東規則制定權的股東協議制度將失去實際意義。
此外,英國普通法在公司章程修改方面確立了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即修改公司章程必須是“出于善意的為了之公司利益”(actingbona fide in the interests 0f the company),從而防止控股股東濫用控制權壓榨小股東。在一案中,Lindley MR法官首次提出這一原則,即任何試圖通過股東表決權修改公司章程的行為必須能夠被證明乃是有利于公司的整體利益,如果其修改章程之行為僅僅增加了某股東的私人利益,那么這一修改行為將被法院認定為無效。此后英國法院承襲了這一測試原則并在實踐中發展出了更為具體的判斷方法,以確定在控股股東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同時因公司章程修改而獲益的情形下,該修改公司章程之行為的正當性。在ShuttleworthuCox Bros Ltd(1926)一案的判決中,英國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確立了“理性人原則(the reasonable men standard)”,即任何修改公司章程的行為應當通過以下兩個標準進行測試:(1)某一修改公司章程的行為是否在任何理性人看來都是符合公司整體利益的;(2)某一修改公司章程的行為是否如此的不合理以至于任何站在公司利益的理性人都不會做出這一修改公司章程的決定。總之,在判斷公司章程修改的正當性問題上,英國法官堅持保守主義的觀點,通過理性人標準對于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修改公司章程的正當性予以測試和判斷,而盡量回避以法官自身的主觀判斷干預公司內部決策。
(二)派生訴訟的嚴格化
派生訴訟(derivative actions)制度并非英國公司法獨有,但英國歷史悠久的判例法傳統使派生訴訟在維護公司以及公司成員利益的事業上尤其發揮著重要作用。英國公司法上的派生訴訟源自普通法上的“Foss規則”:在Foss u Harbottle(1843)一案中,法官Wigram認為:公司與公司成員分別享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因此當公司利益受到損害時應由公司而非公司股東代表公司提起訴訟。然而,在公司由公司董事會牢牢控制——特別是當違反義務的公司董事同時也是控股股東時,指望公司向加害方提起訴訟幾乎是天方夜譚。這顯然對于公司利益和小股東利益的保護都是非常不利的。在這一背景下,英國公司法逐漸發展出了上述原則的例外規則,即現在通行的股東派生訴訟規則。一般來說,所謂股東派生訴訟是指在特定情形下,當公司利益受到損害時公司股東代表公司向加害人(如違反受信義務的公司董事)提起訴訟以要求加害方履行義務或予以賠償。由此不難發現,股東派生訴訟在維護小股東利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它是以維護公司利益的面貌出現的。
普通法判例一般認為“對于小股東的欺詐(fraud on the minority)”是最常見也最為重要的股東派生訴訟的適用情形。英國法院認為,對于小股東的欺詐只有在同時滿足以下兩個要件時才允許公司股東提起派生訴訟,即欺詐行為(thewrong)和欺詐者利用其股東投票權控制公司的行為(wrongdoer control of the general meeting)o首先,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欺詐”要比普通法規則中的“欺詐(fraud)”寬泛很多——在Esman-co u GLC(1982)一案中,Megarry VC法官指出在欺詐小股東案件中,欺詐的認定不僅包括普通法規則中的欺詐,也應當包括任何濫用權力以產生相同欺詐效果的行為。雖然“欺詐”要件看似為小股東提起派生訴訟提供了巨大空間,然而,在第二個構成要件(即“欺詐者控制公司”)的認定標準上英國法院采取了嚴格主義的做法。早在Pavlides u Jensen(1956)一案中,法官指出:原告必須能夠證明加害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50%的投票權,才能提起派生訴訟。盡管在著名的Prudential Assurance co.,Ltd u Newman Indus-tr/es Ltd(No.2)(1982)判決中,法官認為“控制”標準應當不限于50%的股東投票權也應當包括雖持股不足50%但有能力對公司產生實際控制效果的情形,但在股權分散的英國公司中,試圖證明某一股東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是一件費時費力的事情,因此,英國法院依然傾向于就“控制要件”進行嚴格化限制并通常在投票權標準之外還要求大多數“無利害關系的小股東(disinter-ested minority shareholders)”也愿意提起派生訴訟,從而盡可能明確派生訴訟的適用情形,防止濫訴。
派生訴訟的基本規則源自歷史悠久的普通法判例,其司法程序的煩瑣以及原告證明責任的繁重都將對英國現代公司治理效率產生不利影響。因此,過度依賴于派生訴訟以維護小股東利益被認為是復雜且不明智的(complicated and unwise-ly)。基于這一考慮,英國《2006年公司法》對于派生訴訟程序予以了成文化,旨在盡量降低司法對于公司事務的干預并節約訴訟資源。根據英國現行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派生訴訟須經法院預審才有可能進入正式審判程序:在預審程序中股東必須提供足夠證據證明其有資格提起派生訴訟,否則法院將不予立案,且在法院預審程序中公司不必做出任何回應。此外,該法第263第2款規定了法官必須拒絕受理股東派生訴訟請求的情形,包括(1)被訴方是基于董事身份而促成公司成功之行為;(2)被訴方行為在發生前已經得到了公司的授權;(3)被訴方的行為雖然已經發生,但事后被公司追認。由是觀之,盡管股東派生訴訟在維護公司小股東權益方面功不可沒,但無論立法還是司法實踐,英國股東派生訴訟都被施加了更為嚴格的構成要件審查標準,從而防止公司治理淪為硝煙彌漫的股東名利場。
(三)不公平損害救濟
公平對待公司中的每一位股東是英國公司法實踐中的一項古老而重要的原則。盡管派生訴訟為股東在公司利益受到侵害時提供了一種獲得救濟的途徑,但畢竟派生訴訟規則保護的是公司獨立人格下的公司利益而非股東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因此,當獨立于公司利益的股東,特別是小股東的利益受到控股股東或公司董事的不公平對待并導致合法利益受損時,英國判例法認為應當通過司法干預為當事人提供單獨的法律救濟,這便是英國公司法上獨特的不公平損害救濟制度(unfair prejudice remedies)。雖然不公平損害救濟的基本規則同樣散見于判例法,出于簡化司法實務的目的,《2006年公司法》將其基本構成要件予以了成文化:一是根據該法第994條第1款之規定,公司成員在如下兩種情況發生時有權向法院申請不公平損害救濟,即(1)公司事務(company affair)正在不公平地損害全部或部分公司成員的利益,或者(2)某一被擬定的公司行為將有可能對公司成員造成這樣的不公平損害。二是如果法院認定公司的某一行為的確已經或將要對公司成員造成不公平的損害,則基于該法第996條之規定,法院有權向受害方提供如下救濟:(1)規制公司在將來的某一行為;(2)要求公司就某一行為作為或不作為;(3)授權該個人或數人以公司名義起訴;(4)要求公司在未經法院許可的情況下不得修改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中的某些特定條款;(5)允許其他公司成員或公司本身購買公司成員股份,且在公司購買其成員股份時按照公司減資處理。在實務中,由法院簽發指令要求公司或控股股東購買申請人股份是最為常見的救濟措施。
在不公平損害救濟制度的實務運作中,最為棘手的問題乃是對于“不公平”標準的認定。由于英國公司法從未就這一概念進行具體界定,因此法官的自由心證就成為了解答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在著名的一案中,Hoffman法官給出了被英國司法界普遍認可的兩個判斷標準:(1)公司作為以一定經濟目的(economic purposes)而產生的“人的聯合”(as-sociation of persons),其往往在組建這一聯合時便有相關章程存在,那么,具體的公司事務應當如何進行首先應當由章程條款進行規范。故在股東沒有違反公司章程的情形下,法院一般不能給予不公平損害救濟;(2)如果某些公司章程條款在實際執行中確實產生了與衡平原則(equitableconsiderations)明顯的沖突,法院可以考慮提供不公平損害救濟。對于所謂的“衡平原則”,必須要結合不公平損害救濟制度的適用范圍方能準確理解其在英國司法實踐中的主要含義。事實上,不公平損害救濟一般被應用于小型私人公司而非大型股份公司中小股東權利的救濟,正如英國公司法學者總結的:不公平損害救濟通常針對那些“類合伙(quasi-partnership)型公司”,因為在這類小型公司中股東們往往建立于充分的私人友誼和信任而攜手經營企業且公司成員多共同參與公司管理決策,故而在內部關系上具有類似于合伙企業的性質。因此,享有控制地位的公司成員在公司經營過程中試圖以各種方式排除部分公司股東參與公司管理的行為便被視為違反了衡平原則,有失公允和道義。
盡管不公平損害救濟一直被認為是英國公司法中獨具特色的小股東救濟手段,但實際上保守的英國法院對于這一司法干預的適用予以了嚴格的限制。首先,盡管法律并沒有剝奪大股東提起該類訴訟的權利,但司法實踐一般認為,大股東有能力通過行使投票權左右公司決策從而維護自身利益,因而沒有必要提起不公平損害之訴。其次,雖然公司成員對于正在發生或即將有可能發生的不公平損害有權申請司法救濟,但如果公司成員或公司股份的受讓方在成為公司股東前已經明確知悉可能發生的不公平損害,則法院亦有可能以此為由拒絕申請人的訴求。因為,作為公司的股東在受買股份前應當盡到理性判斷風險的義務并對自己的出資行為負責,而不能事后將全部風險轉嫁給法院,否則這是對于社會資源的一種浪費。此外,即便申請人有足夠證據證明其利益受到不公平損害,法院也未必會提供救濟,而是首先考慮公司內部是否已經彌補了申請人的損失。綜上所述,英國判例法中的不公平損害救濟制度同樣秉持司法保守主義,公司章程的具體約定是法官判斷是否給予救濟的最重要依據。此外,與派生訴訟一樣,無論是通過股東行使投票之不公平損害沒有得到公司內部救濟時才能尋求司法救濟——畢竟耗時耗力的司法程序對于任何以效率為先的商業組織都將造成不小的干擾。
四、域外反思:股東會中心主義何以可能
通過梳理英國現代公司立法與司法實踐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英國的股東會中心主義致力于解決股權分散所有權結構下的小股東保護問題并通過加強股東會權力和克制司法干預的方式激勵公司股東積極參與公司治理,維護股東自身權益。股東會中心主義治理模式不僅折射出英國作為世界金融資本主義強國對于市場效率的推崇和契約自治的尊重,同時也是英國偉大的民主傳統和平等觀念在商事組織治理中的最佳詮釋。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放諸四海皆準的公司治理理論和治理模式,在不列顛運用得如魚得水的股東會中心主義治理模式在其他社會環境是否依然能夠發揮其獨有的優勢便是值得探討的。實際上,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治理模式早在20世紀末的東歐轉型國家便進行了大規模的法律移植試驗,然而其結果卻是悲喜參半。因此,探究英式股東會中心主義得以生存的制度土壤便是頗具現實意義的話題。
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之痛源于其缺乏能夠及時替代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并迅速建立市場機制的法律體系。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在“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社會改革下試圖引入資本主義商法體系以期快速推行私有化。在兩位美國公司法教授的主持下,俄羅斯聯邦于1996年正式頒布《俄聯邦股份公司法》,其最大特征便是極力推崇以“自我執行模式(self-enforcing model)”為核心的公司治理結構。實際上,所謂“自我執行模式”的公司治理乃是建立于全面的股東會法定權利并將公司內部機制作為維護股東權益的主要途徑(例如:董事任命中的法定累積投票權;小股東救濟的決定權以及公司控制權變更后的小股東優先出售權等),而司法和金融監管體制則被置于輔助地位。然而,由于俄羅斯轉型初期的國企私有化直接由私人企業家接管國有企業產權,從而使俄羅斯公司的所有權迅速集中于極少數曾在前蘇聯政府和國企身居要職的個人手中。同時,由于近乎真空的金融監管體制和司法實踐無法為小股東提供有效救濟,俄羅斯建立的以股東會中心主義為藍本的公司法不但沒有為小股東提供有效保護,反而淪為了內部人瓜分公司財產、肆意壓榨小股東的幫兇——至此,俄羅斯公司完全淪為了大股東分贓的野蠻戰場。
波蘭作為轉型國家的另一個代表,其公司法的制度移植效果卻與俄羅斯截然不同。波蘭的市場化改革始于1989年并于翌年恢復了商事立法。與俄羅斯相似,波蘭的《公司法》也同樣賦予了股東以廣泛的權利(包括小股東否決權、小股東異議權、優先股制度等)。然而,波蘭政府在實施私有化政策時沒有將國有企業產權直接轉讓給私人,而是首先由波蘭財政部建立投資基金收購國有股份再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出售股份給機構投資者。故而波蘭的私有化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公司內部形成大股東壟斷公司控制權的現象。此外,波蘭早在1991年就頒布了證券法并建立了統一的證券監管機構,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市場和信息披露機制并最終贏得了海內外投資者對波蘭公司的信任。也正是在相對完善的外部救濟機制的支撐下,波蘭公司法賦予股東的廣泛權利才始終沒有違背其保護小股東利益、增進公司治理效率的良好初衷。
通過觀察上述兩個轉型國家引入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法的經驗教訓,我們不難發現,英國式的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法固然為股東自主參與公司治理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并對契約自治予以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然而,其自身制度優勢的發揮有賴于公司股權結構的平衡。換言之,如果公司所有權結構中存在“一股獨大(single majorityshareholder)”的現象,那么,被賦予了廣泛權利(力)的股東大會將立刻淪為大股東壓榨小股東的工具,進而其制度設計的初衷將被徹底違背。其次,公司股權結構的分散化也只是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法得以良性運轉的必要條件——在公司法賦予股東(特別是小股東)以廣泛自治權的同時必須及時建構有效的外部救濟機制,在小股東利益受到損害而又難以通過公司內部機制獲得充分救濟時,唯有強大的司法與監管體制才能為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治理模式下的公司股東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五、結語
公司治理理論的發展、創新與特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密不可分,無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尚處于經濟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其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都必須能夠與一國自身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背景相契合。本文回顧了英國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治理模式誕生和發展的社會背景并認為英國公司分散的股權結構乃是促使股東會中心主義在英國公司治理中得以迅速發展的社會基礎。同時,本文通過詳細梳理英國《2006年公司法》,試圖將英國立法在完善股東治理權以及加強小股東自我維權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予以一一呈現。此外,通過解讀英國普通法判例并結合英國現行公司法的具體規定,本文認為:英國股東會中心主義公司治理模式在實務中不僅體現為小股東保護機制的內化發展,也體現為司法干預權的大幅度收縮。正是以上兩種機制的配合使得英國公司治理在不放棄傳統普通法規則體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要求股東在參與公司治理的時候做到理性決策并尊重股東間的契約精神,同時盡量減少司法干預對于公司正常經營的干擾,節約社會成本。最后,通過對比東歐轉型國家在引入股東會中心主義治理模式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本文認為:英國立法中的股東會中心主義在轉型國家得以成功運作的前條件之一乃是公司股權結構的相對平衡,同時,完善的外部司法救濟和監管體制仍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無論是在崇尚股東自治的英國還是自身缺乏監管制度根基的轉型國家,完全依靠股東理性實現公司治理的公平與效率都將僅僅是一個美好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