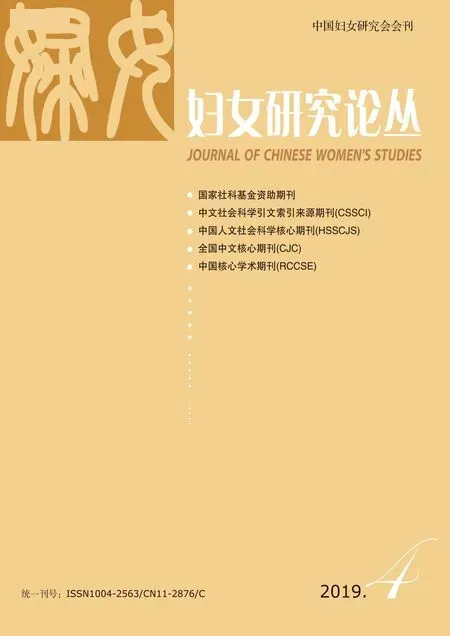韓國“慰安婦”議題的形成、發展過程與社會意識問題*
[韓]李貞玉
(1.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350;2.天津外國語大學 亞非語學院,天津 300204)
韓國“慰安婦”問題因韓日外交、社會觀念和個人心理傷痛等原因被塵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40年間鮮少被提及。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在韓國女權運動發展和女性權利意識崛起的前提下,經過社會團體的不懈努力、受害者的公開證言、媒體的報道、民眾的討論和聲援等活動,“慰安婦”問題由一個靜態的歷史問題發展為由一系列事件推動的具有現實影響力的社會議題。本文試圖梳理韓國日軍“慰安婦”議題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并從口述文本化、受害者權益和民眾心理等多個角度分析“慰安婦”議題的建構與傳播及其背后所隱含的基礎共識與多重分歧。
一、韓國“慰安婦”問題的歷史背景
1931-1945年,為防止大規模強奸行為、性病傳染以及軍事機密泄露,日軍在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等地強制征召年輕女性,將她們集體收容在前線和占領區的慰安所,成為日軍的性奴隸。由日本民間主導的隨軍慰安所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就存在,而日本軍隊主導建立的隨軍慰安所則始于20世紀30年代。1931年,日本海軍在上海以“貸座敷”(日本公娼制度中對取得官方經營許可妓院的稱呼)為基礎建造了海軍慰安所,成為慰安所的范本,隨后,日本陸軍開始在占領區各地建造慰安所。1937年,日本軍隊開始系統設立隨軍慰安所。
收容在慰安所中的女性年齡一般為11-30歲不等,規模較小的慰安所有七八人,規模較大的慰安所有四五十人。此外,戰爭期間日本在庫頁島和日本九州等地區為了推動軍工廠及戰爭建設相關公司的發展,以強制勞動的工人為慰安對象,政府和企業聯手運營了企業慰安所,亦有大量女性被征召。



嚴格來講,女性“挺身隊”不能等同于日軍慰安婦,但從殖民時代到現在,韓國社會常常用“挺身隊”指代“慰安婦”,原因是當時“被日本拉走就意味著失去貞潔”的認識比較普遍,而且“挺身隊”的女性也有一部分被送進了慰安所。因此,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等民間組織的活動均圍繞“慰安婦”問題展開,韓國語境下談及“挺身隊”問題也普遍默認成“慰安婦”問題。
韓國“日軍性奴役受害者”問題的社會議題化建構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逐漸開始的,當時伴隨著韓國民主化運動中女性運動和勞工運動的開展,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等民間社會團體提出“慰安婦”的歷史問題。在此之前,“慰安婦”問題僅少量存在于文學作品中對相關歷史的描寫,并沒有形成社會議題。
二、韓國“慰安婦”社會議題的形成過程
1945年8月15日,朝鮮半島取得獨立。1948年8月,大韓民國成立。戰爭結束后,相當一部分日軍性奴役受害女性被當場槍決,或被逼迫自殺,也有一部分幸存者回到了韓國。日軍性奴役受害者是戰爭期間日本軍隊性暴力行為的犧牲品,遭受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創傷,在當時的韓國父權社會中備受歧視和排斥,由于貞操觀念等原因,她們自身也感到羞恥,不愿提及慰安所的經歷。戰爭結束后“慰安婦”并沒有被明確為日軍強制征召的受害者,甚至社會輿論中還存在“賣春”的說法。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的將近40年間,由于韓日間外交關系、韓國社會倫理意識、個人對于傷痕記憶的壓抑等諸多原因,韓國的日軍性奴役受害者不得不保持沉默,集體處于失聲狀態,韓國社會對“慰安婦”問題也反應冷淡。
“慰安婦”問題在韓國社會開始引起反響的一個重要事件是1991年7月18日,有過從軍“慰安婦”經歷的金學順打破沉默,發表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證言。這也是韓國女性以“慰安婦”身份出現的首次公開證言。“慰安婦”問題被揭開,一方面是受到韓國女權運動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民間組織的不斷努力,金學順也是在民間組織的協助下得以公開發表證言的。在金學順公開發表證言的當天,多個民間組織聯合組成的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召開會議,向韓日各界發送公開書函,并向國會發出請愿書,要求韓國政府關心和解決有關“從軍慰安婦”問題的6個要求事項[1](PP 320-331)。金學順的證言鼓舞了更多受害者發聲,一些受害者陸續公開發表證言,展開對日本侵害行為的控訴。1991年12月,“從軍慰安婦”受害者文玉珠、金富善先后發表證言。日軍性奴役受害者站出來揭露日軍罪行,揭發被遮蔽的歷史事實,成為韓國“慰安婦”社會議題發展的基本前提。1991年12月6日,日本官房長官加藤纊一發表“日本政府困難對付從軍慰安婦問題”的言論,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向日本大使館發表公開書函提出抗議,表示決意定期游行,直到“從軍慰安婦”問題解決[1](PP 320-331)。

有關“慰安婦”問題的研究隨之在韓國學術界和民間機構展開。1992年1月,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發現了戰時資料《陸支密大日記》并公開發表,其中披露了關于“從軍慰安婦”的重要記錄。此后,吉見義明聯合日本其他學者成立了日本戰爭責任資料中心,圍繞“慰安婦”議題展開資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公開日本防衛廳防衛資料室收集的日軍回憶錄等材料,以施害國的身份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成果,出版了《從軍慰安婦資料集》,這對相關史料不足的韓國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慰安婦”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系列證據以及韓國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壓力下,1993年8月4日,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就“從軍慰安婦”問題發表了“河野談話”,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認強制征召“慰安婦”的事實。
韓國研究界在“慰安婦”問題歷史資料收集上遇到了較大困難。一方面,較多重要資料被日本政府和軍隊銷毀;另一方面,大多數有價值的史料在日本和中國兩地,很多重要的資料未被公開。因此,韓國研究界初期研究主要以已經公開的資料和證言為基礎,集中于以口述證言揭露日本罪行,對“慰安婦”事實進行確認。與此同時,并行展開對受害者的生平研究。“慰安婦”的證言和口述資料對復原歷史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朝鮮居住的樸永心曾通過口述證言敘述了在中國充當“慰安婦”的經歷以及在昆明美國管轄的俘虜收容所的生活,美國情報部門和軍隊的報告書和照片印證了樸永心的證言,后來參加云南地區作戰的一名日軍士兵證言被發掘,多重史料交叉印證了史實。

經過韓國各界十多年的努力,“慰安婦”問題從塵封的歷史變成韓國社會和民眾最關心的社會議題之一,并獲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日本政府對“慰安婦”問題的態度在韓國不斷受到強烈批判。
三、圍繞口述文本化展開的“慰安婦”議題傳播以及其后受害者權益的保障

慰安婦受害者口述文本化活動,一方面收集證言和史料,以證言的形式揭露罪行,這有助于確認“慰安婦”事實,核實日本帝國主義對日軍性奴役受害者實行征召的強制性;另一方面采用受害者口述生平史的方法,重視她們的語言內容和主觀感受,以日軍性奴役受害者的個體經驗和記憶創造公共歷史。無論戰爭期間還是戰后,“慰安婦”群體基本都是韓國社會結構中的底層,往往受到他人、社會環境和制度的多重排斥。慰安婦受害者的口述生平史關注作為女性的“慰安婦”的個人經驗,重視主觀感受敘述。日軍性奴役受害者在強制征召時期遭受性侵犯和性暴力,造成了身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后遺癥。口述文本化重視受害者的生平史,將受害和創傷的歷史一直延續到當下,通過深入訪談,關注她們的經歷和創傷,以及性奴役造成的肉體和精神的后遺癥對當下生活的影響。其后韓國國內外政策對“慰安婦”的支持和資助,也是以證言為基礎展開的。
除了通過口述研究確認受害者的事實之外,韓國學界還進行了歷史學、女性學、心理學等多個層面系統性的研究,如“慰安婦”制度的成立和運營狀態、作為施害者的日本兵心理分析、受害者的精神后遺癥、日本的法律責任等。
戰爭結束后,慰安婦受害者回到韓國,往往和家人斷絕聯系,不愿回老家,且難以維持生計。有人放棄了婚姻,年老后無人贍養。也有人滯留在中國,缺乏返回韓國的途徑,直到中韓建交之后,才恢復國籍。一些慰安婦受害者當初由朝鮮到中國,已經無法再回到朝鮮,與家族離散。



四、“慰安婦”議題的社會意識:基礎共識與多重分歧
目前韓國社會整體形成了關于“慰安婦”問題的基礎共識,對于日本提出的諸如“慰安婦”是否自愿參與隨軍慰安、“慰安婦”是否是戰時公娼等議題的討論,持堅決否定的態度,形成全社會憤慨之勢。歷史教科書中“慰安婦”部分的編纂、術語的使用也逐漸形成統一的歷史表述。對慰安婦受害者身份的質疑成為韓國社會無法容忍的言論,韓國大學中甚至出現了對“慰安婦”問題持不同看法的學者因被視為發表不當言論而遭解職的情況。

對于整個韓國社會而言,“慰安婦”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罪惡的受害者,而且作為日據時期韓國民族遭受屈辱的縮影,成為歷史傷痛的象征,因此“慰安婦”問題又聯結著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日本右傾化等多個議題。而關于“慰安婦”問題,在韓日政府之間、韓國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韓日民間社會之間多個場域,也存在著多重分歧。

韓國民間團體也認為日本方面的反應不夠充分,繼續要求日本政府和加害者公開謝罪并進行法律賠償。日本政府應當被追究國家責任,日本軍人、公務員及部分個人招募性奴隸,設置、運營慰安所,應追究個人刑事責任。1992年1月8日,日本首相宮澤喜一訪韓之前,慰安婦受害者向日本駐韓大使館轉達了要解決“慰安婦”問題的訴求,大使館沒有回應。民間組織自此開始定期抗議集會,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前開展“星期三示威活動”,提出日軍要承認對“慰安婦”的犯罪行為、道歉并進行法律賠償、處罰相關人員等一系列要求。“星期三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今天,并作為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示威活動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隨著韓國慰安婦受害者不斷離世,人數不斷減少,少女像成為韓國慰安婦受害者的象征,而少女像問題逐漸成為慰安婦問題最重要的指向之一。少女像具有受害者、傷痛記憶和“星期三示威活動”的多重象征意義。首個少女像誕生于2011年12月,當時為了紀念“星期三示威活動”20周年,在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組織下,經過公眾募捐,由知名雕塑家完成名為“和平碑”的少女像,立在日本駐韓大使館門前。日本政府就駐韓大使館門前的少女像撤出和搬遷問題與韓國政府不斷交涉,這個過程反而強化了少女像作為抗議運動象征的形象。之后,韓國各處的少女像數量不斷增多。

雖然《韓日慰安婦協議》并沒有出現“強制拆除”等詞匯,但該協議簽署的第二天,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等團體就開始發起全民反對協議的運動,韓國年輕人自覺加入保護少女像的隊伍,首爾大學生24小時守在少女像跟前,以防少女像被拆除。2016年12月,位于釜山日本領事館后面道路的少女像一度被拆除,但是通過釜山民眾和大學生的力量,又重新豎立起來。2016年10月底開始在首爾舉行的燭光示威(要求樸槿惠下野的抗議游行)中,一度出現過巨大的少女像,樸槿惠政府被認為在“慰安婦”問題上失誤頗多,受到各界強烈的批評。按照《韓日慰安婦協議》,韓國政府需要協助拆除少女像,但之后少女像劇增,到2017年8月15日,韓國至少有80余座少女像,韓國中學還發起了百所中學建像運動,美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等處也建成并豎立了少女像。2017年5月,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在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電話中表示,出于尊重國民心理的考慮,日本政府要求韓國政府盡快拆除少女像是不現實的。
韓國文在寅政府擱置《韓日慰安婦協議》之后,重申了“慰安婦”問題的國家立場:在“慰安婦”問題上,日本政府從國家立場上有責任,但韓國政府不愿意因慰安婦個人的補償問題而影響韓日之間的外交關系,也不會圍繞《韓日慰安婦協議》展開法律論爭,但“慰安婦”問題終究還是人權問題,韓國政府會爭取在聯合國等國際舞臺上獲得支持并展開活動。換言之,韓國政府支持為贏得國際輿論的各種活動和慰安婦個人對日本提出補償的請求,但不會將“慰安婦”問題提升為韓日間正式的外交問題。韓國政府這一立場顯然是考慮韓日外交關系、民間力量等多個因素所提出的符合政府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五、結語
多種力量的協作與對抗共同推動了“慰安婦”議題的擴散,多重分歧的存在也將使“慰安婦”議題得到更充分的討論和更持久的傳播。有關“慰安婦”的討論不是單純的日本方面是非對錯問題,圍繞議題采取的措施也不只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手段,國家地位、民族尊嚴、公眾情感和政要形象等因素都夾雜其中,難以剝離。“慰安婦”議題隱含了韓國遭受的歷史傷痛,在韓國國內形成了相對統一的基礎共識,但在此之上又存在著多重分歧,包括民眾與部分學者對“慰安婦”問題所持態度的分歧,民眾對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政府對日本所做妥協的不滿等。雖然各方一直提出追求基于“歷史和解”共識,但就韓國方面而言,對于“慰安婦”問題,國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持續高漲,尤其對于日本殖民地時代所遺留的歷史問題更加敏感,這點從國內對于“慰安婦”問題歷史敘事中“受害者”意識不斷加強也可以看出來,甚至各方對于“慰安婦”問題的分歧并沒有趨向解決,而是不斷加劇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