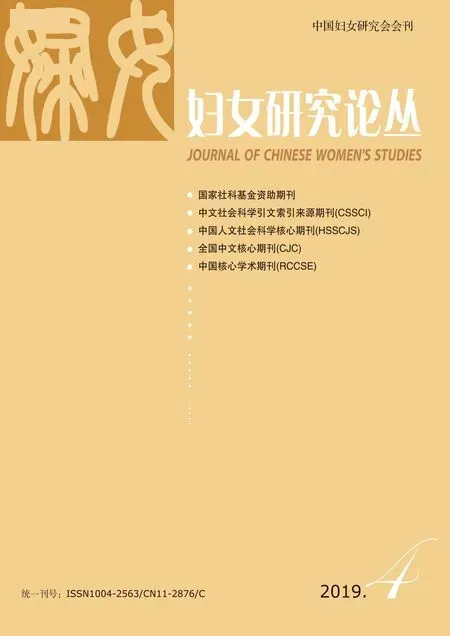陪讀媽媽:性別視角下農村婦女照料勞動的新特點*
——基于陜西省Y縣和河南省G縣的調查
吳惠芳 吳云蕊 陳 健
(1.3.中國農業大學 人文與發展學院 社會學系,北京 100193;2.英國謝菲爾德大學 社會學系,謝菲爾德 S10 2TN)
一、研究背景
照料勞動包括涉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家務勞動以及對兒童、病人和老年人的直接照料[1]。目前關于照料勞動的研究主要和女性就業機會、女性地位與性別關系等問題相聯系,且這類研究集中討論其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呈現[2](P 8)。關于有酬照料勞動的研究,尤其是“全球照料鏈”(global care chains)的討論,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女性流動到發達國家與地區從事有酬照料勞動并引起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照料赤字及福利不平等的相關問題[3](PP 369-391) [4](PP 1-21)。關于中國的照料勞動問題,已有研究多聚焦家庭照料勞動負擔對城市女性就業或從事其他有酬勞動機會造成的影響[5](PP 43-54)[6](PP 61-68)[7](PP 9-10)以及家政女工問題[8](PP 51-57)[9](PP 16-21),但后一類研究更注重流動女性務工人員的權益問題,并沒有特別強調有酬照料勞動的分析視角。關于中國農村照料勞動的研究包括了農村兒童照料服務的質量及其政策意義[10](PP 55-71),也涵蓋了照料老人對農村女性勞動時間的影響[11](PP 1-15)。總體來說,照料勞動作為一種分析視角,在農村婦女的研究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采納。
與農村婦女照料勞動問題相對應的是兩大社會現實問題:一是勞動力鄉城流動背景下的農村婦女照料勞動與責任問題;二是近十多年內發生的農村教育快速轉型。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非農產業流動規模的持續擴大,無論是“離土不離鄉”的本地非農產業就業,還是“離土又離鄉”的外出務工,以務工收入為主的非農收入對農村家庭的貢獻率越來越高,農村家庭的生產功能不斷弱化,情感功能與照料功能變得越來越重要[12](PP 64-66)。同時,由于傳統“社會性別規范”[注]查菲茨的“性別公正理論”中的一個概念,見喬納森·H.特納著,邱澤奇等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176-180頁。(gender norm)的影響,農村婦女依然承擔著照顧和教育子女的責任。因此,在勞動力流動的背景下,留守在農村的女性不僅承擔了對子女物質生活的照顧,而且成為家庭教育的主角和學校教育的配角。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3.2%的留守婦女正在照顧至少1個未成年子女,其中35.5%的婦女照顧兩個未成年子女[13](P60)。即使有流動的機會,她們在流動與留守狀態之間徘徊的人生軌跡亦隨著照料責任的變化而不斷變化[14](PP 178-190)。在這一時期,農村婦女從事的照料活動主要在鄉村完成,本文將其稱為“在鄉照料”。但是,在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政策實施逐步深入并導致縣域內城鄉教育資源重構之后,農村婦女照料勞動的空間、內容和形式也發生了變化。
進入21世紀后,農村教育政策對農村家庭照料勞動的安排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使農村學校數量銳減,大量農村兒童進城讀書。有研究指出,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使得農村小學數量由2001年的416198所減少至2015年的118381所,下降幅度之大、時間之短,為歷史所罕見。在城鄉發展程度差異和城鄉優劣觀念的影響下,辦學城鎮化,村落教育衰弱,造成了“文字上移”現象[15](PP 110-140)。這一現象背后的原因包括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衡、城鄉學校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農村家庭經濟收入提高、家長對子女的教育預期提升等[16](PP 66-74)。現有研究的主要關注點是學生的成長與學校教育管理問題,如教育的城市導向、寄宿制問題、教育資源浪費、村莊的離散凋敝[17](PP 2-12,P 188)等。與之相伴的農村家庭照料安排則是愈演愈烈的陪讀現象。有研究顯示,全國各地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陪讀現象,西部地區或經濟欠發達地區尤其明顯。已有研究不僅文獻數量較少,而且主要關注陪讀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學生的教育質量問題[18](PP 97-112)[19](PP 249-251)[20](PP 121-124)[21](PP 53-54),鮮有研究專門關注進城陪讀的農村女性群體。本文所討論的“陪讀媽媽”,是指為了給進城讀書的子女提供日常照料而陪讀的農村婦女群體。借助關于勞動力“離土”與“離鄉”的討論,與前文所講的“在鄉照料”相對照,本文將陪讀媽媽的照料勞動定義為“離鄉照料”。對于農村婦女來說,“離鄉照料”既是其承擔照料勞動的一種形式,也是其流動的一種形式,但它又與農村女性勞動力為尋求有酬勞動機會的流動相區別——婦女通常在縣域內流動,從事的勞動以家庭照料為主,處于無業或不充分就業狀態。
本文期望借助照料勞動的分析框架和性別分析視角,關注“陪讀媽媽”這一個獨特的照料者群體,試圖揭示農村婦女照料勞動的新特點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對陜西省Y縣8位陪讀媽媽、河南省G縣12位陪讀媽媽[注]為了保護被調查者隱私,本文所用案例均做了化名處理。的深度訪談,本研究形成了20個陪讀媽媽的典型案例資料。同時結合對這2個縣4所學校的4位教師、3位村干部、婦聯工作人員、教育局工作人員的訪談,以及針對家長的小組訪談,嘗試探討以下4個問題:第一,陪讀媽媽群體形成的社會條件和家庭照料分工策略;第二,陪讀生活對婦女個體的影響;第三,陪讀媽媽在陪讀地(通常是縣城)的社會融入與社會排斥問題;第四,陪讀這樣一種“離鄉照料”勞動對于婦女發展與鄉村社會文化的意義或影響。
二、陪讀媽媽:農村家庭教育期望攀高與教育資源走低的結果
前文提到,西部地區或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陪讀現象更為明顯,其主要原因在于,越是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教育資源越有限,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和教育質量差距越顯著。本研究以筆者2016年和2017年分別在陜西省Y縣及河南省G縣開展的實地調查為基礎。Y縣和G縣均有數量龐大的陪讀媽媽群體,但在形成原因、群體特征、社會融入以及縣城社會對其的態度等方面,有共性也有差異,因此既能表現陪讀媽媽的群體性特征,又能展示其在不同社會情境下的多樣化特征。
陜西省Y縣陪讀媽媽群體的出現與農村家庭收入提高、農村家庭教育期待提升以及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學校數量的銳減是同步的。Y縣地處山區,地理位置較為偏僻,20世紀90年代初Y縣農村勞動力開始外出務工,外出規模迅速增長,至20世紀末達到高峰。但是,外出的勞動力以男性為主,女性多在家務農、照料家庭。21世紀初,隨著Y縣不斷出臺相關支持政策,當地的林果業得到快速發展。一方面,林果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另一方面,林果業的收入較傳統糧食作物收入高得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緩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速度。隨著當地農民收入的不斷提高,農民對子女的教育期待也不斷提升。然而,同一時期,Y縣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2002年,Y縣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工作。據縣教育局統計,2003年,全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為200所。2015年,經過十余年的農村學校布局調整之后,全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僅有27所,甚至還有數所農村學校的在校生數量不足50人。通常情況下,一個鄉鎮有1-2所中心小學和1所初中,且往往會獲得高額的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有新建的教學樓,圖書及教學設備等配備齊整,但由于鄉村整體的落后狀況、教師待遇低等問題,鄉村教師不斷流失,教學質量難以保證,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學生流動到縣城就讀。2016年,在農村義務教育學齡段兒童中,94.4%在縣城學校就讀。無論是初中還是小學,農村學生的比例都在逐年增加。進城讀書兒童日益低齡化,甚至延伸到幼兒園時期。縣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超班額現象十分突出。例如,Y縣A小學43%的學生來自農村,有陪讀家長,且80%以上的陪讀者為母親;B中學7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有陪讀家長,其中78.8%的陪讀者為母親。陪讀媽媽和孩子大多在縣城租房居住,聚居在特定區域。通過觀察陪讀家庭聚居的居住區,筆者發現,這些家庭大多租賃面積20-30平方米的房屋,既有平房也有樓房,居住空間較為擁擠,但通常離孩子就讀的學校較近,以方便上學。總的來說,Y縣農村家庭的教育期望日益攀高,農村學校的方便程度和教育質量卻逐漸走低,導致農村兒童大量進入城市就讀,陪讀媽媽群體隨即出現。
G縣是河南省人口大縣,也有數量龐大的農村學生帶著“陪讀媽媽”進入縣城讀書。20世紀80年代初,G縣已有人外出務工,是河南省農村勞動力最早外出務工的縣之一,目前該縣有超過一半的農村勞動力在外地務工,形成典型的“打工經濟”。與陜西省Y縣相似的是,G縣農村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期待也較高,但經歷過波動。20世紀90年代,是當地打工經濟最盛行的時期,大部分農村家長并不追求孩子上大學,多希望孩子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掙錢。進入21世紀,G縣人員的務工類型開始轉變,工廠就業、自主創業者增多,務工者逐漸意識到受教育程度對其職業發展的制約,教育期待開始攀升。與陜西省Y縣不同的是,盡管G縣也執行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布局調整政策,但因其人口總量大、地勢平坦、居住集中,被撤并的農村學校并不多,對農村學校格局的影響不大。對G縣農村學校影響較大的是教師問題。早期,G縣每個村都有一所小學,教師多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聘用的民辦教師。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民辦教師辭退工作的逐步推進,民辦教師數量銳減,村級學校開始合并。經過10年左右的調整,G縣重新形成了學校格局并延續至今——基本每2-3個村有一所小學,每個鄉鎮至少有一所初中。但是,盡管縣教育局不斷出臺政策鼓勵為鄉村學校聘任新教師,但年輕、高水平教師流失現象越來越嚴重,對鄉村學校的教育質量產生了不良影響,也促使農村家庭開始尋覓更好的教育資源。
與鄉村學校下坡式發展不同,G縣縣城教育快速發展,尤其是私立學校教育的發展引人注目。2008年,G縣教育局發布了一系列鼓勵和支持私立學校發展的政策,包括同意公辦學校教師到私立學校任職等。總的來說,私立學校對農村學生及家長更有吸引力主要在于:第一,教師工資幾乎是公立學校的兩倍,吸引了大批高水平教師入校任職;第二,學校管理嚴格,實行教學業績考核制度,以學生考試成績衡量教師業績;第三,開放招生,只要付得起學費即可入校。因此,一方面是鄉村學校優秀教師流失、教育質量下降,另一方面是縣城私立學校師資水平高、教學質量高、管理嚴格。近10年時間,越來越多的農村學生進城就學,縣城學校尤其是私立學校的學生規模迅速擴大。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鄉村學校的在校生數量迅速縮減。例如,全縣學生規模最大的4所私立中學,在校生數量均超過5000人。由于私立學校沒有住宿條件,農村進城讀書的學生只能住在校外,需要家長陪同照料,因而催生了規模幾乎同等龐大的陪讀媽媽群體。大部分陪讀家庭在縣城租房陪讀。由于G縣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起步較早,部分務工人員收入較高、有一定積蓄,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陪讀家庭在縣城購房。可以說,G縣農村兒童被日益走高的家庭教育期望推出了教育質量下降的農村學校,縣城快速擴張、教育質量高、完全開放的私立學校則吸納了這些學生,同時伴生了大規模進城的陪讀媽媽群體。
三、離鄉照料:農村女性的勞動固化與人身依附
兒童教育流動與陪讀媽媽群體的形成,與城鄉學校布局和教育發展密切相關,陪讀媽媽的生活狀態卻與縣域經濟發展狀況有更大的關系。根據陪讀期間是否務工或務農的情況,本研究把陪讀媽媽分為全職陪讀和就業陪讀兩類。陜西省Y縣地處黃土高原,全縣人口約12萬,其中縣城常住人口約6萬。該縣農業經濟以林果業為主,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留在本地務農,林果收入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Y縣縣域工業較為落后,工業產值不及工農總產值的1/5。然而,Y縣卻是一個教育大縣——縣城常住人口中,學生人口占1/3左右,其中包括周邊縣來Y縣知名高中就讀的學生。大量的流動學生造就了規模龐大的陪讀媽媽群體。據縣婦聯調查,全縣有2617名陪讀媽媽在學校周邊地點租房居住。河南省G縣位于平原地區,全縣人口約180萬,縣城常住人口約27萬,市區初具規模、人口密度較大。該縣糧食產業發達,機械化操作程度高、農業勞動力需求較低,農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來源中占比較低。該縣目前約有70萬人在全國各地務工,務工收入是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決定了縣城就業機會的種類和數量,也影響了陪讀媽媽的就業機會。
(一)全職陪讀媽媽的被動與能動
案例1:白鳳,35歲,在陜西省Y縣縣城租房陪讀照料兩個孩子,兒子讀初三,女兒讀小學三年級。她曾經和丈夫一起在北京務工,生兩個孩子時都曾在村里留守一段時間,一般把孩子帶到一歲大后就再次外出務工。2011年,他們發現兒子在鄉里的中心小學學習成績不好,也看到周圍很多人家把孩子送到縣城讀書。于是,他們也托關系讓孩子轉學進了縣城的小學,由奶奶陪讀。2014年,兒子升入縣城的一所中學,女兒也于同年進入小學讀書。為了更好地管理子女的學習,白鳳和丈夫商量,決定由她回來代替奶奶陪讀,丈夫繼續在北京務工。白鳳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3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00元,開始了陪讀生活。兒子每天早上7點出門,女兒8點出門;兩個孩子都要在家吃午飯;下午,女兒4點回來,兒子五點半回來。白鳳有打工經歷,非常希望能在縣城找到一份工作,哪怕賺得少一點。但是,她的空閑時間嚴重碎片化,連超市都不愿意聘用她。她說:“我感覺我干的活兒都是廢活兒,天天干也看不見活,錢又沒賺著。”孩子成績一出現波動,她就開始擔心:“我已經啥活都不干,全力撲在孩子身上,如果照顧不好、孩子學習不好,對不起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過年回來我也沒臉面對他。”
全職陪讀媽媽把全部精力用于陪伴和照料孩子,既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也沒有機會從事非農生產勞動,她們沒有個人收入,丈夫的收入是其全部生活來源。既然陪讀媽媽勞動的全部內容是照料,那么照料的結果或效益便成為衡量其勞動價值的標準。白鳳感嘆的“我已經啥活都不干,全力撲在孩子身上,如果照顧不好、孩子學習不好,對不起丈夫在外打工的辛苦”,也“沒臉面對他”,可以解釋為陪讀媽媽把自己的價值系于孩子的學業成績上。有的陪讀媽媽不堪壓力也會對孩子直接表達“我受了天大的委屈給你做飯,你不好好讀書就把我虧了”這樣的話。就陪讀媽媽而言,如果需要照料的子女超過2個,照料的勞動需求與時間分布很難給陪讀媽媽留出務工的機會,“一天做三頓飯,中間2個小時空,哪個老板招工人會要我們這樣的工人”?有的陪讀媽媽在農忙時會回鄉務農,將孩子寄養在親戚家,或由老人陪讀,甚至讓孩子自己買飯吃。但是,她們認為這只是臨時性的、輔助性的勞動,家里的林果收入是丈夫創造的,她們將自己的回家勞動比作“省了一個工人的工資”。同時,男性將“帶好娃娃”“顧好孩子”作為妻子的第一責任,認為她們放下孩子出去掙的錢,“還不夠給孩子買吃的”,所以“不如在家做飯帶孩子”。“女的苦一天看不見錢,男的苦一天,總有收入。給你一毛錢都是人家掙的錢”——一個陪讀媽媽這樣評價自己的陪讀勞動;同時,一個在外務工的爸爸這樣評價自己的勞動:“家里的貢獻當然是我貢獻大了,我一個人賺錢。”即使婦女有工作,她們的收入依然被男性認為是“輔助性”的,是“入不敷出的”。筆者在Y縣訪談的8位陪讀媽媽中,僅有1人在超市打工,且只能打半日工,日薪30元;有2人在周末或農忙時返回村里幫助丈夫勞動;其余5人均為全職陪讀。因此,全職陪讀、照料孩子雖然表面上看是媽媽們的主動選擇,但其本質是母親對家庭照料需求的被動回應,是家庭內部照料勞動的性別分工。
案例2:盧云,42歲,在Y縣縣城陪讀兩個女兒。她的兒子已經20歲,在南京做學徒工;丈夫43歲,在福建一家模具廠務工,每月工資4000元左右。18歲時,盧云外出去西安務工,經老鄉介紹認識現在的丈夫,婚后兩人一起在外務工。22歲時,她懷孕返鄉,生下了兒子,兒子滿周歲后又繼續外出務工。兒子7歲時,盧云生下了女兒,因婆婆無力照料兩個孩子,她開始留守家鄉,一邊種地一邊照顧孩子。3年后她又生下了小女兒。2010年,她把家里的耕地流轉出去,計劃到縣城務工。盧云把兩個女兒都轉到縣城學校,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由車庫改造的房子,每年租金2000元。幸運的是,盧云在一家節能燈廠找到了工作,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每天早上,她送大女兒上學,然后把小女兒送到姨媽家照料。中午大女兒在學校吃飯,盧云通常帶著饅頭、烙餅和咸菜作為午餐。下午4點,她收工接大女兒放學,再去接小女兒,然后回家做飯。因為娘家所在村莊離縣城很近,她從娘家“借”了一小片地種菜,以節約生活支出。兩年后,小女兒也開始上學。因學生數量暴漲,學校擔心孩子安全問題,要求學生在學校吃完午餐后必須回家休息,下午上課時間再回學校。如此一來,盧云因為中午要回家照料兩個女兒,工作時間被打斷,因此很快就被工廠辭退了。她只好繼續尋找新的就業機會。截至2016年夏天接受訪談時,盧云仍未找到合適的工作。盧云和三個孩子每月花費在1000元以上,但是她的丈夫每年只在過年回鄉時主動給她三四千元,“他說不能多給我,怕我亂花錢”,平時都是等她要錢才給。盧云說:“他(丈夫)還嫌我在家不賺錢,家里開支全靠他一個,沒有他這個家就塌了。”
在勞動力外出流動較多的地區,盧云這樣的案例并不鮮見。農村婦女隨著照料責任變化而不斷變化的人生軌跡,與她們的生命歷程緊密聯系在一起[14](PP 178-190)。“在鄉照料”模式中,因為老人或子女的照料需求,婦女在家鄉村落與務工地之間不斷地往返流動;轉入“離鄉照料”模式之后,陪讀媽媽則不斷在有酬的就業勞動與無酬的照料勞動之間變換軌跡。為子女獲得更好的教育而流動,是女性作為母親的能動性體現,但照料責任是父權制社會結構賦予的女性責任和女性勞動,農村婦女很難逃離這一結構性力量。關于陪讀照料勞動和務工/務農賺錢的勞動價值之間的比較,陪讀媽媽大多認為“人家(丈夫)比我貢獻大”,“他比我辛苦,我一天照顧娃娃,吃了還有個休息時間,他白天黑夜都要忙,整天忙,忙完還要自己做飯”,“我和孩子有什么需要的東西,都得跟人家(丈夫)伸手要錢,人家賺錢,我倆是純粹的消費者”。陪讀使婦女陷入完全的、顯性的失業狀態而失去對家庭經濟的決策權。
(二)就業陪讀媽媽的掙扎與驕傲
案例3:李云彩,40歲,在G縣縣城陪讀兩個孩子。她婚前曾在外務工5年,婚后留守在家8年后隨丈夫外出務工。但是,務工兩年以后,女兒在村里學校的學習成績令她非常擔心。她雖然沒有期望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學,但務工經歷讓她充分領會了教育的重要性。她認為,縣城的學校比鄉村學校管理更嚴格、要求更高,一定可以改善孩子的學習狀況。于是,李云彩和丈夫商量后,決定自己回鄉照顧兩個孩子。她在縣城租了一間房子,把女兒和兒子分別送到縣城的小學和幼兒園,并開始尋找打工機會。但是,照顧孩子讓她的工作時間受到很大限制,從2009年到2013年一直沒有工作。2014年,李云彩因偶然機會參加駕校學習并拿到了駕照。她跟別的司機合作承包了一輛出租車。如果她跑白班,接孩子、做飯,都不耽誤;如果跑夜班,更不會耽誤白天照顧孩子。2015年底,在面臨翻建家鄉老房子還是在縣城買房的選擇時,考慮到孩子讀書和他們夫妻的長遠職業打算,他們在縣城買了一套房子。因此,李云彩成為G縣少數“住在自己家里”的陪讀媽媽。在此期間,李云彩和丈夫一直種著自家和娘家的土地共15畝,除了供應自家糧食和蔬菜外,每年農業純收入萬元以上。家里大部分農活靠公婆雇機器或雇人完成,李云彩的丈夫在農忙時返鄉干活。過幾年公公婆婆年齡就更大了,李云彩希望丈夫可以回縣城跟她一起跑出租車,以方便照顧孩子和老人。
由于陪讀流動,農村婦女不僅改變了居住地點,她們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中國傳統社會性別觀念里,女性首要的社會位置是嵌入于家庭之中的,因此對于女性來說,作為生產性勞動的務工和作為再生產勞動的生育和家庭照料需求一旦發生沖突時,她們將不得不放棄前者。但是,生計壓力又迫使她們和其他家庭成員一起,以多種方式謀求生計改善。李云彩一家人的生計方式多樣,農業生產、本地務工和外地務工三種方式的結合,為家庭生計的穩定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由于孩子進城讀書及自己長期在外務工,他們已經逐漸改變了之前打工、賺錢、翻蓋新房的想法,而將家庭發展的中心轉移至城鎮,成為縣域城鎮化的主要人口群體。
案例4:張英,44歲,河南省G縣陪讀媽媽。她曾在廣東、鄭州等地務工10年,育有一兒一女。她的兩個孩子曾經在鄭州上學,后因戶籍問題回老家上學,由爺爺奶奶照顧。一年以后,孩子學習成績下降很多,她認為一則爺爺奶奶對孩子的監管不夠嚴格,二則本村學校的教學質量也不夠好,隨即把兩個孩子轉入縣城學校,同時自己返鄉陪讀。陪讀期間,她嘗試在縣城找過多種工作。她試過半日工作制的超市工作,但這項工作容易影響接孩子和做飯;在毛織廠干過計件工,雖然工作時間靈活,但是工作時間長且收入低;最后她做了保險銷售員,工作時間自由、收入也相對較高。2016年,女兒考入大學,張英的照料任務大大減輕,她在孩子學校附近開了一個美容院,雇了一位陪讀媽媽。盡管丈夫認為張英的首要任務是“帶好孩子,賺不賺錢不重要,賺那一點錢耽誤孩子學習不值得”,兩個人因此不斷吵架,“他看不上我掙的那一點錢”。但她覺得,一方面賺錢讓自己說話“硬氣”了一點,另一方面,假如她像有些陪讀媽媽那樣,“除了洗衣做飯就是打牌玩手機,會給孩子樹立一個壞榜樣、懶惰不上進的榜樣,不可能陪好孩子的學習”;而她努力工作,會讓孩子覺得媽媽很辛苦,很努力,他們自己也會懂事,會努力學習。因此,盡管丈夫強烈反對,她一直沒有放棄工作的機會。
張英的故事是陪讀媽媽獨立謀求務工或就業行動的成功案例。務工經歷與個人能力、個性都增強了她的個體能動性,再加上G縣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創造的有利環境,使其可以突破社會文化的結構性力量,為子女塑造一個獨立、自強的母親榜樣。然而,她的言語中卻充滿著對全職陪讀媽媽的不屑,用“壞榜樣、懶惰不上進”形容她們。她開店的區域也是一個陪讀媽媽聚居的地方。有的人家庭經濟條件好,租住在樓房里;家庭經濟條件差一些的,租住車庫改建房或與人合租。在她眼里,盡管都是因為子女讀書流動到縣城,她是在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己,而其他沒有工作的陪讀媽媽則是不值得學習的對象。陪讀是因為照料責任而產生的婦女流動,它成為農村婦女群體內部分化或分層的一個新機制,有工作的陪讀媽媽和沒有工作的陪讀媽媽形成了兩個階層。
(三)在家“就業”的陪讀媽媽:無酬的陪讀與商品化的照料
案例5:張玉,38歲,在G縣縣城陪讀兩個孩子。她曾和丈夫一起在河南省漯河市、鄭州市等地務工多年,中間因孕育兩個孩子,間斷性留守4年。兒子曾隨他們在漯河市上學,但因他們工作忙碌而無暇照顧,又回鄉上學。然而,成為“留守兒童”(張玉自己用語)兩年期間,兒子的學習成績不斷下降。張玉夫婦倆認為,兒子學習成績下降與鄉村學校教學質量和管理質量有很大關系。因此,2014年,張玉停止務工,返回家鄉,把兩個孩子帶到縣城讀書,成為G縣陪讀媽媽的一員。然而,十幾年的務工經歷讓張玉并不甘心只做一個洗衣煮飯的陪讀媽媽,她想方設法找工作,但一直沒有找到。兩個孩子的照料工作讓她的空間時間零散成上下午各兩個小時左右,沒有任何一個雇主愿意雇用她。同村一家人得知張玉陪讀,委托她照顧他們在縣城讀書、獨自住在校外的兒子,每月付給她伙食費600元、洗衣費300元。這個孩子和張玉租住在同一棟樓,張玉欣然接受了這份“工作”。通過這個高中生,她了解到有些高中生為了夜晚學習時間更長,自己租住在校外,無人照料。張玉表示,在女兒高中畢業之前,她恐怕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因此她計劃長期做這樣的“編外保姆”。
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經濟越來越發達,其日常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會不斷提高,原來滿足家庭需要的自給物品和勞動就會被市場購買所替代。由于G縣勞動力務工歷史較長,經濟較為發達,商品意識已經深深地嵌入每一個人的價值體系中。在G縣,保姆等家政業態并未興起,但是農村商業化的幼托機構和養老照料機構正在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家庭照料需求正通過市場來實現。由于G縣的人口基數大,農村兒童大規模進入城市就讀,陪讀照料成為家庭照料的新需求,也出現了商品化或市場化的趨勢。專門針對農村進城讀書學生的純商業化的照料機構在逐漸出現,但依然停留在非正規水平,被當地人描述為“一套單元房、幾張上下床、兩個做飯娘”,沒有一般照料機構的營業執照、健康證等。筆者在G縣訪談的12位陪讀媽媽中,有2個媽媽同時承擔了其他孩子的照料工作,并收取一定的費用。在學校無法為流動進城的學生提供合適的食宿條件、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無法陪讀、私人照料機構可信度和照料質量低的情況下,農村家庭通過私領域的社會關系,找到像張玉這樣的陪讀媽媽提供照料服務,建立起公領域非正式的勞資關系。盡管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制約,但雙方憑借熟人信任,實現了非正規的商品化照料服務以滿足流動學生的照料需求。
家庭不僅是生產單位,也是人口與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場所,因而承擔著再生產性勞動與生產性勞動的雙重任務。如果從社會再生產[22](PP 1341-1359)的框架來看,婦女進城陪讀本質上是家庭照料勞動性別分工與地域轉移的表現。第一,全職陪讀媽媽不再從事生產性勞動,因此被視為家庭純粹的消費者,其所從事的再生產性勞動由于不能為家庭創造“可見的”現金收入,其價值評判就完全取決于子女的學習表現。第二,陪讀照料責任使婦女被勞動力市場排斥或邊緣化,同時由于照料的“離鄉”特點,她們又游離于家庭農業生產勞動之外,失去了參與勞動收益的機會。第三,無論是居家就業的陪讀媽媽還是在外就業的陪讀媽媽,都承受著來自父權制和就業市場的多重壓迫,其生產性勞動的價值被認為是輔助的、次要的,陪讀照料的再生產性勞動是其首要勞動任務。這種家庭內部的性別勞動分工,是男性承擔生產性勞動、女性承擔再生產性勞動的分工,也是男性承擔有酬勞動、女性承擔無酬勞動的分工,更是男性承擔可見勞動、女性承擔不可見勞動的分工。這樣的性別勞動分工,是對傳統性別觀念中關于再生產性勞動是女性勞動的進一步固化,也是對父權制下農村婦女依附性地位的強化。
四、閑散婦女:陪讀媽媽的社會排斥與群像污名化
陪讀媽媽在城鎮的居住區域與活動區域與當地人口有著明晰的“邊界”[23](PP 201-204)——盡管來自同一縣域,但她們的生活世界與城鎮人口存在很大的不同。在Y縣,由于農村進城讀書的學生數量的比例較高,在縣城小學中自然分化出不同的層次。C小學被認為是縣城戶籍兒童入學的主要學校,該校家長通常在縣城有穩定的工作,包括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等。其余小學被認為是農村學生較多的學校,尤其是D小學和N小學,農村學生幾乎占學生總數的90%。而在這些學校的周邊區域,集中居住著大量的陪讀家庭。陪讀媽媽通常母子2-4人租住面積30平方米左右的一間房子,有的是平房,有的是樓房。當筆者在Y縣開展調查時,當地人可以很明確地指出哪些區域是陪讀媽媽居住較為集中的區域。這些區域通常是在學校周邊,環境擁擠,一個平房院子可能住四五個陪讀家庭,一套單元房則可能住兩三個陪讀家庭。在這些區域的住宅墻上,貼滿了各式各樣出租房屋的小廣告。
陪讀媽媽的娛樂休閑時間十分有限,同時因為遠離熟悉的家鄉社區和人群,她們很難在城市發展出自己的朋友圈或休閑伙伴,其社會交往圈狹窄,與當地婦女的日常生活存在明顯的界限和疏離。在G縣,由于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歷史較長,不僅縣城人口規模較大,流動人口所占比例也比一般縣城高。陪讀媽媽的社會交往并沒有融入縣城本地人的圈子,她們聊天、打麻將的對象依然是陪讀媽媽或者陪讀老人。和流動到城市務工的農村婦女相比,陪讀媽媽的照料勞動價值幾乎被完全忽視,反而是其無業、無收入狀態以及休閑時間與城市節奏的不協調被無限放大,被當地人稱為“閑人”。
城市社區對陪讀媽媽群體的休閑生活、社會交往也形成了污名化的評判——進城陪讀讓農村婦女變成“不負責任的母親”和“不安分的妻子”,在子女照料方面失責,導致農村離婚率攀升。照料孩子被認為是陪讀媽媽的首要責任和全部任務,其他影響其照料的活動都可能被放大為該群體的污點。然而,對于陪讀媽媽來說,由于脫離了鄉村的熟人和親友圈,她們的社會生活圈狹小,跳廣場舞、打麻將、看電視、聊天包括微信聊天便成為其主要的休閑方式。但是,除了在家看電視,其他活動都被認為是“不管孩子”的表現。學校老師在談到農村孩子進城、媽媽陪讀有什么問題時,就舉例說陪讀媽媽打麻將、跳廣場舞和聊微信,影響其監督孩子做作業,是“不負責任的陪讀媽媽”。但是,細究起來,陪讀媽媽由于時間零散而導致的就業困難,因文化程度較低難以對孩子進行學業指導,其陪讀大多僅為對孩子的生活的照料,這些并沒有被考慮到。
2015年平安夜,一位陪讀媽媽因赴網聊情人的約會,導致無人照料的孩子半夜從窗戶摔下致死。這一極端事件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在當地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當地農村離婚率持續上升這一社會問題也被歸因于婦女進城陪讀后受“花花世界”誘惑而嫌棄農村家庭和丈夫,社會輿論和媒體開始將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缺陷導致的農村離婚問題轉嫁到陪讀媽媽群體之上。
Y縣電視臺制作了微電影《進城以后》,講述了一個陪讀媽媽“誤入歧途” 與商人發生婚外情、只顧花錢享樂而不顧孩子,后因孩子生病、學習退步,母親又“幡然醒悟、回歸家庭”(婦聯干部語)的故事。除此以外,Y縣還有多首流傳甚廣的打油詩,描述陪讀媽媽的出軌現象:
為了娃娃受教育/娘倆搬遷進城去/丈夫辛苦把工打/妻子不久便心花/可憐孩子染重病 /多虧園丁把愛灑……
農村家戶有了錢/都把娃娃城里轉……各個巷巷都住滿/都是為娃把書念/進了城,開了眼/花花世界才看見/描眉畫眼巧打扮/沒事就到廣場轉……拿手機,聊微信/你有情來我有意……麻將場里玩幾圈/弄到半夜兩三點/娃放學,不見媽/肚子餓的吱哇哇/家里人,和老漢/辛辛苦苦撫果園/提起婆姨心不安/金戒指,銀項鏈/看見老漢不順眼……
大眾媒體選擇性的報道將個別陪讀媽媽的局部特征放大為其群體形象,在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的同時,也在不斷強化著陪讀媽媽的負面形象,使之在更大程度上被暴露于社會公眾面前,更加凸顯了其污名記號,進而勾勒出其被社會排斥的群像。某位在縣城居住的被訪談人在談到陪讀媽媽的情況時說:“現在進城的農村婦女把城里的風氣污染得不成樣子了,很多婦女扔點錢讓孩子去吃飯,自己就去逍遙找樂,和別的男人約會,打麻將……”但是,當問及具體案例情況及判斷的具體依據時,她也說不出所以然,只是舉了上述陪讀媽媽出軌導致孩子無人照料致死的故事。由于陪讀媽媽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殊群體,關于這個群體的負面形象信息傳播速度和廣度、受關注度均遠大于其正面形象信息的傳播,而普通大眾則易于接受這樣的信息,從而塑造和強化了關于陪讀媽媽的負面形象。
基于當地離婚率不斷升高、陪讀媽媽群體不斷擴大以及上述極端案例引發的社會影響,Y縣政府部門也開始實施一些針對陪讀媽媽的干預措施,以預防相關問題嚴重化。縣政府辦公室曾經制定文件,指出“隨著農村學生向縣城聚集,許多農村婦女涌入縣城”,要求相關部門加強“進城閑散婦女管理和教育工作”;縣婦聯出臺了《六個方面加強農村進城婦女教育管理工作》的文件,提出要通過舉辦“道德講堂”等活動,對進城的農村婦女“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以“提升農村婦女的精神品味”。一方面,陪讀媽媽在照料子女之外的閑暇時間與城市職業婦女的工作時間重疊,因此從時間上講,其休閑活動與城市生活節奏不協調,顯得其“閑散”;另一方面,她們打麻將、跳廣場舞這樣的休閑活動,被認為與城市的“精神品味”不協調,因而其“精神品味”需要提升。換句話說,這些文件賦予陪讀媽媽的名稱“進城閑散婦女”,充斥著對于這個群體的排斥和歧視。“進城”是對其農村來源和農民身份的歧視;“閑散”是對婦女的職業歧視,或者是對其照料勞動的無視;“婦女”則是性別歧視。在這些文件的指導下,縣教育管理部門和婦聯、政府聯合開展了多種對陪讀媽媽進行“管理和教育”的工作。農村學生較多的學校在組織家校互動會時,專門針對陪讀家長開設講座。學校老師在討論有學習問題的農村學生時,常常將原因歸結在陪讀媽媽身上。婦聯還開設了“社會閑散婦女講座”,三八婦女節文藝匯演表演了關于陪讀媽媽問題的小品,希望“利用多種形式對她們進行教育”,影響她們的行為。縣委黨校在幾所中小學校開展了關于“母德母愛”的講座,講座部分文本內容的媒介話語分析更清楚地呈現了其教育、“呼喚母教回歸”的目的(見表1),陪讀照料被認為是母親的天職,社會問題被認為是由于婦女違背母親天職的結果。

表1 關于Y縣“母德母愛”講座的媒介話語分析
據我們調查,Y縣農村離婚率近年的確出現快速上升的趨勢,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農村戶籍人口離婚對數分別是結婚對數的19%、26%和23%。筆者在綜合了縣婦聯、律師事務所、教師及村干部、農民訪談中所列舉的離婚案例后,總結出農村離婚率上升的核心影響因素是人口流動。其中包括:農村夫妻二人在外務工導致離婚;一個在外務工、另一個留守在家導致離婚;男性外出務工帶回外地媳婦兒,貧困、婆媳不和等因素使跨地區婚姻難以維系,最終離婚;農村婦女進城陪讀導致離婚。筆者訪談的Y縣3個村近5年內僅有4個離婚案例中的妻子是陪讀媽媽。對于妻子進城陪讀,留守在村的丈夫們認為,“陪讀造成的兩地分居對婚姻沒什么影響,畢竟為了供孩子讀書的共同目標是不變的”,“兩個人分開或在一起都是為了家”。
陪讀媽媽對于媒體的污名化消費和社會組織的“教育管理”持妥協態度。對于媒體塑造的負面形象、社會傳播的污名故事,被訪的陪讀媽媽或者表示自己“沒看過、不知道”,或者表示“聽說過,但是應該只是極少數”,同時極力展示自己經常在家、“微信聊天的人也都是認識的人”等良好形象。有些陪讀媽媽表示,聽完婦聯的講座之后會反思自己照顧孩子的行為是否符合要求。陪讀媽媽被迫以社會要求的“母德母愛”“婦德綱常”等要求來評判和約束自己的行為,社會對陪讀媽媽的形象書寫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她們對自身的角色期待。由于在城市社會處于話語劣勢,盡管其“污名”形象愈來愈彰顯,但陪讀媽媽們并沒有反抗,反而是以沉默、妥協應對。
五、結論與思考
陪讀現象體現的是中國城鄉關系中,作為照料勞動承擔者的婦女、作為勞動力再生產方式的教育和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陪讀媽媽群體的出現,是繼勞動力外出務工與留守人口共同支撐的“拆分型”[24](PP 13-36)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之后,中國農村家庭再生產系統為了適應宏觀社會變遷而出現的又一次調整,而且是跨地區的調整。在照料體制中,國家的行動和進退對于照料責任擔當方影響很大[5](PP 43-54)。在國家教育政策調整、農村家庭教育期望提升和傳統父權制、家庭主義價值觀共同作用下,大量農村學生進入城鎮學校就讀,產生了新的照料需求并由此出現陪讀媽媽群體。與以往備受關注的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不同,農村兒童的教育流動催生出農村家庭照料的新特點:離鄉照料。在很多區域,“留守”已經不再是農村婦女的重要特征,她們成為流動的留守婦女。離鄉照料也使農村家庭的離散化程度進一步加劇,由于婦女的日常生活脫離了鄉村的地域,對農村老年人照料供給可能帶來影響。因此,陪讀媽媽群體的出現,也是農村家庭承擔社會公共政策和國家以教育推動城鎮化發展[25](PP 163-179)代價的表征之一。
陪讀是傳統性別規范對婦女再生產角色的強化,也是對父權制的強化。20世紀60-80年代,女性主義研究者強調了婦女的無酬照料勞動和家務勞動在社會再生產中的關鍵作用,并指出其中蘊含的維護父權、性別與階級不平等的意義[26](P 2)。照料勞動和性別關系、父權制問題也經常被放在一起討論。陪讀媽媽既脫離了鄉村的生產性勞動,又被城鎮的勞動力市場排斥或邊緣化,成為純粹的依附者,孩子的學業表現成為她們再生產勞動價值的評判標準或依據。由于父權制把價值賦予了孩子,因此陪讀媽媽獲得尊嚴或蒙受恥辱的根源,都是和孩子密切聯系在一起,成為一種約束女性行動的社會規范。
陪讀媽媽因不創造有形及可見的勞動價值,其被城市社區排斥的程度甚于一般城市社區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成為被 “區隔”的群體和政府規訓的對象。一方面,城市及媒體利用強勢的話語權力創造偏頗的社會輿論,將婦女“制造”為農村家庭離散化背景下婚姻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如果陪讀流動被看作一種城市嵌入的嘗試,那么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居民利用他們的優勢,以媒體、政府、社會組織為代表,給作為外來者的陪讀媽媽貼上了種種社會標簽,如嫌棄農村家庭和農村丈夫、不負責任、背棄母德等,并對她們進行管理和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流動的陪讀媽媽則妥協于父權制思想下的這些約束,將污名化的群像作為自我管制及自我約束的參照。
當前,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中國婦女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明確提出加強農村婦女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推動廣大婦女以主人翁姿態參與鄉村建設與鄉村發展行動。然而,在中國教育發展、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農村婦女并未成為“發展”的受益者。從在鄉照料到離鄉照料,性別化的照料責任分工依然是農村婦女發展的障礙。推動全社會對婦女再生產勞動的正確認識,培育婦女的主體意識進而促進性別平等,應是新時代農村婦女發展與鄉村振興有機融合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