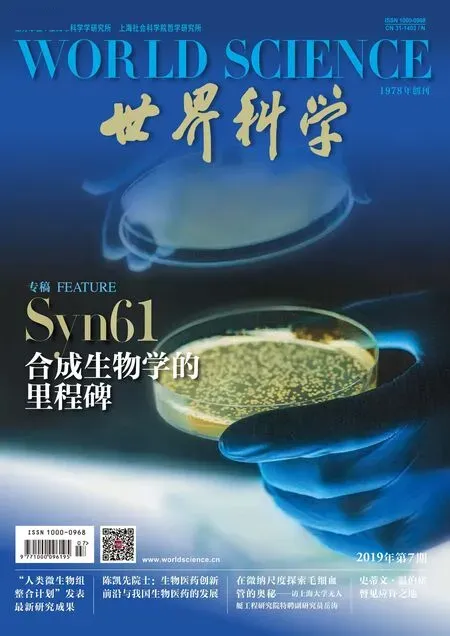斯諾風暴
編譯 韓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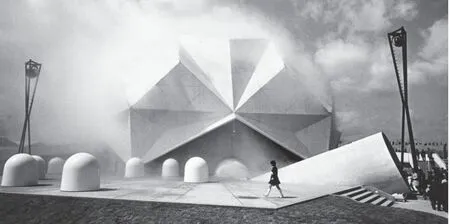
1959年5月,查爾斯·斯諾(Charles Percy Snow)現身劍橋大學理事會大樓,為年度瑞德講壇做“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講。這位從化學轉行寫小說的英國人臉頰肥圓,雙下巴,身姿龐大蹣跚,這讓大家打趣說,斯諾除了智力上圓融外,身材也很圓滿。斯諾在這場演講中概要地提出了自己對所有西方民主國家未來的一種擔憂。他觀察到英國的文科和理科正微妙地彼此隔絕并厭惡,盡管厭惡的方式不同。這種文科學者和科學家之間的溝通障礙不僅僅是一種智力上的損失,更會影響到現代國家應對全球性問題的能力。
演講隨后變得尖銳起來。他嘲諷牛津和劍橋的人文學者是躲在象牙塔內的盧德分子,應該為英國國力下行負責;與此相反,科學家則是樂觀派,他們有能力推動國內外繁榮進步,他們從骨子里就代表了未來。斯諾斷言,蘇聯比英國更具優勢,因為英國的行政系統被一種專注于向后看的人文視角所統治;而在蘇聯那邊,向前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則更有影響力。
斯諾的“診斷書”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反對意見、報復文章甚至人身攻擊紛至沓來。“兩種文化”提法本身就暗示鴻溝的存在,辱罵性口水仗借鑒了這種暗示,深入瞄準到英國在社會階層、教育、支配力方面既存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分水嶺。而從愛國主義立場來看,這場爭辯則表示人們開始討論二戰后英國應該把科學與技術的專業人才放在什么樣的位置上,其中斯諾很大程度上為技術專家們站臺。
文化沖擊飛躍大西洋
斯諾的演講瞬間點燃了英國,一開始美國的反應卻顯得很冷淡。《紐約時報》直到1960年1月才刊登一篇長評介紹斯諾的觀點,該評論已被出版成中等篇幅的書。加拿大地球物理學者威爾遜(J. Tuzo Wilson)懷著對斯諾的敬意,一邊說自己熟悉的當代文學圈,一邊不痛不癢地反駁了斯諾的部分主張,最后,他斷定斯諾的核心論證“還沒有人能駁倒”。次月,美國也被點燃。哥倫比亞大學把《兩種文化》列入大一新生必讀書目清單,時任參議員的約翰·肯尼迪贊美了斯諾的洞見,美國的圖書俱樂部則迅速把《兩種文化》推薦給他們的會員。最初針對英國特殊國情而開出的“診斷書”現在已經開始滲入美國公共話語之中。
美國在冷戰時期的科學焦慮
“兩種文化”在美國獲得異乎尋常的重視,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1960年左右國家政策制定方、工業領袖和研究員們對科技持續的、近乎癡迷的關注。那時,蘇聯發射了人造衛星,在蘇聯的刺激下,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案,決心改革理工科教育。巨額的資金投入加上由太空和軍備競賽帶來的人力資源缺口促使大量年輕人進入物理和工程這樣的科技領域就學。結果,當人們一想起20世紀60年代早期那場關于“兩種文化”的辯論潮,蘇聯人造衛星發出的“嗶嗶”聲就成了絕佳又持久的背景樂。
劍橋演講的第二年,美國的理工科期刊開始出現贊同、引用或駁斥斯諾的評論。歷史學家阿薩·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發表長文贊同斯諾的部分主張,但同時指出他的觀點是一種二元的簡化主義。類似的評論也見于《今日物理》和《原子科學家公報》。
斯諾的劍橋演講不僅使他成為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也成功造就了“兩種文化”現象。引用“兩種文化”成為一種簡短有效的方式用來指涉大家的一些更為復雜的概念與關注,盡管有時也沒法做到特別精確。縱觀整個20世紀60年代,斯諾的“兩種文化”就成了一種萬能溶劑,各種擔憂、焦慮,以及隨之而來的補救方案都可以被收納進來。人們可以很輕松地設想兩種文化,“兩種文化”的部分魔力正來源于這種提法內在的二元性,這也是這句短語至今被人稱道的原因。
將技術專家人文化
這些探討所處的大背景是二戰后美國教育界的改革運動。1945年,曾經是化學家和哈佛大學校長的詹姆斯·康納特(James Conant)授權了一項著名的“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研究,其中建議所有學生都接受綜合的文科教育,以此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并激發他們更靈活開放的心態。研究強調需要平衡文理科的課程配置,借此規避斯諾所謂的兩種文化現象,即文理科之間互不融通、各說一套的現象。
對工科來說,接觸人文學科更加迫在眉睫。工程師們還在費勁地贏取和科學家平起平坐的專業地位,他們總是被夸張的描述為成一群帶點挑釁且“粗魯、物質、麻木”的人,其夠得到的最好的文學與藝術只是“廉價電影和漫畫書”。這種對于工程師的典型印象似乎預示了想把未來的技術專家變得“人性化”可能更加不容易。
有一個解決方案是將他們沉浸在美術中。麻省理工成立了由卓越的藝術史教授和東海岸一些重點博物館的董事們共同領導的“視覺藝術研究委員會”,希望藝術與人文不只是提供一層“文化鍍金”,而且能通過提升工科學生的創造力帶來實際的好處。這種呼吁在20世紀60年代末顯得越來越緊迫,當時的學生激進分子、反越戰人士和大型毀滅性技術系統的批判者越來越使得工程師被貼上“服務大型企業的無道德技術專家”的標簽。
工具主義、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的張力充斥在20世紀60年代教育改革者面前堆積如山的報告中。這些報告可能并沒有明顯地引用“兩種文化問題”這種字眼,其實也不需要引用,因為與斯諾的兩種文化概念一樣,教育工作者和許多工程實踐人早已把促進理工科與文科和諧共處作為值得追求的目標。
學術圈外的藝術與科技
斯諾風暴也席卷到學術圈外。20世紀60年代,從企業實驗室、冷水公寓、出版社到美術館和畫廊都爆發出一大批旨在團結藝術家與科學家、工程師的激勵措施。這些努力背后的支柱是當時繁榮的經濟,使得公司和企業實驗室在多年的盈利條件下有能力承擔,甚至鼓勵他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藝術家為伍。
1966年,工程師比利·克盧佛(Billy Klüver)和藝術家羅伯特·羅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一起在紐約創立了“藝術與技術實驗”,這是當時最知名的藝術化運動之一,為工程師和藝術家搭建平臺共同制作出高質量的藝術與技術項目。藝術和科技融合的支持者認為這種運動可以解決“兩種文化”問題或至少達成一種和解。他們認為藝術非常要緊,不能僅僅是藝術家的分內事,工程師和科學家也得做。
Steam:靈感,實用,兩者兼備?
創意性協作是50年前的藝術與技術運動的首要目標,至今仍被企業領袖和大學管理層推崇備至,致力于藝術與科技交互的會議、期刊、社團也越來越多。2010年以來,全國的教育領導人都開始贊賞把藝術和設計加入傳統的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與數學(Math)框架,標記為“從STEM 到 STEAM”,其中“A”代表藝術(Art),這些當代運動正反映了50年前那群藝術與技術倡議者的雄心。不同的是,曾經的協作驅動力來源于繁榮的經濟并帶有明顯的烏托邦憧憬,今天“從STEM 到 STEAM”熱情的理由則更加平凡一些。大部分聯結藝術與理工科的活動發軔于2008—200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不是沒有原因的。政客們總是(錯誤地)宣稱某些學科——比如學戲劇或者歷史——是不務實際的奢侈專業,會讓人找不到工作。
與此同時,教育者和政策制定人最關心的是如何教育并拿什么去教育新一代的技術人員。一些教育專家再次想到了把藝術納入理工科課表。此外,融合創造性文化的努力常常暗示技術化藝術(或者說藝術化技術)可以是一種商業創新與盈利的途徑,因此,今天的STEAM倡導者在追求他們的目標時,有時會顯得更工具主義而不是理想主義。
關注共同文化
斯諾演講中彼此爭執互不兼容的“兩種文化”版本傳播到美國后幾年,《科學》雜志發表了一篇短文挑戰他的主張。作者是一名歷史學教授,他認為在科學學科和人文學科之間存在的鴻溝并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大,他所在的小小的人文學院不是有兩種而是“恐怕有200種”文化,其中任何一種文化都可能神秘又狹隘得不可救藥。但除了對校園官僚的集體厭倦之外,大家依然分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比如:學術自由,尊重證據,相信更多知識、更深理解本身就是一件純粹的好事。
理工科和文科的一個共同的文化傳統在于尊重事實證據,尊重按照一定方法來產生事實證據。而今天,不遵守這種傳統的情況比比皆是。如果斯諾還活著的話,他也會鼓勵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工程師和藝術家一起關注我們共同屬于的那一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