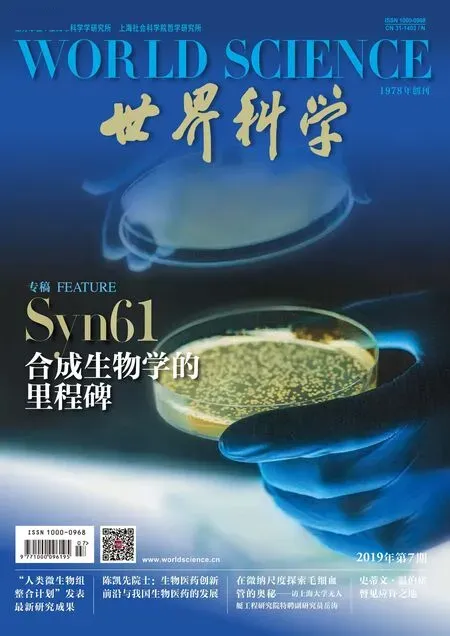化微生物為活工廠
——弗朗西斯·阿諾德的傳奇
編譯 傳植
這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利用自然規律替代了從零開始的新生化試劑合成過程,成果頗豐。

“工程師的真言,”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工程教授弗朗西斯·阿諾德(Frances Arnold)認為,正是“保持簡單而直白(Keep it simple,stupid)。”阿諾德博士2018年成為歷史上第5個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女性,她的故事卻不那么簡單直白,反而有時具有洛可可風格。
我們來看看她辦公室墻上掛著的那些光彩瞬間。有一張2013年的照片:奧巴馬總統笑容洋溢,慶祝阿諾德博士獲得美國國家科技創新獎章。
當時一定很開心吧?“當然,”阿諾德博士說,“除了送獲獎者的小巴士在白宮門口停下時突然著了火。車里都是煙,車里的人掙扎著、叫喊著逃到車外,扶老攜幼——迎接我們的卻是一群特勤局的特工,用槍對著我們這些獲獎者的腦袋。”
“他們一定覺得我們是恐怖分子,”阿諾德博士說,“我們當時都覺得他們要開槍了。”
好,讓我們再來看看這一張:阿諾德博士和英國女王的合影,光彩照人。
這又是個有趣的故事!當時阿諾德博士和她16歲的兒子喬·蘭格(Joe Lange)從加利福尼亞花了12小時飛到英國,邊境工作人員問她來英國的緣由。阿諾德這位炙手可熱的名人,宣稱她當晚要去一個招待會和女王會面。
“真的嗎?”工作人員相當懷疑,看了看她有些不修邊幅的樣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化學工程師。”
“那勞駕您告訴我您之后的行程如何安排呢?”
“我之后要去意大利總統府參加一個頒獎儀式。”阿諾德博士回答。
“女士,”工作人員說道,“如果您要去白金漢宮,您得有請柬。我能檢查一下嗎?”
“哦,我沒隨身帶著,”阿諾德博士說,“我把它放手提箱里了。”
“到此為止,”工作人員合上他的分類簿,抓起阿諾德和喬的護照,“請跟我來一趟。”
母子二人于是在機場滯留了兩個半小時,直到工作人員確認了她說的是實話,最終二人差點沒趕上招待會。
“他們準覺得我是個瘋子,”阿諾德博士說,“顯然有很多60歲的女人說她們要見女王。”
這兩個故事都佐證了阿諾德博士的另一個行事準則:“不要認為你能掌控生活,最好的選擇是去適應,去計劃,去靈活面對,去感知環境并做出反應。”
或者干脆不做反應,“喬之后對我說:‘媽媽,你下次最好閉上嘴。’”
工程師的夢想
那時的阿諾德博士62歲,已經功成名就,她的想法是:與其讓人去進行實驗,不如讓位于一個比任何武裝警衛甚至國家元首更強的力量——進化。
讓阿諾德博士名揚天下并獲得諾貝爾獎的,是她開發的一種稱作定向進化的技術,能夠合成大量新的酶或其他生物分子,用途甚廣,像制造化學藥劑的解毒劑,或制造干擾農業害蟲交配的物質,又或是在環保的冷水中去掉衣物上的污漬,也可以讓人們不用有害的金屬催化劑來制造藥物。
照常理來說,合成新的蛋白質應該是先進行精確計算,然后將部分組裝成整體,但許多蛋白質化學家卻屢戰屢敗。阿諾德將之讓位于進化演算法,讓其進行蛋白質的組裝和優化。
這種方法確實實現了工程師們的夢想——簡明。
你先拿出一個你感興趣的某種功能的蛋白質,譬如在高溫中穩定或是能夠神奇地分離掉脂肪。然后用聚合酶鏈反應這種常規試驗技術,隨機地讓編碼這個蛋白質的基因發生變異。
接著就需要瞧瞧產生的新蛋白是否在一些能力上有小小的提升,譬如活性變得更高了,或是出現了新功能的蛛絲馬跡,又或是一些功能在以前無能為力的條件下可行了。
然后就是要讓升級版的蛋白質繼續變異,并篩選出具有更強功能的蛋白質,由此按需要進行重復操作。這里可以用大腸桿菌進行試驗,或是選擇從冰島一個溫度超過175華氏度(約79.4攝氏度)的溫泉中分離出的外來微生物。
接著還需要用抗生素處理蛋白質和其載體微生物,就像人們對病原微生物濫用抗生素,但這里的目的卻是為了讓微生物應對生存挑戰,去適應并存活下來。
通過定向進化,阿諾德博士的實驗室成功培養出自然界中未曾發現的具有某種功能的微生物。有些能夠把定義生命的元素碳和硅——沙子、玻璃和計算機芯片的材料,但迄今為止還不是生命的元素——拼接在一起。(除非你是硅基生命Horta,《星際迷航》中那個出名的和Spock進行靈魂交流的石頭狀生物。)
這一切僅需要對細菌的細胞色素c這種蛋白質進行幾次變異調整。
“我們第一次證明了生命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碳和硅用化學鍵連起來,”阿諾德博士實驗室的博士后詹妮弗·坎(Jennifer Kan)進行了這個實驗,她說,“甚至都不需要重復很多次就能達到目的。”
那碳和硼能不能結合起來呢?又或者一個彎曲度很高的碳環,可以具有像盤曲起來的彈簧那樣的能量——這些化學鍵從未或者極少在自然界中被發現,直到定向進化的出現為之指明了道路。

2018年12月,斯德哥爾摩,阿諾德博士從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受諾貝爾獎
“我們在實驗室發現自然能以我們未曾想到過的方法產生化學物質,”阿諾德博士說,“我們正不斷為生物的化學世界添磚加瓦。”
加州理工學院主持“愛因斯坦全集計劃”(Einstein Papers Project)的阿諾德博士的親密朋友戴安娜·柯默思-布赫瓦爾德(Diana Kormos-Buchwald)說:“弗朗西斯本質上來說開創了進化化學這一領域。傳統上是對化學物質進行分析,然后通過標準的化學合成方法來嘗試制造化學物質,但她發明的方法是用自然本身來拓展生物或化學上重要分子可能的衍生物。”
阿諾德博士的另一句真言是:自然從不在乎你的計算如何。阿諾德的團隊在分析了進化上的變異后,找到了調整蛋白質功能最為有效的變異位點,而這些變化出現在了各種出乎意料的地方。
“有些變異可能離蛋白質的活性位點很遠,或者在蛋白表面,”她說,“大家認為無關緊要的地方恰恰成了關鍵。我開心地拿著結果去找生物化學家:‘你看,你沒能預測到這個,但我直接找到了。不僅這次,我以后都會這樣找到它們。’這想必惹毛他們了。”
在探索生化鍵的奧秘時,阿諾德博士的動力不只是單純的好奇心。(說真的,為什么自然沒有利用這個星球上充沛的硅元素來造一個地球版本的Horta?)
作為一個擁有普林斯頓大學機械和航天工程學士學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化學工程博士學位的“正統工程師”,阿諾德博士的動力還是要創造有用的東西。
同時,因為她又是個環境保護人士,她的“有用”也意味著環保。
相對于傳統上依賴溶劑、塑料和貴金屬的工藝,定向進化能夠創造出特化的酶來進行想要的反應,更加清潔,效率也更高。
“我所有的項目都關注可持續性和生物修復,以更干凈的方法行事,”阿諾德博士說,“一些學生會說他們想做幫助他人的事情。那么我會說,人類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幫助,為什么不去幫助這個星球呢?”
她創建了一些公司,包括由珍·古道爾(Jane Goodall)熱情支持的Provivi公司,致力于開發清潔、低廉的大規模合成昆蟲交配信息素的技術手段,以此趕走農作物害蟲,而非把它們殺死。
4月,阿諾德博士和她過去的3個博士后開始籌辦新的公司Aralez Bio,將用定向進化作為技術手段為藥品公司設計定制氨基酸生產技術。
就現在來看,整個制藥業都異常“不環保”,新公司的首席科學官克里斯蒂娜·博維利(Christina Boville)評價道。
“相比產出,他們正制造著百倍的廢料,”她說,“我相信我們能做得好得多,因為我們的技術確實有效。”
年輕的企業家有資本這般樂觀——創業失敗的概率大概有90%,而阿諾德博士在2005年創辦的3家公司到現在還在經營。
不言放棄
阿諾德博士是如此獨特,她展現出他人少有的迷人自信,尤其作為一位女性——或許這是因為她是家里5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兒。
“我比男孩子還像男孩子。”她說。
她也十分聰明,小學時就開始提前上高年級的課程了,但并沒有因此趾高氣揚。
“她熱情而體貼,同時做事嚴謹,不說廢話,”加州理工學院的化學工程教授米克黑爾·夏皮羅(Mikhail Shapiro)說,他2005年認識了阿諾德教授,當時他研究生一年級,向阿諾德教授尋求過幫助,“我以她為楷模。”
阿諾德博士有軍人的氣質,也有些反傳統。她的祖父是一位三星中將。父親是個核物理學家,同時還在預備隊中。但她卻表現得相當逆反,甚至在14歲就離開家,自己住到匹茨堡,做過服務生、出租車司機,在爵士樂俱樂部和披薩店打工謀生。
“但凡你能想到的,我都做過。”她說。當父母聽說她想去普林斯頓大學之后都很驚訝,但開心地為她交了學費。盡管在政見和哲學觀念上與父親爭執頗多,阿諾德和父親還是保持著親密的關系,直到他2015年去世。
“我們總是吵架,”她說,“但他是懂我的。”
她旅居世界各地,獨自一人往返南美和印度尼西亞,摩旅穿越歐洲和土耳其。她會說5種語言,會彈吉他、鋼琴,還會管風琴。
11月, 阿 諾德博士會像林-曼努爾·米蘭達和杰夫·貝索斯一樣,在史密森尼國家肖像館參加美國肖像典禮,她很快成為美國的名人。
她的辦公室里堆滿了成箱的獎杯和被邀去世界各地演講的“毫不夸張有上千的邀請函”。
阿諾德博士幾乎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了一輩子,這里總共出過38位諾貝爾獎得主,但她是第一位女性。
“我不介意成為一個名人,”她說,“因為我的照片比我本人要好看。”其實并不是這樣。
她的朋友稱贊她出眾的廚藝。她建成于1948年的加州牧場風格的房子雅致而舒適,位于帕薩迪納附近,花園里種了橘子、橙子、藍莓、檸檬、金橘、洋薊、羽衣甘藍、黃瓜、土豆、薄荷和香料,多到可以自給自足,甚至分給當地的食物賑濟處。
這種生活確實很美好——但沒有什么是十全十美的。
第一次婚姻,她嫁給了生物化學家杰·貝利(Jay Bailey),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結束,貝利在2001年因結腸癌去世。2004年,阿諾德博士被診斷患有乳腺癌,已經轉移至淋巴結,她經歷了18個月折磨人的手術、放療和化療,同時養大了3個小男孩,還保持每周工作60小時。
“我以前的記憶力和相機一樣好,”她說,“但化療毀了它。”
2010年,阿諾德博士事實婚姻的丈夫、宇宙學家安德魯·蘭格(Andrew Lange)自殺,留下阿諾德博士吞聲忍淚,到現在也沒能完全原諒他。

2018年秋天,阿諾德博士和她的兒子詹姆斯·貝利(James Bailey,左)、喬·蘭格(右)在加州理工學院。阿諾德博士另一個兒子威廉·蘭格2016年因事故去世
但最傷心的莫過于她的次子威廉·蘭格(William Lange)2016年意外死亡,年僅20歲,她至今不愿提起這件事。
“弗朗西斯的生活絕不一帆風順,”加州理工學院的神經科學家、也是阿諾德博士親密朋友的薇薇安納·格拉迪納魯(Viviana Gradinaru)說道,“但盡管生活如此,她還是獲得了諾貝爾獎。”
若別人因此過度稱贊阿諾德博士的骨氣,她會有些不耐煩。
“沒有人的生活是順風順水的,”她說,“想想敘利亞的人民,我有朋友是大屠殺的幸存者。那我面對我的生活該怎么樣,放棄嗎?告訴自己撐不下去了嗎?不。我還有其他的孩子。我實驗室還有一群年輕人。我為什么要放棄呢?”
首先,你得知道你不能掌控你的生活。接著你要振作起來,拿起你的請柬,去見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