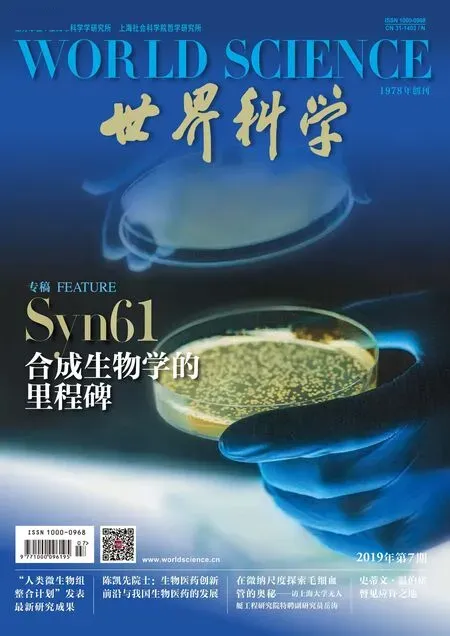在螞蟻研究中,他發現了未來的希望
編譯 陳軼翔
不管是否存在爭議,威爾遜的作品致力于論述一個主題:我們必須了解博物學和進化理論,才能充分理解這個星球上人類的未來。

E. O. 威爾遜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博物學家、進化論理論家和作家,他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社會生物學的概念。在他90歲生日前夕,他仍然為進化論和生態科學與人類發展的相關性而爭論不休
60多年來,頗具影響力的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簡稱E. O. 威爾遜)一直在尋找進化論、生態學和行為學之間的聯系,這常常在科學界內外引發爭議。
在生物學領域,從來沒人有過像E. O.威爾遜這樣的職業生涯。威爾遜是世界領先的螞蟻研究權威之一,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進化論理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多產、暢銷和備受尊敬的作家——幾十年來,他一直處于科學爭議的中心,而且這些爭議已經從科學期刊上傳播到公眾中。在環保運動的積極分子中,威爾遜是一位年長的政治家,是精神領袖,他的著作成為環保運動的依據。在即將慶祝90歲生日之際,他也絲毫沒有失去對這場戰斗的熱情。
紐約賓厄姆頓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大衛·威爾遜(David Sloan Wilson)說:“我來告訴你一些關于愛德華的事。他有點像一個聰明的手榴彈投手。他喜歡挑釁,這對于像他這樣有名望的人來說是不尋常的。”
E. O.威爾遜十幾歲時就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在家鄉亞拉巴馬州對每一種螞蟻進行鑒別和分類。29歲時,威爾遜因在螞蟻、進化和動物行為方面的研究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終身教授職位。20世紀60年代,他的學術聲譽更響了——他和著名的群落生態學家羅伯特·麥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發展出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以解釋在海洋中孤立、貧瘠的小島嶼上,生命是如何形成的。這項研究成為當時保護生物學學科的支柱。
1975年,威爾遜出版的《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一書掀起了波瀾。在這本書中,他把自己對昆蟲行為的所有了解都應用到了脊椎動物身上——包括人類。這項研究表明,人們身上的很多社會行為,包括利他主義等優秀品質,都可以歸因于自然選擇。威爾遜很快發現自己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者和基因決定論者提供智力援助。坎布里奇街頭的示威游行要求解雇威爾遜。1979年,威爾遜憑借其通俗版的社會生物學著作《論人性》(On Human Nature)獲得普利策獎之后,爭議才平息下來。
在第一次獲得普利策獎之前,威爾遜就是一位筆調流暢、文筆優雅的作家,大部分作品都是學術領域的。但在獲得普利策獎之后,威爾遜開始向大眾普及自己的觀點,將生物學和他自己的研究轉化為一種通俗易懂的形式。
時隔多年,他與行為生物學家伯特·霍爾多布勒(Bert H?lldobler)合著的《螞蟻》(The Ants)再次獲得普利策獎(1990年)。他還寫了一本回憶錄、一本小說和二十多部紀實作品,其中很多與《社會生物學》一樣備受爭議。
不管是否存在爭議,威爾遜的作品致力于論述一個主題:我們必須了解博物學和進化理論,才能充分理解在這個星球上人類的未來。例如,在1986年發表的《親生命性》(Biophilia)中,他提出,人類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生物學需要,即融入大自然,并與其他生命形式相關聯。在2016年出版的《半個地球:人類家園的生存之戰》(Half 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一書中,他提出了結束破壞世界生物多樣性的建議:政府應該把地球的一半作為自然保護區。
不久前,威爾遜的最新著作《創世紀:社會的深層起源》(Genesis: The Deep Origins of Society)問世,對他早期著作中介紹的一些進化論觀點進行了更新和反思。他強調《創世紀》是“我寫過的最重要的書之一”。
為了討論《創世紀》,并了解威爾遜對這本書可能引發的新爭議的看法,《量子雜志》拜訪了他在馬薩諸塞州列克星敦的家。以下是經過編輯和濃縮的長達三個小時的訪談內容。2019年6月就是您90歲生日了吧?
是的。我簡直不敢相信!我覺得自己大概才35或45歲。早上起床時,也和往常一樣輕松(或困難),我感覺精力依舊。其實,在我40歲的時候,曾想過,等我90歲的時候,會做同樣的事情嗎?事實證明,現在的確如此。
我每年寫一本書,時不時我還去旅行,去接觸大自然。最近,我打算去莫桑比克(非洲南部國家)的戈龍戈薩國家公園,為我的下一本書做實地考察。然而,那里發生了一場悲劇——臺風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很多人在臺風中甚至喪生。我在莫桑比克的朋友們建議我緩一緩再去。
所以現在我在列克星敦,寫我的第32本書。即使我現在不能旅行,在這里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現在寫的這本書聚焦在什么方面?
生態系統。2018年,麻省理工學院邀請我做一些關于生態系統的講座。在準備我的演講時,我發現人類對它知之甚少。我摸索著前進,逐漸意識到理解生態系統中威脅它平衡的因素將是生物科學的下一個重大課題。為了拯救環境,我們必須了解如何拯救生態系統。
您有點工作狂傾向嗎?
嗯,是的。我認為當個工作狂并不是件壞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年,也就是我13歲的時候,我的家鄉亞拉巴馬州莫比爾市缺少送報紙的男孩。18歲的孩子們都在打仗,所以我接受了一份送報的工作,每天早上遞送420份報紙。我會把我能拿的所有報紙,裝到我的自行車上,然后送出去。送完后我再回到郵局,拿另一堆,再把它們送出去。我要在早上7點以前送完報紙回到家,吃早餐,去上學。
我認為這樣的狀態很正常。我一直把長時間努力工作視為我的習慣。做一些不尋常的事情,肯定要付出很多努力。我寫了很多書,也是一樣,那是很辛苦的工作。
您認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幾十年來,威爾遜一直是研究螞蟻的世界權威之一。20世紀40年代,十幾歲的他在家鄉亞拉巴馬州對每一種螞蟻進行鑒別和分類
你這是慫恿我吹牛嗎?(微笑)。好吧,我覺得自己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想法,創造了一些全新理論。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成為現代保護生物學的基礎。然后我還做了一些事情,比如破解螞蟻的化學密碼,我與化學家和數學家一起研究螞蟻是如何交流的。我編輯過“生命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Life)”,我首次提出并命名社會生物學,這又催生了進化心理學。據說您的一項偉大貢獻是將科學思想進行整合。這樣表述是否準確呢?

E. O. 威爾遜解釋了進化的昆蟲行為與人類本性的相關性
我想說我一直是個“合成器”。我喜歡觀察大自然的某些方面,學習所有可以接觸到的東西,把它們都收集起來,看看自己能否從中找到與一些大問題相關的東西。
關于這一點,可否給我們舉個例子?
我的第四本書《昆蟲社會》(The Insect Societies)就是一個例子。在20世紀60年代,有很多昆蟲學家致力于研究社會性昆蟲:蜜蜂、黃蜂、螞蟻等。但我們并沒有對所有已知的內容進行總結,也沒有對這一切意味著什么進行分析。1971年,我出版了《昆蟲社會》,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實上,這本書獲得了國家圖書獎的提名,我自己其實也很驚訝。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從事文學創作的工作。這本書的成功提示了我,我應該對脊椎動物、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兩棲動物和魚類進行類似的綜合研究。
在那個時候,你會看到很多優秀的生物學家研究不同種類脊椎動物的社會行為,比如靈長類動物學家珍·古道爾(Jane Goodall)和迪安·福西(Dian Fossey)。我認為是時候把他們最新的研究納入一個更普遍的理論中,與我和其他人研究的無脊椎動物的相關理論聯系起來。1975年出版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就是這些方面的整合,包括了對靈長類動物社會行為的新研究。
事實上,在這本書的最后,我用了整整一章來描述智人,一種經歷了很多進化過程的靈長類動物。我認為,人類的很多社會行為都可以用特定活動和步驟的自然選擇來解釋,從而導致更加復雜的群體選擇。
這不是什么新鮮事。達爾文以無可挑剔的邏輯提出了這個觀點,而我的創新是把現代人口遺傳學和進化理論引入了人類社會行為的研究。我想把生物學和社會科學結合起來,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人性。當您在寫最后一章的時候,是否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
寫的時候,完全沒有意識到。我當時以為會有褒獎,因為它將為社會科學提供一個新的寶庫,包括背景信息、比較分析、術語和一般性概念,可以闡明人類社會行為中此前未被研究的各個方面。
但20世紀70年代初,當這本書寫出來的時候,是一個激烈的政治爭論時期,其中大部分與越南戰爭、民權和對經濟不平等的憤怒有關。在哈佛大學,我的一些同事——在這里我不提他們的名字,他們對人類可能有本能這一想法有異議。他們認為《社會生物學》是危險的,充滿了種族主義和優生學的暗示。事實上,我的書與種族主義無關,只是總有人用我的理論去描繪他們自己的臆想。他們認為《社會生物學》這本書支持基于遺傳學的種族主義?
我想你可以這樣描述他們的觀點。無論怎樣,當時出現了很多抗議,情況非常糟糕。當我在哈佛科學中心就這個問題發表演講時,一群暴徒聚集在大樓外,我必須由警察在后面護送才能到演講廳;當我出現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組織的一次會議時,一些抗議者走上講臺大聲抗議,其中一名抗議者從我身后過來,把一罐冰水倒在我頭上。
那您當時是怎么應對的?
我抹了抹身上的冰水,繼續演講,其實那也是我唯一能做的。雖然您沒有廣泛地談論您的政治觀點,但人們都感覺您是一個信仰自由主義的人。當時,被形容成“極端反動分子”,您是怎樣的感受?
當時我擔心這會干擾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女兒。一天,哈佛廣場上有一群暴徒,他們阻斷交通,要求學校開除我,說因為我有“種族歧視”。不過我的家人從來沒有受過影響。我知道自己是對的,我知道自己必須挺過這場風暴。
果然,過了一段時間,《社會生物學》一書的思想開始滲透開來:遺傳學是理解生物進化和行為學等方面的一種有效方法。隨著時間的推移,認為這本書有害的觀念開始消失,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對這種方法表示贊同,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采用了這種方法。
真正結束一切爭議的時間點是在兩年后,我獲得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授予的國家科學獎章。我還面向更多的讀者撰寫并出版了一本關于社會生物學的書籍——《論人性》,它獲得了普利策獎。
最近出版的《創世紀》一書談到了《社會生物學》中的一些觀點。您重新審視的問題之一是“什么是人性?”您還問“是自私驅動了人類進化嗎?”我很好奇,為什么現在寫這本書?
20世紀60年代初,我遇到了英國遺傳學家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D. Hamilton)。他有一個絕妙的想法,即社會行為起源于所謂的“親緣選擇”或“廣義適應度”,即群體中的個體對那些與他們共享最多基因的人表現出利他行為。
在親緣選擇中,個體可能會犧牲他們的財產,甚至他們的生命——為了那些與他們共享最多基因的親屬的利益。因此,一個人可能更愿意為兄弟姐妹犧牲,而不是堂兄弟姐妹或非親屬。親緣選擇的最終結果將是一種利他主義,盡管它僅限于你的親屬群體。
這一觀點很快成為進化生物學領域的絕對真理。我曾幫助宣傳漢密爾頓的作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它產生了懷疑。
當然,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觀察到復雜的社會是通過群體選擇進化而來的,在這種社會中,個體會為了群體的生存而利他,螞蟻就是一個例子。事實上,你想想看,主宰地球的很多生物都是合作性的——螞蟻、白蟻、人類。
與此同時,哈佛大學應用數學家馬丁·諾瓦克(Martin Nowak)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他和同事科瑞娜·塔尼塔(Corina Tarnita,目前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一直在準備自己的論文,詳細闡述他們對親緣選擇的理解。我們的努力是一致的,最終合作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在文中我們斷言漢密爾頓的理論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我們覺得它無法解釋復雜的社會是如何產生的。
您于2010年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文章引發了又一輪的學術爭論。論文發表幾個月后,您的同事們——130多位進化生物學家,給編輯寫了一封信,對您的論文提出了質疑。您有沒有想過“哦,不,又來了?”
《自然》雜志的編輯們有不同的看法。在論文發表之前,他們從倫敦請來了一位編輯,我們就論文中的問題開了一個研討會。他們有相當高的標準,后來,他們很滿意,認為這是一篇論證充分的文章——也許在一些細節上有錯誤,但他們決定發表。事實上,他們非常喜歡它,把它做成了一個封面故事。
那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騷動呢?
我要取消或試著替換一個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已經獲得了相當多的追隨者,他們把它寫到自己的博士論文和簡歷中,他們的事業依賴于它,他們就這方面寫過文章,著過書,還開過研討會,所以他們不喜歡我。他們說:“很明顯,這就是真理。你怎么能否認呢?”而我們表示:“我們有數學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
隨著《創世紀》的出版,您重新揭開了舊傷疤,這不是與批評者針鋒相對嗎?
我曾經確實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關于群體選擇的問題。我認為把理論建立在堅實的數學和證據基礎上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就應該把它推翻。
《創世紀》是我寫過的最重要的書之一。這本書表明,群體選擇是一種可以被精確定義的現象,我可以證明它至少發生過17次。

E. O. 威爾遜正在搜集與莫桑比克戈龍戈薩國家公園有關的科學信息
群體選擇是進化的巨大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生命從類細菌生物體進化到內部有結構的細胞,再到由這些細胞組成的簡單生物體,再到形成組織分化的生物體等等。我在群體和個體選擇的背景下介紹了這些轉變。
現在我們知道,有一系列的社會行為是高級社會的基礎。對于人類來說,我們的進步得益于我們是兩足動物,擁有自由的手臂和可以握緊的手指,而且我們最初生活在稀樹草原上,那里頻繁的自然火為我們提供了燒熟的動物。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個良好的長期記憶力和高水平的合作能力,還有一個強大的激勵因素——利他主義。
漢密爾頓理論暗示,當親戚們聚在一起時,就有一種機制在起作用,由于有共同的基因,他們更有可能形成一個群體。然而,這種解釋從數學角度來看,漏洞百出。我們進化成功部分是因為群體的形成,往往是利他的。不管有沒有基因關系,這些群體經常合作。
就您的理論,能給我們總結一下嗎?
我的同事大衛·威爾遜是這么說的:在群體內部,自私的個體會打敗利他的個體,然而,群體之間爆發沖突時,由利他主義個體構成的群體會打敗自私個體組成的群體。
關于人性的消極方面,我們已經聽到了很多了。有很多證據表明,我們進化是因為我們認為團結一致對未來是有利的。
威爾遜博士,您本人非常和藹可親,彬彬有禮。那么,為什么您會成為一個富有爭議的人呢?
也許是因為相比那些僅僅是令人愉快的想法,我更喜歡原創的想法。
您與馬丁·諾瓦克的合作非常成功,您經常與數學家合作嗎?
是的。我認為數學模型是一種思考復雜的定量和定性問題的好方法。
數學模型可以精確地預測一些事情。生物學研究驗證了這些模型。就像我在《創世紀》中所寫的那樣,當我試圖建立一個精確的可驗證的理論時,我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應用數學家,如果幸運的話,他們會解決問題的。
這種方法令人興奮。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我與諾瓦克的合作,我開始相信一門全新的學科正在興起,它將把該領域的博物學與數學建模和類似于實驗室中進行的實驗結合起來。
這種科學對公眾來說會更有趣,對希望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年輕人也會更有吸引力。它也將給我們一個更堅實的基礎,以拯救自然世界。
當您考慮與一位數學家合作時,您對對方一般有什么期望?
就像我要找一位水管工或建筑承包商,我希望他們把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
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您還和誰有過類似的合作?
當我在研究信息素傳播理論時——氣味是如何在螞蟻和蛾子之間傳播的,我和比爾·博塞特(Bill Bossert)合作。他是一位應用數學家,后來獲得了哈佛大學的教授職位。
早些時候,我和另一位受過數學訓練的杰出生態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已故的羅伯特·麥克阿瑟一起合作。我們一起創立了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在不同大小的島嶼上有一定數量不同種類的生物體。我們的研究是基于此前我去南太平洋研究螞蟻物種時收集的數據。麥克阿瑟構建了合適的模型來確定如何將我的數據應用于新問題。
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成就了您的事業,但隨著您90歲生日的臨近,您是否想過自己最希望被人記住的事情是什么?
說實話,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笑)。
嗯,也許我想被人記住的是,自己活了這么大把年紀,但一直富有成效;我想被人記住的是那些自己為之付出了努力的事情;我當然希望人們記住我創造了幾個對科學產生影響的新學科和理論體系。
提一個敏感的話題,我想知道您是否考慮過“死亡”呢?
哦,我已經能夠坦然面對死亡。我最喜歡達爾文的一句話,是他留給家人的最后一句話:“我一點也不怕死!”
我也一樣不怕死。我把生活看成一個故事,在故事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好多事情。其中一些事情,對你和其他人來說非常有意義,甚至有些事情對你而言是很艱熬的,但你挺過來了。最后,別人把你做的各類事情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故事。這就是生活的意義。
太多的人認為死亡是一個等待來生的車站,或者一些人關注能否找到一種方法,將生命時長延長10%或20%。我并不欣賞這種做法。我對死亡沒什么害怕和擔心的,當下,我的注意力更多放在目前正在寫的關于生態系統的這本書上,然后想辦法去莫桑比克做實地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