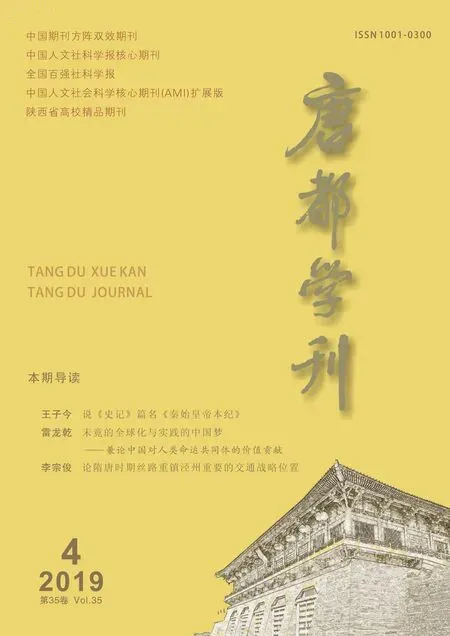秦二世“壞宗廟”試解
邱文杰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北京 100872)
一、問題的提出
賈誼《過秦論》為漢初著名政論[注]《文選》即收錄其上篇列于“論”體之首,參見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51《論一·過秦論》,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707~709頁。。司馬遷所撰《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篇末錄有其文,《史記索隱》引鄒誕生說,謂“太史公刪賈誼《過秦》篇著此論,富其義而省其辭”[1]283。《過秦論》下篇在論及秦二世時有這樣一段表述: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后奸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其中,“壞宗廟,與民更始”一句,中華書局《史記》1982年標點本、2014年修訂本都以“壞宗廟與民”連讀[注]《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84頁。《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357頁。此處標點略有調整。。《史記集解》在此句下引徐廣說“一無此上五字”,點校者的處理或受此影響。再者,“壞宗廟”“與民更始”在秦史文獻中極為罕見,所以梁玉繩《史記志疑》即認為:
徐廣謂一無“壞宗廟與民”五字,甚是。二世無壞宗廟之事。“更始作阿房宮”為句,謂復作阿房宮也。[2]
但此后俞樾《諸子平議》認為“與民更始”四字應單獨成句[注]參見俞樾《諸子平議》卷27《賈子一》,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44頁。實際明人凌稚隆所輯《史記評林》亦作如此斷句。參見凌稚隆輯《史記評林》(第一冊),廣陵書社2017年版,第590頁。。近年來,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秦簡中有所謂“二世元年詔書”,其中有“宗廟”“與黔首更始”等相關表述: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事)及箸(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以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正面)吏、黔首其具(俱)行事,毋以(徭)賦擾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注]釋文參見張春龍、張興國:《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出土簡牘概述》,載于《國學學刊》2015年第4期。相關校改參見陳偉:《〈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通釋》,載于《江漢考古》2017年第1期。收入所著《秦簡牘校讀及所見制度考釋》第十四章,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362頁。
此外,北京大學藏漢簡《趙正書》亦載有類似表述:
北大漢簡整理者即在注釋中引述賈誼《過秦》與兔子山二世詔書,并指出了其中的聯系:
簡文說秦二世“壞其社稷,燔其律令”,未見于傳世文獻。賈誼《新書·過秦》稱二世“壞宗廟,與民更始”,其說與《趙正書》有相似之處。《趙正書》下文李斯稱秦二世“滅其先人”,當指“壞宗廟”而言。[3]191
此處將“壞宗廟”和“與民更始”點斷[注]相關句讀又見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北京論壇(2016)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互信·合作·共享: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分論壇論文及摘要集》,2016年,第10頁。王志勇《〈史記〉新考》,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58頁。王文在句讀校改時亦曾引兔子山詔書與《趙正書》,但僅關注到“與民更始”的句讀問題,未涉及“壞宗廟”問題。,同時提示《趙正書》“滅其先人”與“壞宗廟”之關系,值得重視。但句讀校改之后,“壞宗廟”單獨成句則需進行解釋,本文即在此基礎上結合相關出土與傳世文獻試為申說,以就正方家。
二、二世皇帝元年“議尊始皇廟”平議
實際上,有學者已經指出“二世元年分明載有將襄公以下之歷代先君廟盡行‘軼毀’事,賈誼語蓋謂此”[注]參見韓兆琦《史記箋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4頁。盡管此處僅為推測,但據筆者目力所見,只有該書提到這兩者的關聯。。同時,也有學者注意到益陽兔子山二世即位詔書“宗廟吏(事)”即與《秦始皇本紀》所載二世元年(前209)這份“議尊始皇廟”詔書有關[注]參見鄔文玲《秦漢簡牘釋文補遺》,“秦漢史研究動態暨檔案文書學術研討會”論文;此處轉引自王子今《秦始皇議定“帝號”與執政合法性宣傳》,載于《人文雜志》2016年第2期。相同意見還見陳偉《〈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考釋》,收入所著《秦簡牘校讀及所見制度考察》,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頁。,下面對此次元年廟議做具體分析:
(二世皇帝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注]參見錢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頁注釋。韓兆琦《史記箋證》,第493頁。“或在西、雍”一句標點參考王子今:《關于〈史記〉秦地名“繁龐”“西雍”》,載于《文獻》2017年第4期,第5~6頁。
此處群臣奏議相較二世“議尊始皇廟”之詔令要求遠為豐富,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部分。
前半部分“古者”至“不軼毀”是其理論依據。“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這一記載多見于先秦儒家經典。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即指出“此議與《穀梁》《王制》《禮器》《荀子》合,博士之議固存也”[4]。皮錫瑞《經學歷史》在探尋經學在漢代之前的源流時,也提到此次廟議事件:“秦廷議禮,援天子七廟之文;見《秦始皇本紀》。……良由祖龍肆虐,博士尚守遺書。”[5]58周予同在注解中說道:“博士,秦官。秦焚書后,博士伏勝藏《尚書》,至漢,以傳朝錯,即博士尚守遺書之一例”[5]61。意即此次廷議,群臣所奏“天子七廟”之說應主要來自儒家思想。但秦王朝已經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三十四年(前213)兩次分別否決丞相王綰、博士淳于越“封子弟功臣”的勸諫,即此時的秦王朝已經廢除諸侯之制。所以,此次廟議是在秦朝已全然實現“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背景下進行的。所以,二世與群臣最終僅截取“天子七廟”之名,諸候、大夫之廟則因郡縣體制被廢棄。這是先秦以來宗廟制度發展的重要變革,也應當是賈誼批判二世“壞宗廟”所包括的內容。這亦與西漢中后期興起的“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6]3079不同。
后半部分就是在“天子七廟”的理論指導下群臣給出的具體解決方案。但是,對于奏議中“所置凡七廟”,學者認識有分歧,一說此七廟包括始皇廟:
此時所立皇帝“七廟”中,除了秦始皇廟和秦襄公廟外,其他五廟極有可能是秦始皇以前五代祖先宗廟。秦始皇廟作為秦皇帝宗廟始祖廟,世世不毀。其余六廟將隨世數的遞進,親盡后依次遷毀。[7][注]相近觀點還參見范云飛《從新出秦簡刊秦漢的地方廟制——關于“行廟”的再思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40,2016-05-03。
但此說與二世“尊始皇廟”之主旨難以契合,將始皇廟列為七廟之末,即使作為“帝者祖廟”也未盡尊崇之義。還有學者認為,所置七廟與始皇廟分屬兩個序列,其說可參:
“始皇廟”作為二世的父廟,規格已經夠高了,如欲再增,只有將始皇廟升格為天子“祖廟”,由天子“獨奉酌祠”,而不再祭祠襄公以下諸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的諸廟,合并為“七廟”,由“群臣以禮進祠”,從而使始皇廟成為秦帝國第一代祖廟。這樣,既符合“天子七廟,雖萬世世不軼毀”的古禮,又適合二世推崇始皇的現實需要。秦國的宗廟系統經此重新編組,就形成一個新形態的國廟系統。[注]參見錢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第188頁;具體標點改動還參見同頁注釋。相近觀點又見韓兆琦:《史記箋證》,第500頁。張益群《秦—西漢時期皇帝宗廟制度變革及其政治文化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11頁。
從上下文意來看,后說將此次廟議分作先王“七廟”系統與“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系統應更符合事實。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再來理解此次廟制改革,便可以有新的認識。二世“議尊始皇廟”與秦始皇“議帝號”一樣,對秦帝國皇帝制度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此次廟議確立以始皇廟為秦王朝皇帝祖廟,不僅是二世自身鞏固執政合法性的重要舉措,客觀上也使得宗廟系統完成了從“天子—諸侯”向“皇帝—郡縣”的徹底轉變。
此處還需辨析出土文獻中出現的“泰上皇”與“泰上皇廟”問題。近年出版的《岳麓書院藏秦簡(肆)》中出現“泰上皇廟”的表述:“泰上皇祠廟在諸縣道者……325/0055(2)-3”[8]202。有學者將之與漢高祖劉邦在其父去世后“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6]68相聯系,認為“秦始皇、漢高祖的做法如出一轍,只不過秦朝以縣道為單位立廟,西漢則是以郡、王國為單位”[9]。這是較為合理的推斷,對于我們理解賈誼“壞宗廟”的認識亦有啟發。
整理小組認為“此令稱‘泰上皇’,后又有‘二年’紀年,其抄寫年代必不早于秦二世二年”[8]226。其所謂“二年”紀年,實際是指同書所載“泰上皇令”“二年曰復用”(簡329-331)之令文,但學者也指出此“二年”應為秦王政二年[10]。筆者認為后種意見更為合理。又由于此簡下端字跡漫漶,所以詳細內容無由得知。
二世元年廟議之后太上皇廟應該已經并入襄公以下迭毀過后的七廟之中,其地位在二世時應有相應調整。下面我們可以結合秦史中皇帝神性的抬升與西漢太上皇廟的安排兩個層面分析此說的合理性。
有學者據里耶秦簡“更名木方”中“泰上觀獻曰皇帝[觀獻][注]釋文參考游逸飛《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選釋》,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簡帛》(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頁。,天帝觀獻曰皇帝[觀獻]”以及里耶簡中令史的“行廟”記錄,并參考岳麓秦簡的材料,認為:
里耶“秦更名方”還記載了皇帝祭祀承襲了天帝祭祀的儀式。意味著皇帝等于天帝,秦始皇帝被充分神格化,泰上皇亦然。岳麓秦簡與里耶秦簡兩相參證,可推測遷陵縣的泰上皇廟使用的祭祀儀式是原先天帝祠廟所使用的祭祀儀式。我們甚至可進而推測秦始皇在遷陵縣立的不只是泰上皇廟,可能還有自己的始皇帝廟。秦始皇在活著的時候就在郡縣廣立始皇廟,讓地方官吏以天帝祭祀儀式祭祀始皇帝他自己。原因無他——秦始皇帝是神,秦帝國是一個神權統治的國家。皇帝的神權無遠弗屆,直至天邊,這似乎就是秦代普立郡縣宗廟的真諦。[11]
從上文分析來看,二世既然下詔“議尊始皇廟”,則秦始皇生前自行立廟的可能性不大。里耶秦簡記載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相合,有學者指出“‘追尊’使用‘皇’而非‘帝’,既與‘皇帝’可相參照,又與‘皇’較‘帝’為高,卻又較‘帝’號虛化,可相聯系”[12]。筆者認同這一觀點,同時“泰上觀獻曰皇帝”“天帝觀獻曰皇帝”兩條與“莊王為泰上皇”同時出現于更名木方,也說明皇帝與泰上皇之不同。
此外,皇帝得到等同“泰上”“天帝”的待遇,實際后者也是一種虛化的神權符號,這與將“泰上”冠于“皇”字之前有可模擬之處,更進一步證明秦始皇時莊襄王之宗廟待遇不太可能是“原先天帝所使用的祭祀儀式”。而且,在秦始皇時代,伴隨著始皇個人神性的抬升,先王“宗廟之靈”開始逐漸讓位于始皇“陛下神靈”,這可以從傳世文獻中找到依據。有學者曾指出秦始皇非常重視“宗廟”在其并天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3],但筆者注意到,李斯等人在與始皇的奏對中實際已經有將天下一統是“賴宗廟之靈”轉化為“賴陛下神靈一統”的趨勢,這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的兩次廷議中表現得極為明顯: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廷尉李斯議曰:“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始皇曰:“……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廷尉議是。”[1]235-239
從上述表述來看,盡管秦始皇兩次提及“賴宗廟”,但李斯奏對則是“賴陛下神靈一統”,那么他是在奏議中有意抬高始皇個人的神圣性,其后,始皇三十四年周青臣亦有“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1]254的相近表述。所以,從李斯到周青臣,再到二世元年“議尊始皇廟”,始皇“陛下神靈”應是逐漸抬升的。所以,“先王”與“皇帝”之間的張力實際在始皇時代已有所顯現。
所以,學者所提示“秦更名方進一步揭示皇帝神格化的內涵:皇帝不僅是天下的統治者,更是可以取代‘泰上’、‘天帝’的神明”[14]等信息,值得我們充分重視。實際皇帝名號的神格化應與李斯奏對中所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密切相關,由“宗廟之靈”到“陛下神靈”正體現出這種神格化的演變趨勢。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就如劉邦尊其父為太上皇一樣,他們作為帝國的開創者,既需要追溯自身的來路,同時又必須凸顯開國始、太祖的神圣性。所以,始皇此舉更可能是先推尊其父為太上皇,這樣就使得始皇帝與秦“先王”之間有了過渡或緩沖,但太上皇又不同于真正的“皇帝”,所以就更可能是從“宗廟之靈”轉向“陛下神靈”的一個過渡階段,其地位應處在先王與皇帝之間。
始皇死后,二世的合法性實際來自“遺詔”和“宗廟事”,也就是兔子山詔書開篇所宣稱的內容。但他所面臨的現實情況與始皇稱帝時已完全不同,他是在其父已然稱帝之后即位,所以,如何處理始皇的宗廟地位就成為其即位后的頭等大事。秦二世只有通過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以及“天子獨奉酌祠始皇廟”才能實現“二世皇帝”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還有,從上文分析來看,秦更名木方中“泰上”“天帝”與“皇帝”的對應已體現“陛下神靈”的發展,二世元年廟議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在宗廟系統中抬升始皇作為帝者之祖的神性。所以,二世時“泰上皇廟”理應歸入“先王七廟”,以示“帝者祖廟”的區別。
盡管目前缺乏更為詳細和直接的證據,但我們對照西漢初年的歷史,也能為上述論點提供佐證。觀察漢初歷史,我們發現,不唯泰上皇之名號與立廟一事秦與漢相同,漢惠帝在高祖下葬后同樣也與群臣有過議尊高祖廟的舉動: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1]392
惠帝與群臣議尊高祖廟的地點值得注意。《漢書》同敘此事,作“反至太上皇廟”。這是因為彼時高祖尚未確定廟號,漢家唯一的宗廟即是劉邦所立太上皇廟,所以在太上皇廟為劉邦議廟號是合適的。
但秦二世詔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的現實情況與漢不同[注]顧頡剛曾言“漢初立廟本無計劃”。即因劉邦出身平民,漢惠帝也無需如秦二世一般需要處理龐大的先王宗廟問題。參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八冊《湯山小記(四)》“韋玄成、匡衡等請廟、寢、園以親盡迭毀與其波折”,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第八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5頁。,因為秦王朝統一之前還有長達五六百年的“先王”時代[注]秦自襄公始封諸侯至秦二世而亡,《秦始皇本紀》所附《秦記》與《秦本紀》《六國年表》所載年數不同。參見《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364頁。相關辨析又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自序》,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31~32頁。。同理,秦二世與群臣為始皇議廟必然要在統一之前歷代先王的基礎上進行,這也就是群臣為何提出“自襄公以下軼毀”的問題。二世時所面臨的太上皇僅是秦歷代先王中與始皇血緣關系最近的一位,在他即位之時,太上皇這一名號的象征意味應大大弱化了。所以,秦二世所面對的問題與西漢初年劉氏宗廟除劉邦外僅存太上皇廟是不同的。而且我們能夠看到,在西漢中后期進行宗廟迭毀時,太上皇廟也是親盡宜毀的對象。
惠帝初年,其與群臣所面臨的僅是從未踐天子位的“太上皇”,復因當時“天下初定,遠方未賓”,所以才“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6]3116。但到元、成時期,就出現宗廟系統過于龐雜的問題:
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6]3115
所以,漢廷也面臨宗廟的取舍,韋玄成等人曾上奏:
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后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注]《漢書》卷73《韋玄成傳》,第3118頁。西漢中后期宗廟制度改革參見楊英《祈望和諧:周秦兩漢王朝祭禮的演進及其規律》,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27~446頁。
如上所述,他們的解決方案是將高帝廟作為“帝者太祖之廟”,“太上皇”廟“宜毀”。反觀秦朝,秦“先王”祭祀系統也極為龐大,所以秦廷群臣所要解決的是如何安排秦“先王”宗廟以及在此基礎上如何“尊始皇廟”。他們的方案也是尊始皇帝廟為“帝者祖廟”,但由于先王系統過于龐大,肯定不能全部毀棄,從而找到“自襄公以下迭毀”的方案,但迭毀之后的先王祭祀禮儀必然會因始皇廟作為“帝者祖廟”而有所區別。
對照西漢宗廟制度的發展,我們認為,秦二世與群臣所面臨的情況較漢惠帝時更為復雜。既要在秦先王宗廟系統的基礎上“議尊始皇廟”,同時必須對先王系統進行改造,以突出始皇廟作為“帝者祖廟”的特殊地位。因此,二世與群臣對宗廟系統的改造應如錢杭等學者所說,分為先王“七廟”與始皇“帝者祖廟”兩大系統。
至于秦始皇時所立之太上皇廟,盡管目前缺乏直接材料,但從二世元年的廟議,以及皇帝名號逐漸神圣化的趨勢,乃至西漢宗廟迭毀時亦毀太上皇廟的舉動,都能說明太上皇及太上皇廟在秦二世時期的地位應伴隨著始皇地位的抬升而有所下降。所以,此次廟議實際是在宗廟系統中實現從秦國向秦帝國的轉型:從縱向時間線來看,秦二世迭毀先王廟,使得先王宗廟與帝者祖廟形成兩個序列,從而實現始皇廟作為帝者祖廟之尊崇;從當時的現實政治及空間格局來看,秦二世進一步鞏固了剔除諸侯之后的“皇帝-郡縣”的全國宗廟系統,而且僅僅皇帝有資格“奉酌祠始皇廟”,而地方郡縣對始皇廟之祠祭則完全與血緣或宗親無關。天子、諸侯、大夫的廟制序列亦不復存在。
由此可見,這次宗廟系統的改革最終實現了宗廟制度與秦“皇帝—郡縣”體制的真正適配。
三、“過秦”——從“尊始皇廟”到“壞宗廟”
秦二世元年“議尊始皇廟”實際包括先王“七廟”與始皇“帝者祖廟”兩個系統。同為二世元年的兔子山詔書在開篇也有“宗廟吏(事)”的記載,上文所引鄔文玲、陳偉等學者已指出可能與“議尊始皇廟”有關,筆者認為此說是合理的[注]除前文注釋所引,王子今也注意到兩種文獻之間的聯系,并認為“所謂‘宗廟事’,似乎宜于結合較寬廣的政治崇拜傳統和國家權威信仰的意識背景予以理解”。參見王子今《秦始皇議定“帝號”與執政合法性宣傳》,載于《人文雜志》2016年第2期,第82頁。確實如此,始皇廟地位之“尊”,正在于其與“先王廟”之間的區分。。同時,賈誼《過秦論》所謂“壞宗廟”實際也應來源于此,只不過其所側重是在秦先王“七廟”之迭毀。實際上,秦二世元年“議尊始皇廟”之內涵非常豐富,如上所論,群臣必須在合理安排先王諸廟的基礎上為秦始皇這位秦朝皇帝之祖尊立宗廟,這就使得兔子山詔書之“宗廟事”其實也應該包含上述兩層含義。當然,詔書明顯偏重“尊始皇廟”而確立二世自身皇帝身份的合法性,而賈誼之批判二世“壞宗廟”則偏重二世對先王宗廟之迭毀。因此,二者所論均為《秦始皇本紀》所載二世元年“議尊始皇廟”事。
需要說明的是,二世在詔書中宣揚之“今宗廟吏(事)及箸(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與賈誼《過秦論》所謂“壞宗廟”之批判大相徑庭。我們以為,賈誼的批判實與其所處之西漢初年的現實政治環境有關。
《過秦論》《趙正書》與兔子山二世元年詔書這三份文本存在微妙的聯系。我們看到,前兩者的相關表述實際均來源于后者。“與民更始”一語就極為明顯,我們在敘述秦二世時期歷史的傳世文獻中很少見到這一語匯。即使存在于《過秦論》中,歷史上諸多學者也多認為當依徐廣之說進行刪節。
但從兔子山詔書原文來看,《趙正書》與《過秦論》這兩種西漢初年的文本就直接如實引用了二世詔書,當然又在此基礎上展開了各自對二世的批判。除此之外,《趙正書》中的“燔其律令”與兔子山詔書中的“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可以相互聯系。同時,兔子山詔書中“宗廟吏(事)”與《趙正書》“滅其先人”以及《過秦論》“壞宗廟”亦可對讀。由此可知,《趙正書》與《過秦論》保留了某些歷史細節,他們所依據的史料都在司馬遷《史記》成書以前,因此其所保存之吉光片羽對于我們理解當時的歷史有著重要意義。
據《史記》記載,賈誼入仕以前即“頗通諸子百家之書”,而且被廷尉吳公“召置門下,甚幸愛”[1]2491。所以,其青年時代之讀書、游歷應主要在惠帝、高后時期,則《趙正書》等文獻肯定包含在“諸子百家”之中,或者說至少此種對秦始皇以及二世時期的歷史敘述以賈誼之博學是應當熟知的,而且彼時去秦亡不到三十年,二世詔書必然世所習知。此外,尤為值得重視的是吳公的身份,他“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因此對秦王朝的統治實況應較為了解,賈誼在其門下,日常問對中必然對秦朝史實有所涉及[注]傅樂成即認為賈誼應當深受吳公影響,“賈誼受知于廷尉吳公,而吳公是李斯的弟子,自是法家。賈誼雖非吳公弟子,但受吳的影響,則可以想見。故誼少時雖以能誦詩書屬文見稱,然亦‘頗通諸家之書’,且明習法令,熟諳制度”。參見所著《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49頁。。因此,賈誼《過秦論》等政論思想與其被吳公“召置門下”的經歷可能有密切關聯。如此,我們再來看“壞宗廟,與民更始”的具體語境:
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后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注]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4~16頁。此處標點略作改動。
此處節引之首段是在批判秦始皇“王天下”而不能改弦更張,其中就有對其盡廢分封的不滿。“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是較為明顯的表述。“殷周之跡”與“三王建天下”實際也屬同類。秦始皇三十四年咸陽宮之議,博士淳于越即有“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以為枝輔”的表述,即是勸諫始皇分封。自然,賈誼此處更深層次的涵義當指安撫臣民使不為禍亂,但其對封建的態度則無疑是肯定的。
接下來“今秦二世立”一段,實際是賈誼“替秦二世設計了一個救亡自存之道”[15]。但事實上,秦二世也在“縞素”之時進行了一番改作,即兔子山元年詔書所言宗廟、律令、解除故罪等方面。所以,賈誼此段的邏輯是以自己的立論批判二世的政策。
在這樣的文本情境下,我們看到在“縞素而正先帝之過”之后緊接“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國立君以禮天下”兩句,則是認為二世應該復行封建,對功臣、宗親應當“裂地”“建國”。
王夫之《讀通鑒論》即指出賈誼此論之背景:“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于封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勢有所不得遽革也。”[16]蕭公權在探討賈誼思想時也曾引用這兩句話,認為“賈生對于始皇之郡縣制亦不能同情”,其又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并且進行了總結——“賈生此論欲兼用封建、郡國之長,蓋亦根據漢代之實踐經驗以立言,又非純懲秦弊矣”[注]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89頁。王興國所著《賈誼評傳》也提到“賈誼并不反對分封制”,賈誼“把秦二世不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國立君以禮天下’,作為其失敗的原因之一”,參見所著《賈誼評傳附陸賈晁錯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頁。。
確實如此,賈誼認為封建制也必須順應時勢變化而進行靈活調整,他在勸諫文帝調整諸侯封國時就曾舉高祖劉邦滅異姓功臣而立諸子的做法:“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6]2260-2261此外,我們從引文第三段中也可看到“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的表述,實際分別可以對應宗室與忠臣,亦能凸顯賈誼對秦統一之后實行徹底的郡縣制的批判。漢初諸帝因無先王問題,所以對宗廟的設立并無統一規劃。高祖時令諸侯王立太上皇廟,惠帝時亦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廟。所以賈誼所處時代漢王朝的宗廟系統應為“皇帝—諸侯/郡縣”模式。諸侯王國亦各有宗廟。
反觀秦二世元年廟議結果,其不僅迭毀先王廟,而且在繼續始皇所確立之郡縣制的基礎上推行以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的新的皇帝宗廟系統。不難推想,如果秦沒有二世覆亡,則秦始皇時在郡縣所設太上皇廟亦會因始皇廟作為帝者祖廟的影響而逐漸式微,因為本質上太上皇還是屬于先王一系,其過渡性在始皇時期具有重要意義,但在二世時因其父皇帝稱號之已然確立,其現實意義和價值當有所削減。同時,李斯“賴陛下之神靈一統”的表述既有迎合始皇之意,同時還為其下文“皆置郡縣”“置諸侯不便”提供法理依據。因為皇帝神性及其地位之抬升,又參以相對完備的官僚制系統,諸侯就徹底被排除,西周以來的宗法分封亦完全瓦解。“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這一先秦宗廟系統就僅保留“天子七廟”。所以,二世元年“議尊始皇廟”的舉措在身處漢文帝時代的賈誼看來,一是迭毀先王廟定然會對先祖有所不敬[注]明人徐孚遠《史記測議》在“所置凡七廟”句下將二世迭毀先王宗廟、獨祭始皇廟的行為與東晉桓玄相對照,認為二世因不祭其祖而亡國滅身——“桓玄祭不及祖,晉人以為譏。今秦二世亦不及其祖,自身而失之,二事同也”。參見陳子龍、徐孚遠輯:《史記測議》卷6《秦始皇本紀》,吳平等編《〈史記〉研究文獻輯刊》(第三冊),影印明崇禎十三年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頁上欄。,二是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后形成的即是從皇帝到郡縣的宗廟體系,因不復行封建,而與漢初諸侯、郡國廣立宗廟的體制不同。而且亦無“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注]《漢書》卷5《景帝紀》,第138頁。顏師古引張晏說,“王及列侯歲時遷使詣京師侍祠助祭”。這種保持皇帝與諸侯王、列侯血緣認同的舉措,所以此宗廟之制既不合漢人所理解的殷、周之制,亦有違西漢初年的宗廟體制。

至于“壞其社稷”,則是指對功臣的屠戮,亦即《趙正書》的核心議題,在李斯這段話之前,子嬰在勸諫二世時曾列舉趙、燕、齊三王殘殺忠臣、重用佞臣因而亡國之事,隨后有一句總結——“是皆大臣之謀,而社稷之神零福也”,此處實際是將社稷與大臣(忠臣)建立聯系。因而,《趙正書》中“壞社稷”實指二世不聽子嬰、李斯等進諫而屠戮功臣,從而與燕、趙、齊三王一樣自毀社稷。所以,兔子山詔書“宗廟事”、《趙正書》“滅其先人”與《過秦論》“壞宗廟”這些表述都提示我們,二世元年的這場廟議對秦末漢初的歷史曾有過較大影響。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文本都產于生在《史記》成書以前。而且與《史記》相比,《新書》的敘述重心不在二世得位之正與不正[注]陳侃理曾指出“賈誼《過秦論》也不見對二世即位的正當性有何懷疑”,“可以肯定的是,其立論大致以二世合法即位為基礎,看不出‘胡亥不當立’的意識。賈誼在文帝之初年僅十八歲,應是生于劉邦稱帝以后;出生地洛陽在戰國末已屬秦,當地人在反秦戰爭中未見突出表現。他的言論,應當反映了反秦楚人以外存在的另一種歷史記憶”。詳參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而在于他不聽諫言、不改始皇之道,這一點與《趙正書》的敘述邏輯比較近似。又從他們三者都保留有“與黔首(天下、民)更始”這一語匯,我們可以推斷,《趙正書》與《過秦論》應該都是以秦王朝當時的官方正式文告(即詔書)為基本敘事框架而進行立論,盡管他們對二世的舉動基本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但卻也為我們理解秦王朝末年的一些歷史事實提供了幫助。
綜上所論,《史記·秦始皇本紀》如實記錄了二世元年廟議的具體細節,隨后兔子山詔書則是秦廷向全體郡縣頒布這一宗廟改革成果,而《趙正書》與《過秦論》對二世宗廟改革進行批判,實際是為各自觀點服務,前者側重二世不聽勸諫、誅戮功臣宗族,后者則是批判二世不行封建、不改始皇之道。所以,我們在理解《趙正書》作者及賈誼對二世宗廟改革的批判時,需要跳出《史記》所載二世陰謀篡位的邏輯(因為《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相關記載都將二世的諸多行為與其陰謀篡位相聯系),回到《史記》以前去認識漢初文本對二世政策的解讀,這樣對秦末歷史或許會有更豐富和多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