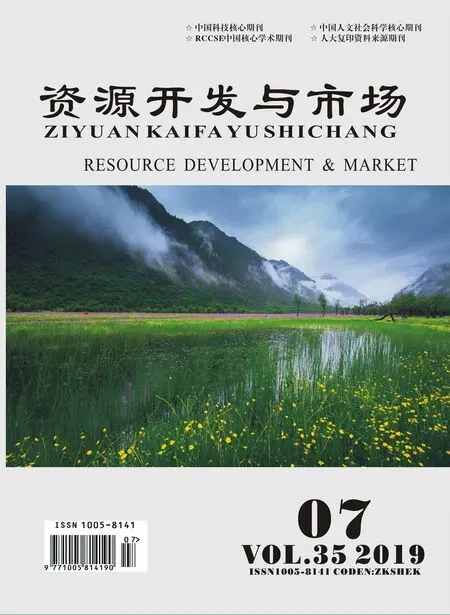基于條件價值評估法的江蘇省農戶秸稈還田受償意愿研究
余智涵,蘇世偉
(南京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37)
1 引言
我國作為世界農業大國,農作物秸稈產量巨大[1]。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方面糧食產量和農作物秸稈資源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農村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產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作物秸稈作為生活燃料、牲畜飼料、工業原料等利用方式發生了改變。以秸稈作為取暖、做飯的能源利用方式逐漸被煤、天然氣等取代;機械化作業減少了對牛耕的依賴,秸稈飼料化利用逐漸減少;為保護水資源生態環境,以秸稈為原料的小型草漿造紙廠停止生產。由于存在高額的收集成本和儲存成本,秸稈作為發電原料的資源化利用方式存在較大的發展瓶頸[2,3],在每年農作物收獲季節,大量秸稈無法得到有效利用,農戶普遍采取就地焚燒的方式[4]。2010—2017年全國每年秸稈理論資源量高達8.5億t,約有18.59%的秸稈被露天焚燒[5]。我國東部和南部秸稈焚燒影響了大氣質量和交通安全,在北方由于秸稈焚燒產生的固體顆粒物更是霧霾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6-9]。
事實上,農作物秸稈中含有豐富的氮、磷、鉀等微量元素,具有較高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秸稈用作肥料可改善土壤性質、減少農業生產對有限資源的需求提高農業生產率[10,11]。雖然可能會存在還田后播種出芽率低、易生病蟲害、機械設備不配套等問題,但秸稈還田仍是世界公認的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重要方法[12]。目前,有關秸稈還田的文獻資料主要集中在以下3類:①秸稈還田的生態效益研究。Yin等分析了現有秸稈利用方式的合理性,發現秸稈還田能有效減少化肥使用量,提出我國政府應將推廣秸稈還田作為發展綠色農業的重點[13];Yao等對比了秸稈還田與合成氮肥對土壤肥力和作物產量的影響,發現秸稈還田在增加農作物產量的同時還能有效減少N2O排放[14]。②秸稈還田的適宜方式與數量研究。Hu等研究了不同秸稈還田方式的生態影響,發現溝埋秸稈還田方式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維持農作物產量[15];Zhou等使用響應面分析法研究了不同秸稈尺寸、數量、埋藏深度的秸稈還田對土壤有機碳和養分的影響,并確定最佳秸稈長度、還田比例和埋藏深度[16]。③秸稈還田的農戶決策行為研究。顏廷武基于農戶的視角就“愿意”或“不愿意”參與秸稈還田決策使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其影響因素,發現農戶認知水平和外部環境對秸稈還田意愿的影響較顯著[17]。
綜上所述,現有的秸稈還田文獻多集中于以農田實驗為基礎的生態效益、適宜方式和還田數量研究,提出農戶參與秸稈綜合利用需要政策激勵與引導。Mueller指出,鼓勵廢棄物回收通常比懲罰機制更有效,補償政策是激勵人們參與農業廢物回收利用的關鍵因素[18]。根據高尚賓的研究,秸稈還田的補償政策應根據WTA(受償意愿)制定[19],對此提出以下兩個問題:①多少補貼才能調動農戶參與秸稈還田的積極性?②哪些因素會影響農戶秸稈還田的受償意愿?本文基于生態補償的視角,以江蘇省農戶為研究對象,使用受償意愿(WTA)來量化農戶秸稈還田的決策行為,利用Cox比例風險模型分析其影響因素,從而確定農戶參與秸稈還田所需補償的金額,為政府制定農戶秸稈還田補償政策,實現秸稈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供重要依據。
2 材料和方法
2.1 研究背景
作為我國農業大省的江蘇省農作物秸稈資源量巨大,年產量平均約為4000萬t,以稻麥秸稈為主[20]。目前,江蘇省多數城市秸稈焚燒減排壓力較大,2015年由于秸稈露天焚燒而產生的SO2、NOx、NH3和PM2.5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分別為3.72Gg、15.25Gg、2.65Gg和44.70Gg。就空間變化而言,排放量呈現出蘇中、蘇北、蘇南逐步遞減的趨勢[21,22]。為了減少秸稈焚燒、保護生態環境,國家針對秸稈還田機械、秸稈粉碎還田、秸稈還田的農機合作社和農機手等進行了秸稈政策補貼,補貼標準因各省市經濟狀況不同而異,主要集中在20—50元/hm2[23]。除了中央財政下發至各省的補貼外,部分省、市、縣也依據地方財政實力加大了補貼力度。江蘇省秸稈還田的省級財政補貼標準在蘇南、蘇中、蘇北地區分別為10元/hm2、20元/hm2、25元/hm2[24],但該標準是否以農戶秸稈還田WTA為依據,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考慮到江蘇省秸稈資源密度呈現蘇中、蘇北、蘇南逐步遞減的趨勢[25],本文選取秸稈資源分布密集區的蘇中揚州市、秸稈資源分布一般區的蘇北連云港市、秸稈資源分布稀疏區蘇南的南京市作為樣本點,對上述地區隨機抽取農戶進行調查,面對面詢問其WTA水平。
2.2 調查方法——CVM
本研究使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來調查政府需要給予農戶多少經濟補償才能激勵農戶參與秸稈還田,即研究農戶秸稈還田的具體受償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CVM是一種應用廣泛的陳述偏好評估法,調查者通過計算個人或總的WTA,可了解人們對環境資源或服務的偏好程度,從而求出此環境改善計劃或環境資源質量損失的經濟價值[26,27]。在實際調查中,由于少數被調查者故意夸大或減少自已的實際意愿,因此本研究使用二分法來調查農戶的WTA[28]。即首先詢問農戶如果政府給予補償是否愿意參與秸稈還田,如果農戶回答“是”,則給定一個初始的補償價格水平W1,即補償W1/hm2,詢問農戶能否接受。如果農戶不愿意接受,則調高至Wu1,繼續詢問農戶,如果此時農戶愿意接受,則結束詢問,確定農戶的WTA水平位于區間(W1,Wu1];如果農戶對補償價格水平Wu1仍不愿意接受,則繼續上調至Wu2,如果農戶愿意接受則結束詢問,確定農戶的WTA水平位于區間(Wu1,Wu2]。以此類推,直到達到預先設定的最大值Wu max為止。若此時農戶仍有繼續上調補償價格水平的意愿,則確定農戶的WTA水平位于區間(Wu max,+∞)。對愿意接受初始補償價格水平W1的農戶,按照上述步驟依次降低WTA水平,直到農戶不愿意接受為止。若農戶的WTA水平為0,則詢問具體原因。因此,二分法將得到半開半閉的區間數據或右截尾刪失數據,即農戶的WTA水平區間。
秸稈還田將增加切碎、耕作等成本,大多集中在50元/hm2左右[29]。本文確定初始補償價格水平為W1=50元/hm2,同時確定最大補償價格水平為Wu max=100元/hm2,區間長度為10。為了避免受訪者對回答調查問卷的問題存在各種顧慮,在開始正式問卷調查之前,調查人員會告之此次的調查目的是將數據用于學術研究,并解釋秸稈還田具有許多無形的好處,如保護環境、提高農作物產量等。
2.3 非參數估計法
根據He的研究,在不考慮家庭特征和其他相關變量影響的情況下,采用非參數估計法來測定農戶秸稈還田的的最大和最小WTA水平[30]。
農戶WTA水平最大值的估算公式為:
(1)
式中,E(WTA)max代表農戶WTA水平最大值;j表示愿意參與秸稈還田的農戶數量;WTAi表示農戶i的WTA水平,以每個半開半閉區間的中位數表示,區間(Wu max,+∞)取Wu max即100;Pi表示每個農戶i所占的權重,即為1/n。
農戶WTA水平最小值的估算公式為:
E(WTA)min=E(WTA)max×愿意參與秸稈還田的農戶數量÷接受問卷調查的農戶數量
(2)
2.4 模型建立
由于有右截尾刪失數據(100,+∞)的存在,傳統回歸模型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等無法進行數據處理[31],本文使用Cox比例風險模型來分析農戶秸稈還田WTA的影響因素。Cox比例風險模型的一般表達式為:
h(t,X)=h0(t)×exp(β1X1+β2X2+…+βmXm)
(3)
式中,h0(t)表示基準風險函數,即所有影響因素均取0時的風險函數;X1,X2,…,Xm表示m個影響因素;β1,β2,…,βm表示相應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其含義為由某一個影響因素變化引起的相對風險度變化的自然對數值;h(t,X)表示t時刻(即支付水平t)暴露于各影響因素下的風險函數,即農戶秸稈還田WTA水平為h_t的概率是其在補償價格水平t上不愿意接受,但在補償區間(t,t+Δt]內愿意接受補償的條件概率極限。
取Δt=1,由風險函數和生存函數的關系可知:
(4)

ht=1-exp[-exp(Xβ+ηt)]
(5)
假設農戶秸稈還田WTA水平在補償區間(t,t+1]外的概率為1-ht,則第i個農戶在第j個區間內相對風險度的似然函數為:
L=ηtΠ?j1-ht=[1-exp(-exp(Xβ+ηt))]Π?j[exp(-exp(Xβ+ηt))]
(6)
式中,用fi為農戶秸稈還田WTA水平所在區間特征,若該區間是半開半閉區間,如(50,60],則取fi=1;若該區間是刪失區間,如(100, +∞),則取fi=0,表示截尾數據。
總體相對風險度的似然函數可表示為:
(7)
使用迭代法對式(7)進行極大似然估計,即可得到各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β。由于Cox比例風險模型通過結合“失敗”事件發生與所經歷的時間進行分析,因此本文需要確定時間變量與刪失變量。其中,時間變量表示某一事件“失敗”發生前或到觀測結束時“刪失”的時間長度,刪失變量表示該事件是以“失敗”結束(賦值為1)還是以“刪失”結束(賦值為0)。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為WTA值的大小而非詢問次數,且本文獲得的區間為農戶的最低WTA水平所在區間,即對低于該區間的補償水平均不接受而可接受等于或高于該區間的補償水平,因此對區間[0,10]的時間變量賦值為1,對區間(10,20]的時間變量賦值為2。以此類推,對刪失區間(100,+∞)的時間變量賦值為11。此外,就刪失變量而言,除了區間(100,+∞)是以“刪失”結束之外,其他的區間均以“失敗”而結束。

表1 各變量定義及分析應用分類處理
2.5 變量選擇
根據現有研究結論,生態保護受償意愿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個體和家庭因素,環境認知因素和外部因素。李國志研究了農戶對公益林建設的受償意愿,發現受訪者的受償意愿與其受教育水平呈負相關,與其年齡呈正相關[32];李曉平、楊美玲的研究表明,受訪者的收入水平對生態保護受償意愿的影響顯著為正[33,34];朱紅根等發現,受訪者對生態環境的認知水平越高,其受償意愿就越低[35]。此外,外部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和當地是否有秸稈回收點也是影響農戶秸稈處理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36]。
本文選擇農戶秸稈還田WTA水平為因變量,其影響因素為自變量。根據“經濟人”假設,農戶具有完全的理性,農戶決策目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綜合已有的文獻和研究結果,將影響因素分為以下3類:第一類為農戶個人與家庭特征,包括性別、年齡、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數、家庭耕地面積;第二類為農戶對秸稈還田處理的認知,包括秸稈還田有益于環境保護、露天焚燒秸稈污染環境、秸稈還田有利于增加農作物產量、秸稈還田成本;第三類為政策和外部環境因素,包括政府是否積極宣傳秸稈還田、政府是否禁止露天焚燒秸稈、當地有無處理秸稈還田的配套設備、當地有無秸稈原料的企業。由于本文所有自變量均為分類變量,為了便于解釋,對于二項分類變量均按0,1編碼;對多項分類變量均用啞變量編碼。具體對變量的處理見表1。
3 結果
3.1 描述性統計與農戶受償意愿分布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收到有效問卷462份,問卷有效率為92.40%。其中,愿意參與秸稈還田的調查問卷共429份,揚州市、連云港市和南京市分別為112份、110份、207份。對于不愿參與秸稈還田的原因,農戶大多數表示無法獲得秸稈還田的配套設備,少部分農戶則表示秸稈可用作飼料或燃料,或對政府發放補償金沒有信心,見表2。

表2 農戶不愿意參與秸稈還田或WTA水平為0的原因
在429份愿意參與秸稈還田的有效樣本中,男性245名,女性184名,分別占比為57.11%和42.89%;從受教育水平來看,高中或更低學歷農戶占比為81.59%,大專或更高學歷的農戶占比為18.41%;家庭人口數方面,2名成員及以下的家庭占比為21.68%,3—4名成員的家庭占比為53.15%,5名成員及以上的家庭占比為25.17%;家庭人均收入方面,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6701.63元,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萬元以下的占比為31.00%,在1萬元以上2萬元以下的占比為47.09%,在2萬元以上的占比為21.91%。
根據2007年的《江蘇統計年鑒》,2016年江蘇省農村男性居民占50.33%,家庭人口數平均為2.94,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606元[20],這些數據與調查結果是基本一致的。其他變量如受教育水平、年齡和人均耕地面積接近江蘇省的平均水平,因此調查樣本具有代表性,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3。對秸稈還田有利于保護環境、露天焚燒秸稈會污染環境、秸稈還田有利于增加農作物產量等常識性認知,樣本均值均大于2.1,絕大多數的農戶則表示認同或非常認同的態度;在秸稈還田成本支出方面,部分農戶表示擔憂。政府在秸稈綜合利用方面積極宣傳秸稈還田并禁止露天焚燒的政策效果有限,樣本均值分別為0.8135和0.6527;當地秸稈還田配套設備和秸稈原料企業的數量也較少。

表3 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4 農戶秸稈還田WTA水平分布
由表4可知,在愿意參與秸稈還田的有效樣本中,農戶WTA水平主要集中在40—80元/hm2,這部分約占總樣本的64.88%,呈現出正態分布特征。此外,有7位農戶表示自己的WTA水平為0(表2)。進一步詢問原因,主要有以下3點:①農戶明確意識到秸稈還田有利于環境保護,有義務對生態環境負責;②農戶對政府積極宣秸稈還田較滿意;③農戶容易獲得全套的秸稈還田設備。WTA水平為0,可理解為農戶對秸稈還田的支持,因此將此部分樣本納入[0,10]區間。由此計算出農戶WTA水平最大值為每年每戶60.15元/hm2,最小值為每年每戶55.86元/hm2。其中,南京市最大,分別為每年每戶61.74元/hm2、57.33元/hm2;連云港市最小,分別為每年每戶57.50元/hm2、53.39元/hm2。可能的原因是,南京市秸稈資源可收集量在3個城市中最少且經濟發達程度最高,農戶需要更多的補償才愿意參與秸稈還田。
據統計,2016年江蘇省農戶約為2581.95萬戶,農戶人均耕地面積約4.44hm2/戶,農業總產值約為2569.37億元[20]。因此,農戶秸稈還田補償最大值約為68.96億元,最小值約為64.03億元,分別占2016年江蘇省農業總產值的2.68%、2.49%。該數值略高于王舒娟調查的江蘇省農戶的秸稈還田支付意愿水平,除了經濟發展以外,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損失規避、謹慎消費、適應性心理和捐贈效應也是WTA大于WTP1—2倍的原因[37,38]。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客觀地反映出江蘇省農戶進行秸稈還田生態補償的WTA水平。
3.2 實證分析結果與解釋
本文運用Stata15軟件對前文構建的Cox比例風險模型進行求解,結果見表 5。模型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模型整體回歸結果顯著。年齡、受教育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人口數、人均耕地面積、農戶認為秸稈還田有利于保護環境、露天焚燒秸稈會污染環境、秸稈還田有利于增加農作物產量、秸稈還田成本較高和政府積極宣傳秸稈還田是影響農戶秸稈還他受償意愿水平的關鍵因素。

表5 Cox比例風險模型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上顯著。
具體分析為:①農戶個人與家庭特征。要求補償金額較高的農戶多集中于受教育水平較低、可支配收入較高、家庭人口數較多、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家庭,且年齡越大所要求的補償金額越多。如農戶的受教育水平為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時,比受教育水平為小學的農戶相對風險度分別提高了21.56%、43.47%、24.85%,即WTA水平分別降低了21.56%、43.47%、24.85%。隨著國家農業政策傾斜和農村收入結構改善,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純農業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因此政府需要給予更高補償以激勵其參與秸稈還田。年齡較大的農戶對傳統農業生產模式產生了“路徑依賴”,不愿意輕易地改變生產模式[30]。此外,因化肥過度使用等不合理的耕作方式所導致的土地退化也無形減少了人均耕地面積,阻礙了規模經濟發展,增加了秸稈還田成本。②農戶對秸稈還田處理的認知。本文選取了4個變量來反映農戶對秸稈還田處理的認知,分別為秸稈還田有利于保護環境、露天焚燒秸稈會污染環境、秸稈還田有利于增加農作物產量、秸稈還田成本較高。其中,農戶對這4項認知感到“非常認同”的均在1%或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都是影響農戶WTA水平的重要因素。大部分農戶能認識到秸稈還田給生態環境所帶來的益處,且這種認知顯著降低了他們的WTA水平。但是作為“理性人”,農戶為了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仍愿意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避免高額的還田成本,要求他們參與秸稈還田需要給予更多的補償。這反映出當前農戶對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認知嚴重不足。根據調查結果,僅有18%的農戶接受過高等教育,大多數農戶對生態環境的認知仍停留在表面,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破壞對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消極影響。③秸稈綜合利用的政策效應。本文選擇政府是否積極宣傳秸稈還田和實施秸稈禁燒政策來分析政策效應對農戶WTA水平的影響,發現這兩項政策均提高了農戶的WTA水平,但回歸系數僅為-0.2683和-0.1680,且政府禁止露天焚燒秸稈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對秸稈還田的宣傳仍流于形式,制訂的處罰措施難以得到有效執行,使農戶對政府管理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難以得到農戶的積極響應。④外部環境因素。當地有秸稈原料企業和秸稈還田設備提高了農戶的WTA水平,但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是,江蘇省經濟水平較發達,盡管可將秸稈出售處理給企業獲得附加收入,但農戶對于更高補償的訴求較弱。此外,受到樣本地區土地經營規模化程度制約、大型機械器具使用限制、還田技術規范和工藝標準的缺乏,農戶秸稈還田意愿不足,因此當地是否有秸稈原料處理企業和秸稈還田設備對農戶WTA水平的影響不大。
4 政策建議
秸稈還田是實現我國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提高農作物產量的同時也為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做出了貢獻,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政府理應制定合理的激勵機制來鼓勵農戶參與秸稈還田并給予一定的補償。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3點激勵機制:①制度激勵。制度激勵是一種長期穩定的根本性激勵機制,政府必須嚴格執行各項法律法規,提高政府人員的行政效率。一方面,政府應明確制定獎勵措施,或定期進行模范評選,對積極參與秸稈還田的農戶給予一定獎勵以形成示范效應。另一方面,加強政府內部人員管理,優化人員結構,保證各項獎勵、處罰措施能及時有效地執行到位,以加強農戶對政府的信任度,積極響應政府的各項政策。②外部激勵。在制度激勵充分滿足的條件下,可成立秸稈還田生態補償基金以進一步形成外部激勵。生態補償基金是我國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以政府為主導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可以在提高生態補償基金運行效率的同時,保證生態補償機制的可持續發展[39]。該基金既可用于當地還田農業裝備的研發與推廣,也可用于補貼、獎勵積極參與秸稈還田的農戶,在降低還田成本的同時調動廣大農戶的積極性。③自我激勵。使農戶形成參與秸稈還田的自我激勵是政府政策的最終任務。通過定期組織農戶學習有關秸稈還田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相關知識,宣傳秸稈還田對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強調現代化農業生產模式較傳統農業生產模式的優勢所在,可以提升農戶對生態環境的認知。根據Feo的研究,環境知識是個人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的基礎[40]。在意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后,農戶將進行自我激勵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從而逐漸轉變生產模式,積極參與秸稈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