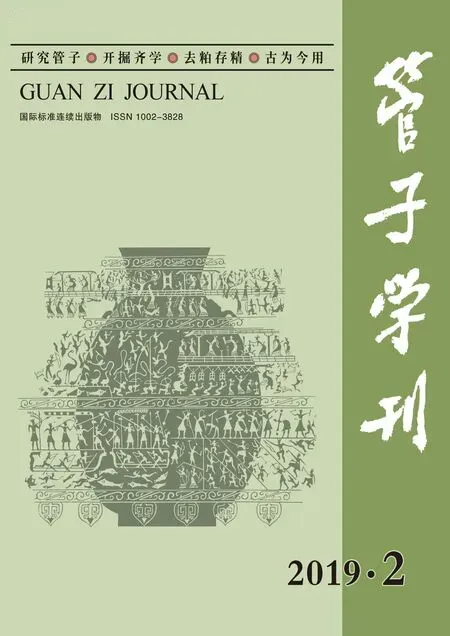鄭氾地考
尉侯凱
(武漢大學 簡帛研究中心,武漢 430072)
春秋時期的鄭國有兩個氾地,一個在今河南中牟,是為東氾:
《左傳》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杜預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1]3974
《左傳》襄公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黡、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杜預注:“眾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陸德明釋文:“氾,音凡。”[1]4216
《左傳》昭公五年:“楚子以屈伸為貳于楚,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杜預注:“氾、菟氏,皆鄭地。”陸德明釋文:“氾,徐注徐指東晉學者徐廣,下同。②按:杜預雖然沒有注明這個氾地的方位,但它既然與菟氏并舉,表明兩地應該相距不遠,菟氏在今河南尉氏,那么這個氾地應當就是位于河南中牟的東氾扶嚴反。”[1]4432②
另一個位于河南襄城,是為南氾: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冬,王使來告難,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杜預注:“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陸德明釋文:“氾,音凡。后皆同。”孔穎達正義:“南氾是襄城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于楚,西近于周,故王處于氾。及楚伐鄭,師于氾,皆以為南氾。”[1] 3946—3947
《左傳》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杜預注:“氾,鄭地,在襄城縣南。”陸德明釋文:“氾,音凡。”[1]4132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御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杜預注:“于氾城下涉汝水南歸。”陸德明釋文:“氾,音凡。徐扶嚴反。”孔穎達正義:“《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是知于氾城下涉汝水而南歸也。”[1]4325
《漢書·匈奴傳》:“后二十余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蘇林曰:“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顏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2]3746
需要說明的是,《左傳》并沒有對兩個氾地貫以方位,而是統稱為氾,但由于它們同屬于鄭國,為了有效地進行區分,西晉杜預根據其地理位置的不同,將位于滎陽中牟的氾稱為東氾,位于襄城縣南的氾稱為南氾。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亦云:“(僖)二十四年氾,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氾,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有氾澤。”[3]789—790對于東氾、南氾之“氾”的讀音,歷代學者如漢末魏初蘇林、東晉徐廣、隋陸德明皆注音為“凡”,說明這個字應該從水、聲作“氾”,而非從水、巳聲作“汜”。
巧合的是,當時鄭國的成皋附近還存在一個汜地:
《左傳》成公四年:“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杜預注:“汜、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陸德明釋文:“氾,音凡,注同。或音祀。”孔穎達正義:“既為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汜水也。字書水旁巳為汜,水旁為氾,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汜’,今汜水上源為汜谷。”[1]4128
從字形上看,“氾”“汜”二字極為接近,因此經常發生訛混現象,導致后人對東氾、南氾、汜三地的認識頗為混亂。例如,鄭國成皋附近的“汜”,陸德明卻錯誤地認為應當作“氾”,“音凡”,按《續漢書·郡國志》,河南郡成皋縣有汜水[4]3390,汜地當因汜水而得名,因此成皋附近的地名應為“汜”而非“氾”。上引孔穎達正義對此作了詳細考辨,準確可信。
又《漢書·高帝紀》云:
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于成皋,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顏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2]43—44
按:漢高祖與曹咎相持于成皋,曹咎渡兵汜水與之交戰,這個汜水應該就在成皋附近。眾所周知,方言由于口耳相傳,會比較忠實地保留較早的讀音,當地人既然“呼之音祀”,說明成皋附近的這條水自古以來就叫“汜”,而不應該是顏師古所說的“舊讀音凡”。因此,曹魏學者如淳為此水名注作“音祀”,無疑是正確的。不過,他把《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鄙在鄭地氾”之“氾”與《漢書·高帝紀》“兵渡汜水”之“汜”混作一談,皆注音為“祀”,卻不一定可靠[注]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汜水”時也引用《左傳》“周襄王處鄭地汜”,其誤與如淳同,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第3390頁。。
宋代學者王觀國對這一問題也有關注,他認為:
《后漢·郡國志》河南郡有汜水,杜預或言中牟南,或言成皋東,其實即汜水一水也,音祀是也,音凡非也,音凡者自是一水,不在鄭地。陸徳明不能分別,乃于《春秋》成公四年“取汜、祭”既音凡,又音祀,存兩音者,非也。《前漢·高祖紀》曰:“漢果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顏師古注曰:“此水舊音凡,今呼音祀。”案此汜水,乃河南汜水音祀者也。顏師古見陸徳明釋《春秋左傳》皆音氾作凡,師古亦不能分別,乃曰此水舊音凡,今呼祀,亦存兩音,則非也。夫字音期于當而已,豈有舊音某而今音某者耶?惟其存兩音而不能決,故后學莫之適從也。[5]280—281
王氏指出,陸徳明注《左傳》成公四年“取汜、祭”之“汜”時既音凡、又音祀,顏師古注《漢書·高祖紀》“漢果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之“汜”時謂舊音凡、今呼祀,皆中無定見,模棱兩可,給后世學者帶來了很大困惑。進而認為,《左傳》成公四年“取汜、祭”之“汜”應在河南成皋,音為“祀”,這是可信的。但他將河南中牟南的氾澤與成皋東的汜水混為一談,皆音為“祀”,又認為“音凡”的“氾”不在鄭國,恐怕尚可商榷,河南成皋東確實有一條汜水,但中牟南的氾澤與流經成皋的汜水沒有什么關系,兩地的用字、讀音皆不相同。河南中牟縣南的氾稱為東氾,音凡,河南襄城縣南的氾稱為南氾,也音凡,東氾、南氾都屬于春秋時期的鄭國,怎么能說“音凡”的“氾”不在鄭國呢?可見王氏的觀點是有很多問題的。清代學者臧庸曾經撰寫了“汜氾兩義”“汜水”“氾城”“氾澤”“氾水之陽”等多條考證對王說加以反駁,其中“汜氾兩義”條云:
《左傳》、《史》、《漢》之汜水音祀,在成皋,如淳、劉昭以襄城之南氾當之,張晏又以濟陰之氾水當之,陸德明亦出祀、凡兩音,深滋學者之惑矣。宋王觀國撰《學林》,知汜水當音祀,音凡非,而不知南氾本音凡,王氏又以中牟之氾澤、共縣之汎城相混,則理絲而益之亂矣。余弟和貴知其說之有誤,家書來楚館,請為考定,因作《汜水考一》《氾城考二》《氾澤考三》《汎城考四》《氾水之陽考五》,《左氏傳》“汜”“祭”連文,而鄭有兩祭,故《祭城考第六》,作竟,以詒和貴,審此,而地理之學易易矣。[6]8892
“汜水”“氾城”“氾澤”“氾水之陽”等條征引繁富,論斷準確,但頗嫌瑣碎,不便全部加以引用,概括來說,臧氏認為《左傳》成公四年“取汜、祭”之“汜”音祀,即河南成皋之汜水。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襄公二十六年“涉于氾而歸”之“氾”音凡,即河南襄城之氾城,是為南氾。《左傳》僖公三十年“秦軍氾南”、襄公九年“師于氾”之“氾”亦音凡,即河南中牟之氾城,是為東氾。而《史記·高祖本紀》“還至定陶,即皇帝位氾水之陽”之“氾”則音敷劍反,在山東定陶,與鄭地的南氾、東氾無涉[6]8892—8893。不難發現,臧氏對東氾、南氾、汜的讀音、位置辨析地至為明晰,結論穩妥可信,連以好譏彈著稱的李慈銘,也不由地對這幾條考證大加贊賞:“臧氏之學,頗嫌饾饤,繁而寡要,此數條折衷諸說,剖斷詳明,極有功于經學、史學。”[7]203
綜上可知,春秋時期的鄭國有東氾、南氾兩個城邑,分別位于今天的河南中牟、襄城,此外還有一個汜地,位于今河南滎陽(成皋)。汜地的得名來源于汜水,汜水即從河水分出去又匯入的小水。《說文》:“汜,水別復入也。從水,聲。《詩》曰:‘江有汜。’”[8]558《爾雅·釋水》:“決復入為汜。”郭璞注:“水出去復還。”[9]5696比較而言,兩個氾地的得名原因就顯得比較模糊,臧庸曾作出推斷說:
案杜元凱以鄭有南氾、東氾。劉元卿云:“尋討傳文,未見。”考杜注東氾及圃田皆云在滎陽中牟縣,兩《漢志》中牟皆有圃田澤,而無氾澤,疑氾澤即圃田澤,甫、一聲之轉耳。《毛詩·車攻》傳云:“圃,大也。”氾亦廣博泛大之意。傳曰原圃,原亦大也。識此以俟考。[6]8892
臧氏認為東氾的得名可能與同在中牟的圃田有關,觀點可謂新穎,當然也有一定的道理,首先,氾澤和圃田澤都位于河南中牟,地理位置比較吻合。其次,圃訓為大,而氾亦有泛大之意,二字含義接近。第三,上古音圃屬幫母魚部,氾屬滂母談部,幫、滂為旁紐,魚、談為通轉,從音理上來說,“氾”“圃”通假是沒有問題的。不過,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發現二字可以相通的直接證據,因此,東氾的得名與圃田是否有關,還有賴于更多新材料的發現來驗證。上文已經指出,東氾、南氾是西晉學者杜預根據它們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加以命名的,兩地在《左傳》中均被統稱為“氾”,雖然它們同屬于鄭國,但當時的人們并沒有對其進行嚴格的區分,說明兩地的得名、含義和用字在春秋時期似乎存在著不同。按照臧氏的解釋,東氾之氾即圃田之圃的音轉,那么位于襄城的南氾就顯然不會與中牟的圃田有什么關系,即南氾的得名應該另有原因,南氾與東氾在后世被統稱為“氾”,只是用字恰好相同而已,它們的得名、原因甚至早期的用字應該是有所區別的。
最近有位臺灣學者金宇祥先生,對鄭國的兩個氾地有了不同見解,他認為東氾、南氾之“氾”皆系“汜”字之訛,實際上又基本回到了宋代王觀國說的原點,其根據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清華簡《系年》簡85:“楚共王立七年,令尹子重伐鄭,為之師。”簡130:“郎莊平君率師侵鄭,鄭皇子、子馬、子池、子封子率師以交楚人,楚人涉,將與之戰,鄭師逃入于蔑。”[10]174-175金宇祥先生認為“”其實即是“黍”字,《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與簡文“為之師”對應,那么《左傳》“師于氾”之“氾”當為“汜”字的訛寫,此汜即襄城縣的南汜,因為“汜”屬邪紐之部,“黍”屬審紐魚部,聲類相近,韻部魚、之旁轉,因此二字可以相通。
第二,《漢書·高帝紀》:“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如淳既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則周襄王所居之鄭地當作“汜”[11]91—105。
按:“汜”“黍”通假,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但二字聲紐相差較遠,且文獻中沒有直接相通的例證。將“”釋為“黍”,也不見得一定準確,最近黃德寬先生據安徽大學所藏戰國竹簡《詩·柏舟》的“髧”寫作“”,而將“”、“”(二形為一字之繁簡)釋為“湛”,認為是“沈”的古字,義為貍沈。清華簡《系年》中的“”,應當釋為“湛”,“氾”與“湛”地理位置接近,《左傳》的“師于氾”,與《系年》的“為湛之師”,當是同一事件由于史官記載的不同而造成的差異。抑或“湛”可以讀為“氾”[12]。如果此說成立,那么金宇祥先生將“”釋為“黍”并將其與“汜”在聲音上發生聯系的做法就失去了文字、音韻學上的基礎。相反,如果“湛”字可以直接讀為“氾”(“湛”為侵部,“氾”屬談部,侵、談為旁轉),則為河南襄城之“氾”當為從水、聲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語音證據。近期董珊先生也對古文字材料中的“”“”進行了梳理和討論,雖然他認為此字象禾生水中,應是水稻之“稻”的初文,但他也將清華簡《系年》“為之師”“楚人涉”之“(稻)”讀為“氾”,認為此“氾”即周襄王曾居之南氾[13]112。至于如淳注所謂“汜,音祀”,臧庸認為“祀”當作“凡”,“祀”是后人據顏師古注誤改所致[6]8892,即使如淳注本來即作“汜,音祀”,也不能作為《左傳》“鄙在鄭地氾”之“氾”當作“汜”的絕對證據,上引漢末學者蘇林在為《漢書·匈奴傳》“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之“氾”注音時謂“氾,音凡”,蘇林的生活年代早于如淳[注]張儐生先生推斷蘇林生在漢末桓靈之間,殆公元155至245年間人。見張儐生:《漢書著述目錄考》,《女師大學術季刊》,1931年,第2卷第2期。如淳的生活年代約在公元221—265年,見(英)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384頁。,他的讀音顯然更應該值得重視,因此,僅憑如淳所謂“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是不足以說明南氾之“氾”當作“汜”的。總之,金玉祥先生論證春秋時期鄭國南氾、東氾之“氾”皆當作“汜”的意見是不能成立的。
附帶談談新出土的楚簡中可能與鄭地南氾有關的幾個地名。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簡4—6云(釋文采取寬式):
昔吾先君桓公,后出自周,以車七乘,徒三十人,敷[注]敷,簡文作“故”,整理者讀為“鼓”,網友“無痕”讀為“敷”,“敷其腹心”,即古書中的“布其腹心”,見《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初讀》第6樓發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6&extra=page%3D2,2016年4月17日。其腹心,奮其股肱,以[注],整理者疑即“協”,徐在國先生改釋為“”,見徐在國:《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札記一則》,簡帛網,2016年4月17日。于偶,胄鼙[注]鼙,整理者釋為“”,讀為“擐”,網友“bulang”釋讀為“鼙”,見《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初讀》第7樓發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6&extra=page%3D2,2016年4月17日。甲,刈[注]刈,整理者釋為“”,讀為“擭”,徐再國先生釋為“刈”,見徐在國:《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札記一則》,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19,2016年4月17日。戈盾以造勛。戰于魚羅,吾[乃]獲、。覆車襲,克鄶廟食[注]廟食,整理者釋為“”字重文,讀為“迢迢”,網友“ee”釋為“廟食”合文,見《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初讀》第33樓發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6&extra=page%3D2&page=4,2016年4月23日。,汝[注]汝,簡文作“女”,整理者讀為“如”,今按:似應讀為“汝”,太伯稱鄭文公為“汝”,參看拙作:《先秦時期臣下稱君為“汝”現象試論》,未刊稿。容社之處,亦吾先君之力也。
魚羅,整理者讀為“魚麗”:“‘于’與‘以’同義,見《詞詮》(第四三一頁)。‘魚麗’為陣名,《左傳》桓公五年(鄭莊公三十七年):‘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或說為地名。”[14]121
從上下文意來看,“魚羅”當以解釋為地名比較合適。筆者曾考慮將“魚羅”讀為“魚陵”(“羅”、“陵”雙聲)[15]127—128,魚陵在今河南省襄城縣西南,鄭國因“戰于魚羅(陵)”而得到“”“”,那么“”“”二地距離“魚陵”應該不會太遠。薛培武先生主張“”讀為“氾”,認為即鄭地南氾注見王寧《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函”、“訾”別解》文后跟帖,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801,2016年5月20日。,吳良寶先生讀“”為“訾”,認為應是《左傳》成公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之“訾”,江永《春秋地理考實》云:“奔許而自訾求入,則訾當在鄭南。”或以為在今河南省新鄭縣與許昌市之間,或以為在今河南省新鄭縣南[16]182。而“氾”“魚陵”相隔很近,位于新鄭縣以南的“訾”雖然暫時無法判斷其確切位置,但離“魚陵”也不算太遠,這應該不會只是巧合。然而,吳良寶先生認為河南襄城的氾不符合典籍記載的鄭國東遷之初的范圍,即在黃河以南的“濟、洛、河、潁之間”,因此不同意將“”讀為“氾”[16]180。按典籍對鄭國東遷之初范圍的記載應該大體可信,但也不能保證一定沒有疏漏。簋銘文云“率有司、師氏奔追戎于棫林,搏戎害夫”,其中的“棫林”一地,裘錫圭先生認為在今河南葉縣附近,“害夫(胡)”應在今河南郾城。根據古本《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的記載,說明鄭國最初就是在東方而非宗周畿內立國的。《世本》謂鄭桓公居棫林,這個棫林可能就位于葉縣附近,因為《韓非子·說難》記載桓公之子武公襲胡取之,而胡就在棫林旁邊[17]388—391。若此說不誤,葉縣、郾城也不在“濟、洛、河、潁之間”,而且其位置比南氾、魚陵更加偏南,這該怎么解釋呢?眾所周知,典籍的形成通常比較滯后,導致早期的歷史信息往往得不到完全和真實的反映,因此,對出土文獻的解讀,除了依托有關典籍的記載,還應結合其他的有關材料,從而做出一些合乎情理的推測。魯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因王子帶之亂,避居鄭地南氾,說明從洛陽到南氾似乎存在一條便捷通道,否則很難解釋為什么周襄王不就近選擇鄭國的其他城邑,而偏偏去了更加遙遠的南氾。鄭桓公經營東方,可能也是從成周洛陽出發,到達今河南葉縣附近的棫林,并以之為中心,通過魚陵之戰和武公滅胡,獲得南氾(今河南襄城)、訾(今河南新鄭南)和胡(今河南郾城)等地,進而初步奠定了鄭國的早期疆域。總之,將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簡6的“戰于魚羅,吾[乃]獲、”之“魚羅”讀為“魚陵”,“”讀為“氾”,“”讀為“訾”,是可以將簡文所反映的歷史、地理信息基本解釋清楚的,而簡文的有關表述也彌補了典籍的重要失載,為了解春秋早期鄭國經營東方的情況提供了新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