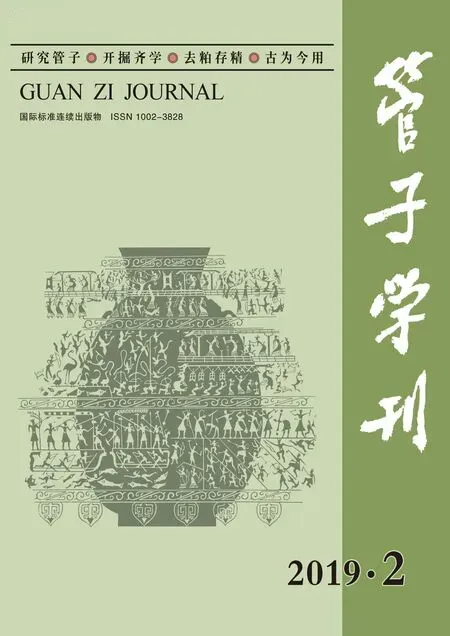試論《晏子春秋》思想體系的構造
王玉喜
(青島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青島 266520)
晏子作為齊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思想主要集中在《晏子春秋》一書當中。《晏子春秋》雖非晏子手著,但該書的思想與晏子的民本、禮治、節儉、輕天等主要觀念相合。也就是說,晏子的思想與《晏子春秋》一書難以分割,學者基本上將《晏子春秋》視為研究晏子思想最主要的資料來源之一。目前,學界關于《晏子春秋》思想內容研究的總體趨勢是,以微觀的視角,從政治、經濟、外交、哲學、軍事、倫理及法律等諸多方面進行細致、深入的研究。用思想史分類研究的范式探究歷史人物的思想,能夠使學術問題做細做精,缺陷是易失于人物思想的整體把握,往往會導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性結果。從宏觀上專門研究《晏子春秋》理論體系構造的成果尚不多見注專門將《晏子春秋》的思想作為一種理論體系進行研究的論著并不多見,迄今為止,只有邵先鋒《晏子思想研究》較為系統地梳理了《晏子春秋》中晏子的思想體系。然而,該書雖系統梳理了晏子的各類思想,但卻未深入探討晏子思想或者《晏子春秋》所反映的思想內容各條塊之間的關聯性。參見邵先鋒:《晏子思想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39-148頁,其原因可能大致有二:其一,部分學者受《晏子春秋》體裁性質爭議的影響,以為傳記類著作或小說集所反映的思想真實性令人懷疑;其二,另一部分學者受《晏子春秋》內容重復雜沓、附會迭見的局限,主觀上以為《晏子春秋》的思想理論不具有系統性構造,即缺乏內在的邏輯關系。仔細研讀《晏子春秋》,我們就會發現,該書的體裁性質雖有爭議,編纂也不似儒、墨、道、法諸家的經典嚴謹、整齊,但其思想理論自成體系,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已經具備一家之言的基本條件。弄清這一問題,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晏子春秋》在春秋戰國齊學及齊文化的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一、《晏子春秋》一書的性質
關于《晏子春秋》一書的性質,學界大多圍繞著體裁和學派歸屬而爭論不休,而很少從其反映的思想內容上來看待其性質。個別學者認為,“該書的主體不在‘論思想’,而是在‘記言行軼事’”,因此斷定《晏子春秋》一書的性質“應該是一部記述重要人物言行軼事的記敘類著作”[1]。這種觀點的得出,是典型的現代學科思維導致的。誠然,《晏子春秋》一書大部分內容是以晏子與他人對話為中心形成的故事,其中記“言”的特征最明顯,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晏子春秋》一書并非簡單地以記“言”而講故事。該書語言和故事的背后,蘊含著系統、豐富的政治思想。從先秦諸子學說的緣起上看,《晏子春秋》的思想理論屬于典型的治國學說。
呂思勉先生曾指出,“先秦學術之原,古有二說:一為《漢書·藝文志》,謂其皆王官之一守,一為《淮南子·要略》,謂其起于救時之弊”,二說皆有道理,前者是因,后者是緣,“先秦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2]437。此言一針見血地抓住了先秦學術性質的關鍵。先秦學術源自王官之學,又起于救時之弊。王官之學是施政的經驗總結,救時之弊則是對現實政治的補救學說。先秦諸子所謂“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就是各家皆欲以自己的學說或思想來改變現實政治局面。從這個角度理解,先秦諸家學說應該都屬于治國思想。作為一種政治思想,《晏子春秋》所反映的治國思想大多“起于救時之弊”。目前,我們基本清楚的是:一方面,與《左傳》相印證,《晏子春秋》記述的晏子本人的言行和事跡,其思想的形成與晏子本人生活的春秋后期的時代背景聯系密切;另一方面,《晏子春秋》大約成書于戰國之際,其著者并非晏子,應該是與戰國田齊統治時期的稷下學派有密切關系[3],該書不可避免地又與撰寫者所生活的戰國時期的時代背景不可分割。
《淮南子·要略》在追述各家學術之源時,將同屬于齊學系統的“太公之謀”“管子之書”“晏子之諫”分別與儒、墨、縱橫、法諸家思想并列,而談及談及“晏子之諫”時說:“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廳下,郊雉皆呴,一朝而用三千鐘贛,梁丘據、子家噲道于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4]710-711這里的“晏子之諫”實際上就是指《晏子春秋》。觀《左傳》《國語》等信史可知,晏子生活的春秋后期,姜齊的統治者聚斂無度,生活腐化,“民參其力,二入于公”[注]以下凡引用《左傳》均參照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百姓轉而支持施惠于民的卿大夫田氏。對于公室的淪落、卿大夫的崛起以及百姓生活的悲慘,“晏嬰懷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感與危機感”[5]115,而晏子的這種憂患感和危機感所流露出來的信息,本身已經蘊含了“救時之弊”的治國思想和主張。如與《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記載基本相同的《晏子春秋·外篇上·第十五》,就提出通過恢復禮制以挽救姜齊政權不被田氏取代的主張,“救時之弊”的色彩已然相當濃厚。
我們再從《晏子春秋》產生的時代和作者上看,該書所反映的思想只能是一部應時而生、具有很強的“經世致用”色彩的思想著作。學界基本贊同,齊國的稷下學派興盛于田齊威宣時期。戰國時期的齊國以富庶著稱,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國力的增強,齊威王、齊宣王時期,齊國經過改革,國力大增,威行天下。正如學者所言,田氏代齊之后,更加注重延攬士人,“一方面是樹立田齊統治者尊賢重士的形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圖利用士人的喉舌,鼓吹其取代姜齊的合法性,并為其爭雄于諸侯、統一天下制造輿論”[6]98。《晏子春秋》一書不僅未避諱齊景公時期田氏代齊的大勢,更是借晏子與景公的對話反襯姜齊政權壓榨百姓、橫征暴斂的落后腐朽性,并高倡“以民為本”的時代洪音。為了實現“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注]以下凡引用《孟子》均參照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的稱霸天下的政治目標,齊宣王繼續鼓勵稷下學宮的學術事業,給予稷下先生以優厚的政治和經濟待遇。《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注]以下凡引用《史記》均參照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不治而議論”是謂稷下先生雖不職掌具體行政事務,卻專門對治國理政進行自由的討論。《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稷下先生的事跡時交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稷下先生著書的內容主要是“言治亂之事”,其目的是“以干世主”。這與《淮南子·要略》所謂的“先秦諸子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具有共同的旨趣。《晏子春秋》為稷下先生所撰,它的思想內容也主要是以“言治亂之事”為主。“言治亂之事”就屬于典型的治國學說。
綜合上述,《晏子春秋》一書所反映的思想性質只能是治國思想,而非其它的東西。一般而言,先秦諸子的學說要想“以干世主”,其思想和理論必定有一套系統的理論闡釋。很難想象,雜亂無章的思想片段能夠說服“世主”。從表面上看,《晏子春秋》貌似僅是一本記錄晏子的言論和事跡的著作,故事性色彩較為濃厚,其治國思想似乎并沒有儒、墨、道、法諸家的豐富而系統。但我們仔細閱讀該書就會發現,《晏子春秋》在晏子言行事跡的背后也蘊含了十分系統的治國思想理論。
二、《晏子春秋》治國思想的取法對象、哲學方法論與政治目標
《晏子春秋》治國理論以“先王”為取法對象,以“和”的思想為哲學方法論,以“善政”為政治目標。
《晏子春秋》治國思想的取法對象是“古之王”(《內篇諫上》,以下凡引《晏子春秋》者,只注篇名)[注]以下凡引用《晏子春秋》均參照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1962年。、“圣王”(《內篇諫下》)、“古之盛君”(《內篇問上》)及“明王”(《內篇問上》)。以上取法對象中,有時代坐標的是《內篇諫下》中的“圣王”及“古之盛君”。《內篇諫下》中的“圣王”生活的時代大約在夏、商、西周三代及上古時期。據《內篇諫上》晏子所言,商代的湯、太甲、武丁、祖乙乃“天下之盛君”,與“古之盛君”相仿,因此,大致可斷定,《晏子春秋》所謂的“圣王”“盛君”等,當指三代及上古時期的“圣王”。《晏子春秋》治國思想取法的對象還包括齊國的“賢君”,據《內篇諫上》可知,晏子稱“太公”“桓公”為“賢者”,《內篇諫上》又稱“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是以太公、丁公及桓公是“賢君”。廣義上,齊國的“賢君”也屬于“先王”。概言之,《晏子春秋》治國理論的指導思想是“法先王”。“法先王”的內容包括學習“先王”的德行(《內篇諫上》《內篇問上》)、節儉(《內篇諫下》)、尚賢(《內篇問上》)、治國(《內篇問上》)、教民(《內篇問上》)等諸多方面。“先王”是《晏子春秋》治國理論的取法對象,同時也是其思想的道統來源。“法先王”也為《晏子春秋》治國思想的實踐提供了合法性的源頭。
《晏子春秋》治國思想以“和”為其哲學的方法論。《晏子春秋》“和”的哲學思想仍是一種政治實踐論,它并非是一種單純的“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7]。《晏子春秋》“和”的思想主要集中《外篇上》,這就是著名的“和同之論”。晏子與景公探討君臣關系時,晏子以宰夫烹飪羹肴為例,指出君臣關系達到“和”的最佳狀態是“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而臣一味的阿諛奉承君的意見和看法,這就是“同”。“和”與“同”是相互對立的矛盾,而“和”本身卻是對立統一的矛盾。很顯然,晏子這里所謂“和同之論”的對象是君臣關系,它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實用理性,都能直接運用于現實的政治生活當中。
《晏子春秋》中所謂的“和”實為重視和追求事物的均衡、和諧和穩定的狀態。如“和同之論”中,《晏子春秋》特別強調君臣意見的互補性,這種君臣之間“可”與“否”的互補結果就是“政平而不干”,亦即一種均衡而穩定的和諧。《內篇問上》中晏子回答景公“謀必得,事必成”之“術”時說:“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具體來講,“謀于義”與“因于民”就是一種“和”的狀態,這里就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因此,晏子說:“其謀也,左右無所系,上下無所縻,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謀于義”的主旨是上下左右無所偏廢的一種均衡狀態;“因于民”更是將“事之大小”“利之輕重”進行平衡,這就是典型的“和”的哲學理念。《內篇問上》晏子回答景公“圣人之得意何如”時,說:“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圣人之得意也。”這里的“世治政平”與“和同之論”中的“政平而不干”都是指社會秩序的和諧狀態。“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中的“調”與“和”就是一種追求穩定、和諧與均衡的政治實踐,而“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則是在人的“調和”的政治實踐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和諧的宇宙秩序。二者相合,即“天人感應”,本身就是一種“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除了指導思想和哲學方法論以外,《晏子春秋》治國思想還有最終的政治目標。縱觀《晏子春秋》一書,書中關于晏子的一切言行軼事都圍繞著一個目標——“善政”,即治理好國家。《內篇問上》中開篇齊景公很自負地告訴晏子:“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以“官未具”塞之,并直接告訴景公“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的原因是“未有能士敢以聞”。這說明,晏子認同“善治齊國之政”這個政治目標。又,《內篇問下》景公問晏子:“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答曰:“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從字義上看,這里的“安”是指國家安定,但仔細揣摩文意,我們不難發現“安”即是內政、外交皆達到一種“和”的局面,亦即“善政”。可以說,“善政”在《晏子春秋》治國思想體系中處在政治目標的位置。
三、《晏子春秋》治國思想的邏輯構造
“以民為本”是《晏子春秋》治國思想的核心,同時也是連接該書其他治國思想的脈絡。實際上,部分學者已經注意到了“以民為本”在《晏子春秋》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馮瀟[8]312、邵先鋒[9]447、宣兆琦及張曉連[10]457-468都指出“以民為本”在《晏子春秋》的核心地位,但卻皆未繼續深入探討“以民為本”與《晏子春秋》的其它治國思想之間的關聯性。學界之所以未曾將《晏子春秋》的治國思想進行有體系有邏輯的闡發,根本原因在于將“治國”這一概念作了狹義的理解。實際上,“治國”有廣、狹兩種定義。狹義的“治國”僅指治理本國內部事務的措施和政策;廣義的“治國”則泛指一切以達到“善政”為目的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外交諸多方面的措施和政策。自古至今,“治國”向來就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先秦諸子的論著所反映的思想大都屬于廣義的“治國”范疇。從內容上看,《晏子春秋》的治國思想分忠君愛國、尚賢遠饞、重禮權宜、節儉廉讓、輕天重民、以民為本、禮交諸侯等七個方面,其治國思想的核心是“以民為本”,忠君愛國、尚賢遠饞、重禮權宜、節儉廉讓、輕天重民、禮交諸侯等六個方面的思想都是以“以民為本”作為理論基礎的。
《晏子春秋》的“忠君”思想非后世所理解的那種大臣對君主單向的絕對服從和效忠,“國”(社稷)也與近代以來的民族主權政治實體不盡相同。《晏子春秋》的“忠君”和“愛國”思想緊密相連,二者皆以愛民為基礎。當崔杼弒齊莊公之時,晏子犯難而來,撫君尸而哭,卻并追隨國君而死,當其從者問之,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內篇雜上》)及崔杼、慶封以直兵指胸、白刃加頸威脅國人與盟時,晏子嘆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晏子將社稷置于君主之上,君主只有為社稷而死,為社稷而亡,臣才有義務或為其死,或為其亡。這里的社稷不是現代意義的民族主權國家實體,但社稷卻是萬民的共同體。君主只有為這個共同體服務,即愛民、恤民,臣子才有盡忠的責任和義務。概言之,《晏子春秋》的“忠君”思想是以“愛國”為前提,而“愛國”實為愛民。“以民為本”是《晏子春秋》“忠君愛國”思想的根基。
國家治理,用人是關鍵。《晏子春秋》在任人方面的主張“尚賢遠讒”。“尚賢”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一大特點。《晏子春秋》在講統治者“尚賢”的同時,也極為重視“遠饞”。國家安危系于任人,任人之關鍵在于分辨善惡。《內篇問上》載景公問晏子為政何患,晏子答曰:“患善惡不分。”景公問:“何以察之?”晏子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聽聞此事,說:“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賢人當朝,讒佞無入之孔,國家就能得到治理。“尚賢遠讒”,實為讓“賢人”當政,成立“賢人政府”。“賢人”上佐君主理政,下代君主治民。君主不親治民,官僚在君民之間起了橋梁作用。《晏子春秋》認為,君主若要內安百姓,“賢人”愛民是關鍵。《內篇問下》中晏子講齊桓公之所以能致霸業,就是因為“先君(即齊桓公)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桓公正是任用賢能,才使得民懷其政,諸侯畏其威。試問,賢能之士若不愛民,民何以懷桓公之政?《內篇問下》中晏子向景公解釋“為臣之道”時說:“君用其言,民得其所利。”這里的“其”就是指“賢人”,君主若用賢人,百姓則受其利。賢人輔佐君主治理國家,實為造福百姓。《內篇問下》晏子在向叔向闡釋“正士之義”說:“正士處勢臨眾不阿私,……通則事上,使恤其下,……不以刻民尊于國。故用于上則民安。”“正士”就是真正、純粹的“賢人”,一旦“處勢”或“用于上”,就能做到愛民,民當然也就安居樂業了。這在《內篇問下》即已言明。晏子說:“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眾,不廉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臣子輔佐君主的道理,主要在于安國、導民和懷眾,此即“以民為本”。作為臣子,叔向和晏子探討“意孰為高、行孰為厚”的問題時,晏子直言:“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內篇問下》)概言之,“賢人”的賢與否,衡量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能夠做到“以民為本”。由此可見,《晏子春秋》的“尚賢遠饞”的政治主張,其理論基礎就是“以民為本”。
《晏子春秋》相當重視禮的作用,并將禮樂的得失上升到國家興亡的高度。所以,《內篇諫上》說:“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因此,《外篇上》又說:“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立。”是以《晏子春秋》將“禮制看成與天地同時生成的事物”,且“明顯帶有將禮制神圣化的傾向”[5]117。《外篇上》認為禮可厘清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姑婦五對社會基本的倫理關系,又可以作為一種化解卿大夫專權的政治制度(《外篇上》)。結合春秋“禮崩樂壞”的實際情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將三代以來形成的禮樂制度發揮到極致。較之三代的禮樂制度,儒家重構的禮樂制度將制度的“籠子”扎得更加緊密,禮樂的外在形式必然脫不了“繁”和“奢”的境地。《外篇上》以極其嚴厲的口吻批評儒家的繁禮奢樂,認為東周以來的“民行滋薄”“世德滋衰”的道德滑坡應由儒家負責。因此,《晏子春秋》主張,禮樂制度應該回到三代去。《外篇下》引三代圣王時期的禮樂制度時說:“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于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眾也,以為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晏子春秋》認為,制禮作樂的基本精神是“便事”“和民”。換句話說,禮樂制度的設計乃是以方便“人”和“事”作為根本的出發點。所以,《內篇雜上》載晏子使魯之時曾經告訴孔子,禮可以權時宜而變,基本法則就是“大者不逾閑,小者可出入也”。“閑”,王更生訓為“防”[11]249,即限制或約束,也可以稱之為大原則、大方向。在《晏子春秋》看來,與天地并立的禮只要不違背辨尊卑的大原則,細枝末葉是可以有所出入的。這實際上道出了一種革新禮制的方法論,變革禮制所遵循的原則:一是不違背辨尊卑的大方向;二是具體細節可根據“便事”與“和民”的精神進行改革。后者對禮制的革新也透射出節儉的精神。《晏子春秋》主張簡禮,實為簡化儀節,其目的本身就是為了“便事”“和民”,即不影響百姓生活、不浪費百姓的資財。“以民為本”的思想就在《晏子春秋》“重禮權宜”的主張中體現出來。
晏子以節儉聞名于世,《晏子春秋》中更不乏節儉的思想。《晏子春秋》許多篇章呈現出晏子不計較吃(《內篇雜下》)、穿(《外篇上》)及交通工具(《內篇雜下》)的簡樸作風,有些細節甚至提到晏子節儉到每餐若多一雙筷子就都吃不飽的地步(《內篇雜下》)。晏子出身貴族,又為景公倚重,累至卿位,祿至百萬,顯然家庭并不貧窮(《內篇雜下》)。家庭優渥的晏子將節儉下來的財富“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內篇雜下》)。晏子將家財皆施舍給三族、士人以及百姓,是以由富返貧。《晏子春秋》主張統治階層要首先要“節欲”(《內篇問下》),即節制嗜欲(《內篇問上五》)。節制嗜欲有兩途:于國家政治,統治者要“儉于藉斂”(《內篇問上》);于個人生活,統治階層要“自養儉”(《內篇問上》)。統治階層應“不私其利”(《內篇問下》),將節儉下來財富分給百姓,讓民眾富裕起來,即“施惠于民”。所以,《內篇問下》中景公問晏子“富民安眾難乎”,晏子答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內篇諫下》載晏子之言曰:“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于身,謂(惠)于民。”《晏子春秋》認為,統治階層的財富不能藏而不用。《內篇諫下》說:“夫藏財而不用,兇也,財茍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己也。”《晏子春秋》將統治者對待財富的態度和行動上升到國家存亡的高度。由此可見,《晏子春秋》的節儉思想重點不僅僅講個人的修養,更是一種政治思想。《晏子春秋》的節儉思想從內到外散發出“以民為本”的氣息。
《晏子春秋》的節儉思想又衍生出廉讓觀。《晏子春秋》認為服飾和居室等外在的物質僅僅是為了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不在享受。在滿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情況下,統治階層應克制自己的嗜欲(節欲)。晏子將統治階層“遂欲滿求”視為“非存之道”(《內篇諫下》)。這句話反過來說,統治階層的“存之道”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克制人性中的貪欲。克制人性的貪欲,節儉是在個人生活方面的自我克制,而廉讓則是針對于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系方面的克制。《內篇雜下》以慶氏的覆滅為例提出“足欲而亡”的警告,并指出統治者若欲長有其位,必須做到“幅利”的主張。所謂的“幅利”,《內篇雜下》說:“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幅利”的本質即是克制自己的貪欲。在位者只有能夠克制自己的貪欲,“利”才能源源不斷。懂得并利用“幅”的人才會有“福”。這就是晏子的廉讓觀的基本內核。
《晏子春秋》“輕天重民”思想本身就洋溢著“民本主義”的色彩。《晏子春秋》對“上帝”最高權威已經產生了懷疑,《內篇諫上》曰:“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對于人的禍難疾病,《晏子春秋》反對“慢行繁祭”“輕身恃巫”(《內篇諫上》)。對于自然災害,《晏子春秋》又能秉持樸素的唯物主義,拒絕將其視為神靈作祟的事件,明確表明“祠無益”(《內篇諫上》)。于天人之間,《晏子春秋》輕天重民。然《晏子春秋》的“輕天重民”思想基本上屬于“天人感應”的范疇。《內篇諫上》載景公睹彗星而欲禳除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景公病且久,將其歸罪于祝史,晏子認為“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上報鬼神,“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若祝史“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以欲厭私,……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若祝史再向鬼神言君主之好,“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外篇上》)。晏子認為,君主有德無德才是鬼神降福的關鍵。這里的“德”最重要標準的就是君主愛民。《內篇問上》中晏子直言:“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君王求福的重心在于“政必合乎民”。民的地位上升,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童書業先生指出,春秋時期“重民輕天”思想的本質乃是執政貴族中之較開明分子“以為迷信鬼神無用,唯有得國人支持,依仗‘國人’以生存,并發展自己之勢力”[12]196。此論可謂公允。
在外交方面,《晏子春秋》主張“禮交諸侯”。《內篇問上》曰:“不侵大國之地,不秏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禮交諸侯”即“德行教訓加于諸侯”(《內篇問上》),這本身就是一種和平主義主導的外交主張。作為一種外交方面的思想,《晏子春秋》“禮交諸侯”的思想似乎并不涉及“以民為本”的內容。但眾所周知,在國家治理體系當中,內政與外交從來就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一對矛盾。《晏子春秋》自始至終都將內政和外交視為達到“善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百姓“內安其政”是諸侯“外安其義”的前提條件(《內篇問下》),而“內安其政”的關鍵就是“以民為本”。是以《內篇問上》中晏子答莊公“威當世而服天下”采取何種具體行動時,將內政中的“能愛邦內之民”與“能服境外之不善”對應,并且把前者放在首位。此篇又云“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安“仁義”的對象其實就是民。《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仁”。《內篇諫上》中晏子謂景公以飛鳥而殺無知之人的行為為“無仁義”之舉。又,景公所愛馬死,景公怒而令人操刀殺圉人,晏子以“堯舜肢解人從何軀始”反諷景公并親數圉人之“罪”(實無罪),景公覺悟,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內篇諫上》) 以禽獸而濫殺無辜之人,景公尚且稱之為“不仁”。“愛民”“以民為本”在世界觀層面上就是“仁”。既然《晏子春秋》以為“服天下”的前提是“安仁義”,那么這里的“安仁義”其實就是“以民為本”。
通過以上論述可知,《晏子春秋》思想的核心是“以民為本”,“以民為本”將其他六個方面的治國思想串聯為一體。《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世界觀是“仁”。儒家的“仁”實為倫理法則,是指人與人之間之間的友愛、和諧的狀態。具體來看,《晏子春秋》中的“仁”就是指“利民”,較之儒家尤其是孔子的“仁”,更具有現實主義色彩和可操控性。《內篇諫下》曰:“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后子孫享之。”《內篇問上》又講“圣王其行”的關鍵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只有做到“利民”才能子孫常保有其國。《內篇諫下》載晏子在回答景公“后世孰將把齊國”時說:“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統治者與民并無血緣關系,若要得到百姓的支持,必須做到“利民”。《內篇問上》中晏子又說:“先與人利,而后辭其難,不亦寡乎!”統治者先施惠于民,等到其有難之時,百姓才不辭其難。儒家罕言“利”,《晏子春秋》卻在“民本”思想中高調突出“利”,并且認為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
綜而論之,《晏子春秋》的整個思想體系實為一種治國思想,它有自己的取法對象、哲學方法論和政治目標,其思想內容以“以民為本”為核心,形成了一套有較強邏輯架構的思想體系。《晏子春秋》的思想在齊文化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淮南子·要略》就將“晏子之諫”與齊學中的“太公之謀”“管子之書”與儒家、墨家、法家、縱橫家等諸家思想并列。從《晏子春秋》思想的系統性和邏輯性上看,《晏子春秋》在齊學系統乃至于先秦諸家學說系統中,應該是自成體系的獨立學說[注]如李學勤先生就曾在《齊文化縱論》一書的“序”中指出,應當視《晏子春秋》為齊文化的一方面代表,宣兆琦先生在其專著《齊文化發展史》中就曾提出“晏子學”一說。參見管子學刊編輯部:《齊文化縱論》“序”,華齡出版社,1993年,第2-3頁;宣兆琦:《齊文化發展史》,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