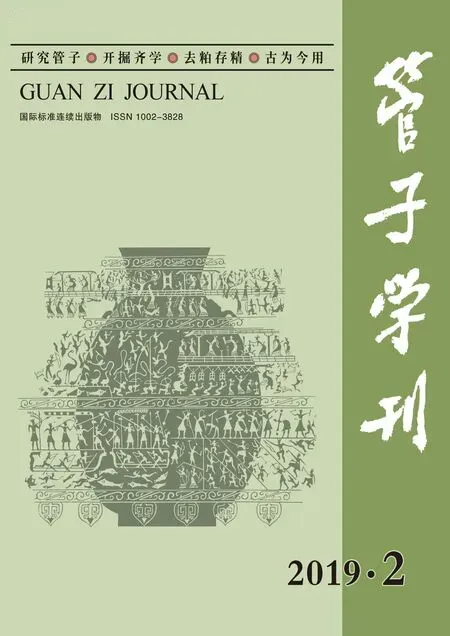先秦漢代儒家典籍關于孔子《尚書》學論述的分析
楊兆貴,吳學忠
(1.澳門大學 教育學院 中國 澳門 999078;2.香港浸會大學 語文中心,中國 香港 999077)
有關孔子與《尚書》的關系,古今學者的看法不同:傳統學者認為彼此的關系密切,《史記·孔子世家》《漢志》說孔子既編訂《尚書》,并給《尚書》各篇作序。現代學者如傅斯年認為孔子與《尚書》沒關系[1]402。錢穆認為要了解孔子的思想,不必了解《尚書》及其他經書[2]16。當代學者運用雙重考據法,贊同傳統之說。如程元敏指出孔子倡孝道、中道等本于《尚書》[3]360-366。馬士遠從文獻學角度論述孔子及其弟子引用《尚書》篇目、文本,論述《尚書》篇章文義等[4] 98-211。
可見,孔子曾編次《尚書》,以《尚書》為教材并寄寓思想,其微言大義被弟子及再傳弟子接受、傳揚,成為儒學一部分。先秦漢代儒家典籍如《禮記》《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孔子家語》《孔叢子》等保存不少“孔子”“夫子”等有關引、評、論《尚書》的材料。這些材料尚未引起學者足夠的重視,學者尚未專門深入論述。本文的研究,是希望填補學界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我們會問:這幾本典籍所記載的“孔子”言論真的是孔子說的嗎?筆者經過研究,認為有這幾種情況:一是這些言論與《論語》里的孔子所說的相合(《論語》當是記載孔子言行的一手材料,是判斷其他記載孔子言行真偽的基本材料、標準[5]1),一是儒家托孔子說的,并加以闡釋;一是孔子曾說過,但《論語》沒記載,這些典籍保存下來。
本文希望通過這些相關材料深入探討孔子與《尚書》的關系,孔子及儒家對《尚書》一些篇章、章節的看法,由此窺見所產生的版本演變、不同時代儒家對《尚書》的解釋,及這些思想觀念的演變。同時,這幾本書有的保存孔子家言,有的紀錄先秦漢代儒家的思想,它們之間有重復、先后等關系,它們對同一事件的思想觀念有同有異,可見儒家對孔子與《尚書》的關系已經形成說法,儒家內部思想有差異、有發展。
由于孔子及儒家論《尚書》的內容豐富,且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論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說(屬政制)、對殷高宗肜日不同說(屬祭祀)、孔子禮刑論這三方面。希望通過這些材料探討孔子與《尚書》的關系,孔子及儒家對《尚書》一些篇章、章節的看法,由此可見不同時代儒家對《尚書》的解釋及思想觀念的演變。
一、論《尚書·說命》“高宗梁闇,三年不言”說
《說命》清華簡、偽古文有,今文無。清華本《說命》三篇的第二篇與傳世《說命》中的某一篇非常接近,其他兩篇可能不是《書序》所指的《說命》篇章[6]214。《說命》先秦時已存在,《左傳》《國語》《禮記》都曾引用[4]308-319。可見,《說命》自先秦以來就有不同的版本。
《尚書大傳·殷傳六·說命》記孔子論“高宗梁闇”之事: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兇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7]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7]
這是伏生的經說,也是他認為孔子對殷高宗武丁“梁闇”的看法。
“梁闇”,《無逸》篇、《論語》皆作“亮陰”,《呂覽》作“諒闇”,《漢書·五行志》作“涼陰”。《尚書大傳》解為“兇廬”。《偽孔傳》、孔穎達釋“陰”為“默”,鄭玄解為“柱楣”[8]247、431,朱子解為天子居喪之名[9]1473,郭沫若解為不言癥[10]1536。
伏生指出:孔子是從三年守喪的禮制來解釋“梁闇”的:前君去世,世子繼位,不親政,三年必聽于冢宰,把朝政交給冢宰處理。世子是未來君主,起著表率臣民之用,因此,他必須恪守三年守喪而不親政的禮制。他認為孔子把家庭倫理之孝道應用于政治。
此事《論語》有記載。《憲問》記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孔子說:“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孔子除了把孝道應用于政治外,他還極重視孝道、三年之喪。他在《論語》常常提到“三年”,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又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陽貨》)天下所有的人都有父母,孝順父母是所有人的義務。一般人守孝三年,君主更不例外,應作表率。因此,孔子把孝道當作一個政治原則。
孔子回答子張而提出兩個要點:一是孝道,一是自古以來“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的禮制。其后儒家典籍《禮記》《孔子家語》《韓詩外傳》都記載,并加以闡述。
《禮記·檀弓下》記孔子回答子張之問說:“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9]274本段與《論語》所記也差不多,但有兩重點:一是三年喪是通喪,自天子到普通百姓,莫不如此;二是子張擔心世子三年不聽政,禍亂可能產生。孔子說冢宰總攬權力就會杜絕禍亂。《坊記》記高宗此事基本與《檀弓》同,但說“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是高宗說的[9]1287。《喪服四制》解釋孔子提出守三年喪的原因:“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圣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9]1472圣人根據對死者的悲痛心情日減而制定三年守喪期。該篇稱贊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且解釋武丁稱為高宗之由,因他是“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另外,“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9]1472。可見,《禮記》記殷高宗三年亮陰不言,既繼續《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又解釋孔子所言的禮意。
《孔子家語·正論解》所記與《檀弓下》基本相同,只把“讙”改為“雍”,與《無逸》同;把“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改為“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本篇還舉太甲、成王為例:“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11]496這兩例子可視為本篇對《論語》孔子說“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的解釋。伊尹、周公都是“古之人”,是世子居喪而行冢宰之權的典范。
孔子提出守三年喪通義,把孝道貫徹于政治、且視為一條重要的政治原則,《韓詩外傳》對此有進一步說明,說士受君主之爵,目的是“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以為親也”[12]233。忠、孝都是儒家提倡的,但是兩者有時會發生沖突。自孔子以來,儒家對孝、忠孰重孰輕有所論述。曾子在孔子學說基礎上對孝道進行闡釋,一方面把子女對父母的敬愛發展為普遍的抽象的準則,視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根本法則;另方面把孝道與忠君聯為一體,把忠當成孝的內涵的組成部分[13]6-8。郭店簡《六德》提出“為父絕君”,意即父喪與君喪同時發生,應服父喪而絕君之喪[14]97-100。郭店簡認為孝比忠重要。韓嬰生活于周季漢初,《韓詩外傳》是記載儒家面對漢王朝建立新的中央集權政府所帶來的壓力而如何自處的[15]73-103。韓嬰在上文這段文字肯定孝比忠重要:士入仕,收祿、受爵是要孝養雙親、尊顯父母。與曾子相較而言,韓嬰對孝道的看法更接近孔子的意思。
《呂氏春秋·重言》說:“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16]1155該篇重點是說高宗重視說話,明白作為天子說話的重要性,因此不輕易發言。這與儒家論孝忠關系、孝與政治的關系關涉不大。
典籍除了論述“三年守喪”“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外,一些典籍論述了冢宰的職權,認為冢宰位居六官之首,輔佐天子,其地位僅次于天子。《周禮》的說法最重要,也最有影響力。《周禮·天官·冢宰》說“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冢宰的職權是“掌邦治”、輔佐君主“均邦國”,鄭眾解“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六官皆總屬于冢宰。鄭玄注云“大宰總御眾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孫詒讓認為此大宰即王之相[17]1-2。賈逵解“均邦國”為“均節財用”[17]15。可見冢宰既統領六官,又輔佐君主理財,則冢宰既是首相,又兼財相。《內則》說“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后王指天子,以自己的道德修養而教民[9]725。《大戴禮記·盛德》的意思與此相同:“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18]146傳統典籍記載冢宰的職權基本相同。近來學者考察冢宰職務演變,認為宰本乃上古貴族家內職役,多與飲食有關,至周代演變為各級貴族的家務總管,掌管財用,后來發展為君主的最高輔相[19]47-65。又,郭沫若引《殷虛書契前編》有關帝乙舉祭的卜辭,證明商代新王在即位后第二年四月、十二月舉行兩次殷祭,斷言殷代王室沒有三年之喪[10]1535。如此,孔子是根據周代冢宰職位、三年喪來說明高宗三年諒陰之事的。可見,學者哲人(包括孔子)解說以前故事,有時受到當前史料、時代觀念等所限,未必能知道故事,就以自己所聞見的材料為說。這些傳說、聞見未必是以往的史實。
可見,孔子對“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提出看法,主要涉及孝道及其在政治運用中的原則,與“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的禮制問題。其后《尚書大傳》《韓詩外傳》《禮記》《孔子家語》都對這兩個看法進行闡論,或闡釋孝的內涵,提高其義理地位,或提出忠孝沖突問題,或闡述三年守喪之義等,不一而足。可見,不同時期儒家內部不同派別對孔子的思想都有闡釋,但重點有所不同。
二、孔子論《高宗肜日》“德之有報之疾”說
孔子評論殷高宗的除了三年諒陰說外,還有論高宗肜日雉飛升鼎而自我內省,重譯者來朝,故有“見德之有報之疾”說。《尚書大傳·高宗肜日》說: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7]
《高宗肜日》記武丁的兒子祖庚彡祭武丁[20]240-244。“彤”是商代祭祀之一,傳統注釋者大都說“彤”是祭祀的明日又祭,是正祭后的又一次稍次于正祭的祭祀。然楊樹達等根據卜辭考證,認為肜日即彡日,是依王名之日祭祀該王的一種祭祀,比前夕的“彡夕”祭祀更隆重的一種正祭。祭某王就在該王廟號所屬天干的日子里舉行,如祭太甲在甲日[10] 995-997。
《尚書大傳》對《高宗肜日》的闡釋在本篇注釋史上具有轉折意義:它與《尚書》的原意不同,而后代注釋者多受它的影響。先說它與《尚書》的原意不同。《尚書》原文寫: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臺。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10]992
這段文字記高宗之子祖庚舉行彡祭,有野雞鳴叫,這對信仰鳥圖騰的殷人來說深感驚詫。武丁的兒子祖己(孝己)勸祖庚不要害怕,把政事辦好,并說天帝給人的壽命有長有短,人們短命是因為他們不順從天帝,做錯事又不幡然悔改(自絕其命)。凡做君主的繼承大業,他們都是天帝的兒子,對祖先舉行常祀,不要偏重親近而不按上帝的規定去辦理[10]1022。
《尚書》與《尚書大傳》的說法不同:一是《尚書》說“高宗肜日”,舉行祭祀,《尚書大傳》明說是“武丁祭成湯”。二是祖己所說的內容不同,《尚書》把雞鳴作為警戒性的兇兆,所以祖己以人壽長短及舉行祭事要依常道來勸勉祖庚;《尚書大傳》里的雞鳴成了吉兆,預言將來有遠方來朝的盛事,果然三年后“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最后,劉起釪說《尚書大傳》最后一句是編造“孔子贊嘆的話來增加分量”[20]248。易言之,“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不是孔子說的。這一看法見仁見智。《論語》記孔子談及“德”而與本段的意思比較接近的主要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君主要修仁義禮樂的政教來招徠不服的遠方之人,恐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孔子曾說自己執政需要三年才有成績:“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如果王者行仁政,“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同上),則需三十年。所以,三年可以說是“疾”。
有關高宗肜日一事,上博簡《競建內之》也提到。簡文記隰朋提到高宗祭祀有飛鳥至,向祖己請教。祖己回答說:“昔先君客(格)王,天不見禹,地不生見龍,則欣(祈)諸鬼神曰:天地明棄我矣!……今此祭之得福也,青(請)(火)量之以寖……既祭之后,修先王之法”云云[21]169-171。大意是成湯時天大旱,成湯禱于山川、桑林、鬼神以自責,即求鬼神及修善政,現若要借祭祀天以求福,則須將此雉用湯汁烹煮,祭祀完畢,修先王成湯之法。高宗依照祖己之言,用湯煮雉,推行成湯之法,結果,“服之人七百邦”。簡文與《尚書》不同:一是前者說雉鳥在祭祀的彝器前鳴叫,后者只說雉鳥鳴叫;二是前者指出以先王為鑒,而后者強調遵天帝、按規定舉行祭祀;三是前者建議用湯汁烹煮雉鳥,后者提出“祀無豐于昵”。簡文記“服之人七百邦”,對《大傳》“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說產生影響。
自《尚書大傳》把雞鳴說成吉兆,且預言將來有遠方來朝之事,又加上孔子贊嘆之言,后代儒家及相關典籍多受其影響。
《書序》說是“高宗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7],明確說是高宗祭成湯,與《尚書大傳》的看法相同。
《史記·殷本紀》所記與《尚書》及《尚書大傳》各有同異。它與《尚書》相同的是:一是以雞鳴為兇兆而非吉兆,因此“武丁懼”。二是祖己所訓之言與《尚書》基本相同,但有兩處改動:一是把《尚書》“民中絕命”改為“中絕其命”,前者的主語是民,他把自己送上絕路;后者的主語是天帝,它在半路上滅絕君主的命。一是把“祀無豐于昵”改為“常祀毋禮于棄道”,前者是說不要對自己親近的神靈祭祀分外豐厚,后者說在經常祭祀時,不要失禮背道[22]155-156。它與《尚書大傳》相同的是:一是明寫武丁祭成湯,二是寫野雞升鼎耳。《史記》加“明日”,可能是根據“肜日”而來的。史公受今文學影響,但撰寫此段未完全接受《尚書大傳》的說法。
《孔叢子·論書》記孔子對《高宗肜日》的評論,說:“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茍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23]18該篇提出“見德之報”云云與《大傳》相同,又加說“茍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一句,說若君主行事“典厥義”,遵從天帝之德,則推行政策,可使遠方的民歸服,且對君主深致敬意。這句話是《論書》篇加上的,所以冢田虎說:“此意于今《高宗肜日》無所見焉……(《尚書大傳》)‘遠方君子殆有至者’是今意爾。”[23]30
《說苑·君道》也提到高宗、祖己之事。該篇所記主要與《尚書大傳》相同的較多,然亦有相異處。相同之處如說武丁修身,三年后七國蠻夷重譯來朝貢的。相異之處比較多,一是說武丁召其相,相所說的一番話傳自祖己;且祖己說的內容與《尚書大傳》不同,這里說的是會亡國,而《尚書大傳》則根據《尚書》說法而來。二是時間、地點完全不同,地點是武丁看到朝廷長了桑谷,時間不是彡祭之日;武丁沒聽到野雞鳴叫,而看到凄凄野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說以桑喪、谷生解說殷國將亡[24]1411。劉向可能把太戊時桑谷共生與高宗時雞鳴相混,所以在《說苑·君道》篇記載之事與《尚書大傳》不同[24]1410。
《論衡·異虛》篇的記載基本上繼承《君道》篇,不同的是該篇記高宗見桑谷七日大拱而先后問相、祖己。高宗聽了祖己之言而修身行政,本篇多“桑谷亡”一句;又說“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25]213-214,國數與《君道》所說的不同。王充最后批評此是虛說,他指出祖己之言無益朝亡,高宗修身無助除禍。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于行之善惡,而在命之長短;國之存亡不在君政得失,而在期之長短[25]214。
從以上論述,可見:(1)從版本學來看,《高宗肜日》在先秦漢代流傳過程中有不同的版本。在這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傳世《尚書》本、上博簡本、《尚書大傳》本等。其中,傳世本、《尚書大傳》本是比較重要的版本。不同版本在一些敘事上有所不同,如上博簡《競建內之》、《尚書大傳》、《說苑·君道》對來朝的邦國數目有不同記載。(2)不同時代《高宗肜日》版本也會增減字數、內容,以致內容、內涵有了變化。如傳世本記雉鳥鳴叫,并作為警戒性的兇兆。而《尚書大傳》把雉鳴當作吉兆。《說苑·君道》篇則說武丁沒聽到野雞鳴叫,而看到凄凄野草。《史記》改動字、義,如把《尚書》“祀無豐于昵”改為“常祀毋禮于棄道”。(3)不同時代、思想人物對《高宗肜日》有一些不同的特獨的看法。
為方便了解先秦漢代儒家對《高宗肜日》的不同說法,簡列一表如下:

時間人物事由各家說法要點《尚書·高宗肜日》彡祭祖庚、祖己有雉鳥鳴叫(作為警戒性的兇兆) 1.祖己建議祖庚把政事辦好。2.人壽長短在于是否遵從上帝。3.君主舉祭不要偏重親近而不按上帝的規定辦理(祀無豐于昵)。上博簡《競建內之》武丁、祖己雉鳥在祭祀的彝器前鳴叫 1.祖己指出以先王成湯為鑒。2.文本也用“惟先格王”,與《尚書》同。3.祖己建議用湯汁烹煮雉鳥。4.服之人七百邦。《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雉鳴(吉兆) 1.祖己說遠方將有來朝貢。2.武丁內反諸己,思先王之道。3.三年后編發重譯來朝者六國。4.孔子說“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史記·殷本紀》武丁祭成湯(與《書序》同)的翌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叫(與《書序》同;雞鳴為兇兆,與《書》同) 祖己所訓之言與《尚書》基本相同,但有兩處改動:一把《尚書》“民中絕命”改為“中絕其命”;二把“祀無豐于昵”改為“常祀毋禮于棄道”。《孔叢子·論書》 1.孔子說“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與《大傳》同)2.加論“茍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說苑·君道》武丁沒聽到野雞鳴叫,而看到凄凄野草 1.武丁問相,相說聞之于祖己。祖己所說的不是他親自告訴武丁。祖己說桑谷生,將亡國。2.武丁推行一些措施: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興、滅、舉、明四項是其他典籍沒有記載的)。3.三年之后,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上博簡說七百邦,《大傳》說六國,數目不同)。
三、孔子論《呂刑》之刑法:孔子禮刑觀
上文論孔子重視德,孔子也重視刑。孔子以前的一些歷史人物曾對刑提出一些看法,如周公提出“明德慎罰”,《呂刑》提出刑法的具體內容與實施原則。他們對孔子產生影響。秦漢儒家論述孔子論刑,可見他們確信孔子除了提倡仁,也重視刑罰。孔子的刑罰觀有些受《呂刑》影響。
(一)《呂刑》篇簡介
《尚書·呂刑》篇是現存最早的寫于先秦時期的較有系統的法學篇章。它闡示用刑的精神、原則、要求,向君主提供“用刑之道”。晁福林師指出,《呂刑》所說的刑是周初“義刑義殺”的體現。刑罰只是周禮的末節,而非主體。周人把刑納入周禮,以激發人的恥感與社會責任感[26]114-120。《呂刑》由初本到定本有一發展過程,初本寫于郭店簡之前,今本可能是戰國后期齊國法家學派寫成的[27]25-26。文本有一發展過程,最終定本應吸收與它同時或早前不同時期的思想觀念。
(二)儒家的至治時代及刑罰產生說
堯舜是儒家的圣王。儒家認為堯舜時期不用刑罰而天下大治。《尚書大傳·周傳》記孔子說“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的原因是“教誠而愛深也”“五刑有此教”[7]。
此段《孔叢子·論書》所記基本相同,只把孔子回答改為“五刑所以佐教也”[23]18。《孔子家語·五刑解》記孔子肯定三皇、五帝“制五刑而不用”的“至治”是可信的,其說法可補充《尚書大傳》“不刑而天下治”之說。這篇文章指出,孔子認為三皇五帝之時雖有五刑而不用。他分析了百姓出現奸邪、盜竊、非法、胡作非為等現象的原因,是由于他們“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因此,要根據這些現象而制定相應的喪祭、朝覲、鄉飲酒、婚聘四種禮儀,控制百姓的嗜好和欲望,使他們能分清好壞,順應天道。易言之,這些禮儀的制定是有針對性的,如喪葬之禮針對不孝之罪,婚禮針對犯淫亂之罪。如五禮已制定、已宣化,而百姓仍有頑固不化的,就要向他們重申禮意,并闡明法典的實質意義,加以強化。三皇五帝做到這點,因而是“至治”之時[11]346-347。可見,孔子認為先根據社會出現的問題,對癥下藥,有針對性地制禮,從人心這一本源出發,制定禮儀才能解決問題;刑罰只是輔助禮制。禮本刑末,這是孔子的一貫主張。
《孔子家語》說三皇五帝是“至治”時代,《尚書大傳》及《孔叢子》說堯舜是理想時代。儒家一般認為堯舜是理想時代[28]25。此一時代之所以不用刑罰,子張認為主要原因是君主對百姓“教誠而愛深”,孔子則以為是“五刑有此教”,施行以教化為主的刑罰。孔子提出這樣的看法,是因為周代社會秩序主要依靠血緣親情、道德來維系。同族人若犯錯,主要是施以道德懲戒,使他們感到恥辱。從道德教化角度出發,施行的主要刑罰是“象刑”。呂思勉說象刑是“刑將施于本族,而猶未忍遽施,乃立是法以恥之者也”[29]356。象刑帶有道德教化之意,使罪犯感到恥辱,從而改過從善。《尚書大傳》《孔叢子》提到“一夫而被五刑”,其意涵乃強調道德教化為先,刑罰為次。又,孔子提出“五刑有此教”(《尚書大傳》)、“五刑所以佐教”(《孔叢子》)可能與他整理《尚書》而從中獲得思想有關。偽《尚書·大禹謨》說“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偽孔傳》解弼為輔,言“以刑輔教,當于治體”[8]91。《大禹謨》被認為是偽書,但該篇記禹征苗民的“文德”內涵與儒家“干羽以懷遠”的理想相悖,該節應是先秦文字[30]139-144。另該篇提及的“六府三事”也見于《左傳·文公七年》,因此,閻若璩也認為該篇所言“句句有本”[31]130。因此,孔子有可能看過《大禹謨》相關材料而吸收其中的思想。
(三)孔子及儒家禮刑說
孔子重視禮尤甚于刑。《論語·為政》記孔子一段關于禮、刑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認為只用政法誘導、刑罰來整頓百姓,百姓只能暫時免于罪過,而沒有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誘導、禮教來整頓百姓,百姓不僅有廉恥之心,而且人心歸服。孔子這段話比較含蘊,后世儒家典籍《緇衣》《孔子家語》《孔叢子》等都加以闡釋。
《緇衣》現有三個版本,包括《禮記》本、郭店簡本、上博簡本。三個版本的內容基本相同,但一些用字不同,反映了一些思想的差異、演變。學者或從文字差異、或從思想演變論述三個版本的異同[32]50-56。由于本文并非討論三篇文字異同,且三篇內容大同小異,因此,本文只引用《禮記》本為說:
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9]1323
這段話應是儒家對孔子禮、刑說的早期解釋。孫希旦解“格”為“至”,“謂至于善也”;訓“遯”為“逃”,“謂茍逃刑罰而已”[9]412。意即君主推行德禮,則民有歸至之心,反之則做事只有只求逃避刑罰之心。另外,本段文字引用《呂刑》。《禮記》作《甫刑》。《甫刑》即《呂刑》。《呂刑》此句作“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傳世本把“靈”作“命”。錢大昕、段玉裁都認為“命”是“令”之誤,“令”“靈”古多通用,都有善義[10]1932。《呂刑》此句句意是苗民之君不用善道,只知制訂重刑,創制了五虐之刑叫做“法”,以濫殺無辜、殃及無罪之人。易言之,真正刑罰是由苗民之君開始制訂、實施。這種唯刑是從的做法為儒家所反對。儒家相信“五刑所以佐教”,象刑所以“立是法以恥之者”。因此,儒家大力反對只重刑罰而忽視德教的做法。《緇衣》引《呂刑》這段文字,應在說明真正實施刑罰、且唯刑是尚的是由苗君開始,而非儒家圣王堯、舜制定推行的。《緇衣》篇提到民有“格心”“遯心”“勸心”“免心”等,說明它重視民心的重要。
《大戴禮記·禮察》也論此觀點:
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18]22-23
本篇內容基本與《緇衣》相同,但有危機感,強調“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強調“積”的重要性,認為以禮義治民則積禮義,結果是百姓和親;反之若以刑罰治民則積刑罰,結果是百姓的怨恨倍增。文章指出,“以德教”或“以法令”都是君主統治的手段。本篇與孔子、《緇衣》有不同之處:前者認為德教、法令的結果分別是民的“康樂”“哀戚”,指出分別推行這兩種措施導致不同的結果;后者認為推行德教、法令的結果分別是百姓既知道羞恥又能不犯刑罰,或百姓只知道避免刑罰而沒有羞恥之心。兩種結果不可同日而語。另外,本篇強調康樂、哀戚,是從感情方面來說的;本篇又把情與禍福連接起來:有康樂則有福,有哀戚則有禍。本篇強調的禍福結果與孔子、《緇衣》強調百姓應有道德心(羞恥心)不同。
《孔子家語·始誅》記孔子誅殺少正卯、處理父子爭訟時說:
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言必教而后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11]13-14
這里孔子提出的禮刑觀比《論語》《緇衣》《禮察》篇較詳細。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孔子對當時社會的看法,一是他對先教后刑的看法。關于前者,他認為當時教化淆亂,刑罰繁多,統治階層沒有盡責去教化百姓,而只以刑罰處懲他們,結果出現刑罰越多越禁止不了的情況。面對這樣嚴峻的局面,孔子提出“必教而后刑”的看法,其中的步驟是:君主先身體力行,以身作則,使百姓信服;其次從積極方面以尊崇賢人的方法——樹立榜樣——勉勵百姓;再次從消極方面廢黜無能;如果仍沒成效,就以教令的威勢使百姓忌憚;最后才用刑罰對待那些不聽從教化的奸邪之徒。可見,《始誅》篇有關孔子禮刑觀基本上與《論語》相同,但這里談得比較詳細。
《孔子家語·刑政》記孔子回答仲弓之問說:
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11]355
本篇也提出先德后刑的看法,與《始誅》篇互補說明。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明顯地把德、刑之治分了兩個層次:以德教民、以禮齊民是最好最高層次的,以政治引導百姓、用刑罰禁止則不如德禮之治。其次,本篇明確指出刑罰的對象,是針對那些損害道義、傷風敗俗、屢教不改的人。最后,本篇提出施刑的原則:必須符合天道,施刑罰時即使罪行很輕也不能隨意赦免,君子辦理案件要盡心盡力。
《孔叢子·刑論》篇記孔子說“古有禮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23]77,把實行禮、刑作為古今刑罰省繁的原因。
除了以上大、小戴《記》、《孔子家語》、《孔叢子》相關篇章記孔子談論禮先刑后、禮主刑輔的看法外,《史記》《漢書》相關傳文也記載漢代士人引用孔子禮刑言論,如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22]5980、班固在《漢書·刑法志》[24]1094都直引“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段。此不贅。
(四)孔子及儒家古今刑罰省繁論
因為孔子重道德、禮教,因此《尚書大傳》記孔子論古今刑罰省繁,其原因與那時代是否重視禮有關,若重視禮,先禮后刑,那么刑罰簡省,反之則刑繁: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后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7]
《孔叢子·刑論》也有一段基本相同的記載: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后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茍免。”[23]77
《尚書大傳》與《孔叢子》都從重禮(而非德)與否來解釋刑罰省繁之因。《尚書大傳》“伯夷降禮,折民以刑”,傳世本《呂刑》、《墨子·尚賢中》、《漢書·刑法志》、《孔叢子·刑論》都作“伯夷降典”;“折民以刑”或作“折民惟刑”(傳世本《呂刑》)、“哲民維刑”(《墨子·尚賢中》)、“悊民惟刑”(《漢書·刑法志》)、“折民維刑”(《孔叢子·刑論》)[10]1964。傳統學者多訓“典”為“禮”。顧頡剛認為吳澄、王引之釋“折”為“制”比較符合原意,“折人惟刑”意即“制民人者惟刑”,句意“管理人民只有以刑法制裁之耳”[10]1966。“殷罰有倫”出自《康誥》,是周公告訴康叔到衛國治民,要按照殷代刑法來治獄,這才符合程序。 “諸侯不同聽”,《孔叢子》“聽”作“德”[23]78,應該比較符合原意。
孔子重視德、禮,也重視刑、訟,說:“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意即一定要使訴訟的事件完全消滅才好。范祖禹解釋說:“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33]137楊時說:“圣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33]137使民無訟是正本清源之方,是孔子的理想。這也是儒家的理想。
孔子主張先禮然后有刑,后世儒家繼承此說,并闡以己意,上文已論述。這一看法與《呂刑》相同。《呂刑》通篇強調先禮后刑。先禮后刑也是西周人的觀念。西周人也認為禮是道德倫理規范,是本,刑是末,禮主刑輔[26]119。
(五)孔子論施刑的原則
《尚書大傳》記孔子對施刑提出一些原則: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罪。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克,不赦有過謂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7]
根據《尚書大傳》所說,孔子就施刑罰提出幾點原則:一是“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對待那些貧窮、孤獨矜寡、老幼不肖無告的(現在所謂的弱勢團體或人士)要采取“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的方法,對待老弱則采取不施刑、不入罪的方法。一是采取“哀矜哲獄”的判案審案原則。三是采取“言不越情,情不越義”的原則。
孔子這些施刑原則,繼承《呂刑》而來。
《呂刑》提出以刑輔德,關心鰥寡無依之人:“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10]1901,諸侯及其臣下奉行明德,不要像往日那樣失去常理,要連鰥寡孤苦無告小民也沒有受到傷害[10]2078。
《呂刑》確立了案件審理及刑罰運用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其中一項是明確罪與刑罰對接適用的基本原則,要求君長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掌握刑罰尺度:“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10]1995如果所犯的罪于法沒有專條時,就可上比其重罪,下比其輕罪,上下相比以定其罪,但不得妄亂供詞,以奸亂法。治獄不該用不當之理以羅致成獄,應該察其罪行而正用其法,一定要詳加審核使不錯亂。這是要求官長要慎刑。如果犯的是上刑,其情節適于輕的,就可服下刑;如果犯的是下刑,但其情節可惡而適于重的,就可服上刑。這是要求判刑根據罪犯情節輕重、嚴重性而定,與《康誥》“明德慎罰”說相同[34]585-586。另外,要衡量罪行輕重以處罰,權衡其情況后才決定。這是就個人判刑輕重來說。刑罰還隨時世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決,這是就時代判刑輕重來說。可見,《呂刑》提出判刑根據罪犯犯罪情節性質、輕重、時代背景而定的看法。這樣,刑罰不是雜然無統,可以隨意加重減輕的[10]2081。以上這些是判刑的原則。
另外,《呂刑》提出“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10]1995。治獄以哀憐矜惜之心來處理刑獄之事;要明白無誤地開讀刑書,與眾人共同參透拈準,這樣,斷獄才能中正而無冤濫過誤;所判五刑五罰,都必須詳加審核,不可輕率。這樣才能使人信服[10]2082。
《呂刑》這一思想影響了孔子,也影響漢儒。《鹽鐵論》所記文學之言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35]567《漢書》記載相關之論,如“《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圣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24]3396-3397。
《呂刑》發展了周公“明德慎罰”思想[34]585-587,提出:其一,“德威惟畏,德明惟明”[10]1901,上帝對那些放肆行虐刑的人報以威嚴的懲處,這樣使那些行虐之徒無不畏其威嚴;又以德施明,使百姓尤其是那些久處幽枉之民無不蒙受其明。其二,“惟敬五刑,以成三德”[10]1982,所謂三德,指刑當輕的柔德,刑當重的剛德,刑不輕不重的正直之德。官長應敬于五刑之用,以成三德。這就是引政入教,以法令約束、引導百姓,最后達致三德。所以,《呂刑》又說“爰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10]1901,治理百姓要用適中的刑法,從而教導百姓敬行道德。
可見,孔子論施刑的一些看法受到《呂刑》影響,而《呂刑》也繼承了周公思想。
結語
先是本文的不足。由于孔子及儒家論《尚書》的內容豐富,本文只論述孔子及其后儒對“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殷高宗肜日“德之有報之疾”及禮刑論這幾方面。論述不夠全面。
其次,本文通過《禮記》《尚書大傳》《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儒家典籍記孔子之言,對《尚書》記載的一些思想、制度進行評論,可見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這幾本典籍所記載的“孔子”言論是否孔子說的。這可分為兩種情形:其一應記載孔子的言論,如說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當為孔子所說。其一托孔子之言而論述的,如論《堯典》“舜年三十不娶謂之鰥”而提出男三十婚、女二十嫁說。
二是反映先秦漢代儒家對孔子一些思想觀念的繼承與闡揚。如孔子的禮刑觀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緇衣》篇提出君主實施德禮或政刑而使百姓產生不同的“心”的看法。《大戴記·禮察》則從感情、禍福方面來說明推行德教或法令的結果。《孔子家語》提出“必教而后刑”的步驟、施刑的對象、施刑的原則。
三是反映先秦漢代儒家對《尚書》一些看法的繼承與轉變,也反映儒家的一些思想。如《尚書·高宗肜日》提出君主舉祭不要偏重親近,要按上帝的規定祭祀。《尚書大傳》《孔叢子》《說苑》等稍改《高宗肜日》的說法,或提出“惟先格王”,或提出內反諸己,思先王之道,推行其他措施,則“德之有報之疾”的收獲,最后不少邦國前來朝貢。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之一。
可見儒家思想隨著外在環境(如政治、社會、其他學說影響)、內在思想演變而不斷發展。他們對孔子的學說也不斷進行闡釋,而側重點有所不同。這是儒學也是思想史的發展規律。這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