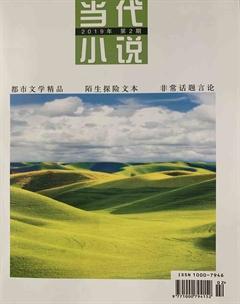張牙舞爪(短篇小說)
趙卡
我說的還是養雞場那點破事兒。
關于這個挖地三尺都糊滿雞屎的地方,我在以前好幾個小說里都提到了,沒看過的可以自己去找。這回,我不說別人,單說徐強強,他的事兒說完了,我就不再寫養雞場的小說了。不過也說不準,人們都說我說話總是不那么靠譜,說不準哪天我又寫了。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為了哄騙一個女同事的感情,我對她說,今生非你不娶,她竟感動了,我得手了,可后來,我娶的老婆不是她。我毫無害臊之心這么說的意思,是我自個兒,有時也不大相信自個兒說過的話。
徐強強的事兒,我馬上就會講到,大家不要急。在講徐強強之前,我決定還是先從呂二霞講起,沒有呂二霞起頭,就沒有徐強強結尾,這么說吧,不這樣講,這個故事就沒頭緒了。
呂二霞是從養雞場建場之初就跟隨老板路長征來了。那時候的路長征頭是窄條形的,身形像根攪屎棍子,插隊青年,從北京下來的。北京人,知道意味著什么嗎,祖國的心臟首都的人,有知識,有文化,有魄力,有想法,有腔調,見過大世面。這么一個五有一見的青年,在呂二霞的老家殺縣,一干就是多少年,具體多少年,呂二霞也記不清楚,反正,在她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就知道了全縣的革命勞動模范路長征,他發明的小麥增產技術,獲得了當時縣和市革委會的通報嘉獎。說呂二霞是從養雞場建場之初就跟隨了老板路長征,不是說呂二霞跟養雞場的老板路長征有一腿,或者干脆說她是路長征的老婆、情人、二奶、小三什么的,這種話也不能瞎說,他倆的歲數差了一大截子,我最終的意思是想表明這樣一個事實,呂二霞從一開始,就是養雞場建場的元老之一。
路長征作為那個轟轟烈烈年代上山下鄉的北京知識青年,那時候是分派在呂二霞他們家的,和呂二霞他爹呂高兵很快就混熟了,結下了只有貧下中農才具有的牢固友誼。十年文革結束,路長征也結束插隊工作,但他并沒有和其他知青一樣,為了回城到處找關系,他不屑于干那種事,相反,他在當時做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誰也沒有想到的決定,自己創業,扎根農村。當時,路長征的同學,他的父母,他的朋友,都勸他慎重考慮一下他的決定,但他義無反顧地拒絕了他們的好意。既然決心下了,路長征首選便是養殖業,他一點也沒表現出多悲壯的樣子來,反而很高調地說他要實踐中國特色的私營農業產業化。有通內幕消息的人曾偷偷找了路長征,壓低嗓音說老路啊你這私字打頭,不想活了,趕緊的,把那個私字擦了,你忘了斗私批修么。路長征很討厭這種鬼鬼祟祟的行徑,不慌不忙抖露出了當時的農業部部長給他的親筆信,說瞧見沒,政策在這兒,杜部長親筆寫的。杜部長是誰,一般人都不知道,反正是個挺大的官,和鄧小平同志的關系最近,改革派闖將之一。
呂二霞不懂路長征的農業產業化宏偉藍圖,也不懂什么是私營企業,她只是跟著路長征,她父親也放心她跟著路長征學本事,從殺縣來到了呼和浩特市南郊,在一個荒廢的兵站扎下了根,搭起了簡易的雞棚,開始養雞。除了呂二霞,還有幾個人,都是路長征攢雞毛湊撣子湊的,一個月工資十五元,但管吃管住,愛干不干。按道理是沒人干,工資太低了,別說人,連狗都養活不了,其實不然,那幾個愿意跟了路長征的人,原來都是流浪漢,正好沒個住處和吃處,路長征的南郊養雞場正是養老的好去處。這樣看來,路長征的起步創業,一個他,一個呂二霞,還有幾個流浪漢,說起來也夠寒磣的。
十年后,在路長征臥薪嘗膽般的創業下,南郊養雞場已然擴大了一千倍的規模,員工四百多個,存欄雞只十五萬,位列中國民營養雞場規模第三,地位僅次于上海大江有限公司,那是當時中國的養雞老大。路長征從一個知識青年變成了企業家,瘦子變成了胖子,腦袋也漸漸禿頂了,自然,人們改口路禿子了。呂二霞也一晃成了大齡女青年,二十六歲了,也有說二十七歲的,還有說二十八歲的,不管二十幾歲,反正離三十歲不遠了。眼看著小姐妹們都結了婚,甚至都抱上了孩子,呂二霞還是光棍一條,生活枯燥無味,按今天的話說,是剩女,不由得著急起來。
好的都讓你們撈走了,剩下的都是歪瓜裂棗,姐怎么辦,呂二霞常常自我解嘲。
連公司董事長路禿子都看不下去了,逮點空當,就勸呂二霞說,將就一下吧,看對哪個和我說,給你辦得風光點兒。
呂二霞只是笑笑,不吭聲,沒說要將就,也沒說不將就。呂二霞笑起來的時候,臉上皺紋明顯多了,仿佛人民幣的花邊邊兒。小年輕們則一副深諳世事的樣子,說女大十八變,全憑棒子旋,呂二霞呂姐沒有男人開荒澆水,一塊好地都旱多少年了,著實可惜,沒雨露滋潤,老起來就快。小年輕們還說了,你看史二他老婆,一個離婚的老女人,快四十的人了,還帶著一個七八歲的姑娘,以前簡直就是黃臉婆,自從改嫁了史二后,沒半年就容光煥發,臉上的褶子都沒了,好像年輕了十歲,說明了什么,說明了魚兒離不開水,女人離不開男人。
話糙理不糙,這誰都明白。史二的老婆都能明白的事,呂二霞就更明白了,但她明白得的確有點晚了。我以前寫過一篇叫《郭老板借槍》的小說,里面提到了呂二霞,你們要是不嫌麻煩,我借這篇小說一點地方,大致給你們說說呂二霞怎么回事。我在那篇小說里寫到了郭老板當時在養雞場下夜,你說你下夜就下夜吧,不知怎么回事,慫恿路禿子聘請的場長曹禿子弄把槍,說是為了嚇唬雞場周邊的地痞無賴。的確,當時養雞場離市第一勞教所距離太近,老有一伙文身光頭,在附近放豬,隔三差五來騷擾。曹禿子性格粗魯,做事一般不過腦子,為了防止勞教犯等地痞無賴的滋擾,真的給郭老板借了一支叫做教練槍的家伙。教練槍可不是小孩玩具,真槍裝實彈,一百米射程之內絕對要命,子彈出了一百米射程后就沒威力了。嚇唬死狗日的,曹禿子說。郭老板拿了槍,倒是沒有詐唬那些來養雞場騷擾的地痞流氓勞教犯,而是打狗,打了就燉了吃,曹禿子好這口,夸郭老板好鋼用在了刀刃上。結果,也是這把槍,惹了大禍,一天夜里,郭老板拿槍殺了他對象,自己也自殺了,害得曹禿子差點被路禿子免了職。呂二霞和郭老板的對象都在養雞場化驗室,關系甚好,郭老板的對象被槍殺,呂二霞當時聽了消息,就嚇癱了,尿了一褲子,曹禿子怕再出人命,連夜叫了一個班組長,姓孟,把呂二霞送到市里的職工醫院,據說,那天夜里,呂二霞嚇得要命,直往男人的懷里鉆,那個姓孟的班組長就趁機在醫院的病房里,下手了她。
我在這里說《郭老板借槍》這篇小說的意思,就是透露一個信息給你們,呂二霞應該在嫁給徐強強之前就失身了。當然,這一切誰也沒見過,都是聽那個姓孟的班組長說的,那個家伙沒多久就不干了,音訊皆無,沒法對證,至于是不是真的,就不好考證了。
現在我就可以說徐強強了。我那時候還不認識徐強強,徐強強是怎么認識呂二霞的呢,這還真是一樁奇遇。呂二霞在養雞場受了驚嚇,說什么也不敢再回化驗室呆了,路禿子看呂二霞可憐,又念她跟隨自己十余年有功,就把呂二霞調到了市里的供應科,做個統計員。做了半年之后,呂二霞終于走出了夢魘,臉上又綻出了笑容,這樣一來,就顯得好看多了,但還是沒有男朋友。不過,呂二霞在工作閑暇,無意間接了一個電話,讓呂二霞有了男朋友。這個男朋友就是徐強強。徐強強也是無意間打錯了電話的,后來我們才知道,那會兒徐強強剛從大學畢業,那種自費大學,不包分配的,畢業即失業。徐強強無所事事,就到朋友的單位找朋友,朋友不在,他想聯系另一個朋友,就抓起朋友桌子上的電話,公家的不怕費錢,給另一個朋友打電話,撥錯了一個號碼,撥到呂二霞那兒了。這徐強強也實在是無聊,一聽是女聲,還比較優美,將錯就錯,和呂二霞聊了起來,一聊,還聊得挺投機,徐強強就記了呂二霞的電話,隔三差五地打,直到呂二霞被徐強強打動了,約好見個面,吃個飯,他們就見了面,吃了飯,吃完飯后,互相印象頗好,就秘密好上了。
徐強強沒工作,社會上漂著也不是回事兒,呂二霞就找了路禿子,希望給小她五歲的男朋友找個崗位。路禿子一聽呂二霞終于有了男朋友,很高興,仿佛是她女兒有了男朋友一樣,不假思索就應允了。呂二霞帶徐強強見路禿子那天,路禿子問徐強強有什么本事,徐強強差點答不上來,呂二霞替他說了,說徐強強除了大學畢業外,還練過武術,還在大學里拿過演講比賽三等獎,還善于與人溝通。路禿子認為這么多本事隨便就能安排一個崗位,說那就讓小曹給安排到養雞場吧,我給他說,這事必須辦。路禿子的話就是命令,何況是養雞場元老呂二霞的事兒,曹禿子忙不迭把徐強強安排到了保衛科,這也是照顧了徐強強會武術的特長。自然,呂二霞又回到了養雞場化驗室。
我那時候在養雞場的飼料加工車間,和保衛科的劉二亮,蛋雞車間的額爾敦倉,還有幾個酒友,司馬北孔慶西周大平什么的,每日廝混在一起。徐強強的到來,第一天就和我們混熟了。他不喝酒,但喜歡酒局,尤其喜歡和喝酒的人在一起玩兒。經常這樣,他喝飲料,偶爾喝點啤酒,我們喝白酒,喝完了,徐強強就提議干各種事兒,除了偷雞摸狗,主要是上城里玩。我們那時候工作忙,加上手里沒錢,又離城里遠,一般不敢上城,但徐強強說,沒問題,有他在呢。就這表態,徐強強始終讓我們很佩服,解了我們的很多疑懼,一般人是不敢這么說話許諾的。
城里好玩,哥幾個一合計,走就走唄。我們瞅了一個星期天,出了養雞場,步行到了公路邊,等了一輛進城的班車,買了票,朝城里刮去了。那天,徐強強和劉二亮穿了保衛科的衣服,就是那種乍一看像公安局的,細看卻不是的那種二狗子制服,一般在公安廳附近的勞保商店都能買到,花不了幾個錢。我和額爾敦倉還是平常的衣服,不過額爾敦倉戴了一副墨鏡,總是朝天瞧著,像港片里的警察黑社會,挺威風。到了城里的南門,我們就下了,換乘1路公交車,我們兩眼一抹黑,徐強強熟悉城里的娛樂場所,他說怎么走我們就怎么走。1路公交車是老牌線路,終點站是火車站,所以每趟車上的人都特別多,過了兩站,我看見一直坐在機蓋上的一個家伙,挺年輕,燙發頭,二十來歲的樣子,估計是喝了酒,滿嘴污言穢語,還動手動腳,調戲公交車司機。司機是個小女孩,眉清目秀,估計剛上崗,沒見過這等陣勢,有點慌亂,一時不知所措,差點就哭了。滿車的人,男女老小,都假裝沒看見,敢怒不敢言。這下,更讓醉鬼有恃無恐,如入無人之境般手舞足蹈。
我有點看不下去了,低低地問徐強強,這家伙還不如咱廠茅坑里的蛆有教養,動手不?
徐強強瞧了一眼額爾敦倉說,那還用問,動了也白動,這種人我見多了,揍狗日的。
額爾敦倉本來是墨鏡朝天的,聽了徐強強的話,站起身,臉上透出一股神氣,朝機蓋上的醉鬼走過去,二話不說,照著醉鬼的臉上就是一腳。醉鬼完全沒防備,臉上帶著花紋鞋印,一個趔趄從機蓋上滾了下來,還沒等爬起,劉二亮跟了上去,用腳狠狠地在醉鬼頭上踩了幾下,醉鬼的耳朵里都出血了,額爾敦倉則是照著醉鬼的肚子狠踢。醉鬼一時哭爹喊媽,滿車打滾,司機估計是害怕了,嘎吱一聲,踩了剎車,打開車門,大聲喊著讓醉鬼下去。醉鬼本來被揍暈乎了,正不知道該怎么辦,聽了司機的話,就像撈著了救命稻草,連滾帶爬跌下了車,拍拍屁股,像受驚嚇的豬吱吱叫著跑了。
英雄,車廂里的人們都豎起了大拇指,紛紛說,英雄,好漢,見義勇為。
這年頭警察還是好樣的,車廂里的人們繼續說。
謝謝,謝謝,女司機扭頭朝我們說。
面對著滿車贊譽之詞,我后悔沒上去也打兩下那個醉鬼,要不,我也英雄一回。只有徐強強紋絲不動,一副老大的做派,還裝出一副極不高興的樣子。劉二亮顯然把自己當警察了,假迷三道地問徐強強,隊長,到了么?
徐強強一仰脖子說,下一站就到了,現在的治安的確有點不像話。
下了車,徐強強領著我們到了一家舞廳,是個二層舊樓,名字叫蘭桂坊,可能是霓虹燈壞了,我看成了三桂坊,其實就是那種窮人樂,一塊錢一張門票,可以跳到你累癱的那種場子。進進出出的人很多,看穿戴打扮,和我們差球不多,兜里都是沒多少錢的。我們一共四個人,徐強強應該是舞廳的常客,認識門口那個賣票的,說四個人三塊錢行不,賣票的一開始說不行,接著又說行了,這面子給得大方,我們就魚貫進去了。舞廳內大音箱震天響,說話還得湊在耳朵邊兒喊,不然聽不清,頂子上吊著一個大轉球,折射著五顏六色的光線,舞池子里男男女女摟抱著,轉著圈,跳著舞。徐強強讓我們先找了座,說看對了哪個女的,就主動上前邀請,不要怕,一般情況下,女的會接受邀請。我們三個都土鱉似的說不會跳舞,徐強強說,那你們坐著,看我就行了。
我們的確土鱉,不會跳舞,肯定沒法去邀請舞廳里的女人了,只好坐著。不一會兒,徐強強摟著一個三十來歲的燙發頭女人,在舞池里轉了起來,而且,看起來很親熱,說說笑笑的。那女的比較肥一些,尤其是那兩瓣屁股蛋子,要不是褲子兜著,估計能掉在地上。額爾敦倉和我說,不會跳舞虧了。我說,回去得趕快學幾招,你看徐強強那手,老往那個女人的兩瓣屁股蛋子上摸,肯定挺軟乎受用。
徐強強把我們晾在一邊,他接連跳了三曲,換了三個女人,都是三十來歲的,有一個看上去像是四十多歲了。徐強強的舞姿說實在的,真好看,看得人眼花繚亂。我觀察了一會兒,好像明白了一種叫慢三的舞步,我決定試試,邀請一個女人跳,我早就瞅上了,細腰,大胸,大披發。我剛站起身,忽聽舞池里哇一聲,接著,一個小胖子渾身是血跑了出來,后面跟著幾條精瘦壯漢,追打渾身是血的那個小胖子。跳舞的人一下就炸了,迅速退回座位,舞池中央躺著一個人,看樣子是個女的,或者是男的,面目不清,在一下一下地抽搐,我一下就明白了,估計剛才渾身是血的那個小胖子,拿刀捅了躺在地上的那個女的,或者男的,那個不男不女的家伙受傷嚴重,怕是支撐不了多久了。
我們三個正看著,徐強強走過來說,走吧,又他媽出人命了。
我們就這樣面面相覷地出了蘭桂坊,走在大街上,眼界一下子開闊起來,剛才驚魂未定的心,也逐漸平緩下來。徐強強說,到前面一個十字路口,左拐,有一個老字號面館,吃口回勺面吧,那個飯館的回勺面,你們是不知道,可好吃了。他這么一說,我們還真的餓了,都說好主意。其實,這主意并不好,我們好不容易上一趟城,最希望的是,徐強強帶我們下一次大飯館,多點幾個菜,來瓶酒更好,但我們都清楚,我們的兜里,湊起來的錢也就能吃口回勺面,甚至,都不能要大份兒的。
十字路口寬闊,那時的交通信號燈還不怎么靈光,交警也沒那么敬業,人們也就不那么認真遵守交通規則,不管湊不湊夠一伙,亂走一氣。在花里胡哨的人流中,一個殘疾少年坐在路邊,面前擺了一攤報紙,他半身抽搐著扯了嗓子喊,下周電視報,下周電視報!看上去應該是小兒麻痹導致的后遺癥,身體蜷縮著,臉都變形了,他每喊一聲下周電視報,好像都從肺里掏出來的聲音,凄慘無比。但人們似乎沒有多少同情心,看殘疾少年一眼的多,真正買的人卻沒有。我們走過他身邊時,這個殘疾少年盯著我們喊,下周電視報,下周電視報!我有點心軟,看不下去這種場合,準備掏錢買一張,盡管我買了也沒用,我們的宿舍里沒有電視,廠里只有一臺舊電視,還是每個星期六日,在食堂里放,人們就像看電影一樣,前擁后擠的。在我掏錢之時,一個衣著時髦的小伙子,滿嘴酒氣,搶在我前面,彎腰抓起了一份報紙,迅速掃了幾眼,嘴里罵罵咧咧,不知道在罵誰。那殘疾少年趁機朝他喊,下周電視報,下周電視報!這少年的聲音實在難聽,仿佛一只冬天的黑老鴰,詛咒似的從嘴里吐出這幾個字,那個小伙子不快地看了他一眼,把報紙劈頭扔在殘疾少年頭上,罵道,喊你媽的幾嗓子,每天喊,每天喊,嚎喪呢,使勁兒嚎啊!殘疾少年不言語了,那小子看殘疾少年不言語了,抬起一腳,把地攤上的報紙踢亂了,轉身就走,沒想到殘疾少年一把抱住了那個小伙子的腿,繼續扯著嗓子喊,下周電視報,下周電視報,下周電視報,下周電視報!這回,這幾個字是從牙縫里艱難地蹦出來的,路人紛紛回頭,目睹了這一幕,但都怒目而視,不敢上前。
去你媽的吧!額爾敦倉按捺不住他火爆的性子,上前一腳,正好蹬在了那小子的肚子上,那小子咕唧一聲,摔倒了。
敲他,徐強強說。劉二亮上前就拿腳踹,專揀腦袋上,連踩帶踢,我這回不能落后了,也上去照著那小子的肚子,狠狠踢了幾腳,覺得不解氣,又照著這小子的襠部踢了幾下,踢完,覺得腳丫子很爽。
行了,行了,徐強強吆喝住我們,別他媽給踢死咱們還得吃官司。
那小子顯然沒想到我們兩旁外人會出手,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頓暴打,鼻青臉腫地看著我們。徐強強對他說,身上有錢沒?小伙子哭喪著臉說,有是有,不多了。
那就好,徐強強兇巴巴地說,把這堆報紙全買了!
殘疾少年有點發呆,估計是他經常受欺負,從未有人給他出過頭,沒想到今天有人抱打不平,好像古代的綠林好漢再世,話也不會說了,只是呆呆地看著我們幾個。那個挨打的小子,如喪考妣,抖抖嗦嗦從兜里摸出五塊錢的零錢,說就這么多了。
徐強強強迫小伙子買了一沓子報紙,全是同一期的廣播電視報,然后才問殘疾少年,這樣行不,殘疾少年說,買一張就行了,謝謝,謝謝,幾個好漢哥哥。徐強強又問殘疾少年,你叫什么名字啊,殘疾少年說,朝魯巴特爾。徐強強就不再問了,喊了我們,繼續朝回勺面館走去。后來,我又無數次進城,每到這個十字路口,都會看到朝魯巴特爾坐在地上,扯著嗓子喊,下周電視報,下周電視報!他那種小兒麻痹后遺癥的聲音,既恐怖,又凄涼無比。
面館不大,倒也干凈,徐強強要了四大碗回勺面,又特意囑咐來幾頭大蒜。不一會兒,面上來了,滿滿當當的,看著眼饞,我們幾下就劃拉嘴里了。吃完后,徐強強問,怎么樣,我們三個都說,不錯,下次還來。一碗回勺面兩塊錢,徐強強給付了,付了錢,徐強強對劉二亮說,晚上你替我頂個班,我在城里還有事要辦,你們先回吧。
我認為后來徐強強出的那件糗事,貓膩就在他經常讓人頂班里。
第一次我們進城,打了兩架,我們三個回了廠子,徐強強沒回,我們還以為他真的有事,畢竟人家在城里念過大學,難免同學多,有個事也是正常,我們就沒多想,其實不是。回去了我們和曹場長替他請了假,曹禿子礙于路禿子和呂二霞的面子,也沒說什么,反正有人頂班就行。
冬天的時候,徐強強和呂二霞在養雞場辦了婚事,就是那種沒領結婚證的典禮,曹禿子給做的證婚人,養雞場里的人,趁機喝了一天酒,平時是沒有這么充裕的時間的。路長征董事長因為在海南出差,沒時間回來,特意給發了賀信,讓曹禿子給捎了一百塊錢的禮金。不管怎么說,自呂二霞跟隨路長征創業建廠以來,總算解決了個人終身大事,要不,再拖下去,呂二霞不止是大齡青年了,恐怕要超齡。不過,令人蹊蹺的是,從前到后,徐強強的父親一直沒露過面,曹禿子還特意問過徐強強,徐強強一臉輕松地說,父母親早過世了。
養雞場的日子是單調的,呂二霞因為懷孕,已經不上班了,一心一意等待分娩,徐強強幾乎可以說是模范丈夫,白天上班,下了班回去伺候呂二霞,其樂融融。不過,他還是和剛來雞場一樣,老是進城,讓人頂班,徐強強的理由是大學同學太多,事兒也多,我們都說,這家伙的大學同學也夠煩的。一直到來年春天,徐強強迎接到了他人生的第一個重大禮物,呂二霞生了,是個女孩兒。徐強強喜滋滋的,少夫老妻得子,他倆翻了好幾天字典,才算取好了一個名字,徐薇。
帶刺的花兒,徐強強說,他說出這話的時候,嘿嘿笑著。
也許是徐強強話中有話,他和呂二霞還沒等迎來徐薇的滿月呢,趙薇上了他家的門兒。
趙薇是徐強強的對象?這是養雞場的人們聽到的最具爆炸性的新聞。這話是從我口里傳出去的,但我用的是疑問句語氣,我用這樣的語氣,表示我也不大清楚,尚在求證中,我害怕出了事讓我擔著呢。人們就紛紛問我怎么回事,我只好從頭到尾,揀重要的細節說了一遍。我說,那天我進城了,花了八十塊錢,在南門附近買了一輛九成新的二手自行車,騎了回來,和我一起進城的是養雞場的辦公室干事張字,他沒買,是他先騎著車子馱了我,回來的時候,我倆一人一騎,一路說說笑笑。趙薇是我們倆快到養雞場時路上碰到的,我倆在后面,老遠就看見一個黑影,近前了,才發現是一個穿了一身黑連衣裙的美女,披肩發,臉白白凈凈的,個子不算高,風一吹,好像有點弱不禁風的樣子,怎么說呢,就是那種你看一眼就會憐惜的人兒。我那時當然不知道她叫趙薇了,是她上了我的車子后,告訴我的。我和張字到了趙薇身邊,張字故意騎得很慢,和趙薇搭訕,到哪里去呀,趙薇說,到養雞場,張字問找誰,趙薇說找徐強強,張字說你叫啥名字,趙薇說她叫趙薇,張字說你找徐強強什么事,趙薇說她是徐強強對象。張字聽趙薇這么一說,就不再問了,湊到我身邊說,徐強強麻煩來了,我趕緊回去報信,剩下的你對付吧。張字一溜煙兒騎著車子跑了。
我是馱著趙薇回到養雞場的,不知道的人,還以為趙薇是我的女朋友呢,其實是我看她可憐,或者說,我還有其他心思,這個不太好往深了說。我騎得很慢,路上故意東拉西扯一些不著四六的話,以拖延時間,凡是趙薇問到徐強強的情況,我全用我是新來的搪塞了她。看得出來,趙薇是個善良的女孩,估計是徐強強這個不要臉的孫子,騙了人家的感情和身體。至于徐強強啥時候騙的,這我就不知道了。
張字跑到門房,慌里慌張和徐強強說,你女朋友趙薇來了。徐強強一聽就慌了,問張字,你咋知道的。張字說,老趙馱著趙薇在后面,馬上就到,你別問了,躲躲吧。徐強強嚇得差點尿了褲子,囑咐張字,這事千萬別讓二霞知道,我藏個地方,你們盡量把那個女人打發走,什么辦法都行,總之讓她走,就說我不在這兒。張字是在趙薇走進了徐強強的家門時,和我說的,他說徐強強臉色都變了,仿佛跑得比狗還快,躲到蛋雞車間了。
這下完了,都讓尋上門了,我說。
可不是,還讓我想法兒打發走那個女的呢,張字說,怎么打發,總不能打她一頓吧?
趙薇的到來,讓呂二霞好不尷尬。呂二霞是個善良的女人,平時一直是我們雞場年輕人的好大姐,她正在月子地里,不速之客不請自來,而且是尋男朋友的,這個男朋友還是她男人,簡直就是天大一個笑話,事情來得突然,一下沒了主意。我們平時和徐強強關系好,就都進了徐強強的家,看事態怎么發展,我和額爾敦倉說了,這女的要是胡攪蠻纏,不行咱們就來硬的,把她架走。額爾敦倉想了一下,說要不要征求一下徐強強的意見,我說征求個球,都火燒眉毛了,額爾敦倉看我這么堅決,就握了一下拳頭說,行。
趙薇倒也沒怎么鬧騰,她進了徐強強的家,看見床上坐著一個面色蒼老的女人,懷里抱著一個吃奶的娃娃,家里一股濃重的尿臊味,就問,這是徐強強的家嗎?呂二霞說是啊,你是……沒等呂二霞問,趙薇又問,你是徐強強什么人?呂二霞說,我是徐強強他老婆呀,你是……話音未落,趙薇當場哭暈在地。
我給額爾敦倉使了一個眼色,額爾敦倉兇神惡煞地走上前去,一把挽住了趙薇的胳膊,厲聲喝道,你什么人啊,連個記也沒登,就擅自闖入廠子,這要出了事兒誰負責,來,來,到門房登記去。那時候趙薇已經癱軟成一攤泥了,稀里糊涂被額爾敦倉和我架到了門房,放在長條椅子上。看到趙薇略微緩和過神來,額爾敦倉說,妹子,剛才對不起啊,我們也是沒辦法,徐強強他老婆剛坐月子不久,怕你沖了人家,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大家都不好交代了;我和徐強強是好兄弟,你有什么話,給我說,我去給你轉達?
叫他過來,趙薇抹著眼淚說。
恐怕來不了了,聽說你來了,他早嚇跑了,額爾敦倉說。
騙子,大騙子,你們男人就沒有一個好東西,趙薇嚎啕大哭。
怎么扯到我們身上來了,額爾敦倉撓了撓頭,嘟囔道,我又沒騙你。
一直到晚上,趙薇還看不到徐強強的影子,在眾人的勸說和威脅下,才算止住了哭鬧,憤憤地丟下了一句,告訴徐強強,誰也不是好欺負的,有他后悔的那一天,走了。走的時候,還是我騎了剛買的二手自行車,把趙薇馱上,馱到了公路邊,等最后一班進城的班車。我在路上和趙薇說,咱倆都姓趙,五百年前是一家,看在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份上,我就多一句嘴,這人啊,得自個兒珍惜自個兒,徐強強已經結婚了,就是個二手男人,就像我這剛買的二手自行車一樣,不值錢了,你要看開點,天下好男人多得是。開始趙薇還聽我的,等我說到二手的字眼兒時,突然,趙薇跳下了車子,一言不發,朝公路走去。我怕有啥閃失,就推了車子,陪著她走到公路邊,直到來了一輛擠滿了人的班車,趙薇上了班車,始終沒再和我說一句話。
我回去后,把情況和徐強強說了,徐強強正蹲在他家地上,手抱著頭,聽呂二霞抱著孩子哭哭啼啼數落他呢。這個時候,我覺得呂二霞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趙薇根本不是。但呂二霞太過善良,在徐強強聲淚俱下的懺悔后,原諒了他這一次,絕不允許下一次。
我的天,事后我們回味起來,說好在那天曹場長不在,上城開會了,要不,徐強強這小子麻煩了。也就是第二天,張字來到保衛科,陰陽怪氣地對徐強強說,你他媽真走運。
感謝弟兄們掩護,徐強強呵呵笑著說,給每人遞了一支煙。
曹禿子一回來,徐強強主動去曹禿子那里說明了情況,承認了錯誤,寫了檢查,曹禿子念他初犯,加上呂二霞也沒深究,饒他這一回,這事兒就算暫時過去了。這事兒一鬧,徐強強還沒滿月的徐薇名字就得改了,徐薇是堅決不能叫了,一叫就會讓人想起趙薇,呂二霞這回不查字典了,她把中外電影女明星的名字寫滿了一頁紙,從里面尋中意的,最后,她發現嘉寶這個名字不錯,外國有個大明星叫嘉寶,長得美不勝收,所以,她姑娘的名字就叫徐嘉寶了。
徐嘉寶的滿一百天喜酒還是要喝的。那天,徐強強和呂二霞簡單擺了一桌,叫了曹禿子,還有幾個平時的死黨,吃喝了一頓。酒席上,曹禿子突然問徐強強,最近還讓人頂班不了?
徐強強一怔,馬上諂笑著說,不啦,不啦!
徐強強最后一次接到趙薇的信,是在他剛給徐嘉寶過完一周歲生日的前三天。那封信我幾乎都能背下來,因為很短,信是這樣寫的:
徐強強,我最后一次叫你親愛的,我這樣叫你,是因為我不是死死抓住回憶不放,其實我早已放下了,我如果不能痛斷肝腸的放下,就等于我自己和自己過不去;我現在就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紙糊的,飛上了天,突然下起了暴雨……親愛的,你的寶寶在我肚子里,我將來如何和他說他的父親長什么樣,住在哪里,活著還是死去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私拆他人信件實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更甭說違法了。也難怪,那個時候的人們,都好像法律意識不強似的,獵奇心理都挺強,郵遞員送來這封信的時候,是劉二亮值班,劉二亮起先拿著徐強強的信,看著上面娟秀的字,和我說,肯定是一個女的。我那會兒沒事老往門房跑,見劉二亮這么說,好奇心上來了,說拆開瞧瞧寫的什么?
拆別人的信犯法,要是讓徐強強知道了,就更麻煩了,劉二亮也想看,但是他找了托詞。
看完再粘住,我說,我有經驗,放心。
我小心翼翼拆開了信,看了一遍,信紙上還有淚痕,看來是含著淚水寫的,悲傷過度,連名字都忘了署。我看到最后一句,你的寶寶在我肚子里,我將來如何和他說他的父親長什么樣,住在哪里,活著還是死去了,我有點害怕了,和劉二亮說,趕快給我從你牙縫里掏點飯垢,粘好了,給徐強強送去。
放屁老是蹦出屎來怎么辦?
徐強強的答案是,找個橛子塞住了。
為什么好馬不吃回頭草?
徐強強的答案是,回頭草都讓馬拉的屎蓋了,吃個球。
要是這么問下去,估計我們就瘋了,但徐強強就這么粗俗這么幽默,而且小姑娘們都喜歡他這么粗俗這么幽默。我們平時總是讓徐強強傳授一點勾引小女孩兒的技術,徐強強先給我們傳授的就是這些,徐強強說,你看上去小姑娘家家的,其實滿肚子壞水兒,你要是不壞,她都看你不是男人;所以,你回答小姑娘的問題,必須出其不意吸引她,不然,就沒意思了。
我是對這一套撩女人的歪理邪說嗤之以鼻,但額爾敦倉卻當了真。他決定和廠里的其他女工如法炮制徐強強那一套。有個女的叫劉金梅,長得小眉碎眼的,白白凈凈,很耐看,性格也好,就是瘦,胳膊,大腿,腰,刀棱刀棱的瘦,大概連五十斤也不到的樣子,走起路來,風一吹,差點吹倒了。額爾敦倉不知從什么時候,就看上了劉金梅,老是找機會搭訕,但劉金梅并沒有表現出對他很熱情的態度,當然也沒表現出對他冷淡的樣子,這讓額爾敦倉拿不準劉金梅的心理,只能沒話找話的東拉西扯。
哎,額爾敦倉,城里有賣增肥藥的沒,吃點啥東西能補補?
額爾敦倉說,找個馬蜂窩,越大越好,把你的細手伸進去,攪和兩下,哈哈,用不了一分鐘,我保證你肥得,連你媽都認不出你來。
哎,額爾敦倉,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他爸是鄉長,他叔叔在公安局工作,舅舅在畜產公司當經理,我該怎么辦?
額爾敦倉說,按說條件是真不錯,不知道你打算跟哪個結婚呢?
啐,劉金梅狠狠啐了額爾敦倉一口唾沫,什么東西,跟人掉四六句,劉金梅翻著白眼,不理額爾敦倉,扭身走了。
額爾敦倉和徐強強說了他的遭遇,徐強強和劉二亮差點笑疼了肚子。徐強強說,記住,要跟城里的女孩兒玩兒粗的,和鄉下的女孩兒玩兒雅的,連這也不懂。
過了一陣子,額爾敦倉還是沒談上一個對象,走起路來很沮喪,他沒事便往門房跑,纏著徐強強給他教點真技術。徐強強一開始煩不勝煩,和額爾敦倉說,這事得自己悟,教是教不會的,徐強強給他舉例子,你問一下咱們廠里找對象的,哪個是教會的,還不是自己琢磨出來的,記住,一要膽子大,二要臉皮頑,三要功夫纏,這三樣基本功你具備了,絕對包你搞上女朋友。額爾敦倉聽了似懂非懂,點點頭,走了。
養雞場的宿舍一共有兩排,我在后排,額爾敦倉在前排,相距不過十五米。宿舍旁邊是一個小樹林,風一吹,嘩啦啦響,據說曾經死過人,是個墳場,聽說早些年有一個什么兵團操演,臨時駐扎過一段時間,兵團撤了,留下了宿舍,我們住的宿舍就是當初兵團留下來的。雖說現在根本看不到任何一點墳墓的跡象,但一說起來宿舍挨著墳場,人們的頭皮還是有點發麻,尤其是晚上,女工們根本不敢出去,即使有膽大的男工,進了樹林里拉屎,也要叫喚上一個同伴,畢竟心底有鬼。但額爾敦倉不怕,也不是額爾敦倉不怕,那天夜里他拉肚子,出去了好幾趟,還是不行,他不好意思叫一個伴兒,就自己一個人去樹林里拉屎,最后一趟,總算拉干凈了,照額爾敦倉的說法,再拉就該往出捋腸子了,肚里一點東西也沒了。
早晨起床的時候,宿舍里的人都起了,惟獨額爾敦倉還躺著,哼哼唧唧的,有人問他怎么了,他說,給我把徐強強叫來,啥也別說,叫來就行。那人就給他叫徐強強了,徐強強那天夜里值夜班,本來下了班要去睡覺,但一聽額爾敦倉叫他,就揉著眼皮過來了,問額爾敦倉發什么羊角風。
你看我這是怎么了,額爾敦倉拉下褲衩,露出了一根碩大無比的肉棒子給徐強強看。
咦,徐強強驚訝得睜大了眼睛,你這,你這,和鎬把那么粗,你干什么了?
徐強強后來和我講起額爾敦倉的老二變粗時,笑得腰都彎了。
徐強強就是這樣,他總是避重就輕,不講他和額爾敦倉是如何進了派出所的,而是東拉西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兒,大講特講了一番他如何拉著額爾敦倉,去醫院咨詢額爾敦倉陰莖變粗的傳奇。其實他們還有事瞞著我,也瞞著雞場的很多人,特別是他老婆,但即使他不講,我也知道他們發生了什么事。
返回來說額爾敦倉的事。額爾敦倉的老二莫名其妙的又粗又紅,嚇得額爾敦倉叫了徐強強給瞧,問怎么了,徐強強也不知道,問他是不是和人交媾了,額爾敦倉說沒有,徐強強又問他是不是手淫了,額爾敦倉說也沒有,就是夜里出去到小樹林拉屎,拉到第五趟時,回到宿舍就變成了這樣。徐強強對小樹林過去是個墳場略有耳聞,但他不敢確定,試探著和額爾敦倉說,那是個墳場啊,是不是你拉人家死人的頭上了,中了陰風?
沒有,我是溜著墻根兒走的,額爾敦倉說。
那得趕緊去醫院,徐強強說。
徐強強就拉著額爾敦倉去向曹禿子請假,說額爾敦倉有急事需要請假。徐強強說話的時候,額爾敦倉總是一只手捂著襠部,額爾敦倉的這個動作,讓曹禿子看了很不爽,認為額爾敦倉有侮辱他的嫌疑,就不準假,非要額爾敦倉說出個所以然來,否則,乖乖回去上班去。
他媽的,這段時間人們盡是請假的,曹禿子氣哼哼地說。
沒有辦法,徐強強沖額爾敦倉使了一個眼色,額爾敦倉放開襠部,把昨夜他拉屎的事兒講了,曹禿子滿臉驚訝,連問還有這等事兒,他媽的,老子也是經常半夜拉屎,看來得多走兩步到廁所,野灘樹林子里拉屎真不保險。說完,曹禿子摸了一下自己的禿頭,就準了額爾敦倉的假,最多兩天,也準了徐強強陪著額爾敦倉去,不過要求徐強強把頂班的事安排好。徐強強唯唯諾諾,說沒問題,我老干這種事,保準萬無一失。
徐強強就領著額爾敦倉進了城,到了南門一個社區門診里面。門診里好幾個人,都閑著,看起來沒什么事兒,徐強強領著額爾敦倉湊到了一個略顯得年長的一個大夫面前,是個女大夫,問,這兒誰是大夫,那女大夫奇怪地看了他倆一眼,說這兒都是大夫,你看什么?
看看他的那個,徐強強說。
哪個?女大夫莫名其妙。
那個……徐強強沒憋住笑了起來。
女大夫頓時明白了徐強強說的那個是什么。
起什么哄來了,嗯?女大夫非常生氣,厲聲問徐強強,耍流氓是不,到哪兒耍流氓來了?
是真的,是真的,沒起哄,說著,額爾敦倉解了褲帶,要給女大夫往出掏家伙。
女大夫大驚失色,起身就跑,額爾敦倉頓時手足無措,徐強強突然明白了什么,拉了額爾敦倉就走,對著滿門診面面相覷的男女白大褂說,不看了,不看了。
徐強強拉著額爾敦倉出了社區門診,一時不知道該往哪兒去,就漫無目的地走著。快中午的時候,徐強強說,有了,我知道怎么治你的病了,先吃飯。額爾敦倉也就隨了徐強強,到了一家雜碎館,兩人每人要了一碗羊雜碎,徐強強特意囑咐老板,多加點香菜。
吃完羊雜碎,徐強強問額爾敦倉,感覺怎么樣,額爾敦倉說,舒服多了。徐強強給結了帳,出了雜碎館,徐強強和額爾敦倉說,我知道怎么治你這個病了,你不是腫了嗎,你這個腫是因為常年沒有女人憋大的,得放一放勁兒,我有個消腫的方法。額爾敦倉問,怎么消?徐強強詭秘地一笑,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額爾敦倉不知道徐強強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就又跟了徐強強,到了一間沒掛牌子的小旅館里。徐強強先讓額爾敦倉坐坐,他一個人找老板嘀嘀咕咕了一氣,老板看上去五十來歲,卻是一副猥瑣相。忽然,額爾敦倉被徐強強和老板的大笑聲驚了一下,他有點暈頭轉向。
跟我走,上二樓,徐強強和額爾敦倉說。
上了二樓,老板給徐強強和額爾敦倉開了一個房間,開完房,老板對徐強強擠眉弄眼地說,等會兒,馬上就到。老板一走,額爾敦倉問徐強強,等什么,徐強強說,一會兒就知道了,給你消腫。
怎么消?額爾敦倉問。
來,我告訴你啊,徐強強說,把牙膏取了,快啊,沾上水抹你那個玩意兒,你知道為什么嗎,我上大學學過這些東西,牙膏是用來減低敏感度,延長摩擦時間的,牙膏里有一種成分叫摩擦劑,說了你也不懂,就是五種化學元素組成的:碳酸鈣,磷酸氫鈣,焦磷酸鈣,水合硅酸,氫氧化鋁,絕對無副作用,我用過這個法子,我們同學都用,絕對好使,我讓老板給你叫了一個女的,歲數多少有點老,你一會兒和她干那事,記住,要狠狠干,泄了你的火,你那家伙就消腫了。
哎呀,這么回事啊,額爾敦倉激動地說,我沒干過那事啊,有點不敢。
怕什么,徐強強鄙夷地說,試過就知道了,妙不可言!
額爾敦倉遲疑了一下,就取了旅館里的一次性牙膏,擠了,果真抹了龜頭,涼颼颼的。額爾敦倉說,真要好使,就省了看大夫的錢了。
后來發生的事是曹禿子去派出所交了罰款,領了徐強強和額爾敦倉回到雞場,看表,已經是夜里十一點了。
作為一廠之長,曹禿子對徐強強和額爾敦倉干下的齷齪之事大為光火。丑事一樁,又沒法大肆宣揚,曹禿子只是和幾個環節干部講了,給各個車間的主任們重點強調了一遍,管住自己的人,管好自己的人,管牢自己的人。
但沒有不透風的墻,馬上,徐強強和額爾敦倉合伙嫖娼的事兒傳遍了養雞場。消息起先是從辦公室干事張字那里出來的,張字和我說了,我和別人說了,別人又和別人說了,這事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好像只有呂二霞不知道,因為誰也不敢和呂二霞透露,怕透露給了呂二霞,會出人命。其實呂二霞啥都知道,只是,她啞巴吃黃連,沒法張口說了。
曹禿子處理起人來,一般還是不手軟的,額爾敦倉被立馬開除了,徐強強停職,留廠察看。額爾敦倉不服,問曹禿子,為什么我被開除了,徐強強沒被開除。曹禿子說,因為派出所的說,他們進門的時候,你在女人的肚皮上趴著,徐強強在一旁觀看,所以,你的罪比徐強強嚴重。曹禿子這么一說,額爾敦倉就沒話說了。
這事兒過了大約三個月吧,呂二霞看徐強強坐下也不是個事兒,就和路長征開口求職,路禿子說,讓他去車隊吧,正好車隊缺人。路禿子說得沒錯,雞場飛速發展,購買飼料等亂七八糟事兒是個問題,什么玉米、麩皮、骨粉、魚粉、豆餅等等,什么氨基酸、維生素、獸藥等等,什么設備、機械等等,不在一個地方,分散在各處,車隊也逐漸龐大起來,司機就成了人人羨慕的寶貝職位。呂二霞挺滿意,就讓徐強強去駕校學車,還給他拿了錢。
很快,徐強強就有了駕照。我問徐強強,哪個駕校學的,半個月就拿上駕照了,徐強強得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學什么學啊,內部有人,買的。
開始,徐強強跟了公司車隊的一輛車學,他師傅劉永旺,是個老油條,又很懶,教他的時候很不耐煩,指給了徐強強一個訣竅,永遠,永遠,永遠,及時踩剎車。徐強強的悟性很高,盡管司機師傅很懶,他卻勤快,沒多久,車就開得很溜了,那種大頭綠皮老解放,跑起來塵土飛揚。車開溜了,人就容易得意忘形,以前不喝白酒的徐強強,居然也學會了喝,因為師傅劉永旺好這一口。
老趙,哪天我拉上你兜風,徐強強說,保準你舒服死。
還是算球了,我說,額爾敦倉他媽的跟你舒服,被開除了,跟上你,我發現沒好。
哧,徐強強就不理我了。他找劉二亮,劉二亮喜歡車。
還真是,劉二亮看徐強強開車很威風,也動心了,就買了一瓶酒,一包煙,偷了一個燒雞,去賄賂徐強強,讓徐強強教他。徐強強也沒客氣,喝了劉二亮的酒,抽了劉二亮的煙,吃了劉二亮的燒雞,就教了劉二亮一晚上,劉二亮基本算是掌握要領了,但還不熟悉,徐強強說,等我哪天有空再教你,這車啊,就像女人,你得調教好,她就聽你的了。
徐強強說是說了,但是,他恐怕永遠也不能再教劉二亮了。我最后一次見徐強強,是在城里的大南街烤鴨店,他拉了我,劉二亮,不知怎么回事,還有被開除的額爾敦倉,還有他們車隊的兩個人。
那天下小雨,淅淅瀝瀝沒完沒了,車隊沒活兒,徐強強嚷嚷著要請客,說他媽的跑了河北河南一個多月,想死弟兄們了。徐強強這人,你和他處,開始有點離不開他,時間長了,你又怕和他在一起,心里作祟的緣故,他老是捅婁子。就說他開車吧,不到半年時間,就撞死過一頭豬,偷跑不及,被豬的主家喊人連揍帶訛詐,還有,他開車栽到馬路下面兩次,差點出了人命,還有,他的車上過一次樹,人們坐他的車,一般都膽戰心驚的。但額爾敦倉不怕,額爾敦倉說,這叫藝高人膽大,只要不撞死人就行。
我就罵額爾敦倉,你他媽這么攛掇徐強強,非害死他不可。
那天,我們喝了不少酒,散攤兒的時候,我說,強強不能開車了,喝得太多了,別他媽出點事兒,把你工資和獎金扣完。徐強強說沒事,他還踢了一個飛腳,看,我沒事兒吧,穩當,我們練過武術的人和你們不一樣。他們車隊的那兩個司機合伙開的一輛車,一轟油,走了。我和劉二亮要回養雞場,徐強強要送,我說算球了,我們騎著自行車。徐強強說,那我送額爾敦倉吧。我說,你路上盡量慢點。
我和劉二亮返回養雞場的路上,小雨住了,這天夜里,街道上的雨積水退得很慢,閃著死寂寂的光輝。我估計徐強強也回到他們車隊宿舍了。
實際上沒有,我估計錯了。第二天,廠里就傳出了徐強強的消息,徐強強殺人了。
這消息太震耳欲聾了,震得排排雞舍都直發抖。我拼湊了一下各種大道和小道消息,簡單整理了一下,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我們昨晚喝完酒后,徐強強開車送額爾敦倉,回他租住的北沙梁村時,路過小南街,小南街比較窄,不如大南街寬敞,徐強強扶著方向盤,看見了一個女人,騎著自行車,一只手撐著傘,一只手扶著車把,歪歪斜斜地在前面騎著,速度很慢,但占了馬路中間。徐強強使勁摁喇叭,摁了半天,那女人好像沒聽見似的,理都不理,徐強強罵了一句,就猛打了一把輪兒,想貼著那女人過去,沒想到,貼得太近了,把那女人卷車轱轆底下了。街道如同荒涼偏遠的草原一樣寂靜下來了,路燈上空是陰森可怕的天幕,這下,徐強強和額爾敦倉頓時酒醒了,出了兩頭汗,趕忙下車,到車輪底下,往出拉那女人,拉出來一看,是個孕婦,身上全是血,鼻孔里還有氣息,兩人慌忙把那女人架到車樓里,風馳電掣般趕往附近的醫院。到了醫院,徐強強正準備往下抬那個孕婦,額爾敦倉說了一句,好像沒氣了。徐強強一聽額爾敦倉說沒氣了,當時就傻了,問額爾敦倉咋辦,額爾敦倉想了想說他也不知道,就丟下徐強強一個人溜了,臨走前,額爾敦倉做賊似的說他啥也沒看見。徐強強看額爾敦倉一走,又看了一眼仿佛死去的孕婦,再往醫院周圍張望了一下,應該沒人看見,徐強強踩足了油門,向荒野馳去,到了一座橋梁邊兒上,看四下無人,徐強強停了車,跳下來,把孕婦拖到了橋底下,回車取了裝汽油的塑料桶,里面足有二十五公斤汽油。
我是這樣猜測的,在寂靜得令人恐怖的夜色里,熊熊大火仿佛暴風雨發出的死亡詛咒,照亮了徐強強那張慘白的臉。
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