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喜福會》到《女勇士》的雙重文化認同
■王 丹/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
20世紀初,歐美等西方國家由于率先實施了工業革命,其發達的科學技術不僅為帝國主義展開殖民侵略提供了堅船利炮,同時也為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在思想文化領域,西方社會所盛行的自由民主之風,吹至東方這塊古老的大地,在中國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開啟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
隨著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國深陷戰爭泥潭。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戰火從未間斷,國內生靈涂炭,人民處于民不聊生的慘境。在這樣特殊的的歷史背景之下,有的人被迫逃離這片生活了世世代代的土地,忍痛拋下一切,不顧前路的危險與艱難,用對生存的執念在另一片大陸上開辟出新的天地。
1848年,美國加利福利亞州金礦的發現所引發的淘金熱導致了勞動力嚴重不足。任勞任怨的的華工在這里終于尋找到了工作機遇,勤勞樸實華工的大批涌入美國,成為當地勞動力市場不可或缺的力量。
譚恩美與湯亭亭均出生于加利福利亞州,她們本人有著第三代移民的身份。而加利福利亞州的移民問題在美國歷史上是最早出現的,其反映的移民矛盾也最具代表性。華裔美籍作家譚恩美的《喜福會》與湯亭亭的《女勇士》均關注到了在這樣特殊歷史時期的本國移民,特別是女性移民在美國的生存處境與心靈困境。
譚恩美與大冢茱莉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度,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把加利福利亞州作為小說的發生地,既是出于對歷史事實的尊重,也與兩位女作家個人的成長經歷有關。生長在移民聚集地——加利福利亞州的生活經歷,影響了兩位作家在創作時對故事發生地的選擇,歷史的真實性與文本的真實性得到了由內而外的嵌合。
就中國知網上所收錄的論文數量來看,研究《喜福會》與《女勇士》的論文多達千余篇,而在這些論文中,其研究類型又大致可分為五種:(1)低語境下的母親與高語境下的女兒之間的關系;(2)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解析文本的藝術價值;(3)在兩代人的矛盾沖突中揭示東西方文化差異;(4)對中文譯本的翻譯研究;(5)電影改編。而對《女勇士》的探討,還多了對東方神話傳說的變形研究的研究層面。
譚恩美(1952— ),1952年出生于美國加利福利亞州的奧克蘭。祖輩父輩均是中國移民,她本人則是在美的第三代移民。1989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喜福會》,在1991年獲美國最佳小說獎。故事主要講述的是母女間的代溝和隔閡沖突,反映了華裔母族文化和異質文化相遇而生的碰撞與兼容以及兩種文化在碰撞中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追溯。
湯亭亭(1940— ),祖籍廣東新會,1940年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1962年畢業于伯克利加州大學英國文學系,1992年被選為美國人文和自然科學院士,2008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杰出文學貢獻獎。
湯亭亭出版于1976年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也即本文的研究對象之一《女勇士》,在美國名噪一時,確立了她的作家身份。小說分為這五則故事:《無名女子》、《白虎山學道》、《鄉村醫生》、《西宮門外》、《羌笛野曲》,分別講述了其自身或其家族的特殊經歷。在論述其家族在中國的過往歷史時,對神話傳說的移位與變形頗具浪漫瑰麗的色彩,引發了廣泛的探討。而在論述自身或其家庭在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文化碰撞問題時,也充斥著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強烈危機與自身文化歸屬的困惑。
《喜福會》中的人物,大約于20世紀40年代移民到美國。華人的社會地位還不太高,她們的生活境遇并沒有當初自己所期待的那樣美好。小說中母親們生活條件都不甚優渥,有時甚至還要通過購買二手物品和做零工才能勉強滿足生活所需。譚恩美對筆下她們的生活際遇描寫,真實反映了華人在美國的處境。
《女勇士》中的人物雖然均以古老中國的典型女性形象為原型,卻也隱射出中國移民在美國受到的壓迫與不公。那種由于異質文化的不相兼容性所造成的“隔”,在作品中無處不在。盡管湯亭亭是以特別具有中國古典特色的故事來敘事行文,實質上卻反映出美籍華人當時處境的壓抑、隔絕、不安與貧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喜福會》與《閣樓上的佛像》均是用英語創作的移民小說,她們在題材擇取方面具有極大相似性,且作品在美國均引起強力反響。她們都關注到了本國移民在美國社會的生存境遇,進行了文化溯源,既追慕母族文化之“根”,同時又反思了中西方文化差異。
兩位作家均通過異語創作的小說詳細介紹了獨具本國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內涵,向美國社會傳達出了真正典雅的東方之美。如《喜福會》的題名,是母親們麻將聚會的名字,本可一筆帶過,但譚恩美卻仔細介紹了“喜”有“歡樂”之意,“福”有“幸運”之意。并把中國人好在牌桌上“討口彩”的習慣用英語娓娓道來,向美國讀者傳達著濃厚的中國情調,反映著中國人獨有的文化趣味。《女勇士》中通過對古老中國神話的移植,雖然加諸了湯亭亭對這些神秘故事的主觀想象,但這五則人物故事依然具有濃厚的中國情調。
另外,從兩篇小說的敘述視角來看,兩位作家主要是以第三人稱的女性視角來進行敘述的。《喜福會》里,分別采用四對母女的眼光來敘事行文,通過兩代人在相異環境下的成長與婚姻中的種種矛盾糾葛細致而又深入剖析了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女勇士》中,五則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傳統中國女性的代表。通過深受美式思想影響的“我”,來看深具古典特色的中國往事。期間夾雜的瑰麗想象與荒誕的敘述,都是在以一種女性旁觀者的身份對無法理解的傳統文化進行主觀臆測式的解讀。這種帶有理解偏差的解讀顯然是因為東西方異質文化中的阻滯點造成,從側面反映出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巨大差異。
這兩部小說在歷史背景、作者個人經歷、文學題材及敘述視角等方面的的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們具有與真實的歷史之間存在著的特殊關系,期間交織著作家經歷加諸作品時的所產生的身臨其境之感,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兩位作家傳達的思想情感與作品中本國移民的心理訴求在精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作品與作家之間的關系由里及外地完美結合使得文本更具張力,故事的發展也就更符合藝術的規律。
在《喜福會》中,母子關系最能窺見中西方異質文化在碰撞中對個人、家庭乃至民族所產生的沖擊。小說中的四位中國母親,是家園的破碎或紛飛的戰火讓她們不得不離開這片生養她們的中華大地,以期求得安寧的生活,可以過自己主宰命運的人生。
如母親吳素云,身心遭受重創的她決定忘記戰亂所帶來的家破人亡的傷痛,毅然赴美開始追求新的生活。小說中雖然并沒有提及后來她初到美國時所經歷的種種,但通過女兒吳精美,我們可以了解到她們在美國的生活并不那么順遂如意。她出于經濟的窘迫,不得不替去做小時工貼補家用。為了讓女兒學鋼琴,決定替老鐘免費做小時工以免去鋼琴課學費。但一場音樂會演出的失敗卻讓她發現:老鐘是個聾子。這也讓有著美式思想:“我就是我,我不是天才”的女兒有了徹底不再練習鋼琴的理由。而一心懷著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想將女兒培養成天才的中國母親吳素云,人生的希望卻落空了。
雖然在女兒篇中,吳精美在母親去世后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決心試一試母親曾期待她學的鋼琴。但是母親與女兒早年間由于文化差異所產生的的隔閡卻永遠無法真正消除。母親對女兒成才的期待與竭力保持自我的女兒之間,因為文化與代際鴻溝,出現了本民族傳統精神在傳承上的斷裂。這種關系的斷裂,可以視為母親畢生心力的付諸東流。
《喜福會》中母女關系由于成長環境的不同所導致的文化隔閡最終在母愛的洗滌之下,恢復到了彼此之間的互相理解,進而達到交織與融合的狀態。這體現在在吳素云與吳精美這對母女的關系上:由于小時候拒絕成為母親所期待的“天才”,她一直不愿意去嘗試母親要她做的任何事,包括學鋼琴,因為她要“做自己”。但是母親去世后她再一次彈琴時卻發現自己的確有一些鋼琴演奏方面的天賦,她懷疑母親早在她叛逆的童年時期就已經發現了這一點,三十六歲的她驚訝于母親對她的了解程度,漸漸明白了早年間與母親的那些爭執背后所代表的中國式的母愛。
而在《女勇士》中,母子之情雖未如《喜福會》那般濃墨重彩地描寫,兩代人卻因異質文化最終走向了隔閡。在“我”對母親吼叫著一口氣說出了10件或12件她以前不敢也不能宣之于口的事情之后,“我”感受到的不是輕松與釋然,而是對母親更深的不解。這種不解不僅是對于母親本人,更是對于母親所作所為背后的文化動因。在這篇小說里的母子關系,以心靈深處的迷惘作結,留下了令人深思的空間。
《喜福會》中母子之間的矛盾最終通過代際之間的真情化解,是以情感的融合瓦解了文化的差異。作者將人與人之間純真的情感作為緩和異質文化矛盾的中介,提出了解決東西方文化差異一種可能的方案,沖淡了東西方異質文化的對立性。
但在《女勇士》中,作者卻將女兒對母親那一輩的不解推向了更深的層面。作為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子女永遠也無法理解那遙遠東方國度的文化精髓。湯亭亭在最后一個故事中以蔡文姬孤獨吟唱那異邦人無法理解的悲歌作結,表達的正是對東西方文化之間“隔”的不可逾越性,突出了異質文化的對立性可能永遠也無法消解。
母子親情本應是世界上最親密的情感。但在東西方的不同文化境遇里,這樣真摯的感情卻經受著考驗。他們都曾因為相異文化的不可兼容性出現家庭的感情危機,這種感情的危機又令他們陷入思索:“我是誰”的民族身份溯源問題。這兩部小說都在情感層面關注到了人對于愛的精神需求,觸摸到了本國移民在艱難的異國環境之下所面臨的共同心靈困境,折射出作品的人道主義的溫情。
在《喜福會》與《女勇士》中,母親們向女兒們傳達民族傳統精髓以期女兒們和自己能達成某種文化共識。但是她們的女兒們由于成長環境和教育氛圍,由內到外地影響到了她們的心理狀態與精神氣質,她們的頭腦里只有最純粹的美式思維。因而,母親們與子女們在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上的關系出現了不可彌合的斷裂。兩位作家共同反映出了兩國移民在強勢的主流文化浪潮與艱苦的生活環境雙重夾擊之下,異族的她們只得靠著各自的努力與人生哲學,艱難地在必須融入但又無法徹底融入美利堅民族的尷尬處境里維持著本民族的精神傳統,深刻揭示出中國移民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艱難求索。
《喜福會》與《女勇士》這兩篇用英文創作的小說,描寫了中國女性移民希冀在美國追求她們在故土尋而不得的美好生活,最終卻由于語言、文化、種族等隔閡,美夢幻滅。盡管如此,這些異鄉人依舊只能在這片對她們可能會永遠陌生下去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正如湯亭亭筆下《女勇士》中蔡文姬在遙遠的胡地低沉地悲歌。這也為英語讀者在心靈層面揭示了在美國的日本移民由于文化差異所導致的真正精神困境,讓更多的美國人看到那個時代日本移民的境遇以及美國主流社會一段過往的歷史,啟發他們思索有關人性與尊嚴等重大命題。
譚恩美與湯亭亭都描寫了本國人民或出于避難求生,或出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約而同決定移民到美國。然而當她們最終抵達未知的大洋彼岸,挑戰卻遠遠多于機遇。兩位作家共同反映出了中國移民在強勢的美國主流文化浪潮與艱苦的生活環境雙重沖擊之下,異族的她們只得靠著各自的努力與人生哲學,艱難地在必須融入但又無法徹底融入美利堅民族的尷尬處境里維持著自身,深刻揭示出中國移民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艱難求索。
生活理想與情感依托本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與精神基礎,但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中國移民面臨著在美國生存與心靈上的困境。兩部小說通過藝術的手法再現了社會歷史,反映出了中國移民既無法完全融入當地主流社會,也無法被當地主流社會徹底接納的現實。揭示了民族身份的相異性則是她們無法扎根于西方文化環境的重要因素,她們尋根于遙遠的母族文化,以期求得自我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的主題。雖然兩部作品在描寫時側重不同,但兩篇小說都通過生存與心靈等問題藝術地再現出民族身份認同在惡劣生存境遇下的人類共同心理困境,彰顯了人性的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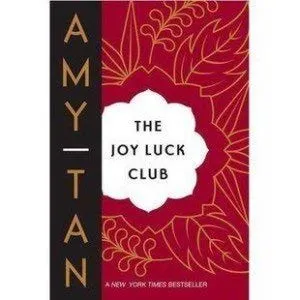
圖1 《喜福會》

圖2 《女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