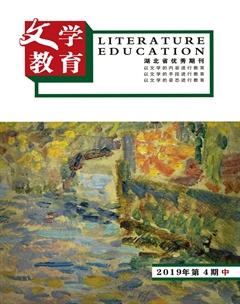作家何存中寫真
劉昕蕾 胡國民
天下著秋雨。秋雨梧桐,楓葉飄紅,滴滴嗒嗒的雨點,與室內鍵盤敲字的響聲,此起彼落,彼落此起,在這樣的環境里寫作,何存中的腦海里的巴河故鄉黃黃的秋草漸漸變成了嫩綠,在巴河岸邊,生出一片一片的鵝黃,春草發芽的時候,他的《農民作家》三部曲之一的《在河之洲》近二十萬字也變成了《芳草》上公開發表的長篇小說作品。
他略微松了一口氣,血脈中奔騰著的那故鄉巴河的濤聲仿佛一片歡騰,他的思緒很快又進入了這部自傳體長篇巨著的下一個激流漩渦,他滿眼是淚……
何存中告訴我,他不論是寫有關故鄉巴河故事的長篇小說《沙街》,還是寫另一部關于故鄉的長篇小說《青禾遍地》,哪怕是筆下有關巴河的短篇和中篇,很多時候隨著人物命運的起落變化,總是禁不住一個人淚流滿面,寫長篇巨制《農民作家》第一部時,更是如此,有時如雨般流淌的淚水就如這窗外的秋雨落在巨大的落地窗玻璃上一般,模糊了他的眼簾,有好幾次我到他的創作室,他的思緒從電腦里走出來,仍止不住淚光閃閃!
他把一生獻給了文學,對文學創作如醉如癡。
存中寫了幾百萬字的以他的故鄉為背景的短、中、長篇小說作品,打動了無數相識或不相實的讀者,我是他的忠實讀者之一。我喜歡他的“巴河系列”。因為那是用生命中最真誠的淚水和心血煉成的那個偉大時代的人生精華和時代巨骨。看了存中的小說,我們就看到了那個活生生的時代,以及那個活生生時代里的眾生,也看到了那個時代的我們自己。
我一直很固執地認為,他的“巴河系列”就是關于那個時代文學化的歷史和史詩化的文學,我讀它們時,既把它們作為當代最為杰出的描寫中國農村的文學作品來欣賞,更是把它們作為斷代史來閱讀,因為那里有活著的當年的那個不能忘卻的年代,還有栩栩如生的我們自己。每次讀存中的作品,我都有一種這樣特別特別的感覺。透過那些文字,我仿佛聽到他的血脈里澎湃著巴河的濤聲!
文學創作到了這個份上,我認為就是最大的成功。那作品無疑也是不朽的,存中雖然得了很多文學創作大獎,長篇小說《太陽最紅》甚至還入圍過茅盾文學獎。這些都是對作家的認可,當然都很重要。但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最重要的還是要過得了讀者這一關,讀者認可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計。
何存中從年輕時就開始搞文學創作,一生就吃文學這碗飯。他是從故鄉巴水河邊寫到縣文化館,然后寫到黃州。浠水是個出文人的地方,歷史上的文人就不說了,近代的就有大詩人、大學問家聞一多,以及新儒學大師徐復觀。
他們都是學貫中西、著作等身、對中國和世界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人物。
論存中的作品及影響,當然也是浠水籍的一個在湖北文學界、以至中國當代文學界很有地位很有份量的作家。不服不行呵,這是個憑數字說話和重事實、講究真憑實據的時代,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動車、高鐵更不是,憑的是硬東西。白說沒人信。存中的文學作品近千萬字,都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由正式刊物和大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的,不是像某些人的自賣或自慰品。
我很佩服存中的文學創作天賦,當然包括他的才氣,但更敬佩他的堅守和毅力。我們那個年代的人,讀書讀到高中就到了頂,上大學是要推薦的,推薦之前還得回農村在爛泥巴田里經受烈日酷暑和雨雪風霜的考驗,接受沒有讀書或根本就大字不識一個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即便經受鍛煉和接受再教育最好,也不一定上得了大學,進得了工廠,還要看你的“背景”和身后“靠山”的硬度。
那時有點理想的年輕人,不少是走寫作曲線“跳農門”這條終南捷徑的。我常想,那是我們老家浠水有重文的好傳統,為當時無路可走的我輩年輕人打開的一扇通往理想之路的門。前面有魏子良、張慶和、王英、徐艮齋四大在全國全省名氣很大的農民作家給我們帶路。那時,縣里非常重視農民作家隊伍建設,除了縣文化館有農民作者長年輪流值班,不少公社文化站都是農民作者當家,縣直部門也千方百計到下面農村挖能寫作的年輕人。一些在《湖北文藝》和《湖北日報》發表了文藝作品的文學青年還能夠直接成為武漢各個大學的工農兵學員。
前提當然是要能寫,還要有作品!
存中就是那時到縣文化館的,逐步由一個農民作者成長為文化館的專業文化干部。跟存中一樣寫出了“農門”的還有郭強昔等一大批業余農民作者,他們后來都轉成了國家專業文化干部,吃上了讓人羨慕的商品糧,拿上了國家每月發的工資!
但從那個時候一直寫到現在,而且寫出了名堂,整個浠水只有何存中一人!
這就是存中的與眾不同和不同凡響的地方!
無論是歷史,還是時代,成就一個人,環境雖然很重要,但那只是外在條件,最重要的還是靠內在的動力,當然還有不可缺少的才氣,你不是作家的料,霸王硬上弓也不行。這也是何存中讓人敬佩的地方。
我們和存中曾經都是那個時代的人,當時作為比較冒尖的業余農民作者,經常一起出入于我們心目中最神圣的文學殿堂一一浠水文化館《浠水文化》編輯室,他那時的文學創作才華就開始展露,在浠水曉有名氣。他發表在《浠水文化》上的一些泥土味十足的詩和小戲,充滿了靈氣。我是個地道的農民,看了他的作品,感覺總是水靈靈的,讓我聯想到我家菜園里清晨陽光下灑滿了露水珠的那些生機勃勃的時蔬,很是惹人憐愛,讓人很有“食欲“。說句實話,那時我輩中的很多像他一樣對文學充滿超極熱情、懷著文學大夢的青年文學才俊并不少,好像是人人都抱有荊山之玉,個個都操著靈蛇之珠,大家在浠水文學創作的海洋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也許文學創作的殿堂太苦,也許還有些寂寞,很多人功夫不夠,在這個神圣清靜的殿里都沒坐住,漸漸被文學女神淘汰出局。存中卻憑他的自信和優雅,從縣文化館那個對他來說有些狹窄的地方一路寫進了黃州那個屬于黃岡市文聯的鋪滿老石板的小巷深處,那里的隔壁是黃岡最高學府黃岡師范學院,墻內滿滿一篷竹子掩映著文聯二層辦公小樓,我經常去那里看存中,向他索討作品,認為這寂靜的小巷深處幽幽地隱藏著作家的文學夢。認為這里有黃岡的文學奇才。那時在文學界名頭很響的熊文祥先生是這里的掌門人。
存中帶著他的“巨骨”(在他小說創作生涯中有著里程碑意義的中篇小說),來到蘇軾當年生活的赤壁龍王山下,如今一晃二十多年,他的筆下猶如赤壁磯頭滾滾東去的大江,浪濤澎湃,不僅中短篇小說如串串晶瑩剔透的珍珠,不斷給人驚喜,《姐兒門前一棵槐》、《沙街》、《太陽最紅》、《青禾遍地》、《最后的鄉紳》、三卷本自傳體巨著《農民作家》第一部《在河之洲》等六部長篇小說,接二連三連四連五連六、如滾滾春雷不斷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天空炸響,給黃岡文壇增添了一道又一道光彩奪目的亮色!
二〇一六年,他被評為黃岡有突出貢獻的十大名人。
他的長篇小說《姐兒門前一棵槐》被改編成四十集電視連續劇《紅槐花》,在中央電視臺和全國三十多家省市電視臺熱播,創造了不少電視臺觀眾收視率之最,這在黃岡還是頭一回。
我們常常感嘆,為什么浠水當年那么多的年輕文學才俊在最開始的一場爭先恐后、你追我趕的文學創作馬拉松大賽中,最后單單剩下何存中一枝獨秀呢?在前面我對這種現象已提出并進行了初步分析,但與存中的長期接觸與交談中,以下這幾方面應該是最主要的:
一是作為一個作家必須擁有十分豐富的生活經歷。文學泰斗沈從文先生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曾經有不少文學青年向他求教,想當一個像他那樣受讀者歡迎和祟拜的作家,寫出像他筆下那樣的好作品。沈先生不假思索地問,你們經歷了什么?你們頭腦里擁有多少?我當過舊時代的兵,我年輕時就在湘西的大山里進進出出和在湘西的沅江上來來往往,我熟悉那里的風土人情,我的這些經歷你們沒有。所以你們寫不出我的那些小說,也寫不出我的那些散文,因為你們不可能再去經歷一遍我那樣的生活。沈先生的話雖然說得通俗,但的確是至理名言。他自己也有這樣的困惑、茫然和痛苦。那是他在新中國剛成立時,寫了歌頌新北京的作品寄到《人民文學》。以他的名聲,放在今天,不說他那么鄭重其事地向《人民文學》投稿,就是他“沈從文”三個親筆沈體字,許多刊物也要搶著登,但《人民文學》的編輯搖了搖頭后,給他退稿了。沈先生一陣難過之后,最后明白了,他還不了解新北京,更談不上熟悉新北京人的生活;這樣閉門造車、感情用事,縱然是才高八斗,能異想天開,也寫不出真正反映新北京的好作品來。先生后來棄文學而研究中國服飾史,恐怕也有這方面的原因。我由此想到存中從年輕一直到現在年逾花甲,仍然保持著如此旺盛的文學藝術創造力,就不難理解存中的許多作品的風骨里為什么總是飽含著巴河的情愫,包括那山那水那天那地那人那事還有那些河邊迎風起伏的莊稼,即使是反映大別山革命戰爭年代題材的《姐兒門前一棵槐》和《太陽最紅》等長篇巨制,為什么也可以讀出巴河的味道來。我認為,這是存中骨子里最可寶貴的東西,他有,別人沒有,他的血脈里永遠澎湃著的是巴河的濤聲,他作品中的人和事都是有巴水靈性的,都是鮮活的。所以讀起來就有味,就有感覺。
何存中的作品能夠讓人百看不厭,這恐怕是主要原因。因為他擁有別人所沒有的豐富生活經歷。存中生長在家鄉巴水河邊,在那里的生活經歷太豐富了,巴河的故事,巴河的風土人情,巴河的一草一木,都在他心里裝得滿滿的,就像早春積滿了塘堰的春水,直往他筆下洶涌……
何存中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自己生活的底子是生他的巴河土地,滋養他的是巴河那匯聚了千千萬萬的溪流,從大別山流下來的巴河水。巴河有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巴水是他永不枯竭的創作源泉。何存中站在他的心靈高地上,笑看文學創作的一江春水向東流。永遠的巴河,永遠的巴河水,已經在中國當代作家何存中的筆下伴隨他的作品,匯入滔滔中國文學史的長河!這就是作家何存中心中的巴河,心中的故鄉!亦如沈先生與他的故鄉湘西一樣!
二是作為一個作家必須具備才氣。實話實說,僅僅具備豐富的生活經歷,只是具備了文學創作的基礎,只是有了文學創作的源泉,沒有才氣是寫不出好的文學作品的,也成為不了一個出色的作家。何存中是很善于利用他所擁有的巴河這座文學創作的富礦的,什么時候寫那里的沙,什么時候寫那里的山水,什么時候寫那里的莊稼禾苗,什么時候寫那里的早晨炊煙或夜半月色,他都把握得很好,拿揑得很準,寫出來景情交融,就很動人。
再現生活,將生活文學藝術化、文學藝術生活化,是作家的真本領。看存中的小說這種感受猶深,他是深得其中三味的。你看他筆下人間五月巴水河畔那些即將收割的黃燦燦麥子就知道,麥子分明是長在地里的,他卻寫“麥子們一排排在風里站著”,一個“站”字,把麥子活生生寫成了有靈性的人。社員收割麥子他偏不寫收割,他這樣描寫:“那麥們便在社員頭天晚上磨得雪白的鐮刀下一排排倒下。”虛也,實也,這樣的句子,這樣的描寫,也只有存中筆下才有,那是一幅水墨,那是一幅寫真,如此表現力,如此手筆,沒有非凡才氣,談何容易!
遍讀存中作品,這樣的錦言妙句比比皆是,令人驚嘆叫絕不已。這是存中創作生命之樹常綠之所在。
三是一個作家必須具備坐功。當然也包括耐得住寂寞。何存中就有這個功夫和定力。他年輕時寫小說兩天三夜可以不離板凳,現在年事日高,但坐功仍不減當年,他在他的創作室,在微機前,經常是一坐就是一上午,外面的風聲雨聲全然充耳不聞。說來也是令人唏噓,當今社會,紅塵滾滾,功名利祿,聲色犬馬,還有多少人能耐得住這個寂寞,堅守得了文學這一方靜土。存中堅守住了,幾十年青絲變白發,好也罷,歹也罷,甜也罷,苦也罷,晴也罷,雨也罷,就做這一件獨事;無怨無悔地寫小說!這也是他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是一個作家必須充滿生活激情。存中是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情、充滿感情、充滿激情的人。他熱愛生活,熱愛故鄉,對生活對故鄉始終充滿感情和激情。說起他的故鄉,說起兒時巴河邊的事,他便壓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說到動情處常常漲得滿臉通紅,笑出了眼淚。我坐在他的面前,他跟我談起他正在寫作的小說中的人物命運,那個人其實就是他兒時的伙伴,說著說著,他的眼淚就止不住流出來了。而說到人物命運的轉機時,他又止不住心中的高興,開心地大笑起來,笑得那么真誠,見性見情。可以說,他在書中寫了多少人物的悲歡離合,就注定了他有多少喜怒哀樂!
存中除了筆耕不掇以外,平時很注意學習,我們經常在黃州的書店邂逅,每次在書店我們都要買些新書,但他所翻的書和所買的書,都是有關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鮮明的史料性著作,我知道他是為寫作“打貨”備料。與他的交往中,我發現他幾乎不看別人的文學作品,也很少談及別人的文學作品。我后來漸漸悟出了點“門道”。一個成熟的作家,年輕的時候,該看的那些中外文學名著他都看了,文學的底子已經打足了,再多看別人的文學作品,一是沒有時間,更主要的問題是看多了影響自己創作思路,無意中會落入別人的巢臼,影響自己創造性的發揮。為什么在文壇上經常會出現“抄襲”?我想沒有哪個真正的作家“掉渣”會掉到這個絕境,往往是因為看別人的作品看多了,稍不注意,在故事情節的處理,人物的塑造、景物的描寫等方面被別人的作品牽著“鼻子”走了,落入了別人的套路,這樣,“抄襲”之嫌就難免了。一個高明的作家,不僅僅有自已獨立的人格,更有自已與眾不同的獨特創作風格,包括敘事風格、語言特色、表現手法,以及題材和主題的選擇等等。作家的作品貴就貴在“與眾不同”。何存中的作品,無論是短篇、中篇還是長篇,一看語言,就知道是何存中的,看完作品就知道是“何氏造”,獨一無二,但絕對是來自于鮮活的現實,與別人絕對不雷同,不重復,讀他的作品絕對沒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作品就讓人感到新鮮,讀起來就韻味十足。
我曾經擔心存中快把他故鄉巴河的人和故事寫完了,還有那些巴河兩岸迷人的四時風景。深知他的黃岡職院教授南東求笑道:你著這個急,他滿腦子都是巴河的生活,都是有關巴河的事,巴河是他寫作的大富礦,再寫一輩子也寫不完。
存中腳踏巴河三尺硬地,寫作就有底氣,我們期待著他的《農民作家》三部曲早日問世!那中間的巴河故事一定會更多!
窗外的秋雨停了,秋風也住了,金黃的秋葉遍地,雨后斜陽,空氣分外清新。巴河兩岸的農民開始秋收了。存中說,他計劃整理出版《何存中文集》,那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他今年六十五歲了,也在準備他的“秋收”。
血液里澎湃著巴河濤聲的何存中,他的浩大的文學工程中,巴河的泥土芳香同樣會更加濃烈、更加有味!
(作者單位:湖北省黃岡市文廣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