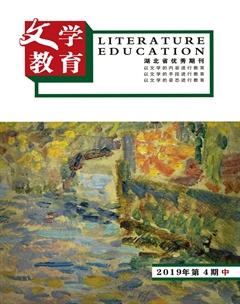《詩經》與《荷馬史詩》中的神話色彩比較
內容摘要:《詩經》與《荷馬史詩》作為中西方文學源頭,內容以詩歌的形式分別記述了我國西周至春秋、歐洲古希臘的社會歷史事實。兩部史詩巨著帶有自然現象的神話人物與傳說是其共同的重要特征。然而因受不同地域文化、自然條件、歷史發展的限制,兩部史詩神話特征也不盡相同,甚至鮮明呈現了各自風格,可比性強。論文通過文獻資料法,邏輯分析法等對它們的神話色彩表現、成因以及本質差異進行比較。研究表明,《詩經》和《荷馬史詩》的神話色彩客觀的展現了中西方早期不同文化與價值的取向,是后世中西兩種文化體系形成的根源,帶有濃郁的神話意義。
關鍵詞:《荷馬史詩》 《詩經》 神話色彩
《詩經》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而成,是我國古代詩歌的開端,在先秦時又稱《詩三百》。它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篇311首(現存305首),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表現手法有賦、比、興。《詩經》反映了其所產生時期的近五百年的社會面貌,被稱之為周代時期社會面貌的一面鏡子,后世大家孟子、韓非子等人在自身論著中常有引用。漢武帝時期《詩經》被奉為儒家經典。史學家司馬遷稱贊《詩經》道:“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荷馬史詩》記述了公元前十二世紀特洛伊戰爭的始末及特洛伊淪陷后奧德修斯返回伊薩卡島王國的遭遇和故事,它全篇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上下兩部組成,均分為24卷,據傳由古希臘詩人荷馬創作而成。《荷馬史詩》在西方影響深遠,是古希臘口述文學的重要開端代表作,也是古希臘從氏族社會過渡到奴隸制時期的一部社會史,被稱為西方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①論文通過《詩經》與《荷馬史詩》中帶有神話色彩的部分或篇目進行分析比較,主要從它們不同的敘事模式和神話人物形象探討中西神話文化的差異成因及其對后世文化產生的重要影響進行細致的論述和梳理。當下學界對《詩經》與《荷馬史詩》神話色彩進行比較的研究不多,而神話作為人類文化體系形成的根源,立足文化背景及作品本身對兩部巨著的進行神話審美與探索剖析是必要而迫切的,這將有助于人們提升對兩部作品審美鑒賞的高度和有效追溯神話的精神起源,更為精確地了解中西文化早期的差異狀況,具有現實意義。
一.神話色彩之表現
我國古代神話傳說非常豐富,我們可以從《山海經》、《淮南子》等古老的典籍中找到神話的影子,也可以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楚辭、殷商青銅器的鑄像、銘文等尋找到古老神話的蹤跡。它們呈現了奇偉瑰麗,燦爛輝煌的神話色彩。但是,我國古代神話元素與西方有不同之處,那就是沒有形成完整而系統的記錄和保存。《詩經》是我國最早以詩集的形式記錄神話存在,但它內容上的神話素材主要集中在頌篇,篇幅也較少。而《荷馬史詩》中的上部《伊利亞特》篇中就包含有大量的古希臘神話,與下部《奧德賽》及其赫西俄德《神譜》共同創建了古希臘完整的、系統的神話體系。[1]P122史詩中神與人相互交流、影響,神話與現實相雜,天上人間融合成了一個整體。《詩經》和《荷馬史詩》在內容上存在的諸多神話元素,具體我們立足文本剖析內容,可以從它的敘事模式與神話、人物的神話形象兩個方面的呈現進行探討。
(一)敘事模式與神話
《詩經》中神話篇目的敘事模式主要是敘事空間化傾向模式和敘事抒情化模式。《詩經》中帶有敘事性質的篇目,大都被冠以敘事詩之名。這些篇目基本上遵循的是四句成章的敘事結構。《荷馬史詩》側重于時間化的思維方式進行敘事,清晰地交代故事前因后果邏輯關系。而《詩經》敘事傾向于空間化的思維方式,講究鋪排效果,忽略故事而轉向抒情,追求“詩中有畫”的境界。②在《詩經》的敘事整體內容上以風、雅、頌的分類來構成,國風反映的是當時社會民間百姓農事狀況,大雅、小雅多為反映貴族階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頌詩用于宗廟祭祀內容也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例如頌詩中的《商頌·玄鳥》契誕生神話等對君權的神化,“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③已具有了神話的文化因子,有明顯的神話敘事色彩和特征。《大雅·生民》中后稷誕生神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等神話描寫多以復沓的章法構成鋪排,正是這種敘事空間化思維習慣所致。
《詩經》敘事抒情化模式的藝術特征主要體現在它的敘事詩上,在其它類別的諸如情節型與紀實型詩歌中只是部分有所體現。在《詩經》中敘事詩指的是以記敘為主要表達方式的詩歌,它以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為主題。[3]P92如敘事詩《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④這首詩通篇運用對比和暗喻,借用牛郎織女的神話和豐富而奇幻的想象交錯,描寫了西周中晚期百姓受統治者慘重盤剝的情形。真實地反映出西周統治下的民間困苦圖景和詩人憂憤抗爭的激情。具有很強的敘事抒情色彩。《尚書·堯典》說:“詩言志,歌詠言”;可見,詩歌的敘事抒情轉向是根植于我國古代的傳統文化思想,早期詩歌的抒情性與時代文化關系密切,且對后世的影響是廣泛的。《毛詩序》說:“詩者,志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⑤《詩經》敘事抒情化表現了”詩”與“情”分不開,有情感藝術形象才擁有生命,情感越是強烈生命愈是旺盛。
《荷馬史詩》被稱之為:“西方文學的濫觴”[2]。這部西方史詩取材于希臘神話“金蘋果事件”,這一事件預示了伊利亞特戰爭的爆發。金蘋果事件主要發生在三個女神之間爭奪最美女神的糾紛。事情發生的經過是人間英雄佩琉斯與海中女神忒提斯結婚的宴會上,當時這場婚事因為是由天神宙斯撮合的,所以婚宴上邀請到了一些級別比較高的神赴宴。而管轄糾紛的女神厄里斯未被邀請卻不請自來,在宴會上留下了刻有意為:“獻給最美麗的女神”希臘文字樣的金蘋果。帕里斯王子把金蘋果評判給了愛神阿佛洛狄忒,赫拉及雅典娜兩位女神對此懷恨在心,蓄意報復。帕里斯獲得了希臘斯巴達貌美的王后海倫,但伊利亞特戰爭導火線隨即被點燃,戰爭迅速爆發了。
對于文學藝術而言,《荷馬史詩》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敘事模式。《荷馬史詩》運用的敘事模式大致分為兩種:戲劇性的敘事模式和組構拼合的雙線模式。《荷馬史詩》的時空特點是“現在——過去——未來”的戲劇性敘事模式,一般的戲劇性敘事模式比較重視故事情節,以及情節里戲劇的沖突律、角色命運性格刻畫、起承轉合節奏等方面的遵循,并且是依照因果聯系的陳述規律的固有特點進行文本的展開。《荷馬史詩》雖然并不是按照固有的時空順序即:“過去——現在——未來”進行敘事,但是它在情節的沖突、轉承等方面具備了戲劇性敘事模式的內在特征。如史詩中的上部《伊利亞特》篇中的戰爭故事便按照戲劇性敘事模式展開。即使《伊利亞特》本身取材就源自于希臘“不和的金蘋果”的神話傳說,但是詩人荷馬并沒有按照神話敘事結構的先后順序那樣從頭到尾的敘述戰爭全過程,而是提取了戰爭進行了九年零十個月的約五十二天內的戰爭情況進行敘述。對于伊利亞特戰爭的過程,詩人只是在適當的地方加以補敘和提及,使得戰爭全過程得以在轉接中完美呈現。
《荷馬史詩》的另一種敘事模式是組構拼合的雙線模式。在《荷馬史詩》中,戰爭爆發之后的十年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都與神有關,甚至在神界都分成兩派進行角逐,赫拉、雅典娜等支持希臘聯軍,另一派阿波羅、阿佛洛狄忒則庇護特洛伊城邦。這十年可以說是希臘社會的縮影,詩人荷馬把這些事件的敘事情節采用了高度集中手法注入了中心人物如赫克托耳、阿喀琉斯等人之中,使一個事件在小段時間內構成完整的系統。而《奧德賽》主要描寫的則是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結束之后撤兵回歸的十年海上歷險和他重新返回到希臘重建家園的故事。《荷馬史詩》在史詩敘事上采取了雙線結構,《伊利亞特》以阿喀琉斯的憤怒為線索貫徹全詩,《奧德賽》以奧德修斯海上歷險及家族中貴族求婚子弟的胡攪蠻纏為線索展開,倒序、插敘、順序相互結合的敘述手法并用,使情節在交叉敘述中有序的結合起來。《荷馬史詩》的敘事情節安排布局巧妙、裁剪得當、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
(二)人物的神話形象
《詩經》里出現的神話人物大致有崇德尚義,開天辟地等形象特征。例如《大稚·文王有聲》中記錄的大禹治水神話:“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大稚·奮高》中記錄的岳神神話:“袋高維岳,駿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與申。”等都是具有開天辟地的力量的,這些神話在民族發展與壯大中起到積極推動作用,他們成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決條件也決定了他們作為大神的責任與擔當。《詩經》中信仰神的人物形象,以歷史人物而真實存在的有如公亶父、公劉、文王、武王、周公等,也有現實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如戰士,征人,農夫,農婦。在《詩經·大雅》中,有6篇被認為是敘述西周歷史的史詩:《生民》、《公劉》、《文王》、《大明》、《皇矣》、《綿》。這些詩塑造了君王的人物形象,這些君王都非常敬奉天神,常有祭祀活動,或祈福戰事順利,或拜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非統治階層的人物形象里有種田的農夫(《七月》)、樵夫(《伐檀》)、漁人(《九戢》)、獵人(《兔置》),采摘的勞動婦女(《卷耳》)等等。[4]P80-81他們對神靈亦是十分崇拜,性格樸素善良,平凡而簡單,大致都比較溫和又常能多愁善感反映現實困境中的生活。
希臘神話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傳說兩部分。在《伊利亞特》篇中,神人同形同性是非常顯著的特點。諸神們有愛有恨,圖享樂虛榮,時常會到奧林帕斯山與人間美貌男女偷情。神王宙斯不僅跟女神談情說愛,還跟人間女子芥蒂良緣。神的生活實際上就如同人的社會化生活。《荷馬史詩》出現的主要人物都帶有神話般英雄色彩。比如《伊利亞特》中的赫克托耳最具有英雄主義氣概和集體主義精神。他只是一個凡人,但充滿了“神”的力量,對神滿懷敬奉之情。在作者筆下他是富于理性、勇敢而成熟的軍事領袖,同時也是最具悲劇色彩的古代氏族英雄形象。對于特洛伊城來說他是第一勇士,榮譽至上,他以特洛伊城邦利益為重。阿喀琉斯是海洋女神忒提斯和英雄珀琉斯之子,擁有神的血緣,勇猛過人,銳不可當。他的英雄主義體現在他不計前嫌,毅然出戰;個人利益意識強,愛憎分明,為好友報仇,使希臘聯軍轉敗為勝。在下部《奧德賽》中奧德修斯是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是伊塔卡國王,在希臘聯軍攻陷伊利亞特城邦之后率領軍隊撤退回國,在途中歷經十年艱辛險阻終于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他具有奴隸主的各種品質與才干,足智多謀,能言善辯,還具有百折不撓、敢于歷經磨難也要回歸故土的能抵制女神誘惑對愛情及家人情感專一的英雄形象。
二.神話色彩差異成因之探討
馬克思說:“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產生了”。一般而言,神話乃是對自然現象、與自然的斗爭的反映,以及社會在廣泛藝術概括中的反映。神話正是處于原始時代的人們對于世界認識的急切而將其落后的原始思維以及好奇心轉化為對大自然及自身創造的一系列荒誕故事的合理解釋。《荷馬史詩》和《詩經》中充滿了豐富的神話色彩,但它們的成因與差異的不同特征,是中西兩種不同文化體系根源所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天人合一”與“天人各一”的神話信仰。中國文化的核心強調集體主義、群體意識,義務本位的思想深入人心。我國古代是以農業為主的田園文明,長期生活的環境也是比較的封閉,其自給自足的方式構成了“天人合一”的整體思想,對“天”的推崇比較強烈。“天”在《詩經》中總共出現達167次,“天”高于“人”,“天”有絕對的權威,它全知全能,是宇宙的支配者,“天”是具有了人格、意志、超自然的至上之神。[5]P90-91西方文化構成因素有古希臘文明、猶太文明;古羅馬文明作為源頭交匯而成并以基督教的形式鑄成了強大的文化體系,構成了“天人各一”的二元論世界觀。城邦人際關系依靠契約或者說是法律、道德、上帝來維系,強調的是個體意識和權屬意識,把個人尊嚴與榮譽看得非常之重。
文本內容的神話意義不同。正因為“天”是至上之神,是不可違逆的,所以在《詩經》中對神的推崇及神力量的提倡是普遍的。例如《詩經》中頌歌這類詩大都出自公卿樂官之手,有的頌帝王歌天命,為周王統治的合理性尋求神學依據,如《維天之命》、《文王》;有的歌頌戰功,如《殷武》、《江漢》;有的頌宴飲贊嘉賓,如《鹿鳴》、《南有嘉魚》等。而在《詩經》中存在的田祖神話:“同我婦子,位彼南畝,田咬至喜。⑥”(《幽風·七月》),大禹治水神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⑦”(《小雅·信南山》)等則與反映社會現實,對農事活動等有道德教化的作用,帶有‘思無邪的特征。而西方城邦文化的個體意識、個人尊嚴至上等不難在《荷馬史詩》中得到印證。希臘神話主要提倡英雄主義的神話色彩,每一個情節的發生與轉變都與神的角逐緊密相連。《荷馬史詩》上部《伊利亞特》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被稱為“阿喀琉斯的憤怒之歌”。《奧德賽》敘述了奧德修斯歸國途中漂泊的故事,他受神明捉弄,歸國途中在海上漂流了十年,到處遭難,最后受諸神憐憫始得歸家。神界與人間雙線發展,相互影響。在內容上它們呈現了兩種不一樣的神話效果。
取材視角及神與人關系不同。中西方神話信仰和神話認知的不同,導致了早期人們對神的崇尚程度也不同。《詩經》中的部分詩歌來源于神話,如《大雅·生民》、《大雅·裕高》和《商頌·玄鳥》都具有明顯的神話色彩。《詩經》中后稷的神異才能、超凡本領和顯赫功績實際上正是原始周民族才能和智慧的集中概括,是這些內容的虛幻的神話反映。神話的產生也以宗教生活和宗教神話觀念為基礎,中國儒家知識分子對神以及宗教的態度使他們更多地注重自己的內心道德自覺,而不是外在的上帝決定論。《詩經》中的神大多相貌丑陋,但都是倫理道德偶像,他們高于人間凡人,更不會出現神人同形同性,而是神人二分的。[6]P81《荷馬史詩》的取材直接來源于希臘神話“不和的金蘋果”,在史詩中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神話與現實相雜的顯著特點。《荷馬史詩》中出現凡人所不具備的力量的另類靈性―英雄,如史詩主要人物阿喀琉斯為神與人所生,他英勇善戰,重視榮譽,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崇尚力量、自由樂觀的性格。《伊利亞特》中所描繪的諸神同人并沒有什么不同,諸神們或威嚴或俊美或嬌艷或機智,他們具有人性的貪欲、嫉妒、荒淫、野蠻、婚戀和虛榮。
三.神話色彩對后世審美文化的影響
《詩經》神話色彩的呈現情況來看,從神話信仰的角度來講,它是“天人合一”,“天”至上的另一種表現。在哲學史上,后世的諸多學派如漢儒董仲舒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成為二千年來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觀點。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講“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構成人的本質,在人間體現為倫理道德“三綱五常”。“人欲”是超出維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違背禮儀規范的行為,與天理相對立。后世道家的宇宙觀和自然觀同樣也是與早期神話色彩有所共鳴之處。老莊的重新闡釋,并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魏晉玄學,如郭象認為“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這些例子說明,早期的神話色彩帶有的文化信仰——先“天”后“人”的思想已然同步呈現并且影響深厚。此外,中國《詩經》中包含的神話元素同樣影響了我國文學的發展。其中神話當中的浪漫主義就成為了屈原的創作素材,在他的《天問》、《九歌》中便大量采用了上古神話。后期如莊子《逍遙游》、明清小說《西游記》、《紅樓夢》等都深受影響。神話敘事方面其中的現實追求對后世詩歌創作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比如漢樂府詩歌的敘事性藝術和主題體現,唐代詩人杜甫、白居易等對樂府歌行的敘事詩的創作和敘事主題的追求,構成了古典敘事詩“質實”的美學風格特征。[7]而在《詩經》中的“牛郎織女”神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玻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小雅·大東》)⑧”,在后世文學《古詩十九首(之十)》、宋秦觀《鵲橋仙》等的創作中經常被引用。《詩經》中所涉及的神話傳說不僅使文學上諸如現代郭沫若《神女》等作品深受影響,在現當代的電影、音樂等方面也經常成為它們注入的神話題材。
《荷馬史詩》的神話色彩對后世的影響主要在于它本身帶有的古希臘神話中的神人同化和英雄主義,為榮譽而戰。希臘神話中,神的本質是“不死、永生、極樂”,而凡人的本質是“有死、衰老、憂愁”。因此在神與凡人之外,還有許多介于這兩者之間的存在,那就是神人同形。這主要得益于西方二元論世界觀的影響與發展和對人的重視。當然,神話、種族以及文化都沒有孰優孰劣,只是由于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的不同產生了萬千差異,而這一文化差異從神話中呈現出來的即是古希臘人或說西方人的傳統精神是不依賴統治者的個人道德,因為最高神都和一般人一樣,所以他們依靠制度,而在我國古代人們則依賴統治者個人高尚的情操和道德,認為仁者無敵,也只有偉人才能統治天下。這就形成了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分野。即西方更傾向制度的制約,中國古代就形成專制的認同。此外,在文學方面,它成為了部分文學體裁的業余優勢,神話色彩及其敘事模式對后世的影視、文學等都潛移默化地起到沖擊和帶動作用。《荷馬史詩》和《詩經》的神話色彩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刻,這種影響在文學上表現比較突出。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神話都是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它以文學藝術與哲學的形式真實而形象的還原了人類社會早期最本質的面貌,反映了人類發展初期同自然的斗爭等等。《荷馬史詩》作為西方神話的一個重要源頭,直接影響了文學創作的發展,莎士比亞、歌德、艾略特等后世文學大家都從中選材。
四.結語
《詩經》和《荷馬史詩》的神話人物和故事是比較珍貴的,是中西不同文化體系構成根源,神話色彩帶有的審美張力極其豐富,甚至在文本內我們可以看到古老神話賦予的生命力。兩部作品在哲學、文學、文化、軍事等領域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然而,當我們借用神話投入到其它體裁的創作中時,其作品的思想內容、思維空間和思想層次上的信息量不僅是將大幅度上升這么簡單,而是正因它帶有的神話語言與精神內核的審美張力才能使得藝術作品走向深化。可想而知,它們對中西方的后世哲學理論、文學創作、音樂、電影等方面的神話題材都產生了重要指引作用。《詩經》和《荷馬史詩》始終代表著兩個不同神話旨趣的審美主張,在中西方記錄神話傳說的原始典籍并不多的情況下,《詩經》和《荷馬史詩》作為十分珍貴的神話文獻資料,客觀的展現了中西方早期不同文化與價值的取向,是后世中西兩種文化體系形成的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王景遷,于靜,從荷馬史詩《伊利亞特》論析史詩與神話的辯證關系[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5(06):P121-125頁.
[2]劉琳,何英嬌,世界文學5000年[M].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
[3]張寶林,《詩經》敘事藝術特征闡釋[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03.9P:90-93頁.
[2]劉琳,何英嬌,世界文學5000年[M].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
[4]盧燕麗,《詩經》人物形象的文化史意義[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P:80-83頁.
[5]吳瑞裘,《伊利亞特》和《詩經》中的至上神比較[J].外國文學研究.1992(03):89-94頁.
[6]趙艾,從《詩經》和《荷馬史詩》看中西方文化差異[J].作家,2011(20):80-81頁.
[7]楊宏,陳靜,漢樂府民歌對《詩經》民歌敘事藝術的繼承和發展[J].太原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22卷.P50-53頁.
注 釋
①[英]加斯帕·格里芬,Jasper,Griffin,荷馬史詩中的生與死[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②徐定懿,荷馬史詩與《詩經》敘事詩之比較[D].重慶:重慶師范大學,2008年.
③程俊英譯注,詩經[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678頁.
④程俊英譯注,詩經[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408頁.
⑤孫敏強,中國古代文論作品與史料選[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P38頁.
⑥程俊英譯注,詩經[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265頁.
⑦程俊英譯注,詩經[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431頁.
⑧程俊英譯注,詩經[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408頁.
(作者介紹:吳天威,貴州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2016級美學專業碩士研究生,荔波高級中學語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