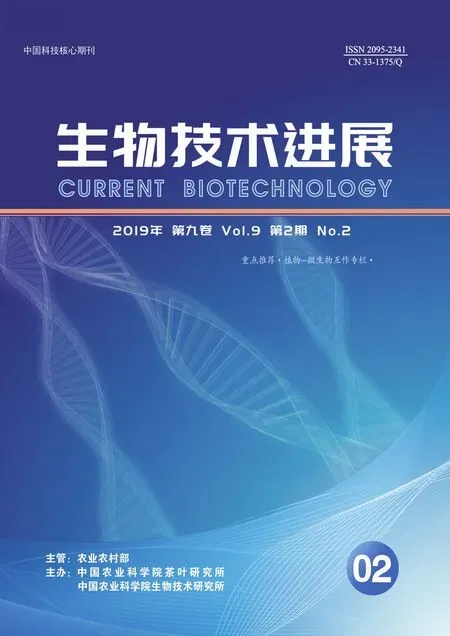膠質母細胞瘤相關分子標志物研究進展
劉夢昱, 謝 飛, 張 鑫, 趙鵬翔,2*
1.北京工業大學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學院, 北京 100124;2.北京工業大學激光工程研究院, 北京100124
膠質瘤是一種由腦部或中樞神經系統的膠質細胞發展出來的原發性腫瘤,約占腦部和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總數的30%[1]。其惡性程度極高,占所有原發性惡性腦腫瘤的80%[2]。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alth Organization, WHO)按照形態和發病部位將膠質瘤分為星形細胞瘤、少突神經膠質瘤、混合膠質瘤和室管膜瘤。WHO根據腫瘤組織病理學特征(如腫瘤細胞增殖能力、細胞核多形性、細胞結構和壞死程度)以及惡性程度由低到高將膠質瘤分為Ⅰ、Ⅱ、Ⅲ、Ⅳ四個等級。低等級膠質瘤,即Ⅰ、Ⅱ級膠質瘤,腫瘤細胞分化程度高,腫瘤呈良性,患者有較好的預后,但是在治療后有極高的復發可能性,并隨著時間延長能夠演變為等級更高的惡性膠質瘤。高等級膠質瘤,即Ⅲ級和Ⅳ級膠質瘤,惡性程度高,具有腫瘤細胞分化程度低、病人預后差的特點。腫瘤組織學上認為,GBM具有高度異質性,該特性體現在細胞的類型,如不同大小的未分化細胞、纖維形膠質細胞和多形性星形膠質細胞、有絲分裂的數目、細胞的分布密度以及血管生成情況和壞死程度等[3]。不僅如此,GBM瘤區還有可能包括非膠質細胞生成的腫瘤細胞。由于這些特性,GBM被劃為IV級膠質瘤,同時,這些特性也反映了GBM的高度惡性行為產生的原因。
腫瘤治療中,手術切除被認為是最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但是由于膠質瘤的腫瘤細胞具有侵襲周圍組織的特點,使得僅僅通過手術治愈膠質瘤并不可行。此外,膠質母細胞瘤對放化療有很強的耐受性。因此,盡管經過了手術切除和常規治療,GBM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仍只有12~15個月[4]。研發新的治療手段幫助延長患者生存時間、改善生存質量成為目前膠質瘤治療中最迫切的需要。因此,深入全面的了解腫瘤標志物對研究新的治療GBM的方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對已發現的腫瘤標志物進行全面的綜述,以期為膠質母細胞瘤的治療研究提供參考。
1 膠質母細胞瘤診斷及預后相關標志物
1.1 O6-甲基鳥嘌呤-DNA甲基轉移酶(O6-methlyguanine-DNA-methyltransferase, MGMT)
GBM中,許多基因的啟動子特殊位點會發生甲基化,這一變化會直接導致基因表達水平的改變,如腫瘤抑制基因p53、RB1以及pten等[5,6]。臨床上,MGMT啟動子是GBM最重要的DNA甲基化標志物之一。近40%的原發性GBM患者樣品中均能檢測出MGMT基因的轉錄沉默。有研究報道,對GBM患者使用烷化劑化療過程中,其MGMT啟動子的甲基化水平可以作為一種預后標志物[7,8]。
MGMT基因位于10q26號染色體上,其編碼的DNA修復蛋白能夠將重要的DNA烷基化位點,即鳥嘌呤O6位置的烷基基團清除。當DNA修復消耗的MGMT蛋白得不到補充時,未得到修復的DNA會受到損傷,如化療誘導的鳥嘌呤O6的甲基化,會引起細胞毒性和凋亡[8]。烷基化試劑,如替莫唑胺(TMZ)能夠將烷基基團轉移至DNA上,通常的轉移位點為鳥嘌呤的N7或O6位置[9],這一過程中,若沒有DNA的損傷修復,便會直接導致DNA損傷,最終引起細胞死亡。MGMT啟動子的CpG島位點若發生甲基化,該基因的表達將會受到抑制,這一結果可以加強DNA對烷基化試劑的敏感性。之前的研究表明,高達45%~47%的GBM具有MGMT甲基化的特征[8,9]。對于進行烷基化試劑治療的患者,其腫瘤組織MGMT基因甲基化水平與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以及整體生存時間有著重要聯系[10]。通過對相關腫瘤患者的組織樣品進行分析,發現幾乎只有MGMT啟動子甲基化的膠質瘤患者會在化療中得到一定的治療效果[8]。其中,對于初診為GBM的患者,最主要的治療手段是使用烷基化試劑進行化療,其中MGMT甲基化水平較高的患者會產生更好的化療效果,若腫瘤患者MGMT基因未發生甲基化,則該類患者預后較差,生存率較低。對于晚期GBM患者而言,相較放療,MGMT基因甲基化對TMZ治療效果的影響更加顯著,研究表明,TMZ對MGMT甲基化的患者往往會產生更好的療效[4,11]。同時,GBM患者的MGMT甲基化水平與腫瘤復發無關,患者自身MGMT基因甲基化水平也沒有發生改變,因此,對于MGMT基因甲基化的GBM復發患者,再次使用TMZ治療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10]。這些結果也表明MGMT啟動子的甲基化不僅在預測腫瘤預后上起著一定作用,甚至可以作為GBM的預后標志物。最近的研究也再次證實了在IDH1/2野生型和突變型的GBM中,MGMT 基因甲基化患者的化療預后效果更佳[12]。
目前在臨床上,無論患者的甲基化水平高低,通常都會選擇TMZ來進行治療。對于早期GBM患者,MGMT啟動子甲基化作為重要的預測標志,對未來的治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8]。并且可以根據MGMT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將患者進行更好的分類,以采取更合適的治療手段。但是長久以來,對于非早期GBM患者,MGMT甲基化水平是否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即便如此,MGMT甲基化水平對于區分非早期GBM患者仍然是有意義的。
1.2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factor growth receptor,EGFR)
EGFR由胞外受體結構域、跨膜區和胞內具有酪氨酸激酶功能的結構域組成,在細胞增殖、遷移和生存等相關通路中起著重要的作用。EGFR活性可通過基因水平上調或它的變體EGFRvIII的缺失突變增強,后者能夠保證縮短后的受體保持持續的活性,進而促進有絲分裂的級聯反應[13]。EGFR的擴增出現在40%~60%的GBM中,其中只有很小的部分發生EGFR突變,產生變體EGFRvIII[14]。EGFR基因擴增水平可以通過熒光原位雜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技術檢測,而突變體EGFRvIII的表達可以使用免疫組織化學檢測。近年來,關于EGFR基因擴增和突變體EGFRvIII產生影響的相關研究報道結果不一,在GBM研究中存在著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7,15]。以EGFR作為靶標,在多種癌癥的治療中均被證明是有效的。如針對EGFR的藥物單獨或聯合化療用于結直腸癌、非小細胞肺癌和胰腺癌等[16]。從這些結果來看,研究者認為在癌癥治療中,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5]。EGFR是第一個被認為與GBM的腫瘤發生相關的分子[17]。雖然EGFR的過表達或突變是GBM最重要的特點之一,但是,以EGFR作為靶標的GBM臨床試驗中的結果卻不盡如人意。臨床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的藥物無法穿過血腦屏障以及突變帶來的抗藥性等。
1.3 異檸檬酸脫氫酶1/2(IDH1/2)
異檸檬酸脫氫酶是檸檬酸循環中的組成成分,作為關鍵的代謝酶類,能夠催化異檸檬酸和NAD+發生反應并轉化為二氧化碳、NADP和α-酮戊二酸。在多種腫瘤中均能夠鑒定出IDH1/2 的突變。Stancheva[18]首次在GBM中發現IDH1/2突變后,隨后的研究表明在所有的GBM中,近8%~13%發生了IDH突變,其中包括了高于80%的繼發性GBM的IDH突變。最常見的突變為IDH1 R132和IDH2 R172位點,該類突變占所有IDH突變的90%,而在由低等級發展而來的II級或III級膠質瘤以及GBM中,前者突變占IDH突變的70%[19]。IDH突變使α-酮戊二酸轉化為腫瘤代謝物D-2-羥戊二酸,由于依賴α-酮戊二酸的組蛋白和DNA脫甲基酶受到抑制,積累的D-2-羥戊二酸導致了表觀遺傳的調節發生異常,從而阻礙細胞分化[20]。同時,該突變也會減少NADPH的形成,促進氧化應激從而導致DNA的損傷[7]。但是也有研究顯示,在膠質瘤中IDH突變會延長12~30個月的生存期,提高TMZ和放療的敏感性[21]。同時,有研究表明與野生型相比,突變的IDH1可以通過手術最大化切除區域,達到延長生存期的目的[22]。現今,IDH突變的檢測手段包括測序和免疫組織化學方法。臨床前期研究證實IDH突變的小分子抑制劑能夠降低細胞內D-2-羥戊二酸的水平,調整表觀遺傳調節異常并促進細胞分化[23]。抑制IDH突變顯示其在血液腫瘤中作為治療手段的可能性,并在實體瘤和膠質瘤中得到進一步研究。IDH突變抑制劑作為單獨藥劑使用或聯合其他治療手段應用于腫瘤治療中,在針對其他致癌通路的治療中,也有一定的臨床應用前景。
1.4 1p19q共同缺失
染色體1斷臂和染色體19長臂的缺失導致其整個染色體臂著絲粒的移位,被定義為1p19q共同缺失。在GBM研究中, Cairncross 等[24]首次在少突神經膠質瘤患者中發現1p19q 共同缺失,并證明檢測1p19q基因水平可以在臨床上起到一定的疾病預測功能。2016 年WHO 標準中, 1p19q共同缺失與IDH突變共同出現的膠質瘤被定義為少突膠質瘤。大約60%~80%的Ⅱ級或Ⅲ級少突神經膠質瘤和20%~50%的Ⅱ級或Ⅲ級少突星形膠質瘤,以及低于10%的彌散型膠質瘤中會出現1p19q共同缺失的情況[25]。對于少突神經膠質瘤,如出現1p19q共同缺失,那么會有較好的生存率、化療(甲基芐肼、環己亞硝脲和長春新堿聯合化療以及替莫挫胺)和放療效果[26],這種對于治療手段敏感性的原因尚待研究。在GBM中,1p19q共同缺失的相關研究結果并不一致。Boots-Sprenger等[27]的研究中彌散性膠質瘤包括GBM患者的1p19q共同缺失、MGMT啟動子甲基化和IDH突變預示了更好的預后,但其中仍有10位病人的組織病理學結果表明1p19q共同缺失與此無關。而Zhao等[28]運用Meta方法分析了28篇研究中3 408個膠質瘤樣品結果,他們提出1p19q共同缺失與生存期的延長有關,而與組織學分級無關。1p19q共同缺失的檢測方法包括微衛星序列分析、PCR和基因組雜交技術等,其中FISH法最為常用。
1.5 α-地中海貧血伴智力低下綜合征基因(α-X linked alpha thalassaemia/mental retardation,ATRX)
ATRX基因首次在X染色體連鎖精神發育遲滯綜合征病人中被發現,該基因編碼的蛋白參與遺傳穩定、染色體重塑和DNA甲基化等過程[29]。ATRX基因失活與端粒替代延長(ALT)機制密切相關。在真核生物中,端粒是染色體末端的DNA重復序列,維持著染色體的完整性。ALT作為一種調控端粒長度的機制對細胞的生存和增殖至關重要。近年來,ALT在膠質瘤的生物活動中的作用才被發現。突變的ATRX基因經常伴隨著IDH突變,但幾乎不與1p19q共同缺失同時出現。生存曲線分析表明, ATRX缺失的星形膠質瘤患者作為IDH突變中的一個子群,伴有更好的預后[30]。Koschmann等[31]研究表明,ATRX缺陷小鼠的GBM模型中,ATRX突變會導致腫瘤基因不穩定,在沒有任何治療的情況下,腫瘤具有更高的侵襲性。但是,對小鼠的雙鏈DNA損傷進行修復,與對照組相比,治療后的小鼠生存期得到延長。ATRX表達缺失通常使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其他檢測方法還包括PCR、測序和蛋白免疫印跡[14]。
1.6 端粒酶反轉錄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TERT)
染色體末端的端粒重復序列產生的帽子結構由幾百個核酸組成,當缺少端粒酶活性時,端粒會隨著每一次細胞分裂過程被縮短[32],隨著細胞的不斷分裂,端粒被逐漸消耗,最終導致細胞的休眠或死亡。端粒不僅對細胞的生存十分重要,與腫瘤的生成也密不可分。癌癥的標志之一就是端粒維持的調控異常,而這一過程正是由端粒酶調控的。90%的晚期惡性腫瘤中,都能檢測到端粒酶的活性。TERT是端粒酶的一個催化亞基,能夠將額外的DNA序列插入至端粒中[32]。TERT的表達與多種腫瘤相關。在IV級星形膠質瘤中,TERT啟動子突變活化的情況經常被報道。突變的TERT與1p19q共同缺失密切相關,而與IDH突變或ATRX無明顯關聯[32]。Killela等[32]在多種類型的膠質瘤中開展了IDH1/2突變與TERT突變的相關性研究。結果表明,在GBM中,沒有IDH1/2突變的情況下,TERT突變預示著更低的整體生存率。此外,Simon等[33]和Labussiere等[34]的研究也表明TERT突變可以作為一種獨立的預后訊號,在原發性GBM中預示著較差的預后。Eckel等[35]基于IDH、1p19q和TERT的水平進行各組比較得出結論,在出現IDH突變和1p19q共同缺失的膠質瘤中,TERT突變預示著相對較好的治療結果,但是在只有IDH突變而沒有1p19q共同缺失的GBM中,TERT突變卻預示了較低的生存率。如今,TERT突變水平可通過甲基化特異性PCR檢測,此外,也有研究報道通過術中快速測試的方法檢測TERT突變[36]。
1.7 MicroRNA
MicroRNA是一類長度約為20~25個核酸的非編碼RNA片段,通過結合mRNA引起mRNA的降解并最終抑制蛋白質的合成。研究認為microRNA與多種癌癥的起始和發展有關,因而microRNA具有巨大的潛力成為一種診斷和治療工具。如今,已經有超過1 500種人類microRNA被鑒定出來,其中許多microRNA的表達水平在多種癌癥中均檢測到不同程度的上調或下調。研究表明一些microRNA與GBM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可以作為一種預后標志物[37]應用在臨床治療或診斷中。同時,通過檢測得到的microRNA表達水平也能夠幫助人們將GBM更準確地分類。此外,瘤內或微循環中的microRNA也可以作為GBM檢測、診斷、使用藥物如替莫唑胺治療或放療的預后或預測標志物。
針對GBM分類,Henriksen等[37]通過對應臨床數據與161個microRNA進行分析,根據結果將GBM患者分為兩類,分別對應長期和短期生存期。另外,Kim等[38]根據癌癥基因圖譜(TCGA)中膠質瘤相關的261個microRNA表達水平的分析結果,鑒定出臨床上截然不同的5組GBM亞群,每組亞群分別對應不同的神經前體細胞,這些細胞亞型包括放射狀膠質細胞、少突膠質或神經元前體細胞、神經元前體細胞、星形膠質細胞前體和神經間質細胞前體。同時,Li等[39]使用基因芯片和非負矩陣分解法分析了TCGA中RNASeqV2數據,其中包含了169個GBM樣品和5個對照組樣品數據。不僅如此,其他研究中通過microRNA幫助腫瘤分類的作用也得到了驗證。由于在組織學上難以分辨,一些研究者也致力于通過microRNA表達特征區分原發性與繼發性GBM。通過對比原發性和繼發性GBM樣品,Rao等[40]篩選出7個microRNA來幫助鑒定不同類型的GBM。
根據microRNA表達差異可以幫助GBM分類,不僅如此,隨著近年來對microRNA在GBM中表達水平的深入研究,鑒定出了一些能夠對患者的預后進行一定程度上預測的microRNA。Srinivasan等[41]通過對TCGA數據與對應的222位GBM患者生存期的microRNA表達水平進行比對,鑒定出一組microRNA,包括的10個microRNA被認為具有幫助預測GBM患者生存期的作用。其中7種microRNA(包括miR-31、miR-146b、 miR-148a、miR-193a、miR-200b、miR-221和miR-222)在生存期較短的患者中處于過表達水平,另外3個microRNA(包括 miR-17-5p、 miR-20a和 miR-106a)的表達水平則較低。另外,也有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Guan等[42]研究表明miR-196a和miR-196b的表達與較短的生存期有關,而Lakomy[43]的研究卻認為miR-196b與較長的生存期呈正相關關系。除此之外,其他研究報道了處于高表達水平的miR-326和miR-130a,低水平表達的miR-323、 miR-329、 miR-155 和 miR-210,與更長的GBM患者生存期密切相關。
治療GBM的傳統手段仍為放化療后進行手術切除,但收效甚微。而GBM耐藥性的機制在分子水平上也仍需更深入地研究。近年來,許多研究通過不同的治療效果與microRNA表達差異相對應進行比較分析,這一方法為發展更好的預測療效和針對性治療帶來了新的思路。許多研究檢測了藥物處理后GBM樣品中的microRNA水平,為進一步的分析提供了數據基礎。例如有研究檢測了60位經過放療和替莫唑胺治療的GBM患者的miR-125b的表達,發現患者中高水平表達的miR-125b的中位生存時間僅為9個月,而低水平表達miR-125b的患者生存時間為18個月[44]。同時,Zhang等[45]對有無替莫唑胺治療的GBM患者的microRNA表達水平進行比較,鑒定得到一組包含5種microRNA的特性指標,該指標能夠預測病人的生存期和替莫唑胺治療的效果。類似地,有研究根據9種microRNA表達特征建立了一種風險指數分析方法,對使用替莫唑胺治療的GBM患者也能起到一定的療效預測作用[46]。
大量研究表明microRNA在未來能夠作為重要的診斷和預后標志物,但是如今microRNA作為標志物并不能為臨床治療決策提供充分的分析依據。隨著對microRNA在GBM的發生發展中的影響以及不同的microRNA表達特性的更深入研究,能夠促進人們對GBM進行更完善更準確的分類,并對疾病的發展模式進行更深入的理解,最終使患者的生存期得到延長,生存條件得到改善。
1.8 免疫相關標志物
除了在細胞信號通路和蛋白質中發生突變,GBM腫瘤發展惡化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其能夠逃脫免疫系統的監控。通過表達免疫抑制細胞因子和強化調節T細胞的活性,GBM形成了一套抑制免疫應答機制。這種免疫被抑制的微環境中,兩種重要的免疫關卡蛋白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TLA-4)和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PD-1)起著重要的作用[47]。CTLA-4僅在常規T細胞中上調表達,通過與協同刺激分子CD28競爭,CTLA-4與B7配體相結合,進而負調控早期處于活化狀態的T淋巴細胞。而PD-1在多種細胞中均能表達,包括 B細胞、自然殺傷細胞、樹突細胞、處于活化狀態的單核細胞、巨噬細胞以及T細胞。同時,PD-1在免疫應答的多個階段中起到了調節作用,從而改變外周組織中T淋巴細胞的活性[48]。TCGA數據表明PD-1的配體PD-L1和CRLA-4的mRNA在GBM中大量表達,這一結果也反映了這些免疫關卡蛋白和GBM惡性程度的相關性[49]。但是,在GBM中這些免疫關卡與預后是否相關仍存有爭議。Bergho等[50]研究了117例GBM患者的樣品,并沒有發現PD-L1與病人生存期具有相關性。同時,Liu等[51]研究顯示PD-L1對GBM患者生存期具有正面和負面的不同影響,產生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歸因于膠質瘤亞群的不同以及PD-L1調控分子表達水平的差異等,其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為腫瘤微環境中表達PD-L1的細胞類型。而近期大量臨床研究表明在多數的GBM樣品中,PD-1以及PD-L1均可以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出來,PD-L1基因的表達水平也與GBM亞型密切相關。最近的研究顯示PD-L1在一小部分GBM患者中過表達,而高水平表達的PD-L1與較差的預后結果具有一定相關性[52]。
免疫關卡抑制劑成功應用在黑色素瘤、腦轉移瘤、肺癌和腎臟腫瘤的治療,為這些抑制劑能夠成功應用于膠質瘤臨床治療帶來了希望。多種針對GBM及復發的低等級膠質瘤的免疫關卡抑制劑的臨床實驗正在進行中。這些研究將會驗證這種方法對膠質瘤是否有效。目前,樹突細胞疫苗的三期臨床實驗數據顯示,對CTLA-4表達進行監控也許能夠預測GBM患者的生存期,同時表明CTLA-4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治療預后生物標志物[53]。然而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在GBM的免疫治療發展中,復雜的腫瘤微環境仍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針對不同CTLA-4、PD-1和PD-L1水平的患者進行鑒定分類也將在GBM臨床中為制定重要的治療決策提供依據。
1.9 影像學相關標志物
組織學、蛋白組學以及下一代測序技術作為GBM診斷和預后的參考標準不斷受到挑戰,并且由于腫瘤侵襲性和樣品抽樣的偏差,這些方法并不能更好的分析瘤內和瘤外的異質性特征。因此,不同于傳統方法,近年來逐漸應用于治療性干預后腫瘤情況監測的影像學相關標志物,極大地改善了病人的個性化管理。雖然當下GBM影像學相關標志物應用于臨床的條件還不充分,但是近年來先進的影像學技術包括彌散加權磁共振成像(DW-MRI)、動態磁敏感對比增強灌注加權成像、頻譜成像(MRS)和電子成像術(PET)在鑒定不同的GBM腫瘤表型方面顯示出巨大的潛力。已有研究認為針對GBM獨特的生物學特性,將基因組學和影像學數據相結合進行分析,或許能夠提高早期診斷的正確率并制定更適合的治療手段。有報道應用MRS對2-羥戊二酸(2-HG)水平進行評估,結果表明在發生IDH突變的膠質瘤中,檢測到了 2-HG表達水平上調,將兩種檢測結果相對應,通過更深入的研究,能夠為未來的腫瘤診斷和預后提供更多的數據支持[54]。同時,研究證明眾多的GBM相關核磁共振(MRI)參數指標,如降低的表觀擴散系數(ADC)和升高的相對腦血容量(rCBV)等,能夠預測體內EGFR表達水平增強,對腫瘤的發展進行一定程度的評估[55]。在低等級膠質瘤中,rCBV檢測水平已經可以作為一個有效的預測指標應用于腫瘤惡性程度、無病進展生存期和腫瘤復發等情況的評估。
除了MRI,許多PET放射性示蹤劑也被作為潛在的影像學生物標志物,促進人們更加深入的了解腦部腫瘤的病理學特征。現今,雖然18F-FDG是 PET最常使用的放射性示蹤劑,但是由于與其他組織相比,腦部具有較高的葡萄糖攝取量,導致低等級腫瘤、腫瘤組織較小或復發腫瘤早期的18F-FDG無法被檢測,使得在GBM的影像學中18F-FDG的應用十分有限。因此,近年來其他的PET配體應用于影像學檢測中,如放射性標記氨基酸及其芳香族類似物,這類標記物能夠克服18F-FDG的局限性,它們的PET影像學結果中,腫瘤組織與背景對比更強,易被觀察。PET氨基酸示蹤劑得到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是它們能夠通過氨基酸轉運穿過血腦屏障進入腦部,得到從低等級到高等級的膠質瘤可視化影像。同時,Kim等[56]的研究證明了在臨床上,PET氨基酸示蹤劑11C-蛋氨酸(C-MET)的攝入與膠質瘤患者較短的生存期密切相關,表明了該示蹤劑可以幫助預測患者的預后情況。 Pauleit等[57]發現另一個PET示蹤劑18F-FRT在腫瘤的非增強區域攝取升高,因而不適用于腫瘤的影像學檢測。雖然如今許多研究表明分子成像標志物在評估治療效果和生存曲線中具有一定的發展前景,但是若想真正將影像學分析應用于臨床,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將全面的基因組數據與影像學結果整合分析,不僅能夠幫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GBM在遺傳學、代謝組學或表觀遺傳學等方面的異質性,同時為鑒定出更加準確的預測生物標志物創造了可能。
2 治療靶點相關研究進展
2.1 酸性神經酰胺酶
酸性神經酰胺酶(ASAH1)首次發現于大鼠腦組織勻漿中,隨后從人體尿液中被分離純化出來。ASAH1是一種溶酶體半胱氨酸酰胺酶,通過催化作用將神經酰胺轉化為鞘氨醇和游離脂肪酸。之后,鞘氨醇被鞘氨醇激酶1(SPHK1)或2(SPHK2)磷酸化生成鞘氨醇磷酸酯(S1P),該物質通過上調尿激酶纖溶酶原激活物及其受體和侵襲促進分子CCN1(富含半胱氨酸血管生成蛋白61)促使GBM侵襲周圍組織[58]。另一方面,神經酰胺合成酶生成大量攜帶有14~26碳脂肪酸側鏈的神經酰胺,伴隨著放化療后體內釋放的細胞色素C活化Caspase-9和Caspase-3,促進細胞的凋亡 。由于ASAH1的多種產物與細胞增殖調控相關,許多ASAH1與不同癌癥的相關研究被陸續報道。研究表明ASAH1在AML中能夠作為一種新型的藥物作用靶點進行進一步探究[59]。而在前列腺癌中過表達ASAH1卻會引起化療的耐藥性。研究認為放療后前列腺癌中上調的ASAH1表達水平能夠幫助腫瘤細胞在輻射后繼續存活[60]。因此,當ASAH1的活性被其抑制劑B13抑制后,細胞會對放、化療更加敏感并通過不斷積累胞內神經酰胺至細胞毒素水平最終誘導凋亡[61]。ASAH1的另一個抑制劑Ceranib-2同樣能夠通過抑制乳腺癌細胞系MCF-7和MDA MB-231的細胞生長產生相似的作用[62]。最近發現了一種新型ASAH1抑制劑卡莫氟,用該抑制劑處理宮頸癌細胞,抑制了腫瘤細胞的增殖水平和代謝。其中,Wnt/β-catenin信號通路起到了重要的調控作用[63]。臨床上也嘗試使用卡莫氟幫助治療,有研究報道乳腺癌早期患者使用卡莫氟作為一種術后佐劑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64]。

圖1 鞘脂類信號通路示意圖Fig.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phingolipid signaling pathway.
隨著對GBM的研究,鞘脂類代謝在GBM的作用逐漸被人們了解。研究表明,S1P促進了GBM細胞系U87MG的遷移,與正常腦灰質組織相比,GBM組織中的S1P水平顯著升高[65]。同時也有研究證實了ASAH1水平與GBM的生存期呈負相關[66]。另外, 為了研究ASAH1在GBM放療抗性中的作用,人們發明了一種穩定的GBM放療抗性研究模型,即通過輻射U87 GBM細胞篩選出存活的細胞并留存進行研究。在該模型中,成人GBM細胞系U87和小兒GBM細胞系SJGBM2的細胞內ASAH1水平以及它的胞外代謝分泌物水平同時上調,表明ASAH1加重了GBM的放射抗性。GBM患者的免疫組化結果顯示,在放療后的組織中具有更高的ASAH1水平。這些研究表明通過增加GBM腫瘤細胞化療抗性,提高促進細胞存活的S1P分子水平,ASAH1可能帶來減少GBM生存期以及促進復發的結果。但是,不論這些細胞的化療抗性如何,其對ASAH1抑制劑卡莫氟仍具有一定的敏感性[67,68]。在U87細胞以及前列腺癌異種移植實驗中同時使用常規放療和ASAH1抑制劑,能夠明顯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在此基礎上,研究認為ASAH1抑制劑可以作為放射致敏劑應用于臨床[61,69]。臨床上, ASAH1抑制劑卡莫氟已被應用于治療直腸癌患者[70]。但是,在廣泛應用卡莫氟前,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卡莫氟在水中的溶解度極低,這一特性使其難以應用于靜脈注射,同時卡莫氟透過血腦屏障的程度仍不明確。最新解析的酸性酰胺酶晶體結構為提高卡莫氟溶解性提供了一種新思路,該技術可以幫助預測卡莫氟活性位點,并通過修飾使其溶解性增大從而產生更好的療效[71]。另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法是誘導免疫系統產生自身抗體抵抗胞外的ASAH1分泌物,從而抑制ASAH1代謝物產生的放療抗性,同時也能夠緩解GBM放療抗性引起的腫瘤細胞的增殖和浸潤。ASAH1的自身抗體的進一步研究為GBM的治療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2.2 BRAF突變
最常見的BRAF基因的熱點密碼子錯義突變為V600E出現在多種神經上皮腫瘤中,包括多形性星形膠質細胞瘤、三分之一的神經節膠質瘤以及偶發性纖維狀星形膠質瘤。近5%的GBM患者中能夠檢測到BRAF V600E突變[72]。已有研究報道GBM中高頻發生的BRAF突變常伴有上皮樣細胞分化的組織學特征,如上皮樣GBM。2016年WHO首次將上皮樣GBM單獨歸類[73],該類患者通常為兒童或青少年,其中BRAF V600E發生突變的患者超過50%[74]。索拉菲尼是一種多重激酶抑制劑,作用靶點包括BRAF、VEGFR、PDGFR和受體絡氨酸激酶,最近有研究表明,使用BRAF抑制劑維莫非尼治療后,小兒GBM患者的BRAF V600E突變能夠得到回復[75]。在黑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和甲狀腺癌中已能靶向治療BRAF V600E突變。因此,對BRAF突變進行分子檢測或DNA測序以及使用BRAF V600E特異性抗體進行免疫組織化學檢測等方法,也許能夠發現一個針對一部分GBM患者的潛在治療靶點。
3 展望
近年來,GBM中研究發現的基因和分子通路上的異常為建立可行的臨床相關分子標志物提供了生物學基礎,并為發展新的治療手段提出了需求。對GBM在分子水平上分類的研究過程為發展出更有效的靶標治療手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許多臨床相關分子標志物已經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膠質瘤患者的臨床治療判斷標準中起到重要作用。如今,GBM患者(特別是晚期患者)的MGMT啟動子甲基化水平以及少突神經膠質瘤患者的1p19q共同缺失和IDH1/2突變水平,在腫瘤診斷或臨床治療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7,9,26,37]。與此同時,包括基因學、表觀遺傳學和轉錄組學以及近年來發展較快的影像學的多平臺分析為腦瘤的分類及預測病人預后提供了有效的分析研究手段。最近關于小兒GBM的研究表明該類腫瘤通常由組蛋白H3.3表觀遺傳變化誘導,除成人IDH1/2突變和IDH1/2野生型GBM,小兒GBM可能代表了第三大類的GBM。分子水平上的深入研究,為分子檢測的進一步優化提供了可能,并服務于臨床。這些技術有望被標準化和被更廣泛的應用,并成為更有價值的技術手段。在不久的將來,分子診斷作為補充手段填補到如今以組織學為基礎的腦部腫瘤診斷中,使基于生物學的腫瘤基礎研究與針對腫瘤患者的治療相結合,在分子水平上重新定義患者,使患者得到更精準匹配的治療。在未來,分子水平上的研究理論得到實質上的進步后,將使治愈GBM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