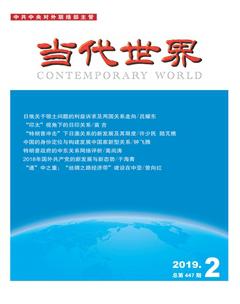“特朗普沖擊”下日澳關系的新發展及其限度
許少民 陸芃樵
【內容提要】近年來,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外交、防務、經貿和地區事務上的合作都呈現出穩步推進的態勢。“特朗普沖擊”無疑是推動日澳加快合作步伐的重要外在因素,但兩國關系的發展也具有穩定的內在驅動力,集中體現為促進經濟互補的需要、防范地區權力轉移的潛在風險、延續對其有利的區域秩序以及實現各自所重視的政治目標。然而,由于兩國在深化安全合作關系上面臨著諸如國內政治博弈、對“中國威脅”的認知差異,以及穩定對華關系的不同訴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掣肘,日澳在短期內實現軍事同盟化的可能性較低。
【關鍵詞】“特朗普沖擊”;日澳關系;同盟化;“印太”;“美國優先”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2.003
日本和澳大利亞是亞太地區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日澳兩國同為美國盟友,是美國維持亞太地區安全體系的“雙錨”。與此同時,由于在安全上嚴重依賴美國,日澳往往會因美國國家戰略的變化而調整其外交和安全政策。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競選之日起就彰顯出明顯的反傳統和反建制風格,上臺之后更是不遺余力地貫徹和落實“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特朗普政府在戰略和外交上呈現收縮傾向,在國際義務上要求給美國“減負”,在國防事務中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在經貿議題上采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以上主張和做法都給日本和澳大利亞造成了不小的“沖擊”。日本主流媒體和學界將這一現象稱為“特朗普沖擊”。不可否認,“特朗普沖擊”是日澳兩國近年深化戰略合作的重要外在推動力。然而,日澳兩國的合作也具有強烈的內在驅動力,畢竟兩國在安全、外交、經貿和地區秩序的認識上有著廣泛的共識和相似的利益關切。因此,客觀剖析“特朗普沖擊”下的日澳關系新發展,對于全面了解兩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動向,進而研判亞太局勢的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全方位穩步推進的日澳關系
過去15年來,澳大利亞安全政策的一個“亮點”是與日本發展緊密的戰略伙伴關系,兩國都宣稱彼此是除美國以外最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1]自從日澳在2014年7月正式宣布建立“特殊戰略伙伴關系”以來,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都保持著穩步推進的態勢,甚至有官員認為日澳已發展成為“準同盟”關系。[2] 2017年11月底發布的《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白皮書》對近年來日本國防和戰略政策改革表示歡迎,明確支持日本提升其軍事實力及在地區安全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白皮書還指出,澳大利亞會進一步在海洋安全和軍事研發等領域提升澳日防務合作水平。[3] 相應地,2018年5月發布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同樣高度評價日澳關系的全方位發展。該藍皮書特別將強化美日同盟重點表述為“強化美日同盟以及推進盟友/友好國家的網絡化”。[4]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臺之后,日澳在安全、外交、經貿和地區秩序等方面的合作步伐明顯加快。
一是保持頻繁且多領域的高層交往,鞏固戰略互信。2016年11月16日,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后數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便與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通話。雙方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交換意見,決定加強雙邊以及各自同美國的關系。[5]2017年1月,安倍訪問澳大利亞,日澳雙方就《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安全防務、地區秩序、朝核危機等議題進行深化合作達成廣泛共識。[6]在接受《澳大利亞財經評論》專訪時,安倍表示“日澳兩國關系處于歷史上最為緊密的時期”。[7]2018年1月,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選擇將日本作為當年外訪首站。訪日期間,日方給予特恩布爾極高的禮遇,邀請其出席由安倍主持、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和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參加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該會議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決策場所,其議事細節被視為國家絕密。特恩布爾是繼其前任總理阿博特和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后,第三個受邀列席該會議的外國首腦。這一特殊禮遇顯示出兩國關系的親密程度,以及日本試圖進一步強化雙邊關系的用心。2018年11月,安倍再次到訪澳大利亞,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一同來到達爾文市,拜謁二戰戰歿者紀念碑,以此彰顯日澳已就歷史問題達成和解。與此同時,日澳之間其他高層對話機制也在持續進行。例如,2017年4月和2018年10月,第七輪、第八輪外長和防長級磋商會議(以下簡稱“2+2”會議)如期舉行。2017年12月,日澳第三次網絡政策對話會舉行。2018年7月,日澳首輪經濟部長對話會舉行。此外,日澳兩國還在持續推動美日澳和日澳印三邊高層對話。
二是務實推進雙邊國防合作,積極拓展多邊防務協作。2017年1月,安倍訪澳期間,兩國簽署了《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的“升級”版。該協定于當年9月生效,允許日本自衛隊和澳軍相互提供彈藥等軍需品。澳大利亞是除美國之外,第一個與日本簽署該協定的國家,該協定的升級意味著日澳防務合作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日澳兩國當前還在加緊就《互惠準入協定》進行談判,這一協定將為兩國部隊在對方國家的訪問、駐留、演習、武器裝備進出境及軍人犯罪司法管轄等事項明確法律適用問題。該協定一旦簽署,將為日澳日后建立全面軍事合作關系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8]2018年10月,日澳在“2+2”會議中達成共識,提出日本航空自衛隊與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將于2019年進行首次聯合軍演。在雙邊合作之外,日澳兩國還積極在多邊框架下加深防務合作。例如,日本近年來已成為美澳間代號為“對抗北方”的年度軍事演習的常客,參演兵力和裝備水平逐年提升。2018年5月,日澳首次參加美國與菲律賓第34屆代號為“肩并肩”的年度軍事演習。2018年7月,日澳參加美國組織的環太平洋軍演,三國部隊首度演練實彈擊沉敵艦科目。2018年11月,美日澳三國展開海上掃雷聯合訓練,澳大利亞皇家海軍首次參與這一美日間海上定期聯合訓練。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報道指出,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加拿大所組成的情報共享網絡“五眼聯盟”正與日本等國加強針對中國的情報合作。[9]
三是深化雙邊經貿關系,共同捍衛戰略性自由貿易協定。日澳都是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堅定支持者。意識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原則將會給全球貿易體制帶來沖擊,兩國遂加緊在雙邊和多邊層面開展經貿合作。2017年1月,安倍訪澳期間,兩國代表簽署了氫能源供應鏈、澳大利亞Ichthys液化天然氣項目和農業合作等重大合作倡議備忘錄。2018年1月,特恩布爾訪日期間,兩國決定繼續深入推進上述合作項目并創設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和澳大利亞貿易、旅游和投資部部長間的經濟對話機制。兩國合作的成果在多邊層面體現得更為突出。日澳同為TPP的簽署國。在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國退出該協定之后,圍繞該協定的談判一度面臨被終止的窘境。然而,日澳兩國始終就該協定的存續保持著密切溝通,并一致決定在美國退出的情況下繼續推動該協定的達成與盡早生效。在兩國共同領導下,除美國外的原TPP成員國于2018年3月簽署《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并于2018年12月31日起生效。兩國目前還在繼續主導推進該協定關于接納新成員的相關談判,希望擴大該協定成員國的數量,增強兩國在塑造新一代貿易規則方面的影響力。此外,日澳兩國近來還就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議題保持著密切磋商,在2018年經濟部長對話會、“2+2”會議和首腦會晤期間,兩國都聲明將就改善WTO功能加強合作,并在產業補貼、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等熱點議題上增強政策協調。
四是合力推進“印太”概念,強化重點區域的政策協調。日澳同為“印太”概念的積極推動者,在推動特朗普政府采納“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戰略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兩國在這一概念下拓展多邊及區域合作的態勢非常明顯。在區域安全合作方面,目前日澳主要圍繞“四國安全對話”做文章。在2017年11月的東盟峰會上,美日澳印重啟“四國安全對話”。2018年6月和11月,第二、三輪“四國安全對話”相繼舉行。“四國安全對話”在時隔十年之后重啟,意味深長。盡管從目前來看,“四國安全對話”朝著軍事同盟化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其針對中國的企圖非常明顯。換言之,日澳試圖通過重塑這個機制,以美國作為安全保障的核心,拉攏印度平衡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在區域基礎設施合作方面,日澳正聯合美國共同推進“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倡議”。該倡議被視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方案,矛頭直指中國。2018年7月,時任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宣布,美日澳將為印太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建立“三邊伙伴關系”。[10]2018年11月12日,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澳大利亞外交部和出口信貸保險公司聯合簽署合作備忘錄,決定加強在印太地區開展第三國基礎設施、能源和自然資源領域的合作。2018年11月18日,澳大利亞、日本、美國、新西蘭與巴布亞新幾內亞政府達成協議,計劃在該國建立電網,以期至2030年能讓該國70%的人口獲得穩定的電力供應。
日澳關系深化的動因
2016年11月,奉行“美國優先”原則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預示著美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將會出現明顯轉變。出于對美國維持亞太地區安全秩序決心和意志的擔心,日澳兩國主動調整外交政策,加強雙邊戰略合作,以應對亞太地區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
其一,“特朗普沖擊”放大了日澳兩國對美國安全承諾可靠性的懷疑,推動了兩國在雙邊和多邊框架下的安全合作。特朗普在處理同傳統盟友的關系時,更強調現實利益和交易,較少關注意識形態。競選期間和上任之初,他頻頻指責包括日本在內的盟友在安全上“搭美國便車”,認為美國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過多,因而多次強硬要求盟友負擔更多的駐軍費用,并增加國防支出。在加征鋼鋁關稅等貿易爭端上,特朗普政府最初也并未對盟友網開一面,而且持續對日本等盟國施壓以實現貿易上的“對等互惠”。在亞太地區權力轉移的背景下,日澳兩國戰略界近年來已對美國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障盟友的安全有所懷疑。奧巴馬政府推行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安撫該地區盟友的考量,可視為對其盟友的“再保證”。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言行無疑加劇了日澳兩國的擔憂。因此,日澳兩國在安全領域都加強了“兩面下注”:一方面,采取種種措施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系,不厭其煩地要求美國確認其區域安全承諾;另一方面,強化和美國其他盟友及安全伙伴的防務合作,從而確保即使美國在安全領域力有不逮或者意興闌珊的情況下,各自的國家安全也能有所依托。日澳由于具備良好的防務合作基礎,且都是亞太區域內具有一定軍事實力的國家,因此安全領域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兩國強化合作的重點。
其二,“特朗普沖擊”加劇了兩國對現有國際秩序發生動搖的憂慮,促進了兩國在維護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和地區秩序等方面的合作。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引領西方國家建立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日澳兩國都將這一體系視為其國家賴以發展和繁榮的依托。然而,特朗普認為,美國過度負擔了提供公共產品和安全保障的責任,對于維護這一體系的熱情不高,因而一度表露出戰略收縮的傾向,并且接連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和多邊條約。這引起了日澳的高度警惕,擔心這一國際體系遭到嚴重削弱。這一擔憂在貿易秩序和區域秩序上體現得尤為突出。特朗普傾向于采用雙邊方式處理經貿關系,對于多邊自貿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似乎非常不屑,上臺之初便選擇退出TPP。由于日澳為推進這一協定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資本,都認為其能夠鞏固西方世界在貿易規則方面的主導權,因此美國的退出引起了日澳兩國的極大反彈。在區域事務上,日澳也非常擔心實用主義色彩濃厚的特朗普可能會展開“越頂外交”,即在不征詢盟友意見情況下和中國就亞太事務達成戰略協調。這些擔憂迫使日澳在上述領域加緊合作。
然而,盡管“特朗普沖擊”是近年來日澳深化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外在因素,但歸根結底,日澳關系的發展有其穩定的內在驅動力。這一驅動力在短期內很難發生顯著變化,因此可以預判兩國關系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會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具體分析如下:
一是兩國經濟具有高度互補性和深厚的合作基礎。兩國資源稟賦各異,產業高度互補。自1957年日澳簽訂商業協定并恢復正式經濟交往以來,兩國經貿關系迅速發展,奠定了兩國在其他領域開展良好合作的基礎。2014年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鞏固了雙邊經貿關系。2017年,日本是澳大利亞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場。[11] 日本市場對于澳大利亞而言至關重要。作為嚴重依賴資源和原料進口的工業國,日本也需要澳大利亞穩定地供應戰略資源。深化兩國關系對于促進各自經濟增長都大有裨益。
二是兩國都對中國崛起引發的權力轉移非常擔憂。中國的迅速崛起使得地區權力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兩國在不同程度上都將中國崛起視為戰略挑戰,彼此都擔心崛起后的中國會使用強力解決相關安全矛盾,尋求亞太地區主導權,抑或嘗試改寫區域乃至全球秩序規則等。兩國經濟上的對華依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這些憂慮,這是因為兩國擔心中國可能利用這種經濟相互依賴關系,對兩國施加政治影響力。因此,兩國都希望通過“抱團取暖”的方式來對中國形成某種制約,減少權力轉移可能帶來的風險。
三是兩國都倚重“以規則為基礎”的區域和國際秩序。日澳關系的深化還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因素作為基礎。兩國都自視為民主國家,自視在堅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區域和國際秩序上立場吻合,并且對中國等政治經濟制度有所不同的國家持保留意見。這在兩國保守政黨執政時期體現得非常明顯。尤其是在地區權力結構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兩國對于某些國際規則的堅持更為突出,更加希望通過強化合作來加強這些規則對于大國的約束力,從而保障自身利益。
四是雙邊關系深化有利于促進兩國各自的政治目標。對日本而言,深化和澳大利亞的關系有利于實現其“大國抱負”。長久以來日本都希望在國際舞臺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但其軍國主義歷史也時常引起周邊一些國家的擔憂。因此,對日本而言,澳大利亞的支持顯得難能可貴,往往能夠緩和日本在東北亞面臨的外交窘境。澳大利亞甚至還投日本保守政治勢力所好,對日本推動“新安保法案”和謀求“修憲”等頗具爭議的議題展示出支持態度。對澳大利亞而言,與日本構建良好的關系有助于其融入亞洲,甚至在地區事務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澳大利亞長久以來都面臨著在其西方的“歷史”情結與靠近亞洲這個“地理”因素之間的艱難調和。[12]不少亞洲國家對于澳大利亞加入一些亞洲區域組織,或對亞洲事務“指手畫腳”心懷不滿。然而,日本的加持讓澳大利亞能夠成功地加入諸如東亞峰會等區域組織,使得澳大利亞能夠更加名正言順地就該地區事務發聲。
日澳關系同盟化的限制性因素
盡管日澳關系近年來發展熱絡,但短期內兩國發展為具有共同防御義務的軍事同盟的可能性較低。這是因為日澳軍事同盟化面臨一系列內外限制性因素,這些因素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發生明顯變化。
首先,日澳關系往同盟化方向發展時面臨著各自國內政治的束縛。這一束縛在日本方面體現得尤為突出。盡管日本右翼勢力力圖實現所謂“國家正常化”,但在社會層面和平主義理念仍然深得民心,秉持和平主義理念的政黨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制衡作用。并且,盡管以“和平憲法”為代表的相關制度安排可能逐漸被弱化,但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間被全然推倒。在這個背景下,日本與除美國之外的第三國達成軍事同盟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日本憲法,并為日本民眾廣泛接受,非常值得懷疑。事實上,澳大利亞在2007年就提出與日本達成類似于澳印(尼)《龍目條約》的正式安全協定,但當時安倍內閣自知這一提案難以合憲,也難以爭取到民眾支持而最終選擇放棄。[13]在澳大利亞方面,雖然澳大利亞自由黨和工黨在諸如美澳同盟、融入亞洲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這些事關國家安全的議題上已經形成共識,[14]但兩黨對于某個具體的外交和安全議題的重視程度和操作方式時常存在差異甚至矛盾。如何協調與日本和中國的關系,始終是澳大利亞兩大政黨面臨的重要考驗。政黨的輪替,甚至是執政黨黨魁的輪替都可能給日澳安全關系的實質深化帶來變數。
其次,日澳對“中國威脅”存在認知差異。盡管日澳都視中國崛起為戰略挑戰,并且擔憂中國可能對其國家安全和區域秩序造成負面影響,但對于“中國威脅”的嚴重程度,以及應當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日澳的認知存在“溫度差”。與日本不同,澳大利亞在同中國交往時沒有歷史包袱,兩國間也不存在領土及海洋權益爭端。因此,相對于日本而言,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看法相對積極。盡管澳大利亞一些政客和媒體近年來竭力炒作“中國干涉論”和“中國滲透論”,但澳大利亞民眾對華的看法仍然相當正面。譬如,澳權威智庫羅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18年公布的民調顯示,82%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更像是“經濟合作伙伴”,而非“軍事威脅”。在評估對澳大利亞核心利益的潛在威脅程度時,“中國日益增長的國力”僅僅排在第11位,只有36%的受訪者認為其是“重大威脅”。相比之下,42%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是重大威脅。[15]因此,澳大利亞要同日本發展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關系并不具備充分的民意基礎。此外,一旦與日本結為軍事同盟后,澳大利亞對可能被迫卷入中日間圍繞島嶼或海洋權益發生的軍事沖突的前景非常擔憂,因此并不希望簡單地將自身與日本的國家利益完全捆綁在一起,不愿意貿然大幅提升澳日安全關系。
再者,日澳在經濟上極其倚重中國,都希望在深化雙邊關系時避免過度刺激中國,維持對華關系的穩定。中國的經濟騰飛給日澳帶來了豐厚的經濟紅利。近幾年,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保持了自2009年以來的領先地位。自2007年開始,中國一直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國。經濟上對于中國的倚重讓日澳兩國在發展雙邊軍事關系時不得不有所顧忌。這種希望避免過度刺激中國的基調在日澳兩國安全合作起步之初便已確立。在1997年第三次臺海危機之后,當時安全合作尚淺的日澳兩國決定加強防務合作。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出于安撫中國的需要,排除了迅速提升澳日安全合作的選項,推崇以逐步拓展安全對話的方式來加深合作。[16]在此后澳日深化安全合作的過程中,這一基調貫穿始終。一個明顯的例證是2007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出于穩定中澳關系的深思熟慮,最終選擇退出美日澳印首次“四國安全對話”。[17] 另外一個例證是2016年日澳關系發展看似“如火如荼”,但澳大利亞最終卻棄購日本蒼龍級潛艇。這一決定似乎也很難與中國因素相剝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澳兩國擔心被中美間可能加劇的戰略競爭所牽連,都在積極謀求改善對華關系,以獲得更大的外交轉圜余地。例如,安倍晉三于2018年10月成功訪華,成為近7年來首位訪華的日本首相,反映出中日關系持續回暖的勢頭。為消除中方警惕,日本在近期甚至將“印太”戰略改稱為更加中性的“印太構想”。2018年11月,澳大利亞外長佩恩訪華,也表明近一年來“凍結”的中澳關系出現緩和。在這一背景下,日澳日后在繼續深化軍事合作時無疑會更加謹慎。
結 語
綜上所述,日澳雙邊關系的深化是兩國面對特朗普上臺以來的國際形勢變化,為維護自身國家利益而采取的一種理性行為。經過多年的良性互動,兩國目前已經建立了成熟的合作機制。雖然兩國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同盟化,即在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上存在一定變數,但可以預測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兩國仍會繼續“抱團”。客觀地說,日澳合作有多重目的,制衡中國并不是日澳加強合作的全部出發點。其合作對中國的影響也存在正反兩面。在維護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反對貿易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堅持自由貿易方面,日澳加強合作對中國而言是利大于弊,中國應當予以鼓勵。但對于兩國加強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合作,以冷戰思維和零和思維干預區域事務,并合力在國際社會渲染“中國威脅論”,以及建立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排他性”俱樂部則要保持高度警惕。目前,中日、中澳關系都迎來了積極的發展勢頭,三方都應當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局面,切實維護好中日、中澳關系的政治基礎,以實際行動積極拓展三方國家利益交匯點,拓展在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第三方市場開發和基建、科技創新等多領域的務實合作,從而促進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
(第一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副研究員;
第二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責任編輯:魏丹丹)
—————————
[1] Nick Bisley, “Australia Navigates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in Jeffrey Reeves, Jeffrey Hornung, and Kerry Lynn Nankivell eds., Chinese-Japanese Competition and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Complex,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207-215.
[2] John Garnaut, “Australia-Japan Military Ties are a ‘Quasi-Alliance, Say Officials”,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australiajapan-military-ties-are-a-quasialliance-say-officials-20141026-11c4bi.html.
[3]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7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p. 41.
[4]《平成30年版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fp/pp/page23_002506.html。
[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Australia Summit Telephone Talk”, https://www.mofa.go.jp/a_o/ocn/au/page4e_000557.html.
[6]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Meeting Outcomes: Visit to Australia by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218411.pdf.
[7]Michael Stutchbury and Angus Grigg,“Shinzo Abes ambitious Indo-Pacific agenda”, https://www.afr.com/brand/business-summit/shinzo-abes-ambitious-indopacific-agenda-20180119-h0l6g6.
[8] Jamie Smyth and Robin Harding, “Australia and Japan Eye Military Co-operation Pact”, https://www.ft.com/content/ec00b39e-fb0e-11e7-9b32-d7d59aace167.
[9] Noah Barkin, “Exclusive: Five Eyes Intelligence Alliance Builds Coalition to Counter Chin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fiveeyes/exclusive-five-eyes-intelligence-alliance-builds-coalition-to-counter-china-idUSKCN1MM0GH.
[10]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Australia, “The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nounce Trilateral Partnership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au.usembassy.gov/the-u-s-australia-and-japan-announce-trilateral-partnership-o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in-the-indopacific/.
[11]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Japan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ttps://dfat.gov.au/geo/japan/Pages/australia-japan-bilateral-relationship.aspx.
[12] Paulo Gorj?o, “Australias Dilemma between Geography and History: How Consolidated is Engagement with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3, No. 2, 2003, pp. 179-196.
[13] Greg Sheridan, “Security Treaty Rejected by Tokyo”,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nation/security-treaty-rejected-by-tokyo/news-story/501f3084e08d35fe1630752abec0f316?nk=664c3e893046fd95d732ffacc9f813e2-1544000015.
[14] Andrew Carr, “Is Bipartisanship on National Security Beneficial? Australias Politics of Defence and Secur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63, No. 2, 2017, pp. 255-259.
[15] Lowy Institute, “2018 Lowy Institute Poll”,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2018-lowy-institute-poll.
[16]《日豪共同記者會見記録-(概要)》,https://www.kantei.go.jp/jp/hasimotosouri/speech/1997/0502soriaust.html。
[17] Takeshi Terada, “Evolution of the Australia-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Toward a Softer Triangle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Asian Visions, No. 35, Oct.2010,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