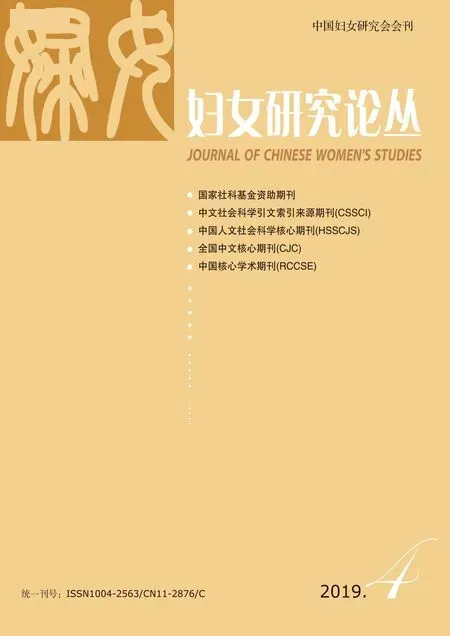婦女地位:概念、測量與理論*
——全領域與家庭領域的觀察
宋 健 張曉倩
(1.中國人民大學 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2.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與人口學院,北京 100872)
婦女地位是衡量“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實現程度的重要指標。家庭領域的婦女地位指相對于其他領域而言的、婦女地位在家庭領域中的表現,很多學者也將其稱為婦女家庭地位。本文在下述情景下使用家庭領域婦女地位和婦女家庭地位兩種說法:前者強調范疇維度上其與婦女地位整體概念的聯系,以及與其他領域婦女地位的比較;后者側重指標測量維度。由于婦女地位呈現相對性及多維性特點,迄今為止,國內相關研究對婦女地位的概念界定和指標測量仍存在分歧,并因此影響到對家庭領域婦女地位性質和定位的認識,也阻礙了婦女地位深入研究的開展。
本文試圖回答如下問題:如何界定與測量婦女地位?家庭領域婦女地位在婦女地位中的定位和作用是什么?婦女地位及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研究中有哪些常用的理論視角以及存在哪些分歧?為此,本文首先明確婦女地位概念及其在家庭領域的內涵;其次梳理婦女地位的測量現狀及其在家庭領域的體現;再次比較分析婦女地位及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研究的理論視角及可能存在的分歧;最后對現有研究進行評述并對未來研究走向提出建議。本文的可能貢獻是,通過對現有研究的梳理,澄清基本概念,明確測量誤區,實現理論認同,以便對后續研究提供借鑒和啟發。
一、婦女地位的概念及其在家庭領域的內涵
(一)婦女地位的概念辨析
在現有的國內文獻中,對婦女地位的概念名稱使用及概念間的相互關系還存在分歧。
其中一種理解是將“婦女地位”和“婦女社會地位”視為可交替使用的同一概念,指婦女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中所處的位置[1],是不同女性群體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中與男性相比較的權利、資源、責任以及婦女作用被社會認可的程度[2];其中婚姻家庭只是“婦女地位”概念的一個測量維度,因此“婦女家庭地位”是從屬于“婦女地位”或“婦女社會地位”下的子概念[1][2]。
另一種理解是將“婦女地位”和“婦女社會地位”兩個概念相區別,認為“婦女地位”是指婦女研究中所有涉及婦女地位維度的總稱,而“婦女社會地位”和“婦女家庭地位”均是從屬于婦女地位下的子概念。由此可從三個視角對“婦女社會地位”和“婦女家庭地位”關系進行觀察:一是從社會領域和家庭領域視角,認為二者是相互獨立且平行并列的概念[3];二是認為這兩個概念分別從宏觀和微觀角度反映了“婦女地位”[4][5];三是認為這兩個概念分屬于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6]。
(二)婦女地位概念的特點
盡管在概念名稱上存在分歧,但現有研究對“婦女地位”概念的特點卻基本達成了共識,即認為其具有相對性、多維性、多重定位性和情境依賴性等特點。
相對性體現在它是從性別平等的視角出發、以男性地位作為參照系的概念。
多維性(multidimensionality)體現在,由于性別不平等現象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使該概念包含了婦女的威望(prestige)、權力(power)以及獲取或控制資源(resources)的能力和程度等多層次內涵[7][8]。值得注意的是,婦女地位不同內涵維度的方向可能并不一致,如女性具有較高威望,不一定等同于其具有較大的自主權和對資源的控制權[7][9]。
多重定位性(multiple locations)是指婦女地位在不同空間和時間上存在差異性,如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不一致[10](PP 347-378);處于不同生命周期時不一致(如在某些亞洲國家,婆婆的家庭地位高于兒媳;在某些彝族家庭中,有孩子女性的家庭地位高于沒有孩子的女性)[7][11];等等。
情境依賴性(context dependency)是指在不同文化或歷史情境下,某社會習俗或法律權利對女性地位的影響有所差異。如某一情境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可能與其地位提升高度相關,但在另一情境下卻未必如此[12]。因此,在對婦女地位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有必要清楚地掌握婦女群體所處的文化情境,這有助于決定婦女地位的哪些方面對于研究是重要的,也有利于決定這些變量如何被解釋[13]。
(三)西方研究中婦女地位概念使用的演變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相關研究中,婦女地位這個概念本身已遭到質疑。凱倫·奧本海姆·梅森(Karen Oppenheim Mason)在對“婦女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或female status)概念進行梳理的過程中特別指出[7],社會中至少存在兩種獨立的分層體系(即不平等的制度化體系),分別是種族或階層的分層體系以及性別分層體系(gender systems of stratification)。這兩種分層體系彼此交互作用,使得難以辨認“一個女性之所以貧窮,是由于其性別特征,還是由于其屬于貧困階層,或源自兩者”。“婦女地位”概念雖然是在性別分層理論視角下進行討論的[5][14](PP 667-700),但在研究中卻難以將其與種族或階層分層體系相區別,“地位”(status)這個詞又往往會與“威望”(prestige)、“尊重”(esteem)等詞相混淆[12]。加之“婦女地位”是以男性作為參照系的、衡量女性與此參照系偏離程度的概念,可能會扭曲社會現實,因此最好用更公平、準確的“性別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或具體類別的性別不平等概念代替含義模糊的“婦女地位”概念進行分析[7]。
在其后的研究中,更多西方學者不再籠統使用“婦女地位”概念,而是使用“自主權”(autonomy,強調個體層面)、“賦權”(empowerment,偏重于強調群體層面)等概念來反映婦女的自主決策權和資源控制力,并用其分析性別不平等的不同維度及其程度[12][15](PP 1222-1263)[16](PP 367-381)[17](PP 77-97)[18](PP 775-796)。
(四)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的概念與特點
從上述概念辨析可以發現,婦女地位在范疇維度上可能涉及多個領域,其中對社會領域是一個廣義的覆蓋性范圍還是狹義的與其他領域相平行的范圍的理解,導致對概念名稱使用上出現分歧。相比較而言,家庭領域界定相對清晰,特指由家庭成員組成的私領域,是婦女地位范疇維度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領域。家庭領域的婦女地位是指婦女擁有或控制家庭資源(財產、收入等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能力、在家庭中的威望和權力(包括收入管理權、收入支配權、消費決定權、對子女前途的發言權、婚姻自主權、生育決策權、勞動分工決定權等)以及主觀滿意度[11][19](PP 1-9)[20](PP 17-25)[21](PP 134-152)[22](PP 60-76)等,對整體上婦女的資源掌握、權力威望及其幸福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家庭領域婦女地位同樣具有相對性、多維性、多重定位性及情境依賴性特點。所不同的是,“婦女地位”概念的相對性是以男性為參照系;而家庭領域婦女地位則以其他家庭成員為參照系,既有相對于橫向的代內關系如妻子與丈夫的比較,也有相對于縱向的代際關系如兒媳與婆婆的比較[23](PP 87-93)[24](PP 102-110),還有婦女作為家庭成員個體在家庭總權益格局中與其他所有家庭成員的比較[25](PP 71-76)。
二、婦女地位測量及其在家庭領域的體現
(一)婦女地位的綜合測量指標
與對婦女地位概念認識的不斷深化相對應,對婦女地位的測量總體而言經歷了從試圖構建統一的綜合指標體系到轉向精細化測量的過程。
1988年美國人口危機委員會(the 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曾建立了一套評價婦女地位的綜合指標(PCCI),試圖用5大類20項指標綜合評價世界99個國家和地區的婦女地位,每項指標5分,滿分100分。這一綜合指標包括健康、教育、就業、婚姻與生育、社會平等(social equality)5個測量維度,每個測量維度中包含4個測量指標,前3個指標比較國家間婦女地位,第4個指標描述國家內部的性別差異程度。其中,健康測量指標包括女嬰及女童死亡率,15-45歲育齡婦女死亡率,女性平均預期壽命,以及平均預期壽命的性別差異;教育測量指標包括中學女教師比例,女孩小學和中學的入學率,20-24歲婦女的大學入學率,以及識字率的性別差距;就業測量指標包括15歲及以上婦女自我就業比例,15歲及以上婦女有報酬就業比例,15歲及以上婦女中專家、技術、管理人員比例,有報酬就業的性別差異;婚姻與生育測量指標包括總和生育率,15-19歲女性早婚率,已婚婦女避孕比例,男女鰥寡居、離婚或分居人數之比。社會平等測量指標包含經濟平等,政治、法律平等,婚姻、家庭平等,以及男女社會平等對比[26](PP 39-44,51)[27]。
這一指標雖為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一些報告所采用,但其缺陷在于未考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境,用同樣的方法來界定婦女地位易造成偏誤;且該指標未能區分婦女的絕對地位和以男性為參照的相對地位,國家間絕對指標的直接比較并不能反映性別差異,只能反映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因此,指標受國家貧困程度或人均收入的極大影響,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發達國家排名靠前、發展中國家排名靠后。
為了彌補這些缺陷,巴基斯坦學者[27]構建了更符合發展中國家情境的、包含更多測量指標的婦女地位替代性綜合度量指標ACI(Alternative Composite Index),將測量維度擴展為8個:健康、就學、成人教育、勞動參與、就業條件、家庭生活、政治代表性以及法律權利,每個測量維度僅包含2個反映性別差異的測量指標。每個測量指標賦值1-100,分數越低,說明情況越差。16個測量指標加總分類后再進行國家間的比較,得到的結果與使用PCCI排序的結果有很大差別。然而,ACI指標中并未對上述8個測量維度及每個測量維度中選取2個測量指標的合理性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因而其應用也并不廣泛。
(二)家庭領域婦女地位在測量維度中的體現
根據業已構建的綜合指標體系發現,婦女地位的內涵維度(資源控制力、威望、權力等)和范疇維度(社會、家庭等)均被糅合進測量維度中。總體而言,在國內外學者構建的婦女地位綜合指標中,取得共識的測量維度包括:經濟地位指婦女在經濟活動方面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以及婦女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程度,是構成婦女地位的物質基礎;政治地位指婦女享有的政治權利(right)和擁有的政治權力(power);教育地位指婦女受教育機會的多少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健康地位指婦女的身體健康狀況;家庭地位指婦女獲取或控制家庭資源的能力及其在家庭中的威望和權力。除了上述測量維度之外,法律地位、勞動地位、生活方式、社會參與/社會地位、社會性別觀念等有時也被納入婦女地位的測量中[2][28][29]。
一方面,我們注意到社會領域的婦女地位并未以“婦女社會地位”的統一名稱出現在指標的測量維度中,而是被分解為政治地位、教育地位等其他測量維度,反映了社會領域婦女地位的廣闊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家庭領域的婦女地位雖然在概念名稱上略有參差,以“家庭地位”或“婚姻家庭地位”[30]出現,但這一測量維度幾乎包含在所有的婦女地位測量指標體系中,這充分說明了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研究的重要性和相對獨立性。
各測量維度包含的測量指標因情況而異。一般而言,經濟地位多采用女性在業者的平均月收入、女性就業比例、失業人員中女性比例、婦女有報酬就業的比例、各行各業勞動者中女性所占比例等測量指標。政治地位一般通過女性參政議政程度或采用職業分層指標來衡量,通常涉及婦女所從事的職業在職業分層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在工作中是否處于領導地位,如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中女性比例;也涉及是否有女性權益保障的專門法律或法律條款等測量指標。教育地位一般使用各級、各類學校女性入學、在學比例,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同類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女性比例等測量指標。健康地位包括女嬰/女童死亡率、棄嬰中女嬰比例、育齡婦女死亡率、女性平均預期壽命、平均預期壽命的性別差異、健康自評狀況等[26][28][29][31]測量指標。家庭地位測量維度的具體指標隨后將單獨闡述。
(三)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的測量
與社會領域婦女地位測量缺乏統一概括性名稱不同,家庭領域婦女地位在測量維度上集中使用“婦女家庭地位”概念,在這一共識基礎上,不同學者的研究視角略有差異。如通過依附地位和成就地位兩個視角衡量婦女家庭地位[19],前者指未經后天選擇和努力、依附男性而得到的地位;后者指女性經過自身的選擇和努力而獲得的地位。或者將婦女家庭地位劃分為家庭政治地位和家庭經濟地位兩個組成部分[29]。也有學者從法律地位、自主地位、管理地位、決策地位以及時間利用地位5個維度構建婦女家庭地位的綜合評價指標[32]。
早期學者主要使用宏觀指標(如各測量維度的性別比或率指標等)構建婦女家庭地位綜合指標。而后有學者基于普查資料和問卷調查將家庭地位指標區分為間接指標(分性別戶主率之比、分性別的平均初婚年齡、夫妻平均年齡差等)和直接指標(夫妻家務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之比、夫妻對家庭資源的支配權力、對自身和家庭成員及重大事務的決策能力、對家庭規模及生育的決策權等)兩類[19]。隨著國內婦女研究相關調查數據的日益豐富,特別是1990年以來三次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開展,許多學者開始逐漸采用抽樣調查問卷中的微觀數據構建婦女家庭地位指標。如有學者系統整理了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家庭地位相關問題,構建了基于該數據庫的、較為完整的、微觀層面的家庭地位指標,包含了家庭事務決策、個人事務決策、夫妻權力責任分擔、夫妻財產占有、夫妻關系、家庭暴力以及家庭地位主觀滿意度這幾個方面的測量[3]。隨著研究的深入,家庭地位指標的測量日益細化。
威望和權力作為婦女地位的重要內涵維度廣受關注。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研究中,家庭威望和權力一直是重點研究內容,其中夫妻的相對權力結構最為引人注目。關于夫妻權力關系的早期主要發現來自于布拉德(Blood,R.O.)和烏爾夫(Wolfe,D.M.)在1954年所做的基于大量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其重要貢獻之一在于說明了夫妻權力的多維性特征,認為對夫妻權力的單維測量是不適用的[33]。之后有學者將夫妻各自占有的家庭資源視為權力的基礎,將雙方在商議事情、解決問題和處理沖突方面的互動過程視為權力的實施過程,將最終由誰做決定視為決策結果,由此構成家庭權力運作的三大要素[34][35]。有一些學者用賦權(empowerment)概念來代表婦女地位的權力維度[36],因此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也被看作“去權”(disempowerment)的一種極端形式[37]。國內早期研究多關注家庭事務決策權和家務分配情況[19][26][29][38],但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學者提出應區分家庭事務決策權和個人事務決策權,認為提高婦女家庭地位的努力主要不在于把提高妻子擁有家庭實權的比重作為發展目標,而應將關注點集中在倡導平等、獨立、和諧、互惠的夫妻伙伴關系上,因此,個人事務自主權作為婦女家庭地位滿意度的預測指標更具有解釋力[35]。而后徐安琪在文章中進一步梳理了婦女家庭地位研究中權力測量指標從“經常性和一次性決策家庭事務話語權”“重大家庭事務決策權”到“多元指標綜合判定法”“個人事務自主權”的演變脈絡,提出可用“個人家庭生活各項事務自主權”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觀滿意度”兩大類、9項指標構建婦女家庭地位指標體系[21],其貢獻在于將主觀滿意度納入婦女家庭地位測量維度中。但這類指標體系只關注了決策的結果,忽略了權力運作的動態性和過程性,在指標構建的過程中還應當進一步關注權力基礎和權力實施過程[34][39][40]。
三、婦女地位及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研究的理論視角
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相較其他領域,現有研究對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的概念界定更為清晰,測量更為集中,特別是基于問卷調查數據的微觀層面分析使測量與現實結合得更加緊密。部分學者已注意到了這一概念本身強烈的情境依賴性,因此對不同群體婦女進行測量時選取了更有特色的指標,如對農村婦女家庭地位測量中增加了村莊社會交往權[41]、父母或公婆贍養決策權[42]等適應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的項目。但由于理論視角的不同,在家庭領域與社會領域婦女地位相互關系及影響機制等關鍵性問題上仍存在較大分歧。
(一)婦女地位研究的理論視角
婦女地位研究主要基于性別分層的理論視角。20世紀60年代中晚期女性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后,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在對經典社會學關于階層分析的批判中,最主要的批判是認為其忽略了性別維度[43](P 6),而性別分層是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表現。性別分層是指女性和男性有著不同的勞動分工角色,并因此在對資源控制的類別和數量上存在差異[7]。女性主義的性別分層理論包括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的“四大機制”理論(即將女性受壓迫的機制概括為生產、生育、性和兒童的社會化)、蓋爾·盧賓(Gayle Rubin)的性/社會性別制度理論等[43](PP 122-124),其主要思路是把性別作為分析社會不平等的分層指標,以性別視角研究男女兩性社會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狀態,旨在揭示社會分層結構[44],刻畫女性這一群體相較于男性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中的位置。
正因為婦女地位研究的這一重要理論視角,凱倫·奧本海姆·梅森在其發表于1986年的經典文獻中提醒注意性別分層體系與種族/階層分層體系間的彼此交互作用會干擾對婦女地位的研究和判斷,并建議采用其他更準確具體的概念以避免歧義[7]。
(二)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研究的理論視角
在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相關研究中有多種理論視角,如生命周期理論、性別平等理論、女性主義理論等,最普遍使用的有三種視角:文化制度論、資源論、相對的愛和需要理論(relative love and need theory)。后兩種視角實際都源自社會交換論的理論框架,即認為價值資源的交換是社會的基本過程,社會互動圍繞著行為者之間的資源交換而展開,社會關系即資源交換關系[43](P 75)。
文化制度論(也稱文化決定論)認為,家庭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婦女地位都受制于社會的文化背景。父權制是造成社會性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制度性因素,在以從夫居為表征的父系宗族結構中,婦女以依附性的角色出現,從屬于父系家庭和宗族,其地位無足輕重。由于文化變遷的惰性,傳統的制度文化特別是家庭文化仍形塑著當下家庭的權力結構[24]。
資源論(也稱經濟決定論)中最典型的當屬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觀點之一,因此恩格斯在其關于婦女問題的闡述中提出,男人掙錢養家的事實賦予了其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只有女性走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勞動,才能提升女性地位[48]。在家庭領域,個人所擁有的威望和權力來源于配偶雙方所占有資源的比較,女性由于在教育程度、職業階層和收入等方面劣于男性,在家庭關系中容易處于不利地位。但家庭成員依靠社會地位所獲取的社會資源,并不直接決定其家庭地位高低,還需要在家庭中根據其所處的不同角色和地位重新分配[19]。有學者提出“相對資源稟賦結構”概念[3],指在特定的資源分配體系(可以是家庭、組織、社會)中,不同的個體或群體所處的相對位置,其位置決定了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對地位。
相對的愛和需要理論關注婚姻擇偶中資源交換在家庭的延續,指男女通過結婚交換各自的資源,由于其本身自帶的資源可能不平等,因此在婚姻中獲利較多的一方往往較依賴配偶并在日常生活中較順從對方;而對夫妻關系較少依賴或相對缺乏興趣的一方,更可能利用本身的資源影響家庭決策。在傳統的社會中,通常認為女性往往將婚姻作為自己的歸宿,在經濟上和感情上更多地依附丈夫,更需要守住家庭,因此有更大的概率放棄權力或接受配偶的支配從而處于低下的家庭地位[34][35][39]。在這一理論基礎上,國內有學者基于中國當前農村婦女雖經濟上依附于男性但在家庭中卻具有支配性強勢地位的“依附性支配”現象提出了新的解釋,認為隨著出生性別比失衡和女性流動人口增加所導致的農村地區婚姻市場失衡,通過經濟分化和情感需求增強兩種機制,農村婦女家庭地位得到提升[45]。
(三)家庭領域與社會領域婦女地位的相互關系
雖然學界公認婦女家庭地位是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的唯一測量維度,但如何看待不同領域特別是社會領域與家庭領域婦女地位間的關系,以及婦女在公共領域的發展是否會影響其私人領域的地位,這兩個關鍵問題仍存在分歧。需要指出的是,社會領域婦女地位并沒有相應的“婦女社會地位”統一測量維度,而是分解為多重測量維度,但現有研究中很多學者仍使用“婦女社會地位”這一概念,并將其與“婦女家庭地位”進行比較。
一些研究證明,女性社會地位越高,其家庭地位越高,家庭內的性別關系越趨平等[4],比如女性的收入越高,其在家庭中的權力也就越大[46][47];但也有研究表明,女性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女性的社會地位未必能直接轉化成家庭中的性別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若干中間變量,如性別文化、女性自我意識、女性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等因素的影響,如女性的性別角色觀念越民主、現代,就越傾向于使用平權或妻權方式來決定家庭重要事項[48]。也有研究認為女性勞動參與的提高和對工作的更多投入,總體而言不會等量提升女性家庭地位和整個家庭的滿意度,甚至會產生負面效應[49]。這種情況被一些學者認為是社會情境差異帶來的影響,因為在西方發達國家資源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而在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受到文化和制度的影響[42]。
此種分歧的存在說明當前國內學界對社會領域和家庭領域婦女地位之間相互影響的機制還缺乏深入探討,對家庭私領域內婦女地位如何受到其社會公領域地位影響的研究還缺少共識。理論上,社會領域婦女地位是婦女地位在家庭外部經濟、教育、勞動等多方面社會分層的反映,是其在家庭外部資源占有程度和能力的體現,因此,探討社會領域和家庭領域婦女地位之間是否存在關系以及存在何種關系,其實質就是探討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地位是否以及如何影響其在私人領域的地位。從資源理論取向分析來看,其資源決定權力的解釋邏輯必然會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聯系,因為女性的經濟能力、教育程度都主要來源于婚姻外部,必然會形成家庭內外部地位交叉影響的情形。但就文化制度論和相對的愛和需要論而言,則不一定認同這種關系,因為這兩種理論取向都更強調權力和權威的作用。
四、簡要的評述及未來研究展望
“男女平等”既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也是社會性別平等理念下全世界追求的目標。以往研究積累了豐富文獻,取得了一些共識,為后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也存在較多分歧,加之現實不斷變化,促使我們深入思考婦女地位及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的現有問題與未來研究方向。
概括而言,現有相關研究的分歧主要基于以下兩個重要問題:如何分辨與理解婦女地位的內涵維度、范疇維度與測量維度?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構建婦女地位綜合指標體系?
對于第一個問題,筆者認為,有必要區分婦女地位不同層次的維度,這是化解分歧、凝聚共識的重要步驟。現有研究所提及的婦女地位“多維性”特點是針對其內涵維度而言的,內涵維度包括威望、權力、資源控制力,這一點學者已經基本達成共識。需要討論的是,主觀滿意度是否應該納入婦女地位整體概念的內涵維度?目前分歧主要存在于另外兩個維度層次。范疇維度的被忽略及其與測量維度的相混淆,是目前有些概念混用和誤用的原因所在。理論上,范疇維度可區分為宏觀/微觀、公/私、社會/家庭領域,這些區分現有研究在概念界定時或有提及,但并未在維度層次上加以明確。需要討論的是,對范疇維度進行二分法是否最為理想?除社會和家庭兩個領域外,還有哪些領域可以被納入范疇維度層次?測量維度是目前分歧最為集中體現的地方,其中家庭領域婦女地位因在測量維度上集中使用“婦女家庭地位”概念,認識相對一致;而社會領域婦女地位并沒有統一的“婦女社會地位”概念在測量維度上予以統領,因而造成了很多困惑,如一些研究中界定的“婦女社會地位”也包含了家庭地位。需要討論的是,“社會”一詞應該在廣義還是狹義上去理解?其與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教育地位等的關系是什么?如果說后者均是對社會地位測量維度的分散表達,那么又應該包含哪些測量維度以便充分體現婦女社會地位?健康地位是否應納入婦女社會地位測量維度?
對于第二個問題,筆者認為,婦女地位綜合指標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測度、概括和比較婦女地位的重要作用,在理論上,其構建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從可行性上而言,現有研究中綜合指標體系的構建存在較大的困難與分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指標類別的取舍,涉及主觀/客觀指標、絕對/相對指標、宏觀/微觀指標等。以健康地位測量維度為例,平均預期壽命是衡量健康狀況的常用指標,但有學者認為女性較男性壽命長是天然優勢,并不能反映其真實的健康地位狀況,用主觀健康自評指標更合適[28]。而如前文所言,健康地位在婦女地位中的定位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加以明確,更不用說其測量指標的取舍。滿意度作為一個重要的主觀指標曾被納入一些研究中以測量婦女社會地位或家庭地位,但測量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原因在于,每個婦女對社會地位的期望值或評價標準都不一致,其對滿意度的回答是相對于其期望值或標準而言的[8];家庭地位滿意度并非取決于雙方的權力對比或平衡,而是得益于夫妻角色互動的溝通性與平等性、相互尊重與包容[21],因此所得到的主觀地位指標和客觀地位指標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方向相反的問題。此外,社會對婦女的主觀評價及態度也是婦女地位的重要反映,但是否以及如何將其納入指標體系還無定論。第二,權重的設置。權重反映了各個測量維度及其具體指標對婦女地位的貢獻度或重要程度,在不同時期、不同婦女群體中應該有所不同。目前大多數綜合指標的構建采用平權設計(或算術平均方法),也有的學者采用定量方法(如層次分析法)或者定性方法(如德爾菲法)進行權重設置,幾乎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權重對綜合指標的數值具有重要影響,即使各測量維度全面、測量真實,如果權重設置不合理也會影響最終結果。平權處理的情況下,測量維度及其具體指標數量的多寡無形中也起到了增加或減少權重的作用。諸多指標既有宏觀指標也有微觀指標,既有絕對指標也有相對指標,既有正向指標也有負向指標,如果不加處理、不進行標準化就納入所謂的統一指標體系中,那么會導致指標間不具有可比性,指標體系的科學性也就無從談起。
隨著婦女地位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由于婦女地位概念本身特點(多內涵維度地位方向的不一致性、多重定位性及情境依賴性)所帶來的構建普遍適用綜合指標體系的困難,但又不能用單一指標來衡量婦女地位,因而轉向偏重從某一內涵維度出發進行精細化和具體化測量。如20世紀90年代后期各國普遍開展的人口健康調查(Demographic Health Survey,DHS)中,就開始將反映女性賦權的相關問題納入問卷,包括決策權指數(decision-making index)、行動自由指數(freedom of movement index)和對性別角色態度的測量[50];一些研究注重在具體的情境下測量生育自主權(reproductive autonomy)[17]或決策自主權(decision-making autonomy)[18]等,并依據情境對相應指標進行調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有效的策略。筆者認為,內涵維度的精細化和具體化測量并不妨礙其結合范疇維度和測量維度從整體角度進行社會地位綜合指標構建,但這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其工作難度不能等閑視之。
需要指出的是,對上述兩個問題的討論與回答都應建立在有說服力的理論基礎上,而如何構建適應中國國情的、能夠充分反映婦女地位發展路徑與前景的理論體系,則是另外一個難度更大也更為基礎的問題。
就家庭領域婦女地位而言,各層次維度間及與其他領域婦女地位間的關系還有待澄清,相關的實證研究仍較為缺乏。關于婦女家庭地位的影響因素及其機制仍需要結合中國國情進行深入探索。目前家庭權力的測量仍聚焦于橫向夫妻權力的比較,考慮中國代際關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應當進一步注重縱向關系如婆媳之間的權力比較。生育是女性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但是婦女家庭地位測量維度上對于生育方面的指標仍然較少涉及。此外,指標構建中,女性本身的自主權和意愿還較少被考慮。比如女性承擔家庭事務的多少往往取決于其本身的身體狀況、時間安排和興趣領域等,承擔較多家庭事務的女性并不一定是地位低下或幸福感較低的,家庭領域中婦女地位的衡量不能單一地以一方承擔多少家務勞動或獲得多少家庭管理權來衡量,而應當看其是主動還是被動,是自愿還是被逼迫,客觀性指標與主觀性指標的有機結合仍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研究所依托的社會環境正在發生劇烈變遷,特別是在宏觀層面,低生育水平下的家庭和婚姻模式呈現多元化和混合性特點。一方面,婚育觀念、居住方式和代際關系都在形塑著未來越來越多元化的家庭模式[51][52];另一方面,盡管城鎮化、工業化、現代化不斷沖擊傳統文化的根基,傳統的家庭模式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家庭逐漸形成傳統與現代模式并存的現狀[53][54][55]。當前中國家庭呈現出兩方面的特征:一是由于現代化的影響,中國家庭逐步進入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所言的“后家庭時代”,產生了諸如原先從以縱軸代際關系為主向橫軸夫妻關系為主的轉變[56];二是由于中國地區差異大、民族文化豐富,傳統家庭文化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在不同的地區往往呈現出復雜多樣、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家庭文化。與此同時,女性在公共領域越來越取得與男性日益平等的地位,過去30年來,女性在家庭事務中的決策權也有所提升[57][58],但現代家庭中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經濟日益獨立的女性其工作與家庭雙重壓力困境日益凸顯,并成為近些年特別是生育政策寬松化實施后的熱點問題。這些變遷均對家庭領域的婦女地位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綜上所述,整體而言婦女地位及家庭領域婦女地位相關研究在概念間的內在邏輯、相互關系及測量維度和指標選取上還存在較大分歧,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筆者認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應包括:在不同層次維度婦女地位的分類上形成共識;實證檢驗不同范疇領域特別是社會領域和家庭領域婦女地位間的關系;在構建不同內涵維度或測量維度婦女地位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探索構建婦女地位綜合指標體系;等等。在上述研究中,應注重理論與實證的有機結合,即以多學科理論作為基本立足點,以實證分析研究作為事實依據,基于情境依賴性特點,對婦女地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理解與準確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