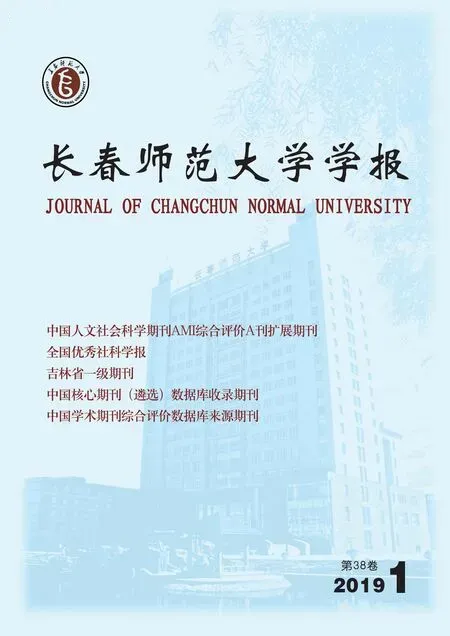后現代詩學下《夜車》對傳統偵探小說“元敘事”的解構
唐 婕
(蘭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隨著后現代批評理論的演進,后現代小說試圖解構W. C.布斯(Wanye C. Booth)的“可靠的敘事”[1]93(reliable narrative)和法國文藝理論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Jean-Francois Lyotard)的“元敘事”[2]4(metanarrative),企圖闡釋不同的歷史、社會和文化活動,全面、適當地解讀世界。傳統偵探小說采用“可靠的敘事”或“元敘事”,“形成了一套基本定型的情節建構”,故事時常以神秘可怕的謀殺案為開端,雇傭一位偵探調查事件真相。偵探收集證據,據時間邏輯推敲證據,推理,查出真兇,“最后的結局是‘封閉式’的,正義的一方必定勝利,善與惡是涇渭分明的。”[3]
Joanna Stolarek 稱“所有的偵探小說都基于兩起謀殺案,第一起由謀殺者所犯,并為第二起埋下伏筆。”[4]Heather Worthington提出“犯罪小說主要圍繞犯罪與探罪。”[5]Edward Quinn則認為犯罪小說“基本范式是一起謀殺案。”[6]Karen Seago堅信“犯罪小說致力于探究犯罪的動機與手段,這與人物、心理、日常生活密不可分。”[7]“傳統偵探小說解決的是如何解釋世界的問題。”[3]
然而,二戰毀滅性地改變了人類對生活、意義、現實、世界和文學的態度,歷史、社會、文化開始懷疑“可靠的敘事”或“元敘事”的權威性,投向“不可信的敘事”[1]160-161和“小敘事”[2]213、“對元敘事的懷疑”[2]4,反對意義的唯一性,擁抱后現代詩學的多音齊鳴、開放性、自我矛盾性、非關聯性等。顛覆與反叛傳統偵探小說陳規俗套的“玄學偵探小說”(metaphysical detective fiction)抑或“反偵探小說”[3](antidetective fiction)“一是擯棄一元的、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描寫小說中的虛構世界和現實生活中的歷史‘真實’之間存在的顯而易見的對抗;二是動搖小說中的虛構世界,使之變得朦朦朧朧,像鏡中月、霧中花一般不可捉摸。”[3]反偵探小說關注生而非死的問題。
一、《夜車》沿襲傳統偵探小說的“元敘事”
如傳統偵探小說,《夜車》以警察局局長湯姆的女兒珍妮弗·羅克韋爾的自殺開篇,湯姆堅信女兒自殺理由不充分,女警探邁克·胡里罕負責調查死因。
珍妮弗是“天文學家”[8]10。邁克認為她“完美到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步。”[8]10但珍妮弗卻把手槍塞進嘴里自殺了。湯姆請求邁克偵察女兒死亡一案,因為她是“‘優秀審訊員’,文書工作做得棒極了。”[8]6湯姆猶信“這件事有點蹊蹺”[8]20,“你看過比珍妮弗快樂的人嗎?你聽說過比珍妮弗幸福的人嗎?誰的生活比她平靜穩定?她是如此陽光燦爛。”他“打算揪出一個兇手”。[8]38湯姆最初給邁克“一個數據夾,袋上寫著:珍妮弗·羅克韋爾,編號H97143,”“找一點能讓我相信的理由回來。”[8]24在接下來的調查過程中,湯姆不斷提供各類文件,如“驗尸解剖記錄”[8]25、“法醫的化驗報告”[8]52、“解剖報告”[8]72等;篤定兇手是珍妮弗男友特雷弗·福克納,“他(特雷弗)心中一定存有邪惡的念頭,”[8]51“費盡心思想挖出特雷弗先前的不良行為,”[8]44以期盡可能快地查出女兒死亡的真相。馬丁·艾米斯筆下的湯姆戲仿了傳統偵探小說中的人物,一心尋求真相,堅信“事實是不容置換的。事實就是事實。事實就是這樣”[8]17,期望一個滿意的結局:所有真相都會被揭露,以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定。
在答應湯姆的請求后,如傳統偵探,邁克開始調查珍妮弗的死因,“需要一切能作為確切依據的東西,在心中重構這個事件發生的經過。”[8]28珍妮弗死亡當天3月4日:邁克照例勘察現場,畫現場素描,“這是一個‘不,有問題’自殺案件。”[8]116日:從湯姆處獲得一系列與珍妮弗相關的報告文件、錄像帶。7日:回顧案件,到解剖室等待解剖結果。9日:和另一位警察西爾維亞一起,“打給所有認識珍妮弗和特雷弗這對情侶的人,請教他們的看法。”[8]3610日:到珍妮弗的居住區查訪街坊鄰居。11日:見珍妮弗的房東羅菲太太,詢問槍聲、珍妮弗的心情、珍妮弗和特雷弗當晚是否發生過爭執、特雷弗離開的時間等。13日:審訊特雷弗,包括兩人相處情況、未來計劃、特雷弗4日的具體行程、珍妮弗當天的心情等。14日:收到湯姆親自整理建檔的解剖記錄。還拜訪珍妮弗的家庭醫生海·塔金霍思,詢問珍妮弗的過往病史以及珍妮弗服用鋰鹽的情況;檢查珍妮弗的所有個人物件:信件、賬單、記事本、通訊記錄等;調查與珍妮弗有交往的阿諾·戴比,了解兩人的相處情況;拜訪珍妮弗的大學室友菲利達;走訪珍妮弗的工作地點,詢問其系主任珍妮弗的工作內容、4日的具體行程、最近的心態等。邁克孜孜不倦地記錄了所有的證據,希冀通過時間線重構整個案件,找出真兇,謀求一種圓滿結束的感覺。
在第一部“反沖”中,馬丁·艾米斯戲仿傳統偵探小說的程式,明確標出警探邁克破案的時間線,試圖向讀者展示傳統偵探小說的解碼過程,這種“元敘事”希望獲得意義的合法性,解答“‘發生了什么事’、‘怎么會這樣’、以及‘這是誰干的’”[3],一旦找到答案,故事圓滿結束,善與惡涇渭分明,維護了社會秩序和道德。
二、《夜車》解構傳統偵探小說的“元敘事”
隨著《夜車》情節的推進,因缺乏證據和邁克情感的變化,破案失敗。馬丁·艾米斯挑戰了傳統偵探小說的“元敘事”,反對其終極意義,而基于后現代詩學下的不確定性、懷疑、碎片化等,“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含蓄地質詢虛構的小說世界以及其中人物的存在方式。”[3]
《夜車》體現了利奧塔爾的“對元敘事的懷疑”:“敘述功能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裝置,我們構成的語言組合也并不一定具有可交流的性質。”[2]4-5二戰后,人類逐漸意識到事物并未如他們預期的一樣發展前進,世界陷入了混沌,生活失去了意義。利奧塔爾認識到知識生產體制是短暫的和局限的,因此“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失去了可信性。”[2]135隨著意義呈多樣性、開放性,Joanna Stolarek認為二戰后,“傳統偵探小說創作模式無法滿足新興閱讀群體的期望,因而需加入新的元素,比如犯罪的動機、罪犯或偵探或受害者的身份,以迎合新生讀者的品味。”[4]28作為戰后“產物”,《夜車》選擇了“對元敘事的懷疑”,一步步解構傳統偵探小說中的“元敘事”,迎合讀者的閱讀需求。
身為現任警察局局長,湯姆在得知女兒死訊后的一些行為實屬費解。邁克3月6日去見湯姆,看見的“是一種不常出現在那些極度悲傷者身上的情緒:驚慌,一種原始、弱智的驚慌。”[8]19湯姆起始便一口咬定是特雷弗干的,甚至邁克都疑惑,“這種看法需要一點時間才能確定。的確,有時候一樁明顯的自殺案,在經過偵查后,會轉成蓄意謀殺。只是,這種偵察所需時間大概不到兩秒。”[8]21為了證實自己的猜疑,湯姆費盡心思,試圖找出特雷弗以往的不良行為,但在邁克眼里,對這些行為的指控有的是微不足道,不足以成為破案的實質性證據。邁克告訴湯姆或許珍妮弗內心存有他人不知的傷痛,湯姆“聲音噎了一下,像是想到什么恐怖的事。”[8]23湯姆一直堅信這案子符合他殺,卻一直未能提供有用的線索。更費解的是,湯姆隱瞞珍妮弗服用鋰鹽,隱藏藥物報告。湯姆的行為與他一定要個明確、合乎道理的答案的訴求背道而馳,同時也增加了讀者的疑惑和邁克探案的難度,造成案件陷入更混亂的狀態。
對于邁克,她在小說開篇就埋下了伏筆,“現在我要講的,是我所遇過的最糟的一件案子,”[8]3“我已經把一個打得很死的結,松成一推亂七八糟的線頭”,“以下的數據和文件記錄,是在過去的四星期中,一點一點地拼湊起來的;”直接承認“我自己也是這個即將開展的故事的一部分,”[8]7-8這些陳述與傳統偵探小說大相徑庭。因傳統探案手段失敗,邁克放棄時間線,開始心理解剖;列了一個“內容朦朧如雨霧”的“壓力來源和誘發因素”的清單:“1、重要的他者?特雷弗。他沒見的東西?2、經濟狀況?3、工作?4、身體健康?5、心理健康?錯亂性質:a)心理方面?b)思想的/官能的?c)抽象的?6、深藏的秘密?創傷?童年陰影?7、其他重要的人?”[8]93-4在審訊特雷弗并多次與他見面后,劃掉了第一點;珍妮弗葬禮后,在第四點上打了叉;仔細查閱珍妮弗的個人物件后,勾掉了第二、六點;走訪珍妮弗工作地點、見了阿諾·戴比和菲利達后,劃掉了剩下的幾點,最后“什么都不剩了”[8]162,“又都回到了原點”[8]173。雖然邁克嘗試“變換所有已知條件”[8]135,卻千瘡百孔。邁克以失敗告終,不得不承認“線索全都斷了頭”[8]180,“事情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平白無故,就這么香消玉殞了。”[8]75
在探案過程中,邁克自身情感的投入使整個案件更加撲朔迷離。名字和身材多次被錯認為男人、能力受到質疑、電視等媒體對職業警察的大規模虛構化,不斷加劇邁克對自身身份的焦慮;在得知湯姆曾強暴過珍妮弗后,邁克不時回想起自己童年時類似的遭遇;邁克對特雷弗感情的變化,審訊完特雷弗,“嫌犯和偵訊者的雙手緊握,兩個人留下了淚水。”[8]72再見特雷弗,從不費心打扮的邁克竟花了一個多小時打扮;特雷弗協助邁克穿夾克,“他觸碰到我,手指輕輕劃過我的領椎,讓我的心神為之一蕩。”[8]150小說的焦點成了生者邁克,而非死者珍妮弗。
在第二、三部“自殺重罪”、“視相”中,邁克未能據時間線破解這起疑案,馬丁·艾米斯也未遵照傳統偵探小說的程式,打破時間線,碎片化地將探案過程嵌入邁克故事的故事中,解構了傳統偵探小說犯罪—探罪—罰罪的模式。邁克的失敗模糊了善與惡的界限,解構了意義的終極性,《夜車》的結構是松散、混亂的,神秘事件不了了之。
三、結語
作為后現代主義的理想媒介,反偵探小說盡管采用傳統偵探小說中“偵探調查罪案的基本程序,卻顛覆了其中的許多或全部規范,如邏輯演繹、偵探的英雄角色、神秘事件的圓滿解決,而致力于探究與神秘事件無關的各種問題,不但不提供令讀者‘滿意’的謎底,反倒將他帶入一片無涯的混沌。”[9]馬丁·艾米斯通過描寫邁克失敗的破案經歷,反對追尋終極意義、理性的“元敘事”;借助“小敘事”,如對死因的不同解讀、隱藏證據、秘密、盲點等,艾米斯有意隱瞞珍妮弗的死亡真相,而非解決它,戲仿、游戲傳統偵探小說的模式使讀者的閱讀期待受損。通過代表黑暗和未知的夜車,艾米斯試圖證明后現代詩學下反偵探小說或許是傳統偵探小說的一種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