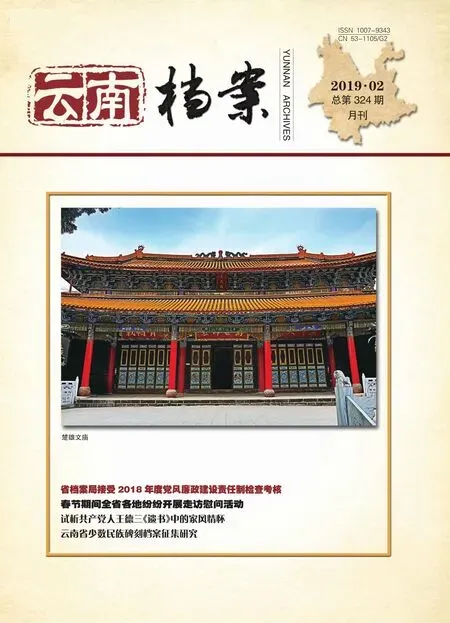新時代檔案元數據核心集構建的需求研究
■崔杰
《“魂系歷史主義”的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構建研究》這一項目,旨在“歷史主義”原則的指導下,構建檔案界專有的元數據核心集,即由檔案歷史聯系的三維結構要素(來源、事由和年代)及要素之間的關系組成的,包括來源、事由和年代三種元數據。[1]
為什么要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這實際上是由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需求所決定的。所謂需求,是指由需要而產生的要求。[2]在我國,學界對檔案元數據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隨著新時代檔案信息化的到來,檔案理論、檔案實踐與元數據技術三股力量的深度融合與變革,形成了強大的內在動力,促使檔案學者產生了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需求。
1 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需求層次圖
如圖1所示,從檔案元數據核心集構建的需求層次圖可以看出,其包括理論層、實踐層和技術層三層。從下向上看,第一層為理論層,即為新時代中國檔案界對“全宗群物質形態”的需求;第二層為實踐層,即為新時代中國檔案界對“檔案整理實踐”的需求;第三層為技術層,即為新時代中國檔案界對“檔案元數據技術”的需求。三個需求層次均發展成熟且相互作用,隨即推動了檔案學者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需求。
具體地講,檔案學界是要運用計算機及其“元數據技術”(技術層)來實現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構建,以此在檔案實踐中創建出全宗群整理體系(實踐層)和形成全宗群這種檔案物質形態(理論層),這便是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需求所在。
2 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需求層次解析
2.1 理論層:新時代中國檔案界對“全宗群物質形態”的需求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傳統檔案學在“全宗理論”的框架下,揭示了“檔案”具有“案卷”、“全宗”和“全宗群”[3]三種檔案物質形態,就已經意識到“全宗群”是一種比“全宗”具有更高層次的檔案物質形態。但那時的“檔案整理”還處于手工整理、并用檔案物質實體的排序來形成檔案物質形態的技術階段,因而檔案整理只能形成“案卷”和“全宗”這兩種檔案物質形態,還無法形成“全宗群”。因為當時的檔案整理不能實際地形成“全宗群”,于是“全宗群”這種檔案物質形態的存在就無法得到檔案實踐的證明,所以“全宗群”這一比“全宗”具有更高層次的檔案物質形態的存在,就被認為是認識上的一種空想,而“全宗群”也就漸漸地成為了檔案學中的一個無足輕重的泛泛概念。
但新時代中國檔案界非但沒有放棄“全宗群”的概念,反而將“全宗群”這種檔案物質形態的存在作為了一個“假說”,并在這一假說下,繼續并更深入地展開了檔案學理論的研究。經過多年的研究,學界發現:“全宗群”這一檔案物質形態存在的本身,將意味著“全宗”不再是最高層次的檔案物質形態。而“全宗”一旦失去了它在檔案物質形態上的最高位置,那么已有百年歷史的“全宗理論”,也就會隨之喪失它在檔案學中的統治地位。于是檔案將從“全宗”進化到“全宗群”、檔案整理將從“全宗整理”進化到“全宗群整理”,而檔案學將從“全宗理論”進化到“全宗群理論”。也就是說,檔案物質、檔案實踐和檔案學都將因“全宗群”這種檔案物質形態的存在,而發生一次巨大的整體進化和變革。
而正是由于相信中國傳統檔案學提出“全宗群”這一檔案物質形態的科學性,并意識到了“全宗群”這一檔案物質形態的存在,將會打破“全宗”和“全宗理論”的一統天下,所以新時代中國檔案界才繼承和堅持著“全宗群”的概念,并且更迫切地需求在檔案整理實踐中能真正地形成“全宗群”,以便用檔案實踐來證明“全宗群”就是客觀存在的一種檔案物質形態。
2.2 實踐層:新時代中國檔案界對“檔案整理實踐”的需求
雖然中國檔案界已經意識到了“全宗群”這種檔案物質形態的存在,但“全宗群”究竟是不是客觀的存在,這并不由我們的認識所決定,而是必須得到檔案實踐的檢驗。換言之,只有當檔案界能用檔案整理的實踐真實地形成“全宗群”的時候,“全宗群”這種檔案物質形態的客觀存在才能得到普遍的認可。由此,新時代中國檔案界就不得不在假說“全宗群”存在的條件下,開始了對“檔案整理”的研究。
目前,學界對“檔案整理”的研究表明:“檔案整理”具有“案卷整理”、“全宗整理”和“全宗群整理”的三個層次。由于這三個檔案整理的層次之間,存在著實施檔案整理的實踐主體的不同、依據的不同、排序結構的不同,以及形成檔案物質形態的不同,所以這三個檔案整理層次是三個不可相互替代的技術體系。通俗地說,用“案卷整理”不能形成“全宗”,而用“全宗整理”也不能形成“全宗群”。因此在檔案整理的層次上,“全宗群整理”仍是一個空白,而要形成“全宗群”,就必須開創性地構建一個全新的檔案整理層次。
學界對“檔案整理”的研究還表明:“檔案整理”是由“檔案物質實體整理”和“檔案歷史聯系整理”兩個不同體系整合而成的。而根據檔案界所發現的“二元檔案實踐體系”理論[4]就可以認識到:在“檔案物質實體整理”和“檔案歷史聯系整理”之間,“檔案整理”的重心并不在“檔案物質實體整理”,而是蘊涵在“檔案歷史聯系整理”之中,“檔案歷史聯系整理”才是“檔案整理”的核心實踐。由于“檔案歷史聯系整理”整理的對象不是檔案的物質實體而是檔案的內在關系,所以“檔案整理”的核心和實質其實是形成“檔案內在關系”,即對“檔案歷史聯系”的信息整理。
而正是由于以上對“檔案整理”的層次、體系和實質的認識,才使新時代中國檔案界意識到,應采用信息處理的技術方法來構建缺失的“全宗群整理”和形成“全宗群”。
2.3 技術層:新時代中國檔案界對“檔案元數據技術”的需求
“元數據技術”原本是游離在檔案實踐之外的一種先進的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只因利用“元數據技術”的功能,能實現檔案界要采用信息處理的技術來形成“全宗群”和構建“全宗群整理”層次的目的,所以它才被檔案界引入到了檔案整理實踐中,使“元數據技術”轉化為一種整理檔案的技術。
但“元數據技術”可以超然地存在于檔案實踐之外,它的功能是由它自身的規范和原理所決定的,因此只有遵循“元數據技術”本身的原理與規則,檔案界才能科學、合理和有效地運用它來實現檔案整理實踐的目的。而另一方面,檔案具有自己的本質,檔案整理實踐同樣有自己的規范和原理,因此檔案界必須在不違反檔案整理實踐的規范和原理的前提下,將“元數據技術”轉化為檔案整理實踐的實用技術。為此,新時代中國檔案界選擇了自己提出的“檔案歷史聯系與歷史的同構性”這一檔案本質觀點,奠基了對“檔案元數據技術”的認識基礎。
首先,依據“數據的數據”這一“元數據”的原始定義,并結合檔案界對檔案本質的認識,具體地將“檔案元數據”規范為“檔案歷史聯系數據的數據”。這就非常明確地表明:在形成“全宗群”的“全宗群整理”中,“檔案元數據技術”的對象只是那些屬于“檔案歷史聯系數據”的“數據”,而“檔案元數據核心集”則只是“檔案歷史聯系數據的數據集合”。
其次,根據“同構性”的檔案本質[5],將檔案元數據技術的規則和原理,規范為“必須最大限度地保持檔案歷史聯系與歷史的同構性”。這就非常明確地表明:在形成“全宗群”的“全宗群整理”中,“檔案元數據技術”必須具有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檔案歷史聯系與歷史的同構性”,即維護檔案本質的功能。
正是因為形成了這種能與“檔案本質”和“檔案整理規則和原理”具有統一性的檔案元數據技術認識,所以新時代中國檔案界才可能科學、合理和正確的將“元數據技術”轉化為形成“全宗群”和構建“全宗群整理”的技術。
3 結束語
“檔案整理”是一個技術體系,而從檔案整理技術上說,學界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是要借助計算機及其元數據技術,使新時代檔案整理技術體系從傳統的“檔案物質實體整理”,演進到更高級的“檔案歷史聯系信息整理”。在檔案信息系統中,實際地構建一個能肩負檔案歷史聯系整理功能的,具有獨立性、規范性、系統性且能作為檔案信息系統內核的“檔案元數據核心集”,并用“檔案元數據核心集”來實現在計算機及其技術條件下的檔案歷史聯系的整理。通過檔案歷史聯系整理,在“案卷整理”和“全宗整理”之后,再構建起一個“全宗群整理”的檔案整理層次和體系,以實現在“案卷”和“全宗”之上,再形成一種更為高級和復雜的檔案物質形態——“全宗群”。
由此可見,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研究工作并不是憑空而來(如圖1所示):實踐層需求(檔案整理實踐)相當于實施環境;技術層需求(檔案元數據技術)實際上是技術手段;而理論層需求(全宗群物質形態)是構建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物質基礎,即在檔案實踐中實際地形成全宗群。只有這三種需求均發展成熟,且相互作用互相契合,才能形成強大的合力,推動學界檔案學者開始進行檔案元數據核心集的構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