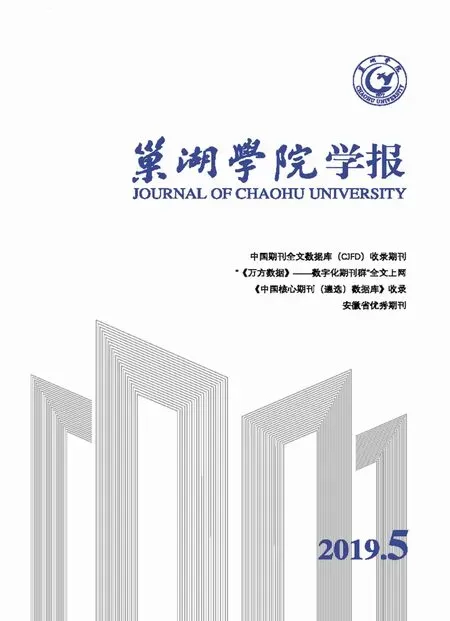東魏與北齊的官僚治理
——以縣令選任變化為中心
項 琦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對于東魏、北齊地方吏治和官員選任,學界早有研究。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嚴耕望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介紹了南北朝時期的縣府組織和縣令的任遷途徑[1];在官員選任和管理方面,汪征魯先生在《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中結(jié)合士、庶兩個階層結(jié)構(gòu)和不同的選舉方式介紹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員選任情況[2];陶新華的《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也從整體上敘述東魏、北齊的官僚管理制度[3]。但是以往研究均是從宏觀的角度進行整體上的概述,缺乏系統(tǒng)、具體的研究。筆者將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具體到縣一級進行探討,期望把握東魏、北齊兩朝的縣令選任和地方吏治變化,探究其中變化的原因,并試圖探析兩朝的官僚治理體系。
一、北魏后期至北齊初期的地方縣令
北齊典章制度基本上沿襲了北魏,據(jù)《隋書·百官志》記載:“高齊創(chuàng)業(yè),亦遵后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但是在具體機制運行上卻遠遠不同。在元魏初期對于縣令的委任多是依靠君王選拔賢良充任,并無一項具體的制度。因而縣令來源是多樣的,或是從歸附人員中選拔,或因?qū)W識高尚而被賞識,或以清廉出名而被征辟,或不愿在朝中為官而自愿外出為官,或因得罪朝中權(quán)貴被排擠外放,或依靠祖上的聲望而獲蒙蔭,或攀附權(quán)貴而得官[4]。總的看來多是文人或者門第出身,但是到北魏后期武人勢力的膨脹,包括縣令在內(nèi)的許多官職都開始被武人掌控。
《魏書·崔亮傳》記載,魏孝明帝時,京中羽林作亂,靈太后被迫允許“武官得依資入選”,但人多官少,引發(fā)不滿。所以崔亮任吏部尚書,行“停年格”之法,“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使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而崔亮回復(fù)其外甥劉景安的規(guī)勸時,又提到“今動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借書計,唯可彍弩前驅(qū),指蹤捕噬而已”[5]。由此可見,崔亮對武人十分輕視,行此制度就是針對時弊、限制武夫的舉措。雖有限制,但武人仍然有晉升之路,尤其后期國家動亂,武人更是借機掌握了大量地方官職。
到北齊建立的時候,地方縣令的主要來源有兩種,一是廝役,二是武人。“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于士流恥居之。……及其末造,國亂政淆,權(quán)移于下,遂至宰縣者多廝役。……入北齊,其風更甚。”[6]廝役,本指從事低賤職業(yè)的雜役,“養(yǎng)馬之賤者”“謂炊烹供養(yǎng)雜役”[7],“初,魏虜西涼之人,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廝役。(胡注:廝,養(yǎng)也、役也、使也、賤也。)”[8]從而泛指品質(zhì)低下的人。可見當時的地方吏治并不受人重視,將親民之官委任給廝役之徒,可見對國家基層治理的輕慢。其中,武人為地方長官現(xiàn)象更為普遍,“邊外小縣,所領(lǐng)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5],“魏自孝昌之后,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9],高歡時,“以戰(zhàn)功諸將,出牧外藩”[9]。雖然很少有直接提及縣令情況,但從州郡長官的來源可以推斷縣令的來源情況。
由于擔任縣令的官員多為武人或廝役,以致時人多輕視外職,“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俊才,莫肯居此”[5]。例如,崔劼因主動讓兩子外任為官就被時人稱贊[9]。又如羊烈同畢義云爭奪州大中正,因?qū)Ψ绞俏淙舜淌范右宰I諷。畢義云盛稱門閥,累世為本州刺史,羊烈則直言:“近日刺史,皆是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9]由此可見,當時出身武將的地方長官不為時人重視,尤其被羊烈這樣的傳統(tǒng)漢人世家輕視。愈是不被重視,真正有才學之士愈是不愿擔任外官,最終導(dǎo)致包括縣令在內(nèi)的外官整體素質(zhì)的下降。隨著弊端的日益突出,改革布新的建議和措施便被屢屢提出。
二、東魏至北齊初期對地方吏治的整頓
對于東魏、北齊的地方吏治的整治,是依時逐步展開的。北魏以來,辛雄、杜弼、元孝友等人都曾建議整頓吏治,但都沒有成行。當時阻礙革新的力量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即國家動亂與地方豪右的抵制。對于地方吏治的弊端,北魏后期辛雄就提議整頓:“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5]但此事沒有成行,史書言恰逢皇帝駕崩,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北魏后期以來對郡縣官的輕視[3],使得朝廷顯貴不愿子孫出仕地方。又有行臺郎中杜弼勸說整頓吏治,高歡卻回復(fù)說:“天下貪污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guān)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fù)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9]可見,高歡也知道吏治問題,但卻因為與西魏、南陳對峙的軍事需要而暫時擱置,以免引發(fā)內(nèi)部分裂。
另一方面,高歡的崛起主要依靠懷朔鎮(zhèn)集團,但也依靠趙魏豪右和洛陽胡漢世族等地方大族[10],所以初期地方大族的勢力也嚴重制約了中央政策的實施。東魏時,元孝友曾經(jīng)主張對三長制進行調(diào)整,他認為過多的基層官員會使國家喪失兵源和稅收,而京城之中七八百家才有一個里正、兩個長史,卻依然治理得井井有條,因此主張:“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yīng)二萬馀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9]他試圖通過擴大地方閭比規(guī)模,從而精簡三長人數(shù),擴大稅收來源和兵源,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但是如此行事,會侵犯地方原本享受賦稅特權(quán)的集團,這便引起地方勢力的抵制,因而事寢不行。
高歡施政的轉(zhuǎn)變在于東西魏戰(zhàn)勢趨于緩和。537年,高歡西征,慘遭沙苑(今陜西大荔南)之敗,而后宇文泰乘勝東進,又為高歡所敗。此后一直到北齊滅亡之前,雖有交戰(zhàn),但都無決定性的大戰(zhàn),東西魏國力相當,分立已成定勢。此時,高歡得以著手整頓吏治。
東魏剛立初期,高歡便“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9]戰(zhàn)事平穩(wěn)后,又采納高隆之的建議,著手裁撤私人部曲。北魏自六鎮(zhèn)起義后,天下私人軍隊急劇膨脹。“正光末,天下兵起……時有詔,能募得三千人者用為別將。”[9]因而時常有民眾或地方長官西引或南叛。針對這種情況,高隆之上書:“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詔皆如表。”[9]通過這項措施,裁撤了非邊要地區(qū)的地方豪右軍隊,這對地方大族的打擊是直接而有效的。
同時,高歡著手打擊一同起事的軍事貴族,“懷朔鎮(zhèn)勛貴與高氏宗親一樣,成為高歡及北齊諸帝限制、猜忌、打壓的主要對象。這是決定東魏北齊國家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變動的主軸”[11]。如尉景,同高歡一同起事,又迎娶高歡之姊,“自恃勛戚,貪縱不法,為有司所劾,系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8]。當時高歡已經(jīng)掌握了東魏的實權(quán),卻仍諧闕請免,意在使勛貴知有王法,以此警戒貴戚。高歡另一高明之處,就是抬出長子高澄整頓吏治。“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舊,委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其權(quán)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quán),故以澄為大將軍、領(lǐng)中書監(jiān),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于澄。……歡謂群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8]如此,高歡便避免了與勛貴直接交鋒,留下轉(zhuǎn)圜余地。在官員當中,高歡父子任用崔暹糾劾權(quán)貴,高歡曾經(jīng)對勛貴直言:“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8]高澄又讓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quán)豪,無所縱舍,于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9]高澄本人任吏部尚書時,“乃厘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9]。這一系列舉措推動了包括縣令在內(nèi)的整個官場氣象為之一新,“內(nèi)外群官,咸知禁網(wǎng)”[9]。
經(jīng)過高歡、高澄父子的整治,地方治安得到改善。東魏初期,時常有地方豪民聚眾反叛和劫掠鄉(xiāng)里的現(xiàn)象,例如:“東雍、南汾二州境多群賊,聚為盜”[9];魏天平年間(534~537 年),“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于本郡起逆”[9];李景遺“好結(jié)聚亡命,共為劫盜,鄉(xiāng)里每患之”[9]等等,此類情況十分突出。尤其是武定年間(543~550年),民眾反叛之事常有發(fā)生。但是此后,地方治安得到大大加強,史稱“奸吏斂跡,盜賊清靖”[9]。
高洋時,正式受魏禪,因此,在位期間多推行德政來彰顯新朝氣象,如興建學校、立定法律、廣開言路等。其中對于地方政治整頓,卓有成效的一項措施就是天保七年(556年)省并郡縣。“魏自孝昌之季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涂炭……牧守令長,虛增其數(shù),求功錄實,涼足為煩,損公害私,為弊殊久,既乖為政之禮,徒有驅(qū)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今所并省,一應(yīng)別制。”[9]高洋通過省并郡縣,裁撤臃腫的地方機構(gòu)和冗官,減少財政支出,極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和郡縣數(shù)量的合理性,便于中央的垂直管轄。更為直接的效果是打擊了趙魏豪右。元魏后期為了改善人多官少的局面,通過在地方多置郡縣來增加官職,其中部分官職便被地方上的大族所攫取,此番省并之后,趙魏豪右的影響力大不如前[10]。時人宋孝王著《關(guān)東風俗傳》云:“遷鄴之始,濫職眾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充公薄。比武平以后,橫賜諸貴及外戚怪寵之家,亦以盡矣。”[12]這番敘述雖然屬于食貨的范疇,談及當時大族對土地占有情況,但是結(jié)合天保這一時間點,便可以發(fā)現(xiàn)大族衰落與省并郡縣的關(guān)聯(lián)。至此,經(jīng)過高歡解除私人部曲和高洋省并郡縣,趙魏豪右的勢力大不如前。
東魏至北齊前期的一番整飭促進了整個國家的發(fā)展,形成“主昏與上,政清于下”[8]的局面,使北齊前期在東西對峙中保持一定優(yōu)勢,也為后來的“士人為縣”提供了良好的基礎(chǔ)。
三、北齊中期的“士人為縣”
北齊后期,地方吏治得到改善的重要標志就是使士人出任地方長官,這有著多方面的背景。漢化的加深、逐漸復(fù)興的經(jīng)學教育以及戰(zhàn)亂帶來的官員傷亡等諸多合力使得“士人為縣”得以出現(xiàn)。
在漢化方面,關(guān)于北齊的漢化歷來多有爭論,但不管程度如何,北齊終究有所漢化。北齊承襲了北魏漢化培養(yǎng)出的一批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而且北齊據(jù)有洛陽和河朔地區(qū),這是漢朝以來的經(jīng)學中心,承襲元魏漢化之風。“由于自北魏遷都洛陽以來,河朔乃北方儒學的中心所在,師承家學源流不輟,且北齊禮律官制又大體承襲太和之制,故而北齊于胡化傾向之外,另有一種禮樂興國的思想潛伏于其中。”[13]而且,北魏末年以來的一批大儒均出仕北齊,如崔亮、魏收、楊黯等,又有經(jīng)學大儒王助、劉悼、劉炫等,“皆北齊儒學之士,而二劉尤為北朝數(shù)百年間之大儒。則知山東禮學遠勝于關(guān)隴也。”[14]
另一方面,北齊諸帝較有見識,注重教育,逐步恢復(fù)和建立了晉亡以來的地方和中央學校制度。文宣在位時,“詔封崇圣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文廟”;受禪之后,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雋,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仗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jīng)。”[9]孝昭時,“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署,依舊置生,講習經(jīng)典,歲時考試”“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9]。可以說,在北齊時期,學校的制度基本完善,從地方到中央,能保持基本運行,初步恢復(fù)了漢晉的庠序體系。這一切便培養(yǎng)了一批較有文化修養(yǎng)的士子。
“士人為縣”更為直接的原因是河清年間(562~565年)的戰(zhàn)爭失利,這場戰(zhàn)爭對于北齊后期的諸多施政產(chǎn)生很大影響。河清二年(563年),北周聯(lián)合突厥出兵攻打北齊,北齊大敗。這種實力變化給北齊君臣很大的打擊。“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8]東西力量對比在武成時發(fā)生改變,由齊強周弱變成周攻齊守。武成新君即位,遭此大難,不得已采取除舊布新之舉來順應(yīng)時事變化。此外,大量地方官吏在戰(zhàn)爭中被殺或被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馀里,人畜無遺”“突厥寇齊幽州,眾十馀萬,入長城,大掠而還”[8],“周將楊忠?guī)洝⑼回拾⑹纺悄竞沟榷嗳f人自恒州分為三路,殺掠吏人”[9],事在河清三年(564年)。這次戰(zhàn)爭橫跨了三個年份,從河清三年(564年)冬至天統(tǒng)二年(566年)春。而元文遙提出“士人為縣”之事在天統(tǒng)二年(566年)。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大量官吏被殺,致使戰(zhàn)后大量官職出現(xiàn)空缺,從而給元文遙提供了一個契機。
“士人為縣”的出現(xiàn)另有其淵源。“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shè)法,不宰縣不得為郎。”[15]西晉針對貴游子弟不愿外出為官一事,就曾推行“甲午制”,即必先出任地方治理百姓,然后才能授用中央。元魏時,辛雄上書:“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nèi)職。”[5]北魏前期,“是人士先為臺郎而后出為地方郡縣官”[3],所以針對地方吏治的弊端,歷來均有有識之士提議整飭,終于到元文遙時得以實現(xiàn)。因為相對辛雄等比較強制且制度化的手段,元文遙的提議更多是一時之策,并沒有硬性規(guī)定擔任中央官僚與出任地方掛鉤,使顯胄之后依然可以直接出仕中央,并沒有損害上層集團對于中央官職的掌控。
天統(tǒng)二年(566年),元文遙提出“士人為縣”:“齊因魏朝,宰縣多用廝濫。至于士流,恥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于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fā)牧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敘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9]這段材料既說明了元文遙是針對縣令弊端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又反映了時人對縣令的輕視。所以,為了平息貴游子弟的不滿,特意舉行隆重典禮,展示朝廷對此的重視,也意在扭轉(zhuǎn)魏末以來對外官的輕慢。“士人為縣”的推行,明顯效果就是提升了地方官員的素質(zhì),地方吏治為之一清。《北齊書》明確記載的就有路去病:
路去病,陽平人也。……敕用士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wù),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嘆服。擢為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nèi)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yǎng)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shù),去病獨為稱首。[9]
除此之外,又有李仲舉等人:
自是李仲舉、盧昌衡等八人,以門資并見征用。仲舉為修武令,人號曰“寬明”;昌衡為平恩令,人號曰“恩明”,時稱盧李之政。以親民之官而寄之廝役,衰亂之朝何事蔑有?此亦可以觀世變也。[6]
路去病、李仲舉、盧昌衡等人在“士人為縣”這一政令下出任縣令,在任一方都政令修明,百姓稱贊。雖然不能覆蓋到所有縣,但是也相當程度上改善了部分縣的吏治。可見,文人出任地方官,施政方面優(yōu)于武人、廝役,也符合一個王朝建立后的發(fā)展趨勢。
“士人為縣”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就是所選士人多出自名門望族。所以,“士人為縣”使自高歡以來受打壓的地方大族得以復(fù)興,是中央對于地方的利益讓步。雖然北朝門閥政治不如南朝那樣顯著,但仍有一定影響,尤其北魏以來就有對官員的任命有“訪第”的傳統(tǒng),例如楊愔辟樊遜為府佐,樊遜卻推辭說:“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9]“東魏、北齊時期,凡中央臺省官吏、督府參軍、地方縣宰、州郡辟召僚佐及察舉秀才,其所選用皆為 ‘衣冠士族’或‘世門之胄’。”[16]可見,北齊官職的選用中,門第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從高澄開始,已開始注重門第,他任吏部尚書時“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9]又如楊愔掌管典選時,“取士多以言貌”[9],辛術(shù)“循名責實,新舊參選,管庫必擢,門閥不遺”[9]。而且北齊有蒙蔭官員子孫的傳統(tǒng),皇建二年(561年),“詔內(nèi)外執(zhí)事之官從五品以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nèi)各舉一人”[9];天統(tǒng)三年(567 年),“太上皇帝詔京官、執(zhí)事散官三品以上各舉三人,五品以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以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郎、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9];武平三年(572年),“詔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9]。諸多詔令中,特別是武成朝開始,次數(shù)較多,這應(yīng)當同河清年間突厥殺掠吏人造成大量官職空缺以及賣官有關(guān)。
被選拔出來的士人,如李仲舉、盧昌衡等八人,都是因為門第而被征用,盧、李均是河東大族。從此看出,因為天保省并郡縣而受到打壓的地方豪右再次參與地方政治。這項措施必然受到地方大族的迎合,相比之前的措施,“士人為縣”爭取到了支持的力量。同時,傳統(tǒng)的軍事貴族也開始向文人轉(zhuǎn)變,也參與到這一行動當中,“北朝的軍功貴族統(tǒng)治仍非‘常態(tài)’,由北朝而入隋唐,軍功貴族們的自身文化水準在不斷提高、在向士人官僚轉(zhuǎn)化。”[17]軍功貴族也在開始向文人轉(zhuǎn)化,所以其抵制并不像開始那么強烈。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所選士人多是地方大族,多為漢人,少有當朝顯貴之后。很多士人少有事跡和列傳流傳下來,甚至不錄姓名,說明他們出身和地位都不高。也就是說,時人對外職的輕視一時還沒有轉(zhuǎn)變,真正的掌朝世家子弟仍然不愿意出任外官。遺憾的是北齊由于自身政治敗壞,使得“士人為縣”難以為繼。此時距北齊滅亡不過十余年,所以很多士人并沒有完整的晉升之路,這使我們無法從更長遠的范圍內(nèi)考察“士人為縣”的影響。簡單來說,“士人為縣”只是北齊吏治整頓的一個舉措之一,是北齊自建立以來的吏治整頓背景下政治進步的慣性使然。
四、中央對地方管理的深入與北齊末期的商賈縣令
北魏曾通過三長制和均田制加強了對地方的管轄,但是后期戰(zhàn)亂不斷,中央的控制力逐漸衰落。隨著局勢逐漸穩(wěn)定,北齊也逐步開始恢復(fù)對地方的管理。如前文所提,天保省并郡縣及其對河朔、洛陽大族的打擊就是一例。通過對縣令選任的管理,使得兩朝治理能力有所提升。
賦稅標準的統(tǒng)一、專門的括戶措施、均田令的重新頒布以及《河清令》的推行,使得戰(zhàn)亂以來國家對地方的松弛管理又重新得到加強。武定時(543~550年),元孝友議改三長制表明北齊仍襲用了北魏制度,但弊端逐漸暴露,欲加以改革,卻難以實行。雖然對三長制的改革沒有實行,但是北齊卻逐步開始恢復(fù)對人口和賦稅方面的管理。在租調(diào)方面,高歡“以諸州調(diào)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為匹。”[7]這便規(guī)范了對調(diào)的征收,改善了賦稅體系。更重要的舉措是高歡對于人口的清查。武定二年(544年),“校河北戶口損益”[8],河北多名門大族,此舉對大族隱匿人口的行為予以打擊。同一年,又有更大范圍和更強程度的括戶,專門派孫騰、高隆之為括戶大使清查地方戶口。“東魏以喪亂之后,戶口失實,徭賦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馀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8]北齊疆域僅有北朝一半,又經(jīng)歷戰(zhàn)亂,仍能得隱匿戶口六十余萬,可見這次清查行動是比較嚴格的,而在戰(zhàn)亂中庇蔭流民的地方豪右勢力被削弱。從結(jié)果上看,此次清查擴大了兵源和稅收,“是后租調(diào)之入有加焉”[18]。高歡掌權(quán)后期,“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后,倉廩充實。”[18]奠定了北齊前期國力優(yōu)勢的基礎(chǔ)。武成帝高湛,廟號“世祖”,他得以稱祖的功業(yè)在于三件事:擊退周師,制定齊律和重新頒布均田令。北朝以來州佐因州軍府強勢而逐漸式微,武成時推行的《河清令》雖然保留了州府一定的征辟權(quán)力,但是通過對官職的“品階化”確定了中央對州官的敕除[19]。在土地方面,河清三年(564年)重新均田,使得中央權(quán)力再次深入到地方。頒布《河清令》、重新均田和“士人為縣”成為并行的、針對地方的措施。“士人為縣”雖然澄清一時之氣,但是并沒有形成一項完善的制度,而武成、后主都是貪圖享樂之君,朝政敗壞,使得地方吏治更是混亂不堪,“然其末流,鬻爵賣官,郡縣之亂,更為前世所未有”[6]。
到北齊末期,由于賣官鬻爵,甚至出現(xiàn)了富商大賈擔任地方縣令的情況。武成后期,“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xiāng)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愛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征稅,百端俱起。”[9]這種弊政發(fā)端于武成,到后主之時情況更加惡化。馮之琮任吏部尚書時,“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后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9]尤其是段孝言任吏部尚書時,“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恣情用舍,請謁大行……富商大賈多被銓擢,縱令進用人士,咸市粗險放縱之流。”[9]這表明了北齊后期地方吏治再次糜爛,因為高湛賣官鬻爵,使得身家萬貫的富商大賈憑借財富占有了大量的地方官職。而通過花錢得到官職的郡縣長官上任后又通過種種手段勒索強奪來損公肥私,形成如同包稅制度一樣的惡劣現(xiàn)象。
北齊后期賦稅在這樣的背景下變得極為繁重。比如,對原來不收稅的項目加以征稅,“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guān)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3、5]以淮南為例,高洋乘侯景之亂,奪得淮南之地時,給予十年的優(yōu)撫,“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18]。到后主時期,“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杰數(shù)請兵于王僧辯。”[8]本來得到稅收優(yōu)惠的淮南地區(qū)卻在后主時期因為賦稅繁重,竟然聯(lián)絡(luò)南朝以求歸附,可見,北齊后期地方動亂十分嚴重。
武成、后主賣官的一個意外結(jié)果就是,加強了中央對地方官員的任免權(quán)力。賣官所需的職缺,迫使皇帝干預(yù)更多官員的任免,擴大自己直接任免官員的范圍,通過這種手段來增加可以授受的官職數(shù)量。于是便出現(xiàn)了州郡主簿、功曹這些官職都通過中旨任命。雖然這種對地方官員管理的加強并不是有意而為,但結(jié)合《河清令》的推行,北齊后期中央對地方的任免權(quán)力確實得到加強。后主高緯在位后期,政權(quán)已經(jīng)風雨飄搖,在北周和南陳的夾擊下接連失地,最終國滅。東魏、北齊兩朝的地方吏治便是以這樣混亂腐敗的結(jié)局而收場。
五、結(jié)語
東魏、北齊兩朝的官僚治理與國勢有關(guān),而官僚治理體系的優(yōu)劣又反過來影響兩朝整個國家的國運。縱觀東魏、北齊兩代地方吏治的演變可以看出,它的整體發(fā)展趨勢是起初不堪,中期經(jīng)過短暫改良,后期又復(fù)歸糜爛。期間對于吏治的整頓和“士人為縣”終究只是臨時舉措,并沒有落實成制度和常態(tài)化。個別州郡吏治清靖全有賴于地方長官個人的品德和才能,其余守宰聚斂收納之事常有發(fā)生。高氏統(tǒng)治者或熟諳軍事、或縱情享樂,他們的治理依然采用的是儒家的道德力量和法家的術(shù)、勢,并憑借個人的才能進行統(tǒng)治,選任官僚多是出于個人喜好和利益權(quán)衡。
東魏、北齊兩朝沒有注重上下貫通體系的構(gòu)建,少有由縣令而至顯宦者,州郡長官也少有履職縣令的經(jīng)歷。在缺乏晉升路徑的情況下,縣令便不再在意自己的政績,反而利用職權(quán)聚斂財富,因而加劇了地方吏治的腐敗。在不重視外官的大時代背景下,縣令的地位得不到提高,社會精英的流動和著眼重心就很難放在地方吏治上,使得東魏、北齊兩朝地方吏治難以走上正軌,也終究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治理體系。